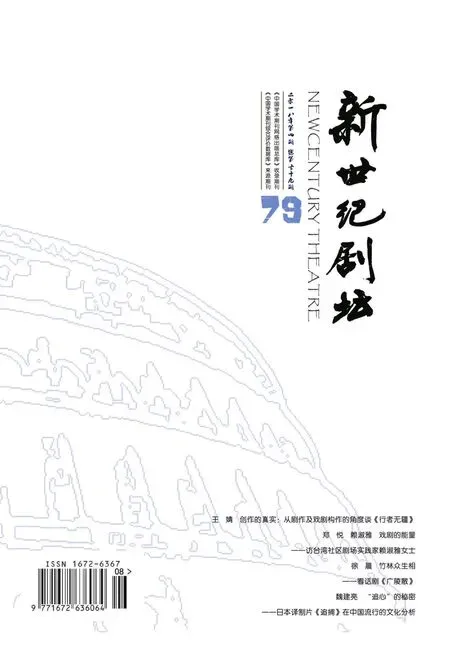诗象入境 行者无疆
——评舞台剧《行者无疆》
李 博
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原创舞台剧《行者无疆》于2018年5月17日在国家话剧院先锋剧场正式公演,这部由中法戏剧创作者联合排演的舞台剧一经上演,便独树一帜,展现了其强大的艺术魅力。作品聚焦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13年的心路历程;以虚实两条线索,一方面借鉴史实讲述张骞在西行路上的种种曲折经历,展现他的家国情怀与民族气节;另一方面通过梦境与想象展露他丰富而神秘的精神世界。《行者无疆》与其说是舞台剧,不如说更像是一部以形体语言探寻张骞精神世界的诗篇。
《行者无疆》是充满诗意之象的佳作,该剧从演员的形体表达到道具灯光设计,从多媒体呈现到琵琶、古筝与电声音乐的融合……让人不自觉地沉迷其中,仿佛跟随张骞的“形体”一同行走了13年的西行之路,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步入诗意之象的境界。
为什么明明是一部舞台剧,却可以读出诗意,品到诗象?因为真正的艺术是“发自内心深处又抵达内心深处”的,只有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浸透在形象化的舞台表达中,戏剧演出才会产生深刻的“意象”。[1]《行者无疆》做到了这一点,同主创者团队的创作理念密不可分。
这部剧的创作和从编剧写剧本到导演排戏的模式不太一样,作为一部主要以形体讲述故事的戏剧,该剧以演员的形体表演为主、台词解说为辅讲述张骞从幼年到两次出使西域的心路历程,结合梦幻的多媒体、山海经中的神兽等奇幻元素,向观众展现创作者心中张骞伟大的功绩和强大的精神世界。该剧的创作首先由戏剧构作王婧提出一个戏剧构思开始,王婧旅法多年,在创作《行者无疆》之前,已有戏剧作品《W效应》《死亡之城·布鲁日》(法国梅斯登剧团演出)《这个孩子》(法国神曲剧团)等,在推进中法戏剧交流上做了很多工作,其旅法经历使得《行者无疆》在创作初期就具备中西戏剧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先天优势。张骞是历史上凿通丝绸之路、推进中西交流的关键人物,而王婧的精神追求与其有着跨越古今的高度契合,在演出宣传册上她说:“选择张骞,是因为他比我想象中的要宽广、丰厚、神秘、动人。史书对他的记载其实只有短短几行,但与他相关的传说、异志却不计其数,一个个读下来,这个两千多年前的人物忽然在我心中有了温度。在家国情怀、民族气节的背后,我看见了一个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我想带着观众走进这个世界。”由此可见,王婧在未创作剧本时已为该剧定下了“诗意”的基调,要在舞台上表现张骞的精神世界。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在中国妇孺皆知,因此,作品用该史实作为一条实线,展现张骞13年间出使西域的种种险境,另一方面,为了“将张骞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人物和他的故事写得生动,有温度,能与现代人的情感和当下的时代命运产生共鸣”[2],她采用“梦境”来展示张骞的精神世界,形成了作品的一条虚线,在舞台呈现中可以看到,张骞出使西域的心理动机和精神诉求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要素。
《行者无疆》以汉武帝登基后欲平匈奴之乱的史实为故事背景,以张骞在黄河边回忆少年时从西行马队领队处得到一卷书卷开篇,展示出其西行的源动力。当汉武帝颁发皇榜,向天下征寻出使西域的人才之时,张骞毅然揭榜,告别老母亲,和甘父、王渊及自己养育的一匹小马一起踏上西行之路,行者就此踏上征途。途中,张骞一行人在给月氏难民送粮时遇到了匈奴人的埋伏并被俘,匈奴可汗为了消磨张骞的意志,将他流放蛮荒放马。一日,马群受惊,万马脱缰而跑,张骞在追赶马群的途中不慎跌落悬崖,一位匈奴女子将他救起,在疗伤时两人渐生情愫,结为夫妻并生下了一个孩子。此时,战事又起,张骞的岳父被征为士兵,留在家里的张骞教匈奴人纺织识字,而后便传来了其岳父战死沙场的消息。月圆月亏,日子一天天过去,但是张骞并没有放下手中的使节,仍然等待着出发的那一天,终于,在为单于做寿的西域魔术师出现时,张骞找到了圆梦的机会,在梦幻与现实的交界间,他与甘父、王渊再次踏上了西去大月氏的路途。路上,王渊不幸在沙暴中丧生,剩下的人因为缺水不得不改道雪山,在翻雪山途中张骞遇到了大夏国国王的亡灵,得知翻越雪山的艰险,张骞内心挣扎一番后决心前行,没想又遭遇了雪暴,一路跟随他的那匹小马也倒在了雪暴之中……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后,张骞终于到了让他魂牵梦萦的大月氏,拜见了大月氏的女王并说明了联合大月氏抗击匈奴的来意,大月氏女王虽惊叹张骞越过雪山来到此地的壮举,但为了维持子民安稳的生活,不愿与匈奴为敌,拒绝了张骞的请求。无奈的张骞和甘父回到了大汉,受到了汉武帝的接见,并带回了大量珍贵的资料。当张骞再次出使西域来到大月氏时,大月氏女王终于同意与大汉联姻,共抗匈奴。至此,一出宏大的西行之路落下了帷幕。
该剧的故事是为展现张骞的精神世界而服务的,《行者无疆》讲述的更像是王婧的一个梦,梦回山海经、梦回大汉、梦回西域,正如她自己所说:“回忆,梦境,潜意识与人物的现实经历融为一体”[3],但是,在舞台上如何表现一个人的梦境状态呢?用台词来表达吗?当然不是,相比于台词,舞台上更能表现梦境的是演员的形体、舞美灯光的设计和音乐的烘托。
以形体戏剧见长的赵淼作为该剧的编剧和导演,在舞台呈现中起到了中心作用。赵淼是三拓旗剧团导演、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教师。代表作有话剧《罗刹国》、音乐剧《你若离开,我便浪迹天涯……》等。在多年的表演实践中,赵淼一直致力于形体戏剧的发展和推广,他受到法国形体大师雅克·勒考克的影响,提倡“诗意的身体”的观点,善于通过演员的形体讲述故事。《行者无疆》“诗意”的构思,先天性与赵淼导演多年来所倡导的形体戏剧有极高的契合度,为该剧“诗象”的表达先行奠定了基础。以演员的形体语言展示梦境,打破了戏剧故事需要连贯的特点,也拓宽了戏剧舞台的表现力,一个人的想象有多丰富,梦境就能多精彩,正如王婧所说:赵淼导演以形体戏剧见长,他的作品视觉性强,充满想象空间,这要求我们的剧本创作也要与舞台构思同步进行,即近些年来欧洲剧场创作奉行的“舞台写作”[4]。形体语言和文学语言共同成为该剧剧本的组成部分,因此,王婧和赵淼共同担任本剧的编剧,而赵淼同时是本剧的导演。
从最终舞台呈现来看,《行者无疆》确实做到了以“诗象”引人入境的效果。全剧充满了各种诗意之象,而这些“象”就蕴含在演员的形体语言当中。一般人如果看到演员表,定会被演员所扮演的“角色”所折服,神兽穷奇、重明鸟、风、沙暴、雪暴、火焰、茅草、海市蜃楼、雪山、祈愿天灯、马队、鹰等都由演员扮演,而且每个演员同时身兼数角,演员用形体语言将一个又一个的“诗意之象”展现在观众眼前。纵观全剧,可以发现这是一个从“人”到“人”的故事,透露出张骞精神世界的光芒,张骞从揭榜西行到与大月氏女王相见,整整13年,他经历了怎样的一段心路历程?他有过动摇、有过疑惑吗?“人”是各种复杂情绪的叠加体,就像导演赵淼所说:“张骞踏上出使西域的征途,五千个日夜七千多公里,总有孤独、彷徨、疑惑、恐惧追随,这部戏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5]那么,该剧是怎样展现张骞的成长和精神世界的呢?
《行者无疆》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以他人视角展现张骞其人。该剧主要表现的是张骞,但有意思的是导演是通过张骞的形体语言而非这一角色的台词来塑造他的。该剧叙事的基本模式是,先由演员用形体语言进行表演,再由和张骞有关联的某个角色用台词对表演的事件加以讲述,并以此为单元叙述故事。在形体表演的过程中,因为没有台词,所以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可能会对某些形体表达似懂非懂,而之后通过台词的解释,观众便可以理解导演想通过形体表达的含义了,在“表演-解释”“再表演-再解释” 不断循环的模式中,观众对演员的形体语言有了认识,从而体会到导演以“诗意的身体”展现“诗象”的用意,最终达到审美愉悦,这正是此叙事模式的巧妙所在。以开场时张骞回忆自己少年时遇到马队并得到书卷的一场戏为例:在一幅落下的星河图之下,扮演张骞的演员手拿书卷慢慢走到舞台的右侧,而舞台中央众多演员以某种特殊的舞步缓缓走动,空灵的琵琶弹拨声营造出时空跨越之感,此时,两个黑衣演员手持一个半人高的人偶缓缓上台,穿梭在众演员间,众演员突然定格,张骞将手中的书卷交给了人偶,众演员继续走动,人群中突然跑出一个女演员,抱起了人偶,此刻,众演员下场,背景显示出大树的图案,三个手持红旗的演员在抱着人偶的女演员的左、后、右方站立,将旗下搭,划分出一个舞台上的临时空间,此时,女演员说道:“前日,带子文(张骞的字)进城赶集,遇到了西征的马队,这孩子从小就对外面的世界特别好奇,为了听领队给他讲沿途的故事,跟着马队走出去了好几里,天黑回来时,手上便多了一卷书,自从那天起,子文的心里,便有了另一个世界。”至此,这一叙事单元结束,从中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地方,由于刚开场,观众对场上的演员代表的人物不完全了解,只能通过装扮做出大致判断,所以在观看表演时是带有疑问的,人偶代表谁?张骞为什么给他书卷?舞台上拿着旗子绕着圈的这些演员在做什么?这些疑问通过台词的解释便让观众豁然开朗了,原来,人偶是少年时的张骞,抱着人偶的人是张母,在舞台中间绕圈的演员是“马队”,而给子文“书卷”的领队,恰恰是在回忆的张骞,再次回味刚才的表演,会感到导演以此表达张骞精神世界的手段令人称奇,这不正是通过形体表达“诗象”吗?观众通过台词知道了“西行途中的奇闻异事”和“西行”对于少年张骞的影响,为他今后出使西域找到了心理依据和精神寄托,再者,用扮演成年张骞的演员给少年张骞亲自送去书卷,而不是由另外一个演员送,仿佛凸显了某种必然性,少年张骞被成年张骞给他的书卷所影响而对西域产生了向往,这种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场景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这难道不正是表现“梦境”的一种绝佳方式吗?该剧就是以这样一种叙事模式推进故事的,剧中的其他重要人物,如甘父、张妻、匈奴单于、大月氏女王等人也是以各自的视角,为观众展示出张骞和他的精神世界。值得一提的是甘父和小马两个角色,匈奴人甘父是张骞西行的向导,也是唯一一位和他回到大汉的人,所以,他在本剧中承担着类似说书人的功能,在舞台上多次讲述故事发生的背景等因素,推动剧情发展;而另一个角色小马则以动物的视角对张骞的精神世界加以解读,演员采用了一系列具有现代舞特质的动作来表现马的形态,为该剧增添了不少亮点。张骞完全没有台词的设定也颇有意味,一方面,史书中对张骞的记载很少,比如史记中说“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以寥寥数十字讲了他的伟大功绩和名望,张骞自己却没有留下话语和文字,在剧中也便不需发声了,另一方面,能够留名的历史人物往往不用自己多言,历史的评判本就更多地建立在他人的语言之中,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不说话的张骞更加具有“诗意”,在众演员说台词的时候他不说,就像是中国画中的留白,将张骞的形象升华了,提升到“诗意之象”的境界。
《行》剧另一特点是无缝的虚实衔接。实的是张骞在西行途中遇到的种种障碍,而虚的是在遇到困难时其复杂的精神世界,导演在展示张骞遇到的种种险境时通过多媒体背景切入、音乐引导和灯光切换的办法实现实与虚的转接,并在其中引入山海经中出现的神兽来表达不同的含义。张骞在西行途中不止一次遇到挫折,而其中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他遇到比较巨大的挫折有被匈奴奴役、群马脱缰滚下山崖、遭遇沙暴、翻越雪山等。在遇到挫折时,场上的演出形式较为丰富,基本上由多人在舞台上扮演不同的形象,导演将多媒体、音乐、灯光和演员的形体相结合表现出各种大场面,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自然灾害的展现。从张骞前往大月氏途经沙漠时突遇沙暴的一场戏就可以看出导演对舞台把握的功力,途中,张骞和甘父、王渊、小马驹一起在途中前行,突然音乐急促起来,背景显示出沙尘弥漫的影像,七八个头围纱巾的演员从舞台一侧急速上台,张骞等一行人做出抵抗大风的姿势,这时,可以知道这七八个围头纱的演员表演的是夹杂着黄沙的“风”,而后,音乐声更加急促,“风”从舞台左侧刮向右侧,张骞等人在舞台上被狂风吹得分离开来,他们手脚并用挣扎的形体动作表现在沙暴中的抗争,接着,众演员和张骞等人围成一个圆圈,以此表示他们被黄沙掩埋,这时头围纱巾的演员自然而然地转化为了“黄沙”,此时,王渊做出了挣扎状,而表演“黄沙”的两个演员一把将其推倒在地,王渊几次想要跑出去,但都被“黄沙”所阻止,终于他失去了力气,被“黄沙”肆意摆弄,王渊趴在地上,而七八个扮演“黄沙”的演员在他身上扑来扑去,突然,全场安静下来,扮演“黄沙”的演员以王渊为中心脚朝里头朝外围成一圈趴在地上不动,这预示沙暴终于过去,而王渊在沙暴之中失去了生命。张骞、甘父和小马趴在地上痛苦万分,接着几个演员拿着象征洞窟的道具从舞台走过,背景多媒体投射出红色都城的影像,他们好像看到了大月氏的都城,倒地的张骞挣扎地前行,没想到他看到的只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而已,此时的张骞内心沮丧,充满了恐惧,而舞台音乐变得诡异,只留下舞台中间的定点灯亮着,张骞仿佛听到了不知哪里的窃窃私语,周围很多“黑影”围住他,他想突围但是却被黑影压在身下,他惶恐地喘着粗气,挣扎开来,出现在他眼前的是甘父与小马,接着,甘父说出了众人面临着缺水而只能改道翻雪山的险况。至此,张骞遭遇沙暴一场戏结束,其中从受到沙暴袭击到进入张骞内心惶恐的切换非常自然,值得玩味。之后翻越雪山的一场戏也与沙暴类似,由演员利用白色三角旗和白色长布等道具扮演雪山与雪,张骞等人用躺在地上蜷起四肢并摆动四肢的形体表现翻山的艰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用形体表达诗意的方面,扮演张骞的青年演员吴俊达,扮演张母、张妻、月氏女王等众多角色的汪玥,扮演匈奴人甘父的何宏宇,扮演张骞小马的田鸽,扮演匈奴单于的吴迪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在表现张骞精神世界的时候,导演还引入了古代神话的神兽形象。该剧出现了两个比较有特点的神兽,一是穷奇,二是重明鸟。穷奇这一神兽有正反两种不同的形象,有的书中记载其是吃人的怪物,如《山海经·西山经》里说“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蝟毛,名曰穷奇,音如獆狗,是食人。”[6]而有的书中又说它能驱赶蛊毒之物,这是一种集矛盾为一身的神兽。在该剧中,穷奇是以一个巨大的面具形象展现的,仿佛只有一个头一般,它一共出现了三次,每一次出现都伴随着红光,而且是在张骞精神恍惚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因此,可以将穷奇看作是展示张骞矛盾的精神状态之存在。而重明鸟是一种眼中有两个瞳孔的神鸟,可以驱除邪恶,是一种吉祥的象征,可以看作是张骞精神世界中纯洁所在。
《行者无疆》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诗象”就是背景中显示的从天而落的星河,这一图像在开场时就出现了,到结尾时再次出现,形成首尾呼应。这一星河其实是张骞展现其历史功绩和对西域向往的另一个“诗象”,赵淼导演认为,“从西汉开始人们都以为张骞西行是为了寻找黄河的源头,传说他发现银河落入大地变为黄河之水,古代人都觉得张骞对他们的生活特别重要。”[7]历史上对于张骞发现黄河源头是银河的传说被导演化为一个重要的舞台意象来展现,这表现了黄河这一母亲河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而传说中张骞恰恰是发现黄河源头的人,其功绩不言而喻;追流溯源不也可以看作张骞西行精神的内涵吗?
剧中对“偶”的运用同样引人注目,剧中少年张骞和张骞在匈奴所生的孩子均由人偶表现。使用人偶的好处是可以更丰富地表现人物儿时的形象,并且丰富了舞台表现力。这并不是赵淼第一次在舞台上使用人偶,他接受采访时曾说:通过演员的操作,把一个普通的娃娃操作得活灵活现。而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我们的演员并不避讳观众,而是当众操作娃娃,观众在观看中认可了这种假定性,使得这个场面又充满了更多的情趣。[8]在开场控制少年张骞人偶的便是两个演员,观众可以自觉忽略他们的存在,而更多地聚焦在故事本身。剧中老鹰的表现也是如此,导演用三个演员控制一只想要抢夺张骞使节的老鹰,由一人控制双翅,一人控制身体,一人控制双爪,这种分体控制的方式增强了鹰和人搏斗的复杂性,增加了戏剧张力。
《行者无疆》削减了语言的干扰,观众可以通过演员的形体动作体会张骞的精神世界,最终呈现的戏剧不是导演想表达什么,而是观众看到、感受到了什么,有意思的是,上文的某些分析是笔者作为一个观众从舞台呈现出的“诗象”中解读出来的,与创作者排戏时的构思或许有所出入,不过,作为观众,通过“诗象”的解读,来揣摩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以达到共鸣岂不是观剧的意义所在吗?
最后,值得一说的是《行者无疆》的舞美设计和音乐设计。来自法国的艾瑞克·苏耶作为舞美艺术指导和舞美设计曹璐、灯光设计温晓楠将舞台设计得简洁而不失变化;来自法国的视频艺术家马修·桑什将来自敦煌的诸多艺术形象幻化为舞台上可视化的效果,对于张骞西行路途的展现和梦境的营造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作曲,鼓手和声电音乐人的于埃尔·巴特雷米和现场乐器演奏、音乐引入者潘瑜,以中西结合的方式带给观众充满想象的听觉感受。
《行者无疆》是一部值得让人回味的作品。在感叹其独特创作理念和诗意化表达的时候,也看到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经过了前半部分拟人化的风、雪、沙、火,以及神兽神鸟的感官冲击后,后半部分的处理显得略为平淡,整场戏在已有历史故事的背景下没有形成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或者豁然开朗的高潮,而且从大月氏女王第一次拒绝张骞的请求到顺利结盟之间略显仓促,这可能和历史故事本身的特点有关,不过用王婧自己的话说,这本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剧,所以可以不完全拘泥于史实,而是更加大胆地表达戏剧构作或者导演对于张骞的想法。另外,背景多媒体展示的大量抽象图像和舞台上演员节奏偏快的肢体动作切换,使得大量的信息短时间内刺激着观众的视听神经,有可能造成信息接受的困难。比如在体味背景多媒体中变化的圆圈是什么含义的时候,可能会忽略场上演员的表演,造成观看的不连贯,在背景屏幕有关键意象(如落下的星河、转动的圆圈等)展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减慢肢体动作的变化频率以留给观众更多的思考与回味的时间,值得考虑。
总的来说,《行者无疆》可以看作是形体戏剧和话剧的结合,该剧做到了以“诗意的身体”进行“诗意之象”的表达,并很好地体现出王晓鹰导演所说的有关从“诗”到“诗意”,从“诗性戏剧”到“诗化意象”的观点,这是在观念与创作之间、剧作文本与舞台呈现之间本质性的贯穿,而所有的形式技巧或者说“舞台假定性”处理手段,都只是由“诗性戏剧”通向“诗化意象”的艺术途经,[9]并以此达到“中国意象的现代表达”。不仅如此,该剧还把张骞的精神赋予了更深的含义,这种西行的精神可以看作丝路精神的体现,那就是相互沟通,相互交流,相互包容,而该剧创作上的中西合璧与其想要表达的内涵不谋而合。
诗象入境,行者无疆,走在戏剧创作路上的王婧、赵淼等创作者的戏剧之路也没有疆界,相信通过《行者无疆》的演出,可以带领更多中国观众踏上感受“诗意的身体”与“诗意之象”魅力的行者之路。
注释:
[1]王晓鹰.话剧的“中国意象现代表达”[J].戏剧文学,2018(5):7
[2]不局于疆域,不绝于时月,千年丝路.《行者无疆》,微信公号幕间戏剧,2018-05-07
[3]不局于疆域,不绝于时月,千年丝路.《行者无疆》,微信公号幕间戏剧,2018-05-07
[4]不局于疆域,不绝于时月,千年丝路.《行者无疆》,微信公号幕间戏剧,2018-05-07
[5]不局于疆域,不绝于时月,千年丝路.《行者无疆》,微信公号幕间戏剧,2018-05-07
[6]李慕古注译.山海经[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56
[7]不局于疆域,不绝于时月,千年丝路,《行者无疆》,微信公号幕间戏剧,2018-05-07
[8]赵淼、许健.诗意的身体:向雅克·勒考克致敬[J].艺术评论,2009(4):90
[9]王晓鹰.话剧的“中国意象现代表达”[J].戏剧文学,201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