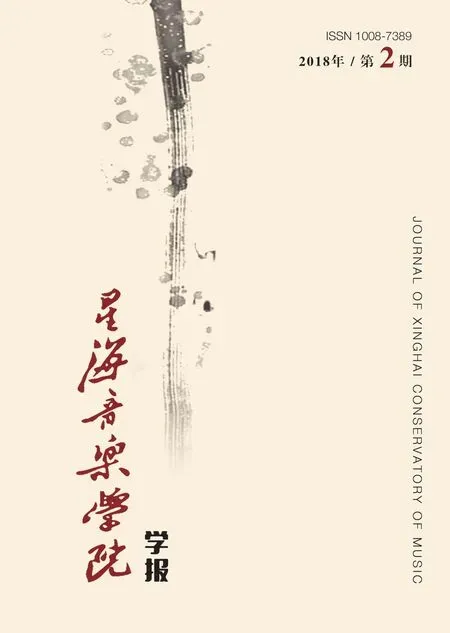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城市化进程中的粤曲与歌坛
潘妍娜
前 言
“歌坛”这一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广式茶楼中的粤曲表演空间,在粤曲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这段时期的粤曲歌坛中,不仅诞生了流传至今的经典名曲与流芳后世的名伶,更重要的是完成了粤曲音乐形态的转变与成熟。独立的曲目、唱腔、表演风格等与早期的粤剧清唱不同,粤曲得以脱离粤剧的附庸而成长为一种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学曲艺艺术,其音乐语言也完成了从“官话”到“方言”的外来“梆黄”本土化历程,这段时期因此而成为粤曲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历史地看,20世纪初广州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带动了城市新兴的茶楼歌坛的兴起,歌坛、粤曲作为当时广州城市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其音乐形态的成熟与广州城市进程之间无疑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而值得思考的是,歌坛作为一种空间性和社会性的存在,其中的文化主体是怎样实践着历史、社会的影响并作用于音乐之上的?探讨这个问题,既是我们理解传统音乐现代性生发与地方乐种形成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也是我们探索音乐人类学“音乐与文化”关系这一经典命题的理论实践。本文通过对粤曲变迁的这段历史进行梳理,希望以一种立体的视角讨论历史、社会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在分析粤曲音乐形态的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粤曲歌坛与当时广州城市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一、从农村的“八音班”到 城市茶楼的“歌坛”
粤曲的前身通常认为是原本为珠江三角洲农村中演出的“八音班”*八音班一般为八名成员八种乐器(故此名“八音班”),后来也有十至十二人的,称为“大八音”。所演唱的“粤剧”清唱。当时的粤剧实际上演的大多是“外江班”带来的“外江戏”(包括西秦戏、徽剧、汉剧、昆剧等),所演剧目、唱腔音乐、表演程式以及舞台语言都与外江戏大致相同。因此,早期的粤剧所唱的音乐是以桂林官话演唱的“梆子”“二黄”为主的外地声腔,“八音班”基本沿用了这种音乐,演出形式为不上妆的清唱,边奏乐器边唱,唱曲的同时也是乐师,一人一角。“每位音乐师担任唱一种角色的唱词,通常是玩二胡的唱旦,拨琵琶的唱生,玩三弦的唱净,玩椰胡的唱末,掌板的唱丑,其他行当则分由各乐师担任。”*鲁金:《粤曲歌坛话沧桑》,香港:三联书店,1994年,第3页。结合演唱的环境节庆、庙会、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来看,“八音班”演出带有很强的民俗性和仪式性。清朝同治时期开始在城市中出现了以唱“粤曲”为业的失明女性艺人“师娘”(也名瞽姬),师娘最初主要是沿街卖唱或到“玩家”(业余音乐爱好者)所开设的“灯笼局”中演唱,演唱的曲目是源于粤剧“江湖十八本”的“八大曲本”。*即《百里奚会妻》《黛玉葬花》《辨才积妖》《弃楚归汉》《鲁智深出家》《附荐何文秀》《雪中贤》《六郎罪子》八部从粤剧传统剧目中的所谓“江湖十八本”改编过来的曲目。直到19世纪末大量广州城市茶楼的兴起为粤曲提供新的演出场所,这一艺术形式在20世纪初的广州与当时流行的茶楼文化相结合,在茶楼中开设专门的粤曲演出场所,被称为“歌坛”。
晚清以降……(广州)城市手工业及现代消费型工业的发展,使生活方式逐步开放、多元而富于更快的节奏,传统的消费观念受到极大的冲击,工人、士绅、企业家、银行家、买办,工商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使新都市人的消费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酒楼、茶馆、妓院、戏院、烟馆和赌馆等场所在“消费革命”中不断发展。*蒋建国:《广州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据资料显示,这时期广州新建了大量的茶楼,“1921年广州市政厅公布的茶楼为380家,到了1928年,全市茶楼为446家”*1922年广州市政厅总务科编辑股编:《广州市市政概要》“广州市公安局警察区域店铺类别表”,1929年广州市市政厅印行:《新年特刊》“广州市商业分类表”。转引自张寿起:《近百年来广州茶座风情的变化》,《农业考古》1993年第2期。。与旧式茶居简陋的环境不同,这些新建茶楼多为三层小楼,“(茶楼)地方通爽,空气清新,座位舒适,水滚(沸)茶靓(好),食物精美”*陈基等主编:《广州文史资料第41辑“食在广州史话”》,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页。。茶楼在这个时期成为新兴行业为歌坛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茶楼林立形成了行业间的商业竞争,为招揽生意,这才开始有茶楼开辟歌坛请当时粤曲的从业者“师娘”(瞽姬)驻唱。大约在1917—1918年间,位于广州十五甫的“初一楼”是第一家开始聘请“师娘”演出的茶楼。*黎田、谢伟国:《粤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最初歌坛的形态“通常是在茶楼大厅一侧用木板架成高台,上置一方茶几,茶几两旁各置一椅,几上摆一副花瓶、两杯茶。逐日轮流邀约两位失明女艺人,分坐几旁。台上是伴奏乐手,面对唱者”*黎田、谢伟国:《粤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页。。与戏班繁复的表演、化妆、多角色制带来的高成本相比,歌坛中一人多角的粤曲清唱的形式成本较低,虽茶价增加,却极受欢迎,很快众多茶楼纷纷效仿开辟歌坛。二三十年代成为了歌坛的全盛期,光是广州市内就有30家以上的茶楼开辟了歌坛。据谢伟国、苏文炳《红尘往事》一书记载,当时广州的歌坛分布基本如下:文明路的“咏觞”,桨栏路的“添男”,西堤二马路的“庆南”,带河路的“顺昌”,小市街的“茗珍”,太平南的“大元”,宝华路的“初一楼(顺记冰室)”,靖远路的“新九如”,大基头的“建南”(二、三楼皆是)、“成珠”、“三如”,一德路的“一苑茶室”“源源”,永汉路的“南如”“涎香”“仙湖”“宜珠”,西门口的“祥珍”,光复南路的“太如”,惠爱路的“云来阁”“利南”“惠如”,小东门的“东如”,东堤的“襟江”“澄江”“茶校”,长堤的“大三元”“一景”“怡香”,清平路蓑衣街的“正南”,十八甫路的“玉坡(河傍街)”“嘉禾”“富隆”,珠玑路的“多如”;*谢伟国、苏文炳:《红尘往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42页。有《竹枝词》谓:“米珠薪桂了无惊,装饰奢华饮食精。绝似歌舞升平日,茶楼处处管弦声”,*雷梦水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009页。描绘的正是当时茶楼粤曲歌坛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
二、商业化运作下的歌坛与女伶
(一)新兴的粤曲表演主体:女伶
20世纪20年代左右,随着歌坛的发展和茶楼商业竞争的需要,为适应茶客需求,明眼“女伶”逐渐代替了盲眼的“师娘”。随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女伶的队伍迅速发展,大批女性艺人涌入此行业。据资料记载,“1927年至1936年间,为广东曲艺的全盛时期,(女伶)人数便增到300多人”*伍苏、黄玉琼、罗志伟、黄晓华口述,黄德琛执笔:《广州“女伶”补遗》,载《广州文史存稿选编》(第6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长住广州市内的约有一二百人。*陈卓萤:《试探广东曲艺源流》,载《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8页。
女伶最初的时候是“陈塘的雏妓,即所谓的‘琵琶仔’,她们为了出局侑酒,学会几段散折粤曲,转业为‘女伶’后,标榜卖艺不卖身,借以脱离为娼之苦”*佟绍弼、杨绍权:《旧社会广州女伶血泪史》,载《广东文史资料》(第34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1页。,但是很快就不尽如此。由于歌坛的繁荣,很多戏班的失意演员、贫家女儿都加入到这个行业,并出现了专门培养(收养)女伶的堂口与教弹琴唱曲的职业教师,当时广州著名的教学唱工的乐师有莫志(当年住广州西关梯云路厚载新街九号)、罗松以及著名女伶小明星的师傅徐桂福。他们皆为乐手出身,既懂音乐,又懂唱功,是20世纪20年代初广州最早出来教人唱曲的师父。教曲师傅同时还充当女伶的“经纪人”的角色,行内称为“包家”,按雇主要求的档次、规模而商定的价钱介绍女伶赴演,从中赚取差价。专业化的训练不但使女伶表演、唱腔、唱法受到严格的培训,同时也使得这一行业向职业化发展,为粤曲在近代得以稳定传承提供了基础。
(二)“轮唱”制度与“捧伶之风”
女伶数量的日渐壮大导致这一行业竞争激烈,为了平衡各茶楼间歌坛的竞争,减少茶楼支出,并满足茶客猎奇的心理,有茶楼老板成立歌坛行会“唱书团”。女伶的演出均由唱书团安排日期、工价轮流安排演唱,各女伶轮流于各茶楼中演唱,而形成“轮唱”制度。例如当时的茶楼九如、大三元、怡香、建南、一园、多如、永觞、玉波这八家的上座率最高,有八大歌坛之称。为避免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它们联合成为一个系统组织,延聘当时的红伶,根据女伶的“声、色、艺、年华”和捧角者人数的多寡来编排“轮值表”,安排日期、场次,轮流演唱。轮唱制度促进了歌坛的优胜劣汰,对“女伶”的要求日渐严格,为歌坛注入新的活力,同时也促使“捧伶之风”盛行。当时歌坛的女伶都有一批为自己捧场的曲迷,称为“舅少团”。“舅少团”为了捧自己喜欢的女伶通常不惜重金,例如20世纪30年代,红伶张月儿、小明星的曲迷就请永汉路拱北楼的老板开设一家只唱夜场不唱日场的歌坛,专请张月儿、小明星各唱十五天,一直持续有半年之久,难分伯仲,成为粤曲史上有名的“星月争辉”*黎田、谢伟国:《粤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页。。捧伶之风无疑促进了茶楼生意的火爆,当时的粤曲歌坛将近舞台的几张台总是早早为舅少团所定,风雨不改,每晚必随歌伶进场。因为女伶的号召力,著名茶楼的茶价可抬高数倍。
歌坛制度化、职业化、经济化的发展形成了以女伶为中心包括撰曲家(词)、乐师(曲)、包家(经纪人)、受众的粤曲歌坛产业链,围绕粤曲的表演实践展开联系,构成这一时期粤曲的文化生态。激烈的商业竞争使得歌坛涌现出一批技艺高超、才华卓绝的红伶,黎田所著《粤曲》一书中记载了在1918—1938年间,由曲迷约定俗成所作出过两次名伶排序。20世纪20年代中的初次排序是:张月儿被称为“一明星”,另被称为“四大领袖”的则是郭湘文为“平喉领袖”、熊飞影为“大喉领袖”、张琼仙为“子喉领袖”、燕燕为“生喉领袖”,而小明星、徐柳仙和张蕙芳则被称为“三骑士”。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名伶排序有所改变,熊飞影与张琼仙依然分别保持“大喉领袖”和“子喉领袖”,小明星上升为“平喉领袖”,另排出“四大平喉”(也称平喉四杰),小明星兼为“四大平喉”的首位,其下依次为张月儿、徐柳仙、张蕙芳。*黎田、谢伟国:《粤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页。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州歌坛呈现出争艳斗技的局面。
三、歌坛时期粤曲音乐变革
歌坛商业化的发展与繁荣极大地刺激了对于艺术发展的需求,早先那种形态简单,仅仅唱“梆黄”的音乐早已不能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唱片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歌坛新曲目的传播。女伶行业的繁荣与商业化竞争催生了个人表演的风格化与流派化,这个时期的粤曲在音乐形态与艺术风格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一)以“文人曲”为代表的粤曲新曲目与传播
最初师娘在茶楼唱的曲目是来自于粤剧的《八大曲本》,音乐是以桂林官话演唱的“梆黄”。这些“八大曲本”往往需时三至五个钟头,且曲目固定、音乐单调、缺乏新意,时间长了必然会使茶客厌倦。进入到女伶时期后,女伶是一个新人辈出、优胜劣汰的行业,为了在歌坛商业化的竞争中获胜,女伶们纷纷竞唱新曲目,从而引导了歌坛撰写新曲的风气。歌坛的繁荣吸引大批文人投入到撰曲的行列,“曲圣”王心帆、“曲王”吴一啸和“曲帝”胡文森等都是文学修养极高的撰曲家,他们喜欢以诗词入曲,熟知粤曲音律、曲牌,大大提升了粤曲新作的文学性,使得粤曲的唱词向精致化发展,形成粤曲独有的“文人曲”*当时的新曲有“文人曲、谐趣曲和时事曲”几种类型,以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要,然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由文人参与创作的“文人曲”。。而同时期唱片业与电台开始兴起,作为歌坛的一种延伸,其将歌坛女伶的新曲录成唱片在电台播放,或直接为电台播放创作新曲的方式推动了歌坛新曲的流行与歌坛的繁荣。当时著名的唱片公司有碧架、胜利、鹤鸣、远东、高亭、百代、歌林等,灌制的粤曲和广东音乐唱片超过千张。在唱片的传播之下,这些粤曲新曲目很快成为了民众追捧的名曲。大量新曲的出现及传播改变了粤曲之前曲目单一的局面,促生了一批后世流芳的粤曲经典曲目,如小明星的《风流梦》《秋坟》《痴云》《多情燕子归》,徐柳仙的《再折长亭柳》《梦觉红楼》等。
(二)粤曲唱腔的革新与定型
早期粤剧清唱时期的粤曲“八大曲本”中,生、旦、末、净的唱腔全有,但唱腔除了梆子(实是西皮)就是二黄,没有南音、粤讴、木鱼等本土唱腔,极少使用曲牌,更没有好听的各种“小曲”,总之远远没有今天的粤曲音乐丰富。新曲目的出现,市场的繁荣,电影业、唱片业的发展,以及观众审美的需要都在促使粤曲唱腔更为丰富化,粤曲新腔的产生也是必然的。这种变革首先体现在对于早先粤曲声腔中以梆子和二黄为主体的单一板式结构的突破。早先的粤曲音乐结构中梆子与二黄在同一首曲子中是不能够混用的,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两腔系的板式互相连接编撰的曲目。而随着这一时期戏曲语言从官话向方言转变,撰曲家们开始在梆黄的音乐体系中吸收南音、龙舟等地方曲艺,此外还吸收大量的民间小曲,如《彩云追月》《妆台秋思》《茉莉花》等;甚至西方电影音乐、流行音乐都开始出现到新写曲目中,创立了很多粤曲独有的唱腔。如粤乐音乐家梁以忠把粤讴的韵味融入粤曲,首创“二黄解心腔”*粤讴又名解心腔,清代道光年间文人招子庸所著《粤讴》一书第一首曲名为《解心事》。,其所创作的《明日又天涯》令众多名伶争相传唱。此外,将民间小调、广东音乐进行填词演唱也是一种创立新腔的办法,据资料记载,最早把“广东音乐”通过填词引进粤剧唱腔的,是粤曲演唱家和革新家吕文成。他在《宝钗悼玉》一曲里首次设计了由[梆子慢板]转接“广东谱子”[雨打芭蕉]的中段下接[西皮]的连接手法,直至今天的粤剧舞台和曲艺歌坛,仍为撰曲者所乐用。*赖伯疆、黄镜明:《粤剧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103页。
(三)个人唱腔流派的形成
在当时激烈的歌坛竞争之下,拥有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成为了女伶脱颖而出的必备条件。早期的歌坛艺人的唱法都是仿照粤剧演员的唱法,但实际上原来粤剧的唱法采用了戏棚官话演唱,其发音并不适合广州话九声的咬字正音。尤其在只唱不演的粤曲歌坛,女伶们对于唱功尤为注意,严格要求是否正宗,务必食板咬线。“女伶与‘戏子’有所不同,坐在歌坛枯唱,毫不动作,又无表情,如果腔口不正,除非别具用心的听众不加挑剔外,一般听曲者就会弃之如敝屣。”*佟绍弼、杨绍权:《旧社会广州女伶血泪史》,载《广东文史资料》(第34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1页。20世纪初期,宣扬革命的志士班首次用广州方言唱粤剧,随后粤剧小生金山炳、小武朱次伯随之在粤剧舞台上对这种唱法进行了实践。很快,降低乐器定弦、采用真声发声的平喉唱法在粤曲歌坛也传播开来,并逐渐发展出与粤剧唱法不同的,以真声发声的女性平喉唱法为代表的粤曲“女伶腔”。
另一方面,文人曲曲词精致,对女伶的唱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让音乐固定的板腔贴合曲词,符合平仄押韵,女伶们在撰曲家与乐师的协助下不断钻研唱腔,除严格准确掌握好音准、音色、音量、节奏、格律外,还必须巧妙地通过适量增加细微装饰音和滑音的手法进行润腔。因此,歌坛中的女伶并不仅仅是表演者,她们需要在对曲词格律、板腔音乐都非常熟悉的情况下,对作品进行具有个人风格的二度创作,由此形成了粤曲具有个人特色的风格流派。当时歌坛薪酬最高的几位女伶小明星、徐柳仙、张月儿、张惠芳、张琼仙、熊飞影等,都是以自己独有的唱腔风格独步歌坛,其中尤以平喉唱法中小明星的“星腔”与徐柳仙的“仙腔”为代表,这些粤曲名伶个人的表演风格经由茶楼歌坛与唱片的传播而成为流传至今的粤曲传统声腔流派。
四、歌坛中粤曲革新 实践的文化解读
经历了歌坛时期一系列改革后的粤曲已经与最初的形态大为不同。新文本的出现、音乐形态的变迁、流派风格的成熟无疑昭示着现代意义上“粤曲”的形成与定型。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的粤曲改革很多时候是紧跟粤剧进行的,但是其改革的深入程度却更甚粤剧。尤其是“改官话为白话、改假声为平喉”的革新,虽始于粤剧舞台,但是歌坛的步伐要比粤班来得猛捷。从音乐社会学的视角看,音乐文化的变迁是特定社会关系变革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结合歌坛这一特殊的表演空间,粤曲在这一时期的革新也就有着更为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可以解读。
(一)歌坛与城市娱乐生活的发展
不同于旧式茶居的新式茶楼的出现,是广州从一个传统型城市发展为一个近代工商业城市的重要标志,而歌坛的出现则是近代粤曲由农村的民间音乐向市民音乐转化的标志,可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茶楼歌坛的兴起见证了早期广州城市娱乐生活的发展。19世纪末,随着广州开放为通商口岸,商贸活动促进了广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陈济棠在广东建立半独立的军事政权后,广州处于秩序相对稳定的和平建设时期,广州的社会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清末之际,一个集贸易、工业、农业为一体的经济体系已经显示出广州在地区市场的强大功能。”*蒋建国:《广州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页。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进出口货物种类的增多,以及城市周边地区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传统商业开始向近代转型。近代工业的兴起使广州城市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从一个传统封建性的区域行政中心与旧式商业城市,初步转变为资本主义工商型的口岸城市。*赵晨:《晚清民国时期广州城市近代化略论》,《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消费的增加,大量的资金、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市民娱乐消费需求日渐增长。
与此同时,商贸往来和工人、士绅、企业家、银行家、买办,工商业主等新兴阶层的出现也需要新的社交平台。但据陈卓莹在《试探广州曲艺源流》一文中记载,辛亥革命后的广州城上演粤剧的戏院为数极少。相对于城市中粤剧演出的贫乏,珠三角农村中的演出却十分火热,有些大公司把全年的演期都尽早订好了,根本抽不出空到广州城内的戏院上演。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在广州经商与就业的人常返乡下看戏。*可以看到很多歌坛的平喉新曲都是以男性的“我”为主体表述。可见当时广州观戏场所的缺乏,这远远不能满足活跃的经济下人们日渐增长的娱乐需求与社交需求,茶楼歌坛的出现无疑是应运而生。虽然与粤剧大舞台上的戏剧扮演相比,粤曲的表演形式较为单一,但是歌坛女伶们精湛的唱功和歌坛文人文雅的曲词都是粤剧表演所不具有的。另一方面,茶楼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各行业互通信息之地,这使得歌坛中的音乐表演与创作,与普通大众的饮茶需要及商贸往来融为一体,独具生活气息——歌坛听曲不仅是一种音乐观赏行为,还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休闲方式,“夜晚饮一顿茶,听瞽姬,看女伶”描绘的正是当时普通城市市民的音乐生活。
(二)歌坛与新兴社会阶层
有钱有闲且文化层次较高的新兴社会阶层不仅是当时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推动力量,同时也是茶楼歌坛的主要消费群体。这一群体成为支撑粤曲在近代发展的经济力量与文化导向,从经济与审美上深刻影响了歌坛的运行及粤曲的创作。“当年曲坛的听众,大部分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士,如官吏、富商、高级职员、社会贤达及文化界人士,还有少量出身富裕家庭的大学生。”*黎田:《粤曲名伶小明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页。他们不仅欣赏歌伶的声腔,还要欣赏唱词的文采;除了以雄厚的财力不惜一掷千金捧自己喜爱的女伶,还会亲自为自己所喜爱的女伶撰曲。*如小明星的曲迷中不少就为她写过曲,其中有几位是中山大学的学生所撰,如莱斯的《恋痕》、薇郎的《孔雀东南飞》等。歌坛文人曲的兴盛以及粤曲音乐唱腔的变革正映照着这一特定社会群体的审美取向与文化诉求。以本土曲艺粤讴入粤曲梆黄体系来说,粤讴向来为本土文人与大众所喜爱的一种文学曲艺体裁,清末民初以来更是成为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面向民众的启蒙武器。这种方言曲艺易唱易懂,不足之处是音乐较为平直,缺少变化。梁以忠独创的“二黄解心腔”,把粤讴中的腔口带入梆黄,融合后的唱腔既有文采,音乐又更加动听,所撰曲目深受听众欢迎并很快成为很多撰曲家常用的写法,这无疑满足了新兴社会阶层对于粤曲文采与音乐的诉求。
(三)歌坛、平喉唱法与近代广东地方文化
平喉唱法的盛行是歌坛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独特现象,目前来看很少有研究关注到这一问题。历史的看,平喉唱法的出现与清末以来粤语方言的推广有着根本上的关系,可以说是近代广东知识分子地方文化建构理念的体现。程美宝认为:“在清末至民国的过渡期间,包括粤语在内的方言成为了维新革命的标志,革命分子也借靠它们去表达自己正在建造的新的国家观念。”*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63页。粤曲与粤剧中“改官话为白话、改假声为平喉”的变革,正是这种观念在戏曲领域的表达。从这个层面看,从平喉唱法改革而衍生出音乐形态上的降低乐器定弦,从梆黄分流到梆黄合流,粤曲音乐的变迁根本上是服务于这场“方言文化革命”的。茶楼中歌坛的音乐表演与创作,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与商贸往来融为一体,这使得歌坛具有了戏院、剧院中大舞台演出所不同的社会性:其不但是一个可以容纳多种社会需求的音乐表演空间,还是一个城市文化传播的窗口。因此,歌坛受众群体的多元性、歌坛受众面之广、影响度之深是远胜于当时的大舞台粤剧的。在这个意义上,歌坛为粤曲平喉唱法的推广提供了比大舞台粤剧表演更为快速与直接的传播,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歌坛中代表性的女伶唱腔主要以平喉为主,而文人尤其喜爱为平喉女伶撰曲。
市民娱乐需求、新兴社会阶层的审美情趣表达以及知识分子文化建构需要三方面因素,集中体现于以王心帆为代表的这类文人撰曲家(其本身也是歌坛的受众)的新曲创作与女伶们的创腔中。对于王心帆所代表的这类撰曲家来说,他们既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同时也深受辛亥革命革新思想的影响,在他们身上同时具有旧式文人与新式知识分子的影子。*王心帆在青年时代深受辛亥革命思潮的影响,与一批具有民族民主主义进步思想的文化人一道,撰写了大量宣传维新改良思想的粤讴,在省港各大报刊发表。粤曲于他们而言,并不仅仅是音乐或诗词,而是一种可以容纳他们变革社会与文化的载体:在来自中原的“梆黄”体系中加入粤讴、木鱼、南音、龙舟等本土曲艺音乐,让粤曲音乐体系更为丰富,更能够容纳他们深厚而丰富的文学修养的同时也实践他们“地方文化”建构的理念。而对于女伶来说,虽然她们是歌坛中音乐表演主体,但值得注意的是她们的表演、创腔都是基于男性视野(撰曲家、乐师、听众)下的音乐行为。例如粤曲星腔的创始人小明星,她的星腔特色很大程度上是在王心帆与梁以忠的指导之下形成的,因此可以说女伶一定程度充当了男性知识分子审美情趣与文化理念代言人的角色。*关于粤曲唱腔流派中女性平喉流行所反映的性别社会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撰文阐述这一问题,故在此不赘。正是她们与撰曲家一起,推动了粤曲音乐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变革,完成了粤曲音乐体系的地方化过程,塑造了粤曲“抒情”的文化性——既是普罗大众的茶余消遣之作,但并未流于媚俗市民趣味,而是具有文学、音乐、精神高度统一的优秀的艺术作品。
结 语
从农村的八音班到城市的歌坛,从官话演唱到粤语方言;平喉唱法的推广,单一的梆黄到多声腔曲种的形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州茶楼歌坛作为一个音乐表演空间与普通民众的日常休闲之所,在音乐表演与日常生活的互动之中,实践着近代广东地方音乐文化“粤曲”的现代转型。这一过程既是外来声腔(梆黄)的艺术本土化的历程,也是粤曲从粤剧的附庸而成长为一种具有独立精神的文学曲艺体裁的过程。从歌坛时期的繁荣我们也可以管窥二三十年代的广州社会经济的活跃度,正是因为经济的支撑,才使得粤曲歌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30年代末由于日军侵华,广州的经济受到重挫,粤曲歌坛纷纷停业,女伶纷纷四处逃散,粤曲随之进入了停滞期。直到40年代抗战结束后歌坛才重新开业,那时候已经不叫歌坛,而改称音乐茶座,粤曲的表演形态也由坐唱改为站立演唱,然而曾经的歌坛林立、群伶争艳、新曲迭出的景象已不复存在。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粤曲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以爱群鸿图居、大同酒家、凤安龙胜酒家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