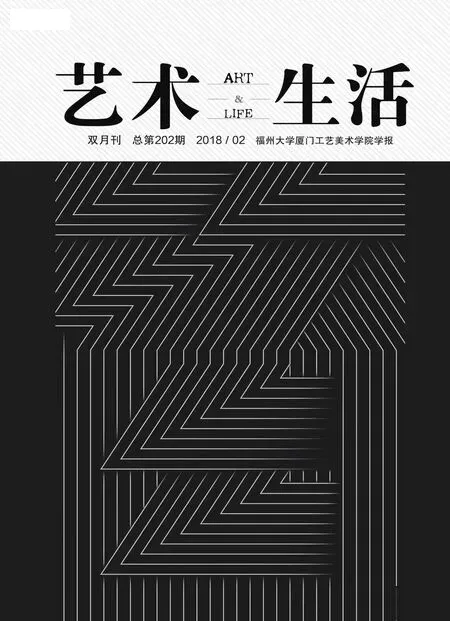《乐记》:有形的教育
黄守斌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
《乐记》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系统的音乐艺术理论专著,极为重要的是它提出“致乐以治心”“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反情和志”等理论,直至当下仍是有影响力的礼乐教化思想,也正是由此它标志着中国儒家艺术思想的成熟。《乐记》从“大音希声”到“乐以治心”的音乐无形论中,遮蔽了其对有形之音的独特贡献。中和地阐释《乐记》中音与心,探究其音心同构的音乐美育大厦,也许更能够体验到《乐记》深刻、全面、系统的音乐文化意义。
一、教育的形式
音乐是一种教育意义的存在,有功能性的教化,也是有着特征性的形式。其中艺术音乐的根在乐音运动形式,它是音乐之所以归结为音乐的本质内涵。当然这不是否认《乐记》作为他律化音乐理论上的卓越建树,而成为他律论的经典代表。它突出音乐的教育性意义的同时,还非常关注音乐艺术形式的建构。《乐记》这一典籍,有一个核心观点∶“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这里指出了音乐生于人心,是心灵的形式,是心与物相互感应、碰撞的结果。至而构成声成文的音,即音乐本身的乐音形式。因为有心的参与,这样形式蕴涵着丰富的人类情感。
可见《乐记》认同了音乐是一种形式,而“文”则是音乐形式的基础原则,有此,音乐方能是一种美的艺术形式。这些表现在音乐不同于原本的自然之声,即寄托、反映了人的情感,又符合“文”的节律,也蕴含着无穷的艺术韵味,简言之,音乐是教育的形式。我们可以从黑格尔的话中得到启示,他说∶“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感性的客观的因素在美里并不保留它的独立性,而是要把它的存在的直接性取消掉。”[1]黑格尔强调艺术存在与现实存在的差异性,现实存在是感性的显现,是自然的客观,而艺术是有了心灵理性参与的感性显现,与《乐记》思想是相通的。《乐记》认为声与音是不同的,声与音是两种不同的客观存在,声包括人的声和器物的声,是自然之声,感于物而形于声的声是音乐之声,为人的情感的自然表现。自然的声相异于“美”的音乐之声,但是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声”呈现强弱高低长短的变化与节奏,这一性质与人类情感的变动形成一种节奏上的耦合共在,“声”成为了心灵的形式。这为人所陶醉甚至迷狂的艺术实在,在音乐这一艺术样式中就是乐音形式本身,即“声之文”的强弱高低长短所构成的节奏与韵律。
艺术是教育的形式,艺术形式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乐本》以此作为开篇,正是源于此。它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的形式是直观的形式,这里的“动”和“形”字,把音乐在形式上的感性直观呈现出来,并且强调了乐音中蕴含这丰富的情感因素。艺术是人类的创造,它不是抽象的概念及其逻辑关系,它是超越功利超越实在的一种具有情感性的实践活动,它不依靠概念、公式而凭借形式,即由声音、表象、装饰及人体动作等所构成的具体形象、画面、场景来表现一种情感和意义,而这正是艺术的形式,在音乐中是乐音的运动形式。简言之,它是有着人类情感参与而创造的直观形式, “艺术是对实在的再解释,不过不是靠概念而是靠直观,不是以思想为媒介而是以感性形式为媒介。”[2]卡西尔的思想与《乐记》是相同的。《乐记》强调艺术的创作因物而激发情感,到外化为形,是不离“声成文”的形式创造。
音乐艺术是一种形式创造,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及完成后的形式上的特性。一部音乐作品的尘埃落定的过程,“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音乐的应有的形式特征在“变与方、情与文”之中。这对于音乐非常重要,无“文”之音就没有了音乐,那音乐中情感的出场与教化功能的落实变成无根的云彩,不管如何绚丽多彩,也不知从何说起。音乐是关于美的形式的创造,人们根据一定的艺术规则,对不同的声加以取舍、重构和美化,而达成“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用马克思的话语说,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造型”,变自然之声为有节奏有韵律的声音。这里的音,就是音乐或美的形式。它也寄寓人类的情感,正是:“乐者,德之华也。”
也就是说《乐记》强调音乐的美感形式,从来就不是空洞的,而是有意味的。卡西尔说:“情感本身解除了它们的精神负重,沉淀为形式并使形式本身获得自身的生命,我们感觉到的也只是形式和它们的生命,而不是带来的精神负重。”[3]从中可见音乐凭借音响、节奏、旋律、音色、速度、力度、曲式等,才能非常强烈地表达人们的情感。习惯上《乐记》把音乐当作“礼”的附属物,是政治与道德的工具,从而淡化了艺术的独立性。“艺术是人的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4],或“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使我们可以得到某种终级现实之感受的形式”[3]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化是艺术创造的需要也是人类的需要。“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乾,礼乐之谓也。”音乐通过礼乐教化为治国安民和友爱邻邦服务,并且减少征战杀伐,这是形式的功能,来源于形式本身的特征。古罗马著名美学家朗吉弩斯说:“和谐的乐调不仅对于人是一种很自然的工具,能说服人,使人愉快,而且还有一种惊人的力量,能表达强烈的情感。例如笛音就能把情感传给听众,使他们如醉如狂地欢欣鼓舞。”[5]《乐记》对于这些尤为重视,突出精神与形式的同在共在:“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丰富多样的感性形式,是人的丰富情感的外在表现,反过来不同的感性形式,则影响着人们的内心世界,所以形式创造是艺术的也是社会的。“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小大相成,终始相生,倡和清浊,迭相为经。”(《乐象》)确实音乐是形式的,是音与心在艺术形式中的同构,其为“心术”,是声音的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二、形式的教育
音乐是“心术”的艺术,寄寓人的情感、思想,是人类创造的文化,其功能旨趣是“文以化人”。自然《乐记》没有忽略音乐作为艺术形式的存在之基即音乐本身的形的同时,也强调音乐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教化功用。和其它的艺术形式一样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如果与人无关,或者说彻底无用,那也就没有了作为存在的理由和根基。这种艺术存在的根在人,为使人进入一种理想之境。它使人通向那理想的人生之境中有了一座可以依靠、通达的桥。《乐记》所说“乐由中出故静……乐至而不乱”的境界,在儒家这精神的桃源之处就是天人合一之境,艺术的助推下人抵达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说,音乐就是一叶看不见摸不着普渡人生的方舟。音乐自律论的西方代表学者汉斯立克也承认音乐对于人性有直接的影响,他说:“乐音的影响不仅更快,而且更直接、更强烈。其他艺术说服我们,音乐突然袭击我们。”[6]可他不承认音乐对人的影响是因为音乐本身表达或传递的感情,而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人的心情因为音乐的运动而变化,这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非常相似。但《乐记》更为中和,“言为心声”,“音”的形成与作者的心灵紧密联系在一起。有人对《声无哀乐论》进行质疑,“《声无哀乐论》提出的一些一般性的理论问题,具有长久的意义,但声无哀乐说,使音乐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命题”。[7](P283-284)《乐记》强调心与术的统一,时刻关注艺术与个体的情感宣泄、人格修养、社会秩序的维护、政治伦理等功能意义。“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这就告诉人们,音乐的功能的巨大,正是《乐记》的音乐旨趣所在。
中国古乐多是音乐、舞蹈、诗歌合一的综合体,对乐的功能主要在欣赏活动中。它不仅要用心去思考、去体验,而且还要调动身体器官,去表演、去参与。“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音乐节奏统领身体的“屈伸俯仰缀”和“升降上下”,音乐与舞蹈动作统合为符合礼义规范的美的形式,并借以“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记》)音乐教育功能的实现,与人耳目口鼻的顺正以及血气顺畅是互相一致的。人心不顺导致怨声载道,需要用礼乐教化来化解,以至于“天下皆宁”政治目的的实现。“反情以和其志”,在受外物刺激而动的情欲,经过乐的美感的熏陶、净化,可以超越了实在物的诱惑,最终返归于平静的原初之性。另外,由于人的行为受到音乐与礼仪的规范与调节,个体和集体易于在节律中,取得和谐一致,而“比类以成其行”。人们通过如此地反复训练,在潜移默化中使流动不居的情感凝聚、固化为一种稳定而高尚的情操,文明的社会人形成。
艺术的教育是从个体开始的。个体保持一种和乐的心理,人心也就自然向善。那么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群体和谐,就水到渠成了。因为音乐是群体的艺术,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乐化》)集体的意识集体的情感认同,需要音乐的教化。个体的素质和文化修养的不同,因此应该培养一种正确的快乐观,超越个体心理之乐,以天下大化而乐,进而天地人同和的和谐之境。通过乐的美感教育把人们情感联系起来,使之亲和,艺术的旨趣与人类目标一致。礼乐可把人与自然谐调起来,实现“大音之形”的化的功用。
三、余论
《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极为丰富,与先秦和孔子的音乐思想相比,它更系统化、理论化了,它没有把音乐当成纯粹他律的艺术形式,同时兼顾音乐本身乐音之美,关注音乐在其符号形式上的特性。故而大象并非“无形”,而是一种有形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