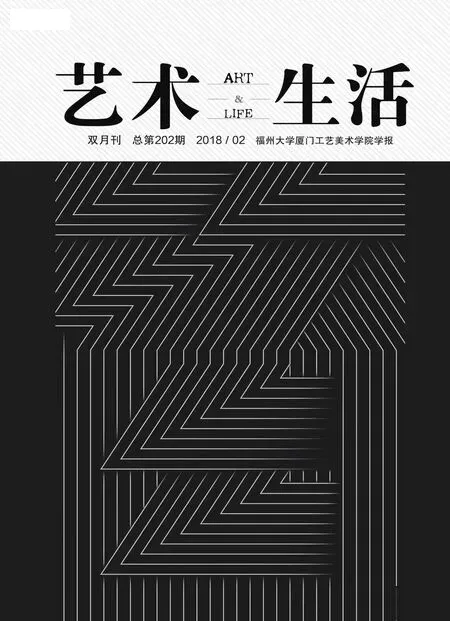区域性审美文化的传与统:以鄂西土家族审美形态为例
杨 黎
(湖北大学 艺术学院,湖北 武汉430062)
审美文化的民族区域研究不同于形而上的纯美学理论的探索,因为它直接面对的是民间,是大众,是日常生活中的审美体验和艺术活动。在中国特定的区域语境中,曾经衍生出各种带有浓郁民族性色彩的审美现象。美学研究只有在不断关注、切近当代文化现实和大众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才能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因此,积极有效地介入民族区域形态审美文化的研究,是符合当下文化现实的。
“文化”一词的容量很大,就审美文化而言,它是从美学角度对文化所作的考察,在具体的研究中它有其确定明晰的考察对象,既有物质形态的,也有观念形态的文化。在切近当代文化现实的过程中,地方性审美文化的民族形态必然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中可能会涉及到如下几个方面:关于区域性审美文化的民族特征,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对民族审美文化的统摄作用,以及特殊与一般、个体与群体、更新与传承等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诸如此类。这些都可以纳入到对地方性审美文化传承与统一关系的研究视野中。
一 、区域性审美文化的民族性与人类性
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北省境内,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除了土家族和苗族以外,还有汉族、侗族、回族、蒙古族等民族。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是鄂西土家族审美文化。据1993年版《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志》中所记载,生活在鄂西的土家族是聚居在湘、鄂、川黔边土家族的一部分,历经了数千年的生息繁衍。在鄂西地区遗留下来的巴人,是如今鄂西土家族的先民。出土于鄂西的古代巴人乐器和武器,大多以虎(白虎)为装饰图案,这些白虎图案见证了巴人的审美趣味。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土家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区域形态的审美文化,如地方性的音乐、舞蹈、建筑、编织等民间艺术。土家族审美文化作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一条支流,以其独特的文化形态流淌和奔腾在鄂西地区。
著名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对文学的民族性有独到的见解。在别林斯基看来,民族性固然是优秀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这种民族性首先是体现了某种“一般人类事物”的民族性,换言之,是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统一。“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一个没有了另外一个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1](p187)简言之,个性只有表现出共性才能实际存在。引申到审美文化中,也可以说,地方性审美文化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等个性特征只是普遍事物的特殊表现和形式。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中曾经说过:“如果一部民族史诗要使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也长久地感到兴趣,它所描绘的世界就不能专属某一特殊民族,而是要使这一特殊民族和它的英雄的品质和事迹能深刻地反映出一般人类的东西。”[2](p124)在黑格尔看来,民族审美文化的真正价值是在于它所反映的“一般人类的东西”,而正是这种“一般人类的东西”使得它成为了具有普遍意义和永恒魅力的审美客体。
从地方性审美文化的角度来说,可以表述为:彰显典型地方性特征的审美形态如果表现出一般人类的东西,必然会得到更多人的共鸣。也就是说,在顺应人类审美文化现实的前提下,表现形式和内容的推陈与出新是为了更广泛地认可和接受,这一点是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需要正视与思考的问题,它涉及到对“传承”与“统合”这一当代审美文化焦点的审视。但另一方面,当代审美文化的发展指向也与维护民族利益,注重审美文化本土化息息相关。对民族化、区域文化圈的重视并不是狭隘的观念设想,只有善于表达极具地方性特色的审美追求才能为世界所肯定,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二 、区域性审美文化的民族特性
(一)群体审美心理与民族审美文化的情感认同
审美文化是一个民族思想情感的表达,它的存在受制于该民族特定时代的生产、生活、信仰、思维等多重因素的渗透和影响。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形成往往与族群审美心理建立起诸多的直接联系。比如审美文化中的共鸣、趋同,即所谓“从众心理”。其审美价值取向的形成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种,是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所描述的个体行为的本能,另一类则是对个人有强制力的集体心理,如荣格所描述的“集体无意识”。当一个民族的审美心理表现为风气的时候,就意味着当地审美文化已经进入传播的阶段。
从审美与艺术创造的心理来看,情感的表现是最主要的。处于湖北境内的巴楚艺术,正是高度重视情感表现的代表。从屈原的《楚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力量在楚地艺术中表现得尤为鲜明。其强烈而生动的楚地特征,与生活在楚地的民族群体发自内心对自然生命的热爱,是密不可分的。楚地人民生性多情、敏感,加上对巫术的崇拜,这种“集体心理”的沉积必然造就楚地审美艺术浓烈、奔放而神秘的情感特征[3](p335)。
以歌谣这种民间口头文学形式为例,它的存在正是土家族人民“集体心理”中浓烈情感的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山歌中的竹枝词是巴渝地区非常盛行的一种较为古老的民歌,它历来被土家族人民长久地传诵,如 “桐子开花一树白,茶子开花隔年结;为人要学茶子树,秋冬四季不落叶”,以比兴的手法,表达了当地人民朴实的民风和人情。唐代诗人刘禹锡曾肯定了竹枝词的艺术特色,将竹枝词融入诗词创作中,使这种民间歌谣有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底蕴,从而广泛传播开去。哭嫁歌也是土家族歌谣中的一大特色,土家族姑娘出嫁前边哭边唱:“门前一股长流水,女儿泪水总长流。”这是一种特殊的自由抒情歌体,歌词的内容很广泛,作为当地习俗长期沿袭下来。土家族人民丰富的生活情感体验正是在歌谣的形式中得到了生动地表达,审美文化积淀的内在动力也正是依赖于民族群体“集体心理”的情感认同而生生不息。
(二) 区域环境与民族审美表现对象的典型性
地域性文化主要受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区域性审美文化所呈现的差异性和典型性特征,正是在这两种环境的影响下确立的。不同地域文化有其特定的特征对象,如民俗、礼仪、服饰、饮食、居所等方面,凝结于不同文化形态中,作为地域文化的典型形式而存在和延续。
根植于鄂西土家族人民生活中的一个典型审美文化形态就是戏剧。其中,尤以南戏为土家族人民所喜爱,它生长在土家族人民的劳动生活中,并涉及宗教祭祀、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南戏是在本民族丰富的传统民间艺术基础上,借鉴和配合汉族的戏剧而形成的。据《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志》记载,南戏是鄂西唯一能在庙台演出的大剧种,它的主要特色在于多声腔的同台表演,分生、旦、净、丑四大行,各行的戏装和人物造型具有浓郁的土家民俗特色。演出剧本大多为传奇和历史故事,现存于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的剧本藏本就有近800个之多。
另一个区域典型是鄂西土家族地区最具代表性意义的建筑——吊脚楼。吊脚楼是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最复杂而又最能显示富有的一种典型的建筑形式。其特征是全为木结构所建,两侧分别为厢房,而厢房的地基却低于正屋地基,所以一般为两层或三层,是一种特有的干栏建筑形式。吊脚楼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厢房的排柱悬空而立,柱子的末端有圆锥形的雕饰,称之为吊金爪。这种独特的民居建筑尤其注重龙脉的风水,依势而建,讲究人神共处的精神旨趣,突显的是土家族人特有的空间和宇宙观念。这一点还反映在吊脚楼的建造和落成仪式上。对土家人而言,新建筑的建造和落成意味着新的生命的开始。在这种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投射作用下,审美对象本身就被赋予了自然与人文双重环境造就的深刻美学价值。[4](p172)
(三) 审美表现方式的历史传承性
这里论及的审美表现方式可以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规范的概念来理解。不同于审美价值取向的内涵,它侧重于形式的表达手段或技巧。如不同区域环境下的民居形式,在其造型、材料、色彩、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其审美价值自然呈现不同的层次。在一个长期选择、改进、发展、完善的循环过程中,一旦某种审美形式成熟乃至定型之后,便成为传承的表现范式固定下来,从而作为当地特有的审美风尚和艺术形态而深入人心。
鄂西土家族的编织艺术呈现的就是这种传承性的审美形式。西兰卡普是土家族的传统编织工艺品。“西兰卡普”是一个土家语,意思是“土家被面”。土家的姑娘从12岁开始便学习传统的挑花、刺绣等技艺,一床西兰卡普就是三幅彩锦所制成。西兰卡普的题材来源于动植物图案、几何纹饰和土家文字,都是取材于当地的风土人情,这种审美形式经过人们的长期筛选和改进,渐渐成为传承的表现范式固定下来,在土家族区域文化中以传承和统合的方式沉淀、流传。
文化是构成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标志。楚地土家族文化与汉族文化长期交流和碰撞的程度相对趋缓,所以鄂西土家族在审美艺术形式方面的辨识度才会呈现得如此清晰。种种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并未造就民族间审美文化的隔阂,反而在其相互影响下更加深了民族审美文化的传承力度,自然而然地生成了独特的区域优势。可见,从当下的审美文化现实来看,深入挖掘民族区域性的审美价值,对于本土文化的构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区域性审美文化与地方性特征的统与合
以上所述的鄂西土家族审美文化的民族特征,就其独有的审美心理、审美对象、审美形式等方面的生成环境而言,文化的积淀才是造就各地区丰富审美资源的深层原因。中国传统文化所主导的审美趣尚,与地方性的人情、人事、人生、人伦一脉相承,凝结成一个个鲜活而长青的果实,如巴蜀文化、湘西文化、齐鲁文化、粤文化、滇文化等地域文化圈。在这些地域文化圈的层级之下,涉及到民族的迁移、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转变、意识形态的影响等方面。审美文化的交融和转型必然会是主要的轴心力量,也可理解为是一种统摄的作用。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之“宗”,可以是“人”的文化,可以是“物”或“自然”的文化,亦可以称之为“道”的文化。
特色地域与人文风情所造就的环境,造就了不同民族间丰富的生活场景。民族审美文化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的统合之流,呈现了多样化的地方性特色。首先,中国审美文化与地域人文环境是相互影响和相互生成的。从地域文化的发生学角度来看,每一类型的地方性审美文化都是建构在与地理环境相合相生的基础之上,如特有的专属文化标志,传承的民风民俗,共同的集体心理特征。简言之,文化与环境的共塑作用正好印证了其统合的关系。审美文化与地域人文环境的关系是顺应自然的。其次,审美文化与地域人文环境呈现互为不同程度的补充。一方面审美文化为自然特色和人文特征的展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而另一方面,地域人文环境也为审美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命动力。
翻开鄂西土家族文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汉族文化大势推行的时候,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就成为一种必须的要求,但是这种融合并不代表鄂西民族文化的消亡,反而是土家族极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吸收了汉族文化的先进因素,使自身特色得到更大的彰显。其繁多的种类、丰厚的内容、多样的形式、独特的风格成就了本民族殷实的审美文化资源。
四、区域性审美文化的传承与统合趋势
审美文化有其沿袭的一面,也有变异的一面,其所彰显的地方性特征自然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在当代文化交流日渐频繁的过程中,民族性、地域性的典型特征还会延续其鲜活的特质。但这其中,始终有两条清晰的脉络贯穿其中,那就是“变”的出陈求新与“统”的中和之道。
诚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5](p43)这段话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启示,各地域民族文化特征的形成是审美文化自身传统延续的直接后果。这应该是我们审视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立场和前提。传统是一条“河流”,我们只有顺着它的时间和空间交汇之势,在审美文化传统这股支流中修正和补充,才能使属于民族的、地域的优势特征得以延续。
当代的审美文化无论作为一种审美实践还是美学理论研究的探索,都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表现出对传统审美文化和美学理论的反思、超越。在各区域性审美文化对话交流日渐频繁的大背景下,努力表现民族审美特色的美学追求是发展的趋势。
区域性审美文化的传承与统和的趋势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区域跨文化交流对民族审美文化的影响。一方面,民族特色的审美文化传承,是实现跨文化交流的对话平台,对本土化的重视并不是保守的观念,相反,只有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审美形态,才能开拓更加广袤的审美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中国本土审美文化研究的话语系统开始转向全球化的语境。现当代美学跨文化、跨区域交流的方式与内容不断得到更新与提炼。这一转变主要是由于受到信息化发展进程的影响,中国本土审美文化观念汇入了世界文化思想潮流之中,这种思想文化意识的自觉为区域性审美文化的特色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展示空间。
因此,吐故和纳新是手段,区域性审美文化的统合之势是方向,探索符合当下审美文化现实的“传”与“统”之道,才是地方性审美文化价值凸显的正途。
———评《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