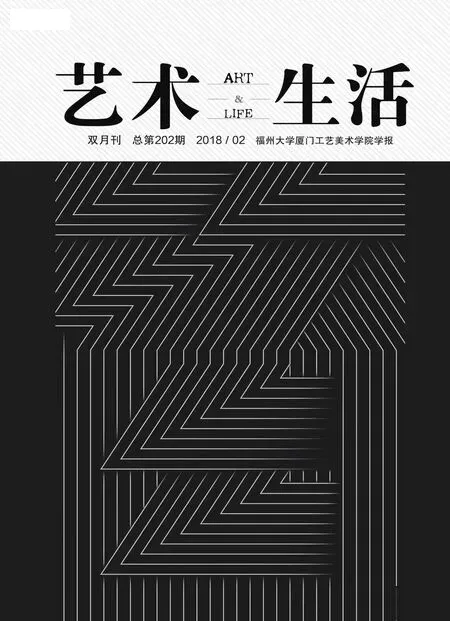现场影像与文化记忆
——读巫鸿《聚焦:摄影在中国》
林 颐
照片是记忆的载体,往昔的遗物。1839年,福克斯·塔尔博特发明了照相机,它旋即被广泛应用于文件建档、新闻报道、家庭留念、社会调查等各个方面,很快变成了一种“观察者的技术”,艺术评论家乔纳森·克拉里曾归纳:“照片不仅在新商品经济中,同时也在整个符号与影像版图的重塑过程当中,成为中心要素。”摄影术的传播极其迅速。
摄影术传入我国的最早记载,根据巫鸿在《聚焦:摄影在中国》(巫鸿著,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引言里所说的,1842年7月16日,一位名叫巴夏礼的英国年轻人写了一则日记,记录了达盖尔银版法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使用。巴夏里时任英国“HMS康沃利斯”号战舰随舰翻译实习生。不过,这则记录只是偶然。外国摄影术在中国的推广使用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
大约在1860年前后,两位有名的西方摄影师来到中国,弥尔顿·米勒和费利斯·比托。米勒以擅长拍摄中国官员、商贾以及妇女的肖像闻名。他的拍摄对象在静态中隐隐透出微妙的个性,至今仍被很多艺术史家和历史学家用作分析晚清末年国民心态的依据。然而,巫鸿通过比较分析和细心排查,指出米勒的照片里频繁出现的一位老妇人,一会儿被定名为官夫人,换个场合又成了商人家的老太太,很多标明不同家族的照片背景比如墙壁和地毯花纹也显示出一致性。推测可得,米勒大概雇佣模特在影楼里完成拍摄,然后给他们安上了不同的身份。米勒镜头里的人物无一例外地表现为麻木和隐忍,这种人为的艺术“造假”,目的是为了迎合当时欧洲对中国人的想象和嘲笑。
费利斯·比托属于第一代“战地摄影师”。其作品的构图和视角气势宏阔,“大连湾”和“香港岛”等都是居高临下的全景俯瞰。比托还拍摄了《陷落后的大沽北炮台内景》《八里桥》等战场实况,附注时间地点和事件概况,保留了烧毁之前的圆明园、佛香阁、多宝塔等影像,这些照片具有很高的史料研究价值。巫鸿在《废墟的故事》里已经说过,比托在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就显现出对记录人类屠杀的兴趣,他的职业爱好恰与英帝国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相伴而生。巫鸿谈及新闻摄影的事件再现功能和这种叙事方式与记忆塑造的关联。尽管新闻摄影强调客观、真实,但它一直都渗透着历史的意识,传达出摄影师本人的历史观。
《聚焦》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以影像表现中国与自我;重访多元视觉传统;摄影当代性的建构。除了讲述米勒和比托,第一部分还探讨了“剪辫子:民族与自我在影像中诞生”,还有以摄影师金石声为样本讨论“内在的、私人的和美学的空间”的中国影像史。巫鸿带着我们再度回到过去景象,透视照片背后隐藏的权力话语,观察摄影师自觉的审美情趣与时代要求的纠结,这部分的阐述鲜明地体现了巫鸿的史家风范。
比托拍摄的夕阳残照的通州宝塔,依稀透露出西方人对东方审美的迷恋与矛盾心境。这一类的“如画风景”如此深入人心,就好像是异途同归的河流,渐渐融入那个主题文化的脉络。这在中国传统里表现为“中国山水摄影的美学和源流”。从秦汉时期的寻觅仙山至弘仁、石涛等人的黄山绘画,直到中国现代摄影师郎静山、汪芜生等人的黄山摄影,东西方文化的最初交汇与吸纳,构成了中国摄影史的多元视觉体系,也显示出摄影由原初的记录功能转向了追求艺术化的呈现。当然,艺术化并不意味着对纪实的抛弃,近年来持续的“老照片热”,显示了民间对“微观历史”的认可;莫毅这样的城市民俗学者,基于对现实生活的社会关怀,依然在坚持不懈地实践纪实摄影或新写实主义的风格。
巫鸿对当代视觉形式及其文化背景的综述,揭示出摄影在技术和艺术层面上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他特别关注了刘铮、荣荣、缪晓春等摄影师的先锋实验。现代摄影深受后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这些摄影师深知他们的相机并不是客观冰冷的媒介,现代相机可以轻松地“欺骗”观众。这些摄影作品很多时候是让人难受的,它们不但直面死亡、变异和扭曲的边缘生存和社会畸态,还要人为不断强化和突出,以醒目的方式抓住我们。日常生活里那些微不足道的碎片,经过艺术化的处理,被赋予了多重解读的复杂内涵。摄影师通过镜头传达警示,相机以一种人类或许从未觉察的方式悄然进入我们的生活,相机甚至也有自己的独特视角。
不管如何,无论回望历史还是面对当下,无论是对现实的反应还是试图解构现实,摄影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