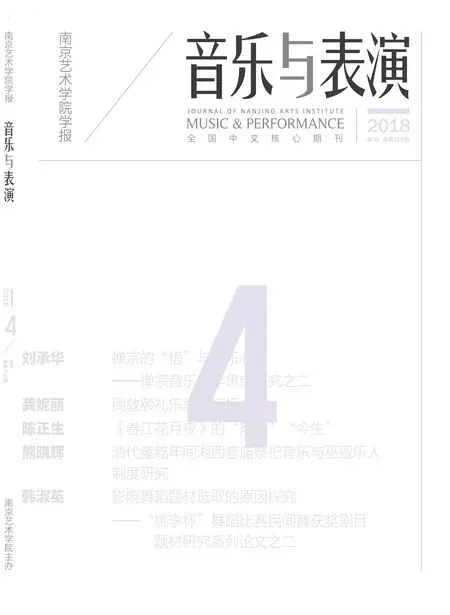跨文化语境下的高罗佩《琴道》研究①
陈 莉(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高罗佩是享誉世界的汉学家,1910年生于荷兰祖芬的一个军人家庭。他的祖父东方艺术,尤其喜爱中国和日本的漆器。他的父亲不仅深爱中国文化,而且在家中收藏了许多带有题诗、绘画和签章的中国瓷器。受家庭影响高罗佩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加之童年时期高罗佩跟随任殖民地军官的父亲生活在印度尼西亚,较多接触东方神秘文化,因而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文化颇有兴趣。高罗佩以一篇研究米芾《砚史》的文章获得了东方研究硕士学位,以研究中国和日本拜马神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之后,高罗佩到荷兰外交部供职,作为助理译员被派往日本东京。期间,他多次前往中国,学习和了解中国文化。1943年,高罗佩来到“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担任荷兰驻重庆使馆秘书。这使他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高罗佩从二十岁开始练习中国书法,其“高体”字笔力雄健,功底深厚。他对中国历史、司法等都充满了研究的兴趣,先将《武则天四大奇案》译为英文,又以狄仁杰为主角创作了十余部探案小说《大唐狄公案》。高罗佩对中国古琴颇有研究,他曾跟从叶诗梦、管平湖等学习古琴演奏技艺,且大量收集中国古琴及古琴文献,并于1941年撰写和出版了《琴道》一书。该书追溯古琴历史,探讨古琴演奏技艺和音乐原理,集中体现了高罗佩对于中国琴学精神的理解。透过《琴道》可以很好地了解一个异域学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解读,加深对中国琴道的认识。
一
用跨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国文化有着较为长远的历史,但由于文化的差异,异域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的解读总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要么将中国想象成一个神秘而富有魅力的国度,要么将中国描述成一个愚昧和落后的国度。高罗佩对中国的认识显然属于前者。他曾这样描述过他想象中的中国:“在记忆中,除了美丽动听的中国诗歌歌声般奇妙的韵律之外,还有一支用古琴弹奏的歌曲,以及长满玫瑰花和菊花的花园,一点点葡萄酒和一点忧愁。”[1]26高罗佩对中国的想象借用古琴、菊花等中国元素,再融进了玫瑰花、花园、葡萄酒等西方情调。正如周宁所说:“这种东方主义仰慕向往东方,美化神化东方,将东方想象成幸福与智慧的乐园。”[2]高罗佩对中国琴道的认识得益于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体会和热爱,同时也融入了他的东方文化想象。
作为一个异域研究者,高罗佩高度认可中国琴道,且对中国琴道有深刻的认识。高罗佩认为古琴的特点是:“古琴音乐基本上不是旋律性的,它的美不在于音符的衔接启承,而恰是蕴涵在每个独立音符之中。‘用音响写意’或许可以用来描述古琴音乐的本质。”“古琴音乐的每个音符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实体,都能引发听者内心独特的反应。”[3]1这是对古琴音乐有着深刻体会的人才能有的感受。更难能可贵的是,高罗佩能够认识到中国琴道重在精神,而不是其外在的形式和技术。而他的《琴道》一书就是围绕着“琴道”(琴学思想)构成主题的。可能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异域学者,隔着一定的时空距离,因而对中国琴学的认识能够删繁就简,直接抓住中国琴道的核心精神。在《琴道》中,高罗佩分别谈了古琴与儒、道、释三种中国哲学的内在关系。
高罗佩能够深刻认识到古琴在儒家文化中的地位,因而,他的《琴道》视《礼记·乐记》为重要理论资源。他指出中国儒家的音乐有两个不同的视角:“一方面是它一般的、宇宙的和神性的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具体的、政治的和人性的方面。”[3]23高罗佩认识到了中国儒家音乐的天地精神,他客观地罗列了《乐记》中的观点:“乐包含了天之和谐,而礼代表了地之和谐”“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异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3]23他也认识到了音乐作用于人是通过天人感应的方式,他说:“音乐与人是紧密联系的,因为音乐可以和人性中的神性呼应。”因为音乐是天意的直接体现,因而“明智的国君会利用音乐协助治理国家。”“音乐可以说是圣明君主把从上天感应到的美德,传给他的子民的工具”。[3]24依据对《乐记》的解读,高罗佩认识到中国音乐与天地宇宙的关系,明白统治者正是利用了人们对于天地的敬畏情怀,达到神道设教的目的。但关于中国古代音乐的宇宙情怀和天地精神,以及天人感应的神秘性,高罗佩基本止于对《乐记》思想的转述。
高罗佩对琴与道家哲学关系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刻一些。他看到了“崇尚人性本真”是道家哲学的核心,也是古琴精神的核心。他知道“乘着超然的、宁静的琴声,琴人的思想得到了净化并且升华至神秘的境界,他的灵魂可以与面前凹凸不平的岩石和潺潺的流水相通,这样他就会体验到与‘道’完全融为一体。”[3]54高罗佩也非常清楚松、鹤、月夜等景物与琴的关系。但是,他更看重的是古琴与养生的关系。他深知“鼓琴可以增强阳气、益寿延年”,也深知鼓琴能够升仙、驱魔和获得其他一些神奇的力量。
至于琴与佛的关系,由于资料比较少,加之事实上琴与佛禅的关系的确不够鲜明,因而高罗佩谈得比较空洞。他认为佛追求空静,因而琴坛应该设在大自然中一个美丽的地点:它必须远离一切尘世的喧嚣,纯净天然,为优美的风景所环绕。其实,这种境界并不为佛教所独有,因而显得较为牵强。为了充实和完善他儒释道并行的理论体系,高罗佩勉为其难地找到一些与佛教有关的琴曲来充实这一部分内容。
可以看出,高罗佩认识到了儒释道三种哲学观念是中国琴学的哲学基础。因而以这三个方面为支点来构建他的琴学框架。应该说,高罗佩抓住了中国琴道的内在精神脉络。作为一个异域学者,高罗佩对中国琴道的领会是深刻的。
二
但是,从高罗佩对琴道的论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虽然他力求构建一个儒释道为逻辑框架的琴学体系,但在对中国琴道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明显的“偏见”,也许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具体来看,这些“偏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高罗佩对古琴神秘精神的解读与中国本土的一贯解释有一定的距离。中国古代音乐的神秘性主要指的是音乐具有沟通天地神人、协调阴阳、与天地万物相互感应的作用。神秘性作为中国音乐精神的突出特征,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尚书·皋陶谟》[4]中就记载:乐师夔弹奏着琴瑟、敲击着鼗鼓、笙镛等乐器,演奏着《箫韶》之曲,最后使鸟兽翩翩起舞,凤凰来仪,达到神人和谐的境界。到了汉代艺术更是成为天人沟通的中介。《淮南子·说山训》罗列了瓠巴鼓瑟游鱼出听,伯牙鼓琴驷马仰秣,介子歌龙蛇文君垂泣等,很多神奇的感应故事。在谶纬神学中,诗更是被定义为“天地之心”[5]。中国古籍中的这些记载,不具有科学性,但却是当时人对世界的生命体验。在儒家文化中,这种神秘的音乐观念演化成天人感应模式,在《礼记·乐记》《春秋繁露》等典籍中得到较为集中的体现。高罗佩认识到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宇宙情怀和天地精神,但他对古乐神秘性的解读仅仅停留在理论认识的层面上,却不能有更深的认识。
进一步说,高罗佩虽然看到了古琴的神秘,但他所领会的神秘性不是天人感应的神秘,而是鬼故事的神秘。比如在该书第六章《关联》中,高罗佩搜集到了大量的与琴有关的鬼故事。如其中一个故事讲的是,嵇康夜晚弹琴,忽有一个戴着桎梏的鬼前来,希望嵇康给他弹一曲。嵇康为鬼弹琴,声清冷遥。嵇康问鬼话,鬼不回答,他疑心这鬼正是蔡邕。因为蔡邕死时身着桎梏。[3]150高罗佩搜集的这些与琴有关的鬼故事,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但与中国音乐中的天人感应精神还是具有一定的距离。或者说,高罗佩能够理解中国神怪小说中鬼的神秘性,但还不能从更远的根源上认识中国艺术中的天地精神,不能明白中国古人对天地和无形的神灵的敬畏情怀。
其次,高罗佩所说的雅乐与中国古琴理论中的“雅”其内涵不完全一样。在中国古代,古琴作为一种雅乐,首先用于集体性的祭祀仪式或宗族燕饮场合。中国的雅乐的确是少数人的音乐。比如在周代,雅乐主要属于贵族阶层。这种音乐以金石等大型乐器演奏,节奏缓慢、肃穆庄严。《礼记》中记载贵族燕饮礼仪要有升歌三终,笙奏三终,间歌三终,合乐三终的音乐演奏程序。《诗经》中有很多诗都描述了宏大的礼乐演奏场面,如《诗·小雅·鼓钟》中写道:“钟鼓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6]诗中将各种乐器发出的声音都做了形象的描摹,将将、喈喈、钦钦的声响在诗中回环往复,表现了雅乐“肃雍和鸣”的特点。这种面向整个宗族的大型礼乐所要维护的是群体生活秩序,传达的是尊卑长幼的统治理念。雅乐是沟通神人的中介,也是统治者传达意识形态,实现社会秩序化的载体。因而,中国古代音乐中的“雅”实际上指的是“正”,是正统的官方音乐、庙堂音乐,是一种群体艺术,表达的是集体情怀,在这种音乐中个体情感是受到限制的。
高罗佩显然要否定这种宗教性、群体性的雅乐,并张扬个体性的俗乐。在对《礼记·乐记》中音乐的天地精神进行了简单提炼之后,高罗佩马上将关注点转移到琴乐的个体性方面,他说:“在《乐记》中,除了讲述音乐在宇宙天道和治国方面的崇高作用,也有几段简述音乐对个人的作用。”[3]25《琴道》一书的自序也鲜明地指出:“自上古时代起,古琴就从其他乐器中分离出来,成为了文人(官员、诗人、画家和哲学家的结合体)形影不离的伴侣。”高罗佩强调的是琴与文人个体之间的关系。为了说明古琴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他甚至将文人的出现说成了“上古时代”的事情。殊不知,中国具有独立意识的文人最早也只能算到春秋战国时期。而春秋战国之前还没有鲜明的个体主体意识,春秋战国之前的音乐主要凸显的也不是个性情怀,而是某种集体理念。高罗佩所认可的恰恰不是中国古代艺术的这种宗教情怀和集体主义精神。相反,高罗佩认为郑、卫民风中的一些古老的爱情歌谣,以及魏文侯所表现出的对郑卫之音的喜爱,这才是中国古代音乐的真实情况。郑卫之声过多表达儿女私情,在儒家传统音乐观念中,被认为是淫声,孔子说要“放郑声”[7],但这恰恰成为高罗佩所认可的音乐。因此,高罗佩认为《乐记》中有关音乐神圣性的记载只是一小部分官方学者对于音乐文化的美好想象,而不是对音乐的忠实描写。他认为中国古代音乐的实际状况是,俗乐构成了文人和平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雅乐只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为有限的听众演奏。纵观高罗佩有关古琴音乐的描述,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在为俗乐鸣锣开道,在有意否定中国的雅乐体制。
与此观点相应,高罗佩对古琴作用的领会与中国儒家对古琴的文化意义的解读存在很大不同。在儒家文化中,琴是君子情操的象征,君子以琴来节制和规范自身的欲望,以便持守各种礼仪道德规范。桓谭《新论·琴道篇》讲:“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8]这就是说,琴不是一个纯粹的玩物,而是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情操和人生体悟的象征物。在遭遇不幸时,琴可以提醒君子独善其身,而不要失去操守;在仕途通达、人生如意时,琴能表达和悦的情怀。高罗佩也注意到《风俗通义》中对“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的论述,并指出由于琴具有控制人的情绪的作用,所以能成为克己守礼的文人精神的象征。如果高罗佩有关琴的认识就止于此,那么,他的基本理解与儒家一脉相承的文以载道精神并无两样。但事实上,高罗佩很快抛弃了这种以琴来禁止淫邪的观点,否定了具有高度政治和伦理色彩的中国儒家音乐理念。在他看来,音乐作为一门艺术有着自足性和自我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受道德或者哲学因素的影响。高罗佩指出:“古琴适合独自消遣。”[3]40消遣的前提是能够承担得起高昂的古琴费用,能够克服难度学会一定的演奏技艺。古琴的“雅”其实主要不在于它与修养个人道德品质有关,而是因为它是一个文人拥有社会地位、显得高雅不俗的标志。高罗佩说:“这是因为一张好琴价格高昂;演奏古琴的技术高难;而传授古琴演奏的教师又寥若辰星。”[3]41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只能买得起一把琵琶或者胡琴,靠死记硬背弹奏一些流行的曲调,但不能买得起、学得起古琴。因而,古琴把商人、平民、歌女等都排除在外,成为一小部分既有情调又有金钱、社会地位,以及懂得演奏技艺的文人特有的一种乐器。显然,高罗佩这里所说的一小部分文人主要指的是像高罗佩那样的有身份、有地位的一小部分文人。
中国古琴是一个意义的载体,富有深厚的文化蕴涵,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古琴的形制和音色、曲韵都充满了象征性。这种象征精神渊源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最终落脚到作为伦理观念的物质载体上面。其重要表现就是以天地作为人的伦理准则的依据。这种象天法地的思想渊源于《周易·系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9]这一思想在器物制作中得到广泛体现,如桓谭的《琴道》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这种象天法地的思想。桓谭指出,琴长三尺六寸,象征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琴上圆而敛,法天,下方而平,法地;隐长四寸五分,象征着四时五行;琴“上广下狭”,象征着长幼、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这就是说,琴效法天地,连接君臣。琴是君子情操的象征,君子以琴来规范自身行为。[8]这就是中国儒家“文以载道”思想的核心所在。
但高罗佩在有关琴的形制的介绍中,几乎完全摆脱了琴的象征精神和文化载体意义。他只是客观地介绍了琴的共鸣箱、琴弦、琴徽等。即便高罗佩的《琴道》专门辟出一章来谈琴的象征性,但在“琴制和琴名的象征意义”一节中也只是告诉读者琴的末端为什么叫作“焦尾”。高罗佩关注中国文化,但显然在回避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精神。如介绍“龙池”和“凤沼”时,他阐述了中国古琴与龙凤文化的关系;在“琴声的象征意义”中,高罗佩努力挖掘的是十六种琴声的审美价值。严格说来,这并不属于象征,而是有关琴的联想和想象。在“指法的象征意义”中,高罗佩介绍的是各种指法与自然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如“捻”的手势就如同大雁衔住一根芦苇一样。将指法与自然事物相联系,其目的是让初学者体会指法的特征和用力的大小等。然而,这种层面的象征与中国古代琴道中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象征完全不是一回事。分析到此,我们对有些学者评价高罗佩古琴理论的观点就不能完全认同。有学者在《高罗佩与中国古琴文化》一文中指出:“高罗佩赞同琴道的基本要素完全符合儒家理论”。[10]笔者认为,仅就琴道而言,高罗佩的认识表面体现了儒家精神,但细究起来就会发现,其精神实质与儒家音乐观念有很大出入。
三
高罗佩热爱中国文化,有着较深厚的汉学修养,虽然他收藏和阅读了不少中国古琴文献,自己也会演奏古琴,但是他对文献的解读自然是有选择性的。选择是跨文化传播的必然,也是接受者对异质文化基于排斥的接受过程,选择是“偏见”形成的重要原因。在对异域文化的接受中,第一步是选择,选择的基础上会有进一步的构建。高罗佩按照自己的“中国镜像”构建中国的琴学思想。而高罗佩的“中国镜像”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以明代中国为背景,其二以明代文人为主体。据高罗佩的儿子回忆说,他们家另一个固定元素是一件中式漆屏,它是由四个版块组成的晚明屏幕。红色漆上有精美的浮雕,在所表现的各种景象里,许多人物在豪华的庭院里游玩。这块屏风成为高罗佩写作小说的灵感源头。而在高罗佩创作的小说《大唐狄公案》中,全部插图、社会习俗和人物服饰都是明代的翻版。可见高罗佩对明代文化的熟悉程度。从明代文人这一视角观照高罗佩对中国琴道的解读,他的琴学“偏见”会迎刃而解。
明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明朝前期,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政策,提倡程朱理学,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文人士大夫胆战心惊,缺乏创造力。明代中后期,一方面是资本主义萌芽,商业得到发展;另一方面是帝王懈怠,朝政荒废。与这两个方面相伴而生的是张扬个性和个体欲望的心学得到了长足发展,甚至心学后学促进了放纵欲望的淫俗文化的发展。在这种时代氛围下,文人士大夫不再以科举和当官作为人生唯一的选择,很多文人主动或被动地投身卖画、卖文行列,文化产业得到发展。文人与商人角色和身份的结合,抬高了明代商业的品味,也使文人趣味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封建社会,文人的行为方式及文人的儒雅趣味被广为效仿。高罗佩选择了明代,他将琴道也建立在明代文化的背景之上,他关于琴道的解读中总是有着明代的影子。
高罗佩对古琴作为雅文化的理解,来自于他对明代文人的高雅的趣味的向往。明代文人赏花、品茗、弹琴、赏画、郊游、雅集,风流倜傥。这种儒雅风流的文人形象成为一个异域“文人”对于中国的美好想象。高罗佩说“尤其自从明代后期以来,具有高雅情趣和品位的学者阶层——他们是培菊、插花、鉴香、养兰的行家”[3]63,高罗佩明显表现出对晚明文人雅致审美趣味的青睐。高罗佩在中国研习中国书法、音乐、美术、收藏中国字画,实际上是中国明代文人诗酒风流、琴棋书画、多才多艺的镜像在吸引着他这样去做。
高罗佩曾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尊明斋”,也将自己的书房布置成地道的明代文人风格的书房,墙上挂的是琵琶、中式条幅和唐卡,书橱上摆放了一尊释迦牟尼铜像,琴台上摆放着一张古琴,中式条案上则堆满了几番周折淘来的中国典籍,以及清代浅浮雕人物山水木制笔筒、双鹊波浪纹辽砚、三足蟾铜砚滴、猴桃蓝釉瓷砚滴等,这是明清时期典型的文房布局。正是浸淫于这样的东方文化的氛围里,高罗佩宁愿将中国琴道理解成与这种情景最为切合的一种精神艺术。
高罗佩常常在文人聚会上表演古琴,这也来自于他对明代文人雅集中琴乐表演的向往。高罗佩说他对中国文化的想象是:“很多文人聚会的场面”[3]69。文人雅集始于中国的魏晋时期,在西晋有以石崇金谷园为中心的二十四友的雅集,在东晋有著名的兰亭雅集,而以绘画的形式将文人雅集表现出来却盛行于宋明时期。宋徽宗、李公麟、文徵明、仇英、唐寅等都表现过文人雅集的题材,所画内容大多有山水的背景,以及文人于松下林间弹琴吟咏的情景。以琴会友也是他心中明代文化镜像的现实化。1943年高罗佩以荷兰皇家大使馆一秘的身份进住中国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当时的重庆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中国最优秀的文化人由于躲避战火而云集于此。高罗佩充分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时常游娱于齐白石、沈尹默、徐文镜、饶宗颐、徐悲鸿等文人雅士之间,以求耳濡目染,加深自己的中文造诣。这些具有官员身份的文人雅士与四川本地的富裕阶层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经常到大地主杨少五的别墅度过美好的周末。在这期间,高罗佩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社会名流组成了“天风琴社”。这样的交游中显然有着中国古代文人的高雅趣味。也正因为此,高罗佩在有关琴道的论述反复指出,琴是少数上层社会中人用来消遣、养生的音乐方式。这种以明代为镜像、以诗酒风流为背景的对琴道的解读,自然会疏忽了古琴载道的社会价值。
高罗佩选择以明代作为自己“中国镜像”的模本,并构成自己对中国琴道阐释和解读的基础,这与高罗佩本人的性情也有密切的关系。高罗佩自幼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对世界政局之类的事情不是非常关注。他依靠他的聪明和善于观察能够在大使馆里完成基本公务,但他对自己的公职只是努力去做,并不会完全用心。在有关高罗佩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在自传稿和记事本里,高罗佩没有谈到中国所处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局势。……但政治局势对他的触动并不深刻,这些远不如他对中国学术和艺术生活的研究和参与那么深入。”[1]101他将文化的兴趣和研究工作放在第一位,外交官的政治工作则放在第二位。高罗佩在谈到古琴的作用时,虽然是从《礼记·乐记》《风俗通义》中琴对淫邪的抑制作用出发的,但是他却还是回到了“古琴适合个人消遣”这个最适合他自己的用途之上。高罗佩是一个天生喜欢追求自由的人,他不愿意受任何约束,也不喜欢在规定的上班时间工作,更不喜欢循规蹈矩。他的家庭对他个人在异性方面的选择从不干涉,因而高罗佩上大学时,就与年长自己18岁的奈丽·勒姆香同居,到日本后又与勝桑、美代子等多个女性有性关系。寻花问柳,追求性享受,在他看来与追寻一个地方的文化一样,是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明代社会“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11]高罗佩的追求个性和性解放的精神是对晚明时期淫秽、放纵的时代风气的殊途同归。高罗佩所搜集的中国性学资料也主要都是明代的。但是高罗佩会赋予明代具有淫秽性质的文化一种更为古老的意义。他认为:“在古代中国,性交被视为等同于与宇宙的创造过程的人类活动,从来没有与道德上的愧疚或犯罪感觉联系起来。”[1]163高罗佩为明代的淫秽性关系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基础。同样,高罗佩也赋予娱乐性的古琴艺术以天地精神,但实际上在他的内心深处,中国琴道与明代文人远离政治、吟风弄月、狎妓宴游的风流气息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高罗佩的琴道表面上是琴禁止淫邪的作用和琴的神秘性,但实际上,琴是有钱、有地位、又有儒雅心性的文人身份的象征。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高罗佩虽然提到了中国古琴的神秘文化特征,但并没有能够对中国古琴音乐的天地感应精神,以及古琴作为中国伦理道德载体这些精神给予足够的重视。高罗佩做了较充分论述的是古琴与“道”的关系,以及古琴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高罗佩研究中国古琴带着对于中国明代文人雅士生活的想象。基于此,他将古琴解读为一小部分文人才有资格拥有的雅文化,关注的是古琴的音声之美,以及古琴作为中国符号的诗情画意性。可以看出,异域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的构建是以他们的前理解为基础所展开的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对任何文本的阐释都有赖于阐释者自己所处时代的“期待视域”,阐释者正是透过这个视野来理解和解释文本的。高罗佩对于中国古琴的认识首先基于自己对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认识,当他接触古琴时,又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了富有“偏见”的解读。因而,高罗佩的《琴道》虽然与中国汉代桓谭的《琴道》同名,但他以为内在精神的是显示文人高雅情趣的琴道,而不是中国古代作为沟通天人关系以及载道工具的琴道。这是古琴接受和传播中的文化变异,体现了跨文化接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