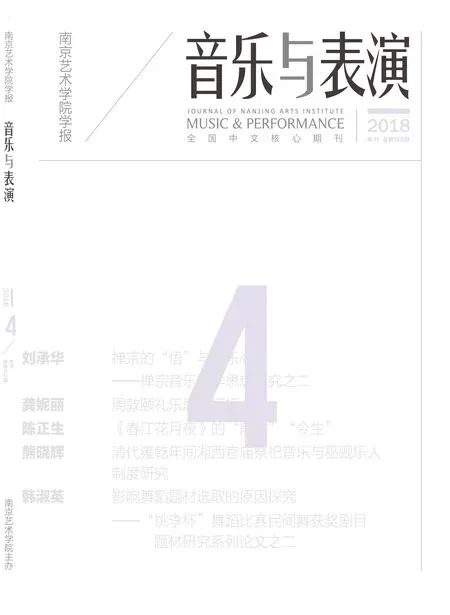《春江花月夜》的“前世”“今生”
陈正生(上海艺术研究所,上海 200031)
一
2016年9月4日,G20峰会在向有天堂美誉的杭州召开。在这次峰会上,《春江花月夜》可谓出足重彩,让与会各国元首欣赏了我国最早的这一首世界名曲。
前不久见到“尚音爱乐”网站的博文:《我们熟悉的国粹〈春江花月夜〉原来是个假造的名,源自一场欺骗》,标题显示了博主的观点。博文中选用了杨荫浏先生刊于《人民音乐》1954年第二期上的文章:《从〈春江花月夜〉的标题谈起》。从行文来看,杨荫浏先生认为,此曲只该有《夕阳箫鼓》和《浔阳夜月》两个名字,而《春江花月夜》“是最不靠谱的”。杨先生作为音乐学家,且不论他的行文是否审慎,议论是否偏执,博主采用此文,无疑就是赞同了杨先生的观点——稀奇的是,他还承认《春江花月夜》是国粹。按照题意,《春江花月夜》既然是假造的,音响就应该选取正宗的《夕阳箫鼓》让人们欣赏欣赏,以正视听,并体现该正宗乐曲之魅力,若选取《浔阳夜月》,至少也应该简单论证一下《浔阳夜月》就是《夕阳箫鼓》的根据——因为这两首乐曲之间毕竟存在着差异。奇怪的是,“尚音爱乐”的博文所选的四首乐曲全都明文标着应予以摒弃的《春江花月夜》:杜冲等三人演奏的三重奏《春江花月夜》、上海民族乐团的琵琶齐奏《春江花月夜》、陆春龄先生等四人所奏江南丝竹音乐风格的《春江花月夜》以及相对具有传统演奏风格的合奏《春江花月夜》。
杨荫浏先生在《从〈春江花月夜〉的标题谈起》一文中,提到《春江花月夜》是伪造。其理由是,在他前一辈所存的谱中(如李芳园《琵琶谱》、沈浩初《养正轩琵琶谱》)都没有《春江花月夜》之名,实际上柳尧章先生改编《春江花月夜》是在这些谱之后。杨先生提到他1953年同程午加先生讨论《春江花月夜》,他可能认为程先生是大同乐会会员,竟然对此曲也不甚了了。实际上这并不奇怪。程先生是大同乐会早期会员,但这是1925年之前的事,1925年10月,程先生就脱离大同乐会而担任了俭德储蓄会国乐团主任,柳尧章先生此时《春江花月夜》才改编成功,刚刚问世。再说郑觐文对《春江花月夜》和《月儿高》十分重视,声言这两首曲子为该会所专有。柳尧章改编出《春江花月夜》之后,只有郑觐文先生的侄儿、郑立三之子、我国著名妇科专家郑惠国能演奏,在大同乐会演奏《春江花月夜》时,柳尧章先生若无暇参与,则由郑惠国先生顶替。1929年,卫仲乐先生参加大同乐会,郑觐文慧眼识真材,让柳尧章先生将《春江花月夜》和《月儿高》传授给卫仲乐先生。1932年,柳尧章先生离开大同乐会自办“中西音乐研究室”以后,《春江花月夜》就归卫先生主奏了。卫仲乐先生参加大同乐会以后,很多事情都表现出郑先生对他的器重。首先是更名,郑觐文觉得原先的“卫崇福”名字太俗,建议他更名卫仲乐(“保卫中国音乐”,师母常戏称他“胃中乐”)。此后便是1932年国立音专朱英的学生杨少彝毕业离沪,以在济南办大同乐会济南分会的条件,学得《春江花月夜》和《月儿高》。
有鉴于此,当年乐林国乐社社长蔡金台先生,获知卫仲乐先生深得郑先生器重,掌握了《春江花月夜》和《月儿高》的演奏技艺以后,便向卫先生索讨《春江花月夜》的演奏谱。他自以为卫先生初次接触琵琶时曾得他指点,索讨一份谱不会成问题。当卫先生向他讲明原委后,蔡金台为学《春江花月夜》便毅然参加了大同乐会。为此,当年大同乐会除少数人员而外,其他人员也多不会弹奏这两首曲子,就更别说其他音乐团体的人了。为此,外界不了解这两首乐曲的产生过程是很自然的。再如陈泽民先生编辑汪昱庭先生的琵琶谱,我就告知陈泽民先生,别把《月儿高》纳入其中——尽管汪先生抄录了此曲。事实上汪先生不擅此曲,他对《月儿高》的弹奏手法还是从其弟子金祖礼先生那儿转手过来的。由此可见,郑觐文先生对这两首乐曲的掌控程度。
基于郑觐文对《春江花月夜》《月儿高》的掌控而不得外传,上海的丝竹界便仿效大同乐会的做法,将琵琶独奏曲中的文曲移植作江南丝竹的合奏曲。1927年7月,国乐研究社李廷松、孙裕德等人(此后的霄雿乐团成员)就将《浔阳夜月》《汉宫秋月》移植作江南丝竹乐曲,随后,《青莲乐府》《塞上曲》也被移植成丝竹乐,丝竹界便称其为“新丝竹”,上海的丝竹团体至今都保留着这几套曲子。由此可见,《春江花月夜》影响之大。
二
至于说《春江花月夜》假托古人之作,这同柳尧章和郑觐文二位先生毫无关系。
1956年,我向甘涛老师学琵琶,最先学的便是《春江花月夜》,谱子是卫先生的演奏谱。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谱的右上角写着“唐 康昆仑作;一说虞世南”。甘涛老师的《春江花月夜》乐谱,当然是卫仲乐先生1935—1936年间在中央广播电台国乐组时获得的。卫仲乐老师精于演奏这两首曲子,但未必知晓这两首曲子的改编过程;甘涛老师做事谨慎,不会给乐曲妄增内容,此事为哪位好事者所为,已难考证。
1957年3月,由(北京)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正谱本《夕阳箫鼓》,所载是李廷松先生的演奏谱,是杨荫浏、曹安和二位先生整理的专册。杨先生继续发挥《人民音乐》所刊载文章的观点。他的研究结论是:《春江花月夜》应易名为《夕阳箫鼓》,才能以正视听。
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应辨别清楚《夕阳箫鼓》《浔阳夜月》和《春江花月夜》是否为同一首曲子;即是否为同曲异名?《浔阳夜月》是汪昱庭先生根据《夕阳箫鼓》改编的新曲,《春江花月夜》则是柳尧章先生根据汪昱庭先生所授《浔阳夜月》改编的新曲,显然不是同一首曲子。既然不是同一首曲子,为什么又要求异曲必须同名,统一归属于《夕阳箫鼓》?汪昱庭先生对李芳园琵琶谱中的《夕阳箫鼓》进行再创作后易名《浔阳夜月》,柳尧章先生又对《浔阳夜月》再改编而易名为《春江花月夜》有何不妥?若不允许对旧有乐曲进行再创作,那李芳园琵琶谱中的《塞上曲》不就是将华秋萍琵琶谱中的五首小曲联缀而成,杨先生为何不进行评论和问责?假若一首改编后的乐曲仍然应该沿用旧曲名,那聂耳《金蛇狂舞》因为同《倒八板》旋律变动极微,更应该沿用《倒八板》旧名,电视剧《水浒传》中的《好汉歌》则应正名为《雅韵由》。《倒八板》还是有些人熟悉的,《雅韵由》恐怕知晓的人极少。《雅韵由》一谱,载于王黄石编的《中华俗乐谱》,1920年由开封文化书社出版发行。“俗乐”就是民间小曲。该谱为工尺、简谱对照。至于该曲何以叫《雅韵由》,可能该曲原先是一首声乐曲,起首三字为“雅韵由”,就如同有些民间小曲佚名以后,民间艺人就根据起首音定名“工尺上”(321)“工四上”(36.1)一样。当然,这是笔者对《雅韵由》曲名的猜度不足为训。再举个大家熟悉的例子。《紫竹调》,20世纪初名为《连湘调》。“连湘”,当年民间盛行的小歌舞,表演者双手各拿一根连湘,边歌边舞。连湘,是一根一米多长的细竹竿,两头及中间共开四个槽,内嵌铜钱敲击以发声。20世纪四十年代,有人对该曲调稍作整理并配上词,更名《箫》,并注明是“苏南民歌”;其词语确有吴语韵味。五十年代,此曲又用于曲牌体的沪剧《罗汉钱》,因歌曲《箫》的首句是“一支紫竹直苗苗”而更名《紫竹调》。《连湘调》是五声宫调式,《箫》是五声徵调式,而《紫竹调》若剔除末两句经过音的变宫,则是五声羽调式,尽管调式都变了,但是一眼就可认出是同一首曲子。此种情况下,我们能说《箫》和《紫竹调》都是欺骗,应该叫《连湘调》?《连湘调》在用于“连湘”小歌舞之前该另有其他名字吧,究竟该叫何调?我们民间乐手的编曲能力是很强的。上海地区流行的两首洞箫独奏曲《柳摇金》和《佛上殿》,孙裕德先生吹奏这两首曲子极负盛名,可孙先生就不知道它们乃是同一首曲子(有当年演奏的节目单为证),与我同辈的人也没想过这问题。那我们该说哪一个名字是“正宗”的,哪一个名字是欺骗了演奏者和听众?
再就杨先生在《夕阳箫鼓》一书中所录李廷松先生演奏之谱是否为《夕阳箫鼓》,本人就持怀疑态度!李廷松先生是汪昱庭先生的得意弟子。何以见得汪先生对李廷松先生器重?以下事实即可作明证。大约1926年前后,汪先生曾被上海富商叶澄衷的孙子叶寿臣请去教琵琶,叶寿臣还和汪先生一道在公众场合登台演奏过一次琵琶。获此殊荣,叶寿臣便购买了一把紫檀木琵琶赠送给汪先生,后来汪先生因其子不弹琵琶,便在众多的弟子中选择将此琵琶传给了李廷松(现传给了郝亦凡)。大约1926年,汪先生便建立了“(汪氏)琵琶研究会”,地址在棉纱公所(今延安东路河南路口,建国后为自然博物馆,现已迁离)。汪先生弟子众多,陈重先生就常去听汪先生授课。众多的弟子中何以独赠李廷松先生?再说汪先生每次登台琵琶独奏,所报曲名都是《浔阳夜月》,教众多弟子的也都是《浔阳夜月》(教柳尧章先生的也同样是《浔阳夜月》),而唯独教李廷松先生《夕阳箫鼓》?本人想选取《夕阳箫鼓》《浔阳夜月》同《春江花月夜》乐谱的相对应部分做点比较分析,可惜尚未找到当年保存的《浔阳琵琶》,只找到友人复印给我的版刻本《霓裳羽衣曲》和《春江花月夜》。笔者深知,根据这两个曲名,在此版本中即使找到《夕阳箫鼓》也未必能作谱例,因为此版本显系三十年代以后的刻本无疑。值得一提的是,无意间我看到了高雄市国乐学会一九八四年元月出版的第六期《国乐会刊》,其中刊载了吴忠泰先生《琵琶古曲——夕阳箫鼓》一文,文所举谱例就是标标准准的《春江花月夜》。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汪先生的众多弟子中,唯有柳尧章、卫仲乐二位先生每次奏的都是《春江花月夜》——从不奏《浔阳夜月》。其原因是柳、卫二位先生掌握《春江花月夜》的奏法,《春江花月夜》的旋律显然优于《浔阳夜月》,别人没机会掌握。1935年,郑觐文先生逝世后,此曲在卫仲乐先生的掌控下得以流传开来则另作别论。
三
现在谈谈《春江花月夜》改编的真实过程。《春江花月夜》的编曲者是柳尧章先生。柳先生是浙江鄞县人(生于1905年10月10日,1996年12月17日逝世,享年92岁)。其父喜好丝竹,柳尧章从小随父亲学习丝竹。父亲在沪经商,柳先生12岁来沪,中学就读于校规极严的徐汇公学,并向校长、意大利神甫Lawaza学钢琴,兼习小提琴和大提琴。柳先生的子女受他影响,经过他的教授,多从事音乐工作:儿子柳和埙八岁即开始学小提琴,1940年3月2日,上海青年会举办沪上儿童音乐比赛,柳和埙(当时名柳仲篪)获最佳成绩,退休前是上海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教师;他的外孙三岁时得到他的启蒙,现在是美国克里夫兰交响乐团小提琴手。
柳尧章同郑觐文的结缘经过也很奇特。1924年2月13日,《申报》刊载郑觐文的文章:《大同乐会筹备修正中西乐》。柳尧章赞同郑觐文的观点,当日就带着报纸去拜会郑觐文,二人谈话甚为投机,遂结为忘年深交。当时大同乐会由郑觐文教琴瑟,汪昱庭教琵琶,欧阳予倩教歌舞,陈道安教京剧,杨子咏教昆曲,于是郑觐文先生便介绍柳尧章先生向汪昱庭先生学琵琶,汪先生遂教柳先生《浔阳夜月》。4月8日,大同乐会于市政厅开古乐舞大会,郑觐文赠票给柳尧章。会后郑先生征求柳先生意见,柳先生遂说:“古乐虽好,然曲高和寡,不及改编丝竹比较便利”,郑先生遂委托柳先生试做此事。柳先生遂将他学得的《浔阳夜月》改编成合奏曲。此曲的改编于1925年10月完成,10行谱,郑觐文起先给它取名《秋江月》。
《浔阳琵琶》,很容易让人引起对白居易《琵琶行》的联想,然而《浔阳琵琶》的分段与标题又同《琵琶行》无涉;《夕阳箫鼓》曲子寓情于景,已无秋风萧瑟之意;《浔阳夜月》与《浔阳琵琶》虽然仍有牵连,然意境毕竟有不小差别,何况演奏上已有不少新的处理;《秋江月》,从标题上仍然不难看出它与《浔阳琵琶》和《浔阳夜月》的牵连。1926年春,郑觐文就将此曲定名为《春江花月夜》,并重新拟定了十段小标题。从乐曲的内容来看,《春江花月夜》不仅曲名与前不同,演奏形式也起了本质的变化:由琵琶独奏变成了具有中国室内乐性质的小合奏;曲调的处理完全符合民间的处理方法——支声复调。在柳尧章先生生前,我还执笔为他写了篇小文章:《我是怎样改编〈春江花月夜〉的》,刊载于《音乐周报》1991年10月18日第二版。内容除柳先生的讲述外,我还寻找了文献加以核实。
这就是《春江花月夜》的改编过程。
四
有关《春江花月夜》的问题,杨荫浏先生的文章所言不足为训。至于说伪造,似乎更不恰当。按照杨先生的推理,《二泉映月》之名不亦显得荒唐?据说《二泉映月》的曲名是杨荫浏先生定的。试问,无锡惠泉能映月?明月照于惠泉之上就是阿炳所奏旋律之意境?杨先生是人,不是神。他的言论和研究,有些是值得商榷的。本人就写过多篇文章是针对杨先生研究不当之处的。本人对杨先生的纠偏,不仅专家们认可,就连杨先生最得意的学生也赞成我的观点——这是尊重事实。
对于师长、前辈,理当崇敬,我们是在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行。但是崇敬不是盲从,否则我们将失去方向而无从进取。杨先生对民族音乐贡献良多,但不是所言皆正确——他生前做的错事最大的我认为有两件:一是在《中国音乐史稿》中列出“历代黄钟正律”音高,误导了此后的音乐考古。我怀疑“历代黄钟正律音高”的频率公式来源于吴南熏先生,我在吴先生的《律学汇通》中见过此公式。但是《中国音乐史纲》的出版早于《律学汇通》,之前他们之间是否有沟通,不得而知,就像杨荫浏先生曾向丁燮林先生学过音乐声学而很少为人所知一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杨先生颇费精力算出的“历代黄钟正律音高”,却未收入以后编写的《中国音乐史稿》,况且在新著中几乎不提“历代黄钟正律”之事,何故?另一件是,杨先生主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律管的鉴定。为显示专家的身份,对这套律管鉴定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难以解释,就武断地判其为“明器”——此时的重要依据可能就是律管所吹奏出的频率,同他计算出的汉代黄钟正律音高不符。对于前一个问题,我写了《黄钟正律析——兼议律管频率公式的物理量》(刊《艺苑》1989年第1期)。该文作为东方音乐学会首届年会的论文,与会的日本东方音乐学会会长岸边成雄先生,就给予很高评价。该文从对律管频率计算公式分析入手,并加以实际的律管验证,除校验管端校正量而外,实证了律管中气柱振动的速度不能等同于自由空间的速度——因存在粘滞阻尼,且粘滞阻尼还随管径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得出运用律管频率公式所算出的历代黄钟正律音高不可信的结论。如今我通过对荀勖“笛律”的深入研究,更深信杨先生算出的“历代黄钟正律音高”不可信。后一篇则写了《应对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律管做进一步研究》(刊《交响》1990年第2期)。上海博物馆马承源馆长曾借出差长沙的机会为我了解律管的保存情况,回来告知这套律管已无法再用来研究。如今我更获知了鉴定过程中的细节——出土时律管就无法吹,依据出土律管测出的内径另做一套两端无管径差的律管吹奏,测得的频率作为这套律管的频率。古人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说到底,杨先生当时对马王堆出土律管的鉴定方法本身就显得草率。
再就《春江花月夜》的命名来说,杨荫浏先生认定此曲是套用了陈后主的《春江花月夜》之名——因陈后主所创诗歌内容是颓废的,因此用类比的方法做出《春江花月夜》曲名不应存在的依据。我们应该重行讨论这结论是否得当。陈后主是创建了《春江花月夜》的诗歌形式,然此曲的命名何以就承继了陈后主的颓废情怀?笔者谫陋,读书甚少,未读过陈后主的《春江花月夜》而不知其诗的颓废程度,只读过唐代诗人张若虚的巨篇《春江花月夜》。张若虚距陈后主生活的年代很近,其间相隔仅150年左右,其作品《春江花月夜》同样是诗歌,张若虚是否也套用了陈后主诗歌形式,其内容是否也颓废?笔者只见到后人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肯定。从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的内容来看,它同乐曲《春江花月夜》的曲情似乎倒是有些许关系。
从曲名来看,《春江花月夜》是确定了乐曲的时空和情境:春夜的江岸花草如茵,游人尽兴而归。此曲韵味十足,宛如一幅无形的山水长卷,一首无言的情境诗!这该是人们喜好它的原因所在。
《春江花月夜》诞生以后,曾以此曲招待过不少外宾。主要有:1927年11月,俄国小提琴家秦巴里斯特(Zmbalist)来沪,与大同乐会联欢,大同乐会压轴的节目就是《春江花月夜》;1933年4月9日晚,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为大同乐会拍摄送美国芝加哥1933年7月举办的万国博览会的彩色纪录片,其中就有9人合奏的《春江花月夜》。
有人撰文说,“春江”就是“春申江”。谁都知道,“春申江”的特指无法替代“春江”之泛指,尽管《春江花月夜》诞生于上海!郑觐文先生在我出世前两年就已仙逝,可1982年以后,我同柳尧章、卫仲乐、金祖礼、许光毅诸先生经常接触,同卫先生甚至一周见两次面,同柳先生、金先生经常谈论大同乐会的事,从未听他们提及“春江”就是“春申江”。
如今舞台上《夕阳箫鼓》已经绝响。若要听《夕阳箫鼓》的演奏,除非依据李芳园的《琵琶谱》翻弹。至于想听正宗的琵琶独奏《浔阳夜月》也很难。说实话,我也没听过真正意义上的《浔阳夜月》,不知北京的李廷松先生过世前留有的《夕阳箫鼓》(抑或《浔阳夜月》)音响,保存是否良好,杨先生出版的《夕阳箫鼓》正谱本所据的就是李廷松先生的录音。我保存着柳尧章先生20世纪20年代手抄的《浔阳夜月》(工尺谱)的复印件,常常从谱中去体味《浔阳夜月》的韵味。后听说有人记录过吾师金祖礼先生演奏的《浔阳夜月》,找到一看,原来还是《春江花月夜》;只是记谱者将《春江花月夜》的旋律按照《浔阳夜月》来分段而已。此外,20世纪90年代,云南音像出版社曾为上海湖心亭丝竹乐队录制过盒式磁带,内中就有丝竹乐《浔阳夜月》,担纲琵琶主奏的是马恒章先生。马先生是20世纪30、40年代上海滩江南丝竹琵琶大王张志翔的弟子,后又拜汪昱庭先生为师,无论是丝竹的琵琶演奏,还是《浔阳夜月》的火候掌握,都应该是老到的。但是有一点,丝竹演奏同琵琶独奏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这就同《春江花月夜》一样,如今的上海丝竹乐队,既奏《浔阳夜月》,也奏《春江花月夜》;但丝竹乐队演奏《春江花月夜》,多带有江南丝竹的演奏风格,不及非江南丝竹乐队演奏得细腻。我听卫仲乐先生琵琶独奏《春江花月夜》和20世纪50年代同孙裕德、陈永禄二位先生合奏的《春江花月夜》,效果就有一定差别。有时我也听到一些演奏家的演奏,曲名标着《夕阳箫鼓》或《浔阳夜月》,可一听,都是标标准准的《春江花月夜》。一些人认定杨先生的说法正确:《浔阳夜月》和《春江花月夜》应归属于《夕阳箫鼓》,尤其是《春江花月夜》一名的使用乃是“欺骗”;试问,那些硬将《春江花月夜》说成是《夕阳箫鼓》的人,是否也是在欺骗?
五
笔者从以上的分析认定,《夕阳箫鼓》已经消亡,《浔阳夜月》也同样式微,而由《浔阳夜月》改编成的《春江花月夜》此后几乎“一统天下”。为什么?因为《春江花月夜》的旋律动人,有意境,韵味十足,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难怪《春江花月夜》一诞生就有人说:脱胎于《浔阳夜月》的《春江花月夜》,“实为丝竹界别开生面”,“韵致天然,无一点尘俗气,闻之如身亲其境”,不听当引以为憾。这该是《春江花月夜》风行的根本原因。
民乐合奏曲中有两首著名乐曲我们经常能听到:《春江花月夜》和《月儿高》(《霓裳羽衣曲》)。它们俩是姊妹篇。我们也常看到这两首曲子的说明:由某某人改编。既然是改编,那么被改编的原始曲目是什么?古曲?非也——前文已陈述清楚。我之所以说它们是姊妹篇,一是编这两首曲子的是同一个人,二是这两首曲子产生于同一时期。《春江花月夜》是柳尧章先生于1925年根据汪昱庭先生的《浔阳夜月》改编而成的;《月儿高》则是柳尧章先生于1927年从华秋苹《琵琶谱》中挖掘整理出来的。《月儿高》于1927年7月2日首演,由柳尧章先生弹琵琶、由时有洞箫大王美誉的王巽之先生吹箫。由于事前《申报》有所报道,致使当日尽管大雨如注,仍然是座无虚席。如今笔者听一些作曲家改编这两首乐曲,颇不以为然。愚以为这些改编后的作品,仅仅是配器而已。
仅凭这两首乐曲,柳尧章先生对民族音乐的贡献就已功不可没,何况他对别人的教授也是无私的。某次中国管弦乐团成员聚会(该乐队成员多为卫仲乐、金祖礼、许光毅三位先生的学生),难得卫仲乐、柳尧章、沈仲章、金祖礼、许光毅诸先生都在场。许光毅先生面对柳先生就动情地说:“柳先生是我们的师兄,作孽呐,他是我们的老师!”我曾问卫先生《春江花月夜》和《月儿高》系何人所教。卫先生正色道:“当然是柳尧章!”实际上柳尧章先生教过许光毅先生二胡,教过卫仲乐先生琵琶和小提琴。尽管如此,所有的音乐辞书却没一本提及过柳尧章先生——柳先生一生淡泊,不知者无过。希望我们以后演奏《春江花月夜》和《月儿高》时能记取柳尧章先生——这不仅是对柳尧章先生的尊重,更是对历史的尊重。
修订于2016年10月6日定稿
上海市黄浦区建国中路1号706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