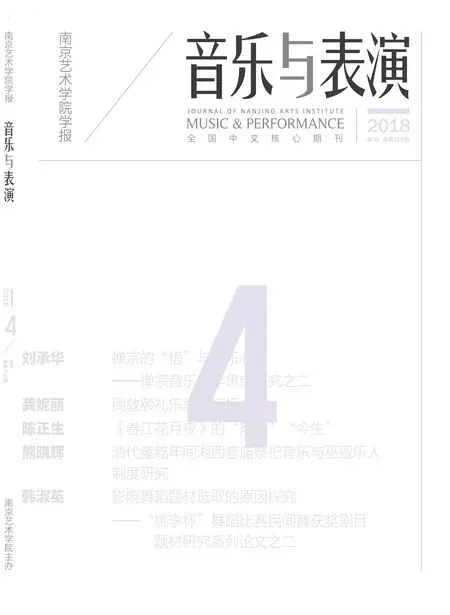禅宗的“悟”与音乐心理
—— 禅宗音乐美学思想研究之二①
刘承华(南京艺术学院 音乐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由“缘起论”得知:色即空,空即色,世事万相,虚幻多变,也都是“空”!但是,人们却总是对它们形成“执”,包括“我执”和“法执”两种。“法执”是执着于自己身外的各种事物,如金钱、地位、权力、荣誉、财物,等等;“我执”则是执着于一个“我”,执着于“我”的优越和高明。这两种“执”,说到底都是一个心理问题,它涉及的是人的身心关系。在佛教看来,这些执着均源于“识”,既是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感官之识的产物,也是与之同时发生作用的意识的结果,再由意识中的“我识”分别形成“我执”和“法执”,给人带来无尽的烦恼。佛教禅宗的任务就是要破此“执”,即:通过改变人的“无明”状态,洞见世界的“空”性,消除贪、嗔、痴、疑、慢等种种烦恼与执着,进入轻松自由、新鲜生动的境界。而“破执”的入手处,则是语言文字概念。
一、禅宗的“不立文字”
如何改变“无明”状态,去洞见“空”的本质?小乘佛教是通过禁欲苦修,大乘佛教则通过“定”“慧”双修。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必不可免,那就是习经,就是通过文字所载经文的研习,来提高自己的觉悟,获得般若智慧。但是,过分注重文字又会带来新的执着,妨碍人们对佛性亦即生命真谛的把握,于是便有了禅宗的“不立文字”,并将其一直追溯至佛主释迦牟尼,谓其“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之义付诸摩诃迦叶,自称“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说一字”[1]上册,10。这表明禅宗奉行的也是佛主释迦牟尼的思想。
禅宗创立以后,“不立文字”成为它的第一大特色。禅宗的实际创立者慧能,即自称不识字而能领悟佛理。“有尼无尽藏者,常读《涅磐经》,慧能听之,即为解说其义。尼遂执卷问字,祖(慧能)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曷能会义?’祖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1]上册,53这里有一个问题:从字面上看,慧能认为无需识字就能解说佛理,是把语言与文字区别了开来。那么,语言与文字是否需要区别对待?两者是否有本质的不同?回答是否定的。尽管慧能自谓不识字而能“解说其义”,其解说无疑用的也是语言,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慧能是否定文字而肯定语言。实际上,语言和文字都只是思想的符号,只不过语言是声音符号,文字是形迹符号而已,两者无本质区别。只是因为语言相对于文字更加接近思想语义,才在慧能的这番表述中得到肯定;而且,透过他的话,我们不难察觉,他真正肯定的还是由语言所表述的思想义理,而非语言本身。所以,尽管语言更接近思想义理,但它还不是思想义理本身,而仍然只是符号。释迦牟尼说自己“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说一字”,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禅宗看来,把握佛教义理,为什么要不立文字,不着语言?首先,佛教的最高义理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这个道理,道家早已指出过。老子《道德经》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最深奥、最根本的道理是语言无法把握的。佛教也有同样的思想,即“第一义”不可说。《楞伽经》曾分析其原因,认为“第一义者,是圣智内自证境,非言语分别智境。……言语者,起灭动摇展转因缘生;若展转缘生,于第一义不能显示。第一义者,无自他相;言语有相,不能显示。第一义者,但唯自心,种种外想悉皆无有,言语分别不能显示。”[2]就是说,第一义是对宇宙生命的体验,是自证的境界;语言则生于起灭变化差异,于第一义无所用。禅宗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在对佛教的改革中将其发扬光大。禅宗的这个特点,胡适曾经从方法论上来理解,认为这是禅宗大师所喜用的一种叫作“不说破”的说法方法。日本铃木大拙则认为这不是一个方法问题,而是因为人的体验中本就存在着无法言说的东西。“般若直觉中有着某种非知性所能把捉、非所谓直说所能说明的东西存在着。并非禅师存心避免使用此种直说的方法。”[3]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便存在着无法由语言表达的思想感受。所以,“道由悟达,不在语言”[1]中册,537,是广大禅师们的共识。
其次,即使能够用语言表达,其表达也没有意义,因为禅宗所着意的是实践,是行动,是体验,不是认知。在以认知为主的文化中,语言是至为重要的,因为没有语言就无法表达,没有表达就无法传达,没有传达就无法交流、评判。而在以实践为主的文化中,认知只是进入实践的一个准备,是手段而非目的。对于实践来说,他更需要的是得心应手,而不是传达,也不是表达,能否交流也是次要的。禅宗的修行主要是实践,所以并不在乎语言表达与否。云居弘觉禅师云:“佛法无多事,行得即是。”正因为“行得即是”,所以不需要另作言说;“汝但作佛,莫愁佛不解语。”[4]佛是从行中觉知,佛之“语”不是言说,而就是“行”,是由“行”而来的体验。赵州从谂禅师问南泉普愿禅师“如何是道?”南泉说:“平常心是道。”赵州说:“还可趣向也无?”南泉说:“拟向即乖。”又问:“不拟争(怎)知是道?”答曰:“道不属知,不属不知。知是妄觉,不知是无记。若真达不疑之道,犹如太虚,廓然荡豁,岂可强是非邪?”赵州于言下即悟。[1]上册,199“犹如太虚,廓然荡豁”是悟道后的体验,只有亲身体验才是真切的,即使他能够将其言说出来,也没有意义,因为它与你无关。对于你来说,它不真切。
此外,语言表达不仅无意义,而且还会成为另一种“执”。修禅是每个人以自己的生命、情境进行的,而每个人的生命、情境又各不相同。因此,每个人的体验必然也不一样。这样,如果将一人的体验境界言说出来,就会使其定格,成为别人的目标,这就变成一种新的“执”,它会成为自己亲身觉悟的障碍。所以,有僧人问药山惟俨禅师如何修道,药山沉思良久后说:“吾今为汝一句亦不难,只宜汝于言下便见去,犹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过。不如且各合口,免杀上累及。”[1]上册,260“更入思量”,就是引发对方形成新的思虑,变为新的执着。所以不如各自闭口,等待“言下便见”式的亲身体验。
语言不足以表达佛的真谛,同样,它也不能完美地表达音乐的美感意蕴。这首先是因为,音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言说性。这个认识在中国很早即已形成。《乐记》云:“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师乙篇》)“言之不足”,这本来是说音乐产生的原因的,内心当中有某种思想情感需要表达出来。其用语言表达者,即为诗;而当语言无法完满表达时,便“长言之”,即声音拉长;若“长言之”还不足以表达,则“嗟叹之”,即加上感叹的词和音调。这“长言”“嗟叹”,就是音乐。这席话倒过来看,正好说明,音乐所要表现的思想情感往往是语言所不能表达或不能完满表达的。禅宗大师也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道理,表达了同样的思想。释空尘在《枯木禅琴谱·自序》中说:“始悟琴旨,各禀性灵,庄生所谓:‘意之所随,不可以言传。’盖节奏板拍,可以传授;取音用意,各随人心。”[5]14-15“节奏板拍,可以传授”,是因为它有形迹,有差异,故可以用语言来描述。而“意之所随,不可以言传”,是因为“取音用意,各随人心”;而人心之丰富复杂,精深细致,如情感的微妙变化,体验的幽邃入微,意念的玄远飘逸,以语言之“粗”,是不足以妥切表达的。
其次,言说只是“指物”之“指”,而非所“指”之“物”。禅宗大师经常喜欢使用“指月”之喻,手指指向月亮,但手指不是月亮,故而不能把手指当成月亮。这是现代符号学中的“能指”与“所指”之关系。按照这个理论,语言、文字只是表达思想情感的符号,而不是思想情感本身,两者有质的不同。但另一方面,要把握“所指”,在一定程度上又离不开“能指”;要找到月亮,有时又不得不循着别人的手指望过去。这里关键之处是,千万别把手指当成月亮。禅宗史上有一个文字禅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是可以使用语言,并致力于研究历史公案中的语言机锋的,但这只是起着“启发”或“激发”作用,而不在语言本身。北宋文字禅大师慧洪云:“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心之缘、道之标帜也。标帜审则心契,故学者每以语言为得道浅深之候。”[6]道不可以用语言传,但可以通过语言呈现出来。因此,要到达道的彼岸,往往也要借助语言之力;但借助语言之力,最终目的还是要进入非语言的境界。他说:“借言以显无言,然言中无言之趣,妙至幽玄。”[7]最终不在“言”,而是由“言”所显的“无言之趣”。这个道理在音乐上亦同样成立。音乐之妙无法言传,但要领略音乐的妙处,又往往离不开语言的引导。释空尘在《枯木禅琴谱·凡例》中说:“弹琴须省题目,一曲有一曲之宫商节奏,或初奏未叶,数句后方入本调。其中起承转合、变音跌宕、入慢结尾俱要意会。起首之慢要有生发,结尾之宕要有结束。审前人制曲命名之义,自可得其意矣。”[5]24这里的“省题目”之“省”以及“审前人制曲命名之义”之“审”,就是通过语言即曲名、标题和乐曲的解题进行的。但这只是一个引导和过渡,最终还是“要意会”,其目的也是“得其意”,让欣赏者自己从心底领会音乐的妙处,而不能只停留在那些语言表述上。历史上各种谱本对乐曲所做的语言解说和文字描述,均可做这样的理解;而且,也只有做这样的理解和对待,才是正确的。
既然对音乐的接受最终都是自己的亲身体会,那么,以前对音乐的种种描述即文字言说就都应抛弃。此即庄子的“得意忘言”,也即禅宗的“随说随扫”。百丈怀海禅师说:“佛是无求人,求之即乖理。是无求理,求之即失。若著无求,复同于有求。若著无为,复同于有为。”“无求”是对“求”的否定,但说了“无求”后,随即又应该将它否定,是对否定又加否定。接着他还引用了佛经中语:“不取于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1]上册,134,进一步说明这个意思。通过连续的否定,不使它落实在肯定上,这就是“随说随扫”。之所以在得“意”后要忘“言”,在“说”后要随即“扫”掉,是因为每个人的经验不同,故对音乐的理解和体会必然有异。如果不“扫”掉,就容易把自己限制在别人的言说上,窒息了将要发生的活泼泼的美感体验;另一方面,如果你真进入自己的美感体验,此前所记他人之言自然也该忘掉,因为已经不需要了。所以,忘掉别人的言说,才意味着你真正进入自己的美感体验,就好像只有离开船,才意味着你已经踏上彼岸一样。而且,别人的言说只是一种陈迹,是前缘的产物;只有抛弃它,才能迎来新缘,创造新的美感境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释迦牟尼才自谓“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说一字”。在此语言只是一个跳板,目的是让你自己上船,去亲身体验。
二、“悟”:心的显现
通过语言而进入的状态,是一个由自己亲身体验的状态,一个由心灵了悟的状态。这个“悟”,便是禅宗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境界。所以六祖慧能云:“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
那么,悟从何而来?从自心、自性中来。虽然悟有时候可以通过语言而达到,但却不是从语言而来,语言只是起到激发和诱因的作用。慧能说:“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8]111自性是本体,它存在于自心之中,所以只须从自心中发现。又说:“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若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即是无念。”(《坛经·般若第二》)①[明]宗宝本《坛经》,《〈坛经〉诸本集成》,王孺童编校,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宗宝本《坛经》分:行由第一,般若第二,疑问第三,定慧第四,坐禅第五,忏悔第六,机缘第七,顿渐第八,宣诏第九,付嘱第十等十个章节。下引《坛经》未作说明者,均系该《集成》中的宗宝本。为节省篇幅,只夹注其章节名,不再脚注。“悟”就是自见本心,自显本性。悟的对立面是“迷”,迷即“迷自本心”。马祖道一说:“性无有异,用则不同。在迷为识,在悟为智。顺理为悟,顺事为迷。迷则迷自本心,悟则悟自本性。一悟永悟,不复更迷。”[8]138可见,从慧能到他的传人,都十分重视“悟”在修禅过程中的意义。
禅宗的“悟”,其状态如何?禅师们常常喜欢用“如桶底脱”来形容。雪峰义存禅师问德山宣鉴:“从上宗乘中事,学人还有分也无?”德山立刻给予当头棒喝:“道甚么!”雪峰后来说:“我当时如桶底脱相似。”[1]中册,379-380在古代禅林中,禅师们所说之桶一般为装漆之桶,里面是黑的。一旦底子脱了,桶内即刻变得明亮了,同时提着桶的手也觉得轻松了。这个感觉恰好同顿悟时的感觉相似:轻松、敞亮,没有挂碍。因为这个缘故,许多人便将禅宗之“悟”的内容理解为“空”。加上无论是印度佛教,还是中国佛教乃至禅宗,无不秉持“空”的思想,认为“色即空,空即色”“五蕴皆空”“万法皆空”。这种所谓“空观”使得这个理解更趋固化,认为禅宗的“悟”就是从内心深处体验到万事皆空,一种对以前所执着问题的彻底丢弃。应该说,这并不错,但不够深刻,也不够全面。即如前面所说,在禅宗那里,无是为了有,空是为了满。它确实表达了对以往所执着问题的取消,但这个取消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人生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所以它不是单纯的取消,不是消极的放弃。如果说是“取消”,那也是一种积极的“取消”,在取消之外还有新的意义。日本现代禅师铃木大拙曾指出,禅宗的悟,“从宗教角度来说它是新生,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它是获得新观点,人们会觉得世界如今焕然一新”。他有一段文字对此做了辨析:
在强调禅宗的“悟”的时候,应该注意的是,禅宗的禅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其他宗派所奉行的“禅那”体系是不同的,通常说到“禅那”,是指那种指向一定思想内容的冥想或疑心。这思想内容,在小乘佛教常常是“无常观”,在大乘佛教常常是寻求“空”,当心灵被训练到意识甚至无意识的感觉都消失,出现了完全的空白状态的时候,换句话说,即所有形式的心灵活动都从意识中被排除出去,心灵中一丝云彩也没有,只剩下广袤蔚蓝的虚空的时候,可以说“禅那”便到达成功了,这可以称之为迷醉(ecstasy或extasy)或梦幻般境界(trance),但不能称之为禅宗的禅。禅宗的禅必须“悟”,必须是一气推倒旧理性作用的全部堆积并建立新生命基础的全面的心灵突现,必须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通过新视角遍观万事万物的新感觉的觉醒。而“禅那”之中并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它不过是使心灵归于宁静的训练,当然这是禅那的长处,但尽管如此,也不能把它与禅宗的禅等同看待。①[日]铃木大拙《悟:禅宗的存在价值》,学佛网:http://wuming.xuefo.net/nr/1/7194.html。亦可参见另一译本:铃木大拙《禅学入门·悟》,谢思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92-104页。译文稍有不同。
在这里,铃木的努力是要把禅宗的“禅悟”同佛教其它宗派的“禅那”区别开来,从而突出禅宗之“悟”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真实的,否则禅宗也就无所谓禅宗了。但从历史形成角度看,禅宗之“悟”同佛教其它宗派之“禅那”并非没有联系,而是在它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其它佛教流派止于对空的体验,而禅宗则特别强调还要由此产生新的发现,新的见解,新的创造,新的境界。
那么,“悟”是如何发生的呢?简而言之,“悟”是“心”的直接显现。
禅宗之“悟”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灵感”。灵感总是针对现实中某个具体的事件或问题,总是对这些事件或问题所做的解决。所以,灵感是直接针对着外部世界的,具有明确的外在性和功利性。禅宗之“悟”则不然,它不是针对外部世界中某个事件或问题,不是指向现实中某个事件或问题的解决,而是着眼于突破心中的种种遮蔽,剥除包裹在心上的种种外衣,返回到自己的本心,使其直接“裸露”。本心得以“裸露”,即可获得一种完全不同以往看世界的眼光,从而才有可能产生对世界的新看法、新见解,创造出自己人生的新境界。所以,它是发自内而成诸外,具有突出的内在性。因为强调内在,常以“本心”“自心”言“心”。这里“本心”“自心”便是禅宗之“悟”的关键所在。慧能常常启发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即是福田。”又说:“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自心”“本心”是修佛了悟的根本,“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个思想应该是直接源自他的老师五祖弘忍,弘忍在慧能临行前即曾告诫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坛经·行由第一》)
既然“自心本净”“即心是佛”,为何还需要“开导”“示教”?还需要“悟”?因为虽然本心自净,但在世俗的生活中已经被种种杂质沾染,自心已“迷”。所以,慧能说:“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缘心迷,不能自悟。”为了凸显“自心”“本心”在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慧能对“智与愚”“渐与顿”进行分析,指出它们的区别与联系均在其“心”的觉知与否。关于智与愚,其区别就在其“心”是否“开”:“智者与愚人说法,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智与愚的区别即在“自心”,其转换的机理亦在“自心”。觉解自心,愚即瞬间转化为智。渐与顿也是如此。慧能强调说:“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钝,迷人渐修,悟人顿契。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坛经·定慧第四》)顿和渐并非质的差异,真正质的差别在于是否“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如果自见其“本心”“本性”,顿、渐皆可忽略不计。可见,在禅宗看来,“万法尽在自心”。既“尽在自心”,那么,“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坛经·般若第二》)这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慧能将其称之为“直心”。他说:“一行三昧者,于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是也。”并且引用《净名经》的话:“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坛经·定慧第四》)而“悟”,也就是“直心”的结果。“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坛经·般若第二》),是禅宗之悟的唯一正途。
“悟”作为禅宗修行的高峰体验,其体验的根本在“心”,因此,禅宗的传播与传承自然就由“心”来维系,于是便有“以心传心”“以心印心”的独特方法。五祖弘忍在传衣于慧能时说,衣只是“信体”,是一个外在标识。更重要的是“法”,“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并强调指出:“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坛经·行由第一》)“信体”是外在的,只是一种符号;“本体”才是内在的,那就是“心”。而“心”又是通过“悟”得以显现的。因此,“以心传心”,就是在“悟”的瞬间使禅宗的精神血脉不断衍生开来,并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而“传心”的机制,禅师们有时候称之为“印”,是“以心印心”。唐代著名禅师黄檗希运《传心法要》云:“自如来付法迦叶已来,以心印心,心心不异。印著空,即印不成文;印著物,即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异。能印所印,俱难契会,故得者少。”[9]“印”的特点是,既非空无所有,亦非着意于物,而就是心与心的契然相合(“契会”),了无中介。由于这种“心心不异”的契合极为不易,故往往少不了得道者(大师)的接引。通过师徒间的日久磨合和反复碰撞,一旦接通,则豁然开朗。这种“豁然”的状态,就是“悟”。
三、音乐与“悟”
禅宗认为,这种“悟”在音乐中也同样存在;不仅是存在,而且是必需。北宋成玉磵《琴论》云:“攻琴如参禅,岁月磨炼,瞥然省悟,则无所不通,纵横妙用而尝若有余。至于未悟,虽用力寻求,终无妙处。”这里表达了两点意思:一是弹琴作乐与参禅修道具有同构性,即遵循着相同的道理,所以两者相通。二是弹琴作乐同参禅修道一样,重点在“悟”,“悟”则一通百通,不“悟”则用力也难求。“悟”在音乐活动中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枢纽,缺了它就不可能达至妙境。
1、音乐听赏与“悟”
这种“以心印心”“心心相印”的“悟”,正是音乐欣赏的奥秘所在。在音乐的欣赏活动中,作者和听者通过音响的中介发生心的交流,当这种交流达到高度契合时,听者便会超越音响的形式,与作乐者发生直接的心的共鸣与默契。这个现象在中国古代早已为人们所觉知,较为著名的例子便是东晋时桓伊与王徽之“邀笛”的故事:“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10]聆听笛音,而无需一言,只有心与心的相互契合。这个状态很像禅宗的“以心印心”。另如伯牙与子期的故事:“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琴!巍巍乎若泰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吕氏春秋·孝行览》)说的也是一种“以心印心”“心心相印”。
同样,在禅师们那里,也时有这类论述。宋永明智觉禅师《宗镜录》云:“丝竹可以传心,目击以之存道。既语默视瞬皆说,则见闻觉知尽听。苟能得法契神,何必要因言说。如琴中传意于秦王,脱荆轲之手,相如调文君之女,终获随车,帝释有法乐之臣,马鸣有和罗之技,皆丝竹传心也。”[11]既然音乐“可以传心”,能够“得法契神”,则语言就成为多余的了。他连续举了宫人漏月鼓琴传意于秦王而得逃脱、司马相如以琴传情于卓文君而成眷属、帝释使乐神紧那罗歌咏于世而法得以演、马鸣作妙伎乐赖吒和罗而感动众人等四个故事,①四个故事的详细内容参见皮朝纲《禅苑绽新葩:禅宗音乐美学探讨的理论问题》,《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说明音乐的“传心”功能。晚清朱敏文为《枯木禅琴谱》所写《序》中,亦有一段湖中赏乐的记载:
吾乡云闲上人,以琴名一世,自余家居时已相往来。……光绪丁亥访余于武林,为鼓《高山》《流水》之曲,空灵幽恠,莫可名状。时浦城祝安伯太守、震泽王梦澂大令、长白文济川柏研香两协戎、杏襄侯游戎,皆善琴,闻上人名,愿一见。余谓上人曰:“师与我湖上移情可乎?”上人笑曰:“诺。”爰与诸君子徜徉六桥三竺间,每抚弦动操,朝烟夕月,别有神韵。自是月必一晤,晤则琴歌竟日,神契益深。
岁戊子,余奉檄入都,上人偕往,操南音于北风。居数月,赏音寂然。自非上人秉志冲淡,几乎作安道碎琴想矣!先是祝安伯太守酷嗜上人雅音,拟结琴社于金牛湖上。事未及行,而庚寅冬余以忧去浙,安伯、济川、襄侯又相继下世,不胜坠雨秋蒂之感。[12]
这虽然只是一段叙事,但也反映了禅师们对待音乐的基本观念。从丁亥到戊子,也就一年时间,但他们听音乐的状态已完全不同。前一年聆听琴曲,还是“空灵幽恠,莫可名状”“每抚弦动操”“神契益深”。这正是作乐人与听乐人的“以心印心,心心相印”,是人们面对音乐时的高峰体验状态。但只是过了一年,情况便全然不同,接二连三的变故改变了作者的心境,失去听乐的心情,以前曾有的“心心相印”的机缘至此已杳然不再。这从反面说明了“以心印心”的机缘之为难得。前述伯牙与子期的故事,子期为伯牙之知音;后“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吕氏春秋·孝行览》),即说明了“知音”的重要。而在禅师们那里,这样的思想也常能见到。韶州后白云和尚就曾为“伯牙虽妙手,时人听者稀”[13]而感叹;另有学人问或庵禅师:“我有没弦琴,久居在旷野。不是不会弹,未遇知音者”,说明只有面对“知音”,弹琴才有意义。接着又问:“知音既遇,未审如何品弄?”或庵禅师的回答是:“钟作钟鸣,鼓作鼓响。”[14]意思是,不要作任何人为的“摆布”,完全按你的“本心”来弹就行。说明“知音”的实质就是“心心相印”,就是心与心的互相感应与契合。
2、音乐传承与“悟”
不仅音乐的欣赏是“以心印心”,音乐的传承也同样如此。后来之人通过音乐以感知古人之“心”和“意”,并通过对此“心”此“意”的印合,才得以成就其源远流长的传统。无论是弹奏古曲还是听赏古乐,都必须循其音声而又能够超越它,进而感其心、会其意。北宋僧人琴家则全都特别强调弹琴要把握古人“用意”,认为“用意”是古人处理节奏的根据:“一曲之中,想古人用意处,抑扬高下,而取与之。此节奏之要也。”为则全《节奏指法》作序者也持同样的看法:“盖古人好琴不在多,但一操得意而已。能听之者,令再三弹此一曲,方识古人用意处。近时听琴便欲热闹堪听,不得已杂以筝琶羯鼓之音,贵其易入耳,以取一时之美听,全失古意,岂不叹哉?”在此,“古意”即古人之“意”,是音乐音响节奏背后的精神和灵魂,它源于心,而存于乐。后人以乐显之,以心印之,以至代代相传,是即为音乐文化与美学传统之延续。另如梅尧臣《赠琴僧知白》诗,也强调声之妙不可传,而“古意”却可传:“上人南方来,手抱伏羲器。颓然造我门,不顾门下吏。上堂弄金徽,深得太古意。清风萧萧生,修竹摇晚翠。声妙非可传,弹罢不复记。明日告以行,图兴江海思。”[15]常识告诉我们,琴之“声”是可以传的,因为它有形,可以记,可以学;而琴声之“妙”是无形的,故“非可传”,它只是弹琴人以自己的心灵、感觉和性情所镕铸出来的。相比之下,琴声中的“古意”也是无形的,因而也是“非可传”的,即不能以通常的方式例如语言相传,但知白的琴声却做到“深得太古意”。这“古意”是如何得到的?在禅宗看来,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以心印心”,以己之“心”去“印”古人之“心”,通过“心心相印”实现“以心传心”。大䜣禅师说:“鼓琴由艺进,读书以学博。过耳音不留,空言亦奚托! 千古会吾心,于焉有真乐。雨过晚凉生,临池看鱼跃。”[16]“千古会吾心”,就是以心印心,以心会心,使得相隔千年之心能够隔空相传。他特别强调,这样以心会心、印合千古之心的音乐,才是“真乐”,即真正的音乐。
当然,传统并非永远不变,音乐的精神也并非全然相同。说到底,传统之所以值得重视,正是因为它有生命,它会生长、变化,是一个“活”的东西。永远不变即意味着僵化、死寂,只有不断变化才会形成无尽的活力。这活力从何而来?也是源于“以心印心”,正是后来不断与之相印的“心”,才能为之注入新鲜的“活水”。释空尘《枯木禅琴谱·自序》云:“始悟琴旨,各禀性灵,庄生所谓:‘意之所随,不可以言传’。盖节奏板拍,可以传授;取音用意,各随人心。昔宓子鸣琴,化及单父;仲氏鼓瑟,见拒圣门。千载之下,犹见其性情。”[5]14-15在禅宗看来,虽然每个人所秉持的佛性只有一个,但其体现佛性之“心”却各不相同,其佛性的具体体现亦各有特色。各以独特的个体之“心”去“印”曲中古人之“意”,其“意”才能不断地生长、创造,才能保证传统之河“活水”长流,才能始终保持其旺盛的活力。释空尘所说,弹奏古曲要能够“千载之下,犹见其性情”,这里的“性情”虽是以古人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是由后世弹者“激活”的,是由后世弹者的生命、精神和气质所“灌注”了的,也就是说,是后者以“心”相“印”的结果。
3、音乐之“悟”的身体化
禅宗着眼的人生,是行动的人生,而非纯粹知性的人生,所以特别重视身体感觉。悟就是伴随身体感觉的心理现象。
禅宗对于音乐,从来都是伴随着身体感觉和形象意味的。南朝释慧皎《高僧传》中有对音乐美感效应的描写:“夫音乐感动,自古而然。是以玄师梵唱,赤雁爱而不移;比丘流响,青鸟悦而忘翥。昙凭动韵,犹令鸟马踡跼;僧辩折调,尚使鸿鹤停飞。”这里说的是音乐能够感动大自然的万事万物,而且其感又是伴随着肢体性动作的。在描述音乐对人的影响时,则有:“动韵则流靡弗穷,张喉则变态无尽。故能炳发八音,光扬七善。壮而不猛,凝而不滞;弱而不野,刚而不锐;清而不扰,浊而不蔽。谅足以起畅微言,怡神养性。故听声可以娱耳,聆语可以开襟。若然,可谓梵音深妙,令人乐闻者也。”[17]作者充分认识到音乐的美感具有沦肌浃髓的效果。在禅宗看来,人的理性与感官本来就是相通的,所以,有理性之知,便随即也会有感性之觉出现;而作感性之觉的同时,也往往能够引发理性之知:两者实为一体而不二的。正是因为音乐具有身体化倾向,所以才能发挥深刻而又持久的作用。明代郑邦福在为《三教同声》所作的《序》中说:“琴之设,无非禁人之不正以归于正。咒为佛秘密语,虽不可以文字解,而其为教,亦欲慑群魔以归之正,此其意旨原不谬于圣人。况道流乎人,患不达先王作乐之本耳。达其本则触处泠然,无往非正性之具。即佛氏之风水树鸟,皆能说法;梵音潮音,皆属妙音:于琴理又何碍也?”[18]“先王作乐之本”即在“修身养性”,它作用于身、心两个方面。因为不脱离身体感觉,所以才有“达其本则触处泠然,无往非正性之具”之语,才有“慑群魔以归之正”的神奇力量。
注重身体化是因为禅宗的核心是“行”。慧能在讲到修行是否要读经时说:“经有何过,岂障汝念?只为迷悟在人,损益由己。口诵心行,即是转经。口诵心不行,即是被经转。”关键是“行”,没有“行”,经也会使人“迷”;落实到“行”,“悟”才会降临。所以,“行”才是禅宗的落实之处。“汝观自本心,莫着外法相。法无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见闻转诵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法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义,不在口争。”(《坛经·机缘第七》)因为最终落实于“行”,所以禅宗一刻不离身体,始终强调“体察”“体验”“体会”“体悟”。禅宗之“悟”就是“体悟”。禅宗大师常常用“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形容“悟”的状态,这饮水之冷暖就是伴随感性的知,一种身体性的觉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