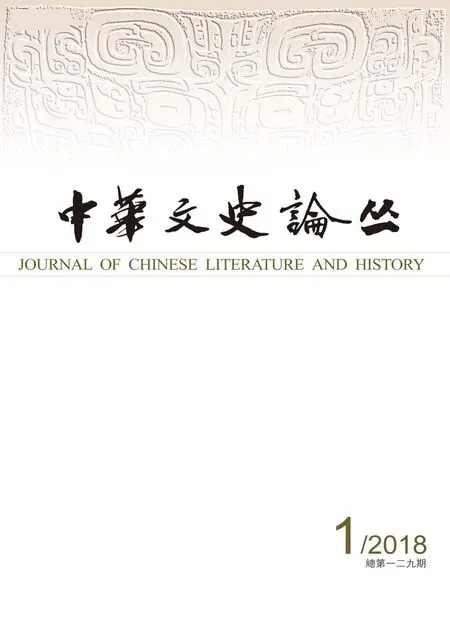朱子作《家禮》説祛疑
苑學正
朱子《家禮》是一部參酌古今、影響深遠的禮書。據朱子弟子記述,其書初步撰成即被竊亡佚,朱子逝世以後纔重現於世。在當時和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家禮》爲朱子所作並無爭議。元武林應氏《家禮辨》雖曾提出懷疑,但其論據十分薄弱,甚至有明顯錯誤,明丘濬已駁之。清王懋竑作《家禮考》、《家禮後考》、《家禮考誤》諸文,不僅對《家禮》成書亡現的有關記載予以否定,還對《家禮》的思想内容提出質疑。《四庫全書總目》采用王説,於是《家禮》非朱子之書幾成定論。但主張《家禮》爲朱子所作的聲音始終未絶,自清至今有不少學者對王説予以反駁,其中束景南先生《朱熹〈家禮〉真僞考辨》一文,考證《家禮》撰著成書和失而復得的過程尤爲詳實,使有關疑點涣然冰釋。不過學者們在反駁王説時,主要針對《家禮》的成書亡現等外部情況,而對思想内容分析用力較少,因而未能完全平息對《家禮》真僞的懷疑。近年彭林先生《朱子作〈家禮〉説考辨》一文即從思想内容方面伸張王説,將這一問題的討論引向了深入。本文沿着彭先生的思路,在對《家禮》成書亡現的相關研究加以概述和申説的基礎上,着重从思想内容方面對《家禮》作者問題進行探討。
一 《家禮》的成書與失而復得
有關《家禮》成書和失而復得的質疑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 《朱子年譜》所載《家禮》成書時間與朱子的相關言論不合。(二) 朱子文集、語録除《家禮序》外無一言提到《家禮》。(三) 陳淳所録朱子之語稱被竊之書爲《祭儀》,而非《家禮》。(四) 有關《家禮》重現於世的記載存在疑問。這些問題的提出,主要是因爲質疑者未能全面掌握相關材料,特别是對朱子本人言論的梳理考證不足,以致誤讀和輕疑朱子門人的相關記述。經過學者考辨,這些問題現已基本得到解決。這裏僅對相關考辨加以概述,對尚存歧見之處略加别擇,對考辨未盡之處略作申説。
(一) 《朱子年譜》所載《家禮》成書時間
《家禮附録》引李方子《年譜》云:“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家禮》附録,《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頁1。李方子《紫陽年譜》原本已佚,現存諸本多據李本累經修訂而成,一般在乾道六年庚寅(1170)下載“《家禮》成”一條,如王懋竑《朱子年譜考異》所引洪去蕪本即是。*王懋竑《朱子年譜考異》卷一,見《朱熹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313。這些記載本身存在一些問題,加之學者對朱子相關言論存在誤解,由此便對《家禮》的真僞産生了懷疑。
明丘濬《文公家禮儀節》引應氏《家禮辨》云:
文公先生於紹熙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云:“某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説,裁定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勉齋先生《家禮後序》云:“文公以先儒之書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爲《家禮》。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未及脱藳而先生没,此百世之遺恨也。”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姑以年月考之,宋光宗紹熙甲寅文公已於《三家禮範》自言“顧以衰病,不能及已”,豈於孝宗乾道己丑已有此書?況勉齋先生亦云“未及脱藁而文公没”,則是書非文公所編,不待辨而明矣。*丘濬《文公家禮儀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114),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頁435上—下。
按: 黄榦《家禮後序》所謂“未及脱藳”者,乃《儀禮經傳通解》,而非《家禮》。其誤丘濬、王懋竑皆已指出,*丘濬《文公家禮儀節》,頁435下;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59册,頁666上。而彭林先生《朱子作〈家禮〉説考辨》(下簡稱《考辨》)仍據以爲説,*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文史》2012年第3輯,頁365。蓋未細考也。至於《跋三家禮範》一條,錢穆《朱子新學案》云:“爲文各有體要,此《跋》乃爲亡友張敬夫之書而作,不必述及己之舊著。且其時《家禮》已亡失,又其書本非定本,尚欲有所增益改定,則正是此《跋》後幅所云云也。”*錢穆《朱子新學案》(四),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頁177。然則《跋三家禮範》所言不但與朱子嘗作《家禮》並不矛盾,反而適可相證。
王懋竑則對諸本《年譜》所載《家禮》成書時間提出了有力反證。其《家禮考》云:“按《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吕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説》往復甚詳。汪、吕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絶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説》爲言耶?”*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62上—下。按: 《祭儀》又稱《祭禮》,其書含《祭説》、《祭儀》、《祝文》三部分,行文不分綱目,是内容、體制均與《家禮》不同的另一種書。據束景南《朱熹〈家禮〉真僞考辨》,《祭儀》爲朱子早年所作,乾道五年(1169)至淳熙二年(1175)間,又經三次修改始成定稿。其間朱子與諸人往復討論,都只以《祭儀》爲對象,而未言及《家禮》。《家禮》當撰於淳熙二年至三年,諸本《年譜》將“《家禮》成”繫在乾道六年確實有誤。*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676—680。
值得注意的是,《家禮附録》所引李方子《年譜》並無“《家禮》成”之文。王懋竑謂“李公晦敍《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62上。未必符合李方子原意。上山春平《朱子〈家禮〉與〈儀禮經傳通解〉》認爲,《附録》所引《年譜》“開首的‘乾道五年九月’乃是指朱子母親去世之時,並不是指《家禮》成書的時期”。*上山春平《朱子〈家禮〉與〈儀禮經傳通解〉》,見吴震、吾妻重二主編《思想與文獻: 日本學者宋明儒學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56。陳來《朱子〈家禮〉真僞考議》也説:“所謂‘又推之於冠昏’本來也不即是説庚寅年即推之冠昏,‘又’即後來之意。”*陳來《朱子〈家禮〉真僞考議》,《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年第3期,頁117。按: 二家之説是也。李方子《年譜》原本雖佚,而真德秀嘗“剟其要”,見《西山讀書記》。真氏剟要缺乾道五年一條,而六年下亦無“《家禮》成”之文,但云:
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甲集卷三一,《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頁27。
考真氏剟要,凡當年有書撰成者,皆於該條首言“某書成”,然後乃述其原委;今既不首言“《家禮》成”,可知《家禮》不成於是年,其言“又推之於冠昏”云云乃預敍其事耳。疑此最近李方子本原貌,後來諸本增“《家禮》成”三字,乃因誤讀其文所致。王懋竑既以後來已誤之本爲據,又誤讀《家禮附録》所引,遂謂李方子所記與事實不合,而以爲朱子不曾作《家禮》之證,蓋考之未詳也。
(二) 朱子本人是否提到過《家禮》
王懋竑以《家禮》爲僞的一個重要理由是朱子本人未嘗言及《家禮》,其《家禮考》云:“文集、語録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62下。並認爲《家禮序》也是僞作。之所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爲王氏没有對朱子文集、語録進行充分爬梳和考證,遺漏了朱子有關《家禮》的自述。
夏炘曾舉出朱子言及《家禮》的一些證據,其《述朱質疑·跋家禮》云:
按文集、語録固無明言《家禮》者,然其輯《禮》之意,豈無言及者乎?葉味道録云:“問:‘喪祭之禮,今之士固難行,而冠昏自行可乎?’曰:‘亦自可行。某今所定者,前一截依温公,後一截依伊川。’”楊信齋《家禮附注》引朱子曰:“某定昏禮,親迎用温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是二條者雖不明言《家禮》,然所定者必有一書。今《家禮·昏禮》親迎用《書儀》,入門以後用伊川説,與葉、楊所記者合,然則所定者即指今所傳之《家禮》無疑矣。*夏炘《述朱質疑》卷七,《續修四庫全書》,95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78下—79上。
但陳來先生認爲:“夏氏此説過於武斷,因爲僅就‘某今所定’、‘某定昏禮’這兩句來説,也都可以是指朱子家中所行之禮,不必指爲一書。”*陳來《朱子〈家禮〉真僞考議》,頁120。按:“所行之禮”若非著之於篇,而只遇事臨時施行,殆非“定”之謂也。但葉賀孫所録在紹熙辛亥以後,時《家禮》已亡,不得言“今所定”。疑此乃單行之本,或如朱子《趙婿親迎禮大略》之類。至於《家禮附注》所引,今見於宋楊與立所編《朱子語略》,但其首句作“熹向定昏禮”,*《朱子語略》卷八,《元明刻本朱子著述集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27。則有可能是指《家禮》。
錢穆也曾舉出兩條證據。《朱子新學案》云:
《文集》卷三十三《答吕伯恭》有云:“熹今讀《易》,覺有味。又欲修《吕氏鄉約鄉儀》,及約冠昏喪祭之儀,削去書過行罰之類,爲貧富可通行者。苦多出入,不能就。又恨地遠,無由質正。然旦夕草定,亦當寄呈,俟可否然後改行也。”此書在何叔京卒後,爲淳熙乙未之冬,朱子年四十六。然則《朱子家禮》,似不在其居憂時作,至是亦尚未成編。又同卷《答吕伯恭》另一書云:“《禮書》亦苦多事,未能就緒。書成當不俟脱稿,首以寄呈,求是正也。”此書白田《年譜》定在丙申。《禮書》未能就緒,即承前引書而來,據此知朱子確是有意修《家禮》,而至是猶未成。*錢穆《朱子新學案》第四册,頁178—179。
束景南先生即據此考定《家禮》編撰時間。*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頁679—680。
不過陳來先生對此仍有異議,認爲:“此處所説‘及約冠昏喪祭之儀’是指約簡《吕氏鄉約鄉儀》中的冠昏喪祭之儀,下接所説‘削去書過行罰’也是針對鄉約而發,故修、約、削,都是指吕氏鄉約及鄉儀,是説要修改吕氏鄉約鄉儀,減去鄉儀中冠昏喪祭的儀節,去掉鄉約中書過行罰的條文,以使成爲貧富皆可以行的地方規約。”*陳來《朱子〈家禮〉真僞考議》,頁121。周鑫《〈朱子家禮〉研究回顧與展望》從之。*周鑫《〈朱子家禮〉研究回顧與展望》,《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433。按: 陳説恐非。《答吕伯恭》在“修吕氏《鄉約》、《鄉儀》”和“約冠昏喪祭之儀”之間有個表示並列的“及”字,説明兩者是互不包含的兩件事。其下“削去書過行罰”一語並不蒙“及”字爲文,與前兩者也非並列關係,而是對“修吕氏《鄉約》、《鄉儀》”的補充説明。之所以將“約冠昏喪祭之儀”插在中間,蓋因朱子“修吕氏《鄉約》、《鄉儀》”時,已確定要將其中本屬家禮範疇的冠昏喪祭之儀删去,另“約冠昏喪祭之儀”而别爲一書,只因事涉《鄉約》而兼及之。“約冠昏喪祭之儀”的“約”字是簡化之義,非删去之義。吕氏《鄉儀》中的冠昏喪祭部分只是原則性的論説,本身已極簡約,無需再作簡化。以朱子《增損吕氏鄉約》而言,除保留吊喪部分外,其餘冠昏喪祭之儀全部删去,恐非“約”之謂也。此外,《答吕伯恭》另一書稱所撰爲“禮書”,吕振宇《〈家禮〉源流編年輯考》認爲:“覈朱子所纂諸籍,與此‘禮書’特徵符同者惟有《家禮》。”*吕振宇《〈家禮〉源流編年輯考》,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3年,頁10。此説是也。考朱子文集、語録所稱“禮書”,皆指《儀禮》、《禮記》、《政和五禮新儀》、《儀禮經傳通解》等禮學專書;而《增損吕氏鄉約》乃所謂鄉規民約,雖亦間載鄉儀,但非專門言禮之書,難當“禮書”之稱。此“禮書”既非《增損吕氏鄉約》,則爲《家禮》無疑矣。
至於以《家禮序》爲僞,不過是因未見朱子作《家禮》的確證而强爲之説,並無實據,丘濬、上山春平、陳來等皆嘗辨之。國家圖書館藏元刻本《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十卷,其《序》後有清查慎行識語云:“此序原刻乃朱子手筆,後來翻刻模仿,漸失其真。”*楊復、劉垓孫《文公家禮集注》卷首,《中華再造善本·金元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頁4。按: 此識語無署名,然此本既爲查慎行舊藏,識語又略見於查氏《敬業堂文集·跋元板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後》,當即查氏所識。《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總目》等著録此本,皆云“查慎行跋”。此本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四著録爲宋刊本,亦云:“序文尚是朱子手書,……白田王氏以此序爲依仿《禮範跋語》者,由未見是本故耳。”*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四,《續修四庫全書》,926册,頁99下—100上。若如查、瞿之説,則《家禮》爲朱子所作就更無可疑了。
(三) 被竊之書是《祭儀》還是《家禮》
《朱子語類》卷九〇陳淳録云:“温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爲閑辭多,長篇浩瀚,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修《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朱子語類》卷九〇,《朱子全書》(17),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3049。王懋竑《家禮考》云:“陳安卿録云:‘向作《祭儀》、《祭説》,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説》而非《家禮》也明矣。”*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62下。按:“祭説”二字乃王氏妄增。然而此“祭儀”是指《家禮》中的祭禮部分,還是獨立的《祭儀》一書,確爲判斷《家禮》真僞的關鍵。
清顧廣譽較早注意到王懋竑所未見的陳淳《北溪大全集》中的幾篇《家禮》跋文,爲正確理解這段陳淳所録之語找到了鑰匙。其中《代陳憲跋家禮》云:
紹熙庚戌於臨漳郡齋,嘗以冠昏喪祭禮請諸先生。先生曰:“温公有成《儀》,罕見行於世者,只爲閑詞繁冗,長篇浩瀚,令人難讀,往往未及習行而已畏憚退縮。蓋嘗深病之,欲爲之裁訂增損,舉綱張目,别爲一書,令人易曉而易行。舊亦略有成編矣,在僧寺爲行童竊去,遂亡本子,更不復修。”*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一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68册,頁608下。
顧氏《四禮榷疑》卷一云:“案此與王氏所引《語類》一條同出安卿之手,而言之有詳略明晦。録第云‘祭儀’,跋則通謂四禮。恐録文有誤,自當以跋文詳且明者爲定。”*顧廣譽《四禮榷疑》卷一,《叢書集成續編》,11册,上海書店,1994年,頁995下。束景南亦云:“陳淳跋文所言《家禮》被僧童竊失,與陳淳語録所記相合,當即一事,證明王懋竑據陳淳録所作竊失之書爲《祭儀》之説,推斷錯誤。”*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頁683。按: 《語類》之所以只言“祭儀”而不言《家禮》,當是受具體語境的影響。上引陳淳所録之語並非全文,從其全文看,朱子這段話是從古人祭禮“甚繁且久”談起的,*《朱子語類》卷九〇,《朱子全書》(17),頁3048—3049。因此無需提及冠、昏、喪,只就祭儀討論即可,但這並不能説明亡失的只是祭儀。同爲陳淳所記,《代陳憲跋家禮》當是對實際情況更爲全面的反映。
這也可以從《祭儀》在當時的存世狀況得到佐證。顧廣譽就曾據陳淳《代陳憲跋家禮》所述“《祭儀》始得王郎中子正傳本三卷”,指出“後所亡者非此書”;*顧廣譽《四禮榷疑》卷一,頁995下。但其將陳淳於臨漳所傳《時祭儀》一篇混同於《祭儀》,以證《祭儀》未亡,*顧廣譽《四禮榷疑》卷一,頁995下。則猶未確。束景南《朱熹〈家禮〉真僞考辨》對此作了更加全面的考察,指出:“朱熹《祭儀》有多種定稿本,並寄張敬夫、吕伯恭、汪聖錫、陳明仲、王子正等,又《語類》卷九〇有輔廣録云:‘舊嘗收得先生一本《祭儀》……’知《祭儀》曾廣爲贈送。”“如《祭儀》被竊,還可就張、吕、汪、陳、王、輔處抄回,絶不至亡失不傳,大發感嘆。”*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頁680。當時《祭儀》傳本甚多,流佈甚廣。在朱子生前,吕祖謙《家範》就已引用《祭儀》,參陳來《朱子〈家禮〉真僞考議》;*陳來《朱子〈家禮〉真僞考議》,頁121—122。朱子死後,陳淳《代陳憲跋家禮》亦據所得王子正傳本而言其内容、體制。*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一四,頁608下。陳淳《釋家君録忌説》還載有其父所録朱子《祭儀》忌日一條,時間在慶元己未(五年,1199),*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一二,頁598上—下。即朱子逝世的前一年。可見從《祭儀》修成到朱子逝世,其書始終未亡,則陳淳録所云被竊亡失之書絶非指《祭儀》,而是指包括祭禮在内的《家禮》。
(四) 《家禮》的重現於世
關於《家禮》的重現於世,不少朱門弟子都有記述。《家禮附録》載: 黄云:“先生既成《家禮》,爲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未嘗爲學者道也。”陳淳云:“嘉定辛未歲,過温陵,先生季子敬之倅郡,出示《家禮》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録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楊復云:“《家禮》始成而失之,不及再加考訂,先生既没,而書始出。”*《家禮》附録,《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頁1。
王懋竑對《附録》所載諸弟子之説的可靠性表示懷疑,其《家禮後考》云:“其述黄子耕、陳安卿語,他無所見,或有所增損改易,未可知也。”*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64上。這自然是因王氏未見陳淳文集的緣故。束景南云:“《家禮》後附陳淳語,與陳淳跋文相同,證明其出自陳淳跋中,《家禮》所附各家語絶非僞造。”*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頁683。
彭林先生則質疑諸家之説不盡一致,其《朱子作〈家禮〉説考辨》云:“如《家禮》始見於何時?楊復等稱始出於‘先生易簀’,陳淳則説初見於‘先生葬日’。朱子易簀在三月甲子,葬日在冬十一月壬申,相去何其之遠!”*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64。按: 此係誤解文意所致。黄、楊所云“先生易簀,其書始出”,“易簀”即死之代稱,“始”猶“纔”也,言朱子殁後其書纔重現於世,這與陳淳所述“葬日攜來”之説並不矛盾。《考辨》將“先生易簀,其書始出”解爲“始出於‘先生易簀’”,顛倒了語序,“始”就成了“初”的意思,文意大變。
綜上所述,《家禮》撰作、被竊和復出的過程歷歷可考,其爲朱子所作並無可疑。《考辨》認爲:“持朱子作《家禮》説者,大多回避應氏與王懋竑之質疑,而强調朱門弟子不以《家禮》爲僞,則其書必不僞。鄙見,以朱門態度爲是非,乃以‘情感’爲判據,而非盡出學術,作用有限。作爲反證,若以情感論,王懋竑何嘗非朱子學營壘中人!”*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67。此説不但迴避了學者對應、王二氏的有力反駁,而且將朱子弟子的如實記述歸爲對朱子的“情感”,殆非通論。即使朱子門人是基於情感來看待《家禮》,也應該和王懋竑采取同樣的態度,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而没有理由將一部未曾耳聞的書歸於其師名下。陳淳、楊復等人明知《家禮》存在不當之處,仍篤信其爲朱子之書,説明他們確有所據。比如陳淳曾親聞朱子有《家禮》之作,朱子殁後又聞其子朱在言及此書,兩者若合符契,絶非出於“情感”的盲目性。
二 從思想内容上判斷《家禮》真僞的標準問題
王懋竑不僅對《家禮》成書、亡失和重現的相關記載表示懷疑,還舉出《家禮》的錯謬之處四十六條,力圖從思想内容上論證《家禮》爲僞。彭林先生《朱子作〈家禮〉説考辨》也認爲“内證是判定真僞之關鍵”,*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67。並在王氏《家禮考誤》的基礎上進行歸納,間出己説,分十個方面辨《家禮》之誤。在辨誤之前,《考辨》先定下了判斷《家禮》真僞的四條基本原則:“其一,不悖逆《儀禮》主旨。”“其二,優於《書儀》。”“其三,無禮學常識錯誤。”“其四,不悖逆時勢。”*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68,369。這些原則固然有一定的道理,《考辨》也舉出了支持這些原則的證據,問題在於有絶對化的傾向,未免膠柱調瑟。
首先,王、彭二家所訂立和遵循的這些原則預設了一個前提,即朱子是一個從來不會出錯的完人,只要出錯就不是朱子的著作。然而這在邏輯和事實上都不能成立。朱子一生的思想是不斷發展的,他的許多著作都屢經修改。就其禮學來説,在深衣制度、時祭卜日、祭始祖先祖等問題上,朱子均曾否定過自己過去的觀點,並不認爲自己永遠都是正確的。況且《家禮》作於朱子中年,黄榦《朱先生行狀》稱“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黄榦《勉齋集》卷三六,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68册,頁427下。則其書原非定本。簡單以思想内容的是非對錯來判定真僞,未必符合朱子禮學思想發展的實際。
其次,這四條原則本身具有片面性,不完全符合朱子的禮學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 朱子尊《儀禮》,但不拘於《儀禮》。
《考辨》舉出不少朱子尊崇《儀禮》的證據,卻忽略了其不拘泥於《儀禮》的論述,而後者更是不勝枚舉。姑舉一例,《朱子語類》卷八九云:“恐怕《儀禮》也難行。……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已是厭周文之類了。某怕聖人出來,也只隨今風俗立一個限制,須從寬簡。”*《朱子語類》卷八九,《朱子全書》(17),頁3002。按:“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煩”,疑是。《考辨》還舉朱子修《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經作爲證據,但朱子以《儀禮》爲經,只是將它作爲禮制源頭加以參考,並非直接用於當世。《朱子語類》卷八四云:“問:‘所編《禮》今可一一遵行否?’曰:‘人不可不知此源流,豈能一一盡行?後世有聖人出,亦須着變。’”*《朱子語類》卷八四,《朱子全書》(17),頁2886。又卷八九云:“古者之禮,今只是存他一個大概,令勿散失,使人知其意義,要之必不可盡行。”*《朱子語類》卷八九,《朱子全書》(17),頁3013。
朱子認爲古禮中冠昏二禮相對可行一些,但也並非完全照搬。如《考辨》引朱子語云:“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是依《儀禮》,只是各改了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68;引文見《朱子語類》卷八九,《朱子全書》(17),頁3000。此條看似固守《儀禮》,其實不然。朱子在批評二家所定昏禮廟見時間不合《儀禮》後,自己也對《儀禮》三月廟見的規定作了改動,云:“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舅姑,第三日廟見,乃安。”*《朱子語類》卷八九,《朱子全書》(17),頁3001。
《考辨》意識到朱子並不拘泥於《儀禮》的儀節度數,所以强调朱子“不悖逆《儀禮》主旨”“不違背《儀禮》禮義”。但在實際考辨過程中,往往用《儀禮》的具體儀節來要求《家禮》,一有不合,輒指爲僞書之證,而對朱子本人的有關論述卻多有忽略。《考辨》所列第三條原則“無禮學常識錯誤”也有同樣的問題。其文未對“禮學常識”這一概念作出界定,但從所舉證據看,仍然是以《儀禮》爲本,與第一條原則没有本質區别。而“常識”比“主旨”或“禮義”更加寬泛,也更容易將古禮中不適用於朱子時代的儀節度數包含進去,這就與朱子不拘泥《儀禮》的禮學思想相違背了。
2. 朱子對《書儀》有所增損,但以繼承爲主。
《考辨》認爲:“朱子於《書儀》是非得失,了然於胸,故若有所作,必不當重複其錯誤。”“若《家禮》爲朱子手作,當後出轉精,不重複其誤,或出現温公《儀》不誤而《家禮》反誤者。”*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69。此説的合理成份是,朱子確實對《書儀》有過一些批評,這些批評理應反映在其自撰的禮書中。問題在於,朱子認爲《書儀》哪些地方有誤,《家禮》應該修正《書儀》的哪些地方,應以朱子本人的觀點爲準,而不應以後代學者的觀點爲準。换言之,“優於《書儀》”的原則應該限定在朱子確曾作出的批評範圍内,而不應濫用到朱子未曾批評的地方。事實上,朱子批評《書儀》之處,如昏禮廟見時間、喪服兼用古今之制、神主尺寸等,在《家禮》中都得到了體現。而王、彭二家所指《家禮》重複《書儀》之誤之處,往往不見於朱子平日所論,而是出於王、彭二家自己的理解。即使這些理解是正確的,也未必符合朱子當時的認識,這就將“優於《書儀》”原則的適用範圍擴大化了。
朱子對《書儀》的修正是很有限的。其《答蔡季通》云:“《祭禮》只是於温公《儀》内少增損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四,《朱子全書》(22),頁1997。《朱子語類》卷九〇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者減卻幾處。”*《朱子語類》卷九〇,《朱子全書》(17),頁3048。可見朱子對《書儀》的態度以繼承爲主。《考辨》片面强調朱子對《書儀》個别地方的批評,並將它擴大化,難免得出不盡允當的結論。
3. 朱子制禮不脱離實際,但也不一味徇俗。
《考辨》認爲:“《家禮》所載冠昏喪祭諸禮,意在普及於民間,若果爲朱子所作,必不能脱離生活現實,提出不切實際之要求。”*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70。竊以爲,朱子固然有隨俗從宜的一面,但也强調不可一味徇俗。其《答劉平甫》云:“泥古則闊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主張“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〇,《朱子全書》(22),頁1796。《朱子語類》卷二三云:“今人於冠婚喪祭一切苟簡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又如何責得它違與不違?古禮固難行,然近世一二名公所定之禮,及朝廷《五禮新書》之類,人家儻能相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爲無補。”*《朱子語類》卷二三,《朱子全書》(14),頁821。《考辨》在一些具體儀節上往往以《儀禮》爲準繩,而在一些根本性問題上卻片面强調“生活現實”,例如質疑《家禮》推行“早已失去根基”的宗法制度等,明顯與朱子的主張不符。
總之,這四條原則不是直接用朱子本人的禮學思想來判斷《家禮》真僞,而是用《儀禮》、《書儀》、宋代禮俗等外在標準來衡量《家禮》,算不上真正的“内證”,由此得出的結論也就難以令人信服。既然要解決的問題是《家禮》是否爲朱子所作,那麽根本標準就應該是朱子本人對相關問題的論述,《儀禮》、《書儀》、宋代禮俗都只能作爲參考,而不是決定性條件。
三 《家禮》思想内容相關質疑考辨
《家禮》爲朱子中年所作,又是未定之本,存在一些不盡合理之處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學者在反駁《家禮》非朱子所作之説時,主要解決的是《家禮》成書與失而復得等外部問題,而對王懋竑《家禮考誤》(下簡稱《考誤》)所舉思想内容上的問題關注較少。但這不意味着《家禮》真如王、彭二家所説的那樣謬誤百出。二家以思想内容的是非來判斷《家禮》真僞,不僅立論的前提和標準存在問題,在具體論證中也有不少錯誤,從而將《家禮》的疑誤之處擴大化了。下面就以《家禮》與朱子禮學思想的關係爲中心,從四個方面對二家的質疑進行考辨,以期爲解決《家禮》作者問題提供更多的内在依據。
(一) 《家禮》對《儀禮》宗法制度的繼承與發展
王、彭二家用《儀禮》來考察《家禮》,卻往往忽略朱子禮學思想與《儀禮》的不同,這突出地表現在對《家禮》宗法制度的批評上。彭林先生認爲“《家禮》最大之問題”是“虚擡宗法”,其理由有三: 一是“《家禮》以宗子主冠禮,昏禮以及祠堂之祭等……違背《儀禮》制度”,“《儀禮》冠、昏、喪、祭之禮,主人皆爲父或祖”。二是《家禮》冠昏由繼高祖之宗子主禮,殊違情理。三是“宗法與宗廟本爲一體,後世宗廟已罕見其存”。*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70,371。但這三條理由都不是以朱子本人的宗法思想來作判斷,與“《儀禮》主旨”也不盡相符。
1. 《家禮》以宗子主冠昏祭禮符合《儀禮》制度。
首先需要説明的是,《家禮》並非處處皆以宗子爲主,一般來説,只有在祠堂或祠堂的替代場所舉行的儀式纔以宗子爲主。*按: 《家禮·冠禮》先告於祠堂,之後主要儀節則在廳事舉行,禮畢復見於祠堂。此廳事實爲祠堂的替代。類似做法古已有之,如《宋書·禮志一》:“《禮》冠於廟。魏以來不復在廟,然晉武、惠冠太子,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也。晉穆帝、孝武將冠,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335。《書儀·冠儀》也説:“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於廟,故冠亦在廟。今人既少家廟,其影堂亦褊隘,難以行禮,但冠於外廳,笄在中堂可也。”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42册,頁468下。《家禮·祭禮》亦先告於祠堂,然後奉主於正寢祭之,祭畢復納主於祠堂,與冠禮類似。《朱子語類》卷九〇云:“欲立一家廟,……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朱子全書》(17),頁3038—3039。可與《家禮》相證。由於在廳事或正寢行禮等同於在祠堂行禮,故其主禮之人皆與在祠堂者無異。以下爲了論述方便,一般統以祠堂言之。如《昏禮》“議昏”章:“凡主昏,如《冠禮》主人之法,但宗子自昏則以族人之長爲主。”*朱熹《家禮》卷三,《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頁1。“納采”章:“主人具書。”注云:“主人即主昏者。……若族人之子,則其父具書,告於宗子。”又云:“夙興,奉以告於祠堂。”注云:“若宗子自昏則自告。”*朱熹《家禮》卷三,頁2。按: 具書不在祠堂,故可以族人爲之;奉書告於祠堂則宗子之事,雖族人之長不得主焉。又如《喪禮》“立喪主”注云:“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以奉饋奠。其與賓客爲禮,則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朱熹《家禮》卷四,頁1。“祔”章云:“按此謂繼祖宗子之喪,其世嫡當爲後者主喪,乃用此禮。若喪主非宗子,則皆以亡者繼祖之宗主此祔祭。《禮》注云:‘祔於祖廟,宜使尊者主之。’”*朱熹《家禮》卷四,頁48。按: 饋奠等事隨尸柩及靈座所在,當於正寢,故以親者主之;祔祭則在祠堂,故以宗子主之。
《家禮》以宗子主冠、昏、喪、祭中行於祠堂之禮,是符合《儀禮》制度的。《儀禮》冠、昏、喪、祭均體現了宗子主禮的原則。
先説祭禮。《儀禮·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於主人之南。”鄭玄注:“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儀禮注疏》卷四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343。然則《特牲饋食禮》之主人即宗子也。《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祝皆曰“孝孫某”,其中的“孝”字,就是宗子身份的標誌。《禮記·曾子問》“稱名不言孝”鄭玄注:“孝,宗子之稱。”*《禮記正義》卷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805。實際上,宗子主祭是普遍性原則。《禮記·大傳》:“庶子不祭,明其宗也。”鄭玄注:“明,猶尊也。一統焉。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禮記正義》卷四四,頁1363。即使庶子當祭,亦須以宗子爲主人,如《禮記》:“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禮記正義》卷二七,頁800。《考辨》謂祭禮之主人爲“父或祖”,不知所祭對象本不固定,主人是其何親亦隨之而變,一般來説當爲所祭之祖的嫡子嫡孫,對其餘子孫而言即爲宗子。即使子先父而亡,主祭者也未必是其父。《禮記·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鄭玄注:“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禮記正義》卷四二,頁1302。然則庶子之子爲殤而從祖祔食,其父不得主其祭,而由宗子主之。《家禮》以宗子主祠堂之祭是完全符合禮經的。
喪禮除祔祭外,其喪主可能是死者之子孫、父祖、兄弟、族人等,未必是宗子。但鄭玄《三禮目録》以《儀禮·士喪禮》所載爲“士喪其父母”,*《儀禮注疏》卷三五,頁1043。則當以死者之嫡子爲主人,亦非《考辨》所謂“父或祖”。至於祔祭,則必宗子主之。《禮記·奔喪》:“凡喪: 父在,父爲主;父没,兄弟同居,各主其喪。”鄭玄注:“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祔則宗子主之。”*《禮記正義》卷六三,頁2147。蓋祔祭在廟,而庶子無廟,故不得自主之,此與尋常吉祭無異。庶子既不得主其妻、子之祔祭,其餘親之祔祭當亦然。《禮記·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鄭玄注:“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禮記正義》卷四三,頁1335。又《雜記上》:“主妾之喪,則自附(袝),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鄭玄注:“祔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禮記正義》卷五〇,頁1599—1600。以《奔喪》注例之,此二篇主祔祭者當皆指宗子而言。蓋祔祭以尊祖爲主,故以宗子爲主人;其餘諸節以哀死爲主,故以親者爲主人: 二者行禮對象不同,固不必爲一人。《家禮》以死者長子爲喪主,以死者繼祖之宗子主祔祭,皆與《儀禮》、《禮記》合。《考誤》批評《家禮》以繼祖之宗子主祔祭,以至於妄疑鄭注,謂“祔則舅主之,其爲宗子與否,則未有明據也”,*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74下。不但將祭主與喪主相混,而且與“支子不祭”的原則相違。
王、彭二家批評的重點是冠昏,其依據主要是鄭注賈疏。《儀禮·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鄭玄注:“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儀禮注疏》卷一,頁5。又“筮於庿門”賈公彦疏:“家事統於尊,若祖在則爲冠主。”*《儀禮注疏》卷一,頁4,5。又《士昏禮》:“主人筵於户西。”鄭玄注:“主人,女父也。”*《儀禮注疏》卷四,頁88。然禮經多據宗子之禮爲正,鄭玄以主人爲父,可能也只是就宗子之家而言,如上《喪服小記》、《雜記》之例。
考諸《儀禮》本文,其以宗子主禮之意也很明顯。如《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鄭玄注:“父兄,諸父諸兄。”又曰:“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於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鄭玄注:“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儀禮注疏》卷三,頁66。此孤子禮於阼,是爲嫡子,父殁即爲宗子。然則宗子冠即自爲主,雖有諸父諸兄,亦不得主之,但爲之戒宿而已。鄭玄注又言宗兄爲冠主,是謂庶子父殁,則不得自主其冠,而由宗兄主之。又《士昏禮·記》:“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没,己躬命之。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鄭玄注:“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弟,宗子母弟。”*《儀禮注疏》卷六,頁157—158。然則父母俱殁,宗子自昏即自命使者,庶子則稱宗兄之命,也體現了宗子主禮的原則。
以上皆就父殁之後而言,至於父在時,若其父爲庶子,是否可爲主人,經無明文,但其所載父之儀節辭令往往爲宗子專有之事。如《士昏禮·記》:“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鄭玄注:“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儀禮注疏》卷六,頁154。按: 《家禮·昏禮》醮辭與此略同,又云:“非宗子之子,則宗子告於祠堂,而其父醮於私室如儀,但改‘宗事’爲‘家事’。”*朱熹《家禮》卷三,頁6。據此,則《儀禮》“承我宗事”云云乃宗子之辭。《考誤》云:“支子不祭,而未嘗不與於祭,則亦有宗廟之事焉。支子之子,又别爲繼禰之宗,於宗事非無所與者矣。今認爲‘宗子’之‘宗’,而改曰‘家事’,其舛誤有如此者。”*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71下。按: 王説似是而非。此昏禮而言宗廟之事者,以昏禮有著代之義,子將代父爲宗子,而宗子祭時當有主婦故也。《禮記·祭統》:“既内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内之官也。”*《禮記正義》卷五七,頁1868。此“夫婦親之”,指主人主婦而言。至於支子,不必待有婦然後與祭,亦不必待父老然後與祭,則其娶婦之時固不必言及與祭之事,所謂“宗事”非支子與祭明矣。王氏蓋亦自知其説之不可通,故又以“支子之子,又别爲繼禰之宗”爲説,然《儀禮》言“承”,則其宗事非自其身始,乃承其父而來,若其父非宗子,則無宗事可承。此與《禮記·曲禮上》“七十曰老,而傳”相近,彼鄭玄注云:“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孔穎達疏:“然庶子年老,亦得傳付子孫,而鄭惟云謂宗子者,爲《喪服》有‘宗子孤爲殤’,鄭云:‘言孤,有不孤者,謂父有廢疾若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鄭今欲會成《喪服》義,故引‘宗子之父’也。又一云宗子,並謂五宗也。五宗之子並是傳祭之身,故指之也。庶子乃授家事於子,非相傳之事,此既云‘傳’,故鄭知非庶子也。必爲宗子父者,以經言‘傳’,傳者,上受父祖之事,下傳子孫。子孫之所傳家事,祭事爲重,若非宗子,無由傳之。”*《禮記正義》卷二,頁24,26—27。據鄭孔之説,惟宗子方可傳宗事於子,所谓“宗子之父”亦身爲宗子。《儀禮》“宗事”既承自其父,則其父爲宗子可知矣。孔疏云“庶子乃授家事於子”,即《家禮》所本,王氏未明其源也。
從禮義上説,冠昏行事於廟,有尊祖之意。《禮記·冠義》:“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禮記正義》卷六八,頁2271。《儀禮·士昏禮》“主人筵於户西”,鄭玄注:“筵,爲神布席也。户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禰廟也。”*《儀禮注疏》卷四,頁88。既然是爲了尊祖,自然應該由宗子主禮。《禮記·喪服小記》:“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鄭玄注:“宗者,祖禰之正體。”*《禮記正義》卷四二,頁1299。庶子非祖禰之正體,若在祖禰廟中主禮,將多所滯礙。如《儀禮·士冠禮》:“主人玄端、爵韠,立於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袗玄,立於洗東,西面,北上。”鄭玄注:“兄弟,主人親戚也。……位在洗東,退於主人。不爵韠者,降於主人也。”*《儀禮注疏》卷二,頁34—35。假使以庶子爲此主人,升降皆由宗子之阼階,而使宗子列於堂下,退於庶子,恐非尊祖敬宗之義。
由此而言,《儀禮·士冠禮》、《士昏禮》主謂宗子之子冠昏之禮,鄭玄注以主人爲將冠昏者之父,自不妨其兼爲宗子;若庶子之子冠昏,非其正例,是否也以父爲主人,是很成問題的。況且《家禮》冠昏行於高祖祠堂,與《儀禮》行於禰廟者又不相同,更不能照搬鄭注了。
2. 《家禮》冠昏所體現的宗法制度與朱子宗法思想相合。
《家禮》冠昏不但由宗子主禮,而且一般是由繼高祖之宗子主禮,這是與《儀禮》最大的不同。《家禮·冠禮》:“主人,謂冠者之祖、父自爲繼高祖之宗子者。若非宗子,則必繼高祖之宗子主之;有故,則命其次宗子若其父自主之。若宗子已孤而自冠,則亦自爲主人。”*朱熹《家禮》卷二,頁1—2。其昏禮行於祠堂諸節亦如之。《考誤》云:“《士冠禮》鄭注云:‘廟,謂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蓋冠於禰廟,故以親父兄主之。……今《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於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矣。”*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68上—下。按:“者之”,原作“之者”,據《儀禮》鄭注改。按: 王氏雖意識到《家禮》冠昏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與其行於高祖祠堂有關,但忽略了行於高祖祠堂與朱子廟制及宗法思想的一致性,仍未擺脱《儀禮》的桎梏。
朱子所主張的廟制與古禮有很大不同。據《禮記·祭法》,不同等級的人所祭世數不同,所立廟數也隨之而異。一般來説,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親廟皆有四,祭高祖以下四世;大夫三廟,祭曾祖以下三世;《儀禮》冠昏皆士禮,而士只能祭祖、禰二世,或二廟,或祖禰共廟。*《禮記正義》卷二三,頁1793。朱子則用程子之説,主張無論廟數多少,皆得上祭四世。其《答汪尚書論家廟》云:“然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〇,《朱子全書》(21),頁1310。朱子即用同堂異室之制,立高祖以下四世之廟。《朱子語類》卷九〇云:“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朱子語類》卷九〇,《朱子全書》(17),頁3038—3039。既作四龕堂,則是祭及高祖也。《家禮》祠堂之制與此完全相合。《考辨》以“後世宗廟已罕見其存”爲由質疑《家禮》,顯然與朱子之説相悖。
宗法與宗廟是密切相關的。按《祭法》所載廟制,大夫、士雖爲繼高祖之宗子,其家亦無高祖之廟,尋常亦不祭及高祖。然而此高祖可能是其族人的曾祖、祖乃至禰,其族人作爲庶子既不得自祭,宗子又毁其廟而不祭,則其族人連與祭於己之曾祖、祖、禰之廟的機會都没有,這就使得宗子不能充分發揮收族作用。而按照朱子廟制,四小宗家廟所奉祖先之數同其各自的宗法身份完全相符,繼高祖之宗子即四時常祭高祖以下四世,而其所統族人咸得與祭;不僅如此,若宗子易世,高祖當祧,而族人猶有親未盡者,則暫不祧毁,而是遷此高祖於最長之房,待親皆已盡乃終祧之,從而保證所有族人都有與祭於己之高祖的機會。*關於當祧之高祖是否可以暫遷於族人之家,朱子前後之説不同,此用其與《家禮》相合之説,詳下“高祖當祧,遷於族人之親未盡者”條。簡而言之,古之廟制不但受限於爵位,而且嚴於嫡庶;朱子廟制則打破了爵制的限制,並盡可能地縮小嫡庶差等,使之皆得廟事高祖以下四世,惟尚存主祭、與祭之别耳。這樣一來,朱子廟制就提高了高祖和繼高祖之宗子的收族功能和在宗族中的地位。《家禮》冠昏在高祖祠堂行禮,由繼高祖之宗子主禮,同這種新的廟制和宗法是相適應的。
冠昏之禮本不局限於小家庭内部,而是與宗廟、宗族有密切聯繫的典禮。即使在古禮中,其舉行場合也不一定在禰廟,而是儘量上及更遠的祖廟。如諸侯五廟,祭及始祖,諸侯本人及其子的冠禮也就在始祖廟舉行。《儀禮·士冠禮》“筮於庿門”鄭玄注:“庿謂禰廟。”賈公彦疏:“士於廟,若天子、諸侯冠在始祖之廟。”*《儀禮注疏》卷一,頁4,5。《説苑·修文》:“諸侯太子、庶子冠,公爲主,其禮與士同。冠於祖廟。”*向宗魯《説苑校證》卷一九,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483。然則《儀禮》冠昏之所以行於禰廟,乃因士禮爵位、廟數之限而不得不降殺。即便如此,其正式行禮前亦須有事於更遠之祖,乃至高祖。如《禮記·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爲庶人,冠、取妻者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鄭玄注:“赴,告於君也。”*《禮記正義》卷二八,頁849。孔穎達疏:“經云‘祖廟未毁’,謂同高祖。”*《禮記正義》卷二八,頁855。《左傳·昭公元年》孔穎達疏亦引《禮記》此文,且云:“既告君,必須告廟。”*《春秋左傳正義》卷四一,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2019中。然則士若與君同高祖,則冠、取妻當先告於其君之廟。又《禮記·昏義》:“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毁,教於公宫;祖廟既毁,教於宗室。……教成祭之。”鄭玄注:“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毁,則爲壇而告焉。”孔穎達疏:“鄭既不云大宗、小宗,則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至於教成告廟之禮,孔疏云:“若有卿大夫以下,則女主之宗子掌其禮也。……假令宗子爲士,只有父、祖廟,曾祖、高祖無廟,則爲壇於宗子之家而告焉。若與宗子同曾祖,則爲壇告曾祖焉;若與宗子同高祖,則爲壇告高祖焉。”*《禮記正義》卷六八,頁2280,2281,2282。然則士家嫁女,若與君同高祖,亦當先告於其君之廟;若高祖廟已毁,則告於宗子之廟,而宗子主之。孔疏謂“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蓋亦以高祖爲限也。《家禮》繼高祖之宗子之祠堂奉高祖以下四世,比古之大夫尚多一世,而與諸侯親廟之數相等,其繼曾祖之宗以下有冠昏之事先告於繼高祖宗子之祠堂,正猶古禮告於同高祖之君之廟或宗子之家。只是《家禮》更進一步,其後續正禮也在高祖祠堂的替代場所舉行,而由繼高祖之宗子主禮。《禮記·文王世子》、《昏義》等篇,可視爲《家禮》對冠昏舉行場所和主禮之人進行改革的歷史依據和邏輯起點。
在主觀上,朱子也有擺脱《儀禮》行於禰廟的限制而擴大到更遠祖廟的意向。《朱子語類》卷八九云:“昏禮廟見舅姑之亡者而不及祖,蓋古者宗子法行,非宗子之家不可别立祖廟,故但有禰廟。今只共廟,如何只見禰而不見祖?此當以義起,亦見祖可也。”*《朱子語類》卷八九,《朱子全書》(17),頁2998。按: 朱子將古之昏禮“只見禰而不見祖”歸因於“非宗子之家不可别立祖廟”的廟制之限,*按: 此言“但有禰廟”,則實爲繼禰之宗子,而言“非宗子之家”者,蓋對繼祖之宗子而言,鄭注《喪服小記》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是也。卻未否定非宗子之家見祖的内在合理性,因而在“今只共廟”的情況下,便主張將廟見的範圍擴大到祖。此“共廟”的具體形制並不清楚,是指祖禰共廟的同堂異室之制,還是指非宗子之家與其宗子共一祖廟,殊難分辨。但從上下文看,在“共廟”條件下“亦見祖”應該不是單就繼祖之宗子而言,而是兼指嫡庶。“今只共廟”與上文“非宗子之家不可别立祖廟”相對,兩者應有共同的討論對象,即“非宗子之家”;且其言“只”,則是無論嫡庶都只如此,而不獨繼祖之宗子爲然也。因此,無論“共廟”是指非宗子之家别立祖廟而祖禰共廟,還是指非宗子之家與其宗子共一祖廟,*這兩種廟制在當時都有實例,前者如朱子弟子李堯卿云:“某往年與先兄異居,不知考禮經,輒從世俗,立家先龕子。”又云:“某家中既有家先,上闕高祖之祭,下無禰祭,於心實不安。”然則堯卿雖爲支子,卻立高祖以下四世之龕。見朱子《答李堯卿》,《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七,《朱子全書》(23),頁2704。後者如《朱子語類》卷九〇云:“吕與叔謂合族當立一空堂,逐宗逐番祭。亦杜撰也。”見《朱子全書》(17),頁3043。兩者相較,前者似更常見。至少都具有這樣的基本要素,即非宗子之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擁有自己的祖廟,從而獲得了見祖的理由和便利。《家禮》是建立在宗法基礎上的,其祠堂之制未必與所謂“共廟”相合,但也與古之廟制不盡相同。其高祖祠堂雖設於繼高祖之宗子家,由其職掌,繼曾祖之宗子以下不得另設,但當宗子易世時,高祖神主並不隨之祧去,而是暫遷於親未盡者之家,可見其高祖祠堂並非繼高祖之宗子所專有,而是所有有服族人所共有。這樣一來,《家禮》祠堂實際上也具備了“共廟”的基本要素,其繼曾祖之宗子以下冠昏之事,自然也可如“共廟”之制那樣行於高祖祠堂了。而按照宗法原則,行於高祖祠堂,自當由繼高祖之宗子主禮。
彭林先生又以《家禮》書名爲疑,其《考辨》云:“此書名爲《家禮》,自當以家爲主體,以父子、祖孫爲核心,此爲天理之自然,親情之體現。若以繼高祖之宗子爲核心,與禮之人物,每每涉及全族,則當名之爲《族禮》,庶幾可也。”*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72。按: 此説與朱子對“家”的範圍界定不合。蓋“家”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家比宗的範圍小,廣義的家則可以包含宗。《朱子語類》卷九〇云“一家有大宗,有小宗”,*《朱子語類》卷九〇,《朱子全書》(17),頁3042。又云“廣西賀州有一人家……見説其族甚大”,*《朱子語類》卷九〇,《朱子全書》(17),頁3043。又云“人家族衆”,*《朱子語類》卷九〇,《朱子全書》(17),頁3052。皆爲廣義之“家”。《儀禮經傳通解·家禮》中有《五宗》篇,亦以“家”統“宗”。若以狹義而論,古之冠昏須告於君或宗子之廟,喪祭二禮亦涉及五宗,皆不得謂之家禮矣;然朱子將《儀禮·士冠禮》、《士昏禮》收入《儀禮經傳通解·家禮》中,其《乞頒降禮書狀》亦有“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之語,*《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〇,《朱子全書》(21),頁929。可見涉及宗族與“家禮”之名並不矛盾。
3. 《家禮》具體儀節兼顧宗法與人情。
王、彭二家質疑《家禮》宗法制度的理由之一是違背人情。以冠禮爲例,《家禮·冠禮》:“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立於主人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朱熹《家禮》卷二,頁3。王氏《考誤》云:“夫繼高祖之宗,嫡長相承至於四世,則年高而分益卑矣,將冠者之父爲其伯叔祖行者有之,爲其伯叔父行者有之,即爲兄弟行,亦有長於宗子者也,乃令其僕僕然隨宗子之後,而竟不能以父之尊命其子乎?”*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69上。彭氏《考辨》亦以此爲《家禮》“殊違情理”之一端。但這一指責不僅不符合古代宗法制度的實際,也忽視了《家禮》相關儀節對行輩尊卑、父子親情的兼顧。
就古代宗法制度來説,宗子主禮,庶子爲長輩而隨宗子之後,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如《儀禮·特牲饋食禮》:“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於門外,西面。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於主人之南,西面,北上。”鄭玄注:“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儀禮注疏》卷四四,頁1343。此“宗子”就未必是長輩。《禮記·曾子問》:“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鄭玄注:“與宗子爲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孔穎達疏:“其昭穆異者,宗子雖祖、父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禮記正義》卷二七,頁801,804,805。然則鄭言“族人皆侍”,雖行輩高於宗子者,亦與子姓、兄弟同立於主人之南,是在宗子之下也。《特牲饋食禮》又曰:“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於堂下,如外位。”*《儀禮注疏》卷四四,頁1353。此於同姓但言“兄弟”,蓋略文也。以門外之位推之,族人行輩高於宗子者當亦從宗子之後而入。《家禮》將冠者之父從主人出入升降,與此無異,是完全符合宗法原則的。
王氏强调“以父之尊命其子”,當是根據《孟子·滕文公下》:“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孟子注疏》卷六上,十三經注疏本,頁2710下。但孟子此説與禮經不盡相符。《儀禮·士昏禮》母命女實有其辭,而《士冠禮》無父命子之辭。趙岐《孟子章句》云:“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孟子注疏》卷六上,頁2710下。此在《儀禮》,乃始加時賓之祝辭,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者是也,*《儀禮注疏》卷三,頁69。非父命子之辭。朱子云:“今看孟子考禮亦疏,理會古制亦不甚得,他也只是大概説。”*《朱子語類》卷九〇,《朱子全書》(17),頁3031—3032。於此亦可見矣。
其實《家禮》並非完全不顧人情。冠者之父立於主人之右,則當堂下序立之時,位在主人之上,表明其爲冠者之父;當堂上加冠之時,又介於其子與主人之間,體現了父子之親;“尊者少進,卑者少退”,亦足以表示對長輩的尊敬。這樣父與子、宗子與庶子、長輩與晚輩,都照顧到了,可説是比較合乎情理的安排。
總之,《家禮》的宗法制度雖與《儀禮》有所不同,但仍符合宗法原則,更重要的是符合朱子本人的宗法思想,是朱子對古代宗法制度繼承與發展的階段性成果。王、彭二家執《儀禮》以繩《家禮》,不僅忽略了朱子宗法思想與《儀禮》的差異,對《儀禮》的理解也不無可商,由此判定《家禮》爲僞,恐難成立。
(二) 《家禮》對《書儀》等後世禮俗的吸收
朱子《跋三家禮範》云:“熹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説,裁訂增損,舉綱張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三,《朱子全書》(24),頁3920。除司馬光《書儀》外,朱子對程頤等人禮説、《政和五禮新儀》及當時俗禮都有所肯定和遵循,並體現在《家禮》當中。而王、彭二家對此或忽視不論,或直接以《書儀》不合理爲由而謂《家禮》爲僞,完全不顧朱子本人的態度。實際上,《家禮》對後世禮俗的繼承吸收,往往可與朱子的相關論述相映證,而二家指爲不合理者也多屬從俗之宜,只是不同於《儀禮》罷了。
1.昏禮無問名、納吉、請期。
《儀禮·士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家禮》只保留其中納采、納徵、親迎三項,注云:“古禮有問名、納吉,今不能盡用,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朱熹《家禮》卷三,頁4。納幣即納徵也。《考誤》、《考辨》皆以此爲《家禮》非朱子所作之證。
按: 問名、納吉是與卜筮婚姻吉凶緊密相關的兩個程序。《儀禮·士昏禮》:“賓執鴈,請問名。”鄭玄注:“問名者,將歸卜其吉凶。”*《儀禮注疏》卷四,頁92。又“納吉”鄭玄注:“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於是定。”*《儀禮注疏》卷四,頁97。但在宋代,此二禮並不能真正實行。《朱子語類》卷八九:“曰:‘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朱子語類》卷八九,《朱子全書》(17),頁3000。此言“古人”如此,則朱子之時納采後並不以卜筮決定婚姻,那麽問名、納吉也就没有意義了。《書儀》雖存此二禮,然於“納吉”下自注云:“計納采之前已卜矣,於此告女家,以成六禮也。”*司馬光《書儀》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42册,頁475上。則在納采前的議婚階段就已占卜過了。故吕友仁、王立軍《宋代婚禮概述》説:“納吉之儀,在宋代純屬虚應故事。”*吕友仁、王立軍《宋代婚禮概述》,《殷都學刊》1991年第4期,頁35。《家禮》删此二禮,是順應當時禮俗的。
《家禮》無請期之儀,《考辨》認爲:“‘請期’也被删除,甚是無理。”*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80。然《家禮》“親迎”章云:“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朱熹《家禮》卷三,頁4。是女家必已先知其期。今《家禮》雖無請期之文,其事則不可省,恐怕並非簡單的“删除”。吕、王《宋代婚禮概述》認爲:“官方之禮和朱熹《家禮》都把請期并入納幣。”*吕友仁、王立軍《宋代婚禮概述》,頁35。此“官方之禮”當指《政和五禮新儀》。按《儀禮·士昏禮》:“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賈公彦疏:“婿之父使使納徵訖,乃下卜婚月。”*《儀禮注疏》卷四,頁98。據此,請期在納徵之後别日舉行,且須另備禮物。《政和五禮·庶人昏儀》則將納成(即納徵)、請期合爲一條,納成之後隨即請期,且不另備禮物。*《政和五禮新儀》卷一七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647册,頁788下—789上。《宋史·禮志十八》亦云:“士庶人婚禮,并問名於納采,并請期於納成。”*《宋史》卷一一五,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2740。不過《政和五禮》雖將二者合并,但仍有使者請期之文,而《家禮》則無一言及之,可能是將請期之事暗含於納幣時的賓主問答或書信往來之中。丘濬《文公家禮儀節》於納幣一節的婿氏具書和女氏答書中補入請期之事,*丘濬《文公家禮儀節》,頁484下—485上。或得《家禮》之意。當然,由於《家禮》原非定本,又前删問名、納吉皆有説明,而於請期獨無,也不能排除本有闕文的可能。
2.婦拜見夫之兄弟姊妹。
《家禮·昏禮》“婦見於諸尊長”注云:“還拜諸尊長於兩序,如冠禮,無贄。小郎、小姑皆相拜。”*朱熹《家禮》卷三,頁10。此婦有拜見夫之兄弟姊妹之禮,與古禮不同。《禮記·雜記下》:“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鄭玄注:“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禮記正義》卷五二,頁1689。《考誤》云:“夫叔嫂不通問,兄公與弟婦亦無相見之禮,故止於其前一過,不更特見。”*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72上。
按: 《家禮》此節用《書儀》之禮。《書儀·昏儀下》:“婦降西階,就兄弟姊妹之前,其長屬應受拜者少進立,婦乃拜之,無贄。拜畢,長屬退。幼屬應相拜者少進,相拜。畢,退,無贄。”自注:“今世俗小郎、小姑皆相拜。”*司馬光《書儀》卷四,頁478下—479上。據此,當時嫂叔相拜皆不爲嫌,《家禮》從之,未爲失也。
3.負版、衰、辟領。
《家禮》斬衰、齊衰之服有負版、衰、辟領(又叫適)三物,於小祥後去之,大功以下則無之。《考辨》云:“《家禮》作者以負、適、衰爲可拆卸之物,並視之爲喪服等差之標誌。黄以周云:‘……如無前衰、後負、左右分適,則衰不可着矣。前衰、後負、左右分適,所以固闕中之領也,非虚贅而可去之物也。’”又説:“司馬光《書儀》與《儀禮》一脈相承,五等喪服皆有衰、負、適,否則不成其服,故僅於總敍五服制度時論及負版、衰、辟領,其下諸服則不再涉及。《家禮》作者似不明於此,以有無衰、負、適區分喪服等次,殊失禮經本義。”*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73—374。
按: 《考辨》謂《書儀》五等喪服皆有此三物,非也。《書儀·喪儀二·五服制度》注云:“裴莒、劉岳《書儀》,五服皆用布,衣裳上下異,制度略相同,但以精粗及無負版、衰爲異耳。然則唐五代之際,士大夫家喪服猶如古禮也。”*司馬光《書儀》卷六,頁497上。又《喪儀五·小祥》注云:“今人無受服及練服,小祥則男子除首絰及負版、辟領、衰,婦人截長裙,不令曳地而已。”*司馬光《書儀》卷九,頁514上—下。據此,不但司馬光認爲負版、辟領、衰是可拆卸之物,用來表示五服等差,而且早在唐代就已如此,《家禮》不過沿襲舊制而已。
《考辨》所説負版、衰、辟領之制還與朱子之説相悖。《儀禮·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幅三袧。若齊,裳内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儀禮注疏》卷三四,頁1027—1030。《考辨》引黄以周云:“此記統言五服衰裳之制,故曰凡,則下文所記適、負、衰、衽,五服皆然。”*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72—373。但朱子並不認爲《喪服記》所載是通論五服的。《朱子語類》卷八九云:“《禮》只有父母服,他服並無,故今長幼服都無考。”*《朱子語類》卷八九,《朱子全書》(17),頁3006。按: 父母服,謂斬衰、齊衰也。此蓋據鄭玄注:“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儀禮注疏》卷三四,頁1030。言“孝子”,則是父母服也。《論語·鄉黨》:“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朱子《集注》:“負版,持邦國圖籍者。”*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朱子全書》(6),頁154。《或問》:“曰: 胡氏以負版爲喪服之在背者,此蓋記者釋上文‘式凶服’爲必重服有負版者乃式之也,然乎?曰: 未可知也。然禮家説大功以下無負版,恐亦或有此禮,姑存其説,以俟知者擇之。”*朱熹《四書或問》,《朱子全書》(6),頁785。朱子雖對《論語》“負版”的爲何物尚存疑慮,但對“大功以下無負版”之説則加以采信。《考辨》捨朱子之説不用而取黄以周之説,以求《儀禮》之義或可,以論《家禮》真僞則非其證矣。
4.婦人不杖。
《儀禮·喪服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賈公彦疏:“此亦謂童子婦人,若成人婦人正杖。”*《儀禮注疏》卷二八,頁865,869。並舉《喪大記》、《喪服小記》爲證。《禮記·喪服四制》“婦人、童子不杖”孔穎達疏與此説同。*《禮記正義》卷七〇,頁2354,2355。《家禮·喪禮》“成服”章注云:“凡婦人皆不杖。”楊復《附注》:“《家禮》用《書儀》服制,婦人皆不杖,與《問喪》、《喪大記》、《喪服小記》不同,恨未得質正。”*楊復、劉垓孫《文公家禮集注》卷五,頁5。《考辨》云:“楊復尚知婦人有杖,《家禮》作者竟然不知,此作者爲朱子?”*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75。
按: 楊復雖主婦人有杖之説,但並不以此懷疑《家禮》爲僞,反而指出《家禮》的依據。《文獻通考·經籍考十五》“朱文公家禮”條載楊復語,説《家禮》“有用先儒舊義,與經傳不同,未見於後來之考訂議論者,若喪服辟領、婦人不杖之類是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一八八,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602上。亦謂《家禮》别有所據。不過,楊氏認爲《家禮》係用《書儀》服制,又謂未見於後來之考訂議論,卻非事實。《書儀·喪儀二·五服制度》注中雖引《喪服傳》婦人不杖之文,*司馬光《書儀》卷六,頁497上。但未置可否。其“齊衰杖期”章云:“子爲嫁母、出母,報。”注云:“報爲母服其子亦同。”*司馬光《書儀》卷六,頁498上。然則《書儀》婦人亦杖。
《家禮》的依據其實是《政和五禮新儀》。《政和五禮·品官喪儀上》“成服”章注云:“童子、婦人不杖,不居廬,不著屝履。若嫡子,雖童亦杖;不能自杖,人執之。”*《政和五禮新儀》卷二一五,頁881下。其庶人喪儀同。*《政和五禮新儀》卷二一八,頁895上。此雖亦用舊文,但“童子不杖”有例外情況的説明,而“婦人不杖”無之,則是凡婦人皆不杖也。其書《序例·五服制度》列“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在齊衰杖期,而“嫁母、出母爲其子”則在齊衰不杖期,*《政和五禮新儀》卷二四,頁226上—下。也驗證了這一點。《家禮》“嫁母、出母爲其子”與此同。朱子雖然對《政和五禮》有些批評,但對其喪服制度卻持肯定態度。其《答葉味道》云:“今考《政和五禮》,喪服卻用古制,準此而行,則亦無特然改制之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八,《朱子全書》(23),頁2784。然則《家禮》用《政和五禮》服制,正是符合朱子之議論的。
5.握手。
《家禮·喪禮》“初終”章“陳襲衣”注云:“握手用帛長尺二寸,廣五寸,所以裹手者也。”*朱熹《家禮》卷四,頁4。又“侍者卒襲”注云:“乃襲深衣,結大帶,設握手。”*朱熹《家禮》卷四,頁6。但未言設之之法。《考辨》據《儀禮·士喪禮》及沈文倬先生考證指出: 握手由兩塊長尺二寸、寬五寸之布縫合而成,其中部經過削約,兩端各有一用以縛手之布帶;握手設於死者左手,右手尚需設“決”,兩者須經繫聯;上古男子重射,握手與決即仿射禮之拾與決。並質疑説:“《家禮》作者不明《士喪禮》之意,僅截取握手一件而不及其餘。禮不虚設,《家禮》此握手之設,其寓意何在?”“《家禮》作者不知握手爲何而設、如何安手,乃率爾操觚,作無法使用之裹手布。此朱子之禮學乎?”*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75,376。
按: 《考辨》述握手之制雖詳,卻不言《家禮》之依據所在。《書儀·喪儀一》:“握手用帛長尺二寸,廣五寸。”注云:“所以裹手者也。”*司馬光《書儀》卷五,頁485上—下。又云:“乃襲深衣,結大帶,設握手。”*司馬光《書儀》卷五,頁487上。亦不言設之之法。《家禮》悉與之同,非無所據也。至於決,《大唐開元禮》、《書儀》、《政和五禮新儀》皆無之,何獨責於《家禮》耶?《朱子語類》卷八九:“問喪禮制度節目。曰:‘恐怕《儀禮》也難行。如朝夕奠與葬時事尚可,未殯以前,如何得一一恁地子細?’”*《朱子語類》卷八九,《朱子全書》(17),頁3002。可見朱子本以《士喪禮》儀節太煩,難以施行。《語類》卷三四云:“射,如今秀才自是不曉。”*《朱子語類》卷三四,《朱子全書》(15),頁1217。又卷八九云:“又如《士相見禮》、《鄉飲酒禮》、《射禮》之屬,而今去那裏行?只是當存他大概,使人不可不知。”*《朱子語類》卷八九,《朱子全書》(17),頁3014。可見朱子之時,尋常士人多不習射,若死後仍仿射禮,備其握手與決之制,反而成了“虚設”。《家禮》之握手用後世簡易之制,自有掩藏和固定肢體的作用,不必更有深意。
6.弔者答拜。
《家禮·喪禮》賓奠酹後,“主人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賓主慰答後,主人又再拜,賓答拜。楊復《附注》云:“按弔禮,主人拜賓,賓不答拜,此何義也?蓋弔賓來,有哭拜或奠禮,主人拜賓以謝之,此賓所以不答拜也。故高氏書有半答、跪還之禮。凡禮必有義,不可苟也。《書儀》、《家禮》從俗,有賓答拜之文,亦是主人拜賓,賓不敢當,乃答拜。”*楊復、劉垓孫《文公家禮集注》卷六,頁3—4。《考辨》云:“楊説甚是。弔禮,賓不答拜,禮書有明文。《禮記·曲禮》云:‘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鄭注:‘禮尚往來。喪,賓不答拜,不自賓客也。’”並舉《儀禮·士喪禮》爲驗。*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78。
按: 楊復已指出《家禮》的依據是司馬光《書儀》及當時俗禮。司馬光《書儀·喪儀一》“弔酹賻襚”章云:“酹畢,主人西向謝賓,……稽顙再拜,賓答拜。”*司馬光《書儀》卷五,頁489下。楊氏《附注》引胡先生《書儀》曰:“若弔人是平交,則落一膝,展手策之,以表半答。若孝子尊,弔人卑,則側身避位,候孝子伏次,卑者即跪還。須詳緩去就,無令跪伏與孝子齊。”*楊復、劉垓孫《文公家禮集注》卷六,頁3。此所謂半答、跪還之禮也。可見弔者答拜之禮早已有之,不獨《家禮》爲然。
(三) 《家禮》同朱子禮學思想與實踐的一致性
《家禮》同朱子的禮學思想與實踐相合之處甚多,卻往往爲王、彭二家所忽略或誤解。上文所述拘泥《儀禮》和忽視《書儀》等書的情況,就往往同時伴隨着這一問題。下面再舉一些比較突出的例子。
1.深衣制度。
《考辨》援引江永《深衣考誤》對《家禮》深衣制度的批評,卻罔顧江永批評《家禮》的前提正是以《家禮》爲朱子所作。江永不但指出《家禮》深衣制度的依據是《禮記·玉藻》孔穎達疏和司馬光《書儀》,而且引朱子弟子蔡淵、楊復之説相證。他的批評也不是專門針對《家禮》,而是包括朱子所有相關論述在内,因此不能作爲《家禮》爲僞之證。
以《考辨》所舉“方領”之説爲例,《家禮·深衣制度》云:“如今之直領衫。”又云:“兩襟相掩,衽在腋下,則兩領之會自方。”*朱熹《家禮》卷一,頁8—9。江氏云:“既相掩,則領不直,而衣不止四幅。豈朱子未定之説乎?”*江永《深衣考誤》,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28册,頁394下。然而朱子以方領爲直領見於多處,不止《家禮》一書。如楊復《附注》引蔡淵云:“先生嘗以理玩經文,與身服之宜,而得其説,謂方領者,只是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又云:“方領之説,先生已修之《家禮》矣。”*楊復、劉垓孫《文公家禮集注》卷一,頁13。可知《家禮》方領之制,朱子生前已爲弟子言之。朱子《君臣服議》云:“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九,《朱子全書》(23),頁3351。標點有改動。所謂“今婦人之服”,蓋指背子之類,兩襟不掩時近於對襟,與《家禮》直領之説相合。
朱子《文集》中也有一篇《深衣制度》,與《家禮》所載基本相同,但不少地方在表述上又有明顯差異。如《家禮》“曲裾”注云:
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如裳之制。但以廣頭向上,布邊向外,左掩其右,交映垂之,如燕尾狀。又稍裁其内旁太半之下,令漸如魚腹,而末爲鳥喙,内向綴於裳之右旁。*朱熹《家禮》卷一,頁9。
而《文集》所載《深衣制度》“曲裾”注云:
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疊兩廣頭,並令向上。布邊不動,但稍裁其内旁太半之下,令漸如魚腹,末如鳥喙,内向而緝之,相沓綴於裳上之右旁,以掩裳際。右幅在下,左幅在上,布邊在外,裁處在内。*《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八,《朱子全書》(23),頁3297。
二者言曲裾之制相同,而文字大異。這説明《家禮》與《文集》所載《深衣制度》不是直接相襲的關係,而是同一篇文章先後修改而形成的兩個不同本子。編《文集》者没有直接從《家禮》中抄録,而是另有所據,在此情況下,《家禮》所載又與《文集》相合,足證其爲朱子所作。
《深衣制度》不是一篇獨立於《家禮》之外的文字。司馬光《書儀》中就有《深衣制度》,朱子欲增損《書儀》,“舉綱張目,别爲一書”,自然也要作一篇《深衣制度》。而《家禮》和《文集》所載《深衣制度》都是綱目體,與朱子的構想相合,應當正是爲了編撰《家禮》而作,這也是朱子曾作《家禮》的一個佐證。
2.親迎前告於祠堂。
《家禮·昏禮》“親迎”章:“主人告於祠堂,遂醮其子而命之迎。”注云:“非宗子之子,則宗子告於祠堂,而其父醮於私室如儀。”*朱熹《家禮》卷三,頁5—6。《考誤》云:“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則父在而不得自主其子之昏矣;至父醮子,亦自知其不可,爲改此例。然必云‘宗子告於祠堂’,不知醮固未嘗告也,何用是紛紛乎?故曰此非朱子之書也。”*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71上。
按: 王氏“醮不告廟”之説蓋本鄭玄。《禮記·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鄭玄注:“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禮記正義》卷六八,頁2274。依鄭説,娶婦之家醮不在廟,亦不告廟。故《禮記·曲禮上》“齊戒以告鬼神”,鄭玄注:“《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孔穎達疏:“齊戒,謂嫁女之家,受於六禮,並在於廟布席告先祖也,明女是先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而取婦之家,父命子親迎,乃並自齊絜,但在己寢,不在廟也。”*《禮記正義》卷三,頁64,66。但朱子並不以鄭説爲然。其《答潘恭叔》云:“齋戒,《儀禮》雖無娶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不知何故不同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〇,《朱子全書》(22),頁2315。此據《左傳》而疑鄭注,謂父醮子亦當告廟也。
又《左傳·隱公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春秋左傳正義》卷四,頁1733中。此謂當先祖而後配也。但此“祖”字何義,説有數家。孔穎達疏:“鄭玄以祖爲軷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春秋左傳正義》卷四,頁1733中。但朱子之説與鄭氏不同。其《答徐居甫》云:“《左氏》固難盡信,然其後説親迎處,亦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説,恐所謂‘後祖’者,譏其失此禮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八,《朱子全書》(23),頁2790。按: 朱子此説蓋用杜預注:“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春秋左傳正義》卷四,頁1733中。既當告廟,自然以宗子主禮爲宜。
3.祔於祖。
《家禮·喪禮》亡者祔於其祖。《考辨》引朱子云:“古人所以祔於祖者,以有廟制昭穆相對,將來祧廟,則以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豫告,使死者知其將來安於此位;亦令其祖知是將來移上去,其孫來居此位。今不異廟,只共一堂排作一列,以西爲上,則將來祧其高祖了,只趲得一位,死者當移在禰處。如此則只當祔禰,今祔於祖,全無義理。”*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77。意謂《家禮》祔於祖與朱子之説不合。
按: 《考辨》引朱子語見《朱子語類》卷八九,但未引全,朱子接着又説:“但古人本是祔於祖,今又難改他底,若卒改它底,將來後世或有重立廟制,則又着改也。”*《朱子語類》卷八九,《朱子全書》(17),頁3011。其《答葉味道》亦云:“然欲遂變而祔於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爲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爲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爲快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八,《朱子全書》(23),頁2782。可見朱子雖然認爲在同堂異室、新主遷禰的情況下,祔於祖並不合理,但在實踐上仍然主張沿襲古制,爲的是將來恢復左昭右穆的廟制後,不用再次變革舊制。《家禮》祔於祖是符合朱子主張的。
4.高祖當祧,遷於族人之親未盡者。
《家禮·喪禮》“告遷於祠堂”注云:“無親盡之祖,則祝版云云,使其主祭。告訖,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遞遷而西,虚東一龕,以俟新主。若有親盡之祖,而其别子也,則祝版云云,告畢而遷於墓所,不埋;其支子也,而族人有親未盡者,則祝版云云,告畢,遷於最長之房,使主其祭。其餘改題遞遷如前。若親皆已盡,則祝版云云,告畢,埋於兩階之間,其餘改題遞遷如前。”*朱熹《家禮》卷四,頁53—54。按: 首句“使其主祭”四字疑爲衍文。楊復、劉垓孫《文公家禮集注》首句作“若無親盡之祖,則祝版云云,告畢,改題神主”,以下俱同宋本。《考誤》云:
此一條最爲可疑。三祝詞俱不載,而族人有親未盡者,遷於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祭”,“庶子不祭祖與禰”,其見於經者至詳。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袓之宗,則本不得祭高祖,而今反得祭;……此皆説之不可通者也。
又云:
《朱子語類》沈僴録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世祖廟主,若叔祖尚在,乃是祧其高、曾祖,於心安乎? ’曰:‘也只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此推之,則謂“遷於最長之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75上—下。
按: 關於高祖祧後,族人親未盡者是否可祭於私室,朱子前後之説不一。主張祧去不祭的,除上引沈僴所録外,還有朱子《答李堯卿》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七,《朱子全書》(23),頁2704。其《答胡伯量》云:“高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别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小孫奉祀,其勢亦當如此。可更考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三,《朱子全書》(23),頁3045。雖亦主張祧去不祭,卻有不滿意之感。言“别未有以處”,則是嘗欲别有以處矣,説明朱子對此問題是有過不同考慮的。《語類》卷九〇包揚録云:“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朱子語類》卷九〇,《朱子全書》(17),頁3042。此則明確主張遷於親未盡者之家,與《家禮》合。王氏云:“按揚録最多妄説,不可據。然《家禮》之出在寧宗慶元庚申,包揚録刻於理宗淳祐戊申,相去幾五十年,乃揚録因《家禮》而附會之,非《家禮》之襲用揚録也。”*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75下。王氏此説並無確證。雖然包揚録刻行較晚,但《朱子語録姓氏》明載其爲“癸卯、甲辰、乙巳所聞”,*《朱子語類》附録一《姓氏》,《朱子全書》(18),頁4350。即在孝宗淳熙十年(1183)至十二年間,時《家禮》已亡而未出,當非襲用《家禮》者。《家禮》此條共有四處言“祝版云云”,皆闕其祝詞,猶是未定之文。疑朱子嘗欲從俗之宜,以就人情,而尚未安排盡當,其書即被竊失,《家禮》闕文正反映了這一斟酌損益的過程。
《家禮》高祖遷於族人之親未盡者,使主其祭,並不意味着與“支子不祭”的原則相悖。《家禮·喪禮》“題主”注云:“神主粉面曰‘皇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其下左旁曰‘孝子某奉祀’。”*朱熹《家禮》卷四,頁39。其親未盡而遞遷者改題神主,即謂改粉面之稱謂及奉祀者。然其遷於族人者不云改題,則此族人雖主其祭,猶不以“孝子”、“孝孫”自稱,實爲攝主。宗子不能主祭而由支子攝祭,古已有之。《禮記·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鄭玄注:“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禮記正義》卷二七,頁805。此謂宗子去國而死者,雖與宗子易世親盡者不同,然同爲宗子已死不能主祭,《家禮》或有取焉。
5.時祭卜日。
《家禮·祭禮》:“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朱熹《家禮》卷五,頁1。《考辨》云:“此舉與朱子所言顯有抵觸。《語類》云:‘問:“舊時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皆是卜日。今聞卻是二至、二分祭,如何?”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温公亦云,只用分至亦可。”’……是朱子曾以占卜定時祭之日,後改用二分、二至,《家禮》所言,與朱子之説違背。”*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82。
按: 《考辨》但見朱子曾有改用分至之舉,就以爲《家禮》也應如此,卻没考慮朱子改變觀點的時間先後。關於時祭是否卜日,朱子的觀點前後有兩次變化。在《祭儀》一書修定之前,朱子本用分至,後來改用卜日。其《答張欽夫》云:“又初定《儀》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今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〇,《朱子全書》(21),頁1326。《家禮》之撰雖晚於《祭儀》,但亦用此制。甚至《家禮》被竊之後,朱子仍長期用卜日之制。陳淳《代陳憲跋家禮》云:“紹熙庚戌於臨漳郡齋,嘗以冠昏喪祭禮請諸先生。先生曰:‘……舊亦略有成編矣,在僧寺爲行童竊去,遂亡本子,更不復修。’是時只於先生之季子敬之傳得《時祭儀》一篇,乃其家歲時所常按用者。……又後慶元己未到考亭精舍,聞先生家時祭今只定用二分二至,不復卜日,校臨漳所傳卜日丁亥,其義又爲益精矣。”*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一四,頁608下—609上。此“臨漳所傳”即陳淳於紹熙庚戌(元年,1190)所見《時祭儀》,時朱子仍用卜日之制。到了慶元己未(五年,1199),陳淳方聽説朱子又回歸到最初的觀點,重新用二分二至。《考辨》所引《語類》爲輔廣所録,乃紹熙五年以後所聞,亦朱子晚年之説。《家禮》撰於淳熙二年至三年,在《祭儀》與《時祭儀》之間,其用卜日之制是符合朱子當時的主張和實踐的。
6.祭饌品數。
《家禮·祭禮·四時祭》“具饌”注云:“每位果六品,菜蔬及脯醢各三品,肉、魚、饅頭、糕各一盤,羮、飯各一椀,肝各一串,肉各二串。”*朱熹《家禮》卷五,頁3。《考辨》云:“《書儀》祭品: 時蔬時果各五品,膾,炙,羹,殽,軒,脯,醢,庶羞(豬羊之外珍異之味),麵食,米食,共不過十五品。朱子云:‘温公《祭儀》,庶羞麵食米食共十五品。今須得一簡省之法,方可。’‘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而《家禮》每位設饌十九品。”*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82。認爲《家禮》“悖逆朱子禮説”。
按: 《考辨》所計品數有誤。《書儀》所謂“共不過十五品”是指“膾、炙”以至“麵食、米食”,不含“時蔬時果”在内。朱子雖以“庶羞”總括肉食,比《書儀》所謂“庶羞”的概念範圍要大,但也不可能將尋常易得的“時蔬時果”包括在内。如果算上時蔬時果,《書儀》祭饌可達二十五品。《家禮》祭饌共二十一品,*按: 《家禮》下文云:“設果楪於逐位卓子南端,蔬菜、脯醢相間次之。”故知上文所云“菜蔬及脯醢各三品”當謂菜蔬三品、脯醢三品,共六品,乃可次於“果六品”而與之齊,非謂脯、醢亦各三品也。吕祖謙《家範》參用朱子《祭儀》,云“醢醬、蔬共六品”,其數同也。不計蔬果則爲十二品,皆少於《書儀》品數。
朱子雖然認爲《書儀》祭饌需要簡省,但主要是針對現實中的具體情況而言的。《朱子語類》卷八九:“問冠昏喪祭禮。曰:‘今日行之正要簡,簡則人易從。如温公《書儀》,人已以爲難行,其殽饌十五味,亦難辦。’舜功云:‘隨家豐儉。’曰:‘然。’”*《朱子語類》卷八九,《朱子全書》(17),頁2998。可見朱子對《書儀》祭饌的批評主要着眼於“行”,未必要在禮書中作出太簡的規定。朱子《答吕伯恭》云:“又欲修吕氏《鄉約》、《鄉儀》,及約冠昏喪祭之儀,削去書過行罰之類,爲貧富可通行者。”*《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三,《朱子全書》(21),頁1458。則不獨爲貧家立法也。朱子同意“隨家豐儉”,其實《書儀》自注固已言之:“若家貧,或鄉土異宜,或一時所無,不能辦此,則各隨其所有,蔬菓、肉、麵米食各數品可也。”*司馬光《書儀》卷一〇,頁522上。《家禮》云:“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朱熹《家禮》卷五,頁9。亦同此意。至於“大祭時每位用四味”之説,蓋亦出於一時之計,所謂“稱家之有無”者也,與《家禮》並不矛盾。
陳來先生曾從吕祖謙《家範》中找出幾條參用朱子《祭儀》的禮文,*陳來《朱子〈家禮〉真僞考議》,頁121—122。其中“祭饌”條云:“果六品,醢醬、蔬共六品,饅頭、米食、魚、肉、羮、飯共六品。”自注:“以朱氏《祭儀》參定。”*吕祖謙《東萊别集》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50册,頁201上。《家範》祭饌除變“脯醢”爲“醢醬”,及無燔炙所用肝、肉外,其餘品數與《家禮》完全相同,可證《家禮》與《祭儀》基本相合,並無可疑。
7.焚香。
《家禮》有焚香之禮,如《祭禮·四時祭》“奉主就位”注云:“主人升自阼階,笏焚香。”*朱熹《家禮》卷五,頁3。又“降神”注云:“主人升,笏焚香。”*朱熹《家禮》卷五,頁4。《考辨》云:“此處焚香,乃沿襲温公《書儀》而來,然朱子頗不以爲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氣味香而供養神明’,‘楊子直不用,以爲香只是佛家用之’。”*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82。按:“焚香乃道家”,“乃”字《考辨》誤作“内”,今據所引原文改正。見《朱子語類》卷九〇,《朱子全書》(17),頁3051。
按: 《考辨》引朱子之語屬斷章取義,與其本意不符。《朱子語類》卷九〇云:“然温公《儀》降神一節,亦似僭禮。大夫無灌獻,亦無爇蕭。灌獻爇蕭,乃天子諸侯禮。爇蕭欲以通陽氣,今太廟亦用之。或以爲焚香可當爇蕭。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氣味香而供養神明,非爇蕭之比也。”*《朱子語類》卷九〇,《朱子全書》(17),頁3051。朱子之意不在反對道家之禮,而是强調焚香“非爇蕭之比”,因而不爲僭禮。《書儀》也用焚香,朱子批評它“似僭禮”,蓋因其書自注云:“古之祭者不知神之所在,故灌用鬱鬯,臭陰達於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所以廣求神也。今此禮既難行於士民之家,故但焚香、酹酒以代之。”*司馬光《書儀》卷一〇,頁523上。以焚香爲爇蕭的替代,則嫌於擬天子諸侯之禮,故云“似僭禮”。朱子批評《書儀》,恰恰是給了焚香以合法的地位。
實際上朱子《祭儀》中就有焚香之禮。吕祖謙《家範·祭禮》:“設香案於廟中,置香爐、香合於其上,束茅於香案前地上……”注云:“以上朱氏《祭儀》。”*吕祖謙《東萊别集》卷四,頁200下—201上。此香案、香爐、香合皆焚香所用器物,其文亦與《家禮》相合。朱子在生活中也常行焚香之禮,如其弟子葉味道云:“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八,《朱子全書》(23),頁2784。朱子《滄洲精舍釋菜儀》:“升,焚香,再拜。”*《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九,《朱子全書》(23),頁3367。《與長子受之》云:“如引入,即詣靈前再拜焚香。”*《晦庵先生朱文公續集》卷八,《朱子全書》(25),頁4791。然則朱子言“楊子直不用”,並不代表他自己也不用。
又按: 以上三條均屬《家禮》時祭儀。陳淳《代陳憲跋家禮》云:“所謂時祭儀,綱目大概如臨漳所傳,但降神在參神之前,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參神之後爲得之。”*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一四,頁609上—下。又《家禮跋》云:“餘杭本再就五羊本爲之考訂,所謂‘時祭’一章,乃取先生家歲時所用之《儀》入之,准此爲定説,并移其諸‘參神’在‘降神’之前。”*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一四,頁610上—下。今《家禮》諸本時祭儀皆參神在降神之前,與餘杭本同,當非《家禮》原本,而是朱子後來所用之《時祭儀》,陳淳所謂臨漳所傳者是也。若然,則《考辨》所疑根本就弄錯了對象,更無須詳辨了。但《時祭儀》單行本久已不傳,無由質證,故仍據朱子平日所論所行,辨之如上。下“餕時主人主婦之位”條同此。
8.始祖、先祖之祭。
《家禮》有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之禮。《考辨》以朱子後來廢此二祭爲由,認爲《家禮》“悖逆朱子禮説”。*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81。
按: 此與對“時祭卜日”的質疑相同,皆未深考朱子觀點變化的時間先後。朱子廢始祖、先祖之祭的言論均在《家禮》成書之後較晚的時間,如《朱子語類》卷九〇:“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此三祭如何?’曰:‘覺得此個禮數太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禰祭如何?’曰:‘此卻不妨。’”*《朱子語類》卷九〇,《朱子全書》(17),頁3049。此輔廣紹熙五年(1194)以後所聞。同卷又云:“堯卿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朱子語類》卷九〇,《朱子全書》(17),頁3054。此黄義剛紹熙四年以後所聞。這些晚歲之説,均無法證明朱子的觀點變化發生在《家禮》編撰之前。事實上,在《家禮》編撰之前不久,朱子仍主張祭始祖,如《答陳明仲》第十二書云:“冬至已有始祖之祭,是月又是仲月,自當時祭,故不更别祭。”*《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三,《朱子全書》(22),頁1949。據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此書在乾道九年(1173),*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增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頁112。先於《家禮》之撰不過二三年,撰《家禮》時尚未改變觀點是正常的。
(四) 相關質疑對《家禮》的誤解
王、彭二家對《家禮》内容的質疑,有不少是由於誤解《家禮》本文而引起的。誤解的原因,一是未能統觀《家禮》上下文義,故而不得其解;二是未能深考古禮、後世之禮及朱子相關禮論,不明《家禮》禮意。以下略舉數例以明之。
1.祭田、墓田。
《家禮·通禮》“置祭田”注云:“初立祠堂,則計見田,每龕取其二十之一,以爲祭田,親盡則以爲墓田。後凡正位祔者皆放此。宗子主之,以給祭用。上世初未置田,則合墓下子孫之田,計數而割之。皆立約聞官,不得典賣。”*朱熹《家禮》卷一,頁3。《考誤》云:“是宗子得分割族人之田,以爲己用,可乎?不可乎?且每龕之子孫,多寡不一,貧富不齊,何以總計而分割之?……今世士大夫家,遠墓有七八世者,有十餘世者,墓下子孫有不相往來者矣,孰得而割其田?又孰有聽其割者?又云‘立約聞官,不得典賣’,是徒啓無窮之爭,而卒亦不可以行也。”*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67上。
按: 王氏將“宗子主之,以給祭用”理解爲“宗子得分割族人之田,以爲己用”,與《家禮》本意不合。祭田的功能主要是供給祭祀。族人雖然不是宗子,但當宗子祭祀時也應與祭。在古禮中,支子與祭要供給牲物。如《禮記·曾子問》:“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禮記正義》卷二七,頁800。既然支子有供給祭祀的義務,那麽每龕子孫將其私田的一部分拿出來作爲祭田,也是合情合理的。
祭田、墓田用於宗族祭祀,並非宗子的私産,而是宗族的共有財産。《家禮·通禮》云:“大宗之家始祖親盡,則藏其主於墓所,而大宗猶主其墓田,以奉其墓祭,歲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其第二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其墓田則諸位迭掌,而歲率其子孫一祭之,亦百世不改也。”*朱熹《家禮》卷一,頁7—8。然則除大宗之始祖外,其餘之祖親盡祧遷之後,其墓田皆由同祖之族人輪替掌管,也體現了共有性和公平性。祭田、墓田的産出除供給祭祀外,剩餘的部分還可用於應對不測和救濟貧乏。如朱子弟子黄榦《始祖祭田關約》云:“獨同慶先祖墳共四所,已三百年,雖族人春秋醵金祭享,其間貧困者亦頗以爲苦。……今輒以本位近歲取贖到古田等處蒸嘗之苗,僅四畝一角六十七步,每歲供納穀十六石,充祭祀之用。緣所入甚微,未足以供諸房輪收,今欲每年於内撥六石充祭享及輸租外,公交族長掌管,以備不測支遣。如無支遣,即將所餘之穀積累增置,俟十年以後,即以增置益厚輪贍宗族貧乏者。”*黄榦《勉齋集》卷三四,頁394上。黄榦雖主張將祭祀之餘交由族長掌管,但約定只用於公共開支,並非由族長私人占有。陳守實《中國土地制度史》第四編《封建地主土地關係(上)》指出:“家族宗法集團的土地占有形式是公社形式的,即宗族公社。”*陳守實《中國土地制度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57。這一論斷完全適用於《家禮》祭田制度。
至於王氏所説每龕子孫多寡貧富不齊、遠墓世久不相往來等情況,在現實中勢必存在,但禮書只需規定一般情況即可,不必對具體情況一一措置。以朱子平生所爲來看,遠墓世久不相往來,也不足以作爲不置墓田的理由。據朱子《婺源茶院朱氏世譜後序》,自其九世祖以下世居徽州婺源(今屬江西),其父松始以仕宦徙建州(今福建南平),後遂家焉,而朱子猶歸婺源展墓,修定世譜,*《新安文獻志》卷一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375册,頁253下—254上。足見朱子追遠合族之意。據元虞集《朱氏家廟復田記》,婺源原有朱氏“先業百畝”,“紹興庚午,(朱子)省墓於婺源,以其租入充省掃祭祀之用”,*戴銑《朱子實紀》卷一一,《續修四庫全書》,550册,頁480下。然則朱子未嘗以世遠而廢墓田也。
王氏以爲“立約聞官”徒起爭訟,此説無理。“立約聞官”恰恰是減少爭訟的有效方式,也是當時的普遍做法。《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民産雜録》載元祐七年十一月五日詔:“諸太中大夫、觀察使以上,每員許占永業田十五頃。餘官及民庶願以田宅充奉祖宗饗祀之費者亦聽,官給公據,改正税籍,不許子孫分割典賣,止供祭祀。有餘,均贍本族。”*《宋會要輯稿》,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2014年,頁7469上。標點略有改動。朱子《朱氏世譜後序》亦云:“熹之曾大父王橋府君無他子,其墓在故里者,恃有薄田於其下,得以奉守不廢。當質諸有司,以爲祭田,使後之子孫雖貧無得鬻云。”*《新安文獻志》卷一八,頁254上。上舉黄榦《始祖祭田關約》亦其一例。這些實例都顯示出《家禮》對時制的遵循及與朱子思想的吻合。
2.跪而加冠。
按: 《書儀》、《家禮》皆於席上加冠,與《儀禮》同。《書儀·冠儀》云:“擯者取席於房,布之於主人之北,西向。”自注:“此適長子之禮也。衆子則布席於房户之西,南向。”*司馬光《書儀》卷二,頁469上。《家禮·冠禮》云:“長子則布席於阼階上之東少北,西向。衆子則少西,南向。”*朱熹《家禮》卷二,頁3。既用席,自當跪坐加冠。《書儀》或用“跪”,或用“坐”,蓋以二者相近而不加分别,皆謂跪坐於席上,非如後世盤腿而坐或坐於椅上也。王氏謂《書儀》“跪”字誤,而必用“坐”字,並無依據;且既謂古者坐與跪一,而“《書儀》一依古禮”,則自不妨二字互用。朱子對“坐”的古今之别作過清楚的分辨,其《跪坐拜説》云:“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八,《朱子全書》(23),頁3290。《家禮》將《書儀》之“跪”“坐”統一爲“跪”,正是爲了彰明其義,避免讀者將古禮之“坐”誤解爲後世之坐。
3.昏禮女從婿出,主人不降送。
《考誤》云:“《昏禮》:‘主人不降送。’注:‘禮不參。’疏:‘禮,賓主宜各一人。今婦既送,故主人不參也。’今《家禮》‘若族人之女,則其父從主人出迎,立於其右’,是有兩主人矣,殊乖‘禮不參’之義。”*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71下—672上。
按: 《儀禮》“主人不降送”乃女從婿出之時,*《儀禮注疏》卷五,頁114。《家禮》“其父從主人出迎”乃迎婿之時,兩者事既不同,義亦殊别,不可相混。《家禮》下文云:“姆奉女出中門,婿揖之,降自西階。主人不降。婿遂出,女從之。”*朱熹《家禮》卷三,頁8。是所謂“主人不降送”也,與《儀禮》同。此時主人之所以不降送,蓋因女與婿將爲夫婦,欲成其匹敵之義;若主人亦降送,而與婿爲賓主,則無法凸顯夫婦匹敵之義。至於此前迎婿之時,女父雖從主人出迎,然迎賓揖入皆以主人爲主,非所謂“兩主人”也。
4.婿從者。
《家禮·昏禮》云:“婦從者布婿席於東方,婿從者布婦席於西方。婿盥於南,婦從者沃之,進帨。婦盥於北,婿從者沃之,進帨。”又云:“婿從者餕婦之餘,婦從者餕婿之餘。”又云:“婿脱服,婦從者受之。婦脱服,婿從者受之。”*朱熹《家禮》卷三,頁8—9。皆不言從者是男是女。《考誤》:“賈疏云:‘女從者,姪娣也。婿從者,以其與婦人爲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也。’《書儀》從者各以其家之女僕爲之,蓋本賈疏之意。今《家禮》删此語,則似男從者乃男僕矣。”*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73下。
按: 此婿之從者爲女僕,不言可知也。朱子《趙婿親迎禮大略》:“婦從者布席於閫内東方,婿從者布席於西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九,《朱子全書》(23),頁3368。亦不言男女。且《家禮·通禮》載“司馬氏居家雜儀”已云:“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不入中門。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朱熹《家禮》卷一,頁16。則於《昏禮》自無須煩言。
5.弔者奠酹。
《家禮·喪禮》“弔奠賻”章云:“入哭,奠訖,乃弔而退。”注云:“既通名,喪家炷火然燭,布席,皆哭以俟。護喪出迎。賓入,至廳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背,不勝驚怛,敢請入酹,並伸慰禮。’護喪引賓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跪酹茶酒,俛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朱熹《家禮》卷四,頁22。《考辨》云:“作者似乎將‘酹’理解爲‘奠’,故賓入廳事曰‘敢請入酹’,哭後‘跪酹茶酒’,均有違常識,故楊氏云:‘程子、張子與朱先生後來之説,奠謂安置也。奠酒則安置於神座前,既獻則撤去。奠而有酹者,初酌酒則傾少酒於茅,代神祭也。今人直以奠爲酹,而盡傾之於地,非也。高氏之説亦然。與此條所謂‘入酹’‘跪酹’似相牴牾。蓋《家禮》乃初年本,當以後來已定之説爲正。’”*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77—378。按:“已定之説”,“説”字《考辨》作“本”,今據所引原文改正。見楊復、劉垓孫《文公家禮集注》卷六,頁3。
按: 楊復之説非也。《家禮》酹前已先有奠,其上文云:“奠用香、茶、燭、酒、果。”注云:“有狀。或用食物,即别爲文。”*朱熹《家禮》卷四,頁21。又“具刺通名”注云:“先使人通之,與禮物俱入。”*朱熹《家禮》卷四,頁22。則禮物已先入奠矣。其茶、酒奠而後又酹之,故言“入酹”,然亦未言盡傾於地也。至於香、燭、果、食非可酹之物,則直奠而已。*香、燭亦可言奠,如《朱子語類》卷八九:“先生殯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見《朱子全書》(17),頁3013。其下文主人對賓之辭云“伏蒙奠酹”,*朱熹《家禮》卷四,頁22。亦奠、酹並稱,非以奠爲酹也。
6.朝祖時舉柩之法。
《家禮·喪禮》“奉柩朝於祖”注云:“祝以箱奉魂帛前行,詣祠堂前。執事者奉奠及倚卓次之,銘旌次之,役者舉柩次之,主人以下從哭。”*朱熹《家禮》卷四,頁32。《考辨》引楊復云:“蓋朝祖時載柩則有輁軸,正柩則有夷牀,後世皆闕之。今但使役者舉柩,柩既重大,如何可舉?恐非謹之重之之意。……恐當從《儀禮》,别制輁軸以朝祖,至祠堂前,正柩用夷牀。”*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頁381;引文見楊復、劉垓孫《文公家禮集注》卷七,頁2。
按: 楊氏謂《家禮》“但使役者舉柩”,而責其不用輁軸,似以此舉柩爲徒手而舉。然《家禮》“治棺”條注云:“四隅各釘大鐵環,動則以大索貫而舉之。”*朱熹《家禮》卷四,頁2。則自有舉之之法,非不可舉也。且《書儀》亦但云“役者舉柩”,*司馬光《書儀》卷七,頁505上。不言輁軸,爲《家禮》所本。
7.祔祭於它所。
《家禮·喪禮》“祔祭”章末云:“祝奉主,各還故處。”注云:“若祭於它所,則祖考妣之主亦如新主納之。”*朱熹《家禮》卷四,頁50—51。《考誤》云:“是亦可祀於新主之寢,而奉祖考妣以從之矣,此不可曉。凡《家禮》之舛誤多若此者。”*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74下。
按: 此王氏不明《家禮》本意而妄疑也。此“它所”並非“新主之寢”,而是指祖考祠堂的替代場所,如廳事、正寢等。其上文云:“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注云:“器如卒哭,惟陳之於祠堂。堂狹,即於廳、堂,隨便。”*朱熹《家禮》卷四,頁47。又云:“詣祠堂,奉神主出置於座。”注云:“若在它所,則置於西階上卓子上,然後啓櫝。”*朱熹《家禮》卷四,頁48。此“它所”即前所謂“廳、堂”也。以廳、堂爲祠堂的替代,是用司馬光之説。《書儀·喪儀六·祭》注云:“影堂迫隘,則擇廳、堂寛潔之處,以爲祭所。”*司馬光《書儀》卷一〇,頁521下。《朱子語類》卷九〇亦云:“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朱子語類》卷九〇,《朱子全書》(17),頁3038—3039。與《家禮》合。
8.餕時主人主婦之位。
《考誤》云:“餕,《書儀》以主人主婦爲主。注云:‘若主人之上更有尊長,則主人帥衆男、主婦率衆婦女以獻壽。’‘更有尊長’,則主人有母在,或伯叔母也。《家禮》以宗子爲主,於饌卻不言主人主婦,但云‘尊行自爲一列’,則必尊於宗子宗婦、長於宗子宗婦者,而主人主婦反退處於衆男婦女之列矣,是不若《書儀》之有條理而分析明白也。”*王懋竑《白田雜著》卷二,頁677上。按: “饌”,當作“餕”。
按: 《家禮·祭禮·四時祭》餕時坐次雖“尊行自爲一列”,但當獻壽之時,則“尊者一人先就坐,衆男敍立,世爲一行,以東爲上,皆再拜,子弟之長者一人少進立”以獻,*朱熹《家禮》卷五,頁8。非無條理也。《家禮》主人、主婦之上可能更有尊長,也可能没有,王氏謂尊行“必尊於宗子宗婦、長於宗子宗婦者”,未必然也。
《家禮》之餕以行輩年齒爲序,主人主婦若非尊長,則退處於衆男衆婦之列,而與正祭時以宗子爲主不同。蓋《家禮》之餕兼有祭畢而燕的功能,而燕以年齒爲序。《禮記·中庸》:“燕毛,所以序齒也。”鄭玄注:“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禮記正義》卷六〇,頁2010。朱子《中庸章句》亦云:“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别長幼,爲坐次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朱子全書》(6),頁44。又《禮記·文王世子》:“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孔穎達疏:“公既不爲主,族人又不爲賓,故列位在父兄之坐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禮記正義》卷二八,頁849,853。按: 《家禮》之餕不僅坐次與祭畢之燕相合,其時間、場所、人員亦皆與燕相似。《儀禮·特牲》、《少牢》之餕皆在陽厭之前,陽厭之後復有徹俎、歸賓俎等事,而《家禮》之餕在歸胙於親友(即“歸賓俎”)之後。《特牲》惟嗣子及長兄弟餕,《少牢》二佐食及二賓長餕,而《家禮》凡與祭者皆餕。《特牲》、《少牢》之餕惟男子行之,皆在廟中,而《家禮》男子在堂,女子在中堂。凡此皆與《儀禮》之餕不同。《詩經·小雅·楚茨》:“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朱子《集傳》:“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詩集傳》卷一三,《朱子全書》(1),頁623。《儀禮·特牲饋食禮》“徹庶羞”鄭玄注:“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内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儀禮注疏》卷四六,頁1414,1415。此所謂祭畢之燕也,《家禮》之餕皆與之合。燕既序齒而親親,故不必以宗子宗婦爲主。《家禮》祭時以宗子爲主,而餕時序齒,尊尊親親之道也。王氏以此爲疑,蓋不明禮意。
《書儀》之餕實際上也兼有既祭而燕之事,之所以仍以主人主婦爲主,是因爲其對“主人”的身份設定與《家禮》不同。《書儀·喪儀六·祭》云:“主人及弟、子、孫皆盛服親臨。”“主人”下自注云:“即目在此男家長也。”又“主婦”下注云:“主人之妻也。《禮》,‘舅没則姑老’,不與於祭,主人主婦必使長男及婦爲之。若或自欲預祭,則特位於主婦之前,參神畢,升立於酒壺之北,監視禮儀。”*司馬光《書儀》卷一〇,頁521上,下。皆不言主人之上更有諸父諸兄。王氏以《書儀》“主人之上更有尊長”謂主人有母或伯叔母,而不言伯叔父,蓋亦有見於此。然則《書儀》僅據小家庭設文,其“主人”本來就是家中男子之最尊長者;其由主人主婦獻壽,仍然符合“燕毛序齒”的原則。
結 論
不論從《家禮》成書與失而復得的經歷來看,還是從其思想内容與朱子禮學思想的關係來看,《家禮》爲朱子所作都是可信的。《家禮》的撰著見於朱子《答吕伯恭》二書,其失而復得則陳淳所記朱子及其子在之語最爲確鑿。從思想内容來看,《家禮》强調日用常行的通禮,將其置於冠昏喪祭之前;突出宗子的作用;在具體儀節上比《儀禮》簡化;大量吸收《書儀》等後世禮書以及當時俗禮,而在行文上較《書儀》更加簡潔。這些特點都與朱子的禮學思想相吻合,無論宏綱還是細節,可在朱子文集、語録中找到依據的不勝枚舉;其個别地方與朱子言論不盡一致,也往往是其觀點發生變化的緣故,並非朱子未曾有過類似觀點。當然,《家禮》確有不盡完善合理之處,但對於一部尚未最終定稿之書來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朱子《答吕伯恭》云:“《祭禮》略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三,《朱子全書》(21),頁1436。而《家禮》尚未定稿即被竊失,未能經過“徐於其間察所未至”的檢驗和改定,因而在個别儀節上存在一些闕略、矛盾之處是正常的,不足以構成僞書之證。
王懋竑等懷疑《家禮》爲僞的學者,不但遺漏了《家禮》成書與失而復得的相關記載,對《家禮》思想内容的質疑也大多站不住腳。這些質疑往往據《儀禮》以繩《家禮》,而忽略了《家禮》對《書儀》等後世禮書的繼承和朱子本人的相關論述與實踐,這在判斷標準上就存在問題;而在具體的質疑過程中,還存在許多誤讀《儀禮》、《書儀》、《家禮》本文的情況,從而造成了《家禮》錯誤百出的假象,爲《家禮》僞書説增加了口實。《四庫提要》未加詳考就采信王懋竑之説,而定《家禮》爲僞,是非常武斷的。
確定《家禮》真僞,是開展《家禮》研究的前提,而從思想内容上辨明《家禮》爲朱子所作,對於考察朱子禮學思想的變化過程,從而全面認識和深入研究朱子禮學,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