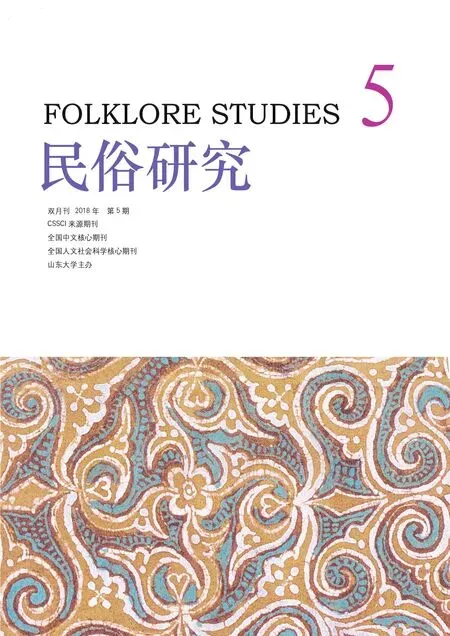雨水与“灵验”的建构
——对陕北高家峁村庙的历时性考察
陈小锋
乡村庙宇规模不等、神灵不一,但追问起庙会“为什么红火、热闹?”,人们的回答基本都指向神的“灵验”,神越是灵验,意味着地方社会的神越具有权威。值得注意的是,灵验问题既是一个地方信仰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信仰研究的理论问题。前者决定了庙会信徒的多寡和香火是否旺盛,后者指隐含在神灵崇拜形式背后需要研究的建构机制。那么,“灵验”在神与人之间如何体现?村庄又经历了哪些变迁,使得灵验在空间与历史的维度得以延伸?本文通过呈现高家峁村以雨水作为感知中介而形成的人神互动历程,解释其背后隐含的雨水的意义转向与灵验的建构机制。
一、灵验研究的理论与问题
“灵验”与否是判断人神互动效果的基本指标,若没有了灵验,就不再有民间信仰,更谈不上民间信仰的持续发展了*陈彬、刘文钊:《信仰惯习、供需合力、灵验驱动: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复兴现象的“三维模型”分析》,《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4期。,因此,“灵验”的解读尤为重要。一般而言,灵验程度可依据庙会的兴衰表象加以判断,似乎分析了庙会的兴衰也就分析了灵验。结构主义视野中庙会被视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赵世瑜通过比较发现,华北地区的庙会作为市镇集场的必要补充,要比南方地区显得较为活跃*赵世瑜:《明清时期江南庙会与华北庙会几点比较》,《史学集刊》1995年第1期。;政治制度也与庙会有着微妙的关系,当国家体制中存在“制度性自欺”*郭于华:《倾听无声者的声音》,《读书》2008年第6期。的时候,庙会被视为异质性力量而被排斥,然而,无论是经济的补充成分,还是政治的排斥对象,灵验问题却被宏观结构所代替或遮蔽;在中观视域中,有学者用信仰惯习、供需合力、灵验驱动构建出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三维模型”*陈彬、刘文钊:《信仰惯习、供需合力、灵验驱动: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复兴现象的“三维模型”分析》,《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4期。结构,认为灵验是信仰需求者与信仰供给者符号互动的产物,这种认识表明了灵验存在和延续的形式,人们可通过庙会或者互动仪式实现与未知世界的联通,但“仪式本身是形式,其本质,应当是灵验”,庙会或者互动仪式本身亦不能完全揭示灵验的渊源与意义。
与结构形式的说法不同,有研究提出神的灵验能带来“经济益处”[注]岳永逸:《民族国家、承包制与香火经济:景区化圣山庙会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乡村研究》(第十三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79页。的功利主义观点,还有对神灵的敬畏和“预置性”心理的心理学说法[注]林国平、詹素娟:《籖占长盛不衰的原因与特别“灵验”的奥秘》,《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第8期。,灵验被界定为前置性的概念。不难发现,二者其实倒置了灵验效应与灵验原因的位置,具有目的论的倾向。
“灵验”是一种主观认识,但它不是悬置在乡村世界上空的结构,也不是简单的功利或纯粹的心理概念。可以确定的是,灵验并非一个先验的、固定的概念,它是在地方社会空间里人与神一次次互动的结果。当然,泛化地强调人与神的互动也不足以说明“灵验”之内涵,人神互动的研究范式尚需“具体而微”的解释主义,因而有了人的主体性解释:一方面,出现“心诚则灵”式的解说,无论“灵”与“不灵”都可归结为个体的“心诚”程度。[注]甘满堂:《灵验与感恩:汉民族宗教体验的互动模式》,《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另一方面,与其说是神的灵验,不如说灵验是人们集体情感或认同的一种确认方式。[注]张晓艺、李向平:《信仰认同及其“认同半径”的研究》,《东南学术》2016年第6期。二者都突显了主体性价值,但却淡化了地方环境、时代变迁的影响。
因此,部分学者将目光转向了“微观性整体”[注]林亦修:《地域研究中的人神互动范式》,《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9期。的解释范式,如曹荣以京西桑村探讨了灵验之于天主教徒的生活意义与乡土社会的文化逻辑问题。[注]曹荣:《灵验与认同:对京西桑村天主教群体的考察》,《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然而,微观场域中人与神的互动并非都是直接互动,在人与神之间需要灵验的感知中介,庙会上的信仰本质上是一种经验信仰,即可感知的观察和控制之下的信仰,赵旭东在河北地区的庙会中发现“神的灵验,通过‘观香’解决矛盾纠纷,裁决的灵验性反过来又强化了神的权威性”[注]赵旭东:《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95页。。除了解释人神互动的中介因素,还应关注人神互动的方向问题,实际上,人与神的互动也并非仅仅是神对人的恩惠,神也有对人“感恩”的一面。从根本上来讲,人与神不仅是互动,更是一种相互构建的关系,互构的过程中嵌入了其它的中间因素。
那么,“灵验”究竟如何成为了现在的模样?在历史变迁中经历了怎么样的过程?“灵验”的解释首先要明确人们如何归因以及为何如此归因,“强调灵验,看似荒诞的传说实则是乡土社会流动的魂,是一个地方之所以成为地方的原因之一,是人们获得认同、培养情操以及与他群交往的方略和手段”[注]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和阳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0页。,因此,乡土语境中的归因自然不同于科学逻辑,需要人文理路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仅有“横截面”的剖析和主体心理的透视还不够,因为“有着‘灵迹’贯串的乡村庙会传说隐喻了民众对其生活空间的想象与建构,和对生活空间所有资源分配的机制,是民众对相应部落历史群体记忆的结果”[注]岳永逸:《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和阳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51页。,灵验的解释与其建构的历史过程紧密相关,问题的研究最终要回归场域,既要有微观性整体的观察,还需加以历时性视野的整合。对村庄变迁、地方性常识“包括民间信仰、神祇构建在内的一切文化事象的理解,都应该放在一个区域发展演变的复杂动态过程中去理解”[注]赵世瑜:《从贤人到水神:晋南与太原的区域演变与长程历史》,《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即从村民完整的生活世界中描述人神互构的过程,通过感知中介解释地方信仰活动中“灵验”的建构问题。
二、高家峁村的“他山之神”与雨水崇拜
高家峁村地处陕北北部,属黄土高原地带,其地形千沟万壑,是榆林市子洲县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附近一带也被称之为南川。空中俯瞰,高家峁位于一个山顶之上,不过山顶犹如被“削平”,山上削平的地势称之为峁,村民在此繁衍生息。该村庄规模较小,土地极为贫瘠,农民主要种植小米、玉米等粮食作物,世代沿袭着相似的生计模式。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是典型的“靠天吃饭”型农业生产方式,“收成好,则民稳;收成不好,则民不安;跌下年成,则民慌。十年九旱,歉收时为多”[注]子洲县志编纂委员会:《子洲县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87页。“跌下年成”,指庄稼因遭灾而粮食歉收。。80年代之后该村发生明显变化,先后多次获得过“先进生产队”“万元户模范村”等称号。目前,该村人口大量外流,土地已大面积抛荒,成为名副其实的“空心村”和“留守村”。
高姓是村里的主要姓氏,相传祖先从山西移民而来。虽说陕北地区“无庙不成村”,村村皆有神灵,而高家峁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没有庙、也没有神像,现在的庙要从文化大革命说起。距离高家峁村东北方向五里路,有一个村庄叫小沟村,当时也叫小沟生产队,两村同属于子洲县下面同一公社。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除四旧”、“破除迷信”浪潮席卷各地,1976年小沟村的庙也不例外,但庆幸的是庙里的龙王神像被转移到高家峁村,被该村村民偷偷地保存下来。
龙王成为高家峁村“请到”的第一位神灵,据村民讲,当时那尊神像“可猴咧”[注]“可猴”为地方方言,指小的意思。。而意想不到的是,自从供奉上了神像,高家峁村的人神“互动”日益频繁,而且神与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甚至气候条件也变得风调雨顺。虽然“有求必应,有应必酬”是一种人神双向互动的模式,但人与神的互动不是单向的人祈愿——神佑护——人感恩的互动,也不仅仅是人对神力的确认,村民讲“(自从)咱庄里把那(神像)抬上,人人光景就好过了……庄稼长得可好咧”。人们言语中直接表达的是神对人的佑护和人对神的感恩,如果从完整的时间顺序来看,其实还隐含着神对人的“感恩”,“偷藏神像”可视为人的善行,风调雨顺可解释为神对人的“感恩”,二者互有感恩,也互有善行。
时至今日,以前只有“龙王”一位神灵,历经多次扩建、改建,先后“请来了”更多的神灵,如“齐天大圣”“无量祖师”“观音菩萨”“财神”“文昌”“水母娘娘”“药王”“土地神”等。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三是庙会正日子,由于神的“灵验”,村庙活动的影响已经超出村界、跨越宗族。2012年,该村庙被确定为县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2014年成了市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那么,高家峁的村庙为何能请来诸神?这不仅得益于龙王的“面子”,也有人们的虔诚和努力,是人与神协作的结果。可以说,人塑造了神,神成就了人。为何神有如此大的感召力,人为何又有如此高的积极性?其答案都指向了一个关键性的因素:神的灵验,神的灵验与乡村生活的中心事件紧密相关。
雨水耕作的农业区域[注]“雨水耕作”指靠天吃饭的耕作方式,区别于灌溉耕作。,雨水是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生存状态与种族延续。正是因为雨水的稀缺性决定了它具有某种神秘性,成为人神互构最为重要的感知中介,承载着人们无休止的困惑和希望。因而,乡土社会历来有水崇拜的传统,流传着各种司水神灵和种种左右雨水的神秘力量的信仰,不仅在民间盛行,而且进入朝廷、官府,与政治发生了联系。[注]向柏松:《中国水崇拜和古代政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陕北气候干旱,当属于雨水耕作区域,整体而言,该区域土地较为贫瘠,但土地依然是村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要素。在水、土关系方面,黄天厚土难移,而水则变化多端,尽管水资源不是收获必需的唯一因素,但是水的多变性决定了土地的产出效益,“蓄水如蓄粮,水足粮仓满”,相对而言,水比土地更具有决定性,在此意义上而言,比起“黄土高原”的称谓,这块土地更像是“水土高原”。
魏特夫的研究表明,在工业社会之前,干旱地区农业所需水源具有不稳定性,“它不仅比其它农业因素更加多变,而且更是一个庞然大物”[注][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极权的比较研究》,邹如山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8页。,然而水又无限重要,治水者不得不想方设法控制这种物质。控制的方式既有“务实”的生产劳动,也有“务虚”的神灵祈祷。在靠天吃饭的乡村社会,村庄最重要的祈愿便是灵验的“雨水”。
雨水为什么能够成为灵验的表征?在人们的认识中,“雨水尚未落地之时,归龙王所有”[注][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2页。,不仅如此,甚至“与水利管理体系基本上并行的是供奉龙王的祭祀体系”,龙王是雨水的“主人”,他可以“呼风唤雨”,所以这个主人被奉为神,不过,人格化的龙王也会有情绪、欲求和选择。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雨水,势必有求于雨水的主人——龙王,那么龙王降不降雨水,可视为人们敬奉龙王效果的验证,如果降水,那便是雨水主人对人们敬奉行为的回馈,即“灵验”现象,当然,龙王也会通过惩戒督促人们要怀有敬畏的心理和做出虔诚的举动。可见,人们希望龙王懂得“人情世故”,但人格化的龙王也有“喜怒哀乐”,由此决定了雨水并不总是“尽如人意”。在变幻莫测的自然界面前,村民总是在追寻一种可控、可感知的信仰,雨水的中心地位以及可感知性,成为通往信仰世界的“感知中介”。
陕北乡村的治水事件贯穿于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从祈雨活动到“箍洞打坝”,从蓄力驮水再到水窖改造,雨水始终是村庄生产、生活的中心事件。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村庄里,决定人们信仰世界的“灵验”力量与世俗中心的“雨水”两个关键性因素不得不耦合在一起,二者基本的逻辑关系是:神给人以雨水展现自己的神灵法力,人以雨水及时与否判断敬神行为的价值。当然,雨水并非判断灵验的唯一因素,但因为雨水与人们的世俗世界有密切的关系,降雨便成为龙王最基本的职责。本质上,该语境中的神灵崇拜也是水的崇拜。
三、雨水的灵验:从“望天乞水”到“不期而遇”
农村改革之前,庙会、祈雨活动被禁止。80年代,祈雨活动在农村得以恢复,遇旱祈雨逐步成为常态,而近些年该村不再举办祈雨活动,多数村民已记不清楚上一次的祈雨活动是哪一年,龙王庙里一块“云行雨施”的牌匾上写着1995年6月23日,意味着可能的最近一次祈雨活动距今已20多年。
高家峁的祈雨活动一般集中在农历五、六月份,那时青苗开始“抽上了”[注]“抽上了”为地方方言,意思是叶子因缺水而卷曲。,人们(仅限男性,女性被禁止参加整个仪式过程)用柳条编成雨帽,光脚、赤膊,由四个未婚小伙抬着龙王“楼子”(类似于轿子,只是比例缩小了很多)参五方,各家都需出一名男性共同组成祈雨队伍,人越多越好。参拜的路线、节奏由龙王临时决定,出发之前需要“问神”。有人曾问抬楼子的小伙“到底参拜(速度)由你呢,还是由那(神)着”,“一阵由我们,一阵由神”[注]祈雨活动中,除了参拜各路神灵,更重要的仪式是吟唱“祈雨调”,“清风细雨救万民,天旱了呀着火咧,地下青苗晒干咧”,“龙王老家显灵吆,下海雨吆,万苗”,“东海老家哪走时雨呦,下海雨救万苗”。。
高家峁的祈雨仪式充满了时节性、神圣感和参与感,在村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次祈雨龙王也都会显灵,庄稼的丰收得以保障,没有出现严重的饥荒现象,多次的祈雨实践使祈愿、活动和效果之间已经形成了紧密的链锁关系。巴战龙对四川的祈雨仪式研究也发现,传统社会的人们依靠人类社会的关系来认识自然,以期通过构建“神话”和“仪式”,使自然的不稳定性降低对人类社会的部分威胁。[注]巴战龙:《村寨遇旱求雨的地方叙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高家峁祈雨过程中,神意决定的参拜路线和速度更是民意的表现,隐含了村民通过掌控的祈雨仪式实现掌控雨水的欲求。
尽管“烂了农业社”[注]村民口语,意思是农业社解散、包产到户。后的生活比起之前已经好了很多,农民有了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单干后的劳动积极性极大提高,土地产出效益好于以前。但80年代的旱灾依然时有发生,只是人们灵验的记忆也具有“过滤性”,生活的好转没有根本上改变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雨水依然对农业收成有关键性的影响,1987年春旱,4月28日气象部门测定10厘米土层含水率为1.8%,30厘米土层的含水率为2.7%,1~5月降水57毫米,5月份降水仅为12毫米,全县旱灾,成灾面积78.77万亩。[注]子洲县志编纂委员会:《子洲县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87-90页。
2017年,高家峁村扩建了村庙,完工后举办的开光仪式(落成典礼)前后几天下了两场雨,这两场雨被村民做了灵验的诠释。
第一场雨,在落成典礼之前。庙里的所有工程已经竣工,院子的土地面也铺上了石板。但是卫生没有打扫,院子里的泥土、屋顶上的尘土,掩盖了新庙的光色。农历六月二十一晚上突然下了一场雨,院子的泥土、屋顶的尘土被雨水冲洗后,整个庙堂焕然一新,村民也都喜笑颜开。当地人认为,落成典礼即将举行,这场雨来地非常及时,称之为“洗山”雨。在正日子农历六月二十三那天,开光仪式把整个活动推向了高潮,村民围绕在院子四周一睹盛况,附近一些村庄的农民也纷纷赶来。
庙会当天,有邻村人嘴里感叹道,“看人家高家峁的庄稼绿格嗒嗒”[注]“绿格嗒嗒”为地方方言,指绿油油的意思。。农历六月正值炎热、干旱,这时期的降雨多为阵雨,分布也不均匀,邻村没有下雨。人们将这场雨的“选择性”分布,也归结为该村神的“灵验”,更为夸张的是多数村民记忆里:“有一次祈雨活动后,站在邻村庄稼地里,看本村地里下着雨”。可见,灵验的意识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得以强化。
第二场雨,在仪式结束后。新庙重新塑造了八尊神像,而且每一位神像都有单独的庙堂,新庙堂比之前面积大了十几倍,新的神像由画师装点得逼真、威严,整个庙宇也比以前磅礴、壮观。经过白云山(陕北地区最大的道观)道士的开光,新神像获得了“合法性”,新的庙堂正式“运营”,新的诸神开始接手保一方平安的事务。随之而来一个让全村人苦恼的问题出现,即被搁置在院子里的旧神像该如何处置?“没办法,撂去吧,没一个人去撂,谁把那个(旧神像)抬着往(山沟)下撂,都脑疼(发愁)时,结果一夜大雨给风化(溶化)了,这个是泥做的”。
旧神像经过开光仪式,他的“法力”和“灵魂”完全被移植到了新的神像上,固然已没有什么价值,只是一个普通的废弃物,而对村民来讲,扔也不是,埋也不是。毕竟,它曾经是神灵,也被村民们供奉了多年,“常在那面前烧香咧,磕头咧”,于情于理,谁也不愿意、也不敢把它扔掉。“这可伤了脑筋了”,当晚一场大雨让神像化为泥土,随着雨水的冲刷基本消失掉了。按照村里人的解释,雨水“不请自来”缘于神的灵验,他始终在为庄里人排忧解难、消除烦恼,这是神“灵”的又一次验证。
从自然角度而言,无论哪一天下雨都属正常现象,“这一天”与“那一天”并无性质的差别。然而,村民生活世界里不仅仅只有自然,在有神力介入的地方社会,下雨的时间选择则被赋予了“灵验”的意义:为什么偏偏在开光仪式开始和结束这几天下雨?雨水的“不期而遇”,其实是神在人们生活世界的“自我证明”,人需要“深谙其道”,并做出“合理”的解释。
由上而论,高家峁村的雨水经历了“望天乞水”到“不期而遇”的发展历程,雨水的意义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转向背后隐含着村庄社会历史变革,但不变的是“有求必应、有应必报”的祈愿模式。那么,雨水为何如此及时?神果真如此灵验?仅凭这两场“及时雨”还不足以解释其中的逻辑。
四、灵验的构建:神秘力量的归因与他指
风水学说的研究正统化、地方化地建构了“灵验”,推动了庙宇信仰的深入传播。[注]王芳辉:《灵验的庙宇:从风水看妈祖信仰在广东的地方化》,《民族艺术》2013年第2期。那么,雨水又是如何构建了高家峁村庙的“灵验”?村庄光景好转真的是因为神灵吗?
据资料记载,60年代到80年代之初,单就干旱天气而言,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子洲县1963年大旱43天,88%的秋田受灾;1965年5月至收秋,未落好雨,损失严重;1967年12月至次年7月旱,是本县罕见的干旱;1972年,发生数十年未遇大旱,旱象持续达180多天,不少群众外流逃荒;1982年,该县淮宁湾、裴家湾、老君殿等公社自春及夏旱,粮食歉收。本地区平均每年出现干旱3.4次,其中小旱发生次数最多,占总次数的49%,平均每年出现1~7次;中旱次之,占干旱总次数的35%,平均每年出现1次;大旱较少,占干旱总次数的16%,平均每两年出现1次。[注]子洲县志编纂委员会:《子洲县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87-90页。
可见,在80年代、特别是农村改革之前,干旱致灾的事实令人刻骨铭心。90年代之后,难道就没有干旱等灾害天气?显然,不是没有干旱,只是90年代的干旱天气已经不足以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一方面村里的水井、水窖和自来水等水利设施日益完善;另一方面,后来外出务工、做生意等人员增多,种地为生的人越来越少,目前常住人口只有16人,人们的生计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此背景下,人们对干旱等灾害影响的感知强度大为降低,龙王主要职责是掌管雨水,既然降不降雨都无关紧要,为何从90年代到现在龙王还被继续敬奉?
90年代之后,村里“出息”的人更多了,“当老板的”、当官的、上大学的人数明显多于邻村,日子好转了,村民也在思考好转的原因。巧合的是之前偷偷保存“神像”的时间正好是“烂光景”和“好光景”[注]指好日子和坏日子。的分界点,村民们似乎已经达成共识:之所以从之前灾害不断、粮食短缺到现在的“好光景”,是因为有神的佑护,其根源在于文革期间本村人偷偷保存了龙王神像,到后来人人供奉、年年办会。“他山之神”的灵验,确保了该村的风调雨顺、人丁兴旺,显然,一种先行后续的时间关系被因果逻辑所取代。
这种归因体现了农民的“想象力”,但它不同于米尔斯的“想象力”,没有在“个人烦恼和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也没有在微观的经验结构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注][美]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6页。,农民的想象力具有局部空间性特点,他们的因果思维方式也不同于科学逻辑的解释,但这种想象力和逻辑恰恰是地方文化的“深层密码”。
1977年陕北马家沟粮食平均亩产51斤,社员平均口粮只有133斤。[注]文磊:《冯森龄与延安调查》,《党史文汇》1997年第6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多次的旱灾,加之“急于求成”的人民公社化制度,还有忽略实际情况的粮食“征购政策”的影响,陕北农民经历了一段困难的历史。那么,这种困局又是如何扭转的?何时开始扭转?具体过程如何?真如村民所说的那样,是偷藏“神像”带来了新的历史“际遇”吗?
实际上,1978年原《解放日报》记者冯森龄在陕北地区通过实地走访完成了“延安调查”[注]“延安调查”并非作者当时对稿件的拟名,而是后期对一系列调查报告的统称。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当时陕北农村地区“触目惊心”的实际困难,感叹“养育了中国革命的陕北老乡,今天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于是他冒着政治风险把这些文章刊登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不久,文章在北京及全国各地的高层领导中引起了极大地轰动。经会议讨论,中央决定从1979年开始,每年给陕北地区援助5000万元,该政策持续了很多年,总额8亿多元。与此同时,陕西省委成立了“陕北建设委员会”,还决定减免陕北粮食征购任务的60%以上。[注]文磊:《冯森龄与延安调查》,《党史文汇》1997年第6期。
这些特殊政策极大地缓解了陕北地区的困难与灾情,加之后来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活市场交易,打破城乡界限,陕北农民的生活进一步好转。而这些背后的故事及政策,在通讯落后、交通不便、文化水平较低的时代,农民并不了解这个事关自己命运的具体改变过程,但是,真切的改变确实存在于农民经验之中,之前苦难的共同感受、对神的敬畏和自然给予的震撼,促使他们探寻改变的“灵验”力量是什么,尽管很多村民说不清楚拜的是佛教还是道教以及庙堂里神灵的左右尊序[注]村庙院子里竖立着“陕北第一佛像”与雕刻着《道德经》的石碑;还有说不清的是佛还是道家的“无量祖师”,事实上,陕北的庙会信仰呈现出佛道一家的现象。,但对村民来讲这些问题并不重要,他们只是要找到一股灵验的力量去崇拜、感恩而已,纵使他们也说不清楚这股神秘力量具体指向如何,所有的不确定最终都找到了具有“灵验”功能的神。
之所以用此事实来说明村民日子好转的过程,并非以此判断灵验的有无、神力的真伪问题,而是为了揭示“灵验”的力量不仅指向神灵,其他所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最终也都归结为神灵。其实,上述事实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神灵的“灵验”,但所谓“解构”只适合外在的阐释视角,从村民的解读方式来看,事实本身与地方认识并不必然一致,当事实存在于村民生活之外时,那就不是他们的事实,所以,村民对“灵验”的解释也不一定迁就于事实。有龙王以来,村民从没有怀疑他的“灵验”,并且在不同时期都努力寻找“合理”的解释,神与人的互惠关系因为灵验的遗产被世代相传。
五、灵验的传承与再建构
从形式上看,神像渐渐由小变大,由一神到多神,庙堂从最初的犄角旮旯变成了现在占地十余亩的大庙,高家峁的庙会活动规模逐年扩大,成为陕北地区“排得上号”的村庙,都源于村民的感恩行动,实质上也是建构神灵的行动。
然而,神的灵验,不仅是形式的构建,更是经验层面上的构建与再建构,而且神的灵验必须以人们知道和能够知道的方式传播,灵验故事、神力传说成为确保神灵有效延续的基本形式。当然,村庄经过历史变迁,雨水不再是观测神灵唯一的“感知中介”,村民的需求、困难不只是“望天乞水以救之”,从农业生产到宅院风水,从治病救人到婚姻生育,龙王逐步衍生出了“佑护”“占卜”“倾诉”等祈福免灾功能,神效的表现无处不在,正如费孝通所言“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避灾逃祸”[注]甘满堂:《灵验与感恩:汉民族宗教体验的互动模式》,《民俗研究》2010年第1期。。虽然现在庙里已经“请来了”药王、财神和文昌等神灵,但每逢庙会,村民在这些庙堂里只是跪拜、烧香,一旦求医问药、预测时运,还是在龙王庙里进行。可见,尽管请来了各路神灵,他们之间各有分工,而人们对于龙王的认可和敬畏之心丝毫未减,村庄的历史记忆依然渗透在人们的言行之中,因雨水而形成的信仰成为世代村民挥之不去的乡土基因。
有一次村里要从山脚下往山上抽水,但是每次按开关就跳闸,电工检查几遍也没查出什么问题。期间有人说“是不是没有经过龙王的同意?”,因此,村民到庙里给龙王做了“说明”,并敬奉了一些“布施”。“一会会,水泵就能抽水了,再也没有出现过毛病。”
灵验传说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发生在人们身边的事件,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类似抽水的故事包括祈雨在内的众多传说都承载着灵验的传承功能,每一个神话传说都会强化神在人们心中“有求必应”的神圣地位。神话证实和确立了相关信仰最初合法性的基础,灵验传说不仅继续强化着神灵信仰的合法性,而且将遥远的人类始祖或英雄转化为人身边灵验的地方神灵,从而使之更好地佑护现实生活[注]安德明:《文体的协作与互动:以甘肃天水地区伏羲女娲信仰中的神话和灵验传说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当然,除了神“灵验”的故事,也会有一些“不灵”的事例,只是村民总会用一套自我解释的逻辑,让神“不灵”变为神“灵”,人对灵验的再建构还体现在人对神意的主观诠释方式。
高某从去年开始做生意,为求以后的财运,找主店“龙王”算了一卦,解曰:“占身不宜出入,失物难寻,病者作福,行人有信未至,求财迟,小口有灾,六甲难产,官事和劝,求官者未达,婚姻难合,六畜田蚕半好”。
该卦基本涵盖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问卦只能占卜某一方面,高某问的是“财运”,也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发财?该卦显示为“中下签”,显然,“求财迟”是神对她的解答,应被解释为发财还要很长时间。明显这一解释不符合求签者心意,在与解卦人沟通时,高某表示自己以前的确心太急,而且做生意也下手晚。不难看出,求签者问的是何时发财?是面向未来的问题,神意显示还需时日,而在心理作用之下,本来面向未来的事情被转化为以前的事情,巧妙地回避了不想面对的“求财迟”,神依然被解释为灵验,人也换得心安。
还需注意的是,神并不是无所不能、“灵验”也并非没有任何条件。正如一位当过干部的村民所说:
“哎,神神灵,人一敬。人品神着咧,神品人咧。再灵那是个神神,人不谋略不行。咋神神灵,人再一敬。人再谋略,神神不灵也不行。光靠人也不行。人发前行,神感应”。
事实上,当人们祈愿时,在内心里也有一层潜意识:人与神需要相互配合,如果神灵,而人不努力,是不可行的;过于离谱、想要坐享其成的祈愿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有时候祈愿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也没有出现什么意外与不测,日子过得平平常常、顺顺利利,在人们心中这也是“灵验”的体现。所以,人们心中的神“灵”不是无所不能,而是有限度的,神的“灵验”需要人心照不宣地默认与领悟,包括相互“体谅”,甚至“多数人的(沉默的大多数)灵验不必刻意去发现什么,而仅仅是等待一种不可能的生活转变成为可能的生活”[注]赵旭东:《龙牌与中华民族的认同的乡村建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六、结 语
由是观之,人与神互动本质上是一种“人格化”的互惠、互构活动,雨水作为中间媒介使人神各取所需,“灵验”成为解释这一过程的核心概念。可以看出,“中国崇拜的神明很多……神明没有绝对的意志和至上的权威”,神灵信仰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实践中近乎一种“自然”,但这种信仰始终以人的世俗欲求为中心,具有实用性特点,区别于西方的宗教信仰。[注]龙群、王立娟:《中西方人神问题研究综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所以,灵验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始终显现在生产、生活的事实里,而不是一种笼罩万有的结构和主观世界的意识,也正是在这些事实里建构了神的“灵验”。
另外,“灵验”也不是一成不变,它本质上是一个权变的概念,灵验的建构融合了历史变迁与地方认知心理。从“望天乞水”再到“不期而遇”转变过程中,灵验蕴含了社会的变迁,人、神的巨大变化更是强化了“灵验”的信仰。高家峁村1976年有了“他山之神”,1979年获得中央援助和粮食征购减免,到1982年人民公社解体、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施行,再到后期的逐步好转,然而,客观事实并没有解构神的灵验,在认知心理的作用之下,客观事实反而以一种“负强化”的方式加深了灵验的扎根。
进而言之,灵验更是一个复合概念,它不仅仅发生在人神之间,实际上,灵验存在于人、自然与神三重世界的相互关系之中,人与自然反复互动过程本身是二维关系,而构建出的神界力量使人的生活世界成为三维空间,任何一种力量都会受到其他力量的牵制,任何两者的关系也需通过第三种力量来解读,三者关系强度越大,灵验的效果愈明显,神灵越是让人们感到“触手可及”。其中人与神互动关系中的自然不仅是二者互动效果的反映媒介,甚至“自然成为了社会和文化关系的载体与映射,蕴含着丰富的人类情感”[注]朱竑:《自然的社会建构:西方人文地理学对自然的认识》,《地理科学》2017第11期。,自然的内涵已经延伸到社会层面,指向了所有人们不可控制、难以解释的力量;而在自然与神界的关系中,人的想象力或归因方式搭起了二者互动的桥梁,当人们的生活需求受制于自然力量时,便寻求一种可能解释的方式,使自然处于人的“控制”之下。随着社会历史变迁、生计方式转型,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着变化,新的祈愿和新因素的介入使灵验也经历了传承、建构与再建构的反复过程,三重世界关系的强度和内容与之前会有所不同,但人通过神来控制自然、神通过自然显示其意志、自然通过神意来与人沟通的三重世界的作用机制依然有效。
总体来看,在一个“我饿”的时代,苦难的记忆在高家峁村民心中种下了灵验的种子,而在“我怕”的现代社会则滋润了种子的发芽、茁壮成长。当然,高家峁之庙作为一个村庙自然并不能代表所有神灵崇拜,但它折射了“灵验”被建构的机制,雨水与“灵验”建构的背后是人、自然、神灵的复杂关系,灵验隐含了多重世界的勾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