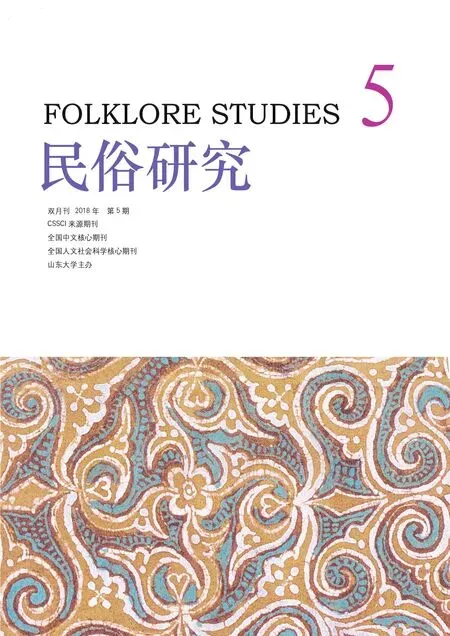道院与财委会:民国时期武夷山的寺产、茶产纠纷
曾 旭
武夷山市是福建省的一个县级市,位于武夷山脉北段,闽浙赣三省交界处。1989年以前,武夷山市称为崇安。崇安作为县的历史,始于北宋淳化五年(994)。民国初年,崇安县曾先后隶属北路道和建安道,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曾先后隶属福建省第十行政督察区(1934年7月)和第三行政督察区(1935年10月)。*刘超然:《崇安县新志》第二卷,地理,民国三十一年。
武夷山是著名的宗教圣地,寺庙林立,该地僧道借助优越的自然条件栽茶制茶,茶业成为寺观重要的经济来源。崇安县境内的马头、天游和碧霄等岩的道院,以盛产岩茶著称。然而,在晚清民国“庙产兴学”与“破除迷信运动”浪潮的冲击下,宗教界危机四伏,各处寺庙因产权关系时起纠纷。在这种状况下,崇安县寺庙道院的生存亦岌岌可危,庙产茶银屡次遭遇地方政府的抢占,由此引发道院、地方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争讼不断。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值崇安县动乱之际,地方政府趁时局动荡与人事变动,大肆侵吞庙产。民国十六年(1927),军阀入境,所有公产概归公有。民国二十年(1931),红军攻陷崇安县,地方人士纷纷出逃,*刘超然:《崇安县新志》第一卷,大事,民国三十一年。地方公产面临无主的局面。民国二十二年(1933),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五旅收复崇安,之后地方财委会重新清点地方公产,将僧道因避难出逃之寺庙指为“荒庙”,意图没收这些“无主”产业。随着僧道的回归,纷纷指责财委会没收庙产的行径。于是围绕着这些寺庙的性质及寺产的归属问题,双方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夺。武夷山马头、天游和碧霄三岩的寺产、茶产纠纷,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发生的。
谢和耐的研究指出,中古时期寺院经济发达,寺院占有地产、庄园、加工作坊和附庸劳动力并不断拓殖。除了举办公益慈善,僧侣还从事租赁、交易与放债等资本运作。宗教团体的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社邑生活和庙堂政治。*[法]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寺院经济研究》,耿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明清是寺院系统式微的时期,学界研究阙如,韩朝建很好地填补了这一薄弱环节,他将佛教置于五台山的社会经济脉络中,考量寺院在多行政体系地域社会中的角色,揭示明清之际五台山寺院系统与王府、卫所、州县及山民之间的互动及力量消长,凸显了寺院的政治与经济职能。[注]韩朝建:《寺院与官府:明清五台山的行政系统与地方社会》,人民出版社,2016年。近代以来,庙产问题再次凸显并呈现诸多新面相,吸引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杜赞奇认为,对于国民政府的现代化改革者而言,民间宗教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财政来源,政府在乡村消灭迷信的过程中,对集体财产和乡村财政来源的控制是一种明显的权势转移。[注][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第98页。梁勇通过研究巴县庙产兴学运动中学董与会首的诉讼纠纷,指出其实质是国家权力不断下移,渗透进乡村既有权力结构的过程。[注]梁勇:《清末庙产兴学与乡村权势的转移:以巴县为中心》,《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陈明华探讨了民间寺庙的产权结构与产权习惯,揭示了庙产从“私契”到“国法”的产权安排变迁。[注]陈明华:《从私契到国法:民间寺庙产权习惯及其制度化(1722-1927)》,《文史》2014年第2辑。林达丰梳理了民初庙产立法的沿革,指出庙产在法律改革过程中的逐步法人化。[注]林达丰:《民初庙产立法检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陈金龙从庙产律法着手,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教关系。[注]陈金龙:《从庙产管理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教关系》,《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总的来讲,围绕着寺院及庙产问题,学界研究成果颇丰。然而,学者对于庙产立法以后地方上具体施行的情况及纠纷处理研究不多。此外,对于各级政府围绕着庙产提拔所呈现出来的权力博弈也鲜有关注。本文以武夷山市档案馆藏的一整套诉讼材料[注]这套材料为笔者于2017年9月赴武夷山考察时由武夷山市档案馆提供,特此致谢。另,就笔者所见,肖坤冰在《茶叶的流动》(2013)一书中也曾关注过这桩官司,然其资料使用有限,对材料的整理和解读也过于粗糙,可商榷之处颇多。为基础,系统分析武夷山三岩茶产纠纷的过程,意图对上述问题予以关照。通过考察庙产在国民政府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命运,为理解近代以来国家、社会、政党及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启示。
一、道院的控诉与妥协
民国二十四年(1935)五月二十七日,武夷山马头、天游、碧霄等岩道院茶山的合伙人刘于豳呈文崇安县长张汉良,控告崇安县地方财务委员会[注]地方财委会于民国二十四年成立。见刘超然:《崇安县新志》第八卷,职官,民国三十一年。强抢道院茶产。据刘于豳呈诉,武夷马头岩、天游岩等道观的茶银,自去年(1934)被崇安县财委会没收之后,再无资本办理茶叶的采制,其本人筹集大洋计九百四十元作为资本,才使三岩的茶叶生产得以继续。茶叶制成后,运至赤石美盛茶庄,却遭到了财委会高腾的抢夺。[注]呈箱茶被抢资本无着恳请押还以保物权而维名胜由,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一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7。
与此同时,武夷山马头岩凝云道观住持潘玄逵、天游岩希微道院住持欧阳玄遧、碧霄洞长生道院住持吴元发也联名指控财委会,并就民国二十三年(1934)财委会没收茶银一事呈文张汉良:“窃民国二十三年马头、天游、碧霄等岩之茶银计共大洋一千八百三十元,概被崇安财务会无端混行没收一案,曾先后呈奉省政府批令,依照监督寺庙条例办理,并令第十区专员督饬崇安县长迅速办理等示,各在案,迄将一载,终未依照办理。黄前任不懂条例,心迹不明,业经上峰责备不浅,案悬至今,情实难堪。兹幸钧长治崇廉明素著,乞检案卷查阅,遵照省政府命令,依照监督寺庙条例办理,……饬令财务会将没收之茶银迅速扫数发还具领,以修庙宇而保名胜。”[注]呈请遵令依照办理饬还茶银以保名胜由,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一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7。道人所称的“第十区专员”,即“福建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本为南京国民政府为“剿共”而临时设立的制度,于各省划区,每区置行政督察专员一人,兼任保安司令,署理军民两政并督察下辖各县行政。[注]杨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创设》,《民国档案》2009年第1期。然而,从潘玄魁等人的呈辞看来,此番专员对县长的督导效果似乎并不理想,故而该案拖了将近一年也未准令办理。另外,本案所援引的《监督寺庙条例》,乃是国民政府时期颁布的最高宗教法律。[注]李继武:《论民国佛教界与中国宗教立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5月。自颁行之后,各地方政府处理寺庙纠纷,均以该条例为依据。[注]陈金龙:《从庙产管理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教关系》,《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宗教人士已经自觉地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了,这较之民国以前大量出现的暴力抗击攘夺庙产现象,无疑是个极大的转变。
对于刘于豳和三岩道人的控诉,财委会避重就轻,绝口不谈强抢茶银之事,而是在刘于豳和道士的人品道德上做文章,将其诬为“讼棍”、“妖道”:“查得该讼棍曾与一班妖道私立条约,如能如愿,与之中分庙产。是前之地方公产已为盗卖,后之绝嗣庙产又设计霸争,以个人之利益扰乱地方之是非”。[注]为盗卖地方公产教唆妖道健讼请严拘究办由,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一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7。除了财委会,联名者还包括崇安县临时清乡善后委员会常务委员彭维康、万钟琪,县图书馆馆长彭志英及各区的区长或代表。这份控词中流露出的对道人的不满和鄙夷,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这一时期民众对于僧道在观念上的转变。当寺庙财产的宗教光环开始逐渐褪色,直至成为道俗两界反复博弈的现实利益时,宗教本身的神圣性或被信仰的思想基础就已经处于被消解的过程中了。[注]里赞:《民国时期民间佛教信仰的失落》,《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4期。
面对咄咄逼人的财委会及地方社团,三岩道人只得作出妥协,由刘于豳出任停调公产,在每年收入的一千八百三十元中,交九百元为地方公用。[注]陆军独立第四十五旅政治训练处公函,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一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7。道院方面亦无异议,并且同意“自本二十四年份起,递年以庙产茶银二分之一缴交地方”。之前的茶银也不再请求发还,呈请县长将新旧两案一并销案了结。
尽管道院方面已经作出极大的让步,财委会及地方社团方面却不依不饶,要求县长和专员将提划庙产之事备案,并将三岩所立的议据归财委会保管,以坐实此事。甚至对道院的人事安排也横加干涉,“各该岩道士如有不当行为,或短欠茶价等项,任凭地方主管绅学各界换人管理”,提出由江元根接替潘玄逵的住持之位。
面对双方的协商结果,县长张汉良认为“似此办法,当属平允妥善”,但表示其本人“未敢抎专”,于是将此案经过情形及调解方案分呈专员盛开第和省主席陈仪。七月十六日,专员盛开第给出处理意见:“仰将所立议单转饬呈署,以凭察阅一面,并俟据情转报省政府核示后再行饬遵。再是项和议既係出于马头各岩道人自愿,应饬各觅原保缮录议单,呈请本署核办,以符手续。”[注]福建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指令,总字第27号,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一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7。接到专员公署指令以后,张县长饬令潘玄逵等人“迅觅原保,缮录和解议单,迳呈专署以符手续而便办理”。至此,该案以道院划拨茶银之半归地方公用为结果,暂告一段落。
二、专员公署的裁决与县府的拖延
民国二十四年(1935)九月,案情骤起变化。道院方面突然反口,否认之前的调解方案,声称划拨庙产方案乃是财委会逼立的,当时係“高腾私使便衣队带手枪,半途押人,逼立议据,逼具呈词”。省政府在获悉情状之后,认为“如该财委高腾确有私逼情事,应即立予撤惩”。潘玄逵等人请求县长张汉良饬令财委会遵照监督寺庙条例将茶银九百元发还给各道院。与此同时,道人出具了与本案有关的税验、印契、庙谱等证件,证明了道院的产权归属。
福建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对此案作出训令。专员认为,该道人能够出具道院的各项产证,且经建瓯县长密查,道人并无还俗及不安分情事,于情于理,都应当将茶银发还给道人。最终,专员公署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七日拟定了解决办法六条:
“1.该县财委会非法侵收马头岩凝云道院茶银八百三十元,天游岩希微道院茶银五百元,碧霄洞长生道院茶银五百元,应由该县查明如数发还潘玄逵、欧阳玄遧、吴元发等具领。2.该县五月间封存马头等岩茶四十二箱,出售后所得价银及扣存之现洋五百元,期票四百元,亦应一并发还该道人等具领。3.该县财委会高腾等所逼立之议据三纸暨呈县结案之呈文,应一并由该县查明注销。4.前项茶银发还后,应由该县责成该道人等将住持各庙院,妥为兴修,以保名胜。必要时,并准该县派员验看兴修情形,分期发还茶银。但兴修及发还期间,至长不得过六个月。5.马头岩等处庙产应由该县依照监督寺庙条例布告定期登记,并切实监督之。如各庙有违反情事,应先将违反情形,呈候本署察核示遵,不得再有非法处置。6.马头岩等处各庙财产登记后,应依法加以保护。其应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者,得由该县依照监督寺庙条例及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办理,但亦应先将办法等呈准本署,然后施行。”[注]福建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训令,总字第18号,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一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7。
该办法前四条涉及茶银的发还与使用。第五条要求寺庙定期进行登记。早在1928年10月,内政部公布的《寺庙登记条例》就规定:“凡为僧道住持或居住之一切公建、募建或私家独建之坛庙、寺院、庵观,均应进行登记。”国民政府进行寺院登记的主要目的在于控制寺庙财产,加强对寺庙的管理,推进寺庙的整顿。[注]陈金龙:《从庙产管理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教关系》,《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然而,由于僧道藏匿寺产及手续繁琐等诸多原因,进展并不顺利,成效甚微。此时专署提出庙产登记,其实质是想加强对寺庙的管控,将庙产纳入法制化监管体系。第六条要求寺庙兴办慈善事业。《监督寺庙条例》规定,寺庙必须按其财产情形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否则住持或僧道要被逐出寺庙或送法院究办。在1932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中规定,寺庙必须每年分两次向政府缴纳款项,用于民众教育、救贫救灾、育幼养老、公共卫生等公益慈善事业。[注]郭华清:《国民党政府的宗教管理政策述略》,《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2期。有学者指出,捐出庙产兴办慈善公益,名义上冠冕堂皇,其实质乃是强迫寺庙捐出寺产,将原来“庙产兴学”时期对庙产的随意侵夺合法化而已。[注]郭华清:《国民党政府的宗教管理政策论析》,《广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道院之所以胜诉,一个重要原因是能够出示税验、印契和庙谱等管业凭证。民国时期,庙产所有权缺乏相关的法律规范[注]林达丰:《民初庙产立法检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司法人员在审理之时并无现成的法律条文可以参考,于是他们引入民间庙产所有权习惯,作为判断寺庙归属的依据,进而作出裁决。一般而言,适用的民间庙产习惯主要有:土地最初来源、寺庙建立和修葺的资金来源、寺庙建制及继承人出任、捐税和登记凭证、寺庙所获捐地契约、寺庙所获捐产在该庙产中是否占支配地位、寺庙土地流转的契据等等。[注]王小丹:《民国庙产所有权认定的依据》,《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16年秋季卷。在本案中,专员公署判决的依据,正体现了民间庙产所有权习惯在司法过程中的适用。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中旬,福建省原有的10个区被合并为7个,崇安县由原隶属第十区改为第三区。[注]杨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创设》,《民国档案》2009年第1期。与此同时,崇安县长也改由陈正民接任,这桩官司于是移交至第三区专员和陈县长手中。潘玄逵等呈请新县长遵照专员公署核定办法发还新旧茶银,陈正民则训令财委会,饬将各款、期票、议据分别发还并注销结案。然而,财委会并未遵令发还茶款,而且一拖就是四个月。民国二十五年(1936)三月七日,潘、宋、吴三人再次呈文陈县长,恳请其严催财委会发还新旧茶银。[注]呈庙宇残破名胜倒塌恳迅遵照核定办法饬还新旧茶银以便遵令妥为兴修而保名胜由,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二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9。陈县长并未作出明确批示,而是以不知道前任县长张汉良是否移交为由,再次将事情推诿给财委会。无奈之下,潘玄魁等只得第三次呈文陈县长:“玄逵等曾以庙宇残破,名胜倒塌,恳迅饬还新旧茶银以保名胜,并敬问张前县长,对于二十四年五月所存现洋五百元,究竟最终有无咨交,恳再明白批示。”
于是,前任县长张汉良“最终有无咨交”,成为左右本案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民国二十五年(1936)四月二十四日,潘、宋、吴三人致函福建省主席陈仪,希望传缉前县长张汉良到案追究:“张前县长汉良,扣存现洋五百元,任意侵吞,席卷而去,并无咨交,似为法所难容,伏见钧府组织审查交代委员会,正为此种官吏而设。若不恳请缉案追还,任其吞没逍遥,匪特有污廉洁之政府,且有妨害新生活之运动[注]该项运动由蒋介石于民国二十三年在南昌行营发起,民国二十六年崇安县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主任干事由县党部指导员兼任,继改由县长兼任。二十九年十二月,各区始成立分会。见刘超然:《崇安县新志》第七卷,党务,民国三十一年。,为此理合备情,呈叩察核,准予严令传缉崇安前县长张汉良到案究追,押还茶银大洋五百元。”福建省主席接潘玄逵等人的陈诉后,于五月十二日训令崇安县政府“令仰该县长查明咨催发还并具报。”接省政府训令后,新任县长杨永礼随即致函前县长张汉良,敦促其就“崇安武夷山马头岩凝云道院住持潘玄逵等呈控侵吞公款一案”作出回复。五月二十九日,张汉良作出了回应,他极力撇清自己与此案的干系,托称“各岩茶息,均为前崇安地方财务整理委员会主席高腾经手,与敝任绝对无涉。”[注]咨复崇安武夷山马头岩茶息均为前崇安地方财务整理委员会主席高腾经手与敝任绝对无涉由,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二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9。前县长的推诿,高腾的出逃,使得该案再度陷入僵局。
三、箱茶的抢夺、封存与发还
民国二十五年(1936)六月二日,县财委会委员长吴心友呈文县长杨永礼,以潘玄逵等意图藏匿、私运岩茶并枭欠应缴地方茶款为由,恳请饬警将该岩茶封存,并将该年九百元茶银缴交地方。[注]呈为马头天游碧霄等岩道人潘玄逵等违背前议枭欠应缴地方茶款恳请饬警将该岩茶封存并传照议将本年九百元茶银缴交地方以重公帑乞察夺施行由,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二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9。随后,吴心友等率警察、壮丁将马头、天游两岩道院所产之茶四十一箱强行封存。天游岩道人卢元宾被拘走,潘玄逵等则出逃至建瓯。六月四日,潘、宋、吴三人呈文县长杨永礼,痛陈财委会“拦截瓜分马头等岩箱茶”之情状,乞求县长“准予遵照依法保护,批令马头等岩箱茶,自由放行”。六月六日,杨永礼复函潘玄逵,称其正在请示处理之中,令静候解决。实际上,杨永礼只是在敷衍潘玄逵等人,他此时正谕令第六区区长衷理基先将岩茶扣存保管。
六月七日,衷理基奉令前往马头等岩封存箱茶,发现原封之茶四十一箱,只剩二十七箱半,于是将具体情形呈报县长:“经察悉,天游之茶,业已全卖兴记茶商,茶已无存。碧霄之茶,亦已扫数拚与奇苑茶商,其拚价五百元,该道人等并已向支清。惟马头尚有存茶,计二五箱七件半,大囤箱二十件,大小共廿七件半,经职将该存茶扫数封存于职公所,遵暂负保管之责矣。再查道人潘玄逵,事前避匿,不知去向。欧阳玄遧已死,吴元发在岩。本日由马头将封存茶挑到职公所,共去发力大洋五元六角,合并声明。”[注]遵令封存马头岩茶大小共廿七件半具报候示由,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二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9。县长获悉情况后,发给封条二十八条,令衷理基查收封存,听候请示处理。
面对道院方面的指控,财委会反咬一口,将三岩道院指为“荒废寺庙”,称“自民二十年,本县被匪沦陷之后,交通断绝,所有马头等岩寺庙住持,非死亡即还俗,于是马头等岩,成为一片荒土”。提出应当按照《监督寺庙条例》第四条“荒废之寺庙由地方自治团体管理”的规定,将三岩收归公有。诚然,《监督寺庙条例》对荒废寺庙确有上述规定,但对于“荒废寺庙”的认定,却没有明确的标准。内政部曾指出,“荒废寺庙之条件,所谓经久无人管理,其经久之范围,不仅以三月为限,且应以客观事件认定之。”[注]《内政年鉴》,礼俗篇,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3页。司法院也提出,“若原有僧人管理之寺庙,偶因事故,至未定管理谁属者,只得谓管理人暂缺,不得谓之寺庙荒废。”[注]《司法院解释荒废寺庙疑义》,1933年3月,《内政公报》第6卷第13期,第659页。在本案中,三岩道人是因为避祸才被迫离开的,时局平稳后又重新归来。由此看来,三岩道院实在算不得是“荒庙”的范畴。
财委会还指控刘于豳“垂涎马头等岩寺庙茶产,阳借保存名胜之名,阴遂其侵吞公产之谋,嗾使业已还俗之道人潘玄逵等伪造证据,呈控前地方财务整理委员会非法侵占……此项马头一案,时而自愿销案,时而藉词翻案,皆土劣刘于豳个人以公产为利薮,稍不满其欲望,即反覆播弄,不特藐视地方,实是捣乱法权,按之国法,势所难容”。指责潘玄逵还俗、挪用私用庙产茶银、不登记庙产、不举办公益事业,违反《监督寺庙条例》。基于此,财务会恳请县政府“迅将该潘玄逵等逐出寺庙,或依法究办,并处刘土劣于豳勾结唆讼、侵吞公产应得之罪,所有该岩茶款,除拨一部份管理各该岩寺庙之外,余悉归地方办公益及地方慈善事业费用”。[注]呈以马头等岩应归地方管理恳按照监督寺庙条例迅将该潘玄逵等逐出寺庙或依法究办并处土劣刘于豳勾结唆讼侵吞公产应得之罪乞示遵行由,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二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9。
崇安县的绅商学各界代表亦联名上书县长,称“山中各寺庙之产茶为每年惊人之巨数”,然而道人对款项并未公示并报告官署。各岩住持道人不宣教义、不修庙宇,平时更是少在庙里,“或久住建瓯,或寄迹民家,每年仅茶市到庙,取得茶款,余未尝履庙一步”。三岩交纳一半茶银后,剩余者“并未置分文于灯油香火间”,而是由道人“完全瓜分,各遂私囊”。各界代表对于逼立议据一事也矢口否认,辩称“果议据逼立,该道等何不于订议数日后即向县府及专员署声明无效,奚必于五月间订议而待八九月始来翻异,其显係刘于豳从中揽讼,隙利变乱是非”。对前专员盛开第的权威更是提出质疑,称“不知该道等如何魔力,前盛专员竟翻前议,令将全部茶款扫数发还,并令将逼立议据等注销,此中情节,不问可知”。呈请县长驱逐道人,将庙产收归地方自治团体管理。[注]呈为马头岩道人潘玄逵等戒律不修混迹空门劣绅刘于豳揽讼希图隙利恳请分别严办并请转呈专员公署取消前案由,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二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9。
双方各执一词,案件悬而不决。如今顺着财委会和地方团体联合指控之势,杨永礼县长也主张惩处潘玄逵和刘于豳:“拟将揽讼之刘于豳、还俗之潘玄逵等,予以分别惩处,一面另选住持料理寺务,以保名胜”。至于递年交缴的茶银仍照原议,本年的岩茶仍由第六区暂时保管。县长将此处理意见于六月十五日分别请示省政府和专员公署。
专员公署否决了杨县长的意见,仍坚持前任专员盛开第的判决及核定办法,要求县长遵照前令办理,“倘该财委会委员吴心友等,有复蹈高腾故辙,目无法纪行动,应立予制止。”[注]福建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训令,专一字第580号,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二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9。尽管专员公署的处理意见已经非常明确,但杨永礼仍不甘心,在六月二十一日呈复专员公署的文中称:“查此案先据财务委员会及地方各社团呈诉,讼棍刘于豳唆使道人潘玄逵不守清规,违背前约,请将岩茶扣存等情,当经县长查明属实,饬逼先将岩茶二十八箱暂为扣存。”眼见专员公署的训令无果,潘玄逵、宋元胜只得于六月二十九日再次呈文县长杨永礼,诉说道院的困苦,乞求县长饬令财委会发还被扣箱茶。然而杨县长并不为所动,复函嘱其“静候饬遵,毋庸多渎”。
正值胶着之际,省政府的处理意见终于下达。省主席陈仪表示“据呈前情,如果属实,该吴心友等殊为不合”,令县长“迅即查明原案,切实秉公办理具复”。[注]省政府训令,府民甲9336,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二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9。七月三日,省主席再次发文,声明支持专员盛开第原定处理办法六条,并斥责杨县长不查案遵办。至于潘玄逵等人“果有不守清规情事,应由该县长酌量情形,依法秉公核办具报”。[注]福建省政府指令,府民甲10441,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二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9。在给省主席的复函中,县长严斥潘玄逵“名为道人,不守清规,久寓建瓯,日事嫖赌,无异还俗。对于寺庙毁坏,茶山荒芜,不图修葺整理,徒知每届庙产稍有生息,驰令返收获,混迹空门,坐食地方之款,利令智昏,莫此为甚。”提出“拟将该不法道人潘玄逵等遵令驱逐出境,另招主持。至本年各岩产息,暂由地方妥慎保存,候交新招主持,以供修葺寺庙之需。”[注]呈复办理马头等岩争执一案经过情形请察核由,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二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9。
大约是慑于杨县长关于驱逐出寺的处分决定,潘玄逵于七月二十八日呈文县长,表示因此案“缠累不休”,情愿“照旧年调解之议约,再就半数中减半,计大洋四百五十元,归作地方财务会公用”。恳请销案,“并乞迅将前项封存茶件,如数发还给领,俾清完案而免讼累”。省主席的敦促训斥,加之潘玄逵的让步,终于使杨县长松口,同意了潘玄逵的呈请,“岩茶二十八箱,准予先行发还,仰即到府具领”。[注]民字第237号,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三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8。至此,潘玄逵终于如愿领回了被抢夺的岩茶二十八箱。然而,县长却仍然坚持驱逐潘玄逵,另招住持。此后,围绕着潘玄逵的住持之位和缴纳茶银的问题,仍然是纠纷不断。
四、案情的翻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八月四日,县长杨永礼训令财务会,将大洋四百五十元尅日缴府,至于“该款作何用途,仰候另行饬遵”。八月七日,财委会复函称“本拟即日缴交,特以款未收齐,是以暂缓”。在潘玄逵所认缴的四百五十元大洋中,包括现款一百五十元,二百元十天期票一纸,一百元阴历七月底期票一纸。目前财委会收缴上的只是现金部分,刨掉挑茶傤茶工食费用十五元八角,实存现款一百三十四元二角。杨永礼在收到现款后,作出批示:“俟期单支讫,全数发交马头等岩专属修理寺庙之用,任何机关不得动用分文”。[注]民循字第187号,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三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8。同时命令财务会催缴剩余的期票三百元。[注]财字第126号,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三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8。
九月,杨永礼离任,蒋伯雄继任崇安县长。九月二十日,专员陈遗风致函蒋伯雄,令其遵行之前省政府关于“该道人潘玄逵如果不守清规,应依照监督寺庙条例第十一条、第七条各规定办理”的指令。[注]福建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训令,专一字第732号,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三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8。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伯雄复函陈遗风,呈报了关于缴纳茶款及潘玄逵住持之位的处理情况。蒋伯雄称,三岩于民国二十四年缴纳之九百元係由前财委会委员长高腾经手,因高腾早已因案逃匿,故无从追缴。民国二十五年所缴纳之四百五十元,将“托交绥靖公署驻崇办事处,于武夷山建筑公墓时,各岩庙宇顺便代为修理”。[注]民国二十五年,驻闽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建中正公园于天游峰、筑赣粤闽湘鄂剿匪军东路军阵亡将士墓于武夷宫,见刘超然:《崇安县新志》第一卷,大事,民国三十一年。至于道人潘玄逵,“为慎重处理起见,各岩庙宇,拟仍准该道人等暂为主持,一面随时派员监督”。
民国二十六年(1937)四月十二日,案情再起变化。道院方面再次对缴交茶产之事表示反悔。面对新任县长蒋伯雄,试图推翻前议。潘、宋、吴三人呈文蒋县长,指责前县长杨永礼不遵前督察专员核定办法,反而偏袒财委会,抢夺其民国二十五年庙产之茶,直至硬勒去茶银四百五十元,始将箱茶发还。道人还称,当箱茶领回后,发现已被财委会窃去顶上奇种茶一百八十三斤。连年以来被财委会所侵吞的茶银共计三千一百八十元。此种情状如果继续,则各道院势必荒废。为此恳请蒋县长按照监督寺庙条例,保护三岩道院庙产箱茶。
面对道院的责难,财委会方面也不甘示弱,一一予以还击。财委会委员长王朝桢[注]王朝桢于二十六年二月在任。见刘超然:《崇安县新志》第八卷,职官,民国三十一年。呈文蒋伯雄,称民国二十四年起递年缴交九百元茶银归地方公用的方案,乃是经过双方公允并呈请张前县长了结在案的。之后由于道人受到讼棍刘于豳的挑唆,不按约定缴纳九百元茶银,财委会前委员长吴心友才将各岩茶产暂时封存,直至杨前县长作出驱逐出寺的决定后,潘玄逵才“惧罪觉悟”,托人向吴前委员长再三要求,称愿缴交四百五十元为地方公用。[注]第2245号,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三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8。
综合道院与财委会双方意见后,县长蒋伯雄作出判定,认为缴交四百五十元归地方之办法“尚属平允”。而这些归公用的茶款也已经“编列廿五年度地方款预算书内,呈奉省府核准公布在案”。同时责问道人“何以不住道院,逗留建瓯”?面对蒋县长的质问,潘玄逵回复称,其上年七月二十八日并未与财委会议定办法,实在是财委会欺骗逼立的结果。道人痛陈“该财委会欺骗盗窃,靡所不为,玄逵有何与之议?且按监督寺庙条例规定,庙产,任何地方团体不能移用,玄逵既为庙院住持,何敢与议办法?此种呈报之议定办法,实出欺骗,而且冤诬”。为此,恳请县长为其申冤并注销此议。至于居住建瓯一事,潘玄逵也予以否认,称“玄逵等常住道院,只因请讬建瓯人办理呈文时或来往,并非逗留建瓯”。
民国二十六年(1937)六月,专员陈遗风训令县长蒋伯雄参照专署前拟六项办法及监督寺庙条例切实核办具报。[注]福建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训令,民字第230号,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三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8。换句话说,专员同意潘玄逵等人的呈请,令县长发还三岩道院茶银。蒋伯雄则以“潘玄逵等每年认缴茶款四百五十元,归入地方预算公产收入项下,以资拨付公益事业之用”为由,对专员的训令不予遵从。
面对县长的强硬态度,省府只得出面干涉,并与县府之间展开了一番拉锯战。省府质问县府“所收潘玄逵等年缴茶款四百五十元,拨充何种公益或慈善事业之用”?并饬令其“详细拟具计划及预算,呈由该专员核明,加具意见,呈转察夺。在未奉准以前,不得动支”。[注]福建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训令,财字第240号,民字第230号,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三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8。紧接着,省府追问“该崇安县政府所收潘玄逵每年认缴茶款四百五十元,在本年度县地方概算内,列何节目”?[注]福建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训令,财字第293号,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三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18。十二月九日,蒋县长复函称“本县所收潘玄逵每年认缴茶款四百五十元,係列在县地方概算内第四项第一目公产茶款之内”。民国二十七年(1938)一月二十一日,省府再次发问:“查崇安县二十五年度及二十六年度预算岁入,经常门均列有公产茶款一千元,而原编概算书并未据详细说明。究竟潘玄逵认缴茶款四百五十元,是否包括在内,无法悬揣。至尚有五百五十元,又係何人认缴之茶款?”[注]福建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训令,财字第324号,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五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21。二月四日,蒋伯雄回复称“该潘玄逵认缴茶款四百五十,是包括本县地方概算书内。至尚有五百五十元,係地方公产,各岩茶山租金收入”。
就这样,终蒋伯雄之任,这场口水官司也未见分晓。随着蒋伯雄的离任,新任县长刘超然接管了此案。
五、道院摊捐的减轻
民国二十七年(1938)四月十八日,三岩道人呈文新任县长刘超然,称道院负担太重,希望恩准减轻捐交财会款:“窃武夷马头、天游、碧霄三岩,自师祖手栽种茶山,藉维庙中香油粮食等。由民国二十四年,每年马头岩捐交财会款二百元,天游、碧霄两岩各捐交财会款一百二十五元,合四百五十元。庙中别无出息,全资茶叶生活,奈近年茶山失败,茶价又跌,……贫道等不揣冒昧,为此据情泣诉,呈请察核,恩准将三岩捐交财会之款分别减轻,以保名胜,以免绝粮。”[注]为呈负担太重恩准减轻捐交财会款以免绝粮由,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五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21。
四月二十二日,刘县长饬令财委会就此事给出处理意见。[注]去文财字第983号,崇安县政府,武夷山寺产茶产纠纷,第五卷,全宗号2,目录号5,案卷号21。财委会委员长王朝桢断然否决了道院的请求,认为“蒋前县长任内,对该三岩茶款,仍予潘玄逵等照廿五年四百五十元之额缴交,已属逾格体恤,今该道人潘玄逵等又如此狡猾,分外请求,实是得寸思尺,贪婪无厌也。”恳请县长转饬道人潘玄逵等“依照廿四年九百元原议案交缴,而维地方经费”。刘县长采纳了财委会的意见,令道人“遵照缴纳为要”。
六月三日,潘玄逵等再次呈请刘县长减轻缴交茶款,称“以前茶价未跌,每斤价值二元余,尚能照额缴交”,而现如今“茶景日衰,茶价日下,缴费浩大,收入短拙”,以至于“庙破修整乏资,佛前灯火冷淡”。恳请县长“大发慈悲,乞赐减轻缴纳,俾得名山不灭,胜迹长留”。出人意料的是,此番恳请居然收到了成效,县长终于作出了让步,“除天游岩茶款一百二十五元,前议拨由武夷公园公墓管理委员会经收充作经费外”,将马头、碧霄两岩应缴茶款三百二十五元,拟准减为二百元。
随着道院摊捐的减轻,本案也就落下帷幕,至于后续是否还有纠纷,也就不得而知了。
六、结 语
民国初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依法治教”成为民国政府宗教管理的显著特色,保护宗教自由也成为当时社会各界公认的一项基本原则。此后,历届政府在制定宗教政策时,始终坚持“信教自由”这一原则不变,这就为宗教人士保护民间庙宇及庙产提供了最根本的法律依据。
尽管有信教自由的基本原则,但由于财政拮据,国民政府还是经常在庙产上做文章,期望利用庙产兴办学校或慈善公益事业,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注]陈金龙:《冲突与调适: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互动关系探微》,《法音》2006年第3期。尤其是在本案发生的1935至1938年之间,抗战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考验,使得基层政府和社会都将佛道两教视为社会的边缘力量,僧道所掌握的庙产也成为各方都企图利用的资源。[注]里赞:《民国时期民间佛教信仰的失落》,《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4期。在本案中,三岩道院庙产之所以得以保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住持能出具税验、印契和庙谱等产权证明文件。面对地方财委会近乎横蛮的侵夺及县长模棱两可的态度,这些产权文书可谓是最后一道屏障。专员公署在“吊验该道人等所持证据”,验明无误之后,作出道院胜诉的判决,而此判决也得到省政府的核准。本案发生于近代产权凭证制度尚未建立之时,从中可以管窥契约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行政长官的判决依据充分反映其对民间契约习惯的尊重,亦体现了民间产权习惯在司法和行政实践中的适用,为我们理解近代以来习惯法典化的进程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道院与财委会的庙产纠纷,逐渐升级为省府和县府之争。省、县之间的权力博弈,让道人的诉求有了权势的依托,使得庙产在“维持名胜”的名义下得以保存。县府之所以能够与省府抗衡,与国民政府对“分税制”进行的系列改革是分不开的。自从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以后,国民政府颁布《财政收支系统法》,确立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体系,打破了以往县级财政依附于省府的状况,赋予了基层政府财政的独立权力。[注]参见刘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地方财政研究(1927-1937)》,安徽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这种状况下,在庙产问题的处理上,县长也就有了与专员公署和省府抗衡的资本。
专员公署这一层级的虚实,是学界颇为关注的话题。作为省政府的辅助机构,专署在提高行政效率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须知,同时期崇安县发生的茶产纠纷不止三岩道院,还有蔡成裘案、陈来成案、南山寺案、徐兴金案及江玉娇案等等,如果没有专署居于省县之间运筹协调,这些案件的解决将遥遥无期。然而,专署的职权却是很不充分的,从最初接手本案的黄相忱县长对专员训令的置若罔闻,到崇安县的绅商学各界代表对专员权威的公然质疑,都证明了这一点。最明显的就是蒋伯雄主政崇安时期,县府与省府的那场持久拉锯战,专署在两者之间只是起到“传声筒”的作用,显得丝毫没有话语权。有学者认为,专员公署乃是从虚级向实级过渡的一个层级,这种“两级一辅”的格局构成了“虚三级制”。[注]参见翁有为:《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探析》,《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翁有为:《南京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法制考察》,《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就专员公署在本案中的角色观之,此论颇有见地。
道院虽然胜诉,但这种胜利是有条件的,那就是需要划拨部分庙产归地方公用。然而潘玄逵两次对“自愿”划拨庙产表示反悔,也是造成本案的纠缠不休的重要原因。综观此案,潘玄逵与其说是自愿划拨,不如说是面对财委会专横强权之下的一种委曲求全。实际上,寺庙财产在依法纳税后,依照惯例,是不需要摊纳地方花费的,南京国民政府对此也没有明确规定。1934年11月,内政部明确指出:“查寺庙应否摊派地方捐项,监督寺庙条例并无规定,但该项捐项,果有合法根据,而又系公平摊派者,寺庙自应与一般人民一同缴纳,不得独持异议。”[注]《内政部就僧道管理寺庙财产应否摊纳捐项事咨各省市政府》,1934年11月15日,《内政公报》第7卷第46期,第2411页。当然,内政部的指令也存在很大漏洞,何谓“合法根据”,何谓“公平摊派”?这根本就没有标准,到头来还是拥有话语权和解释权的地方当权派说了算。于是,也就出现了崇安县财务委员会强迫道观摊纳地方花费之事。这种隐含着地方权势对道院胁迫的“自愿”请求,日后必起争讼。武夷山的茶产、寺产纠纷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就寺院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中古以降直至明清,国家对于寺院的控制还仅仅停留在规模与数量上,而清末民初“庙产兴学”以来则升级为结构上的取缔。在此种情状下,各地的僧道纷纷在夹缝中求生存,这也正是“道士农林化”兴起的大背景,武夷山道院的产业结构与诉讼行为就是突出的表征。正是在“庙产兴学”与寺院求存的过程中,明清以来日渐萎缩的寺院经济又呈现出被重新激活的态势。
武夷山茶产、寺产纠纷,诉讼时间长,涉及面极广,既具典型性,又有地方特色。本案表明,近代庙产问题错综复杂,涉及清末以来“庙产兴学”、民国时期的宗教立法、民间产权习惯、财政体系变迁等诸多问题,是理解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与地方关系的极佳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