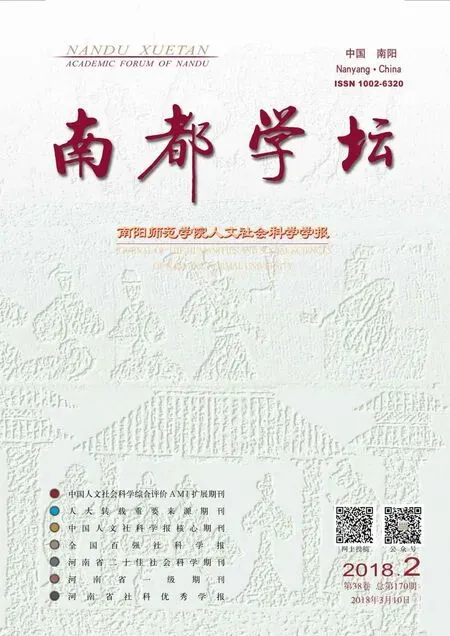张綖“婉约—豪放”二体说来源新探
岳 淑 珍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关于张綖在其《诗余图谱凡例》中提出的“婉约—豪放”二体说,朱崇才先生《论张綖“婉约—豪放”二体说的形成及理论贡献》认为“《诗余图谱凡例》中的‘婉约—豪放’二体说来自《草堂诗余别录》中的‘精工—豪放’二体说”,“‘二体说’与《别录》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是张綖“在长期的词学实践中,特别是在写作《草堂诗余别录》《诗余图谱》等著作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思考,经历了概念的不断选择、提炼及升华才提出的”。他指出:“《凡例》中三次使用‘词体’一辞,在此之前,至迟在写作《别录》时,张綖就已使用这一概念了。”“《凡例》中‘词体’这一概念,正是来源于《别录》。”“在《别录》中,张綖初步提出了‘精工豪放二体说’,正可以看作是《凡例》‘二体说’的雏形。”“《别录》所提出的‘精工豪放二体说’,尚不够成熟,只有到了《凡例》提出‘婉约豪放二体说’,张綖的这一观点才得以用成熟的形态准确地表述出来。”并得出结论:“在‘词体’‘婉约’‘豪放’的选择及解释、‘婉约’‘豪放’对举、‘以婉约为正’等四个方面,《凡例》所提出的‘二体说’,都可以在张綖词学实践特别是《别录》中找到源头。”[1]笔者认为,“婉约—豪放”二体说源自《草堂诗余别录》的说法,值得商榷。
一
就目前所看到的文献而言,《诗余图谱》最早刊刻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这是流传至今张綖词学论著中刊刻最早的一种,此刻本卷首有张綖作于嘉靖十五年夏四月的《诗余图谱序》,而他的《草堂诗余别录》完成于嘉靖戊戌(1538年)五月,张綖《草堂诗余别录序》云:“当时集本亦多,惟《草堂诗余》流行于世,其间复猥杂不粹,今观老先生硃笔点取,皆平和高丽之调,诚可则而可歌。复命愚生再校,辄敢尽其愚见。因于各词下漫注数语,略见去取之意,别为一录呈上,倘有可取,进教幸甚!”*张綖《草堂诗余别录》卷首,明黎仪抄本。以下所引张綖《草堂诗余别录》评点文字,均出此本,不注。(“老先生”当非朱崇才先生文中所谓的张綖其师王西楼,即王磐。因为王磐辞世于1524年。)张綖的《王西楼先生诗集序》云:“嘉靖甲申(1524)九月,綖登西楼,先生执綖手泣曰:‘予恐时至,弗及言惟玆遗稿托君。’时先生略无恙,綖颇怪之。后数日,先生果中疾,不能言,月余竟厌世。”*清左辉春《续高邮州志》,清刻本。(老先生为何人,俟考。)并且在《草堂诗余别录》末另行书写:“嘉靖戊戌五月十三日录上。”*张綖《草堂诗余别录》卷末,明黎仪抄本。此句与卷首序文末“别为一录呈上”上下联系紧密,当为张綖《草堂诗余别录》的完成时间。而嘉靖十五年刻本《诗余图谱》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之前少有研究者见到,从朱崇才先生文中可知,他阐述“二体说”的形成过程主要的理论依据是张綖编撰的《草堂诗余别录》,而他依据的《诗余图谱》版本则是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谢天瑞刻本,显然,他当时应该是没有看到嘉靖十五年《诗余图谱》刻本。笔者2007年4月在上海图书馆查阅文献时,曾抄录《草堂诗余别录》全文,对张綖的评点内容比较熟悉,此时亦无缘研读嘉靖本《诗余图谱》,因此,阅读朱先生的文章后亦同意其观点,并在拙文《张綖〈草堂诗余别录〉考论》中引用其见解[2]。2014年11月,由同门张海涛君惠寄嘉靖本,笔者才有幸一睹其姿容。又一次研读嘉靖十五年《诗余图谱》刻本及《草堂诗余别录》时发现,“二体说”与《草堂诗余别录》确实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但并非如朱先生所阐述的那样,“二体说”源自《草堂诗余别录》。
张綖“二体说”的具体内容为:“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张綖《诗余图谱》卷首,嘉靖十五年刻本。张綖的“婉约—豪放”二体说,是其在词体创作及编撰《诗余图谱》的词学实践过程中,受明代文坛复古思潮影响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当时文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而词的复古无疑是宋词了,而整个两宋,词坛的主流风气则是重婉约,以婉约为词之“本色”,所以张綖引用苏轼对秦观词的评价以及陈师道对苏轼词的评价指出:“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其《诗余图谱》所录“必是婉约”的选词原则也正是这一词学观的反映。
二
阅读《草堂诗余别录》的点评文字就可以发现,张綖在《诗余图谱凡例》中提出了“二体说”以后,似乎觉得不够周延,有进一步作出解释的必要,因此他在《草堂诗余别录》的评点文字中不断阐释“二体说”的内涵。关于婉约词,他认为应该“曲折”“有味”“隽永”,应该“精工”“精丽”“蕴藉”“思深”,有“意致”“有余韵”,可“声歌,叶管弦”,“音调谐婉”“含蓄无穷”,有“言外之情”“温雅蕴藉”,有“含蓄不尽之意”,有“思致”,“精工蕴藉”“温雅富丽”。他最欣赏的婉约词有两类,一是有寓意而蕴藉者,如其评点李玉《贺新郎·篆缕销金鼎》一词道:“寓意托怀,无嫌闺院。”评点曾纯甫《金人捧玉盘·记神京繁华地》一词道:“此词前叙神京繁华风俗,足以见宋亡之故矣。后段悲痛隽永,有黍离之风焉。”评点鹿虔扆《临江仙·金锁重们荒苑静》一词道:“此词写感慨之意于蕴藉之词,谓之古作;而音调谐和,谓之今词。而语意高古,愈味愈佳,允为词式。”评点岳武穆《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一词道:“托物寓怀,悠然有余味,得风人讽咏之义焉。”二是自然精工蕴藉者,他在评点周邦彦《解语花·风销烟腊》一词后加按语云:
美成词正为不能丽耳。夫丽者,岂在纨绮朱翠乎?不假铅华而光彩射人,意态殊绝者,天下之丽也。故西施衣毛褐而国人称美,秦兰服敝襦而陶榖心醉。今美成多取古人绮语,饾饤成篇,种种皆备,而飘洒之风,隽永之味,独其所少,如富室女,服饰虽胜,欠天然妩媚耳。
张綖尤其欣赏“天然妩媚”者,因而在评价郑中卿《念奴娇·嗟来咄去》一词时总结道:“词体本欲精工蕴藉,所谓如登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袪者。故以秦淮海、张子野诸公称首,六一翁虽尚舒畅自然,而温雅富丽犹夫体也。”张綖对婉约内涵的阐释与宋人的理解高度一致[3],由此亦知其对宋代词学观的认同。
张綖在《草堂诗余别录》中亦对豪放词作了客观评价,进而界定豪放风格的内涵。他评点叶石林《念奴娇·洞庭波冷》一词云:“词气跌宕,不可遗。且此调属角音,少平韵者。”评点晁无咎《洞仙歌·青烟羃处》一词云:“前段‘永夜闲阶卧桂影。露凉时、零乱多少寒蛩’,既已佳矣。后段‘待都将许多明,付金樽,投晓共、流霞倾尽。更携取、胡床上南楼,看玉做人间,素秋千顷’。尤为高旷神爽。”评点苏轼《西江月·点点楼前细雨》一词云:“意度旷达,超越千古矣。”评点吕居仁《满江红·东吕先生家何在》一词云:“通篇词俱冲淡高远,太羹玄酒,别是一家滋味。”评点辛弃疾《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一词云:“稼轩此词,为韩南涧寿,可谓高笔……高怀跌宕,则又东坡之流亚也。”评点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一词,更赞赏其旷达胸怀与雄视千古的气度:
赤壁周曹之战,千古英雄遗迹,坡翁既作赋以吊曹公,复作此词以吊周瑜。赋后云“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及此词结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其旷达之怀,直吞赤壁于胸中,不知区区周曹为何物,不如是,何以为雄视千古乎?
“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这是张綖对豪放风格内涵的界定,通过其对豪放词作具体的评价,我们可知他所谓的“气象恢弘”是指“词气跌宕”“高旷神爽”“意度旷达”“冲淡高远”“高怀跌宕”“雄视千古”,他欣赏的是“豪”与“放”之作,即词气跌宕、意度旷达的词作,尤其是那些旷达高远之作。这与他在《诗余图谱凡例》中对豪放词的态度有明显区别:“今所录为式者,必是婉约,庶得词体;又有惟取音节中调,不暇择其词之工者,览者详之。”如果按照张綖此时(1536年)的词学观念,在《草堂诗余别录》中,张綖完全可以不选录豪放词,而对其欣赏的婉约词多加点评,《草堂诗余别录》所选多数是婉约词,这说明张綖在词学实践的过程中词学观念在不断变化,因此自己在《诗余图谱凡例》中提出“二体说”时对“存乎其人”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在对《草堂诗余别录》的具体评点过程中,张綖发现,同一词人兼具两种风格,即婉约与豪放集于一身虽然很难,所谓“人或不能兼”,但又不是绝对的,他在评价辛弃疾《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此词《诗余图谱》不选)一词时指出:
稼轩此词为韩南涧寿,可谓高笔。尝谓:词有二体。巧思者贵精工,宏才者尚豪放。人或不能兼。若幼安“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之类,绸缪情语,虽少游无以过。若“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座中豪气,看君一饮千石”,及此词之类,高怀跌宕,则又东坡之流亚也。
辛弃疾融婉约、豪放于一身,其婉约词虽秦观“无以过”,而其豪放词,又可与苏轼匹敌。他还认为具有“宏才”者也可以创作出含思婉转的婉约词,如他在评陈亮《水龙吟·闹花深处层楼》时指出:“以龙川之豪,降而为此调,所谓能赋梅花,不独宋广平。”又如章质夫“建功戎马,亦人豪也”,而其《水龙吟·燕忙莺懒》“咏柳花,形容曲尽,工于铅椠之士,万不能及”。因此,在张綖看来,具有一定才情气质的词人创作特定风格的词作具有天然的优势,因此有的词人创作婉约词多一些,譬如秦观,而有一些词人则创作豪放词多一些,譬如苏轼。但才情气质与作品风格不是绝对的对立,而词体创作的历史也正是如此。
张綖在此指出:“尝谓:词有二体。”“尝谓”即曾经说过,因此,就现有存世文献而言,“词有二体”应该是指此前在《诗余图谱》中提出的“婉约—豪放”二体说。张綖在《图谱凡例》中把词体风格分为二体的同时,明确指出这两种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乎其人”,即词之风格与作家的才情气质相关,但没有具体指出作家具有什么样的才情气质才能创作出相应风格的作品,而在评点《草堂诗余别录》的过程中,他通过对众多词人词作的评价,而后指出“巧思者贵精工,宏才者尚豪放”,所谓“巧思”,《汉语大字典》“巧”字条云:“《广韵·巧韵》云:‘巧,善也。’”[4]412“巧思”即善于思考,可引申为思维细密深微;所谓“宏才”,《汉语大字典》“宏”字条云:“广博;宽泛。又指胸怀开阔,度量大。晋陆机《吊魏武帝文》:‘咨宏度之峻邈。’”[4]916张綖所谓的“宏才”当指既有广博知识又有阔大胸怀之人。《草堂诗余别录》从词人的角度,或者说从“存乎其人”的角度对《图谱凡例》所提“二体说”作了必要的解释和补充。“精工”与“蕴藉”在《草堂诗余别录》中出现频率很高,各有六次,最终合为一体作“精工蕴藉”是结束在《草堂诗余别录》后集对郑仲卿(原文不注作者)的《念奴娇·嗟来咄去》评点上(见上文引)。通过具体的词作评点可知,在张綖看来,“精工”与“蕴藉”当为同义词。
三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婉约—豪放”二体说不可能如朱先生所论是“来自《草堂诗余别录》中的‘精工—豪放’二体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草堂诗余别录》中从“存乎其人”的角度所提出的“巧思者贵精工,宏才者尚豪放”不能称之为“二体说”,因为它不是就词体风格而言,而是就词作者而言的,因此亦不能与《诗余图谱》中提出的“婉约—豪放”二体说相提并论。“婉约—豪放”二体说是张綖在词体创作以及编撰《诗余图谱》的词学实践过程中,受文坛复古影响的大背景下提出的,《草堂诗余别录》中提出的“巧思者贵精工,宏才者尚豪放”是对“婉约—豪放”二体说的进一步阐释。
张綖的“婉约—豪放”二体说基本符合宋代词体的创作实际,其内涵亦与宋代的词学观念基本一致,因此在当时及后世不仅被广泛关注,而且对词坛产生了深刻影响。但遗憾的是“二体说”仅作为按语附在《诗余图谱凡例》之末,在《凡例》中,人们不能清晰地看出张綖对“婉约—豪放”二体说的详细阐释,再加上《草堂诗余别录》发现较晚,因此学者往往感慨张綖“二体说”内容之简约。现在人们可以依据《草堂诗余别录》,反观张綖词学观中的“婉约”“豪放”这一对词学范畴的具体内涵,更加深入地研究张綖的词学思想。
[1]朱崇才.论张綖“婉约—豪放”二体说的形成及理论贡献[J].文学遗产,2007(1):72-79.
[2]岳淑珍.《草堂诗余别录》考论[J].新乡学院学报,2008(5):94-97.
[3]岳淑珍.唐宋词学批评中的本色论[J].中州学刊,2015(11):146-151.
[4]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1卷[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