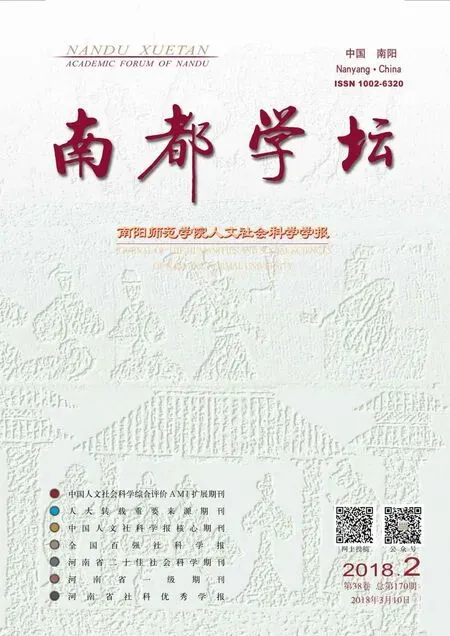杜甫乐府诗的叙事风貌及其转型价值
吴淑玲, 韩成武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与之前的唐代乐府诗相比,杜甫的乐府诗有很大改变,由少用乐府旧题,改为较多使用乐府新题,在写作中注入较多的叙事成分,用叙事手法写人记事,注重场面描写,使得他的乐府诗体现出与之前唐代乐府诗有很大不同。之前的唐人乐府诗注重抒情,叙事成分较少,内容也比较个体化。杜甫则是回归汉乐府并超越汉乐府的叙事特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含蕴深厚,在杜甫诗中最富有诗史意义。
一、杜甫乐府诗的艺术风貌
(一)完整的故事性
杜甫的乐府诗继承了汉魏乐府“缘事而发”的特点,记事性很强,绝大部分乐府诗都有具体的事件,而且叙事相对完整。比如《前出塞九首》就是以一个被征入伍边塞从军的士卒的口吻,写出了他在从军路途的遭遇、自己的所思所想和对立功边塞的态度:“九首诗虽独立成章,然从离家赴边到沙场征战的经历一气呵成,‘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转韵诗读’,连接起来俨然是一篇士兵的小传,可以说是一首初具形态的文人叙事诗了。”[1]27“杜甫正是看到了士兵从家乡到边塞,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必定会有情感的矛盾运动和此消彼长,他抓住并极力渲染这一点,以此来展开情节,推动事件向前发展。”[1]29又比如《哀江头》通过杨贵妃的命运展示唐王朝的历史悲剧,梳理出来后可以清晰地看到杨贵妃当初被宠幸时唐王朝的盛世繁华,看到唐玄宗被迫入蜀并导致杨贵妃死亡的悲剧结局,也就看到了大唐王朝走向衰落的命运。再如《哀王孙》中的王孙,安史之乱中流落长安,因为没有办法生存,竟然向同样落难的杜甫求助,祈求成为杜甫的奴隶以获得活命的资本,而杜甫亦是被俘入长安,根本没有能力帮助王孙,可见这位王孙的沦落已经是连乞丐也不如了。而落难中的杜甫只能用不可能为王孙解决任何问题的劝慰之语告诫王孙休要抛头露面,要等待大唐王朝收复长安的时间。王孙求助无果的悲惨命运,揭示了安史之乱中唐王朝皇室贵族的沉沦。
杜甫的这些叙事诗,与汉乐府不同之处在于,汉乐府的叙事,立足于生活的日常,只是具体的人和事的具体记述,而杜甫则将这些事件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展现时代的变迁,即使像《大麦行》这样的短歌,也是揭示的边塞处于拉锯战地区人民的苦难。正如葛晓音先生所说,杜甫的乐府诗是“通过高度概括的场面描写,以史诗般的大手笔展现出广阔的社会背景,从而突破了汉乐府叙事方式的局限”[2]。这是大手笔的诗人所达到的高度。
(二)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
杜甫生活在以诗歌传情为主的盛唐,其诗坛的主流写作方法是抒情,即使是乐府诗也是以抒情为主,大多数诗人并不注意人物形象本身的刻画和描写,人物形象相对比较晦暗。如果一定说形象比较突出,比如李白乐府诗中抒情主人公自我的形象往往比较突出,但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乐府诗叙事中的主人公,而且李白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是在抒情中留给读者的印象,不是乐府诗歌叙事中作者描写的主人公的形象。但在杜甫的乐府诗歌中,乐府诗歌叙事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比较突出。“三吏”“三别”中的几篇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石壕吏》中力护家人、善于应对、挺身从军的老妇,《新安吏》中愚执公务、罔顾左右的抓丁小吏,《潼关吏》中信心满满的关吏和忧深虑远的诗人,《新婚别》中心思细密、娇羞无限、识得大局、忠贞节烈的新妇,《无家别》中满心凄惶、无奈上阵的败阵老兵,《垂老别》中拄杖踽踽、弯腰驼背、公忠体国的老人,都是杜甫留给后人的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从叙事的角度而言,都是诗中的人物形象,具有客观反映现实生活的特点。
(三)长于剪裁和细节描写
乐府诗歌的记事特点决定了其与歌行、律诗不一样的艺术追求,而对事件的剪裁和细节描写,是乐府诗叙事水平的重要标识。
杜甫的乐府诗讲究剪裁,几乎是后人仿效的典范。杜甫懂得剪裁的必要,而且善于以简约的篇幅,把复杂的故事生动地叙述出来,把深刻的主题表现出来。剪枝裁蔓以突出主干,是杜甫最拿手的艺术能力之一,以《石壕吏》为例,《石壕吏》是杜甫在华州司功参军任上所作,为唐王朝邺城兵败后抓丁的场面之一。本课题责任人之一的韩成武教授在《杜诗艺谭》里有详细的分析,移录于此:
诗的开端二句,光彩就已显现出来。从时间上看,第一句写 “暮”,第二句就入“夜”,时间有跨越。再从事件来看,第一句写的是诗人投宿,第二句写的是差吏捉人,两句在所写的事件上跨度也很大。如果从生活的原貌去考虑,由傍晚时诗人投宿,到夜间差吏前来捉人,这中间该有众多的生活琐事须由诗人去经历,比如,他来到石壕村,要寻找住处,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岁月,人们是不肯轻易留生人住宿的,所以他一定会吃到不少闭门羹;好不容易找到一户善心人家,得以住了下来;还要吃晚饭;洗脚;上床;入睡。这些生活琐事是必须经历的,但诗人把它们统统剪掉了。因为这些琐事与要叙述的中心故事无关,与所要表达的主题无关,如果写了它们,势必会造成累赘,喧宾夺主,乃至冲淡主题……
这首诗明显使用剪裁手法的地方还有很多。例如,“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字面上说的是各走一方,似乎老翁的逃走,老妇并不知道,可是当我们读到下文,发现老妇向差吏报告屋里人口时没有说出老翁来,便可明白,她是知道老翁逃走的。那么,老两口在紧急之际商量对策的情节是被作者剪掉了。剪掉了这个情节,又能在适当的地方给予交代,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最讲究处是叙述差吏和老妇在门前较量的场面,作者只写了老妇的答话,而没写差吏的逼问。对于老妇的答话也仅仅写了十三句。然而诗中分明又说“夜久语声绝”,从“夜捉人”而至“夜久”,这说明门前的这番较量是历时颇长的。倘若只是老妇一人说话,说完这十三句话有几分钟就足够了。实际上,作者是为了节省字面,剪掉了差吏的逼问,而采用“以答代问”的方式,通过老妇的答话去间接地表现差吏的逼问的。这从韵脚的变换来看,用意也很清楚。杜甫把老妇人的十三句话分为三个内容层次。第一层讲外面儿子们的情况,第二层讲屋里人口的情况,第三层讲她个人请求服兵役。而每一个层次的讲话内容,都意味着差吏的一层逼问……作者没有正面去写差吏的逼问,而是通过描写老妇人的三层答话,把差吏的步步紧逼、毫不留情的嘴脸表现出来。这个门前较量的情节,倘若在一般作者的笔下,是一定要把双方的问答言语通通端上来的;然而,如此下笔,把一切都端给读者,把本来属于读者的想象空间,通通占满,把读者的艺术再造的途径,通通堵死,还有什么艺术可言!这样的诗,确乎“老妪能解”了,但艺术的生命却同时被扼杀了。苏辙曾批评白居易的叙事诗,说道:“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苏辙《栾城集》),张戒也认为白居易的诗“其词伤于太烦,其意伤于太尽。”(张戒《岁寒堂诗话》)清人黄子云也认为白居易的叙事诗有这种缺陷,他说:“事太详则语冗而势涣,故香山失之浅;太简则意暗而气馁,故昌谷失之促。二者均有过、不及之弊。非有才气溢涌、手眼兼到者不能。”(黄子云《野鸿诗的》)
从《石壕吏》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杜甫的剪裁手法主要有两点。其一,果断地剪掉与中心故事无关的生活琐事,使故事的主干得以突出;其二,对于中心故事的某些情节,凡是能在其他情节中予以照应、填充的,则把它们剪掉,由此出现的情节断线,交由读者通过联想去作补充。作者是绝不怀疑读者的阅读能力的。[3]
杜甫十分注重细节描写,在描写细节上则不惜花费笔墨,在细节中描写现实,在细节中传达诗人对生活的理解。如《新婚别》中那位与丈夫“暮婚晨告别”的新妇的内心世界,她又担心自己的身份还不明确,又希望与丈夫两相厮守,又不得不支持丈夫走上前线,又要为丈夫守节卸掉红妆的种种心理细节和行动细节,写出了一个在战乱中出嫁的新婚女子缠绵悱恻而又不得不决绝告别的形象;《无家别》中那位败阵的士兵归家后面对田园荒芜、狐狸横行和只有“一二老寡妻”的空置村庄的悲戚和伤感;《垂老别》中老人与妻子告别时,“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的细节展示出老人们在安史之乱中的可怜可悲状况,他自己“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的细节,则翻起了无限波澜,老人家对当年开元盛世的留恋、对今日盛世不再的无奈,都是用细节传达出来的。细节是有生命力的,是会说话的,它将生活的情状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四)善于通过人物语言传达情境
记事的作品,在事件中一定有人物的活动,人物形象的刻画也是杜诗非常成功的地方。杜甫刻画人物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让人物自己站出来说话,像《兵车行》《哀王孙》《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新婚别》等,人物的语言刻画都非常成功。
《兵车行》里,杜甫以记事诗人的身份出现,与参战士卒进行了一组访谈式对话。在这里,诗人的问话已经省去,只留下了参战士卒的答语,所谓“道旁过者问行人”的道旁过者,也许正是诗人杜甫,而“行人但云点行频”之后的连续十二句话都是参战士卒对“点行频”的看法,是诉说征戍对参战士卒和对后方生活带来的灾难。所谓“长者虽有问”的长者应该正是诗人杜甫,而“役夫敢申恨”之后的话语,正是“役夫”所申之恨:兵役不断,赋税连连,人心思安,以至于连中国传统的生男生女观念都想改变了。在这样的谈话中,杜甫写出了参战士卒心中的幽怨,同时也借参战士卒之口表达了人们的反战情绪。
《哀王孙》中,诗人自己的形象透过诗人对流落王孙的关心话语展现出来。诗人遇见王孙,“问之不肯道姓名”,说明诗人很关切王孙的身份,接下来的话语则是诗人告诉王孙,根据你的长相,我已经识别了你的身份,你的身份对外瞒不住,接着又劝慰王孙,要在城中小心隐藏,等待国家中兴。诗人的细心、诗人的劝慰、诗人对国家未来走向的充满信心,都通过诗人对王孙的劝慰之语展现出来。
《石壕吏》是通过对话描写人物,展现时间进程的。诗中共隐含着三组对话:从“三男邺城戍”到“死者长已矣”,是第一次对话。读者可以想见,这是老妇针对县吏的第一次逼问诉苦的。在这以前,诗人已用“有吏夜捉人”一句写出了县吏的猛虎攫人之势。等到“老妇出门看”,这些县吏便扑了进来,四处搜索,却找不到一个男人,扑了个空,于是怒吼道:“你家的男人都到哪儿去了?快交出来!”老妇泣诉说:“三个儿子都当兵守邺城去了。一个儿子刚刚捎来一封信,信中说,另外两个儿子已经牺牲了!……”她很希望以此博得县吏的同情,高抬贵手。不料县吏大发雷霆:“难道你家里再没有别人了?快交出来!”(隐含的)这就引发了第二次答语,老妇只得针对这一点再次诉苦:“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因为如果县吏不问老妇要人,老妇没有必要交代出有小孙子,也没有必要说“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但县吏仍不肯罢手,要求他们家一定要出人,这才有了第三次答话:“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老妇主动请求从军,这其实是老妇很聪明的一种应酬之语,她很希望以自己的老迈应付县吏,更希望县吏说一句:“行了老婆子,你都这么老了,算了吧。”但她没有想到,县吏竟然同意了,老妇人也就不得不最后走上从军之路。在这组对话里,暗含着官吏的凶狠暴戾和不依不饶,写出了老妇人虚与委蛇、巧妙对答、大义护家的性格特点。
《新婚别》全是新婚女子与丈夫分别时的窃窃私语、缠绵倾诉。她依偎在夫君身边,以“席不暖君床”倾诉她的依依不舍、浓情蜜意,以“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表述自己心中的尴尬,以“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欲追随夫君又怕影响军中士气的矛盾复杂心态,以“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向夫君表达自己的忠贞之心。王嗣奭:“一篇都是妇人语,而公揣摩以发之。有极细心语……有极大纲常语……真无愧于三百篇者。”[4]一声声,一字字,都是诗人替新婚女子设想,替她向新婚的丈夫告别,既表达了依依不舍、忠贞不贰,又表现了鼓励丈夫、不扯后腿,分明是一位既小鸟依人又深明大义的女子。
(五)叙事视角的多样性和场面的客体化
杜甫以客观身份记事的作品很多,他很善于进行场面描写,很多都是具体的历史场面的再现,其叙事视角大多时候是第三人称叙事,但有时候诗人也会出现在作品中,而诗人出现在作品中,似乎又往往只是诗中人物而不是诗人自己。杜甫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展示其记事的客观性,使场面尽可能呈现客体化特征。如《兵车行》中的送别场面: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此诗以旁观者的视角入笔,描写所见的悲壮淋漓的送别场景:车声轰响、战马嘶鸣、戎装束箭的士兵、奔跑相送的爷娘妻子、灰尘弥漫的天空、牵衣顿足直达云霄的呼号,构成了壮观悲惨的送别场面,渲染出人们对生离死别的痛苦感受和不愿参战的激烈情绪。但当后来“长者”与参战士卒对话时,“长者”的问话隐身了,只有参战士卒的答语,但所答之语是对“长者”之问的回应,而“长者”很显然是诗人自己,这原是第一人称叙事加入进去的,但第一人称隐身了,而经过这样处理以后就显得极为客观。
《悲陈陶》中唐军惨败的场面: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这是发生在756年(唐肃宗至德元年)冬的一场大战,唐军跟安史叛军在这里作战时,四五万人几乎全军覆没。来自西北十郡(今陕西一带)清白人家的子弟兵,血染陈陶战场。这首诗是完全的第三人称叙事,是诗人在长安遥闻败信后的记录。诗人没有描写四万唐军如何溃散乃至横尸郊野,而是用“血作陈陶泽中水”的恐怖景象暗写唐军惨败的惨烈场面;“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是野外没有声息的场面,渲染的是“天地同悲”的气氛和感受。诗的后四句,从陈陶战场掉转笔来写长安城中,写了两种人两种场面,叛军血水洗箭,都市纵饮狂歌的场面,彰显着叛军的残忍、无情和张狂;人民抑制不住心底的悲伤,面北而哭,为义军,也为肃宗所代表的朝廷,更为他们内心的企盼。所有这一切,都熔铸了诗人为国家哀痛的真情。
再如《石壕吏》中的抓丁场面: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其实从“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一句我们已经知道,杜甫当时就在石壕村的抓丁现场,但整个过程,作者却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客观地记述了整个过程,完全没有进入到叙事过程中,只在事件结束时以“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又露了一下脸,老妇掩护老翁逃走的场面、磨磨蹭蹭开门的场面、来来去去应对盘问的场面,加之最后诗人告别的场面,就构成了“邺城兵败”后的人间悲剧。最后告别的场面诗人登场了,却在客观上隐藏老妇被抓的场面。
又如《哀王孙》中的唐玄宗逃走的场面和诗人与王孙江边会面的场面:
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
唐玄宗出逃的情景,到奉先县接家眷的杜甫并没有亲见,所以叙事口气很客观,而自“腰下宝玦青珊瑚”后,就是诗人亲眼所见和亲自参与的事件了,所以写王孙的极其困顿,都是诗人自然出面,了解情况、进行劝慰,历历如在目前。诗人也是以心痛的心情展示安史之乱后的长安及王孙公子生活的巨大变迁,这些与唐玄宗开元盛世生活形成鲜明对照的场面,在诗人心中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在读者心中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成为盛世唐朝衰落的象征。
《前出塞九首》则采用的是代言体,诗人化身为诗中的主人公,代主人公立言,以亲身经历的种种事件和内心深处的变化表达对战争的态度:“第一人称的自白方式客观地展示了士兵的心路历程和人生经历,而赴国之义与恋亲之情交战所引发的矛盾和痛苦也从士兵的心路历程中真实自然地流露了出来,这是靠作者的主观抒情无法达到的效果。”[1]28这种写法更有表现力也更具说服力。
二、杜甫乐府诗的转型价值
杜甫的乐府诗,是中国古代乐府诗发展的新阶段,它标志着一种新的乐府创作体式走入人们的视野。其转型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一)创制新题乐府,把乐府引向了摆脱旧题、题符诗意的创作阶段
杜甫之前,唐代的乐府诗基本上是旧题乐府,如王维、高适、李白等,而杜甫却根据时事创制“新题”。由于新题“缘事而发”的特点,题目和内容融合得更加紧密,据题写作的特征更加明显,因而创作更加扣紧主题,更加自由疏放。《蔡宽夫诗话》:“齐梁以来,文士喜为乐府辞,然沿袭之久,往往失其命题本意。”[5]608这是说,旧题虽然有其价值,但时间久了,就已经难以适应后来诗歌写作的需要了,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初衷也产生了距离。而杜甫创制新题乐府的做法,打破了旧题的束缚和限制,无复依傍,随事立题,题目和内容完全准确地融合到一起。如果说,李白是把乐府旧题写到了无以复加,是对旧题的终结,那么,杜甫则是开创了新题乐府崭新的局面,开始了乐府诗的一个新时代,《蔡宽夫诗话》:“皆因事自出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述,真豪杰也。”[5]609胡应麟:“少陵不效四言,不仿《离骚》,不用乐府旧题,是此老胸中壁立处。然风、骚乐府遗意,杜往往深得之。”[6]这是对杜甫在乐府诗歌创出新格局方面的肯定。从此以后,乐府诗以新题为主,并逐渐摆脱音乐的束缚和限制,入乐和不入乐已经不是创作者追求的目标。从此以后,新题乐府创作成为一种路径,为唐代的乐府诗开辟了新的天地,也为后世乐府诗能够更好地反映生活找到了一条可以自由创作的康庄大道。
(二)改变了盛唐诗歌以抒情为主的格局
从唐诗发展史的视角看,杜甫的乐府诗具有写作手法转折的意义。在此之前,唐朝诗歌无论初唐和盛唐,也无论何种体式,基本都以写景抒情为主。仅以盛唐而言,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李白等人的作品,也均是以写景抒情为长。单就乐府诗而言,也是如此。盛唐的这些名家,也都有乐府诗题,如王维《陇头吟》《从军行》《苦热行》《少年行四首》等、李白《蜀道难》《北上行》《短歌行》《侠客行》《从军行二首》《行路难》等,虽是乐府题目,却以抒情为主,叙事的成分很少。而杜甫的乐府诗基本以记事为主,如《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哀江头》《哀王孙》“三吏”“三别”等,每首诗都有自己的主人公,每个主人公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述说,每个故事也都有头有尾。这种以叙事为主要格局的诗歌组篇方式,将唐朝诗歌更进一步拉向现实、拉向民间、拉向社会,让唐诗在抒情之外又有了另一种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方式。这之后唐诗的发展,叙事和抒情成为两种基本表达方式,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只以抒情为表达方式了。
(三)思想内容的全景性拓展
杜甫的乐府诗内容深刻丰厚,为历代诗人所不及,大凡社会生活所应该关注的,他都有所触及,而更主要的是,他的乐府诗往往放置于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那些与国家重大决策直接相关的事件,往往关系国计民生、关系人民命运,如开边战争,国势衰微,兵役之苦,社会动乱,粮食生产,民间风习等。宋人评价其诗“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就杜甫的乐府诗而言,此句虽然有过之,但仍是同时代诗人所达不到的。关于此方面内容,本文作者另有《杜甫乐府诗的史诗性审美》进行详细论述,此不赘言。
概而言之,所有杜甫的这些努力,为拓展乐府诗歌的表现范围提供了很好的范本,成为后世乐府诗写作不受拘束和更加自由的样板。杜甫不仅仅是写作律诗的圣手,同样也是写作乐府的大家。他与李白一起,为唐代乐府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陈桂华.情义交战下的征人故事[J].杜甫研究学刊,2000(1).
[2]葛晓音.论杜甫的新题乐府[J].社会科学战线,1999(1):200.
[3]韩成武.杜诗艺谭[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4-8.
[4]王嗣奭.杜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2.
[5]吴文治.宋诗话全编[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6]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