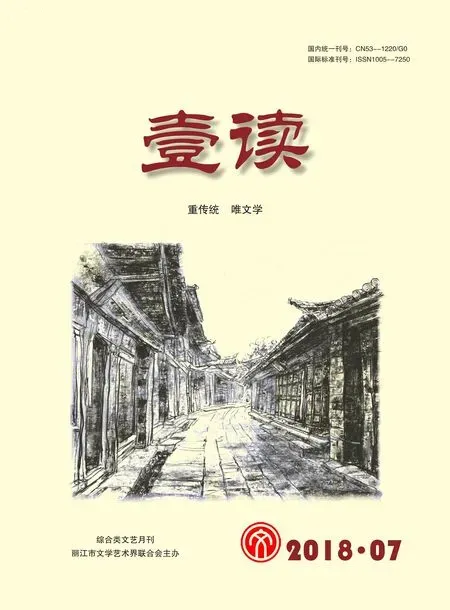“错位”的文学理念与当代云南精神
——当代云南作家文化身份及写作策略浅析
周文英 和建华
(本文作者为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师 )
云南对于外界而言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这一地方神奇的自然景观与独特的民族文化无不让世人以一种惊异的,猎奇的,然而又以某些莫名其妙但可以肯定是非我族类的眼光相看待。这是一种对待云南以及云南文化的复杂心态,也是对我们云南人的一种“他者”的眼光的观照。然而,我们自己又是如何或者应该如何看待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精神呢?下面,笔者将通过文学创作者的身份和文学创作的策略对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由《春城赋》引出的论题
1987年冬日,旅居昆明的纳西族学者周善甫写成后来一时传为奇文的《春城赋》。《春城赋》征材聚事、写物图貌,命义闳博、措辞富丽,全面地赞颂了昆明的历史文化和风光物貌,被公认为继孙髯翁《大观楼长联》之后,多角度多层次吟咏昆明的最佳文学作品。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相反,我们的问题才刚刚开始,“赋”这种中国古典文学中比较难把握的文学体裁在西汉兴盛,唐宋式微之后,到明清即成绝响,遑论民国。周老先生的这一举动是否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笔者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云南作家的“错位”的文学理念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云南作家文化身份与写作策略的变化,周善甫写《春城赋》只是这一问题的一个特殊表征。
文学,今日无法对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文学是什么?”这一关于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已经越来越被现代的学者们悬隔。事实上,在思想观念不断更新以致我们以“多元文化共生”这样的概念来阐释所处的知识大爆炸时代之时,我们已无力解决这一古老的文学本体论问题了。我们以文学理念、文化身份以及写作策略这一更具体但也更明了的阐述来论述问题。
在本文中,所谓文学理念即作者的文学观,它关涉作者对于“文学是什么?”这一关于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基本观点;文化身份指的是作者在创作或在其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作为作品书写者主体身份的文化属性,它关涉作者的文化背景、文化立场和文化观念;而写作策略指的是作者围绕着“写什么?”“怎么写?”“ 为何写?”以及“为谁写?”四个问题而展开的思考及其在具体创作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
从作家的文化身份来看,至少包涵二层面:一为云南籍的作家,如李乔、晓雪、于坚、夏天敏等等;二为旅居或客籍云南作家,如彭荆风、汤士杰等。前者以本土、本民族的文化身份写作,在地域、民族等的问题上以“自我”的眼光进行观照,作品具有“自我叙述”性质。如李乔在边疆民族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就有着较强烈的自传色彩,其代表作《欢笑的金沙江》除具有“十七年文学”的总体特征外,这种作家的文化身份以及“自我叙述”性质是不容忽视的。后者的作品具有较明显的“他者”眼光以及比较文化的意识。如彭荆风的《驿路梨花》,其诗意的叙述,是在隔了一定的主客体的审美距离,在文化比较的潜意识中才可以完美表达出来的。而汤士杰的作品则是以审美距离,文化比较的意识更为浓烈的情况下对云南的人、事、物从一个当代作家的身份姿态所做的极具个性化的书写。
从写作的策略来看,云南当代作家中既有极具先锋性质的于坚的“诗人写作”。于坚自己曾说“在这个诗歌日益被降级到知识的水平的时代,我坚持的是诗人的写作。”并认为“诗人写作乃是一切写作之上的写作。诗人写作是神性的写作,而不是知识的写作。在这里,我所说的神性,并不是‘把你教为神圣’的乌托邦主义,而是对人生的日常经验世界中被知识遮蔽着的诗性的澄明。” 云南当下作家群里,也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的海男的小说创作。而丽江作家木祥的小说《杀猪巷的女人》里的男性和女性世界,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和地位,还处于男性世界和父权制度设定的主题、视觉和风格中。因此,木祥在创作中,强调女性意识并不仅仅是回到女性封闭的内心世界,而是完全放在现实背景上展开了女性主义叙事。促使当代流行的那种软弱的、碎片式的和梦幻式的“女性内心独白”,改变成开发式的更有力的对话。与历史对话,特别是与变动的现实对话,在政治性的双重结构中,也就是在反抗男权神话谱系及其泛政治权力的社会场景中来揭示纳西族的历史面目。但更多的是沿着传统现实主义并吸收了部分现代主义写作手法,并且有所发挥的写作策略在当代云南文学创作实践中占了上风。如以夏天敏、雷平阳等人为代表的昭通作家群,包括年轻作家赵清俊的短篇小说集《透明的夜晚》,从自己切身的生活经历,丰富深厚的现实经验、真切的心灵的感受和敏锐的艺术感悟,勾勒出中国当下高寒山区的真实画卷。在这一个个缩影中,流溢出作者对文学对生活的执着和热爱——生命在梦想中展开。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来存在着一个云南作家的“错位”的文学理念问题。在当今喧嚣浮躁的文坛里,标新立异、各抒己见已为常态和惯性之时,云南作家并不故作姿态或盲目跟风,而是有所秉持,在沿着现代云南作家的足迹继续前进。这就显得云南作家的文学理念不够“与时俱进”,因而出现了某种“错位”。事实与价值对立在认识论上就是一种“错位”,是理性与感性冲突的一种必然结果。“错位”虽然不一定正确,但“错位”不是错误。马斯洛在谈到人的“自我实现”时有这么一种观点,基本心理是,人的认识越客观,越是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则它就越是远离价值。知识分子几乎总是把事实与价值看成是反义词。认为两者是互不相容的。当下云南作家群的创作精神和意义就显现在“错位”的文学理念里。
二、云南诗人于坚的创作轨迹及其文化姿态
于坚及其所属“新生代诗人”曾是当代中国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于坚如彗星般划过当代中国文学的天空,留下一道属于当代云南人的于坚自己的文学创作精神轨迹。关于于坚,几本权威的著作曾做如下评述:
“于坚的诗歌写作可以分成几个阶段:80年代初期是以云南高原的人文地理环境为背景的高原诗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河流》《高山》等;80年代中期是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口语化写作时期,代表作有《尚义街六号》《罗家生》等;90年代以来是注重语言作为存在之现象的时期,主要作品有《对一只乌鸦的命名》《0档案》等。其中长诗《0档案》带有很强的实验性质,其独特的诗歌内容、诗体形式和语言组织方式,得到一部分读者的赞赏,也受到另一些人的非议。但不管怎么说,该诗在诗人的创作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于坚的诗歌已结集出版的有《对一只乌鸦的命名》《诗六十首》等。在诗歌创作之余,于坚还写作诗学随想与诗论,结集为《棕皮手记》与《人间笔记》等。” 此外,于坚近来也写了不少反思性较强的文化随笔和散文。
“于坚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致力于不同于‘朦胧诗’的新的诗歌美学实验,以调侃、游戏、甚至堆砌的手法表现现代生存的平面化、生命的分裂感和心灵的破碎状态。”“《0档案》这首诗是对当代个人成长史的反观,它的意义远不止深入触及社会与个人的龃龉,而且也意味着‘第三代’诗歌对于语言与存在有了新的反思与展望——通过书写档案之外无数游离的、平庸琐碎的个人日常生活细节的狂欢,我们既看到了现实与语言的分裂,也看到了渺小、平庸、琐碎的个人生活细节的文化意义和用它构建诗歌空间的可能性。”
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云南诗人于坚的文学创作的精神轨迹。我们认为重要的是于坚作为一个云南人,一位诗人,一种属于云南又不仅仅属于云南地域的文化姿态——生于大山但并不像祖祖辈辈“守望大山”,而是要“走出大山”,走向世界,面对现实,活在当代,感受当代,并且不忘记回身“凝视大山”的当代云南人的开拓精神,一种“敢为天下先”的云南人的气魄!
三、昭通作家群崛起的文学意义
或许有人会认为诗人于坚只是个特殊例子,是个单数,仅仅一个于坚还不足以代表云南当代文学,那么“于坚之后”呢?昭通作家群的崛起对于云南当代文坛就不是一个特殊的或偶然的文学现象了。1996年12月,中共云南省委六届四次全委会通过了《中共云南省委关于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加强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首次明确提出“让云南民族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努力把云南建设成为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大省”。以此为起点,云南开始了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研究和筹备工作。昭通作家群的崛起与这个大背景有着内在的关联。如果说于坚用自己的喉咙发出了先知先行者的声音,那么昭通作家群则是在云南建设民族文化大省的道路上群体的多声部大合唱。他们表征了“勤奋踏实的云南人”的厚实品格。
昭通作家群的创作主要还是以小说、散文、诗歌等体裁为主,在取材上则以能体现云南文化的个性特征的内容为主,表现手法以写实为主掺以少数现代派技法。前面说过,以夏天敏等人为代表的昭通作家群更多的是沿着传统现实主义并吸收了部分现代主义写作手法,并且有所发挥的写作策略在当下云南文学创作实践中占了上风。事实上,这与云南文化的个性特征息息相关。云南文化的个性特征:一是乡土性,二是边缘性,三是和容性。(当然最明显的特征还是民族性,但此处为了行文的方便以及与论题的相关性,故而掠过民族性。)这种云南文化的特征体现在文学创作上不可能是哪家哪派散兵作战之力就可以成事的,云南作家不能不认真思考自己的文学理念、文化身份以及写作策略这一更具体但也更明了的概念。
夏天敏的中篇小说《好大一对羊》获得了国际国内的各大奖项。作品里所反映出来的直射人心灵深处的让人无处逃躲的贫穷落后愚昧虚弱的农民的生存状态,以及与农民群体相对应的驾驭于农民之上的干部形象,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也是文学的胜利。与全国甚至全世界相比,云南山区农民的生存状态,夏天敏老师写出的是常态是复数,根据典型化的文学创作规律,《好大一对羊》揭示的云南高寒山区启蒙精神的失败和缺失,是云南特困山区里的农民特定而又无法改变的命运际遇。
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昭通作家们,对于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特色食品,风味小吃;故乡的文化传统,著名人物,民风民俗,乡亲逸闻;故乡的生活经历,家族渊源,村庄记忆,现实新貌,无不牵制着作者那敏感的心,即便离开了故乡,来到了省城或是其他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机缘,故乡便不知不觉浮现在心头,心有所动,情有所牵,很自然地就拿起手中的笔,把自己对故乡“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思用文字表达了出来,似乎文字也不尽能够表达自己的感情,只好把目光投向远方,在蓝天白云下,感慨红土地是我的故乡。
斯达尔夫人论南北文学,认为气候和地理条件对一个民族的影响最为显著。“气候影响一个民族的气质和内在的情感倾向,地理环境则关系到一个民族对于生活的态度,是依赖别人还是独立自主,是好逸恶劳,还是勤勉坚忍、勇敢善战。而这些民族的气质和特性又不无反映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昭通作家以故乡作为题材的散文作品中,虽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语言特色各有千秋,结构安排大相径庭,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凝重厚实的情感基调,坚毅卓绝的生命韧性,血浓于水的故里亲情,或许这真的跟斯达尔夫人所论的气候与地理环境有关。从昭通作家的小说、散文和诗歌中透射出,当下昭通作家作品,阳刚之气颇浓,阴柔之美稍逊;深沉凝重有余,潇洒飘逸不足。掩卷闭目,一座座大山就在脑海里出现,这里的人们有着大山的坚韧与厚实……与小桥流水的江南文人那富于书卷气的轻灵雅致的作品相比,明显的感觉就是:这是来自云贵高原红土地上的“昭通制造”。一个前所未闻的地方民族品牌。
四、结论
学者陶东风指出:“不管我们是否承认,在今天,审美活动已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 更有甚者直接宣判“现实主义已经过时”,“文学已死”这样危言耸听的言语也不是什么新闻了。笔者认为这些言论不无道理,但充其量也只是发现并表达了部分道理。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事情表面的背后,于坚还在执着地写诗,不断壮大的昭通作家群也正在用自己的创作实绩证明着文学的生机及现实主义的力量。云南精神,有人曾认为就是“大山精神”即“务实、高远、开放”。但在本文所涉及的论题来说,或者于当代云南文学创作实绩所体现出来而言,一方面是对延续传统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是面向未来的不懈努力。这种精神更准确地概括就是——“凝重厚实,开拓创新”。
——以广西高校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