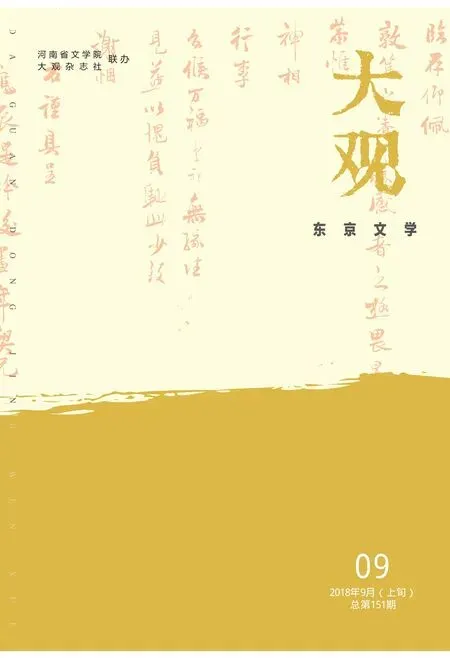亲情怨(短篇小说)
年初一下午,一辆带篷骡车停在五龙沟村口。车把式说:“先生,到了!”
树生揉揉惺忪的眼睛下车。几个小孩围上来。就听有稚嫩的童音高喊:“爹!俺爹来了!”“姑父!俺姑父!”他开心地答应着,蹲下揽起两个孩子,一手抱一个亲着。杏姐、柱子闻声从屋里出来,笑脸相迎。柱子去接包裹,杏姐抱过黑蛋儿打量树生,醉眼迷离,穿得里外三新。过年新买的?咋醉成这样?服丧期这样,不该是树生的脾性。杏姐心里忖度,脸上笑容依旧:“哎哟!可盼来了!”车把式升得与树生约好明天来接的时间,告辞回去。树生和杏姐一家人亲亲热热进了屋。
树生解包裹,孩子们围着看。杏姐倒杯水端来说:“看拿这大兜小包的。一股酒气,喝点水。”树生接过杯,连喝几口水,放下杯又弄包裹。
杏姐犹豫一下去了里屋。树生掏出糖果和鞭炮,俩孩子欢呼着抓起糖就往嘴里放。树生说:“顺儿!”“嗯?”“应该让谁先吃啊?”“娘!”顺儿举着小手跑去里屋,黑蛋儿说一声“爹”,扭脸把糖果塞进柱子的嘴里。杏姐也拿个布包出来,笑眯眯地应声:“乖孩子,真懂事。娘吃糖嘴酸,你吃吧。”顺儿一蹦一蹦地喊:“不嘛!不嘛!娘,你吃!”杏姐接过糖果:“好!娘吃!”俩孩子拿个糖果放嘴里,相互嘻嘻笑着,又缠着柱子去放鞭炮。杏姐望着爷儿仨出门,叮嘱:“小心!不要崩着手!”把布包放在枕边,糖果仍放回糖包里。树生拿出发卡给杏姐:“姐,喜欢吧?还有这布料,是你和柱子哥的。”
杏姐接过发卡,抚摸布料,眼角闪着激动的泪花:“哎哟!兄弟,你月月往家捎钱,顾了老人顾孩子,过得不容易,还破费买这些。以后千万别再给我和柱子花钱!”幸福的目光落在发卡上,反复看着,“真新奇,卡子做成这样。这是啥料的?值不少钱吧!”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她卡好发卡,对盆清水,扭来转去,照着自己的倩影,“哎哟!就是喜庆。俺结两回婚,都没有戴过这么好的卡子。俺兄弟给我带来这么大的福!”
树生看着杏姐美滋滋的样子,很惬意,也暗暗后悔咋没买个镜子。他指着布料:“姐三十七八了,也不显老。瞧瞧,花色咋样?”杏姐拿起花布:“四十了!不老不由人。”拆开纸封,在身上比比,连声说好,“这么好的面料,你姐是见过还从没穿过呀!要说这蓝底素花的,更适合我这年纪。这块红底儿,嗬,花是干枝儿梅!漂亮、喜庆,就是啊,你姐老喽!”抖开红花布往身上一披,遮住补丁旧衣,立刻年轻十岁;忽门帘一响,一柱光线照着杏姐,显得更加光彩照人。柱子进屋,揉揉眼:“黑蛋儿娘?你、你唱戏哩?”杏姐呵呵笑:“柱子,咱兄弟呀,给咱们买的布料,咱俩也能穿上新衣裳啦!”柱子憨憨地笑,杏姐收起布料,“天快黑了,包饺子,咱们吃团圆饺子!”
三人包饺子拉家常。杏姐瞟一眼树生的衣着,说:“你姐没啥本事,做个针线活还凑合。今儿我搭个大黄昏,明儿一早叫柱子也穿上新衣裳。”树生:“早听大嫂说过,杏姐一手好女红。”柱子嘴慢,说:“先做你的。我穿新的,不知道咋走路了。”三人都笑。杏姐像不经意地问:“你这身儿是谁做的?”树生微笑着看杏姐:“比你做的咋样?”杏姐明白了八九分,还故意猜:“比我做得好。裁缝做的?不像,成衣店买的?也不像。”“比起大嫂的呢?”“大嫂那做工是拔尖的。我穿这褂子,是凤儿留下的,就是大嫂做的。看做得多好,布磨烂了,缝口也不会开线。可你这不是大嫂的活儿。一个人一个手劲儿,一比就能看出来。”树生点点头:“哦,就像写字,每人的笔迹都不会一样。那你咋瞧出来不是裁缝铺做的?”杏姐一笑:“裁缝铺谁给你下这功夫?这身衣服,你穿着可身可体的就不说了;看这领口、袖子,沿的这边儿、绣的这口儿,还有这每一颗盘扣,都镶嵌得不留痕迹;颜色搭配讲究,针脚细密匀称,做得严丝合缝,就像是一体的。仙女做的那叫啥呀?天衣……哦!天衣无缝。说天衣无缝也不为过呀!这一针一线都是用了心哩!”树生听得先是美滋滋,后是一阵感动。低头看看,芳草在伤痛中为自己缝制的衣服,这针针线线饱含着多少情!
杏姐见说中了,意味深长地说:“兄弟啊,我跟你柱子哥说多少回了。凤儿走了,不能苦了兄弟。要是遇见中意的,千万别错过。俺们会为你高兴哩!”
树生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心中不知啥滋味:“姐,哥,你们的好意我领了,咱今儿不说这个。”杏姐一口回绝,像在教训不懂事的弟弟:“咋不说?当初你咋劝姐了?你是读书人,更明事理。可不能遇着事自己就犯糊涂。”树生眼泪忍回去,杏姐顿一下问:“这一准是个心灵手巧的女子,有多大了?”
“她正月里生,这就二十一岁了。”树生讲了芳草的故事。杏姐听得感慨:“九岁就没了爹娘,大户人家就怕出败家子!这闺女命也这么苦。”又赞叹,“这么巧,你俩该有这姻缘。多有本事的姑娘,打着灯笼往哪儿找?这事你听姐的,定了!柱子,点灯。”
树生郑重地点点头:“我也想了,今后再婚,我非她不娶。我跟她大爷认了干亲。他们都想见见顺儿。明天我带孩子去。”“带走顺儿?”杏姐心里咯噔一下,又淡淡地说:“哦,有了干爹干娘。我说咋醉成这样。”沉默片刻,“啥时候回来?”
“开学前吧。顺儿也该上学了,今年秋天,叫他在我那学堂上学。”
哎哟,孩子就真离开我了呀!树生再续了弦,这……杏姐心里更不是滋味,觉得眼睛憋胀,泪花涌出来,忙扔下手中的饺子,到脸盆架那儿擦擦脸,稳稳情绪,回到面案前说:“包的够咱们吃了,别擀面皮了。柱子,烧火。”
俩小家伙跑回屋,嚷嚷着饿了。话题就此中断。杏姐包完最后几个面片,忙着煮饺子,张罗大家吃饭。树生可能是醉意未消,也可能有些“木”,还可能是天色昏黑,没察觉出姐的异样,更没去体会姐的心情。
吃罢饭,俩孩子困了,闹着要睡觉。杏姐问树生:“你瞌睡么?”“不瞌睡。上午起得晚,下午坐车又睡一路。”树生吃了一碗饺子,喝了两碗饺子汤,醉意全消。杏姐:“那咱们多说会儿话。叫俩娃儿去里屋睡。”她拉着俩孩子进了里屋。树生要铺外间的床铺,看见枕边的布包:“姐,这包放哪儿?”“哦,那是给你做的衣服和鞋,你收起来吧!”
树生心里一紧,打开布包,是一件长衫和一双棉鞋。想起饭前姐说的话,激动了:“姐呀!你……”杏姐在里屋轻声喝止:“娃儿们快睡着了,别嚷嚷!”
树生抚摸着蓝衫棉鞋,两行热泪涌出,给在摆弄炭盆的柱子说:“哥,过皇年大节,你和姐穿的都是补丁落补丁;日子过得这么紧巴,还给我花这钱……”“俺不讲究,不冷就中。没啥。”柱子仍低头弄炭火。树生擦擦泪,细看这蓝衫、棉鞋,做工也是十分精细。“这一针一线都是用了心哩!”清朗的话音犹在回响,他不禁喃喃起那首古老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杏姐对孩子的关爱无微不至。每到睡觉,热天为孩子扇扇子,冷天给孩子暖被窝。她的心情已平静下来,搂着顺儿在想:鸟儿翅膀硬了总要飞,孩子大了总要离开娘。当紧的是这情义不能断!她想好了谈话的主题。
树生正抚衫低吟,杏姐笑吟吟拢着头发出来里屋:“嘟哝啥呀?我想着,你光棍儿一个,可能过得邋里邋遢。过年了,就给你做件新衣裳。那也是用你的钱买的,有啥呀?谁知道你就那么有福,有个那么好的妹子疼着你。你姐我呀,今后就省心喽!”说着拿把剪子来到床前,把蓝衫棉鞋放包里,“姐做得不好,你替换穿吧。”又卷起被子,把床铺展平,将蓝布抖开,铺到床上,以手指当尺子,比画着给柱子裁剪衣裳。
“瞧姐说的,别说你做得这么好,就是真不好,你弟也不嫌弃。”杏姐仰脸笑看树生一眼,又低头量裁,树生又说,“哎,姐,你别熬着了,就把这长衫叫我哥先穿着,到白天你慢慢做。”
杏姐呵呵笑起来:“叫他穿长衫?那你哥真不知道该先迈哪条腿了!俺们庄稼人,还是短褂子、掩裆裤穿着得劲儿。我量了,这块布,够他一件褂子跟一条裤子。柱子,把火盆弄旺点儿。”接着是一阵剪刀剪布的吱吱声,整块布变成若干不规则的大小片。剪毕,杏姐麻利地叠起一卷拿着说:“咱围着火盆说话。”杏姐到火盆前靠近油灯的板凳上坐下,布卷放在顺手处,从中抽出两片,合一下,接过柱子已经纫好的针线,飞针走线做起来,柱子又调整炭盆里的火苗。树生这才察觉,夫妻俩是相当的默契。
“树生,你听不听姐的?”
树生诧异:“听啊!啥事?”
“那姐有一句话你要记住,就是以后再不要给俺俩花这钱了!你要不听话,以后你就再别登你姐的门了。哎不中,你不来,我还怪想你哩。俺就守着你这一门亲戚,不来可不中。”说得树生、柱子都笑,杏姐也笑,笑得苦涩,“不管咋说,你不能乱花钱!俺缺啥会给你张嘴哩。要是心里真有姐,以后有不穿了的破旧衣裳,不要扔了,记着给姐拿回来,姐就当宝贝了。人得知足。如今有你接济,俺们饿不着、冻不着,比以前好过多了!”
“姐,我记下了。有两件旧衣服,塞在床底下。下次我带回来。”
杏姐这番话无形中给树生留下个念头。此后凡有了不愿穿的破旧衣,马上想起杏姐需要,也就想起这次围炉夜话。
“树生,你说到秋天叫顺儿去城里上学。孩子还小,身边离不了大人呐!我想着,到时候我去给你们做饭,伺候你们,咋样?”
树生笑笑:“不用。学堂里有伙房,孩子晚上跟我住。放心吧。”见杏姐脸色凝重,又说,“明年黑蛋儿也该上学了,叫黑蛋儿也去我那儿上学。你要不放心,我在城里赁间房子,你和哥都去城里住。你照顾俺们,哥打个零工,也不错。”
说让黑蛋儿跟顺儿在一起上学,杏姐心里稍稍好受些:“上学得多少钱?”
“钱的事不用管。俺们学堂是义学,面向平民的,收费很低。穷孩子可以申请免费,只要学习好,还有奖学金。”
“哦,这么好的事,中,去!”
“俺不去!俺就会庄稼活,俺就守在家。”柱子忽然瓮声瓮气冒出一句。炭火映得他脸膛紫红紫红的,与妻子的意见相左是第一次,看得出,他是憋足了劲儿才说出口的。杏姐有些惊讶,瞪一眼:“死心眼儿!人挪活树挪死,知道不?”树生忙劝:“还早哩,到时候再说吧。”
静了会儿,杏姐说:“明天要带孩子去韩府,为啥他们想见孩子?”树生茫然:“是想亲亲孩子吧。我喝了酒,没想那么多。你说为啥?”
“他们知道孩子由他舅舅养,可能就不见了。”
树生讶异:“不会!芳草知道这事,是想跟孩子加深感情吧。”
杏姐看一下树生:“喔……”顿一下又问,“你说,为啥人们常说,‘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这话刺耳,树生皱皱眉:“没想过。为啥?”
杏姐停住针线,盯着树生:“我想,可能是娶了新娇,忘了前情,就是自己的亲骨肉也不那么怜惜了。是么?”
树生明白了,呵呵一笑:“你是怕我忘了前情?没事!姐,就是我忘了,芳草也不会忘。那块蓝花布就是她送你的。她是个侠肝义胆的人!回头你俩见了就知道了,一定合得来。”
杏姐惊喜:“啊?好好好,回头俺们见见。兄弟呀,不是姐小心眼儿,人呐,最怕伤着真情。这人情冷暖,姐是尝尽了,俺真是怕丢了你这门亲戚!刚才说,‘俺就守着你这一门亲戚’,你明白这分量么?”
“知道,姐,你们把我看得很重。”
杏姐又停住针线,盯着树生:“不是一般的重!有你这门亲戚,俺们心里就有底,活得就有劲儿。看见小顺儿,就觉得凤儿还活着!”
树生庄重地说:“姐、哥,你们放心。不管啥时候,咱这门亲戚也不会丢!咱们一直亲!”杏姐心里顺畅了,眼里闪出泪花:“俺有个好兄弟,又有了个好弟妹,俺放心了!肯定能一直亲!”
柱子还在鼓捣火盆,炭块一块燃尽再加一块,弄得火苗不徐不疾。
“兄弟,你真就不回家了?姐想说几句,怕你伤心,不说我憋得慌。你耐住性儿,听姐说两句,中吧?”
ZHAO Jia-yi, HAN Yi-ping, YANG Li-xin, JIN Hai, CHEN Wei, SHENG Jing, ZUO Chang-jing, ZHENG Jian-ming
树生叹口气:“说我的多了,皮了。你说吧,我能耐住性子。”
“大过节的有家不回,那滋味不好受吧?你是个孝子,想娘吧?”树生颔首:“想。”“你觉得你娘想你么?”树生迟疑:“不知道。她的心很硬。可能想点?”
“不是想点儿,是很想!母子连心啊!看她心硬,那是她经的磨难多了,遇事能撑得住。其实,血肉亲情是一样的。拿我说吧,眼下我有了黑蛋儿,可时不时的还是想我前面那俩娃儿。每到饿了、冷了、病了,有好吃的、好穿的,就想!见人家的娃儿偎着娘了,夜深人静睡不着了,有难处了,高兴了,过节了,就特别想!当娘的,这一点该是相通的吧!”
树生以钦佩的目光望着这位不识几个字的老姐,深有同感:“说得真好。我也是在这些时候想孩子,想爹,想娘,想亲人。”
“这不就是了!这个‘亲’字,是咋着也掰不开、扯不断的!想亲人那滋味不好受啊!树生,‘一把圪针捋不到头。’跟亲人较得太真,疼啊!你娘是有错,可谁又能不犯错?要是有了错,一直谁也不饶谁,哪儿还有亲情?听姐的,回去看看吧。我知道,回去会想起爹、想起凤儿,会勾起你的心痛,眼下你有了芳草,心里会好些。怕揪起你和你娘心里的疙瘩,你别在家住,就时不常地去看看。老人一直不见你,也不会很难为你,至多面上骂你两句,那也是心里念你念得狠了,发泄发泄。回去叫家里亲人们的这牵挂劲儿缓缓,也能慢慢解开你跟老人心里的疙瘩。还有大嫂,待你像亲娘,不挂念你?过年这几天,抽空儿回去吧。”
树生被说动了,又有不尽的惆怅,“唉!”地一声长叹。杏姐豁然笑笑:“嗨!看我忘了,兄弟心里还装着大事哩。那也不能拿亲情较劲儿,是吧?到家看看,又没在家住,不算负了誓,是吧?跟你娘和解了,心里轻松了,不会耽误你的大事,是吧?”
三个“是吧”,把树生问笑了:“姐呀,亏你不识字,你要是读了书,就是女萧何!”
“抬举你姐了。”杏姐粲然一笑,该叫兄弟自己想想了,“过半夜了吧?你去里屋歇,跟孩子亲热亲热。”树生说:“我还是睡外屋,抱出来孩子。”
“俺在这儿做衣裳,你歇着不方便。咱是两顿饭,明儿你多睡会儿。”
树生躺在炕上,回味着杏姐的话语,才彻悟过来。思忖:“芳草和杏姐,真是两个奇女子,把家事亲情悟得透透的。一个词正语切,一个民谚俚语;一个语风犀利,一个循循善诱,都说得我心服口服。这份亲情永远不能丢!‘一把圪针捋不到头。’含有啥人生道理?思亲的滋味真是不好受。那就回去瞧瞧?离家的时候,没敢跟大嫂告别,不知她该有多难受,唉!对了,还有竹儿,出嫁心里不顺,不知她在婆家咋样,抽空去瞧瞧她。回去了,娘会咋着?瞧娘脸色好就多待会儿,势头不对就走,反正不在家住……初三去马府,初四去老荣家,初五该上坟哩,就初五,我去上坟,见了弟兄们,跟他们一块回家瞧瞧;初六没啥事就去赵家沟看竹儿。”他打好主意,安稳睡了。
树生正睡得香,觉得鼻孔憋气、脚心痒痒,打个喷嚏一睁眼,两个孩子一阵嬉笑。树生笑嗔:“调皮鬼!”天已大亮,听外屋没动静,忙止住孩子嬉闹。顺儿说:“那你给俺讲故事。”树生想一想,就讲起芳草小时候学武立志做花木兰的故事。俩孩子正听得津津有味,外屋杏姐问:“嘁嘁喳喳啥哩?”顺儿:“娘,俺爹讲花木兰!俺芳草姑是花木兰!”黑蛋儿也跟一句:“花木兰!”杏姐笑了:“你姑姑是花木兰,是穆桂英!柱子,快起,去打壶烧酒,咱也跟姑爷喝点儿。”柱子穿上新衣不自在,扭扭捏捏出了门。树生和孩子们也起了床。杏姐梳洗毕,忙着张罗饭菜。这顿饭是早饭又是午饭。
饭做得好吃,个个狼吞虎咽。边吃边聊。知道树生已打算回家,杏姐很高兴。饭罢,杏姐又做起她的新衣。说会儿话,马车就来接了。
告别自然是难舍难分。杏姐把顺儿抱上车:“佟佟,出去在外面,想娘不?”“想。过两天就回来。”眼望着车离去,杏姐含泪挥手喃喃:“回来、回来,可迟早要走的。”又高声叮嘱,“听爹的话!在外面走要跟紧爹!别乱跑!”
“噢!知道了!娘!爹!回吧!”稚嫩的声音在空中飘荡。
年初二下午,是闺女女婿串亲戚回返的时候。天气晴朗,路上行人比平时增多。有步行的、坐车的、骑驴的、推车的、挑担的……仨一群俩一伙,携儿带女,来来往往。遇见相识的,老远就打起招呼,相互作揖道着吉利话。
顺儿在车里拱来钻去,或伸头朝外看稀奇,或坐车把式旁拍着马屁股吆喝牲口。过一小桥,桥窄人多,顺儿学升得喊牲口:“吁!慢点!慢点!”忽听有人喊:“顺儿!小顺儿!顺子!!!”顺儿张眼四望:“啊?六叔!六婶儿!爹!俺六叔!”树生忙揉揉眼:“升得,停车!”
车过去小桥停路旁,树生和顺儿下了车,麦生推着独轮车也赶了过来。车上坐着六媳妇,媳妇下车给四哥道福拜年,看出来她肚子大了。半途遇家人,哪能不激动?兄弟俩顾不得别的,相拥而泣。六媳妇也把顺儿搂在怀里亲着。顺儿摸摸凸凸的肚:“宝宝?”一家人的亲密影响了走道儿,有行人喊:“哎!往边靠靠!”他们退到空地说话。“哥!回家吧,娘想你,年三十在坟地里等到你天大黑;全家人都想你呀!”树生泪如泉涌,一跺脚猛吼一声:“回家!”叫升得把独轮车绑在车后尾,六弟俩口坐上车,一起回家!
车行一会儿,树生心情平静些,问:“弟妹有喜了?你俩去串亲戚?”麦生说:“六个月了。她娘想她,捎信非叫去。大哥就叫俺俩去瞧瞧。”
树生又问起娘,麦生就把娘怎样想他,年前怎样找他说一遍。兄弟俩越说心里越难受,说一路哭一路。树生开始听着,激动得恨不能马上见到娘,扑到娘怀里痛哭一场。听着听着,心境变了,特别是听到娘在坟地里连哭带闹地不回家,被兄弟们抬了回去的情节,心又怯了:“这贸然回去,娘要再闹起来咋办?”顺儿也哭着说:“爹不哭。俺怕。”树生搂住孩子猛地想到:“到家娘要是不叫孩子出来咋办?”忽听升得问:“佟先生!家在村哪头呀?”“啊?到家了?停停停!”树生撩起车窗帘外望,冷冰冰的拱圈南大门赫然在目,头皮发麻,寒毛奓起,忖度:这门好进不好出啊!不能进。可到了家门口,能一走了之?
“四哥,下车吧。”“六弟,我这样突然回去,娘又闹起来咋办?大过年的,咱娘那脾气你知道,闹出个啥事多不好。你悄悄给大哥大嫂说一声,我在咱坟地里等。”麦生又劝几句无效,叹口气,携妻去了。
树生拉着顺儿站在车旁。有三炷香的工夫,远远见麦生与哥嫂匆匆走来。哥嫂比比画画、好像在争论。树生拉着顺儿快步迎上去,到哥嫂前行大礼。大嫂慌忙拉起树生,眼含热泪泣说:“这是弄啥哩?快起来!”又抱起小顺儿。树生哭:“哥呀,大嫂,我想你们啊!”春生含泪拉着树生说:“过年哩,哭啥?”一指坟地,“到庵子里说话。”顺儿样子乖乖的,细看看大娘,喊一声:“大娘!”抱紧大娘的脖颈,小脸贴紧大脸。
几个人到庵舍里。春生说:“四弟,还是回去吧。娘想你想疯了。不会咋着你哩。最多发一顿脾气,那也是想你想哩。咱当孩子哩,能不叫娘撒撒气?”树生犹豫了,又想回家:“要是娘硬留下顺儿,咋办?”“那就留吧!竹儿娘走得没了影儿,杏姐担心的事不会有了。以后你在家少,就叫小顺儿跟我,我养他,你放心吧?”树生忙说:“不不不。哥、嫂,杏姐把顺儿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我不带走顺儿,咋给杏姐交代?”
春生有些急:“她毕竟是妗子嘛!”大嫂小声劝:“别那样说,杏姐很珍视凤儿留下的骨肉,那亲情超出了一般。”“那又咋啦,就真跟娘结仇了?家里成了这样子,娘心里好受?她比咱更难受!亲娘亲孩子,天大的怨气,过些日子消消气就算了,咋能一直记在心里?你这样做算是孝?听哥的,回去吧。给娘多认错。”
咋大哥的态度有这么大的变化?树生无奈地摇摇头:“哥呀,我都给你说过呀!”春生瞪起眼:“说啥?那都是气头上的话,过了那阵儿,还是亲骨肉!能当真?其实,眼下娘最挂牵的就是你。她也觉得顺儿娘死了怨她,心里愧得慌,一直操心再给你说个媳妇。”
“啥?娘要再给我说媳妇?”晴天当头一声霹雳,树生目瞪口张,脑子里一片空白,只看着哥嫂六弟表面比画实为拉扯地说着什么,却听不见,半晌猛吼一声:“千万不要!”抱头仰面躺下痛哭起来。春生没想到树生会有这么激烈的反应,也激动了,抓住树生的胳膊摇晃大呼:“咋回事?咋回事哩么!娘给你再说个媳妇有啥错?是对你好哩呀!”大嫂擦着泪劝了四弟又劝阻春生:“你不要说了,叫四弟静静!”顺儿不懂就里,哭得更是厉害。老六懂点医,知道四哥是受了刺激,一直给他抚胸按穴:“四哥,心里有啥话慢慢说。大哥,别说他了。急火攻心,能得大病哩。”
树生对刺激性语言非常敏感,呼号着反驳大哥:“我不要她这个‘好’!她想着给我再娶个媳妇,我就好受了?这是打了个盆儿,碎了个碗?重换一个就没事了?为啥我咋着也甩不脱呀!”春生也担心气着树生,不再答言。大嫂一直顺着树生的意思劝:“大嫂知道,四弟重情重义,咋能一下忘了结发妻子哩……”树生拉着大嫂的手:“大嫂、大哥,家里事,我就靠你俩给我做主啊!谁知道,谁知道……俺大哥……”哽咽难言,又哭一阵。大嫂、六弟慢慢劝着,哭声渐小。
春生冷静下来,和颜相劝:“树生,那你啥意思?一辈子不再娶媳妇啦?”
“要是还全由着娘,连面都不叫我见见,不顾我的意愿,我是绝不再娶了。这是我自己娶媳妇,能不能叫我做一回主?!”
春生不解:“儿女婚姻,父母之命。自古老理啊!娘给你说媳妇,是应该哩。这能不听娘的?”树生又激动了:“我不是没听过她的!凤儿是她说的吧?我心里不愿意也听了吧?我忍住委屈成了亲,想跟媳妇好好过日子,结果她给我弄得这叫啥?哼!想叫我再听她的,除非她能叫咱爹再活过来!要是能,叫我去死都中!”说着又哭起来。
大嫂叹口气:“四弟呀,不哭了。你也要多替娘想想。说一千道一万,娘再给你说媳妇,还是想你,想解开你心里的疙瘩,想叫你多回家……”树生打断大嫂的话:“她要是不管我心里啥意愿,就是给我娶一百个媳妇,我也不回家!”
大嫂忙说:“我也是说,再给树生说媳妇,一定要先叫树生满意。这个俺们都帮着劝娘中不中?”
树生一下坐起,擦擦泪,抓住哥嫂的手说:“这事就全靠大哥大嫂了。给娘说,我的婚姻不用娘操心了。只要叫我自己做主,我心里对娘没疙瘩。只要娘答应,我就常回家看看。”
六弟:“要想说服咱娘也难哪!四哥,你在外面不知道,哥嫂在家做多少难。”
忽听升得在庵子外面问:“佟先生,天不早了,啥时候回去呀?”
树生擦擦泪,清清嗓子答:“噢,这就走。”他主意已定,不回家了:“哥、嫂,我走吧。一下劝不了娘就慢慢劝。反正我出去了。我已经立誓,我的事我不能做主就不回家!我不再娶!真有去家说媒的,要让人家女方知道,树生不在家,嫁过来也是守空房,别苦了人家闺女。”说着站起来,想一想又说,“这样吧,我回头专门给娘写信告诉她,我在外面有了媳妇,这事不用她操心了。你们再帮着劝劝。要是娘能答应,我就回来。”
哥嫂想想也没啥好办法,春生叹口气:“信要写得好懂,不要说难听话。哎呀!一个比一个獦獠(脾气怪),这日子咋就不能好好过哩?”
大嫂叹道:“唉!这亲情,亲错了地方,也能变成怨恨呐!”
走出庵子,大嫂拉树生一下轻声问:“你真有了中意的?给嫂说实话。”树生有些哽咽:“韩家芳草对我一往情深……”
大嫂的娘家临近下韩村,对韩家熟悉:“韩芳草?那闺女本事可大。”韩织户家,这门第、她脾性,跟家里合么?啊呀她那个哥,可不是个好东西。大嫂一脸疑惑:“哦,百文的堂妹,你俩是从小的情意。”
事情这样一激,树生下决心了:要与芳草先定了亲!
大家随着出来。树生到父亲坟前叩头告别,起来后忽然想起竹儿:“竹儿咋样?她在婆家好吧?”大哥叹口气没吱声,六弟低头不说话。
大嫂一脸愁容:“唉!这又是一件揪肠子的事。自出嫁就没了信儿。今儿该回娘家哩,等了一天,也没来。至今咱家谁也没见过这小女婿是啥模样。竹儿性子烈呀!这婚事打一开始,她就寻死觅活地不愿意。越想越叫人心焦。俺们正合计着,这几天咋着陪你二哥去她婆家瞧瞧。又觉得在孝期,去了不方便。”
“是这样?”树生停下看着哥嫂,“那我去瞧她。有啥事,给你们捎信。”
春生松口气:“你要能去最好了。啥时候去?”
“这两三天里。”树生接过大嫂怀里的顺儿上车,“你们回吧。”
春生看车篷上有个“韩”字:“你这是去下韩村……百文家?”
树生坐车里答:“嗯,今儿住那儿。”
车启动了,他看见大嫂又在擦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