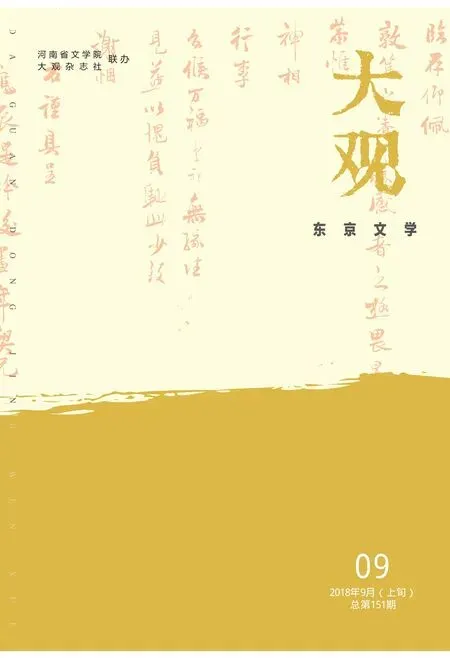流逝着小浪底水下的永恒(散文)
1
有理街道,无理河道。这是不知道哪个年代哪个场景,谁人说出并长期流传下来的自我解脱的话语,在世俗里被人们接受且已公认。
在小浪底北岸王屋山的梁前沟背,散居着无数个所谓的村庄民居,如果是一棵棵树的形式,长高增粗便是一片硕大的森林。然而它们是一座座民宅,有些近前了可以看到土墙黛瓦。瓦,一律传统手工泥坯烧制,在房上细细密密锁扣,接受阳光风雨、冰雹飞雪以及自然界无所不在的考验,以环环紧扣的自信坦然面对,以默默而沉稳地改变自己容颜的形式尽职尽责,青而灰的新鲜成为深不可测的黑褐色的浓重。扬尘的日子久了,积聚在瓦槽缝隙间的尘土在雨水的滋润里就有了生命,一颗颗灰色的塔尖一样的瓦星星赫然在目。院落是在山脚沟畔劈出来的方正,很多只是开挖的窑洞,只能看到辟出的棱头和洞口,远处根本就看不到。就连窑洞旁建起的土房,全掩在山梁沟壑以及蓊郁的树木中,远看只有山的苍茫和植被的苍翠。
在这样的环境里,根本不可能有宽敞而规整的街道。有理的街道只能是窑院门前和接近家的山道,抑或通往梯田的小路,就是说人们经常出入活动的地方吧。这些地方是文明礼貌知书识礼的场所。河道的无理,是说那是相对随便的地方,特别是针对男人而言,夏日洗澡赤裸的随意是天经地义的。
当时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境地只有一两所小学,东岭村还算离学校近的,翻沟越岭也就个把钟头的山路。所谓学校,是原来一孔硕大的窑洞,优势是洞前那片平地,像生产队的一个打麦场,正好能做一个操场。后来逐步重视教育,窑院扩大,建起了一栋红砖楼房,把一至六年级的所有班级全装进去了。很大的玻璃窗户,和原来的窑洞比,简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
陈海潮当时读五年级,到了暑期,教育局照例向各学校发出加强安全管理通知,学校知道,这是“四季歌”,上级也就是尽尽责任罢了。因为在黄河沿线,哪一年能少了青少年在河里出事?尽管学校习惯了,但是都不愿意偏偏就发生在本校。于是校长就照本宣科,让各年级班主任加强管理。最后说:“哪个班出问题,班主任首先负责!”
恰在这时,陈海潮迟到了。老师心里清楚,天这么热,他还能干啥去!况且还有同班的三位同学。本来是见怪不怪,这次李思奎老师动了心思,吩咐同学们做作业,带着班长出了校门。
陈海潮和三位同学正在黄河的一个潭窝里扑通得痛快,突然一个伙伴喊:“老师来了!”大家回头一看,班主任老师带着班长已到岸边,顿时乱了方寸,纷纷向岸边游去。只听老师对班长说:“把他们的衣服全部拿走。”班长叫小雷,手脚麻利,呼呼啦啦全拿了,连一只鞋也不剩。老师撂下一句:“走,叫他们洗吧!”径直往学校走去。
几个人趴在水中看着老师和班长的身影,班长跟在老师身后走,故意倒回头看一眼,给他们递一个得意而坏坏的笑。
四个人上了岸,像四条光溜溜的泥鳅,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刚才的高兴劲早已溜到了九霄云外,没辙了。海潮突然看到岸上玉米地边肥大的蓖麻叶,指着说:“咱们每人摘一片蓖麻叶,遮住去学校怎么样?”
“那会中?遮住前边遮不住后边。”有人说。
“我们总不能不去学校吧!敢叫家人知道,挨吧!”海潮这样一说,小伙伴们又互相看了看,没吭声。
只见海潮噔噔噔跑到玉米地边,摘下两片蓖麻叶,一前一后捂着屁股向学校走去。三个伙伴也纷纷效仿跟了上去。幸亏在路上没有碰到行人。到了校门口,海潮突然闪到门的一侧,扶住砖垛猫着腰向里窥视,三个人也机警地躲在一侧墙根。还好,已是上课时间,不然可就惨了。海潮倒过脸低低地说:“谁先进去?”三个人几乎是靠墙蹲坐在地下,都还把一只手背在身后,互相用胆怯的眼神看一下,不说话,却有人哧哧地笑。海潮正要说咱们一个一个进去时,班长奇迹般地出现在门口,并且把大家的衣服全拿了出来,往地下一丢说:“快穿上,李老师在屋里等你们呢!”
原来李老师早提防着他们呢,能让他们就这样进学校吗?
今天的陈海潮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回忆起那次洗澡事件,感觉很有趣。说进到李老师办公室,挨了很严厉的批评,关键是最后给李老师写的保证,每每心有余悸:“如果再犯,告家长。”告家长可算是当时最严重的事件了,那意味着可怕的皮肉之苦。
2
这条永不知疲倦的黄色河流,没日没夜地奔腾咆哮,随着季节的转换,它也发生着肥肥瘦瘦的变化。对祖祖辈辈厮守在岸边的人来说,很是稀松平常。就像崖畔那棵千年古柏,无论身边的风怎样怒吼,怎样厮磨自己的腰身与枝梢,抑或无论飞雪冰雹如何施压与袭击,仍慷慨着毫无顾忌。面对黄河,经历过无数的未知,还有什么能够撼动那颗与大河一样向前向上的初心?那种磐石般的定力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山民,眼观奔流,耳听涛声,与日月星辰、季节更迭同行。
就见证着日出日落、月盈星稀,以及大旱饥荒、五谷丰登的悲与喜,见证着风调雨顺、人情世故,以及呱呱坠地、坟茔荒草的生与死。那些孩童撒欢儿的笑声听见了吗?还有沙滩上光溜溜泥鳅一样的身影……
海潮是这条沟里的娃娃头,长辈人说海潮像个小土匪。殊不知,海潮小小年纪就救过两条人命。
那是一个山果成熟的季节,秋老虎已到奄奄一息的时刻。海潮和几个伙伴在黄河里尽情地扑腾、戏耍,筋疲力尽的时候就上岸晒太阳,在沙滩上仰面躺卧,或者把暖暖的沙土全拢到各自的肚皮上,享受那种温热的舒服。这时,耳边又有小鸟般叽叽喳喳的吵闹,比海潮小两岁的三顺背个葫芦也来游泳了,身后还有几个更小的娃娃。只见三顺走到水边,没有和海潮几个打招呼,对身后的小伙伴们说,你们都在岸上,我先游。说着脱下衣服,系上葫芦,游了进去。正在得意时,突然葫芦绳断了,只见他一会儿浮出水面,一会儿又没入水中,两手无节制地拍打,嘴里发出“嗷——嗷——”的嚎叫。海潮一骨碌爬起来,急忙跳入水中,可劲游到三顺跟前,拽住一条胳膊,把他从水中拉了出来。
上了岸,三顺瞪着白眼吐水,海潮说:“叫你能,能呗!”
随行的娃娃在岸上害怕了,纷纷扭头往回跑。
转眼海潮已上了高中,已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学校位于大峪乡政府所在地的一条峡谷里,大峪河的水源来自王屋山,常年叮叮咚咚一路欢歌注入黄河,沿途积下不少长藤结瓜般的水潭。夏季,这些水潭便是孩童们消暑洗澡、捉鱼逮虾的好地方。每天吃过中午饭,同学们便三五成群地到水潭边洗澡。凡沿黄河居住的同学都会戏水游泳,并且在入水前,都知道先在浅水处用手往身上撩水,有的干脆用手接了自己的尿往肚脐眼搓撒,让身体尽量适应水的温度,以防不测。那些来自深山里的旱鸭子同学,不知道这些,一到潭边,脱下衣服,便跳入水中。
其实,这个水潭不大,最深处约两米,大部分约一人深。所以,会不会游泳在这里都没关系,不会游的在潭边手触底扑腾一阵了事,会游的在深水处游一会儿过过瘾。
那是午饭后预备铃敲响之前的时间,海潮伙同会游泳的同学先到了潭边,游了一会儿便感觉凉飕飕的,遂上岸坐在石头上晒太阳。这时,一群深山里的同学来了,只见他们脱掉衣服,“扑扑通通”像下饺子似的相继跳入水中。他们游戏了一会儿,都知道不能太占用时间,就纷纷上岸晒太阳。阳光正好,有人惊觉说,李涛呢?大家急忙站起身,往潭里一看,只见一个脊梁漂在水面,李涛撅着屁股头在水里一动不动,同学们都傻眼了,海潮不知哪根神经起了作用,二话不说跳进水中把他拉了上来。同学们七手八脚地把李涛抬到岸边一块大石头上,头朝下吐了一大摊水才清醒过来……
此事自然惊动了学校,人命关天的事,让校长好生为难——关于海潮,是批评,还是表扬?全校师生大会上,校长针对海潮说:陈海潮同学见义勇为的行动值得大家学习,在生命垂危的关键时刻,陈海潮能奋不顾身下水抢救,赢得了时间,挽回了李涛同学的生命,精神可嘉!但是,陈海潮也和李涛同学一样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不顾学校三令五申的纪律,到河里洗澡,应该受到批评,大家应该引以为戒。但是,假如那天陈海潮同学没有违反学校纪律,和其他同学一样坐在教室里,李涛同学怎么办?那么多洗澡的同学,为什么没有第二个陈海潮扑下水救人,都在岸上惊慌,不起作用?因此,陈海潮同学的违反纪律是值得的,他的违反纪律,换回了李涛同学的生命,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呢?
3
黄河最萧条冷落是在冬季了。
河面萧瑟袭人,风从水面反弹上来,像皮鞭一样抽在脸上,冰冷、生疼,不由让你的心揪作一团,周身颤抖。喜鹊在石上站立,风掀翻了雨伞那般模样掀翻着黑色尾巴的羽毛,顺势翻个跟头一扑棱飞走了。
漫长的冬夜,只好无奈地围坐在窑洞里烤火,那个生铁铸造的火盆有些年头了,母亲说是奶奶留下的,一个冬季能烧掉十来个枯树疙瘩。只要盆里有火,满窑洞有青烟熏着,就有足够的热量温暖一家人。
从学校出来的青年人青春勃发,哪能终日围坐炉火度日?山沟的夜晚只有夜莺与虫的鸣叫,往公社跑一趟来回要走五十公里的沟壑山路,再好的电影、戏剧或说书、马戏等,都是事后听别人说说而已。最近的闹市要算新安县的西沃公社,直线距离也就四公里的样子,只是黄河阻隔。为了方便流通,只好凭借两岸船只的摆渡,就形成了南岸的西沃渡口,北岸的长泉渡口。船只互通往来,倒也方便。反而比通往自己的县城、自己的公社镇街还要便利。
船只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工具,艄公更是大家尊敬的人,十里八村的人没有不认识常年摆渡在河上的陈发茂老艄公的。说好了办完事几点钟返回,发茂老人一定会候着,吱扭扭的桨竿吃水,吱呀呀就行走开了。年轻人上船总是不太安分,就抢着划桨,艄公总能准确掌握航向,不偏不倚地停靠到指定地点。
偏远闭塞的山村想看一场电影实在困难,就巴望着村里的富裕人家能够办一场红白喜事,好请一场电影让人们大饱眼福。但是几率太小。一次村里得到可靠消息,南岸西沃公社元宵节晚上放映电影,并且是南斯拉夫的《桥》。当时看到的仅是有限的国产片,如《奇袭》《英雄儿女》《地道战》《地雷战》等,这个外国片被传得神乎其神。陈海潮和一帮年轻娃急得快要发疯了,夜晚不摆渡是长泉渡口的铁律,每天掌灯前就锚了船,并且锁死了船桨。
能不看吗?陈海潮们心有不甘,就密谋策划了一个冒险行动。
天黑透,只有风不知疲倦地在水面、岸上巡逻,八个人各自扛一把自家的铁锨来到渡口,悄没声解开缆绳,把船往上游拉,大约有四五十米的距离吧,按照事先的分工,陈海潮掌舵,兼总指挥,其余七人左边四个右边三个,用自己的铁锨划水。其实海潮根本没有掌过舵,只是坐船多了看到一点。难道就那么轻而易举吗?渡船根本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听话,不自觉就在水中打了个转,大家很用劲就是不往对岸走,只是快速向下游漂。几经周折,陈海潮摸到了点脾气,把舵竿调正,喘着粗气说:用点劲,划!伙伴们有点紧张,谁也不敢说话。按照指挥的口令:左边使劲!使劲!使劲!不行,右边过来一个人,加到左边,增强力量,使劲!使劲!使劲!
终于到了南岸。岂料,船没有停靠到码头,而是下行到五十米开外的地方,已触到了陡峭的崖壁,大家顿时慌了手脚。只见总指挥关键时刻沉稳不乱,命令大伙:沉住气,不要慌!岸边一侧的人放下铁锨,用手抓牢岩石和荆棘,一边推一边拉,不能让船体碰石头;另一边人用劲划水,二炮还回来这边划水,用劲!用劲!用劲!
船靠到了码头,大家大汗淋漓,一个个几乎瘫软在船上。为了看电影,陈海潮在一颗石头上锚好船,说,快走。当大伙儿气喘吁吁跑到放映地,银幕上正好出现一个字:完!有人不自觉哎呀一声,更有骂娘的:我操!
在散场的人流嘈杂中,陈海潮顾不了那么多,急慌慌闪向路旁,边走就边撒着尿,一抖一抖成为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