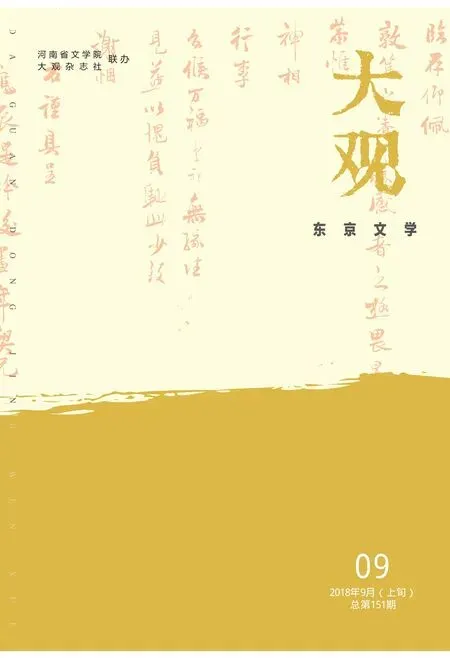凡人俗事(小说三题)
下午茶
在这个三伏天酷热的下午,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到处生烟。焦躁的劳乐开车来到湘楚茶文化研究所,然后从车里蹿出来,直奔这栋小楼的三楼,敲开了言默工作室的门。
“对不起,不速之客来了!”
“你什么时候来,我言默都扫榻以迎。”
汗透了短袖T恤衫的劳乐,一边掏出手帕揩着头上的汗水,一边说:“麻烦兄开一下空调吧。你比我胖,穿着长袖衬衫,只持一把折扇,居然不出汗,怪事。”
言默微微一笑:“因为你心里牵挂的事多,闲也闲不下来。闲可生静,静可生凉。”
“此语可入清人张潮的《幽梦影》。我着急啊,管着一个几百人的企业,质量、产量、销售、人事,哪桩事我不过问?可我劳而无乐,招人厌,上午有好几个高层领导,向我递了辞呈。”
言默摆了摆手,说:“不说这些,你是来喝茶的,快入座。我先开空调,再烧水沏茶,你少安毋躁。”
言默把空调打开了,凉气嗖嗖漫向每个角落;又将电热壶上满了水,一摁开关,便发出嘶嘶的声音;再打开柜子,寻出一把不大不小的白瓷茶壶,舀入几大勺安化出产的贡尖黑茶;再找出两个白瓷小碗,横搁在茶几上。言默这才在茶桌边坐下来,也不说话,目光安详地投向烧水的电热壶。
一切都归于一个“静”字。
他们自小是邻居,又是小学、初中、高中的同学,大学同校只是不同系,可谓相知甚深。一眨眼,他们都过了不惑之年,劳乐是自办的华威电机厂的厂长,言默是茶文化研究所的副所长,正研究员。虽同在一个城市,他们彼此走动并不多,是真格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日各忙各的,偶尔打个电话,发个短信,寥寥数语而已。但劳乐一旦有了烦心事,就会寻到这里来,好好地和言默喝一阵茶,彼此也不多说话,然后告辞。
每次出门时,言默必歉意地说:“劳乐兄,喝好了吗?我说话少,海涵。”
劳乐开心地说:“喝了一怀的宁静,够了,值了。”
电热壶的水,烧开了。
言默摁下开关,在一个白瓷水盂里放入白瓷小碗,提起电热壶倒水,细细地烫一遍,再用一块白绢子拭净碗里碗外。然后,他从容地把开水注入放了茶叶的白瓷壶,说:“这是散叶贡尖黑茶,不是中、下档的黑茶砖,所以第一遍水不必倒掉不用。过下子你试试,微苦中的回甘,妙不可言。”
言默拿起一个小瓷碗递给劳乐,自己也端起另一个小茶碗。
劳乐接过小茶碗,这才发现它不是平底,底部是尖锥形的,这种茶具他是第一次看到。
“这是瓷厂新研制的品种,名叫‘放下’。”
“怎么放下?它放得下吗?”
“你就放在手上。”
白瓷壶里的茶叶闷了一阵,香气飘袅出来,很好闻。
“劳乐兄,用手端好碗,我给你斟茶了。”
言默给劳乐碗里斟满了茶,再给自己斟了一碗。茶碗的壁很厚,并不烫手。
“请试茶,劳乐兄。”
“言默兄,谢谢。”
“怎么样?”
“只知道说一个字:好!”
“酒须豪饮,茶须静品。我们就于无声处慢啜茶吧。”
“遵命。”
白瓷壶里的水续了一次又一次,白瓷碗里的茶添了一回又一回。
劳乐先是两手端着尖底茶碗,慢慢地变成左右手轮流端碗,这两个小时,成了他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腰酸背疼,手上青筋凸暴,只叹茶碗无处可安放。
“言默兄,这茶具我消受不了。”
言默说:“莫急,我自有妙法。”
言默又去柜子里取来两个圆形的器物,高若寸许,中央有一个洞穿的内圆,摆在茶桌上。“劳乐兄,这叫茶托,请将茶碗放上去。”
劳乐把茶碗的尖底放入茶托的内圆,居然严丝合缝,顿时觉得全身轻松,有些僵硬的双手也舒展了。他马上想到,这茶碗、茶托原本是一套的,从放不下到放下,这个过程耐人寻味。他在他的企业事必躬亲,从不肯放手让副手和部下去甩开膀子大干,等于手端尖底茶碗放不下呵。言默招待他喝茶,是无言的劝诫,是让他启悟。
“劳乐兄,放下了吗?”
“放下了,放下了,我知道回去该怎么做了。再见!”
言默送劳乐到门边,笑着说:“劳乐兄,你没注意吧,我早把空调关了。”
“没注意,只觉得心里凉润润的。”
别墅院的菜园子
花甲出头的秋满仓夫妇,终于高高兴兴地在儿子家住了下来,再不嚷嚷着要回乡下的老家去了。
这个住宅区,有个很好听的名字:现代公园。它占地面积大,有山有水有田畴有树林,大道小径井然有序,四时风光各有不同,确实像公园。公园里,全是散落在各处的别墅院,各家有各家的一圈围墙,里面除精致的小楼之外,还有游泳池、芳草地、花圃。
秋家的院子,门牌号A8。一次性付款,优惠价是八百万元。
儿子刚买下别墅时,秋满仓惊得一块脸都白了,问:“秋金富,你哪里发的横财?”
儿媳宦静静是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说:“爹,他早改名了,是我的建议,叫秋声赋。你别叫他小名了,俗。”
“秋金富是我给他起的大名,秋来稻菽金黄一片,才是真正的财富。我叫秋满仓,不是更俗了?”
宦静静噎得再不敢说话。
秋声赋说:“这钱来路正,我创办冶炼厂十多年,是用汗水和智慧赚来的。”
“那就好。我只叫你秋金富。”
“爹,你一叫我就应。”
隔一段日子,秋满仓夫妇会从乡下坐长途汽车来,一是看看他们的宝贝孙女秋丽丽,二是送来自家种的瓜果蔬菜。当天来当天回去,连住一宿也不肯。
秋声赋问这是为什么?
爹说:“看着一院子的好土地,都栽着中看不中用的花花草草,心里憋得慌。”
娘说:“住在这里无所事事,闲得骨头发酸。”
秋声赋渐渐地有心思了,愁得眉毛打结。他是有头有脸的企业家,又是独子,妻子是为人师表的大学老师,他们住别墅院,却把爹娘抛在乡下朝耕夕耘,不是让人看笑话吗?
秋声赋对妻子说:“别人会说我不孝,会说你不贤惠,传到女儿的学校里,同学会怎么看她?可爹娘不肯来,怎么办?”
妻子说:“他们是劳动惯了的人,一闲就病了。我们先请人来,把北墙边的花草拔去,平整出几块菜地。再开车去接他们,说我们的女儿丽丽最喜欢吃他们种的蔬菜。把乡下的房屋、田土,找个亲戚代管,我们悄悄付工钱就是。”
“这个办法行吗?”
“他们就疼爱孙女,一说就灵。”
果然,秋满仓夫妇在一个春天的日子,儿子开车把他们接来了。还带来了工具,锄、钯、粪桶、尿勺……以及各种各样的菜秧子。
秋声赋两口子下厨,做了一顿好饭菜,特意打开一瓶茅台酒,为爹娘接风洗尘。
“爹,娘,我和静静先敬你们一杯酒。”
“好,好,我们高兴。”
吃喝间,秋满仓问孙女:“你真的喜欢吃爷爷奶奶种的蔬菜?”
“真的喜欢。”
“我们种蔬菜,不用化肥、农药,孙女吃了,一定身体好。”
“谢谢爷爷奶奶。”
秋满仓又问儿子、儿媳:“栽什么菜?栽多少?你们有什么想法?”
秋声赋说:“这个院子就是你们的,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只要二老高兴。静静,你说呢?”
宦静静连忙说:“正如孔子说的,我不识园圃。二老是行家,只是不要累狠了。”
一眨眼,几个月过去了。
秋满仓夫妇真的有了回家的感觉。
北墙角上,挖了一个沤烂菜叶、杂草根的水氹,还埋了一个盖了盖子的粪缸。先是开出挨北墙的几大块菜土,种下小白菜、韭菜、菠菜、苋菜、蕹菜。接着,菜土向南扩展,花花草草都拔掉了,栽下丝瓜秧、东瓜秧、南瓜秧、扁豆秧,还树起了支架、瓜棚。
斗笠、蓑衣、草帽、草鞋、粗布衣褂,他们劳作在风雨中、阳光下,淋菜、锄草、捉虫、摘菜。整整一个白天,都属于他们。儿子一家吃过早饭出门,要到傍晚才回来吃晚饭。
有一天夜里,秋声赋来他们卧室请安。
秋满仓问:“你不是说,他们母女吃过晚饭后,要在园子里散步,怎么好久不见出来了?窗子也关得紧紧的。”
“她们这段日子有点累,就不散步了。爹,这个……这个淋菜,不用人粪人尿行不行?”
“那怎么行!”
“哦,我不过说说而已。你们种的菜,真的新鲜可口,辛苦二老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二老发现儿媳和孙女走出餐厅时,赶快带上了口罩,匆匆走向停在院门边的小车。儿子虽没戴口罩,却用手帕扪在嘴、鼻上。
学校放暑假了。宦静静特意告诉二老,她要带丽丽去旅游,先国内再国外,大概有一个多月。她们旅游回家后,住了几天,秋季开学了。因丽丽进入了小学六年级,还有一年就要读初中了,谁不想考入本地最好的中学呢?宦静静又抱歉地告诉二老,她让秋声赋在小学附近买了一套房子,为的是让丽丽免除上学放学奔波的辛苦,集中精力把成绩搞上去,她下班后也住到那里去陪读。
秋满仓问:“金富,你也去陪读吗?”
“我不去,我住在这里陪爹娘。”
秋风紧,秋气深。
豆架上瓜棚里的瓜豆都收完了,菜地里的蔬菜也摘光了,秋满仓让儿子单位的食堂开车来运走,给员工们去享用。然后把院门和小楼的钥匙交给司机,请他转交儿子。
他们该回乡下的老家去了。
比 邻
仲夏时节,五点钟的样子,天就露出了鱼肚色。
七十岁的常惠生,赶忙下床,他的妻子问道:“你到哪里去?”
“到德山家去看看。”
“德山被他儿子接到城里治病去了,那座房子空空的,有什么看头?”
“他临走前把钥匙交给了我,我去开开门,让房子透透气。说不定哪天他就回来了,还来和我们做邻居。”
常惠生从枕头下摸出钥匙,小心地掂了掂,然后塞到口袋里。这一串钥匙可以打开尹家的大门、卧室门、仓库门……不是情如一家人,不会对他这么信任。他走出卧室,穿过堂屋,再打开自家的大门,跨过高高的门槛,站在台阶上,便望见了几百米开外的尹家老屋。当然,只能望见那栋老屋上部的风火墙、晒楼、青瓦屋脊,高高低低的杉树、南竹、马尾松、槐树密密匝匝,如绿帷翠幛。再看看自家的房前屋后,也是林涛起伏。到处是浏亮的鸟鸣声,和飞掠而过的翅影,不经意间震落了树枝树叶上的露珠,发出沙沙的碎响。
常惠生突然觉得眼睛有些润湿,喃喃地说:“德山呀,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他走下台阶,沿着一条被林荫遮蔽的小路,朝尹家老屋走去。
这个村有三四十户人家,住得很分散,到处是半裸半掩的土石山丘和坡地,稀稀拉拉地只长矮小的杂树、荆棘和野草。常家和尹家住的这一面坡地,原叫秃毛坡,但现在却有了成片的树林,还有了许多自开自谢的野花。常惠生的儿子常凯是个农民企业家,先在城里经营农副产品市场,早几年回到老家创建农业科技园,事业红红火火。他的科技园就在坡下的小河边,呼啦啦沿河排开几百亩地,瓜果蔬菜全是早熟、高产、优质品种。他不喜欢秃毛坡这个名字,遂改名为锦绣坡,单位则称为“湘楚锦绣坡农业科技园”。
常惠生曾对儿子说:“这面坡是我家和尹家共有的宅基地和自留山,你改名问过他吗?”
儿子说:“问他做什么?他肯定会同意的。这几十年,你们二老对尹家施惠多多,他报过什么恩?”
“混账东西!有你这样说话的吗?就算我们帮过人家一点小忙,老想着人家怎么回报,那么原本的动机就歪了。”
儿子赶忙说:“爹骂得对,我……再不乱说了。”
常惠生缓缓地走在小路上,不时地见到带露的枝叶横到路中来,他像小孩子一样,用手轻轻拈住枝叶放到嘴边,去舔晶亮的露珠,舌尖似乎有了一点甜味。他和尹德山同年,两家人的上一辈子就是邻居,童年时他们清晨相邀去远处砍柴,见到枝叶上的露珠,也是这样去舔,比谁舔得多舔得快。
常惠生忍不住哈哈大笑。
后来,他们都成家了,又都有了孩子。
这块地方除从土里刨食之外,没有任何门路可以赚到活钱,日子过得实在艰难。常惠生除了种田种菜,当过草药郎中的外公教了他几招治病、采药的功夫,所以他家的日子过得稍稍舒坦。
尹德山个子瘦小,还有哮喘病,从土里刨食都不是个好把式。老天又对他格外不公,儿子尹忠三岁时,妻子患急病突然辞世,常惠生拿钱买棺木,帮着他把丧事办完。尹忠十岁时得急性阑尾炎,又是常惠生催促尹德山,两人连夜轮流背着尹忠赶往几十里路外的镇医院,并代交了医药费,这才保住了尹家的这条根。尹忠读初中、高中、大学时,常惠生不时地资助学费……
村里人常在背后议论:尹德山得常家的恩惠太多了,这辈子是还不起了;老实巴交的尹德山还木讷少言,多说几句感谢话都不会,只知道年年月月做完田里的活计,就是在秃毛坡栽树、护树!
常惠生从不认为邻里之间相互帮个忙,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为什么一定要人家念念不忘。当尹忠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每次回家探亲,必登门叩谢送上一份礼物,常惠生执意不收。当尹忠当上中学校长,经济宽裕了,一定要归还历年来的欠款时,常惠生说:“你爹记的账,我不认,是他记错了。”但这满坡的绿意和清凉,悦目清心,常惠生却不能拒绝。常凯曾问他这树将来属于谁,他说当然属于种树人,常凯冷冷一笑:“种在我家地界上的,自有法律去公断。”在这一刻,常惠生恨不得给儿子一个耳光!
终于到了尹家老屋前,常惠生掏出钥匙打开大门的牛鼻子铜锁,也不急着进去,在高门槛上坐下来,点着一支烟,慢慢地抽。
尹德山去城里治病,一眨眼就十天了,是他打手机让儿子尹忠开车接去的。临别时,他对常惠生说:“我的心脏病有日子了,怕耽误儿子的工作,又舍不得你常大哥,一直没言语,现在看来是拖不下去了。这串钥匙就交给你了,让老屋不长霉不生虫。我会……回来的……”
仿佛尹德山真的回来了,也坐在门槛上。他们平日里相互走动时,就喜欢坐在门槛上抽烟、聊天。
风吹满坡树叶,沙啦啦地响,就像他们高高低低的说话声。
常惠生抽完了烟,起身进了堂屋,打开卧室门,进去后再打开朝南的窗户,屋里顿时明亮起来。床、柜、桌子、板凳,老旧得很。墙上挂着几个大镜框,里面嵌着用毛笔字写的红纸。他走过去一看,分明记着常家资助过尹家的一项项钱款。字很漂亮,应是尹忠的手笔。他叹了一口气,说:“德山啊,你老记着这些干什么。”
走出卧室,他又去打开仓库门、杂物间门、厨房门,再回到大门前,坐在门槛上。风从大门灌进去,又去拜访一个个的房间,去触摸家具、农具、厨具,细润无声。
……
谁也没想到,夏至后,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骤然而来,下得昏天黑地,一连下了五天五夜。山洪暴发,各处山体滑坡,不少人家的房子被夷为平地,还死了好几个人。只有秃毛坡因树木多而密且扎根深,居然岿然不动,常家和尹家的房子毫发无伤。特别是坡下的科技园,因排水系统好,安然度过这一劫。
常惠生对全家人说:“你们不是说尹家没有回报我们吗?德山几十年栽树、护树,不言不语地护佑我们,唉!”
常凯低下了头。
常惠生马上打手机给尹德山,没有回应。再打给尹忠,手机里传来了哭声。这才知道,在最后一个风雨之夜,尹德山在医院溘然而逝。临死时,他交代儿子:不要盒子,就把骨灰埋在自家屋后的一棵樟树下;老屋用来安置失去住所的乡亲;满坡的树都归属于常家。
常惠生忍不住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