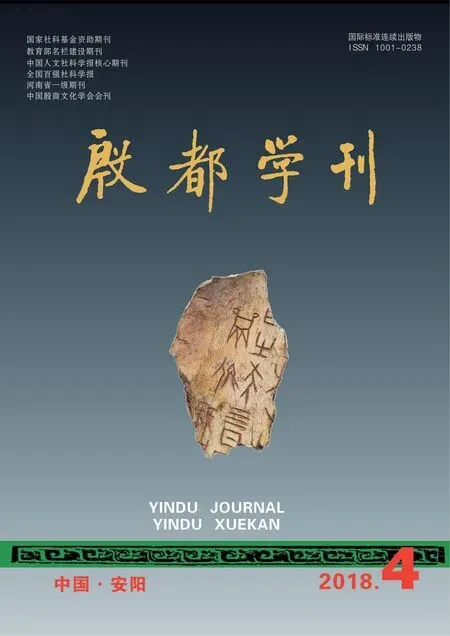论元代士人的游历观念
黄二宁
(北京体育大学 国际文化学院,北京 100084)
自从士阶层诞生以来,游历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方式,对士人的思想、行为、文学创作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谓士无不游。士人通过游学以增进知识学问,通过交游以结交天下之士,通过游说或干谒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通过游历以了解山川物理、风物风俗、天下形势等等。游历又指向对儒家之道的追寻与实践,充分体现了士人以道自任的精神。戴表元《送罗寿可归江西序》曾用简洁的话概括了传统士人的一生历程:“古之所谓士大夫者,少而学成于其身,壮而材闻于其国,及其老而无志于用,则退而以其学师于其乡。”[1](12册P53)
与元代士人游历成风相关,元代士人的游历观念值得关注。除了外在的各种客观条件,游历观念是支撑士人外出游历的重要内在价值支撑。观念上对游历的认同和推许,使得元代士人的游历行为才得以展开。应该说,元代士人的游历观念既有古代士人游历观念的普遍性,同时也具有元代的时代特点。总体上看,在元人有关游历的谈论中,游历对于士人而言极为重要且功能多元。不论是孔、孟的游以行道,还是司马迁的游以著文;不论是唐代士人的游以干谒,还是唐代诗人的漫游作诗,都成为元人游历观念的来源。目前,学术界对元代士人的游历风气有所关注,但对于元代士人的游历观念还缺乏探讨。本文将结合元代士人的相关言论,尝试对其游历观念进行分析,以更好地认识元代游历风气盛行的思想基础。
一、游以致用
蒙元是由蒙古族群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宋元易代之初,出游特别是北游被认为是一种带有政治色彩的行为。除了被俘虏北上者、被征召北上者或者主动投诚者的北游以外,主动的北游干谒还较为少见。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奉命至江南访贤。这对于元代南士北游具有很大的剌激作用和示范效应。虽然不少南方士人没有接受举荐,但是此次访贤行为所释放出来的善意和求贤若渴的意图,也让不少士人看到了仕进的可能,北游干谒的行为从此越来越多,并且慢慢被士人群体所接受。可以说,南方士人对出游的态度有一个从拒绝、尝试、妥协、接受到鼓励的过程,这也是随着第一代宋遗民的逐渐老去和新生代南方文人的不断成长而表现出来的。
赵孟頫是较早北上的南士。由于身为南宋宗室,赵孟頫的出处选择和游历观念对于南士群体的影响是巨大的。赵孟頫的游历观念可以概括为“游以致用”。其《送吴幼清南还序》云:
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甘心草莱岩穴之间,老死而不悔,岂不畏天命而悲人穷哉!诚退而省吾之所学,于时为有用耶?为无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则吾出处之计,了然定于胸中矣,非苟为是栖栖也。[1](19册P66)
赵孟頫认为,士人少而学于家,就注定了必须出而用于国,不然所学何用呢?相比吴澄认为游以求学、助学之说,赵孟頫从学以致用的角度肯定了士人之游的意义。能致用则出游,不能致用则隐居。游以致用类似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最高层次的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赵孟頫对吴澄由游而归的行为也是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的。
当然,游以致用的观念并非赵孟頫独有,更是士人群体的一种集体意识,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士人文化传统本身带有的入世倾向决定的。正如王旭《送康仁叔序》(至元壬辰夏)所言:“士之读书为学,将以用于世,而非欲以独善也。”[1](19册P499)
对于一般的士人而言,“游以致用”的另一个说法是“游以求遇”,即希望通过游历寻找步入仕途的机会。戴表元《送贡仲章序》记载了儒士贡奎由隐而游的故事。文章开头,戴表元就将天之生材与地之产物相比较,认为即使是非常之珍、希有之玩,如果不能被发现,就只能埋藏伏匿、默默无闻,更何况是秀人奇士呢?对于心怀技艺和梦想的士人来说,岂能失去千载难逢的游历时机呢?可见,对于不少儒士来说,隐只是权宜之计,其内心深处魂牵梦绕的始终是入仕。而作用于士人的,除了现实的考虑之外,更是历史上风云际会的士人楷模。正如贡奎自己所说:“奎生三十有一年矣。平居读古传记,见材名气焰士,必快慕之。今纵不得如洛贾生、蜀司马长卿、吴陆士衡,即取印绶节传,为左右侍从言论之臣,尚当赋《两都》、《三大礼》,献《太平十二策》。遇则拱摩青霄,不遇则归耕白云。安能浮沉淟忍,为常流凡侪而已乎?”[2](P148-149)历史上的贾谊、司马长卿、陆士衡等,赋《两都》《三大礼》、献《太平十二策》等求仕行为激励着他,使其内心始终涌动着游以求遇的憧憬甚至激情。这是儒士群体必须经历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历程。
从更现实的角度来看,“游以求遇”即“游以求仕”,其实就是干谒之游。只是在很多时候,出游之人对求仕的目的讳莫如深,反倒是拿出一套别对说辞。蒲道源《送罗寿甫北上序》中的罗寿甫即是如此。他向蒲道源谈起太史公周览天下名山大川而文益奇的故事,感慨“今我幸生明圣之时,四海一家,惟意所适,欲效昔人之游观,开广耳目之见闻,廓达胸中之隘陋,安能局促块居此乎?”当蒲道源问他“子将止于游观耶,抑有为而然耶”的时候,他却笑而不答,蒲道源也就明白了,认为“夫有可用之才,居无可用之地者,君子之不幸也。无可用之才,居有可用之地者,君子之所耻也”,并鼓励他“中州无贤士大夫则已,如有贤士大夫,其必有合焉。则吾子之志,不患乎不伸矣。”[1](21册P188-189)这篇序文深刻揭示了士人在游观的表面之下,求遇求仕的深层目的。这一套修辞和逻辑对于士人群体而言是不言自明的。李祁(1299—?)《赠刘天吉序》将出游士人比作是在渊之珠、在山之玉,必须通过远距离的游历而增价:“夫士之遇于时也,非徒安坐此室,以俟夫人之知也。必其学问之充,闻见之广,而又加之以交游之多,援引之重,然后足以得名誉而成事功。”[1](45册P399-400)可见,士人之游是必要的,目的是求遇,或者求仕进、成事功。
二、游以行志
在元代士人看来,游历建立在士人之志的基础上。戴表元《送庆上人谒永嘉陈使君蒙序》云:“人惟负超旷逖远之志者,必有事乎游。”[1](12册P70)吴澄《送乐晟远游序》评价乐晟远游为“男子之志也”[1](14册P161)。刘将孙(1257—?,江西人)《送戴石玉序》对士人的游历传统有简明扼要的论述: “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此井田既废之叹也。……自孔、孟来,士未有不游,或以师友游,或以宾客游,或以学问游,或以才艺游,或以辞华游,二千年才贤特达,未有非以游而合也。”[1](20册P202)“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的圣人言语成为元代士人解释游历行为的一个依据。在刘将孙看来,士人之游的传统开创于孔子和孟子,是士人实现生命价值的必然选择。虽然具体的手段不同,但游却是士人成名仕进的重要凭借。这从积极的方面充分肯定了游的价值和意义。
元代士人批判甚至抵制士人单纯的“追逐妄走”,而鼓励士人有所为而游。周霆震《送刘弘略远游序》非常典型而详细地体现了这一点:
余昔未壮时,见士之怀才抱艺,有志四方,白首而未遂者,往往悲歌慷慨,怅然负其平生,不胜往日之悔。故凡后进之彦,邂逅相遇,必勉之以不可不出,出之不可后时,又必申其平生悔恨之意而愿望之,若已事之不可缓。间亦为余上下极论。余方盛气自许,以为宇宙分内,何事不可为,在所建立耳,何至是耶!回首三十年风霜百态,心事落落,老已先之。虽伏枥千里,此志尚存,而闻鸡起舞之狂,不为世故消磨者,无几矣。夫然后知其人之志为可感也。[1](39册P147-148)
这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受百转千回的序文,其立论的中心点则是士人之“志”。从“有志四方”的怀才抱艺之士,说到白首未遂的悲歌慷慨,说到自己年轻气盛时“以为宇宙分内,何事不可为”的壮志豪情,再说到自己经历风霜雨雪之后的“此志尚存”,最后说到对“有志盛年”的友人的劝勉鼓励。字里行间回荡的,是作者始终抱有的人生志向不可磨灭的至诚之心。这一点,元末士人王褘《赠郭士中序》中也曾涉及:“然追念余三十许时,驱驰于吴、越、楚、宋、齐、鲁、燕、赵之郊,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不以为难,其好游视今士中尤甚。士中少余十数岁,政余好游之年也,则其操舟趣驾,为是二三千里之行,宜乎无难,是亦志气之盛使之然也?”[1](55册P266-267)那么,这个“志”是什么呢?作者似乎并没有很明确地说明,但给出了相反的说法:“计其足迹所经,殆将遍天下,至于山川形胜,人物气概,古今壮观,名贤志士之所从出,则茫然,孰何?岂为不暇问,就使能问,亦不及知,徒追逐妄走而已。”[1](55册P267)也就是与“追逐妄走”相对立的一种士人之游的状态。
对于士人而言,其最大的“志”莫过于行道,因为“士志于道”,所以“游以行志”也就自然而然地延伸为“游以行道”。元代士人的游历观念始终与士人在政治上的出处、进退密切相关。贡师泰《送谢元功东归序》云:“士君子生于斯世也,读万卷书,驾万里车,将以广吾业,行吾志也。然其出也必以时,其进也必以道。”[1](45册P142)戴良《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亦云:“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处,以存道也。”[1](53册P217)士人群体往往将游历特别是士人的游历与儒道的传承发扬、生命的价值实现等联系起来。南方知名士人的北上在南士群体中引发的反应值得关注。刘岳申在《送吴草庐赴国子监丞序》中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南方士人对吴澄北上的议论,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南方士人的多重心态:
至大元年秋,临川吴幼清先生以国子监丞征,当之京师,郡县趣就道者接乎先生之门。……咸相与言曰:“先生有道之士,不求闻而达者也。监丞七品,其进退不为先生轻重加损也审矣。”或曰:“官虽卑,以教则尊,教胄子又尊。”或曰:“官无卑,君命也。以君命教胄子,先生之任不既重矣乎。方今出宰大藩,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以故中州之人虽有杰然者不在是任,然则南士愈不敢望矣。使先生以道教胄子,他日出宰大藩与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出先生之门,是犹先生之志得而道行也。此世道生民之福也。先生不宜卑小官以弃斯道斯民之福也。”或曰:“先生出处进退有道,众人固不识也。先生尝以翰苑征至京而不就列,又当劝学江右至官而不终淹,今其久速未可知也,由此大任亦未可知也。临川自王氏以文学行谊显,过江陆氏以道显,至于今不可尚。先生出乎二氏之后,约其同而归于一,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者,盖兼之矣。使先生之学行,岂复有遗憾哉。将天下有无穷之休,而复临川有无穷之闻。以临川复显于天下,必将自今始。[1](21册P416-417)
从士人的议论中我们发现,士人的主流意见是支持吴澄北上并对其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通过推行朱、陆之学,得志行道,“以临川复显于天下”。表面上看,这是对江西地域文化的自信和推崇;深层次看,则是对弘扬儒学、从而参与政治的期待。在这个意义上,南人的北游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个人功利目的,带有更深远的社会文化意义,即扩大南方儒学的文化影响力和提升南方士人的政治影响力,为蒙古族群建立的元朝增添更多的汉文化色彩,对于改变“四十年来……故东南人望日以轻”[1](17册P224)([元]徐明善《送彭幼元赞府序》)的局面有积极意义。
但是我们也看到,也有个别南方士人对“游以行道”说不以为然。袁桷《送邓善之应聘序》中对元代士人之游的情状有所描述,表现出了不同于一般士人的游历观念:“夫道成于同而弊于孤,云龙之相从,风水之相应,其理然也。……君子之出也,大言以行道者,夸诬之流也。相时而行,守身于不辱,谨得避难,贞白而无愧,斯近之矣。”[3](P365)此文中,袁桷对“游以行道”进行了批判,认为那只是“夸诬之流”。或许我们可以从袁桷的南士身份来理解他对“行道”说的批判。南方士人在元代政治权力体系中处于边缘,很难对朝廷大政方针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或许正是鉴于这样的政治现实,袁桷才有此说。
三、游以助学
元代士人对游以助学大多持肯定态度。在写给不少北游士人的赠序中,吴澄对出游以增长见闻、丰富学识的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吴澄《送萧九成北上序》云:
今日之事,有书契以来之所未尝有者。自古殷周之长、秦隋之强、汉唐之盛,治之所逮,仅仅方三千里。今虽舟车所不至,人迹所不通,凡日月所照,霜露所队,靡不臣属,如齐州之九州者九而九,视前代所治,八十一之一尔。自古一统之世,车必同轨,书必同文,行必同伦。今则器用各有宜,不必同轨也;文字各有制,不必同文也;国土各有俗,不必同伦也。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而一统之大,未有如今日。睢盱万状,有目者之所未尝睹;吚嗢九译,有耳者之所未尝闻。财力之饶、兵威之鸷,又非拘儒曲士之所能知。君之史学,苟徒稽诸方册之所纪载,而不证诸耳目之所见闻,得无有阙乎?[1](14册P115-116)
这是元人赠序中非常著名的一篇,序文内容极具元代特色。在此序中,吴澄从求学、治学的角度肯定士人之游。在吴澄看来,元代社会呈现出与前代迥然不同的特征,所谓“今日之事,有书契以来之所未尝有者”,呈现出地理大一统、政治大一统和文化多元化并存的文化景观。因此,士人要增益学问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稽诸方策之所记载”,更要“证诸耳目之所见闻”,如此,接地气的“行地之游”自然成为必然的选择。类似的观念还体现在陈栎《送赵子用游京师序》中,所谓“古圣贤立德、立功、立言,学者虽于简编中得之,闭户而可见四海,隐几而可知百代,然未若远游宇内,亲历古人遗迹,而追见其当年,以应简编所云,胜夫想象高唐者之为得也。”[1](18册P82)这与吴澄“证诸耳目之所见闻”的观点殊途同归。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具有元代时代特点的游历观念,是空前扩大的疆域和多元的文化给士人游历观念带来的新变化。
士人群体对游以助学的士人是积极鼓励的。影响所及,即使是没有出游经历的士人,对于士人出游也多给予鼓励和支持。李存是元代中期士人,曾有意远游,但因为家庭之故,未能如愿。因此,当他年老力衰之际,只要有士人远游求序,他一定欣然而作,多加鼓励。士人出游也多向李存求序。《送杨显民远游序》一文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游历观念。李存以隐居教授的学者身份论游,更多关注游历与处隐之别。士人是游还是隐,关键在于对时机的观察和把握,所谓“君子之游处也,惟其时义而已矣”。孔子依然是李存观念中的士人游历应该效仿的楷模。如果不是立志以孔子进德修业之游为目标,则不如不游。李存的游历观念包括两个方面,主观方面是学有所成,客观方面是有道则仕,延续了孔子“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观念,其《送朱可方序》云:“虽然,仆非有动于势利而为是言者。顾以勤苦而为学,遇夫有道之世,不安于独善其身者,当然也。”[1](33册P309)李存将士人的游学、游宦看作是求道、行道之游。程端礼《送娄行所归安吉序》同样表达了“游以助学”的观点:“自学制、田制坏,士贫,始出农工商贾下。穷乡晚学,无书可读,无师可亲,故子游自吴北学,相如东受七经,退之读书江南。士之有志者,其势不得不游且学也。”[1](25册P494-495)序中追溯游学之兴起值得注意。春秋末期、战国时期的游学极为兴盛,诸子百家著述立说、广开私学,而百家弟子则来自各个诸侯国,显示出官学下移、私学兴盛之时士人游学的盛况。杨维桢《送强彦栗游京师序》亦云:
孔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知古人君子未尝不游也。而世之游者漫矣,志无以自信,贸贸焉行四方,以万一乎诡其所遇,取而以复菑其身,以累其人,往是也,乃君子之游。延陵君子之不幸生于东徼也,志不有其国,而独志于上国之游,以历见夫华产之人物、先帝华之遗风善政以广其耳目之陋、意气之隘,约而友之于中,有合不合,斯游之不可已也。[1](41册P259)
对于士人来说,游是一种集观览、学习、求知的实践活动。只有通过游历,士人才能对高山江海、通都大邑、风土人情等有真切认识与了解,才能成为见博识广的“闻人”。
值得注意的是吴澄,作为元代一流儒家学者,他在不同的场合对游历持不同观点,显示出更丰富、更有层次和更多侧面的游历思想。其《收说游说》一文论及士人游的传统及元代士人之游,可以看作是吴澄游历观念的一次集中表述,但他在此文中却表达了与“游以助学”相反的观点。[1](14册P639-640)文章开宗明义“古无游士也”,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在吴澄看来,游士起于王政衰微的春秋、战国之时,以孔、孟为代表的以“圣贤救世之心而游”,其宗旨在于救世。战国游士既有“大肆其意,以傲世主”的一面,同时也有“比之妾妇”、“可贱甚矣”的一面。战国以后的汉、晋、隋、唐,由于封建一统政权的建立,士人之游远远不如战国之盛。南宋末年,由于科举不利,很多士人再次以游求仕或者干谒求官。对于这类干谒之游,吴澄认为是甚可哀伤的。对于元代士人以为学之游为由、“非以蕲名,非以干利”的一套说辞,吴澄有针对性地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如若孔子在世,士人游学孔门是值得肯定的。但现实是世无孔子,还有谁值得士人不远千里前去求学呢?士人真要学习儒学知识,只需要认真研读圣人遗言即可,何必出游?对于不少士人主张的司马迁游以著书之说,吴澄直斥为大谬不然,认为司马迁之学得于家学的父子授受,而非游历,“谓子长因游而有史者,谬也;信其说者,惑也。”也许是出于特殊的写作目的,吴澄在此否认了游对于士人为学的帮助。在他看来,士人治学最重要的还是阅读“古圣贤遗言”,他因此劝说陈熙不要出游,而是在家规规矩矩地阅读家庭藏书。据吴澄自己说,确实有人听从了他的劝告,不再出游。吴澄《赠道士黄平仲远游序》云:“士之远游者过予,予辄止之曰:‘道修于家可也。既仕而驱驰王事,则有四方之役,处士而离父母、去妻子,栖栖奔走,将何求哉?因吾言而不复游者有焉。”[1](14册P110)
作为数次北上的南人吴澄,表达了重内游而非外游的思想。但这并非吴澄游历观念的全部。如果抱以同情之了解的话,作为元代南方大儒,吴澄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有所了解的。他鼓励年轻人重在读书内修,而不鼓励其外出干谒,固然有其理学注重内在修养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或许正与吴澄的北游经历有关。他亲身经历和体会了蒙元政权中的南方士人的处境,因此才对南方士人出游干谒的前景持不那么乐观的态度。与其到处碰壁,不如修养身心,这或许是吴澄内游思想的外在原因吧。
四、游以助文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若乃山林臯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4](P694-695)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古代文学地域风格论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唐宋以前,批评家往往只看到某地域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对这一地域文学艺术家的影响;唐宋以后,逐渐重视社会阅历对创作的巨大作用,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批评观念:不同的地域风貌与各地的民情、文化,可以丰富诗人的审美感受,开拓和形成诗人更为健全的风格,开始重视“江山之助”对创作的影响。[5](P208)事实上,这种山川游历与空间转换确实能对诗人创作的题材风格产生影响。以至于到南宋时期,有“子欲学诗乎?则先学游。游成,诗当自异”[2](P99)([元]戴表元《刘仲宽诗序》)的说法。这种说法是对“江西诗派”主张通过阅读经典实现“无一字无来历”的反动。南宋时期的杨万里、陆游,均强调经验世界是诗歌创作的重要素材。[6](P535—538)
元人的游历观念直接继承了宋人的游历观念。宋代文人的游历观念已经比较成熟,对游历与道德修养、游历与增益学问、游历与诗文创作等的关系已有不少论述,认为游历具有道德、学问和文化意义。[7](P18)比如胡瑷说:“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于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8](卷下)苏辙亦云:“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9](卷119)元代士人继承了这种诗文创作观念。对于有意进行诗文创作的士人而言,在“游以求遇”的功利观念之外,出游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游以助文”[10](P89—96)。太史公游历南北是士人话语中游以助文的典范。李庭《送荆干臣诗序》云:“才质本乎天,闻见存乎人。苟闻见之不广,虽负奇才美质,莫能有所成也。昔太史公以命世之才博极群书,而又南游江、淮,北涉汶、泗,周览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游,故发而为文章,雄深雅健,卓然为一代之冠,岂无自而然哉?”[1](2册P145-146)比如吴莱喜游,在礼部任职期间,曾东游齐鲁,北游燕赵。从礼部辞归后,出游舟山普陀,写有《甬东山水古迹记》、《听客话蓬莱山紫霞洞》等。山水游历对吴莱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曾说:“胸中无万卷书,眼中无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纵能,亦儿女语耳”[11](卷11)这也是普遍存在于士人群体中的一种游历观念。
傅若金《送张闻友游湘中序》中对游历激发起士人文思感慨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昔者,余过熊绎之封,登定王之台,访太傅之庙,古今交于前,忧乐集于中。南望苍梧、九疑絪緼,而有虞巡狩之迹,缤然结乎吾虑矣。北眺大别,江流滔滔,而禹平水土之功,悠然兴乎吾怀矣。左瞻炎帝之陵,则思耒耜之教矣;右顾三苗之山,则慕干羽之舞矣。由是浮沅湘,求骚人之事;并江汉,询文王之化;历河岱,挹邹鲁之风。然后北之京师,以观其会;南至越裳,以极其远。凡吾气之所发,见闻之所益,而于道少有进焉,游之助也。”[1](49册P290)傅若金结合自己的经历,对游历激发文气、增益见闻的阐发可谓详尽。元末士人王祎《赠郭士中序》则结合司马迁游历的经历加以论述:
……余闻之,昔人之好游,非徒游也。昔之好游者,无如司马子长,其足迹殆且半天下,而其所历揽山川之形胜,悉用资以为文。其得于大江、长淮、洞庭、彭蠡,则为文奔放浩漫,渊深而渟滀;得于龙门、剑阁、九疑、苍梧,则为文崭绝峭峻,纡郁而幽深;泛沅湘,吊忠魂,则其文感愤而悲激;过大梁,涉丰沛,观争战之墟,则其文沈雄而凌厉;讲业齐鲁,乡射邹峄,想圣人之遗风,瞻泰岳之尊安,则其文典重温雅,有正人君子之仪焉。是其所以奇于文者,庸非以游故耶?若子长者,其长于游者耶。[2](55册P266)
在王祎的观念中,游以助文的典范是司马迁,他给后人的启示是,士人历揽山川形胜,其最直接的效果体现在“悉用资以为文”。王祎对不同地域与相应文风的形成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虽然稍显呆板,但大体可以成立。因此,王祎认为,士人之游务必“历揽所及而资以为文”,否则即是“徒游”而已。
特别是南北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元代,在论诗者看来,更应该打破地域之界限,游历南北,兼收并蓄,实现南北诗风的融合。张之翰《跋草窗诗稿》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种观念:
宋渡江后,诗学日衰,求其鸣世者,不过如杨诚斋、陆放翁及刘后村而已。固士大夫例堕科举传注之累,亦由南北分裂,元气间断,大音不全故也。余读建安刘近道《草窗诗稿》,见其风骨秀整,意韵闲婉,在近世诗人中尽不失为作家手。然中原万里,今为一家。君能为我渡淮泗,瞻海岱,游河洛,上嵩华,历汾晋之郊,过梁宋之墟,吸燕赵之气,涵邹鲁之风,然后归而下笔,一扫腐熟,吾不知杨、陆诸公,当避君几舍地。但恐后日之草窗,自不识为今日之草窗也。[1](11册P302)
事实上,元代士人的远游经历也确实起到了提升诗艺的目的。比如清江人皮昭德,于大德十年秋如京,第二年南还,“有《北游杂咏》一编,视前作逾超。盖诗境诗物变,眼识心识变,诗与之俱变也宜。……计其一往一来,半载间尔。……不但诗进,而学亦进矣。”[1](14册P474)([元]吴澄《皮昭德北游杂咏跋》)戴表元曾经留意观察游历对诗歌创作是否发生影响,其《刘仲宽诗序》云:“及徐而考其诗,大抵其人之未游者,不如已游者之畅;游之狭者,不如游之广者之肆也。”[2](P99-100)而对于那些因为游历不广而诗艺受限的士人,则多有惋惜之意。比如王执谦(1266—1313),字伯益,大名(今属河北)人。“常谓人曰:‘吾知吴楚多瑰伟奇绝者,当委身往游,乃称吾意耳。’杨载曰:‘然。诚广伯益以山水之胜,视陈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1](27册P505)([元]虞集《王伯益墓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虞集。他认为,元代南北一统,交通便利,为士人之游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因此对士人出游也持鼓励态度。“国家混一以来,有欲观夫徂来之松、新甫之柏,瞻龟山之云、泳沂上之风者,川有舟航,陆有车马,不待赢粮计日而可至。视前代分裂隔乱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则其游岂不快哉!”[1](26册P192)与此同时,虞集也清醒地认识到,士人之游也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即“有其志、有其财、有其时”,也就是要有游历的志向、游历的资金和游历的时间。
总之,元代士人的游历观念绝非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山水观览,而是以孔子、孟子、司马迁作为士人之游的典范,强调广大的地理地域、多元的文化现实、深厚的区域历史文化对士人求学、治学、作诗、作文等修养方面的深刻影响,以及游历对士人致用、行志、行道、求遇等经世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与元代士人面临的时代政治环境和背负的文化责任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南北文化交流的加深,从宋、元易代之初的谨小慎微,到元中后期的自由游走,元人的游历观念经历了颇为显著的变化。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元代士人游历行为丰富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