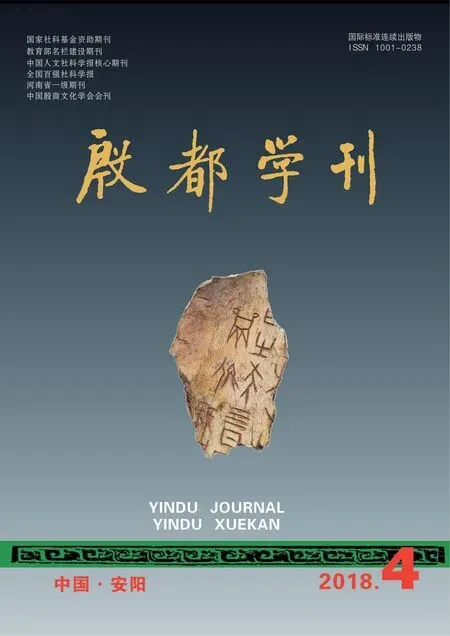“史学”概念的古今演变与中外对接
高 远
(安阳师范学院 历史与文博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历史文化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术语意涵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诚如陈寅恪在《致沈兼士》中提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以“史学”一词为例,始创于魏晋,代表一种学科与一门学问。后经隋唐及以降诸朝不同语境的使用,其指示性也随之变得模糊,在原有的基础上引申出各种不同的词义。概而言之,一种是以“史学”定义为一种学问的修养状况;一种是称研治史书之学为“史学”注据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对“史学”概念古今演变过程探讨最多的应为谢贵安先生,如“史”、“史官”与史学起源;史学独立的形成期:魏晋南北朝史学;隋唐宋元史学的重塑运动;宋代“史学”概念与理论的发展;辽夏金元的“史学”概念;明清“史学”概念的新发展;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晚清至民国。见于氏著《中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瞿林东先生亦列有专节讨论“史学”是什么?指出:“自唐、宋学人从科举取士出发而论‘史学’,到章学诚从认识论方法论的不同角度论述‘史学’,‘史学’这个范畴的演变及其内涵的日益丰富,透视出中国古代史学有了多么巨大的发展。”见于氏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11~12页。邹振环先生对“历史学”或“史学”一词也有精要的论述,文字不多却很有启发意义,见于氏著《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相对而言,学界对“历史”一词语义变化探讨的比较成熟,分别见于周振鹤:《十九、二十世纪之际中日欧语言接触研究——以“历史”、“经济”、“封建”三译语的形成为说》,载氏著《逸言殊语(增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179页;彭忠德:《从“史”到“历史”》,载冯天瑜、[日]刘建辉、聂长顺主编《语义的文化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8~549页;彭忠德:《“历史”一词探源》,《辞书研究》1991年第5期;李开元:《“历史”释义》,《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毛一波:《历史一词的来源》,《大陆杂志》1963年第27卷第9期;[日]佐藤正幸、郭海良译:《历史认识与历史意识:关于“历史”一词的研究》,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史与诗:世界诸文明的历史书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台湾学人方志强先生亦对“历史”与“史学”的定义有一定的探讨,见于氏著:《西洋史学史的定义及其内涵的演变——兼论历史与史学的定义》,《“国立”中正大学学报》1997年第8卷第1期。。清末民初以降,随着西学的大量词汇与概念以及许多西学学科内容的引入,以日本为中介的西学术语大量涌入中国,从而使中国文化的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得以丰富发展。在其嬗变与重构的过程中,本内涵明确而稳定的“史学”语词,在接纳外来异质文化的过程中赋予新的含义,与传统的“历史”语词及近代新生的“历史学”、“史学史”术语缠结在一起,共同经历了历史语义文化演变过程中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今天通用的“史学”一词,便是近代学人借用中国固有的“史学”概念与译介西方相关语汇时,加以融铸再创而成的。可以说,“史学”术语的近代转换,诠释了西学引入的过程既受到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接受需求的制约,也包含着中国人的主观选择。此一梳理、辨析工作,当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亦为“适度解构现有的史学史体系,试图恢复中国史学发展的原生状态”[1](P12)提供借鉴。
一、概念溯源:“史学”词称之语义演变
“史”、“历史”、“史学”是三个关系非常密切的词汇,目前学者对“史”、“历史”两词语义的变迁探讨甚多。如杜维运、黄进兴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论文选集(第1集)》中载有四篇专论“史”字的论文:胡适《说“史”》、沈刚伯《说“史”》、戴君仁《释“史”》、劳幹《史字的结构及史官的原始职务》。[2]另外,学界还有顾实《释中史》[3]、陈梦家《史字新释》[4]、王国维《释史》[5](卷6)等文。好在如今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甲骨文材料,从而使得我们从中考察“史”字的本义和史官的早期形态,已然成为一种可能。
“历史”一词的含义,从历史发展上看,亦有一个变化过程,目前学界对此已有较深研究,如彭忠德先生的《从“史”到“历史”》、李开元先生《“历史”释义》等。从“史”到“历史”的演变过程,既是史学发展上两词所蕴含概念的古今演绎过程,也是近代中外史学交流中的一个重要成果。此饶有意义的课题,应对其学术影响作别开生面的探索。本文将着重考察“史学”古称涵义与近代词义的翻新,探析其在清末民国时期的演化及其史学意义,以期有补于中国史学史研究。
“史”、“学”二字连用,在中国古代书籍里确实出现的很早。据《晋书·石勒载纪》载,石勒于晋元帝太兴二年(319)自立为赵王,以“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8](P2735)。尽管无法确定此时的“史学”究竟在何种程度意义上表示一门学科,但从与其同时设置的还有经学祭酒、律学祭酒,此举在客观上有提高史学地位的意义。尽管由于文献有限,“史学祭酒”的功能还不能在帝王的史学顾问、有资治道之外作更多推论,但是从此前与此时代大致接近的裴松之注《三国志》称杜预研究历史经典《春秋左传》,著述甚多,“备成一家之学,至老乃成”,可旁证任播、崔濬二人当为博学之人。且从《石勒载纪》中令他人著《上党国记》《大将军起居注》《大单于志》等可知,史学祭酒一职与撰著史书等业务尚无较多关涉。南朝刘宋元嘉十五年(438),立儒、玄、史、文四学,“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薇之并以儒学……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9](《雷次宗传》,P2294),此事在《宋书》《南史》中亦载曰:“承天……寻转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聚门徒,多就业者”,可见何承天已将撰著史书与立馆授徒相结合,为后世史学发展中理论教学与撰史实践相结合的滥觞。
魏晋时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史学单独立学,表明史学在中央教育制度中相对于经学等获得了独立,成为了一门具有较大自律性、具有独立的学科任务的学问。到了宋明帝泰始六年(470),“置总明观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10](《职官九·国子监》,P764)故“史学”词称之应用,当起于此一时代。其后,“史学”一词之发展衍变经历了四个阶段:其一为隋唐五代,“史学”概念的发展与进一步确立时期;其二宋辽金元,“史学”概念的基本定型与理论的丰富时期;其三为明清,“史学”概念的完成与新发展时期;其四为清末民初,“史学”概念的嬗变与中外对接时期。欲明近代“史学”概念的重构,有必要对“史学”词称之原始语义进行溯源。
第一,实则一般所谓“史学”,是一种学科、一门学问。所称中国自古有史学,盖谓有此一门学问。石勒建“史学祭酒”,即此门学问之专官,这是一个宽泛层次。至唐代,“史学”作为“历史之学”的概念进一步明晰和确立。欧阳詹称赞马公“好史学,历代英豪得失皆核,其有不正不直,辨论慷慨,若加诸已”[11](《马公墓志铭并序》)。这里的“史学”与“历代英豪”相提,则证明所说的就是历史之学。在唐代学校教育中,史学已成为其中的一门学科。据《唐六典》卷21《国子监》载,唐玄宗时国子监有六学,除了国子学和太学外,还有四门学,即史学、律学、书学、算学。后来这一制度曾遭废寝,唐穆宗长庆二年(822),“谏议大夫殷侑奏礼部贡举请置《三传》《三史》科,从之。”[12](《穆宗纪》,P502)科举之有“史学”自此始。宋代“史学”已成为一种独立学问,直接以“史学”为名的书籍开始出现,如黄继善《史学提要》、熊庆胄《史学提纲》、郑仪孙《史学蒙求笺注》。司马光曾表示自己经学与史学都很热衷:“又好史学,多编缉旧事,此其所长也。至于属文,则性分素薄,尤懒为之。”[13](卷59《上始平庞相公述不受知制诰书》)这里将史学与经书和属文(文学)相提并论,则此史学属于史部之学或历史之学已无疑义。明代胡广等奉敕编撰的《性理大全》,该书第二十七卷以下,捃拾群言,列为十三目。其中“学”字所含内容包括:小学、为学之方、存养、知行、力行、教人、人伦、读书法、史学、字学、科举之学、论诗、论文。可以见到,史学和字学等地位已经相当。明代“史学”已经独立,史学与其他学问分家,是势所必然,也与人的精力有限有关。胡应麟提出:“天之生才有限,士各以其性质所近而专门名家”,并指出“学问之道非一,为之者往往困于资之难兼,而日之弗暇给,于是或以经学名,或以史学名,或以典章经制名,或以百家小说名。”[14](卷100《策一首》)看来,在胡氏所提出的学术框架设计中,史学是占有其重要地位的。不过相对而言,“史学”的地位仍较经学为低。直至清代,“史学”这种专门学问,还仍是教育和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且其重要性较前代还有所增加。如雍正十年,朝廷“议准书院肄业士子,令院长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再以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至每月月课,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酌量兼试”[15](卷74《选举略三·考绩》)。
“史学”不仅是科举考试的科目,也成为了世代相传的家学以及独立的学术门类。《旧唐书·文苑传下》载,宪宗对学士沈传师说:“朕思古书中多有此事,次编录未尽。卿家传史学,可与学士类例广之。”《旧五代史·曹国珍传》称“国珍常以文章自许……经艺、史学,非其所长”,明确指出当时的“史学”与经艺、文章(文学)为不同的学术门类。宋朝王禹锡在为王明清《挥麈后录》所撰的序中指出王明清“家传史学三世矣”。在元代,“史学”更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因此常与“经学”(理学)等相提并论。元朝郝经有《经史》专论,明确使用了“史学”的概念,并与经学相互比较而论之,提出了古无经史之分的论点。元代张之翰在《故文林郎安吉州录事参军叶公墓志铭》称叶氏“未尝一日废书,六经、诸子而下无不读,尤邃史学”[16](卷20《故文林郎安吉州录事参军叶公墓志铭》)。将六经、诸子与史学相提并论,显然是四部概念下的史学词语。清人已有明确的学术分科意识,如阮元认为:“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17](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P7)陆世仪在《思辨录辑要》卷一中把学术分成五种,即经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古学、文辞(文学),并对各种学术的弊端逐一作了论述,显然“史学”是其中的一种,与诸学比肩而立。
第二,所谓“史学”,乃是一种学问的修养状况。自“史学”一词出现后,内涵为历史知识的“史学”便很快成为一种学问的基本素养。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有言:“有一俊士,自许史学,名价甚高。”[18](P207)《南齐书》卷39《陆澄传》称赞南朝梁代的王摛“亦史学博闻”。《旧唐书·王叔文王伾传附》称凌准“有史学,尚古文”。《新唐书·周墀传》称周墀“长史学”。在重视史学素质的背景下,刘知幾提出了“史学三长”的理论。“刘知幾的‘才’是指经营史学的技艺、方法和路数,‘学’是指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和史料,‘识’是指修史的识见,据刘知幾此处的叙述,似乎是指在修史中所持的直书大义。此后,史学素质成为人们衡量士人的重要标准之一。”[1](P145)故人们常用“有史学”、“长于史学”、“尤喜史学”、“究心史学”、“嗜史学”等术语称赞熟知历史知识、掌握研习技能的人。尤其是明清两朝,“史学”已成为士人的基本素质,如嘉靖间人高应旸“博雅多才,史学尤邃”[19](卷79乡贤);万历末艾南英也是“究心史学,为《古今全史》千余卷”[20](卷82人物十七·抚州府三);清毛奇龄称赞康熙间人卢宜“公长史学,熟明代掌故”[21](卷106《皇清敕封文林郎弗庵卢公墓志铭》);施闰章称康熙间房廷祥安葬父母后,“即庐墓侧,读书贯穿群籍,尤喜史学,余力为诗,有手录诗书词赋凡二十四卷,藏于家。”[22](卷19《房季子墓志铭》)看来,史学作为一种精神生活与素养,在现实中是受到人们普遍重视的。在此基础上,章学诚发展了刘知幾的“史学三长”之说,增加“史德”合为“史学四长”。至就史学修养而言,刘知幾、章学诚之著作,被学者公认为史学,其故即在此。诚如金毓黻言:“或又谓吾国自有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有史,自有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然后有史学。”[23](P278—279)
第三,以我国古代观念,大率以“研治史书”为“史学”。西汉中期以前,“史书”概念一般是指书吏应掌握的文字及其书写技能和书法艺术,但在西汉末年逐步转化为历史书籍的涵义。至唐代,史书概念完全成了历史著作和史学图书的意思,成为史学独立的一个重要表征。宋代不再仅仅把“修撰史书”作为“史学”,而是把“研究史书”的学问视为“史学”,包括对史书所做的注释音义、辨疑问疑、刊误纠谬、总结史例、史论史评之类的学术研究。这在南宋尤袤著的《遂初堂书目》所立“史学类”中有所反映。元初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称“先君笃史学”,重视史注博洽、书法义例,故胡三省“史学不敢废”,作《〈资治通鉴〉注》。这里说的“史学”主要是指编纂学、文献学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了“史学”的内涵。明人承继前人观念,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五《史学类》所收的书籍,皆为明末人心中的狭义的“史学”对象。广义的还应包括本书卷四的《国史类》、本书卷五的《别史类》与《霸史类》等。作为狭义的《史学类》,内容包括如下方面:第一,对历史事实与人物的史论和史评;第二,对史书体例和书法的分析和探讨;第三,对史书的考订和辨疑;第四,对史书的补遗;第五,对史书的注释。清人对此“史学”概念的理解更为宽泛,包括种种体裁的史书、纪传体的各部件之学和史传之学、谱牒之学,以及用种种史料考证史实的学问。以此概念界定,“以往史学的工作,不外两大部分:专重考据,近乎汉学;专论事实之得失优劣,近乎宋学。前者之弊,流于穿凿;后者之弊,流于附会。其他一种,专重体例之研究,评骘群史,要非学力渊博,不能率尔著笔。”[24](P18)如朱鹤龄指出:“今幸此书(《三朝北盟会编》)钞本犹存,而字句多脱谬,学士家亦无校雠及之者。甚矣,史学之不讲也!”[25](卷13,P636)这里的“史学”即指史书的校勘工作。
二、世风与语境:“史学”的近代界说与中外对接
道光二十年(1840)发生的鸦片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命运,同时也促使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现代转型。中国“近现代”(modern)史学是一种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历史学科。在清末民初,伴随着西学东渐力度的剧增,以日本为中介的西学术语大量涌入中国,传统的“史学”概念在这样的新学大潮中,进行着自身的改造与迎受。王先明在考察近代新学时曾表示:“新学家们对于西学的引入并不是无选择的,西学引入的过程既受到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接受需求的制约,也包含着中国人的主观选择。”[26](P303)同样的道理,“史学”概念的近代界说,既受到传统“史学”意涵的制约,也受到近代“新生”的“历史”(指近代意义语汇)、“历史学”、“史学史”术语的缠结,它们共同诠释了历史语义文化演变过程中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
其一,“历史”与“史学”的淆用。在近代之前,中国只有“史学”概念,没有“历史学”概念。“历史”及“历史学”是近现代史学的标志性概念。“历史”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于《三国志·吴主传》:“(吴王)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这里的“历史”,是“历”、“史”二字按语法规则联用的结果,并非独立的复合词,意思是“过去的史书”。隋唐以来,“历史”一词几乎不用。明万历年间,有署名袁了凡之《历史纲鉴补》出现,尔后,清代章学诚《文通史义·修志十议》中有“历史”一词,有“夫历史合传独传之文具在”之语。以上几例俱指“历代史书”含义,此意义上之“历史”亦作“历代史”,并无近代意义。由于中国文化对亚洲文化圈的影响,如袁了凡《历史纲鉴补》的就在日本有所流传,此书“早在江户时代的宽文三年(1663)就有了和刻本”[27](P11)。日本近代学者起用中文“历史”二字来翻译西文“history”,或许与此一类读物的流行不无关系。例如,晚清时期,日本汉学家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合著《支那史》传入中国成为晚清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后的最为通行的历史教科书,此书有三个译本:《中国四千年开化史》(1902年)《支那史》(1903年)《新体中国历史》(1907年)。张舜徽先生指出:晚清中国出现了《历代史略》、《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类的课本,“受当时日本所编学校课本的影响很大。”[28](P21)表明中国使用“历史”一词与日本有紧密的的关系。
的确,赋予“历史”以现代词义的正是日本的福泽谕吉,1860年他第一个用中文“历史”对译英文“history”,[注]也有学者认为“林鹅峰是最早使用‘历史’一词的日本人”,“他在这里使用的‘历史’一词是指‘中国历代史书’”。具体论述见[日]佐藤正幸、郭海良译:《历史认识与历史意识:关于“历史”一词的研究》,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史与诗:世界诸文明的历史书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其撰写的《西航记》中述及西方学科之分为五:“第一语学,第二历史……”19世纪末中日交往频繁,日本的译词也进入汉文文献,1889年,黄遵宪访日归来所著《日本国志》的三十三卷《学术志·西学》中,介绍日本兴办西学的情况时提到:“有小学校,其学科曰读书、曰习字、曰算术、曰地理、曰历史。”这可能是中国汉文文献首次使用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一词。后经罗振玉、王国维二人的运用,“历史”一词的近代意义遂为中国史学界所熟知。在此之后,“经过著名学者和新式教科书、新式学堂的推广,黄遵宪从日本接回的现代意义的‘历史’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广泛使用开了。”[29]与此时间甚为接近的1896年,康有为著《日本书目志》指出:“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日本所译盖多,而《历史哲学》……诸书备哉灿烂”、“今考日本之史,若《日本文明史》……《明治历史》……,皆变政之迹存焉”。此可为此期“历史”一词已经得到更多学界认同的见证。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上《重定学堂章程折》,将“历史”取代“史学”作为主要授课科目名正式列入各级学校。“历史”一词,作为授课科目之名称,广泛使用于中文,当由此开始。
由于“历史”一词与history相对译,因此便产生了与传统不同而与西方相接的涵义。“History”来源于古希腊文historia,意思是指研习得知的往事及其记述。在西方,讨论“历史”涵义的专文及专著,可谓汗牛充栋,结果是意见纷纭。一般认为history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指构成人类往事的事件和行动;第二,指对此种往事的记述及其研究模式。前者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称为过去,或称往事),后者是对发生的事件所进行的研究和描述(往事的记录或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学者以“历史”对译“history”时,亦莫衷一是,这在当时出版的史学概论教材中都有反映,如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杨鸿烈《史学通论》、陈汉章《史学通论》、李则刚《史学通论》、李守常《史学要论》等。因为“历史”所具有的双重含义,难免在使用上与“史学”概念混淆不清。
“历史”与“史学”不同。“历史”指人类之活动过程,属本体范畴。“史学”常由Historiography对译,其含义一般具有两种:“历史的撰写”(the writing of history)与“历史的撰写的研究”(the study of the writing of history)或“历史探求过程的研究”(the study of the processes of historical inquiry),属认知范畴。杨鸿烈在其《史学通论》即已指出中外学者将“历史”与“史学”混为一谈的现象。其书第一章导言就首在急于辨别“历史”与“史学”是截然二事。他指出:“‘历史’为文章(广义的)一种,‘史学’为学问的一种;‘历史’尚不过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或材料,并非可以说史籍的自身即成为史学。”[30](P2)并为“史学”定义如下:“研究与‘历史’有关系的种种‘理论’和搜辑、鉴别、整理史料的最可靠的‘方法’与必须技能的学问,就叫做‘史学’。”[30](P30)胡哲敷则谓:“史学是以人类为中心,记述过去演进的事实,求其因果,以激励来者,和明白现在情势的学科。”[31](P15)卢绍稷则言:“史学者,研究人类社会继续活动之迹象,以寻求其因果关系之学也。”[32](P16)周容在其《史学通论》中也指出学人对“历史”与“史学”的淆用,指出“史学是综合整个的历史的历程的事实,发现历史本身的演进与变化的因果关系及其一般的原则的科学”[33](P11)。以上所论的“史学”,明显带有近代语境的痕迹,在古汉语义的基础上接受了外来词汇“历史”概念的影响。
其二,“历史学”等同于“史学”。“历史学”是基于“历史”概念之上形成的一种关乎历史的学科。“历史学”在西方的表述,一般情况下是使用history一词,有时使用historiography(编史学)一词,有时则使用philosophy of history(历史哲学)。显然,西方比较重视历史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哲学之间的区分,而中国则不太注意三者之间的细微区别。“历史学”一词一般认为是从日本引入的,1879年“历史学”一词已经出现在日本学者翻译的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所著《英国文明史》的第一编第七章。汉文文献中目前已知最早在1901年《清议报》上使用了这一词汇。1902年3月10日,梁启超在其发表的《史学之界说》中也使用了“历史学”一词,他指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现象者何?事物之变化也。宇宙间之现象有二种:一曰为循环之状者,二曰为进化之状者。何谓循环?其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如四时之变迁、天体之运行是也。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是也。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进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天然学’。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他这里的历史学是广义的历史学,凡人类过去之活动及所创造都属于历史学的范围。显然,梁启超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对应,历史科学实际上相当于社会科学。此后,“历史学”开始流行。光绪三十年(1904),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命令学务处发布的《学堂歌》就使用了“历史学”的概念:“历史学,知已往,世界变迁弱变强。地理学,先本乡,由近及远分方向。”[34](卷199《乐十二·乐歌声谱》)
由于学术交流和思想自由的环境,“历史学”这一打上西方文化深刻烙印的概念,得以广泛使用。此时的“史学”等同于“历史学”。 1897年唐才常撰成的《史学论略》一文,虽然已赋新义,但仍用“史学”一词。1902年陈黻宸《独史》一文中有“泰西史学所以独绝于一球者矣”[35],此“泰西史学”即“西方史学”之意。晚清时,一位佚名学者专为报纸写了一篇《史学》,指出西方虽不设史馆,但其报馆职能足以当之。特别强调报纸发行面广,史馆成了一国公权,史学也成为人民的一种职业:“况其推广新闻纸之多,虽至酒楼茶肆,往往而有。是史馆为一国公有之权,史学乃四民与知之业。”他还特别将报纸所载的典章制度与中国传统史书中的表志相挂钩,认为二者相同:“且凡地数、民数比校多寡,火车、铁路、电线推算方里,货殖出入吨数以及官制、教会、学校、国计、兵数,靡勿签记赅核,与中史各表志例同。”他还阐述了一种颇有远见的观点:“按《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出稗官,如淳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以讲说之。’盖今日之报章,即异日之史料。政治家、格致家、律法家,胥权衡于此,一举而三善备焉。故本报之首史学专门者,诚重之也,诚慎之也!”[36](卷3《文教部三·史学》)文中使用的概念,不是“历史学”而是“史学”,但这种“史学”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史学,而蕴含了西方历史学之义,等同于“历史学”了。
民国以还讨论“史学”的专书渐多。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大钊《史学要论》中反复使用了“历史学”这一概念,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释“历史”一词。在书中,他用了两个标题“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其中在解释历史学的系统时指出:“最广义的历史学,可大别为二大部分:一是记述的历史,一是历史理论,即吾人之所谓历史学。严正的历史科学工作者,乃是指此历史理论一部分而言。”[37](P95)1930年世界书局出版的刘剑横《历史学ABC》一书,其第二章为《史学渊源》,下列两个子目为“历史学的起源及其发展”、“历史学演进的三大阶段”,明显将“历史学”与“史学”等同。1933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周容《史学通论》一书,明确指出“我们所谓的史学,即是历史科学,即是历史的理论(Theory of history)”[33](P10—11)。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则刚《史学通论》一书,书名以“史学”冠之,而内容所论皆用“历史学”。贺昌群为“史学”所下的定义即以“历史学”名之,他说:“历史学为通儒之学,为古今合一之学,故往往言远而意近。世无纯粹客观之考证,亦无纯粹主观之议论,客观与主观,如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38](《序言》,P1)
其三,“史学”与“史学史”的缠结。中国原来并没有“史学史”这一概念,它应该属于外来词,耿淡如在《什么是史学史》一文中指出:“相等于英文‘Historiography’俄文‘Историоrрафuа’法文‘Historiographie’德文‘Historiographie’。这些词,在外文用法里有时指‘史学’,有时指‘史学的发展史’。”[39](P83)由此可见,“史学史”一词的出现,亦有词根“history”引出。我们在用history一字来描述对过去的探究时,亦具有不同类型。方志强先生在《西洋史学史的定义及其内涵的演变——兼论历史与史学的定义》一文中为我们举出了Carl L. Becker(1873—1945)自述其一生研究历史的例子。其年轻时致力于“历史的研究”(the study of history),此指探究事实(facts)的繁琐的史料考订;中年时致力于“历史本身”(history himself)的研究,此指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的研究,赋予新的意义;年老时则着重在研究“历史研究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tudy),即“史学史的研究”。Carl L. Becker研究历史的过程,亦即“史学”不同语义下所涵盖的内容。“史学史”此一词称的生成,明显是借用了中国古典词“史学”所包蕴的意向,直接对译西洋概念。
“史学史”一词在中国的使用当不晚于1920年代。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了“史学思想史”(注:这门课属于北京大学史学系规定的必修课“欧美史学原理”的内容),李大钊讲课的讲义即名为“《欧美史学史讲义》”[40](P230),此讲义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仅存孤本,由傅振伦赠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并附傅著李大钊事略及讲义编印年月考,然此资料不幸遗失于人民出版社某编辑手中。
“史学史”概念产生后,与“史学”语义紧密相联。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导言曾对“史”、“史学”、“史学史”三个名词加以定义:“史字之义,本为记事,初以名掌文书之职,后仍被于记事之籍,今世造新史者,上溯有史以前,覃及古代生物,而治史之的,仍为人类社会,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求其变迁进化之因果,是谓之史。更就已撰之史,论其法式,明其义例,求其原理之所在,是谓之史学。最后就历代史家史籍所示之法式义例及其原理,而为系统之纪述,以明其变迁进化之因果者,是谓之史学史。”[41](P2)金毓黻对“史学”与“史学史”的定义皆以史学方法论为依据,则显示出其所受时代限制。其实,“史”、“史学”、“史学史”属于三个不同层次的研究,“史学史”本身就是“史学”的一部分,常可称为“历史性的”史学。但必须注意,史学史乃对史学自身之研究,其对象是史学,而非历史。
“中国史学史”这一中文名称,就我们目前所知,是胡适在1924年发表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中最先提出来的,他说:“这一件事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42](《古史讨论的读后感》,P70)无独有偶,几乎与此同时,梁启超1926—1927年间则提出了“史学史”这一概念,并将之作为学术体系进行了讨论,就怎样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发表了具体的、创造性的见解,从而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逐步形成写下了开创性的一页。此后,朱希祖、陆懋德、蒙文通、金毓黻、姚名达、卫聚贤、冯永轩、傅振伦等一些著名学者在大学开设史学史课程,他们编写的讲义(或称“史学概论”),也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中国史学史著作。[注]自20世纪20年代提出建设中国史学史学科问题后,史学史研究就成为历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在整个30年代,并没有出版中国史学史的专门著作,史学史的内容,大都蕴含在史学理论著作中。史学史在这些书中的地位是附属性的,是为论述史学理论服务的。到40年代,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具体论述可参见白至德编著:《白寿彝的史学生涯》,群言出版社2016年版,第149—163页。此类著述,大多以历史编纂学为重心,专注于史官、史家、史籍与体例的讨论;主要任务在于探究历史和史学的定义,以及史学的对象、性质、价值和功能、史学源流、史学思想、史学方法的发展与演变、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史学发展趋势与方向等。
三、意犹未尽:“史学”语义变迁下的几点认知
其一,“史学”词称的古代意涵,是个层累的积淀过程,诚如谢贵安先生言:“在中国史学史领域,实际上形成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学术格局。”[1](P13)“史学”此一概念的演进,即不断注入了主观因素后,结构而成的后世的体系。民国以前的史家很少以专书论述“史学”,多以著史表达其“史学”观念。正如钱钟书所说:“有史书未遽即有史学,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马迁欤。”[43](P418)在钱钟书眼中,司马迁之史学,不在其成系统之理论体系,而在于其在理论和行动上尽力践行“前载之不可尽信,传闻之必须裁择,似史而非之‘轶事’俗说莹沟而外之于史。‘野人’虽为常‘语’,而‘缙绅’未许易‘言’”的准则。本文试图对“史学”这一概念进行某些解构,层层剥离后世叠加上去的文化积层,回复到“史学”概念的原生状态和客观面貌上去。由此过程可知,一方面,“史学”概念的演进是一种主观与客观共进的学术体系,也正是学者们层累的建构,才使史学客体因为主体的介入、阐释和黏合,得以产生体系,形成宝贵的学术和精神财富。另一方面,对建构起来的“史学”意涵进行解构和复原,是学术的另一种运动和发展方式,可以提醒人们事情的本源及前人的主观活动和智慧结晶。
其二,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迫切地需要从古代史学转型为近代史学,这就需要理论模式上的创新。近代“史学”概念的纷歧与“历史”、“历史学”、“史学史”的混淆,应与此背景有关。近代新学背景下造就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史学”概念百家争鸣,乃中国近代史学特征之一。“但最大特征,乃在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史学与哲学不同之受容。‘全盘西化’或‘吸收西学等字眼’,使人误会西方之学问,乃以单一之模式引入中国,此乖离史实甚远。”[44](P495)“史学”术语的近代界说,即是在固有的含义基础之上,受西方史学之影响,完成了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的过程。史学的发展受文化演变的影响,而史学史的研究则深受史学发展的影响。当“史学”在近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后,其在认识论上的层次和特点亦被人广泛认知,新的史学史写作即应运而生,内涵也为之扩大。因此,民国时期的“史学概论”或“史学史”著述主要以理论转型为目的,都会把“史学”概念问题作为史学史研究的一大主题进行探讨。
其三,“史学”概念的近代化,离不开梁启超等晚清学人引入西方学术思潮的贡献。梁启超等曾“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中国”,于是创立强学会,其后梁启超回忆说:“大学校之前身为官书局,官书局之前身为强学会”。裕庚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三日给皇帝上奏汇报出使日本考察日本之高等教育情形时称:“日本功课内,并未尝废汉学,其历史诸书,学中文者,可观古史学,西文者,亦可观西史。”[45](P640)孙家鼐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奏京师大学堂筹办情形时称:“史学诸书,前人编辑颇多善本,可以择用,无庸急于编纂。”[45](P667)许景澄在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给皇帝上奏称:“创设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与诸生讲贯,无庸另立学堂造就”[45](P648),虽当时各方对“史学”在大学堂之存废以及“史学”课本是否借鉴自海外,还有一定争议,但西学已对中国“史学”造成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作为新学养成之基地的京师大学堂,当时各国皆以各种原因,欲推广本国学术,期望京师大学堂延聘本国师资,如意大利驻中国大使照会总理衙门说:“义文之书,多系紧要,如性理、国政、国史、国法各等学问,义书极多,电气天文法均系义国人所觅定。再欧美专门学十种,教习又应请义人教授,以便新立学堂,十分全成”[45](P679);德国使臣照会总理衙门说:“本大臣关心中国,且照顾本国利益系份内应办之事,惟有照请贵王大臣设法在京师大学堂须用德文教习三人,均系德国人,以推广德国语言文字”[45](P680)。可见,外国教习在京师大学堂的教师比例中还是占了比较高的程度。
翻阅相关档案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在本国史学教习之外,外籍教习也成了当时所延揽人才的范围,但是在近代教育体制之下,以什么形式推行史学教育、以什么人士来担当史学教习,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史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史学学术概念在近代实际运作之大事的行为。在广方言馆筹划期间,相关人士关于史学教习和史学课程曾经提议:“馆中延订近郡品学兼优绅士一人为总教习,举贡生员四人为分教习,分经学、史学、算学、词章为四类,而以讲明性理敦行立品为之纲,就肄业生四十名中,度其年岁之大小,记诵之多少,性情之高明沉潜,均匀派拨四人,分课学习。西语西文之暇,仍以正学为本。”[46](P216—217)“习史。经经纬史,为学之序。列史二十四部,卷帙既繁,未易毕读。而编年之书,莫善于《通鉴》,世人多习纲目。而顾炎武独谓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诸生有志读史,务宜心精力果……所望诸生事事体认,取法于古,以增长其识力,无徒侈言淹博,斯为要矣。”[46](P221—222)可见,作为与经学、算学等相并列的传统史学以及阅读《通鉴》等传统史学训练方法,成为与“西语西文”相对应的一门具有应对外来学术冲击意义的标志性学科。但是,西方学术以其凌厉的攻势通过外籍教师、西方学术著作的中译本,逐渐侵吞着中华传统学术的版图。在这个过程中,史学领域也未能幸免。事后有人回忆:“翻译的书籍,简单言之,计有国际公法,经济学,化学,自然,自然地理,历史,法文英文的法典,解剖学,生理学,药物学,外交指南等方面的著作,内中多数是同文馆的印刷所印行,免费分发全国官吏的。这些书籍就象一支杠杆,有了这样一个支点,总可以掀起一些东西。”[46](P184)大致而言,在当时,日本籍教习或有留日背景之教习所占的比例相对较高。其中“历史教习”或“史学教习”中,有坡本健一(引者注,疑当为“坂本健一”)、冯巽占、李稷勋、陈黻宸、汪镐基几人,其中汪是日本留学生。可以想见,近代史学教育中日学术界之习惯表达方式,很有可能通过这批日本籍教师或留日学生在华的史学教学行为得以对中国学术界产生日益显著之影响。
概而言之,清末民国时期,大量新名词、新术语、新概念因译介的需要而层出不穷,就书写形式而言,一部分古已有之,如“史学”、“科学”、“文化”等,它们在文化互动中获得了新义。也许因为其新不在于形而在于义,人们不免只知形而漠视了其义的翻新及学术影响。因此,对近代汉字术语生成的研究,有待于我们深入挖掘。本文由“史”到“历史”、“史学”、“历史学”、“史学史”此一段语义演化过程的探讨,使我们看到了一部丰富多彩的“文化史”,窥见了一幅时代变迁下古今词义间遗传与变异的“精美画卷”。其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期待着我们富有创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