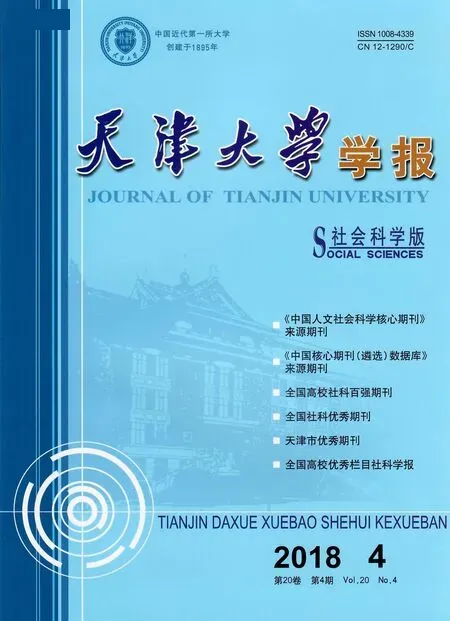论生存的信号博弈基础
,
(天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天津300072)
一、 进化是什么?
达尔文的进化论深深影响着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对生命体和人类起源的基本认识。现存的生物和人类是从遥远的过去,由一种古老的、低级的生命体演化来的,它们为什么能演化成我们现在的样子,达尔文认为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当把这种观点推演到人的起源问题上,达尔文说:“在世界的每一大区域里,现今存在的各种哺乳动物和同区域之内已灭绝了的一些物种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有可能的是,在非洲从前还存在过几种和今天的大猩猩与黑猩猩有着近密关系而早已灭绝了的类人猿;而这两种猩猩现在既然是人类最为近密的亲族,则比起别的大洲来,非洲似乎更有可能是我们早期祖先的原居地[1]”。早期的人类学家极不喜欢达尔文的这一观点,但后来的发展使人类学家不得不将达尔文“人类诞生地是非洲”的观点,作为自己研究的一个逻辑推演起点。
从简单到复杂和现存的相似性成为推演生命体起源的基本思维原则,这一原则既推动了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巨大发展,也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取舍后,将人们的研究引入歧途的危险。以这一原则推演和研究人类起源获得成功的人类学家很多,但就其影响应首推肯尼亚考古和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时,就向自己的导师提出到东非大裂谷寻找人类起源化石的计划,遭到导师的反对。他坚信达尔文的推演,毅然回到东非进行研究,后来的研究证明他和达尔文的推演是合理的,但这一推演逻辑将生物和人类的起源研究过度推向了器官演变的研究方向。对人体器官化石的研究,勾勒出了人类起源的年代序列,这个序列迄今还那么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生命演化的研究思维。当考古学家发现一个极其残破的化石碎片后,会沿着达尔文的推演思维去解释这个碎片,形成一个符合逻辑的演化序列,这个序列会被后续化石碎片所修正。1932年耶鲁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爱德华·刘易斯在印度发现了一片上颌骨碎片,这块碎片后来被宣布为腊玛古猿化石。耶鲁大学的埃尔温·西蒙斯和剑桥大学的戴维·皮尔比姆合作对这块碎片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最初的人出现于距今至少1 500万年前,也可能是3 000万年前,这一结论基于达尔文的推演,被许多人类学家所接受[2]。这一结论很快被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生物化学家阿伦·威尔逊和文森特·萨里奇,运用人和非洲猿的血液蛋白质结构设计的一种分子钟所修正,推算出人类物种出现在500万年前,后被修正为700万年前。
所有被发现的化石碎片都会被排列在这个时间决定的序列里,围绕这些极为稀缺的化石碎片形成了解释人类起源的理论和一系列技术手段。生命体和人类一样,当它们的生命完结后,在时间的长河里,只能留给我们,它们曾经存在过的这样残缺证据,并用这样的证据和现存的生命体和人类进行比对,来推演它们曾经有过的生活历程,这种推演建立的理论其可靠性不断被质疑,为此,人们开发出新的技术手段,不断提高其理论的可靠性。特别是通过基因变异测定来辅助说明人类演化的序列,极大地提高了理论的说服力。
化石残片和基因变异能否有效解释生命体和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历史?是否还有更有效的方法来解释生命的起源和演化?西方学者正在寻找一种新的途径。
二、 草鞋蚧与信号传输
生命演化的结果本来就不是残破的器官遗物,而是鲜活的器官整体和这一整体实现的功能。生命体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它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结构化系统,它随它所处的环境改变着自己,以适合环境而一代代生存下去。生命体器官的变化,其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实现生存下去的功能,所以,生命体器官和结构的演化不是生命的归宿,生命的归宿是建立在生命体基础上的信号传输系统。任何生命体没有一个高效、经济的信号传输系统,都会被大自然所抛弃。达尔文建立的进化论,应该更多地将进化的研究放在生命的信号传输系统上。
生命体延续和它演化的信号传输系统的紧密关系,可以通过一种特殊昆虫的信号传输系统来说明。我习惯于每天早晨从住的小区散步到校园里,其间要走过一段两边栽种着小叶白蜡树的林荫路,路脊和白蜡树之间埋着一排由铁管做成的路灯柱子。大约是2013年3月的一天,我发现在几个灯柱下面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小虫子,拼命的往柱子顶端爬,它们是那么的执着,爬着、爬着从柱子上掉了下来,而后重新出发,踏着同伴的躯体继续往上爬,爬的较高的已被阳光晒烫的柱子烘干,但也阻止不了后来者的脚步,一连三天,我都仔细观察这一奇观。可惜好景不长,三天后,清洁工将这些虫子全部清理干净了,这样的奇观可能是由于清洁工的偶然患病,才让我们看到,后来清洁工每天按时清扫,这样的奇观也就不再重现了。几年了,每到三四月份,我都去那些灯柱下看,有一些,但再也没看到那么大的规模了。
但这些虫子的命运始终没有离开我的思维,我想它们被清洁工清理走的命运也可能是死亡。那时我们课题组正在翻译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学者斯吉尔姆斯的《信号博弈学》,受这本书的启发,感觉这些虫子的生存信号系统出了问题。于是我采集了虫子样本,去咨询了南开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她看后说这种虫子叫草鞋蚧,并介绍了它们的一些生活习性。
既然有了名字,我就可以检索资料,分析它们,寻找它们走向灯柱夭折的原因。草鞋蚧是一种古老的昆虫,它们可能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繁衍了上亿年,以很短的生命周期,叙述着它们的生命奇迹。它们一年发生一代,生命周期很短,也就4到5个月,一年的大多时间都以虫卵的形式,蛰伏在一种白蜡丝构成的卵囊中越夏和越冬。在我国的华北地区,每年的1月下旬至2月上旬,在土壤中开始孵化,根据地面温度情况离开土壤,地面温度高,很快离开土壤,地面温度低,会在土壤中多呆一段时间,白天温度最高为3 ℃时开始出蛰。若虫出土后,会立即寻找树的根茎部分,沿树的茎杆爬至梢部,吸食芽腋、叶腋和新叶的汁液为生,吸食到3月下旬,开始第一次蜕皮。蜕皮前,虫体上白色蜡粉较多,体为暗红色,蜕皮后,虫体增大,活动能力增强,开始分泌蜡质物。4月中下旬开始第二次蜕皮,第二次蜕皮后,雄若虫不再吸食,潜伏于树缝、土缝、树皮下和杂草中,分泌大量蜡丝,缠绕化蛹,10天后羽化为成虫。雄成虫体长4毫米左右,紫红色,有趋光性,寿命3天左右,白天活动量很小,傍晚活动量大增,靠飞爬,寻找雌虫交尾,交尾后很快死去。4月下旬雌若虫第三次蜕皮,变为雌成虫,与羽化的雄成虫交尾,5月中旬为交尾盛期,交尾后,雌虫继续吸食到6月中下旬,开始下树,进入土壤产卵,产卵时,先分泌白色蜡质物附着尾端,形成卵囊外围,开始产卵,产20~30粒后,分泌蜡质成绵絮状覆盖,在棉絮上再产卵20~30粒,继续用蜡质棉絮覆盖,重复这样的过程,到5~8层,雌虫产卵量与取食时间和土壤湿度有关,取食时间长、土壤湿度大,产卵量就大,一般一只成虫产卵100~180枚,多的可接近300枚,产卵期4~6天,产卵结束后,雌虫逐渐干瘪死亡。卵囊初期为白色,逐渐转为淡黄,最后转为土色,卵囊内绵絮状物也由疏松到消失。
草鞋蚧作为一种生命体,除了它的形体进化以外,影响它生存和繁衍更重要的是与它形体一起进化的信号传输系统。任何生命体如果它进化的信号传输系统不能适应它的生存环境,它很快会被生命的长河所淘汰。生命体的信号传输系统是生命体长期与生存环境博弈的最优经济均衡系统。信号传输系统建构得越复杂,其功能会越强大,生存的几率会大幅提高,但强大的信号传输系统会产生巨大的能耗。能量代谢是一切生命体存在的前提,能耗是生命体一切功能存在的基础,某一功能强大,必然要削弱别的功能发挥,在一个能耗均衡的生命体中,如果要提高机体的某一特殊功能,其自然实现途径不外乎两种:一是削弱其他功能,把节省下的能量供应给需要扩充的功能;二是获取更多能量建构更复杂系统,提高其功能。在大自然的演化过程中,这两条途径都受到严苛的自然条件制约,都很难实现,只能是微小的调节。
草鞋蚧的生命体存在的能量基础是小叶白蜡等树木的嫩芽,它的生命信号传输系统需要感知到小叶白蜡等树的嫩芽生长位置和日期来建构,它一生的生存信号系统,从它被孕育过程中就开始了,它的父母亲会将长期进化的蕴含在基因中的,一个经过漫长生存博弈,达到稳定均衡,经济高效,能够感知嫩芽生长的信号系统留在它的机体中,并根据对土壤环境的感知,预测来年的嫩芽生长状况,决定产出它们的数量,根据卵囊的变化,控制它们对温度的把控,以保障它们安全度过一个漫长的越夏和越冬时间,在这个时段里,当温度达到它们孵化的温度时,信号系统要保障它们不被孵化,顺利来到下一个嫩芽生长期。秋冬交汇之际,温度肯定有一个和冬春交汇相近的温度区段,但虫卵不被孵化,其信号传输秘密应该在卵囊的结构中或基因决定的信号系统中,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猜想在卵囊结构的概率比较大,因为这样更适合低能耗原则,下面在假设这一猜想可靠的条件下,继续分析草鞋蚧的信号传输系统。春天到了,当大地温度回升到3℃时,卵囊的变化已适合卵孵化,若虫孵化出后,根据对温度的感知,决定是否离开土壤,离开土壤后,在它基因系统带的信号系统里,只能给它判断高低的能力,没有识别其它的能力,比如它向上爬的是不是树的茎杆,如果加这项信号识别功能,它的父母会消耗更多的能量,建构更复杂的蕴含在基因系统中的信号系统。在远古时期,除了大地和草木不会有别的东西,所以,它们与环境博弈进化的最优经济信号系统,只要能识别高低就足够它们使用了,一旦进化到这一步,就达到了博弈的稳定均衡态,其信号传输系统基本保持进化不变,若虫基因携带的信号系统,会激励它勇往直前向高处挺进,直到碰到它需要的嫩芽。
进入现代社会,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革命性改造,使草鞋蚧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它生活在树茎、灯柱、墙体等交互存在的复杂环境中,它的信号传输系统缺乏对灯柱、墙体、树茎的识别,凡是误把灯柱、墙体当树茎的幼体几乎都会夭折,也可能经过进一步的进化,草鞋蚧会进化出识别树茎的信号传输系统,或由于进化不出这样的系统而出现种群萎缩和灭绝。
从草鞋蚧的信号传输系统分析可延伸到自然界的所有生命体,简单的有病毒和细菌,复杂的到动物和人类,只要在自然中生存,就无法离开各自独特的信号传输系统。正像一种黄色粘球菌,它在漫长的演化历史中,进化出一种特殊的密度感知信号传输系统;还有德国生物学家卡尔·冯·弗里施发现的众所周知的蜜蜂群的“摇摆舞”信号传输系统;美国生物学家切尼和塞法斯在非洲发现的长尾黑颚猴的报警信号传输系统[3];我们还可以通过现代丰富的动物生存视频,观察非洲角马、北美驯鹿和大熊猫等动物的生存信号传输系统,有关它们的生存信号传输系统的理论分析,由于其比较复杂,在这里不作具体叙述。
三、 信号与信号传输
生存信号传输系统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的生命体及它们的种群中,我们能否推断进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信号传输系统,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达尔文在他的研究中无法避免的遇到信号传输问题,他面对这些问题所选的处理方法很值得我们沉思和研究。他处理的方法原则是比较动物的信号传输系统和人的信号传输系统,处理的方法是动物在什么程度上具有人的信号传输系统的功能。为此,他设定人类和低等动物都有心理能力,这样就可以把对人的心智、意识、道德等研究,移植到动物信号传输系统,分析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这些方面的功能或能力[1]97-227。为了更好的说明他的处理方法的科学合理性,达尔文设定动物的信号系统是自然发生的,通过自然适应获得其表达意义,通过演化逐渐被改进。这样的设定可以被动物的报警信号系统和该系统存在的利他主义特点所说明。
达尔文的处理方法是否存在一个与他的进化论不匹配的方法设计,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进化论基本推演是简单的在前,复杂的在后。按照这样的推演逻辑,动物的信号传输系统更为基本,在研究动物信号传输系统时,是否应该避开人类信号传输系统研究的干扰,是否应该剔除人的价值取向,更客观的分析动物的不同生存信号传输系统,使我们更能看到生存信号传输系统的本相。
如果将生存信号传输系统设定为更为根本的生命进化意义,那么是否可推定器官和器官构成的生命体只是实现这种意义的物质基础和实现手段,无论是人,还是其他生命体,其生存意义,是在不断完善自己的信号传输系统,提高自己和其种群的自然延续能力。如果把信号传输系统设定为生命体更高的进化目的,那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视角去审视信号和信号传输?怎样理解生存的信号系统的起源。
如果作这样的推演,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信号是什么?信号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是作为语言的延伸来考虑的,语言是传输意义的系统,关于这个系统是怎么发生的,西方有非常悠久的研究传统,研究的结果可归纳为两种观点:自然发生的和约定形成的,当把这两种观点放进信号传输的分析上,自然发生的观点更具优势。但这种对信号的理解,只能解决信号作为一种表达意义的系统问题,好像没能很好说明信号是什么?英国演化博弈论学者史密斯认为:“信号是一系列表演和结构,它可以改变生物的行为,是为改变的有效性演化来的,是为接收者对其反应的高效性演化来的。”[4]这一定义其实还是沿用了西方的传统,隐含一个设定:具有发送目的的信号发送者,如果把这个发送者的目的剔除,信号又是什么?
信号从本质上讲,是两点之间的能量传递,一个可看作产生信号的A点,一个是接收信号的B点,信号是这两点之间的流动能量,它的根本属性特征在流动,所以,信号是两点之间流动的能量。自然中的信号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流动的能量形式将A点的信息传到B点,信号之所以对生命体和人类意义重大,主要表现在:信号携带信息。由信号引出信息,信息又是什么?信号携带信息,那么信息依托于信号而存在,如果信号是流动的能量,信息是不是能量和物质?关于这一问题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曾说过:“信息不是物质”,那它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哲学问题,也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和我们对信息概念应用的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信息的概念内涵会随历史和学科发展而变化。但它作为一个概念,其意义大概指向客观事物的一种属性,物的属性可以看作物所表现的意义,信息更多指向意义,意义离不开物,但它不是物本身,物只是意义的源,意义必须有意义的受体,没有受体来承接意义,意义也就不是意义了,所以,理解信息,要把信息看作一种结构性的信号传递系统的存在。它离不开物,但它不是物;它离不开接收它的具有思维能力的受体,但它也不是受体本身。信息的意义在于物和受体的互动,互动的媒体是流动的能量,所以,要真正理解信息概念的内涵,必须依靠信号传输模式来理解和说明。
这里我们是不是有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概念,信号是携带信息的流动的能量,信息是被信号携带的意义,所以,信号是能量,信息不是物质和能量,而是意义。
当人们将这样的信号和信息概念带入生命体和人类的生存信号传输系统后,人们会对生存信号传输系统有什么样的新理解和新思考。
四、 信号传输博弈系统
英国演化博弈论学者史密斯和美国信号博弈论学者斯基尔姆斯采用博弈方法来构建生存信号传输系统,他们将自然发生的机制和约定形成的机制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更有解释张力的理论框架。史密斯在其1982年出版的《演化与博弈论》一书,使用博弈论方法建构模型解释生命个体和种群的特定特征,他认为,鸟的羽毛的构造特征是与自然环境博弈的结果,博弈者根据自利的原则所表现的理性行为,在种群博弈中表现为种群的动态性和稳定性,个体和种群在与环境和种群其他个体的博弈演化的结果是出现一个演化稳定性策略,即“如果整个种群的每一个成员都采取一个共同的策略,那么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不存在一个具有突变特征的策略,能够侵犯这个策略”[5]。 史密斯所强调的演化稳定性策略,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化事实,自然选择的实现依靠博弈,博弈的结果产生一个均衡的稳定的策略系统。这种推演的重要性不在策略,而在对于生命体及其种群存在一个均衡稳定的系统,这个系统支撑着生命的延续。史密斯早期的研究并没有追问这个系统的具体表现形式,他的后期研究发现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开始把自己研究的关注点,放在了动物的信号传输系统上,他去世前完成了他在这方面研究的书稿《动物信号》。
斯基尔姆斯的研究更有说服力地推动了信号传输系统的研究。他的研究基于美国哲学家刘易斯的语言信号传输模式,即语言是以:状态—传播者—语言—听众—状态[6]的模式来传输的,他把这种模式推广到所有生命体和其种群的生存信号传输系统方面。他认为任何生命体及其它的种群,会通过博弈的方式演化出一套趋于博弈均衡和稳定的信号传输系统。他这样描述他的信号博弈模式:有两个博弈对局者,一个发送者和一个接收者,自然随机选择一个状态,让发送者观察,根据发送者观察的结果,让发送者发送一个信号给接收者,接收者不能直接观察状态,只能观察信号,通过信号,接收者做出一个行动回应发送者观察的状态。两个状态一致,发送者和接收者回报为1,否则回报为0[7],斯基尔姆斯的模式可表达为:状态—发送者—信号—接收者—状态。他认为,这样的一个传输过程,在生命体及其它的种群中普遍存在,通过不断博弈回报的自然选择过程,逐渐演化为一个合理的、经济的、高效的、均衡的、稳定的信号传输系统。
五、 信号传输博弈模式的理论解释张力
按照斯基尔姆斯的研究进路,当我们把信号传输博弈模式作为进化的目的和意义时,我们对生命的本质、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都会有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当我们用信号看生命的存在时,生命体的器官和器官组合的整体服务于生命延续的目的会变得那么清晰、明了,它们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形成了各自巧妙识别意义和传输意义的系统方式,并依靠这种方式延续着自己及种群的生存意志。
同时,这一模式将我们引进了一个更为奇妙,充满神奇的研究新领域。流动的能量标志着流动的意义,识别流动的意义是生命体最伟大的能力所在。“处于所有生物核心的不是火,不是气,也不是所谓的生命火花,而是信息……。如果你想了解生命,就别去研究那些生机勃勃、动来动去的原生质了,从信息技术角度想想吧”[8]。 信息是信号携带的意义,所以,信号携带给生命体的是”自然状态、是行动的指令、是可发送和接收的策略信息”[9]。信号是流动的能量,流动意味很快消失,它否定均衡和稳定,要在流动中建立均衡和稳定,生命体需要记住在流动信号中识别的意义,意义的保存和使用,是生命体进化出以脑为核心的存储系统。这就引出了从信号到意义存储,再到意义调出复杂的生命意义传输工程研究,也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迄今还无法知道的,生命的信号意义为什么是这样?
当我们关注人的信号传输博弈模式时,对识别的流动意义,除了保存在我们的脑系统之内外,人的生命奇迹就在于将意义保存到了脑外,如语言、符号、文字、数据等,当我们解读这些意义时,人的本质以及人的社会本质都会被推演出来,但这种推演还有漫长的研究历程。
综上所述,以一个新的信号视角解读了生命演化的意义,通过选择草鞋蚧的信号传输系统为案例,重点分析了生命信号传输系统的博弈形成机理,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信号、信号携带信息、信号的意义等哲学问题,对国内有关信号传输系统中的哲学问题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1] 达尔文.人的由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42.
[2] 理查德·利基. 人类的起源[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3-4.
[3] 布兰恩·斯基尔姆斯. 信号博弈学[M]. 北京:人民出版,2014:28-47.
[4] John Maynard Smith,David Harper.AnimalSignal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3.
[5] 约翰·梅纳德·史密斯. 演化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0.
[6] David Lewis .Convention:APhilosophicalStudy[M].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2002:130-131.
[7] Brian Skyrms.SignalsEvolution,Learning,andInformation[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7.
[8] 詹姆斯·格雷克. 信息简史[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7.
[9] Brian Skyrms. The fow of information in signaling games [J].PhilosophyStudies, 2010(147):155-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