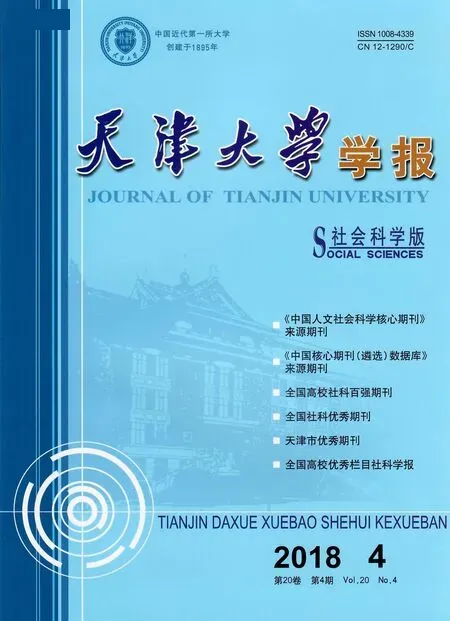莫言的《故乡人事》与孙犁作品比较分析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天津300191)
细读莫言小说新作《故乡人事》[1],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孙犁的作品,尽管这种联想有些特别,因为两位作家无论所处的时代,还是创作风格都有着显著的差异。但如果细细品读莫言的新作,可以发现停笔五年之久的莫言,一反往日的浓烈与绚烂,文字不但干净凝练,而且平淡之中蕴涵着一种宁静、圆润与深邃的智慧,并略带一丝深秋将至的空灵与忧伤交融的回甘。莫言在《故乡人事》中出现的这种变化,显然与孙犁作品的乡土抒情趣味发生了契合,这也是对比分析二者的原因所在。
一、 从《民间音乐》开始
孙犁很早关注到莫言的创作,他在《读小说札记》中对莫言早期作品《民间音乐》进行了批评:“去年的一期《莲池》,登了莫言作的一篇小说,题为《民间音乐》。我读了以后,觉得写得不错。他写一个小瞎子,好乐器,天黑到达一个小镇,为一女店主收留。女店主想利用他的音乐天才,作为店堂一种生财之道。小瞎子不愿意,很悲哀,一个人又向远方走去了。事情虽不甚典型,但也反映当前农村集镇的一些生活风貌,以及从事商业的人们的一些心理变化。小说的写法,有些欧化,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主题有些艺术至上的味道,小说的气氛,还是不同一般的,小瞎子的形象,有些飘飘欲仙的空灵之感”[2]。孙犁不仅表达了对莫言的欣赏,准确概括了这篇小说的特征,而且从小说内容——“农村集镇的一些生活风貌”“人们的一些心理变化”、小说写法——“有些欧化,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和小说艺术性特征——“小说的气氛不同一般”“空灵之感”等方面预言了莫言“高密东北乡”的诞生。这是一位世事洞明、卓有成就的文学老人与正在攀越文学创作巅峰的文学大家之间的文字交往与沟通,透过文字的“气氛”与“灵韵”,孙犁不仅“发现”了莫言,而且对莫言也构成了影响。莫言敬重孙犁的人格,高度评价孙犁,“他既是个大儒,又是一位‘大隐’(隐士)”,感激孙犁提携与鼓励的同时,表示“要以孙犁的人文精神为前导”[3]。他们在精神的世界里相惜相敬,因而在《故乡人事》中发现孙犁的影子就不足为奇了。
《故乡人事》首先创造了一种真实感与纪实感,这种真实感与纪实感来自于作家主体及其文体书写,是莫言自觉追求的结果。同在这篇《读小说札记》中,孙犁谈到汪曾祺小说《故里三陈》:“它好像是纪事,其实是小说。情节虽简单,结尾之处,作者常有惊人之笔,使人清醒。有人以为小说,贵在情节复杂或性格复杂,实在是误人子弟。情节不在复杂,而在真实。真情节能动人,假情节使人厌”[2]。孙犁对汪曾祺小说的赞同与认可,有着夫子自道的意味,因为他自称其晚年所作小说,“多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平铺直叙,从无意编故事,造情节”,但其已经越过小说的界限而走到纪事性散文一端,“强加小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2]。莫言的《故乡人事》有着汪曾祺小说的灵动与精致,更具孙犁晚年小说的朴拙与大气,它在血脉与精神上与孙犁小说实现了双向沟通与对话。借助前贤的文学滋养,莫言也在桑梓人物书写中寻找创作的突破口,其小说在现实与人事的历史互动与关照中获得了躯体与灵魂,以及深入心灵的力量。
“梦中每迷还乡路,欲知晚途念桑梓”[4]。孙犁对《乡里旧闻》的题词可以作为了解和进入《故乡人事》的一个通道。通过与孙犁相关作品的比较阅读,从《故乡人事》中不仅可以探索这一文本的深层含义,而且也能发现莫言文学发展与影响的痕迹与脉络。
二、 地主与长工
《故乡人事》包括《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三个短篇小说。《地主的眼神》叙写了一个名叫孙敬贤的老地主,曾经因为“我”小学三年级一篇题为《地主的眼神》的作文遭受批斗,子女也受到牵连而失学。《地主的眼神》使“我”成为村里的名人,但也受到父亲的警告,他告诫我“再也不许写这样的文章”。在生产队时期的一次割麦中,“我”回头看跟在身后的孙敬贤,“他总是显出无限痛苦的样子,呻吟着,但他的那两只黄色的眼珠子里同时也会射出阴沉沉的光芒”。他的眼神,“泄露了他内心的秘密”,不仅佐证了“我”的那篇作文对老地主形象的刻画,而且坚定了“我”的印象,“我至今也认为孙敬贤不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不紧不慢地跟在我的身后,显然想让“我”出丑,因为“我”留下的麦茬太高,割下的麦捆子太乱,落下的麦穗太多。而他割下的麦捆,“麦穗整齐,麦茬儿紧贴地面。地下几乎没有落下的麦穗”。“我”对地主眼神的描写,得到孙敬贤大儿媳于红霞的赞同:“你写得太好了。孙敬贤这个恶霸地主,眼珠子闪着绿光,那根本不是人的眼睛,而是狼的眼睛!你知道他为什么把我们撵出来吗?这个老畜生,竟然打我的主意。我的奶水多,孩子吃不完,他竟然让我把奶水挤给他喝,说能治好他的胃病。”直至孙敬贤死,小说写道:“我知道很多地主不是坏人,但我也知道,这个孙敬贤的确不是一个好人。这其实跟他的地主身份没有关系。”这是对孙敬贤盖棺定论之笔,在小说中显得很突兀,也让人警醒。与此同时,“我”一直对孙敬贤怀有内疚之感。而孙敬贤所以被划为地主,确有几分冤,孙双亮曾拦住“我”为其父鸣不平:“你写作文糟蹋我爹,真是丧了良心。我爹说,我们家那半顷地,是偏远荒地,三亩也顶不上你们家一亩值钱。但我们家划成地主,你们家划成中农。我爹劳动改造,你爹当上会计。我们是地主子女,连学都不让上,你们可以上学,还写作文糟蹋我们”。用“父亲”的话说,孙敬贤“吃亏就吃在的他争强好胜上”,他不求质量只求数量的购买田地,一方面表现出他对土地的爱,另一方面也成为他被批斗的根源。于是童年视角与成年视角的重合之中,又展现出地主孙敬贤的另一面,即他还是一个争强好胜、打肿脸充胖子孙敬贤。而这一视角,又对前者视角中的孙敬贤构成了一种解构与消解。因而,无论阶级视野中的孙敬贤,还是道德伦理视域中的孙敬贤,都无法涵盖孙敬贤的全部。小说结尾,孙双库为父亲孙敬贤举办的充满示威色彩的隆重葬礼,在孙子孙来雨的眼中成为类似戏说历史闹剧的同时,不仅丰富了孙敬贤的形象与意义,也使得地主孙敬贤进入了历史。
《地主的眼神》情节并不复杂,但孙敬贤的形象却很生动,他割麦时表现出的高超技艺,他的道德瑕疵,及其好面子的性格特征,与孙犁《乡里旧闻》中的“凤池叔”很相像,“凤池叔”是一个身材高大、仪表非凡,总是穿着整整齐齐长袍在街上走动,远近闻名的长工。他不只力气大,农活精,赶车尤其拿手,“他赶几套的骡马,总是有条不紊,他从来也不像那些粗劣的驭手,随便鸣鞭、吆喝,以致虐待折磨牲畜。他总是若无其事地把鞭子抱在袖筒里,慢条斯理地抽着烟,不动声色,就完成了驾驭的任务。这一点,是很得地主们的赏识的”[4]257。就这样一个很得地主赏识的长工,在哪一家也呆不长久,原因在于他“太傲慢”,他不仅从不低声下气,而且还挑活儿,“车马不讲究他不干,哪一个牲口不出色,不依他换掉,他也不干”。另外,他活虽然干的出色,但也只在大秋大麦之时,“其余时间,他好参与赌博、交接妇女”。因此,他经常失业家居。但是,即便饿肚子,“他从来也不向别人乞求一口,并绝对不露出挨饥受俄的样子,也从不偷盗,穿著也从不减退”[4]258。死前,凤池叔把自己的三间北房卖掉了,“为自己出了一个体面的、虽属于光棍但谁都乐于帮忙的殡,了此一生”。地主孙敬贤与长工凤池叔虽然属于不同阶级,作者描写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的面目与精神上都存在着许多相似的地方,都属于泥土性极强的故乡人物。莫言在创造和描写地主孙敬贤时,在无意识的层面接通了孙犁曾经涉足的传统故乡人物的历史。
三、 斗士与混混儿
《斗士》中的武功,也属于泥土性子极强的人物。这位腔调有些“不男不女”的“远房堂兄”,家庭出身不好,“连个老婆都讨不上,相貌也是招人恶”,是村里地地道道的弱者与底层人物。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弱者与底层人物,却性格暴烈,成为一个无人敢惹的“斗士”。他和村支部书记方明德斗,方明德一九四八年入党,参加过抗美援朝,三等残废军人,“家里有三个儿子,还有十几个虎狼般的近支侄子”,权倾一方,“方明德一跺脚,全村都哆嗦”。方明德在村里当了几十年的支书,是一至死都在“战斗”的斗士。村里敢跟方明德叫板的,唯有武功。他不仅没有被方明德制服,而且和方明德死磕了一辈子,成为方明德最忌惮和害怕的人。他和村里最有力气的王魁打架,虽然在身体与气力上吃了亏,但以坚韧的顽强与不怕死的精神,不仅使得王魁屈服,从此再也不敢惹他,而且他还不依不饶,经常站在自家院子里,对着王魁家后窗指桑骂槐。“后来,王魁将后窗用砖头堵上,六月天也不捅开。改革开放之后,人口流动自由了,王魁索性带着老婆孩子走了。走了之后再也没回来过,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院子里的蒿草长得比房檐还高,那房子,眼见着就要塌了,房子一塌,就成了废墟。你说他多厉害!”被仇恨和屈辱所浸染的武功,充分意识到自己作为“弱者”的权力与优势,他以卑微的身份和低贱的性命为资本与各色人物相缠斗,“谁要得罪了他,这辈子就别想过好日子了”,然而,“你对他打个喷嚏,很可能就把他得罪了”。他曾用农药浸泡过的馒头毒死了方明德大儿子家那头三百多斤重的大肥猪,将黄耗子家那一亩长势喜人的玉米统统拦腰砍断,连续十几年的大年夜里,把村里及附近两个村子里草垛点燃。他还装神弄鬼,把顾明义吓成了神经病。“母亲”认为武功这样胡作,总有一天会作死的。但事实证明,武功非但没有作死,而且还被批准为“五保户”,即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所以,小说结尾叙述道:“他的仇人们,死的死,走的走,病的病,似乎他是一个笑到最后的胜利者,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小说的这一判断,既显示了武功可怜的一面,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弱者,同时也表达了他可憎的一面,他的暴戾与怪诞,已成为村里的一害。
武功类似于孙犁笔下乡里混混儿一类的人物。孙犁在《光棍》这篇小说中指出:“幼年时,就听说大城市多产青皮、混混儿,斗狠不怕死,在茫茫人海中成为谋取生活的一种道路……其实就在乡下,也有这种人物的。十里之乡,必有仁义,也必有歹徒。乡下的混混儿,名叫光棍。一般的,这类人幼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寒,但长大了,有些聪明,不甘心受苦。”[4]270《光棍》中孙犁的远房堂兄、老索与姓曹的,就属于这样的人物,他们都出身于乡村底层,又不甘于命运的安排,于是走向他途而成为混混儿。孙犁叙述了老索与姓曹的之间的光棍对决:“有一天,老索喝醉了,拿了一把捅猪的长刀,找到姓曹的门上。声言:‘你不还帐,我就捅了你。’姓曹的听说,立时把上衣一脱,拍着肚脐说:‘来,照这个地方。’老索往后退了一步,说:‘要不然,你就捅了我。’姓曹的二话不说,夺过他的刀来就要下手。老索转身往自己村子里跑,姓曹的一直追到他家门口。乡亲拦住,才算完事。从这一次,老索的光棍,就算是‘栽了’”[4]27。1相对于老索的胆怯与犹豫,武功表现得更为“光棍”,面对逼近咽喉的铁锹闪光的锋刃,武功反倒平静了,“他竟然笑嘻嘻地说:‘铲吧,你今天必须铲死我,你今天要是不铲死我,杂种,你们家就要倒霉了。你力大无穷,我打不过你,但是,杂种,你女儿今年三岁,她打不过我;你儿子今年两岁,更打不过我;你老婆肚子里怀着孩子,也打不过我。你除非天天守在门口,要不,你就等着给你老婆孩子收尸吧!’”而肌肉发达的王魁,“将手中的铁锹,猛地铲在地上,然后蹲在地上,捂着脸哭起来”,他像个女人一样败给了“怂包”武功。武功以命相搏的光棍行为,不仅从精神上彻底打败了村里最有力气的王魁,而且树立了“斗士”形象。在《老焕叔》附记中,孙犁借用古语解读这一类人物:“古人云:不耕之民,易于为非,难于为善。”[5]此言也适用于武功,同时也适用于方明德。尽管他们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斗士,但无疑都属于孙犁所谓的乡里“混混儿”,或此种“混混儿”的畸形后代。
四、 铁匠与童年记忆
《左镰》是一篇从铁匠开始谈起的抒情色彩浓郁的小说,小说虽然简短,莫言却特意在“小引”中解释了写铁匠的缘由,“各位读者,真有点不好意思,我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里,都写过铁匠炉和铁匠的故事。在这歇笔多年后写的第一篇小说里,我不由自主地又写了铁匠。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写铁匠?第一个原因是我童年时在修建桥梁的工地上,给铁匠拉过风箱,虽然我没有学会打铁,但老铁匠亲口说过要收我为徒,他当着很多人的面,甚至当着前来视察的一个大官的面说我是他的徒弟。第二个原因,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曾跟着维修组的张师傅打过铁,这次是真的抡了大锤的……一个人,特别想成为一个什么,但始终没成为一个什么,那么这个什么也就成了他一辈子都魂绕梦牵的什么。这就是我见到铁匠就感到亲切,听到铿铿锵锵的打铁声就特别激动的原因。这就是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想写打铁和铁匠的原因”。这个解释,不仅增加小说的纪实性,而且通过对铁匠的回叙与描写中引出围绕“左镰”关于少年成长的故事。
莫言对铁匠的偏爱,似乎也可以在孙犁《铁木前传》中寻找到原因。孙犁在《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中明确指出该作品与童年记忆的关系:“这本书,从表面上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它是我有关童年的回忆,也是我当时思想感情的体现”[6]。因此,小说开端就写木匠与铁匠对于乡村童年生活与记忆的重要意义,“在人们的童年里,什么事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如果是在农村里长大的,那时候,农村里的物质生活是穷苦的,文化生活是贫乏的,几年的时间,才能看到一次大戏,一年中间,也许听不到一次到村里来卖艺的锣鼓声音。于是除去村外的田野、坟堆、破窑和柳杆子地,孩子们就没有多少可以留恋的地方了”[7]。所以,谁家院里响起木匠斧凿的叮叮当当声音,会吸引他们成群结队地跑了进去,斧凿的声音与墙角用来熬鳔胶的木柴火堆噼剥噼剥的声音,会对他们产生难以割舍的诱惑,然而能请得起木匠做活的家庭毕竟有限。“但是,希望是永远存在的,欢乐的机会,也总是很多的。如果是春末和夏初的日子,村里的街上,就又会有丁丁当当的声音,和一炉熊熊的火了。这丁丁当当的声音,听来更是雄壮,那一炉火看来更是旺盛,真是多远也听得见,多远也看得见啊!这是傅老刚的铁匠炉,又来村里了。”他们每年来一次,“像在屋梁上结窠的燕子一样,他们总是在一定的时间来”,于是,观看铁匠打铁,成为孩子们最期盼和最为快乐的事情,“如果不是父亲母亲来叫,孩子们是会一直在这里观赏的,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要看出些什么道理来。是看到把一只门吊儿打好吗?是看到把一个套环儿接上吗?童年啊!在默默的注视里,你们想念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境界?”[7]391这段看似与小说故事没有直接联系的描写与抒情,不仅是孙犁童年情结与记忆的再现,而且成为小说艺术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
同样,在高密东北乡的许多村庄里,有一些“像我这样的孩子”,每年夏天在槐花盛开之前或之后的日子里,思念着铁匠老韩的到来并成为他们忠实观众。“每年夏天,槐花开的时候,章丘县的铁匠老韩就会带着他的两个徒弟出现在我们村里。他们在村头那棵大槐树下卸下车子,支起摊子,垒起炉子,叮叮当当地干起来。他们开炉干的第一件活儿,其实不是器物,而是一块生铁。他们将这块生铁烧红,锻打,再烧红,再锻打,翻来覆去的,折叠起来打扁打长,然后再折叠起来,再打扁打长。烧红的铁在他们锤下,仿佛女人手中面,想揉成什么模样,就能揉成什么模样。他们将这块生铁一直锻打成一块钢”。童年的注视也许看不出什么道理来,但是,他们打铁劳作的场景,他们的身影,以及铿铿锵锵打铁的声音,牢牢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以至于许多年过去了,“我还经常梦到村头的大柳树下看打铁的情景”。与这种梦中情景对应的是一柄初见模样的左镰,“老韩用双手攥着长钳先把左镰夹出来,放到铁砧上。然后他又将那块钢加到镰刃上。他拿起那柄不大的像指挥棒一样的锤子,对着流光溢彩的活儿打了第一下。小韩抡起十八磅的大锤,砸在老韩打过的地方,发出沉闷得有点发腻的声响。钢条和镰已经融合在一起。老三扔下风箱,抢过二锤,挟带着呼呼的风声,沉重地砸在那柔软的钢铁上。炉膛里黄色的火光和砧子上白得耀眼的光,照耀着他们的脸,像暗红的铁。三个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铁锤互相追逐着,中间似乎密不通风,有排山倒海之势,有雷霆万钧之力,最柔软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徊的音乐。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这段携风夹雨似的描写,通过梦的折射再现“左镰”锻造过程同时,也呼应了开头对钢的锻打,并以隐喻的形式完成了间杂其中“我”与田奎及喜子、欢子之间少年时代爱恨情仇的呈现与消解,它在“诗”的层面实现了“左镰”与田奎之间的融合与同一。小说看似写少年之间的故事,其实也是写“左镰”的锻造过程,更是写作家关于铁匠的童年记忆与梦想。在童年记忆与梦想这一点上,莫言与孙犁实现了“视界的融合”。
五、 结 语
孙犁与莫言对铁匠打铁场面的童年记忆与描写,在技艺与艺术的层面表现和烘托铁匠锻铁为钢,锻造出各种铁器与农具的创造过程,实际上以铁匠的打铁隐喻了作家的创作,他们通过对铁匠创造与激情描述反观自己的文学创作及其灵感的来源。铁匠与作家自我之间构成了“他者”与自我主体对位性的关系。对于孙犁来说,铁匠既是他表现思想与情感变化并使之成为情节与形象的载体,同时也是昭示他创作力爆发和衰减的具体症候。通过铁匠和木匠,孙犁回忆起他的童年,由此成就了《铁木前传》的开始,铁匠叮当的捶打声和那四溅的铁花是其诗情与灵感奔流的象征。但是,当铁匠傅老刚被老朋友黎老东激怒,提起水桶泼灭铁匠炉灶,和黎老东决裂时,孙犁的创作也因病戛然而止,形成只有“前传”而无“后传”的局面。
莫言无疑比孙犁幸运许多,他以《左镰》作为《故乡人事》的压轴,既表现了莫言“精神还乡”的愿望与创作实践,这种实践与此前他对文学意义上故乡的“定义”“发明”与“想象”多了一些纪实性的色彩与自传性的内涵,同时他以“左镰”的锻造,为自己制作了一件“特别用心打造的利器”,一件“真正的私人订制”的属于莫言个人创作的“左镰”。莫言挥舞这个量身定做“左镰”收割《地主的眼神》和《斗士》,完成《故乡人事》创作的同时,一方面在乡土与童年的主题叙事中与孙犁作品发生了关联与互文,这种关联与互文既是他在文学蹒跚学步时因受到孙犁的关爱与奖掖而心生感激的文学性展示,同时表现了他们在人格与精神上的一种契合现象;另一方面,莫言表达了要斩断某种束缚、魔咒和不断突破自己的决心与愿望,《左镰》结尾,媒婆袁春花问田奎敢不敢娶丧夫后无人敢要的欢子,田奎一个简短和坚定的“敢!”字表明了莫言的胆识与意志。它预示着莫言创作的又一次起航的起点,充满着种种可能。
[1] 莫 言.故乡人事[J].收获,2017(5):8-23.
[2] 孙 犁.读小说札记[N].天津日报,1984-05-18(4).
[3] 从维熙.孙犁的背影[N].北京青年报,2007-07-06(D3).
[4] 孙 犁.孙犁文集: 3[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252.
[5] 孙 犁.孙犁文集: 续编1[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236.
[6] 孙 犁.孙犁文集: 4[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615.
[7] 孙 犁.孙犁文集: 1[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