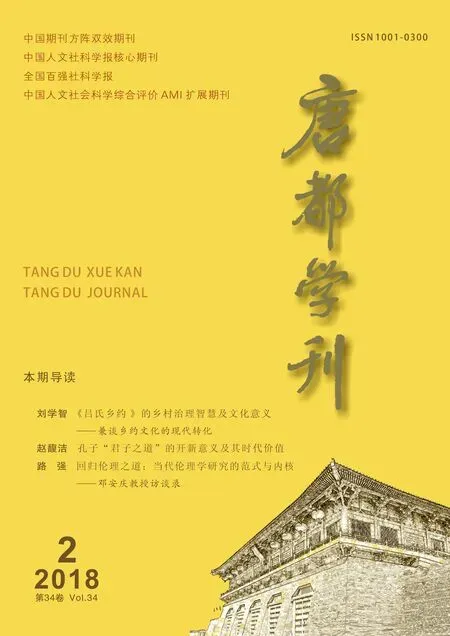《吕氏乡约》的乡村治理智慧及文化意义
——兼谈乡约文化的现代转化
刘学智, 王晓峰
(1.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西安 710119; 2.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 710008)
王晓峰,男,陕西蓝田人,西安市委宣传部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
众所周知,《吕氏乡约》是由张载弟子吕大钧及诸兄弟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制定的。吕氏兄弟基于乡村安定、乡邻和睦而制定了一个以道德教化为主的《吕氏乡约》,它试图通过整合社会秩序来实现乡村自治,彰显乡村道德生活,其旨趣在于去恶扬善、彰显正义、淳化风俗、提升道德,以此感化乡里,移风易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农村乡约。该乡约由吕大钧在蓝田及关中一些地方推行达五年半之久[1],遂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蓝田及关中不仅是《吕氏乡约》的故乡,也是传播和发展乡约的重要之地。《吕氏乡约》在宋明时期影响及于大江南北。南宋朱熹非常关注它,曾对其进行过增损,史称《增损蓝田吕氏乡约》。虽然朱熹考虑到一些困难而尚未实行,但在南宋确有人推行,据魏了翁在《太常博士李君墓志铭》中记载:有个叫李大有(字谦仲)者乃“仿古饮酒礼,且取前贤《吕氏乡约》《乡仪》锓梓以风示之,士习用劝”。而在南宋推行甚力的是阳枋(号字溪),他在四川巴县一带,于淳祐三年(1243)与友人宋寿卿、陈希舜、罗东父等“讲明《吕氏乡约》,书行之于乡,从约之士八十余人”*参见《字溪集》。。明代正德年间山西路州仇氏以《吕氏乡约》为范本制订了《雄山乡约》。明代关学学者吕柟,在谪官至山西解州时,亦以《吕氏乡约》为范本并参考了仇氏《雄山乡约》,在解州制订和推行《解州约》,其实行仅两年,效果显明。其弟子余光又于嘉靖年间在解州制订和推行《河东乡约》。蓝田吕氏的同乡王之士(王秦关),曾发展了《吕氏乡约》,制订了《正俗乡约》。又如明嘉靖年间于广东增城出现由湛若水创立的《沙堤乡约》。明代心学大儒王阳明亦“参酌蓝田乡约,以协和南赣山谷之民”,制定了《南赣乡约》,并在江西南安、赣州一带推行。此外,吕坤有《乡甲约》,明末清初时陆世仪制有《治乡三约》等。甚至一些皇帝也颁行相类的东西,如明太祖的《六谕》等。这样,在历史上就出现过诸多各具特色的乡约,形成了把儒家文化通过民间“制度化”的形式融入乡村社会的乡约文化。这些乡约的共同特点,都具有道德教化、乡村自治和社会调解的意义,其目的是扬善抑恶,提升道德,和睦乡邻,淳化风俗,以期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良好秩序。由于乡约一般都是由乡贤和儒士主导制订和推行的,故其内容往往与儒家的核心价值相合。《吕氏乡约》所以由关学学者开其先,正说明它是张载以来礼教、笃实践履的关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一、《吕氏乡约》的主旨体现了儒家的核心价值
《吕氏乡约》的主旨内容和纲要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十六个字,另外还有关于这四句纲要的解释性细目。从其内容看,乡约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具体体现和阐发了儒家以德性伦理、正义原则、礼教秩序、社会和谐、内省修养为核心的价值观。具体表现在:
首先,《吕氏乡约》以道德教化为主,贯彻了儒家道德理性的精神,把培养乡民的道德意识放在首位。《吕氏乡约》首先提出村民之间应该“德业相劝”。何谓“德”?《吕氏乡约》说:“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仆,能事长上;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规过失,能为人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凡随善为众所推者,皆书于籍,以为善行。”[2]793-795主张村民首先要做到“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认为德的核心是向上、向善、求善,要求每个人都要充分扩充天赋于己的善的本性,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利于社会的人,并强调发现非善的行为就劝勉其改正,并通过将善行恶行皆“书于籍”(记录在册)的形式以彰显其严肃性和权威性。这显然是把儒家的道德价值追求以制度化的形式加以贯彻的具体体现。
《吕氏乡约》指出,有德者的行为体现在多个方面,如能“治身”(严格要求自己)“治家”(和睦家族),能“事父兄”“教子弟”“御僮仆”“事长上”(即能尽人伦);能“睦亲故”“择交游”(能处理好亲属和周围人际关系);能“守廉介”“广施惠”“救患难”“为人谋”(即不仅自己清廉,而且把仁德施于他人,乐于帮助人)。以上涉及到履约者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要求,包括修身、齐家、为人、处事、交游、教育以及扬善止恶的道德目标等方面。《吕氏乡约》还规定有一定的赏罚制度,履行《吕氏乡约》赏罚职责者称“约正”,此人必须是“正直不阿者为之”,即要求由具备较高德行的人来充任。另有“直月”以处理约中杂事。说明《吕氏乡约》不同于一般的乡规民约,它在乡规民约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基层教化组织和乡村自治模式。《吕氏乡约》通过“德业相劝”以及相关约定条文,凸显了儒家道德在乡约中的主导性。
其次,“过失相规”,就是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使邻里之间相互规劝,以纠正过失,赏善罚恶,移风易俗。《吕氏乡约》具体地列举了村民可能会犯的错误,这些错误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犯义之过”,即违犯道义的错误:如酗博斗讼,言不忠信,造言诬毁,营私太甚等。二是“犯约之过”,即违犯规约的错误,就是指违背上面提到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项规约及具体细目的错误。三是“不修之过”,即属于个人修养方面的过失,如“交非其人”“游戏怠惰”“动作无义”等。这些相互规劝的过失,涉及交友原则、生活态度、行为仪范、临事态度、用度之节等。对此,《吕氏乡约》具体规定了入约者应该承担的道德义务。
再次,“礼俗相交”,即“谓婚姻、丧葬、祭祀、往还书问、庆吊之类”,皆一遵礼制。这里,《吕氏乡约》贯穿了儒家重礼教的传统,主张“以礼化俗”,强调把礼仪和乡村秩序的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宋史》称张载之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黄宗羲称“横渠之教,以礼为先”,说明重礼教是关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作为张载之高足,吕氏兄弟在《吕氏乡约》中说:“凡行婚姻丧葬祭祀之礼,《礼经》具载,亦当讲求。如未能剧行,且从家传旧仪”,表明该乡约把礼贯穿到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婚嫁、丧葬、交往、接济等。在吕大钧看来,乡村中婚姻丧葬祭祀等事,皆应遵循《礼》的规定,使礼成为乡民日常行为的规范和准则。他们希望通过礼的实行,对村民进行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影响,使儒家的价值观念、礼仪制度逐渐为乡民所接受和认同,最终收到移风易俗之效。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对此高度称赞:“(吕大钧)先生条为乡约,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最后,“患难相恤”,贯彻了儒家特别是关学惠民、济困、相互帮助以及“民胞物与”、天下一家的精神。《吕氏乡约》针对乡村经常或可能发生的“患难之事”,即“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贫乏”七种情形,分别提出相应的规约举措和制度建设。如若有村民遇到盗贼,大家应该“同力捕之”,如果力不能捕,可“白于官司,尽力防捕之”,也就是先村民自救,自救无力者再由政府权力介入;如有村民有了重大的疾病,须“亲为博访医药”,若其贫困而无钱医治,则大家可以“助其养疾之费”,在经济上予以资助;对于孤弱无依无靠而“不能自存”的孩子,则“叶力济之,无令失所”;对于一直安贫守分但却生活遇到极大困难的民众,他强调“众以财济之”,或“假贷置产,以岁月偿之”。凡有患难的人,即使不是同约之人,只要知道了,“亦当救恤”。这些制度规约,带有明显的乡村自助自救的性质。吕大忠在《吕氏乡约》中特别指出,每一村民与乡党之间,其关系犹如“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恶利害皆与之同”,故“不可一日而无之”,这充分体现了儒家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村民一家的仁爱精神。吕氏通过《吕氏乡约》将乡民互帮互助以制度化的形式常态化,使村民互助共济有章法可循,有制度可依。所以,《吕氏乡约》的制订和实施,可视为儒家思想在乡村的重要实践和表现形式。它一经在乡村实行,就显示出其道德教化、社会治理、社会调解和社会控制等方面的功能,表现出其特有的乡村治理智慧和文化意义。不过,由于它涉及定期聚众集会,牵涉到对乡里参与者的行为惩戒,这也显然存在一定的法理问题和政治风险,关于这一点,吕大钧的兄弟也曾表示过忧虑。
二、《吕氏乡约》的乡村治理智慧和文化意义
《吕氏乡约》虽然历时千年,中国农村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只要传统村落在形式上存在,其依然有可资借鉴的文化价值。这种价值根源于《吕氏乡约》有其超越性的文化意义。其表现出的智慧和文化意义在于:
第一,其价值导向具有启迪村民的道德自觉和自律的智慧。《吕氏乡约》条文凸显的文化精神是道德为本、正义至上,是要引导乡村文化主体德性的提高。当道德自律一旦化入人心,成为乡民的自觉意识*费孝通先生说:“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于《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就能收到“诚于中,形于外”之效,从而引导和教化民众向善为善,互助友爱、遵纪守法,以彰显社会正义和良好道德。同时,以道德性原则去处理邻里之间的关系,就会促成良好的乡风民俗的形成,从而在根本上达到劝善惩恶、感化乡里的目的。“乡约的道德性,正和《周礼》的教化主义治民政策是一脉相承的。”[3]
第二,它体现了一种把社会教化通过民间自愿约定的方式加以实施,这创造了一种类似但又不同于《周礼》“读法”的高超智慧。学界一般把乡约的教化追溯到《周礼》的“读法”。《周礼·地官司徒》曰:“各属其州之民而读法,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以纠其过恶而戒之。”古人对教化的作用有充分的肯定,认为它具有道德指引和“防邪”之堤的双重意义。《周礼》中所说的“读法”本指宣读法令,即地方官员在履行行政职责之外,还负有教化民众的职责,这就为乡间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社会治理模式。汉代董仲舒说:“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教化行而习俗美”[4]《董仲舒传》。《吕氏乡约》所说的“德业相劝”的“业”,包括“教子弟”“教后生”“读书”“好礼乐射御书数”,这些所有的规约条款都有明确的价值指向,即哪些行为是“可为”的,而哪些是“无益”而不可为的;那些是正当的、正义的事,那些是“犯义”“犯约”的“过失”之举等等,这在一定的意义上都具有社会教化、敦本善俗的作用。这一点则与《周礼》的“读法”接近,不同点在于乡约不是自上而下的宣讲法令,而是“入约”者自愿的约定,即采取“入约”者“来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2]797的自由自愿原则。自觉接受乡约的约束,而这种组织方式赖以维系的基础必然是入约者的德性,可见,乡约是依靠入约者的德性魅力来支撑、坚守和持续的,这正说明了乡约具有道德自律的意义,其功能在于防患于未然
第三,它是实现乡村自治的重要形式,体现了传统农业文明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智慧。这种乡约由于是通过大家自愿、自发的相互协议规定下来的约定,它的实现是通过传统礼教对乡党邻里进行必要的道德约束,并通过社会舆论、自我约束、邻里之间的相互监督、必要的奖惩等来加以落实,以实现移风易俗和乡村的有效治理。正如梁漱溟所说:乡约可认定为一个“地方治体”,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地方自治组织”*转引自朱鸿林《孔庙从祀与乡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49页。。可以说,乡约是在中国古代农业文明背景下,在乡村实行的一种介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规约和组织形式。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它可以填补法律与乡村习俗之间管理的真空,成为法律的必要补充。其自治组织的特性表现在:一是村民需要履行“入约”的程序,只有“入约”的村民方受乡约的约束。这样“入约”村民就成为一个特殊的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二是设有主持乡约事务的专门人员,称“约正”和“直月”。“约正”是由“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其职责是“专主平决赏罚当否”,即只对赏罚是否恰当进行评判,并不负责具体的赏罚事务。较重的惩罚则需要“众议”,其处理具体的“杂事”则由“直月”去依约进行。其通过“众推”的乡约“主事”者和通过“众议”来实施乡约,其组织和实施过程一般都不与政府直接挂钩,这显然带有民间自治的性质。当然这里不排除也有后来出现的官办乡约,那将另当别论。三是乡约的制订是由乡贤主导的,它不由政府委派而是由大家公认的德高望众、主持正义者承当的。《吕氏乡约》确实有益于乡村的治理,但是具体实行起来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宋张栻曾指出过这一点,他说:乡约虽然“甚有益于风教,但《吕氏乡约》细思之,若在乡里,愿入约者,只得纳之,难于拣择。若不择而或有甚败度者,则又害事。择之则便生议论,难于持久。兼所谓罚者,可行否,更须详论精处,若闲居行得,诚善俗之方。”*参见《南轩集》卷22《答朱元晦》。张栻对该乡约的实行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说明要真正在乡村实行,还有一些具体事项需要妥善处理。
三、《吕氏乡约》的时代转换与当代实践
今天的时代与早年《吕氏乡约》推行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特别是近年来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在许多地方其原始村落形式已逐渐在解体或弱化,那种通过伦理关系、家族权威、家族祭祀等维系家族和睦、邻里和谐的情况在今天已逐渐失去根基;家庭的小型、微型化,熟人社会为主导向陌生人社会为主导的转化等等,都使乡约在今天的实行遇到了极大的挑战。但是,《吕氏乡约》具有的超越性文化意义,决定了它在今天的农村新文化建设中仍然具有其重要的价值。如果仔细分析,也不难发现《吕氏乡约》中有诸多与我们今天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合之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24字,涉及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修身层面。《吕氏乡约》的内容,主要涉及社会层面和个人修身层面,与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和谐,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等观念相吻合。如所说“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与“友善”相合;“能睦亲故,能择交游。能守廉介,能广施惠”,“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等,则与“文明、和谐,公正、法治”的精神相合;其所要纠正的“犯义之过”,如“言不忠信”“造言诬毁”等,其取向则与“诚信”的价值观相合;其所强调的不“酗博鬬讼”,不“行止踰违”,“行不恭孙”,不“营私太甚”等以及“不修之过”中诸项,其取向亦与“文明”“法治”的价值观相吻合。这些相吻合之处,通过一定的转化,可以成为今天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及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
目前,在一些地方的乡村新文化建设中,已经有行之多年且有明显效果的新乡约或村规民约出现。从这些新乡约或村规民约的内容和实行过程来看,可以看到传统乡约的生命力,也可以发现儒学融入乡村的可能途径。笔者新近对河南登封市大冶镇周山村、山东省泗水县的一些村庄、陕西省蓝田县五里头村、三里头村以及《吕氏乡约》的诞生地乔村、蓝田县白鹿原小寨镇董岭村、蓝田县蓝关街道黄沟村进行了专题考察,切实地感受到乡约文化在今天新农村文明建设中的强大生命力,也发现了儒学在当今融入农村的可能性路径。这里仅以河南登封周山村、陕西蓝田董岭村为例,说明传统乡约实行现代转化的可能性以及儒学融入当代乡村的可能路径。
河南登封周山村地处洛阳地区嵩山山脉腹地,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山村。该村为实行村民依法自治,推进新农村建设,经过民主协商,于2009年、2012年、2015年三次制订和修订,形成了目前行之有效的《周山村村规民约》范本。该乡约与传统的乡约相较,有了更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更为复杂多样的社会生活要素。除了突出传统乡约重视道德性和修身原则之外,更多的是突出了村民的权利意识和应有的环保意识。
民约分为《总则》《村民的权利义务》《村庄事务管理》《集体资源管理》《村民自我管理》《村庄环境保育》《继良俗树新风》以及《附则》等部分,《总则》部分突出了“依法”“平等”“民主”三个主要的精神原则,有了鲜明的时代意识。《村民的权利义务》突出村民的参与权、妇女的权利、老年人的权利以及村民应尽的“爱国、爱乡、爱家”的义务,“保护集体资源,爱护公共财产”“绿化美化山庄”“遵守公德”“热爱公益”“和睦邻里”“团善”“互帮互助”等。其民约的《村民自我管理》集中地体现了儒家的思想观念。所列内容有“诚实守信,互相尊重”“友爱宽容,文明礼貌”“关爱未成年人”“敬老、养老”等。这些内容不仅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与现代生活结合,而且增强了具有现代性的公德意识、文明意识、团结意识等。在《继良俗树新风》部分,规约明确了“婚俗变革”“葬俗变革”的内容,提倡文明节俭办婚礼、提倡新式婚礼,反对铺张浪费、大操大办。规定“葬礼力求节俭”“葬礼中男女平等”“孤寡老人的葬礼,村两委负责操办”等。这些都把儒家提倡的“节俭”“移风易俗”、平等仁爱的精神贯彻其中。通过这些乡规民约,使儒家最核心的仁爱观念、正义原则、秩序理念等落到了实处。该村自从有了这一乡规民约,并通过表彰奖励尊老孝行、义举善行、互敬互爱的人和事等制度化、常态化的活动,民风质朴,村风改观,人际关系融洽,形成了一个极为和谐的文明山村,多次被评为省市、国家级的文明村。在这样的氛围中生活的村民,快乐、幸福、自由、美满,从根本上杜绝了不良现象的发生,所以该村近年从没有违法犯罪的事件发生。充分说明对传统乡约可以进行现代性转化,这也为儒学融入农村提供了一个极其成功的实例。
蓝田县白鹿原小寨镇董岭村所制订的村规民约相对简单一些,但也有不同于周山村的特点。董岭突出的经济发展、社会治安和环境保护,其条文更像为大家订立的法规守则之类。其民约主要有“社会治安”“消防安全”“村风民俗”“邻里关系”“婚姻家庭”五个部分。前两个部分多使用“严禁”“不得”“加强”等词语,如“严禁偷盗、敲诈、哄抢国家集体财物,严禁赌博、严禁替罪犯藏匿赃物”等,所涉范围较之《吕氏乡约》更为具象化。不过,在“村风民俗”“邻里关系”“婚姻家庭”三部分中,则有了更多道德性内容。有关村风民俗方面,提到“反对封建迷信及其他不文明行为”“喜事新办,丧事从俭,破除陈规旧俗,反对铺张浪费”等移风易俗的内容,也有“不听、看、传淫秽书刊、音像”,“严禁随处乱堆垃圾、秽物”等有关提倡社会公德方面的内容。在“邻里关系”方面,强调村民之间“要互尊、互爱、互助,和睦相处,建立良好的邻里关系”,“在生产、生活、社会交往过程中,应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主张邻里纠纷的解决,要“本着团结友爱的原则平等协商解决”,“树立依法维权意识,不得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在“婚姻家庭”部分,提及“男女平等”“尊老爱幼”“反对家庭暴力”“尽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尽赡养老人的义务”,甚至还明确规定“禁止歧视、虐待、遗弃女婴”,“不得歧视、虐待老人”。这些条文中明显包含着儒家仁爱、友善、互惠、和谐等观念,显然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与当代社会生活具体结合的产物。
我们所考察的所有村庄,虽然其乡约(更像村规民约)的具体内容各异,但是有一些共同点:其一,从其内容上讲,儒家的仁爱精神、孝悌伦理、道义原则、修己精神等都以不同的形式得以体现;注意把传统儒家的价值观与当代生活实践相结合,赋予传统的价值观以新的现代性内容,突出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等。其二,在组织形式上,都形成了所谓的“一约四会”,一约即“乡规民约”或《吕氏乡约》,“四会”即“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村民议事会”,这组织虽然有村委会主导,但其运作基本上是带有民间自治的性质。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他们大都设立了“儒学讲堂”“道德讲堂”等,并以此形式来传播儒家思想,宣讲乡约内容,而且这些讲堂之类的形式,也确实为村民们所欢迎并热情参与。我们也注意到,这些讲堂之类的东西,对于引导村民学习知识、提升道德、引领文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重视研究乡约的智慧,把传统乡约引入现代文明乡村的建设并将其普及,不失为儒学融入现代农村的一个可行的路径,已有的乡村乡约的实践范例可以借鉴。
参考文献:
[1] 胡庆钧.从蓝田乡约到呈贡乡约[J].云南社会科学,2001(3):41-45.
[2] 吕大临,等著,曹树明点校整理.蓝田吕氏集[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3] 朱鸿林.孔庙从祀与乡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4]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