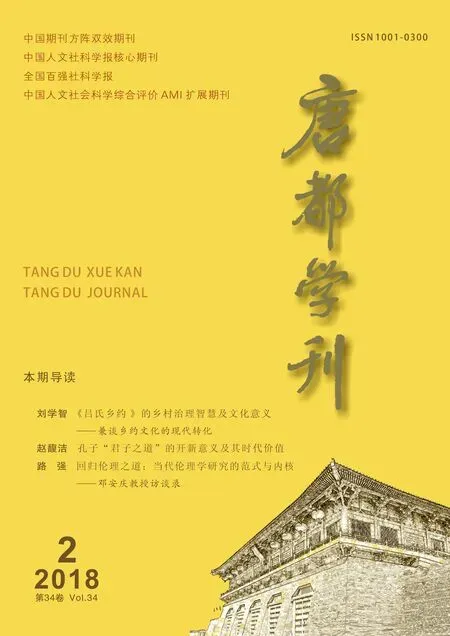汉代儒家价值观大众化的探索与实践
周春兰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江苏 无锡 214121)
推进价值观的大众化,有两个方面的问题至关重要:一是价值观理论自身的问题,包括价值观是否具有科学性,即是否经得起系统的反思和逻辑的论证;是否具有广泛性,即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而非精英定位;是否具有现实性与理想性,即是否反映现实问题和时代追求;是否具有吸引力与凝聚力,即是否得到大众的认同和拥护。二是价值观大众化的路径问题,即方法论问题。价值观普及大众,需要在价值观与大众之间搭建起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桥梁,从而使价值观大众化成为可能。汉代确立了儒家价值观为主导性价值观,并开始了儒家价值观大众化的实践,从理论准备和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实现了儒家价值观大众化的良好开端。
一、汉代儒家价值观大众化的理论准备
由于先秦儒学宇宙论的空疏,因此无法对其价值观给予形而上层面的关照,使得儒家价值观缺乏天道自然的支持,缺乏权威性。作为一种价值学说,儒家价值观要成为主导性价值观并实现大众化,需要有一个天然合理的终极依据为支撑,由此建立其权威性。为此,对儒家价值观进行形上性的阐发,使其成为永恒的价值原则,实现其形上与形下的贯通,这是推进儒家价值观大众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在经过《周易》阴阳观和天道观的洗礼之后,汉初儒者就已经开始自觉为儒家价值观构建形而上之根据,例如陆贾《新语》开篇提到:“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不过对天人关系进行了系统架构的是董仲舒,他将天、人、儒家价值观进行了贯通:首先,论证了天是人类生命的本原,是构成人类生命体的质料之一:“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1]《为人者天》;其次,论证了人性之质朴及其“待教而为善”,都是天决定的。“质朴之谓性”[2]《董仲舒传》,“性者,天质之朴也”[1]《实性》。人性是天所赋予的质朴的东西,既非天然之善,亦非天然之恶,需要进行教化:“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1]《深察名号》,“质无教之时,何遽能善?”[1]《实性》;再次,论证了教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价值观,这一核心内容是由天之阴阳五行决定的。“六艺”是人性教化成善的基本教材,董仲舒将这些教材的核心思想提炼为“三纲”“五常”,这些思想来源于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1]《基义》,又用阴阳附会三纲:君臣、夫妻、父子的关系是源自于阳尊阴卑的天道;五常“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1]《基义》,又把五行、四时附会五常:木为仁、火为智、土为信、金为义、水为礼,仁为春、夏为智、季夏为信、秋为义、冬为礼,从而为三纲、五常建构了形而上的根据。由上,天是人类存在的本原,也是儒家价值观存在的终极依据。董仲舒成功地将最高本原和儒家价值观的终极依据进行了统一,这就使得儒家价值观获得了超越于其他价值观的合理性,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使儒家价值观成为“颠扑不破”的永恒的价值原则。
为儒家价值观构建形而上之根据的过程,也是对儒家价值观内容进行改造的过程。对儒家价值观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价值观赋予了新的内涵。我们知道,先秦儒家对于君臣父子的关系,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价值要求,但君臣父子之间并不是单向的绝对服从,而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父子相隐,甚至是“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参见《孟子·万章下》。。而董仲舒的“君臣”“父子”关系,却是与《易传》中的“阳尊阴卑”“乾坤定位”的天道观结合起来的,并以此为根据,论证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这种强调单方面义务的价值观,这与先秦儒家的思想相去甚远。二是对价值观进行了大众化的新阐释。先秦儒家价值观以仁义为基本倾向,强调“杀身以成仁”“为仁由己”“忠恕”“中庸之德”“安贫乐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义以为上”,它的“高规格”的要求以及自觉自律的落实原则,使其具有一种明显的主体定位,即“士”以上精英阶层。而推进儒家价值观大众化,对价值观进行大众化的阐释是其内在要求。董仲舒对儒家价值观做了相对通俗化的新解。如“仁”,董仲舒认为“仁厚远,远而愈贤”,即爱得越远、越广、越多,就越伟大、越高尚。他以“晋灵公杀膳宰以淑饮食,弹大夫以娱其意”[1]《仁义法》和营荡“爱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长而夫拜之”[1]《五行相胜》的故事来说明:只爱自己、只爱亲属的人,都不能算“仁”。这种大众化的通俗易懂的阐述方式,比先秦的“仁者爱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杀身成仁”显然要更接地气,更贴近普通百姓,也更容易理解,更容易践行。
实现儒家价值观大众化,还需要对价值理念进行一定的提炼,使其更加简洁、更易于被民众记忆和掌握。董仲舒从最具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孝”出发,因为“世袭制则以孝为基础,孝是元德”,“孝是引出其他各种德性的元德,有了孝,就是经受了考验,就能保证履行官僚制最重要的等级义务:履行无条件的纪律”[3]。他继而站在维护大一统社会稳定的高度,以孝德为逻辑起点,在众多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体中,抽出君臣、父子、夫妇三对关系,在天人系统中确立了“三纲”的基本内容,建立了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价值原则。对于个体的价值要求,董仲舒从孟子讲的“仁义礼智”和“孝悌忠信”中“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参见《孟子·告子上》。和“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参见《孟子·尽心上》。捻出“仁、义、礼、智、信”,是为“五常”。“五常”的提炼,是个体应有的五种基本价值规范,“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2]《董仲舒传》;也是主导社会价值取向的需要,如“信”,当时社会风气“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提倡“信”,有利于引导社会价值取向,确立正面的价值观。
董仲舒虽未将“三纲”“五常”连用,但意义却影响深远。张岱年认为:封建时代的基本道德原则是董仲舒确立的,这个基本道德原则就是“三纲五常”[4]。的确如此,董仲舒对儒家价值观用“三纲”“五常”来提炼,并为此赋予形而上的根据,以及对此进行新内涵和大众化的阐释,使儒家价值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理性和权威性,也拉近了与基层民众的距离,为儒家价值观大众化做好了理论准备。
二、汉代儒家价值观大众化的实践开端
秦亡汉兴,自觉地构建意识形态、建立主导性价值观,是摆在大一统新帝国面前的一项历史任务。经过了对法家价值观的批判和黄老价值观的实践,汉初统治者又开始了新的价值选择。面对汉武帝的策问,董仲舒提供了一种新的儒家价值观。这一价值观核心理念清晰,其起源和存在有着至高无上的合理性依据,其内容有利于维护大一统王朝的长治久安,其普及路径切实可行。随着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儒家价值观自然而然地成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成为社会的主导性价值观。为弘扬儒家价值观,引导社会风尚,汉代开始了儒家价值观大众化的实践。通过顶层设计、由上而下的推进办法,开启了儒家价值观在基层民众中普及的历史进程。
1.皇室“以孝治天下”,率先垂范践行儒家价值观
汉立,刘邦大封同姓王,被誉为“皇帝孝德,意全大功,安抚四极”[2]《郊祀志》。孝德,自此开始,成为汉朝数百年的家法。自西汉惠帝、东汉明帝以下,帝王谥号无不冠以“孝”字。皇室的率先垂范,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例如,自秦商鞅变法以来,对家庭有这样的规定:“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2]《贾谊传》。贾谊等人对认为这种分家习俗是“陋习”,建议汉武帝改变这种习俗。汉武帝倡导以孝治国,从舆论上批评父母在世时候分家。“逮及东汉,因为汉世风俗的渐以儒家理想为依归,逐渐有奉父母同居为主干家庭。”[5]此外,认为不孝就是触犯了刑法:“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参见《孝经·五刑章》。,这在舆论上对百姓行孝、落实儒家价值观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初步建立了官学体系,开辟了儒家价值观研究和传播的专门渠道
随着儒学的意识形态化以及儒家价值观上升为主导性价值观,汉代开始了对儒家价值观进行专门的教育和研究,并开辟了专门渠道即建立官学。汉代官学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类,前者即太学,后者即郡国官学。武帝元朔五年(前124),朝廷为博士置弟子50人,太学建立。两汉太学中,设置博士的经学有14家。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300人,元帝时达1 000人,成帝时达3 000人。东汉质帝时,达10 000人[6]。平帝元始三年(414),开始建立地方官学制度,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普遍设学:设在郡国的称“学”,设在县的称“校”,设在乡的称“庠”,设在村(聚)的称“序”。学校设经师一人,庠序设《孝经》师一人。无论是中央官学还是郡国官学,均以儒家经学为教学的基本内容,是研究和传播儒家价值观的专门渠道。
3.循吏作为儒家价值观的教化官,业绩有目共睹
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教化是地方官吏的重要功能,但教化的内容是政府制订的“法律令”,认为“法律令”可以“教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7]《语书》。而“儒家强调政治秩序必须建立在文化秩序的基础之上,因此重‘师’更过于重‘吏’”,“他们在讨论地方官的功能时,也往往把推行‘教化’看得比执行‘法令’更为重要”[8]。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的教化型循吏,是将儒家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典型,“师”是他们的第一功能。制定礼则,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是循吏推进儒家价值观大众化的重要工作。如九真太守任延针对骆越地区“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的混乱现状,移书属县要求“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从而使得该落后地区“风雨顺节,谷稼丰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9]《循吏列传》。又如仇览、许荆等,对不孝敬父母的进行个别教化,使其感悟。他们“为官一任,教化一方”,在引导民众践行儒家礼义方面取得了为后世称颂的业绩。
4.鼓励典型与先进,推进儒家价值观大众化
一是置三老、孝悌官等。汉二年(前205),“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2]《高帝纪》。吕后元年(前187)二月,“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初置”说明此前没有,乃汉家首创;“二千石”,相当于当时郡守的官俸。文帝时,置员开始固定下来,“县置三老二,……,置孝悌力田廿二”[10]。对于有伤风化之事,三老、孝悌还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让(责)三老、孝梯以不教诲之过”[2]《司马相如传》。二是政策鼓励。为推进儒家价值观在基层民众中的普及,汉代不仅在政策上给予优惠,还在物质上给予一定的奖励。高帝时,掌管教化的三老无徭戍,且“十月赐酒肉”。惠帝时,开始注重以“孝悌”化民:“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2]《惠帝纪》,按师古的解释,“复其身”就是“一户之内皆不徭赋”[2]《高帝纪》。文帝时,“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2]《文帝纪》。三是表彰忠孝。统治者宣传“孝”,目的是不仅使臣民对父母“孝”,更是使天下人对君主“忠”。“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参见《论语·学而》。“孝”与“忠”是统一的,“以孝事君则忠”*参见《孝经·士章》。。例如,刘秀对于不忠王莽之士的大力表彰甚至封官,就是要树立践行儒家价值观的标杆,从而在舆论上加以导向,“东汉尚名节”即肇基于此。
三、仅是“开端”而不是“普及”——汉代儒家价值观未能在基层百姓中普及的原因
汉代推进儒家价值观大众化,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到制度均有相关的设计和具体措施,但儒家价值观在民众中的普及非常有限,其大众化的历程可以说是只开了个好头,仅是“开端”而不是“普及”,其原因主要有:
1.“根”仍不够缜密和牢固
作为儒家价值观之终极根据的“天”,是本原之“天”,不过在董仲舒这里,这个“天”还具有神性。“天者,百神之君。”[1]《郊义》“价值源于神秘的天‘本原’之中,又实现于‘天人感应’的神秘关系之中。……这种价值神秘化的意义在于,用超人间的‘天’和神秘的‘天人感应’强化了三纲五常的价值威力。”[11]三纲五常终极根源的神秘特征,在董仲舒之后有增无减,神秘色彩愈加浓厚。在谶纬文字中,“三纲”“五常”得到了迷信甚至荒诞的“强化”。如:“逆天地,绝人伦,则天汉灭见”;“逆天地,绝人伦,则蚊蚕兴”;“逆天地,绝人伦,当夏雨雪”;“逆天地,绝人伦,则二日出相争”[1]《诗纬·推度灾》。“八卦之序成立,则五气变形。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五常,仁义礼智信也”[1]《易纬·乾凿度》。《白虎通义》深受谶纬影响,其“百分之九十的内容出于谶纬”[12]。这种神秘而粗俗的论证以及它的迷信性、僵化性、教条性,经不起人们的追问和历史的考验。白虎观会议之后,作为统治思想的神学经学开始走下坡路,同时兴起了一股强大的怀疑神学经学的批判思潮。批判思潮着力扫除蒙在三纲五常上的神学迷雾,矫正人伦关系中的单向服从原则,致使谶纬和《白虎通》以神学为基础的学说体系轰然倒塌,“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价值观在基层民众中的普及开始陷入了持续低迷。直至宋明理学的建立,重新为儒家价值观赋予了本体论根据,才使其得到了提升、高涨和普及。
2.“家”在普及中的作用有限
虽然皇室鼓励行“孝”,倡导与父母同居,但及至东汉,三代家庭、“五口之家”才逐渐多了起来。据统计,东汉户口最盛时,有9 698 630户,49 150 220口,平均每户5.06口,是典型的小家庭的人口数,被称为“汉型家庭”。这种小家庭形态对于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价值观的普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难以开展蒙养教育。官学教育中没有蒙养教育这一内容,承担启蒙教育的责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民间私学上。而两汉时期,书院和社学等均未兴起,即便是族塾义学也因为汉代家庭的“小”而无法设立。众所周知,蒙养教育对于价值观的培育意义非凡,族学教育的缺位,使得汉代民间普及儒家价值观缺乏了重要载体。二是缺乏家法族规的保障。两汉时期,家训数量有较大增长,但仍主要出自皇亲官宦家族,并且还只是训诫,不具有律令或规诫的意义。在价值观大众化过程中,家庭教育是其重要环节,然而在“汉型家庭”背景下,蒙养教育和家法族规都难以实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至唐代,在传统家训的基础上,开始出现规范性的、强制性的家规族法,宗族权力开始通过制定家规族法对族人的日常生活进行监视和规训”[13]。南宋以来,随着平民宗族的普遍建立,族塾义学承担的蒙养教育的儒家化,以及贯彻着儒家价值观的家法族规的完善和落实,为儒家价值观在基层民众中的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
3.“学”未能普及基层百姓
汉代人口鼎盛时期,达六千多万,但受教育人口所占比例非常有限。汉代中央官学教育是一种精英化的教育,主要是为国家培养官僚人才,如此定位,决定了它与价值观大众化存在着较大差距。从数量上看也是如此,太学生数量最多时达万人,但与当时人口相比,比例非常小。再者,太学虽以儒家经典为教材,但实际上是经学。经学虽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分,但两者在本质上均把儒家经典作为权威性知识来对待,并且繁琐是其重要特征,解经动则几万十几万甚至上百万言,有的博士为通一经,甚至要付出皓首的代价,严重影响了作为价值观传播渠道本身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相比中央官学,郡国官学深入民间,应该来说是推进儒家价值观大众化的重要渠道。但与史籍上着墨众多的中央官学相比,地方官学的记载寥寥无几,地方官学并未在社会基层普遍设立,“政府所注重的,多属于‘学’和‘校’两种学校,而‘庠’和‘序’等小学性质的学校,并未能长期的设立”[14]。而推进价值观大众化,恰恰是需要这些散布在民间的具有小学性质的庠序教育。汉代地方学校的薄弱,使得儒家大众化缺乏统一的有力的基层教育的支持,故儒家价值观也难以在基层民众中间普及。
4.“循吏”之作为不具普遍性
《汉书》《后汉书》记载了循吏的突出业绩和民众对他们的拥戴和怀念,令其形象熠熠生辉。但从汉代官吏整体层面看,不具有普遍性,尤其是他们的政策措施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是典型的人治。汉代郡守的权力极大,正如王嘉在上疏中说:“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2]《王嘉传》。他们可以自设教条,推行教化,甚至还能设立制度、制定法令。因此,基层民众所受儒家价值观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与官员的见解和倾向有直接关系。如宋袅为凉州刺史,曾谓盖勋曰:“凉州寡于学术,故屡致反暴。今欲多写《孝经》,令家家习之,庶或使人知义”[9]《盖勋传》。儒家价值观的推广在全国郡县政府的工作中,并没有统一的要求和规定,循吏的个案在全国范围内不具有普遍意义。此外,即便是史书中浓墨渲染的循吏,其事迹也存在争议。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宣帝》中对龚遂、黄霸、尹翁归、赵广汉、张敞、韩延寿等做了点名批评:“广汉、敞、霸皆任术而托迹于道。广汉、敞以虔矫任刑杀,而霸多伪饰,宽严异,而求名太急之情一也。延寿以礼让养民,庶几于君子之道,而为之已甚者亦饰也。翁归虽察,而执法不烦;龚遂虽细,而治乱以缓”,尤其是赵广汉,其作为乃俗吏所为。为此,王夫之反问:“流俗之毁誉,其可徇乎”,“流俗趋小喜而昧大体,蜂涌相煽以群迷”,提出对于民间评价要理性谨慎看待。
5.“乡官”蜕变影响普及成效
三老、孝悌是承袭古代社会中的村落领袖变化而来的乡官,三老是沿袭古代的称谓,孝悌是汉代根据乡官职务的不同而给予的新称呼。有德、有模范事迹是当选“三老”“孝悌”的基础条件,是日后发挥其教化作用、“帅众为善”的资本。但“官方要求乡三老是‘能率众者’,就是说他们在当地较大的地域范围内对民众要有号召力。这单凭个人‘有修行’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要与乡族势力有某种关联,或者本身是乡族势力的代表人物,或者为乡族势力所认可。”[15]当然,我们对此估计不宜过高,汉代的小家庭结构形态,说明当时乡族的数量不会太多,在民间影响也不会太大,对三老来说,即便是乡族背景,乡族能赋予他的权威也不可能很高。但是,汉代给以三老、孝悌的俸禄却超乎寻常,使他们取得了“非吏而得与吏比者”的特殊身份[16]。随着时间的推移,“三老等人的身份名义上不变,实质已随社会的变化、新的阶级关系的形成而发生蜕变。他们不仅属于被封建皇朝统治者信任和依靠的基层领导阶层,又享有种种特权,汉代社会中与时俱增的大大小小的‘强宗豪右’,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由他们变化发展而来的。”[17]他们凭借权势逐步演变为特权阶层,通过兼并土地等方式,逐渐成为广大农民的剥削者和压迫者,以其言传身教来引导民众践行儒家价值观,其效果要大打折扣了。
综上所述,汉代注重价值观的建设,不仅确立了儒家价值观为主导性价值观,还顶层设计了儒家价值观大众化的具体路径,开展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拉开了儒家价值观大众化历史进程的序幕。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儒家价值观理论自身和推进路径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终汉一世,未能实现儒家价值观在基层民众中的普及。儒家价值观大众化,需要后世对上述问题加以矫正和完善,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
参考文献:
[1] 董仲舒.春秋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07-208.
[4] 周桂钿.董仲舒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8.
[5] 许倬云.汉代家庭的大小[M]∥求古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539.
[6]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5.
[7] 睡虎地秦墓竹简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8]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53.
[9]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 中国全集·历史中国集[M].台北:台北锦绣出版社,1982:56.
[11] 赵馥洁.价值的历程——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历史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77.
[12]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29.
[13] 黄书光.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111.
[14] 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1:72.
[15] 陈明光.汉代“乡三老”与乡族势力蠡测[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4):9-13.
[16] 牟发松.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J].文史哲,2006(6):83-93.
[17] 刘修明.“汉以孝治天下”发微[J].历史研究,1983(6):3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