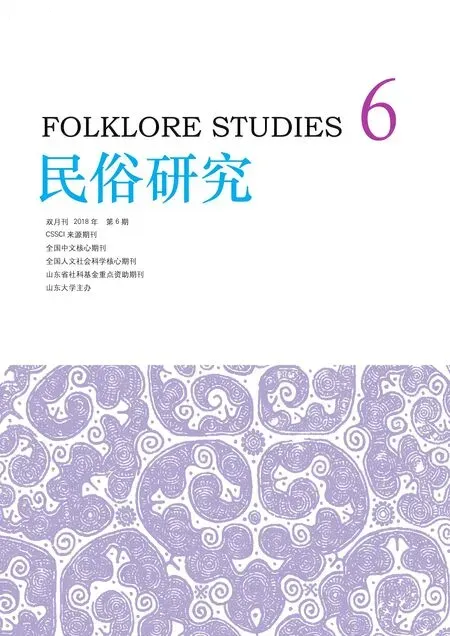西班牙语美洲中的民俗概念
[阿根廷]玛莎·布兰奇(Martha Blache) 著杨慧云 张青仁 译
回顾包括西班牙语美洲*西班牙语美洲(Hispanoamerica)是一个人文地理学的概念,它是对使用西班牙语的所有美洲国家和地区的总称。它们曾经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属于西班牙殖民帝国的一部分,在文化方面深受西班牙的影响,例如它们的官方语言都是西班牙语,主要宗教都是天主教。——译者注学者提出的与民俗有关的论述,在理论方面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差异。我将在本文中对不同的理论进行综合性陈述,使之与阿根廷主流观点形成对比。
所谓的“民(folk)”,或民俗的携带者,一直是使学者之间产生分歧的关键问题之一。在这里我将不会涉及那些认为民俗是“人民”产物的观点,这种观点忽略了构成民俗这个词的其他影响因素。关于民俗的定义是开放且多样的,不存在唯一一种解释。因此,如果没有辨清使用中的民俗一词的真正词义,将不利于我们澄清民俗学的相关概念。
通过对西班牙语美洲学者中民俗概念的初步研究,我将其区分为三种主要的理论观点。[注]Martha Blache y Juan A, Magarios de Morentin, Síntesis crftica de la teoria del Folklore en Hispanoamérica . Buenos Aires: Tekné, 1980.像之前的研究所做的一样,我会根据不同的观点进行综述,所以只会引用到部分学者的观点。另外,这一研究是根据理论范式进行列举,并非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罗列。被提及的民俗学者也是按照其理论范式来排序,没有考虑研究观点提出的时间。
第一种理论观点将民间与一种特定的社会阶层联系在一起。重要的学者包括奥古斯多·劳尔·科塔萨尔(Augusto Raúl Cortazar)和布鲁罗·哈克维亚(Bruno Jacovella)等。[注]Augusto R. Cortazar, “Los fenómenos folklóricos y su contexto humano y cultural”, in Teoría del Folklore en América Latina. Caracas: INIDEF, 1975, pp.45-86; Bruno Jacovella, “Los conceptos fundamentales clásicos del Folklore. Analisis y critica”, in Cuadernios del Institut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onies Folklóricas . Buenos Aires: 1960, pp.27-48; Bruno Jacovella, Sobre el uso de la voz folklore para designar exclusivamente uno de los estratos socio-culturales del complejo civilizado, trabajo presentado al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Folklore Iberoamericano, Santiago del Estero, 22-27 de septiembre 1980.这个特定的社会阶层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农民,他们构成同质的、小而孤立且自给自足的社区,这些社区坚持祖先们的传统,技术简单且缺少分工。家庭在社会制度中扮演着主要角色,依靠神圣力量的主导实现对社会的治理和惩戒。
这些特点与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提出的民间社会(Sociedad folk)一致,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将民间定义为与城市生活相对的社会状态,它是一种没有受到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污染的社会。城市社会被定义为一种异质性的社会,是非私人关系的,具备分工和货币经济的社会。正如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界定方法,因为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并不存在一个完全符合以上所述特征的社会。[注]George Foster, Qué es cultura folklórica?, Revista de Educación., La Plata, Vol. 3, no. 2(1958), pp: 238-60.
另一些学者,如卡洛斯·维加(Carlos Vega)将某些城市地区中还保存着的一些已被现代社会遗弃的文化遗留物也包括其中。[注]Carlos Vega, La ciencia del Folklore. Buenos Aires: Nova, 1960.他们认为文化财产来自于社会上层阶层,一旦文化被上层阶层抛弃,失去了活力和作用,文化便降级成为低级文化。因此,一种文化渐渐式微,便会成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他们将这种研究的过程视为一种文化上的恶化。这些学者默认了一种观点,即民可以模仿民俗现象,但是不能创造民俗。民间只能接受、吸收一种民俗文化,将其代代传递下去。结果,对于这些学者而言,文化转变成为过时之物后,由此又成为民间的遗产。
相反地,由乔治·马丁内兹·里奥斯(Jorge Martínez Ros), 塞索·劳拉(Celso Lara),马克思·梅加·瓦盖斯( Max Melgar Vásquez),和利达·赛伽多(Rita Segato)等学者秉持最新的一种观点,即将民与社会流动性非常低的、由下层阶级构成的被剥削和被压迫群体联系在一起。[注]Jorge Martinez Ríos, “El grupo folk como grupo marginal”, in 25 Estudios de Folklore, México: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Estéticas, Estudios de Folklore, no. 4(1971), pp.123-30; Celso A. Lara, Aproximaci6n cientifica al estudio del Folklore, Folklore Americano, Vol. 22 (Dicembre 1976), pp.81-109; Rita Segato, Folklore y relaciones sociales en América Latina, Un intento de definir el campo del Folklore a partir del nivel y modo de producción, Folklore Americano, Vol. 22 (Dicembre 1976), pp.111-20.这些民俗学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将民定义为无产者群体,他们被社会经济结构和不断生产的社会关系所制约。
尽管上述学者关于民的观点有明显的区别,但他们的观点仍然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即他们均认为民是社会分化的结果,这一分化造成了某些群体在教育和经济地位方面的劣势地位。这些学者以一种过去的、遗留的态度将民联系起来,认为民是处于国家发展边缘地位的,是仍然坚持着过去的传统的群体。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可以预先判定他是否是民俗的携带者。在这种情况下,民俗现象在社会和物质方面都被限定:在社会方面,民俗现象被划分到更低的阶层;在物质方面,民俗现象则被认为更多地存在于农村地区或是城市的贫困地区。
根据学者们所确定的定义,“民”被定义为“农民”或“被剥削者”,他们生活在农村或是城市地区,属于社会的边缘群体。这一说法并非暗示这些专家对民间的轻蔑态度。它只是体现了这门学科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语境下所体现出来的观点。确定民的范围后,俗就被定义为民能够生产的产物,而这正是民俗学这门学科研究的对象。因此,民和俗被割裂开来。个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他是否可以被认定为民俗现象的生产者。
第二种理论观点在定义民俗时并不强调“民”的概念,如艾弗兰·莫罗德·贝斯特(Efraín Morote Best)和胡莉亚·埃莱娜·弗顿·德·波斯(Julia Elena Fortún de Ponce)。[注]Efraín Morote Best, “Elementos del Folklore”, in definición, contenido, procedintientos. Cuzco: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uzco, 1950; Julia Elena Fortún de Ponce, Manual para la re colecciión de material folkliórico, La Paz: Ministerio de Educaciión, 1957.他们认为,携带民俗的人可以是社会的各个阶层;它可能是土著社区、农民阶层抑或是人口密集的城镇。他们没有去除农民在这一群体中的位置,但他们也没有将民俗视为唯一属于农民的遗产,而是指出了在城市里也存在着民俗现象。它与个人的教育水平、工作条件、经济地位或社会提供的科学、技术和艺术信息无关。俗被定义为所有能被识别的文化事实。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像第一种观点的学者那样将民俗局限于一个社会阶层。但这些学者同样将民与俗分开。他们把客体和生产它的主体区分开,好像它们是可以分割的实体一样。然而,个人和知识构成了一个整体。为了理解这一现象,它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被研究,并且考虑它产生的背景,以及它与社会和文化结构等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三种观点的代表是马努埃尔·丹纳曼(Manuel Dannemann)。[注]Manuel Dannemann, “Teoría folklórica, Planteamientos críticos y proposiciones básicas”, in Teorías del Folklore en América Latina. Caracas: INIDEF, 1975.他认为,民俗现象存在于全人类,不受社会地位或地理位置局限,企图区分民俗群体和非民俗群体的观点是一种与现实不符的偏见。在理查德·维斯(Richard Weiss)的支持下,他认为民俗(folklore)是一种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参与其中的行为方式。[注]Manuel Dannemann, “Teoría folklórica, Planteamientos críticos y proposiciones básicas”, in Teorías del Folklore en América Latina. Caracas: INIDEF, 1975, p.30.他还进一步指出,民俗是一种人们在特定情境下行为方式的表现。
这与之前提到的学者的观点在两个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一方面,它没有在民和俗之间进行二分。民俗既不是由它的携带者确定,也不是由俗来确定。它没有将民视为一方,将俗视为另一方,而是将它们视为整体。因此,它不会使人与行为分离,无论这种行为是通过语言,或是行为方式,抑或是一种详细阐述对象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主体和客体是相互依赖产生作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注]Manuel Dannemann, “Teoría folklórica, Planteamientos críticos y proposiciones básicas”, in Teorías del Folklore en América Latina. Caracas: INIDEF, 1975, p.36.它们应该合并为了解一定文化背景中的民俗概念意义的两个方面。另一方面,丹纳曼认为,特定时刻的民俗活动的参与群体在人员构成和持久性方面不具有稳定性,其成员也不一定具有共同的特征。参与民俗的个体并没有共同点。相反,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对于民俗活动的参与者有利的客观情境。[注]Manuel Dannemann, “Teoría folklórica, Planteamientos críticos y proposiciones básicas”, in Teorías del Folklore en América Latina. Caracas: INIDEF, 1975, p.32, p.40.因此,民俗既可以发生在稳定性群体中,也可以发生在偶然性和暂时性群体中。
因此,民俗与群体内部某些特定的条件相关,这些条件可能会随着群体的消逝而消失,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多纳·普·德·萨那多(Dora P. de Zarate)也支持这种看法。[注]Dora P. de Zarate, “Nuestra posición frente a las teorías folklóricas”, in Teorías del Folklore en América Latina. Caracas: INIDEF, 1975, p.133.关于这个问题,我必须指出,我在之前写《西语世界中的民俗理论综述》时有错误,这很重要,因为我是依据先前的这个研究来辨别学者们不同的民俗定义标准的。
第三种理论观点也被称之为适时理论(Coyuntural),除了丹纳曼,我也将多纳·普·德·萨那多归类在这一理论流派中。[注]Martha Blache y Juan A. Magarios de Morentin, Síntesis crftica de la teoria del Folklore en Hispanoamérica . Buenos Aires: Tekné, 1980, pp.22-23.然而在笔者修订这篇文章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错误,并予以改正。[注]Dora P. de Zarate, “Nuestra posición frente a las teorías folklóricas”, in Teorías del Folklore en América Latina. Caracas: INIDEF, 1975.实际上应该将她归入到第一种理论流派中,因为她认为“民俗将它的视野限制在了排除文明民族的非文明群体的生活里。”[注]Dora P. de Zarate, “Nuestra posición frente a las teorías folklóricas”, in Teorías del Folklore en América Latina. Caracas: INIDEF, 1975, p.147.紧接着,她又指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被归类为介于知识渊博和原始之间的中间群体的活动”[注]Dora P. de Zarate, “Nuestra posición frente a las teorías folklóricas”, in Teorías del Folklore en América Latina. Caracas: INIDEF, 1975, p.149.。当她说出以下观点的时候,她的理论立场更加明晰起来:
即使在最发达的文化中,仍然遗留下一些表现为退步、缓慢或者拒绝进化的部分;它们表现为缺少进步,没有达到其他部分的进化水平,但是这些部分在那些没有多少机会达到其他高进化水平的群体中一直存在。这些部分通常构成了民俗材料,可以通过它的特征被识别,它是传统的、匿名的、具象的、前逻辑的,带有诸如永久性、特殊性的非制度化的特征,以及带有诸如偶然性的群体功能和地域性的特征。[注]Dora P. de Zarate, “Nuestra posición frente a las teorías folklóricas”, in Teorías del Folklore en América Latina. Caracas: INIDEF, 1975, p.150.
在澄清了这个错误之后,我将要介绍丹纳曼的观点,他的研究角度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同时这位西语世界中的学者将原来欧洲和美国学者对民俗学的观点推向了前沿。
关于民俗的知识构成,西语世界中的学者有着更好的默契。大多数学者认为,民俗的研究领域既包括所谓的物质文化,也包括人的精神文化;但是米尔德莱德·麦里诺·德·塞拉(Mildred Merino de Zela)除外,他将民俗限定于口头文学、音乐和舞蹈的范畴中[注]E. Mildred Merino de Zela, Hacia una teoría del Folklore Peruano, Folklore Americano, Vol. 18 (dic. 1974), p.55.。然而,专家们并不认为所有的社会事实都属于民俗,只有那些具有特殊属性的事物属于民俗的范围。一般意义上的民俗活动是指那些既有着过去的传统并且又在当下呈现的事实。民俗活动最初的发起者无从判定,它是匿名的。它自发地发生,不通过书本教授,也不由机构或组织指导。它没有受到明确的规定,也不是通过法律规范体系而习得,而是源于这一事实所在群体内部的同化实践。它以一种对个人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而生根发芽,得以发展。它以口头的方式传播,可能发生变化或转变,但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这表现出其具有可塑性。
丹纳曼同时指出:“一个文化实践要想成为民俗,通常只有在特定的群体中产生了共同的、独有的、整合的和代表性功能的情形下才可能。”[注]Manuel Dannemann, “Teoría folklórica. Planteamientos críticos y proposiciones básicas”, in Teorías del Folklore en América Latina. Caracas: INIDEF, 1975, p.29.然而,当学生或是士兵在集会中向国旗敬礼时,也可以发现这些特征。参加这一爱国教育仪式的群体,在这个活动中感受到了一种参与成员之间共享的象征。这是一种具有国家国民身份认同的象征,通过此可以将其与其他国家的公民区别,并借助国籍实现一国国民的凝聚,成为国家的代表。但是,大多数学者并不会认为这一行为属于民俗现象。虽然这可能是一种爱国主义的真实表现,但是在这个情境中,该行为是体制规定而并非自发地形成。这表明,即使丹内曼创造性地指出了民俗研究的新领域,但民俗的特征仍然不明确。
当然,我的目的不在于将学者分类归位,而是要探寻我们研究中表现出的主要倾向。上述的研究表明前人的研究是基于不同的设想之上。一些民俗学者通过这一方式来理解这一概念,定义这一研究的对象。即民是这一概念的主要元素,通过其可以反映出民俗概念的其他内容。当然,也有学者通过对于俗的把握来理解民俗,还有一些学者考虑通过对民、俗和语境的融合来阐释这一概念。尽管后者是最为折中的处理方式,但是仍然不能精确地定义民俗现象的特有特征。
在这些西班牙语美洲关于民俗的理论中,需要注意的是某些要素被忽略了,一些本应被仔细研究的要素却没有受到关注。例如,关于表现的形式和内容。[注]Martha Blache y Juan A. Magarios de Morentin, Síntesis crftica de la teoria del Folklore en Hispanoamérica . Buenos Aires: Tekné, 1980, pp.41-45.前者指可以被感知的外部表象,无论是器物的、口头语言的还是行为的;后者指的是它可能对参与者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前者可以验证,后者可以推断。例如,盛装舞会有着特定的形式,并且对参与其中的群体赋予一定的价值。显然,形式和内容必须同时出现才能使得民俗现象变得具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群体可能会对民俗事实做出改变,从而改变其形式或意义,诚如之前作为劳动活动一部分的盛装舞会后来可能会作为带有慈善目的、为了筹集资金的表演。在这种情况下,形式和内涵都可能具备相似性的改变。因此,形式与内涵都是可以相互独立发生变化。
学者们均认同民俗知识来自过去的观点。然而,他们并未指出民俗现象传播的社会方式和地理路径的多样性。民俗的传播可以借助一种或几种文化,在一个阶层内部或者通过跨越不同阶层得以实现。从知识阶层到文盲之间的传播是最被广泛接受的一种传播方式,但是大多数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其他传播的可能。甚至没有注意到民俗行为模式在不同物理空间上的弥散传播现象。这些行为模式可能分散在一个或几个地理空间内,并且根据农村、城市或是两者之间区域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别。[注]Martha Blache y Juan A. Magarios de Morentin, Síntesis crftica de la teoria del Folklore en Hispanoamérica . Buenos Aires: Tekné, 1980, pp.57-65.
另一个被忽视的方面是民俗的传播。学者们认为个人学习民俗的方式是自发性的,这排除了制度化教育的可能。总体上来说,在理论著作中均没有提及传播的其他方面。这些方面包括了个人学习民俗的时机,也包括民俗传播的地点或实际区域;以及民俗知识散布过程中的参与者和信息的发出者与接收者。[注]Martha Blache y Juan A. Magarios de Morentin, Síntesis crftica de la teoria del Folklore en Hispanoamérica . Buenos Aires: Tekné, 1980, pp.51-57.这显得有点奇怪,学者们对民俗的传播研究缺乏兴趣,但是他们却不断重申植根于过去是民俗的特点之一。如果民俗来自现在之前的某个时间,对民俗传播过程的论证和系统化应该是首要做的事情。
非常不同的是,欧洲和美国的研究人员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从世纪初就开始关注同一群体中,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民俗传播时发生的变化。首先我们应该提到弗兰克·汉密尔顿·库欣(Frank Hamilton Cushing),他在1901年研究了北美原住民中欧洲民俗故事的传播机制[注]Frank Hamilton Cushing, Zuni Folk Tales. Nueva York y London, 1901, pp.411-22.。数年后巴特利特(F. C. Bartlett)致力于发现民俗传播中变化的性质以及它背后的规律。[注]F. C. Bartlett, Some Experiments on the Reproduction of Folk Stories, Folklore, Vol. 31 (1920), pp.30-47.同时卡尔·冯·西多( Carl von Sydow)区分了民俗的主动传播者和被动传播者,对此项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注]C. W. von Sydow, “On the Spread of Tradition”, in Laurits Bodker. Copenhagen (ed. ), Selected Papers on Folklore. 1948, pp.11-18.其他参与这一描述和分析过程的学者还有阿伯特·维斯基(Albert Wesselski),沃尔特·安德森(Walter Anderson y),吉拉·奥图塔(Gyula Ortutay)和琳达·德(Linda Degh)等等。[注]Emma Emily Kiefer, Albert Wesselski anid Recent Folktale Theories, Folklore Ser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no. 3(1947); Walter Anderson. Ein Volksküindisches Experiment, Folklore Fellows Communicationes. no. 141, Helsinki, 1951; Gyula Ortutay, Principles of Oral Transmission in Folk Culture, Acta Ethnographica. Vol. 8(1959), pp.175-221; Linda Dégh and Andrew Vázsonyi, “The Hypothesis of MultiConduit Transmission in Folklore”, in Dan Ben-Amos and Kenneth S. Goldstein (eds. ), Folklore, Performance and Commnunication. The Hague-Paris: Mouton, 1975, pp.207-54.如果将民俗视为一种社会行为,那么这些人的研究便可以理解了。知识的传播过程是复杂的。同样,知识在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代与代之间不断传播也是复杂的。[注]Martha Blache, La transmisión del hecho folklórico, Mundo Ameghiniano. En prensa.
一般来说,西语世界中的学者与其他区域的学者对民俗研究关注点并不相同。这点可以从罗马民俗学家米哈·波伯(Mihai Pop)的研究中看出,今天旧大陆的学者们关注的是民俗现象的结构、功能及其意义,并非民俗的形式与历史。[注]Mihai Pop, Problemas generales de etnología europea, Trabajo presentado en el Primer Congreso Internacional de Etnología Europea, en Paris, 24-28 de agosto de 1971, Traducción del frances por Catalina Saugy.他们还借助了符号学的方法以及使用传播的图案寻找民俗事实背后的隐含意义。目前他们重新思考这些理论和假设,以便帮助他们辨别民俗现象的内在机制。
一些美国人也使用相同的思路,对民俗现象的内在联系和产生它的外部环境进行研究。早在1959年,威廉·哈格·哈森(William Hugh Jansen)就强调了民俗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表现在一个群体的归属感、群体对自身形象的认知以及群体对与其有互动关系的群体的认知上。[注]William Hugh Jansen, “The Esoteric-Exoteric Factor in Folklore”, in Alan Dundes (ed. ), The Study of Folklor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5, pp.43-51.他指出民俗能够强化了群体的身份认同,在形塑对于自身群体认知的同时,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将自身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
邓迪斯(Alan Dundes)和布鲁范德(Jan Harold Brunvand)均认同民俗现象为群体成员提供了共同的身份认同的观点。[注]Alan Dundes, “What is Folklore”, in Alan Dundes (ed. ), The Study of Folklor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5, pp.1-3; Jan Harold Brunvand,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lklore: An Introduction. Nueva York: W.W Norton, 1968.他们认为民俗现象由一系列为群体赋予归属感的传统活动构成。由此,民俗可以被区分成职业的、世代的、民族的和国家的。有时也可以根据宗教、教育、首要的娱乐活动、居民、甚至是家庭来确定。[注]Jan Harold Brunvand,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lklore: An Introduction, Nueva York: W.W Norton, 1968, pp.21-22.然而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认为,虽然民俗的社会认同功能很突出,但是这门学科的根本要义在于研究这个共享传播系统中的民俗和实践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注]Richard Bauman, “Differential Identity and the Social Base of Folklore”, in Americo Paredes y Richard Bauman (eds. ), Toward New Perspectives in Folklore. Austin y Londo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5, pp.31-41.从这个维度上来说,民俗既可以是一种冲突工具,也可以是一种促进社会团结的机制。与此同时,罗杰·亚伯拉罕强调了民俗研究中对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分析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民俗传播与它对观看者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注]Roger D, Abrahams. Introductory Remarks to a Rhetorical Theory of Folklor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81, no. 320 (April-June 1968), pp.143-58; Roger D. Abrahams and Susan Kalcik, “Folklore and Cultural Pluralism”, in Richard M. Dorson (ed. ), 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Hague-Paris: Mouton, 1978.他指出,群体为了将参与者整合在一起使用了种种策略,他们使用传统的说服技术,其中包括移情的方法或是某种控制机制。
此外,就像巴莱·托克(Barre Toelken)和邓迪斯(Alan Dundes)所做的那样,群体的概念似乎已经发展为一种民俗文化研究的世界观。[注]Barre Toelken, “Folklore, Worldview, and Communication”, in Dan Ben-Amos y Kenneth S. Goldstein (eds. ), Folklore, Performance and Communication. The Hague-Paris: Mouton, 1975, pp.265-86; Alan Dundes, “The Number Three in American Culture”, in Richard M. Dorson (ed. ), Studies in Folklore. The Hague: Mouton, 1975. pp.206-25; Alan Dundes.Thinking Ahead: A Folkloristic Reflection of the Future Orientation in American Worldview, Studies in Folklore. The Hague: Mouton, 1975, pp.226-38.这就意味着某种风险,因为世界观(文化对世界编码的方式或是某种价值观之上的秩序)本身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世界观的概念,包括了明确规定一个群体内部的合法行动规范,是一个太广泛的概念。
综上,当西班牙语美洲世界限制了民俗现象的研究领域时,其他国家却并不强调这些差别,而是试图挖掘这一现象的多重内涵。因此,现在要理解民俗现象,必须从它的多种表现形式和它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独有特征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尽管我已试图界定民俗学研究的对象,但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的与民俗相关的问题。最近由理查德·M·多尔逊(Richard M. Dorson)编辑的《现代世界民俗》一书收录了来自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民俗学家的著作。[注]Roger D. Abrahams and Susan Kalcik, “Folklore and Cultural Pluralism”, in Richard M. Dorson (ed. ), 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Hague-Paris: Mouton, 1978.其中美洲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拉丁美洲的学者并没有受到重视。从学者们研究的标题的变化可以看出后工业时代以来这一学科经历的变化。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民俗与城市规划、工业化、意识形态和大众媒体之间的关系方面。这些涉及到不同方面复杂性的学者的观点汇集到一起,能够分析出民俗和其他现象之间的关联。正如多尔逊在序言中所写的那样,学者们认为对于民俗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民俗本身,还要将其置于发生变化的现代世界中。这种对新的研究方向的探索是非常有收获的。并非这些所有的尝试都会有结果,但是它们有助于确立民俗和民俗学研究的独特性。
以阿根廷为例,回顾了我国的民俗研究,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注]Martha Blache, Resea de los estudios folklóricos en la Argentina, Revista del Museo Provinicial. Neuquén: en prensa.第一个时期是学科的开创时期,学者们刚刚开始了解到其他国家的民俗学研究。其中包括罗伯特·莱曼·尼采(Robert Lehmann-Nitsche),他通过1911年至1928年出版的一系列专题研究展示其优秀的分析能力,为我国的民俗研究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注]Robert Lehmann-Nitsche, El Retajo, Boletín de la Academia Nacional de Ciencias en Córdoba. Buenos Aires, Vol. 20 (1915), pp.151-234; La Bota de Potro. Boletín de la Academia Nacional de Ciencias en Córdoba, Vol. 21 (1916), pp.183-300; Santos Vega, Boletín de la Academnia Nacional de Ciencias en Córdoba, Vol. 23 (1919), pp.610-28; Mitos ornitol6gicos, Revista de la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Vol. 3, no. 6 (1928), pp.219-359.他对谜语的分类为阿切尔·泰勒(Archer Taylor)对盎格鲁美国人的谜语搜集奠定了基础。[注]Archer Taylor, English Riddles from Oral Tradition. Berkeley 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5.
第二个时期,阿根廷的民俗研究开始强大,并创建了一个专门致力这一领域的研究机构——国家传统研究所。它的第一任所长,胡安·阿方索·卡里索(Juan Alfonso Carrizo),通过大范围的实地田野,最终收集到了我国西北部地区保留的超过两万首歌谣。[注]Juan Alfonso Carrizo, Antiguos cantos populares argentinos: cancionero de Catamarca. Buenos Aires: Silla, 1926; Cancionero popular de Salta, Tucumán: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Tucumán, 1933; Cancionero popular de Jujuy. Tucumán: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Tucumán, 1934; Cancionero popular de Tucumán. Tucumán: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Tucumán, 1937; Cancionero popular de La Rioja. Tucumán: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Tucumán, 1942.在这个研究所中,学者们相互合作,对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诸多学者中,苏珊娜·切杜迪(Susana Chertudi)因为她的杰出才华和奉献精神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她特别致力于对传统故事的汇编和分类,亦关注于民间叙事的研究。[注]Susana Chertudi, Cuentos folklóricos de la Argentina, primera serie. Buenos Aires: Instituto Nacional de Filologia y Folklore, 1960; Segunda serie. Buenos Aires: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ia, 1964.
在此期间,学者们开始考虑对民俗概念的界定。在所有的理论阐述中,奥古斯托·科尔塔萨的理论是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得到了最为广泛的认可。他的理论是建立在雷德非尔德的民间社会概念的基础上。他划定了民俗现象发生的范围,并界定了民俗的特征,即它应该是大众的、集体的、传统的、口头传播的、匿名的,经验的、功能性的和区域性的。从他1942年提出这个概念以来,虽然也在不断地修正,但多年来这个最初的概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成熟的概念。[注]Augusto Raúl Cortazar, Bosquejo de una introducción al Folklore. Tucumán: Universidad Nacional, Instituto de Historia, Lingüística y Folklore.1942; “Los fenómenos folklóricos y su contexto humano y cultural: concepción funcional y dinámica”, in Teorías del Folklore en América Latina. Caracas: INIDEF, 1975, pp.45-86.
1955年,在科尔塔萨的倡议下,大学里创立了民俗学的学位点。然而,这个学位点只存在了短暂的时间。两年后,民俗学和民族学、考古学一起成为新开设的人类学学位点的一部分。但是除了科尔塔萨对民俗学的支持和传播外,民俗学是学术和科学组织最少推动和鼓励的三个专业之一。1964年国家传统研究所改名为国家人类学研究所。它不再专门进行民俗研究,还包括了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研究。
在前两个时期中,接触民俗研究的学者大多数来自其他专业领域,如语言学家E.贝尔塔·维达尔德·巴蒂尼(Berta E. Vidal de Battini)、律师行业的奥古斯多·劳尔·科塔萨尔(Augusto R. Cortazar)、文学领域的里卡多·罗哈斯(Ricardo Rojas)、伊斯梅尔·莫亚( Ismael Moya)、历史学家阿古斯丁·萨帕塔·戈雅(Agustin Zapata Gollan)、地理学家菲利克斯·科卢乔(Felix Coluccio)、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多·波维纳(Alfredo Povifia)、牙科学家卡洛斯·维亚福德(Carlos Villafuerte)、医药家托比亚斯·罗森伯格(Tobias Rosenberg),奥雷斯特斯·迪·卢约(Orestes Di Lullo),格雷戈里奥·阿尔瓦雷斯(Gregorio Alvarez)。
在第三个时期,民俗研究停滞不前。有几个原因。几乎没有相关主题的书籍在国内出版。拥有大量民俗出版物的两个图书馆在60年代暂停了国外书籍的购买和国际专业期刊的订阅。[注]Biblioteca del Museo Etnográfico, dependiente del Instituto de Ciencias Antropológicas de la Facultad de Filosofía y Letras de la 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 y Biblioteca del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Dependiente de la Secretaría de Estado de Cultura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y Educación.结果,学者的知识更新受到阻碍。他们很难掌握其他国家民俗研究新的理论和方法。虽然大学民俗学教学的开展培养了一批专注于这一领域的年轻人,但是他们的贡献很难评价。阿根廷没有建立民俗研究中心,没法储存民俗资料和民俗物品,而且也没有民俗类的专业期刊。研究人员的文章散布在包含不同内容和优先传播的出版物中,然而这些却都是学科研究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的民俗学者之间缺少有效和顺畅的交流,每个人都孤立地工作。
此外,由于奥古斯多·劳尔·科塔萨尔和苏珊娜·切杜迪分别于1974年和1977年早逝,从而造成了我国民俗研究的中断与空白。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我们学科的支柱。科塔萨尔以其对发表民俗研究论文、传播手工艺品和出版阿根廷民俗研究书目的热情,在实现民俗的循环传播方面备受认可。[注]Bibliografía del folklore argentino. Buenos Aires: Fondo Nacional de la Artes, 1965 y 1966.他通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其他省份出版图书、举办讲座和开展民俗研究的课程,宣传他的研究成果。切杜迪则在她的学术生涯中不断了解不同国家民俗研究的发展状况,并将这些学术信息写成著作或者是以讲座的形式,让其他人周知。
一般来说,在阿根廷,民俗学家的研究一般专注于对农民的研究。大多数学者将科塔萨尔的理论奉若圭臬,然而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任何一种理论范式都可能成为刻板的教条。他们从事的民俗学研究多注重于描述,虽然这是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有必要通过分析对其进行补充。通过对于它们的分析,才可以确定民俗的功能和意义,以及它的组成部分之间的特殊关系,以便能准确把握他们的结构并解释这一行为的特殊性。
科塔萨尔热爱猎奇式地寻找民间风俗,他往往将民俗和对土地乡情的爱混为一体。至于是否严格地表述了民俗的基本概念,或者是否对民俗现象的独特性有所思考,他不太关心。此外,大部分搜集工作都是由业余爱好者完成,似乎这门学科不需要专业和系统的训练。固然,他们对于传统的热爱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这些成果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符合科学的严谨性,也不符合将这些材料作为民俗分析对象的必要条件。
正是因为对经验数据的描述的重视,方法论的应用被搁置在了一旁。而其他国家已经在民俗研究中使用了历史地理学、结构主义、符号学、语言学或是与传播学相关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阿根廷,学者们在研究中也使用了一些方法,如使用民间故事类型的国际索引对民间故事进行分类,或使用“动机”这一概念对于民间叙事进行编目。
就其本身而言,科塔萨尔提出了一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注]Augusto Raúl Cortazar, El carniaval en el folklore Calchlaquí. Buenos Aires: Sudamericana, 1949, pp.248-62.,但就目前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这并不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方法。他提出的民俗概念被限制在农村地区,并且这一概念被预先赋予了某些特点。在他的定义中,民俗由具有民俗性质的其他表现形式汇集而成。科塔萨尔认为,社会事实如果因其特殊性被确立为民俗现象,并被记录下来,就应该对它进行分类以了解它的意义。这种研究方法使得预先假设的有效和不容置疑的民俗概念被强化,同时也阻碍了对该学科研究对象的深入探讨。当我们发现民俗新的表现形式的时候,这种观点既不允许我们接受,也不允许我们扩展已经认识到的丰富现实。这种研究范式只是对已经论证事实的重复论证。
以上所述展示了阿根廷和拉丁美洲民俗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它们提醒我们应该加强我们的学术研究。我没有去关注某个具体的问题,而是渴望去寻找那些我认为会让民俗、尤其是我们国家的民俗研究产生丰硕果实的路径。它们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民俗真的能够满足全人类的基本需求,那么我们应该将这个概念从社会阶层概念中独立出来。
我们需要严格界定这一概念事实及其表现,以便使民俗现象能够在社会现象中具体化,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了解其他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观点,这可以让我们集合所有关于理论、方法和经验问题的努力成果。在研究者之间保持良好的交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获取那些我们参与其中的研究课题的动态,诸如更好地了解人类的某些行为和这些行为背后所传达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