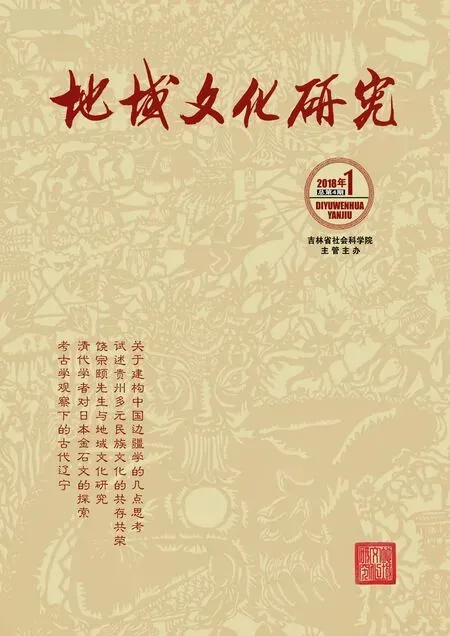清代学者对日本古代金石文的探索
拜根兴
前 言
“上野三碑”是指位于日本群马县的三座古碑,依次为“山上碑”(681)、“多胡碑”(711)、“金井泽碑”(726),其立碑时间相当于中国的初唐至盛唐时代。除《续日本纪》中有创建“多胡郡”关联内容,以及1511年连歌师柴屋轩宗长《东路のつと》中记载《多胡郡碑》之外,18世纪之前似未见其他记载。随着1720年伊藤东涯《盍簪录》著录“多胡碑”,1786年奈佐胜皋《山吹日记》提到“金井泽碑”,1800年松平定信《集古十种》,1818年狩谷望之《古京遗文》两书收录三碑,以及1819年木部白满“三碑考”的问世,人们对此三通碑石才有了一定的认识①参见[日]前沢和之《古代东国の石碑》,东京:山川出版社,2008年。。然江户、明治之际,可能因日本正处社会大变革浪潮之中,以及明治时期奉行“脱亚入欧”国策的缘故,日本学界对此关注有限。相反,这一时期清朝学者对日本的金石文却有着极大的热情,有人收到朋友寄赠的拓片如获至宝,进而撰述跋文发表看法;有人千里迢迢前往实地考察,收集日本所在的资料,编撰日本专门的金石著作,成为当时日本金石学最前沿的研究。清朝学者此一期间对上述“上野三碑”等金石文的研究新意频出,值得探究。然而,此后中国学界对日本金石文的研究趋于停滞。据笔者查阅相关文献,虽然有一些文章隐约提到清朝学者的日本古代金石学研究②金烨曾对日本上代金石文与汉语俗字做过探讨,其中提到“山上碑”中的“黑”字,“多胡碑”中的“弁”字。参氏著《日本上代金石文与汉语俗字》,《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但专论者至今还未看到。笔者力图在现有零星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清朝学人了解研究日本金石文的动机,爬梳清朝学者对日本金石文的探索成果,以就教于诸师友方家!
一、清代学者对日本金石文的关注
众所周知,清朝自雍正时期实行严格的文字狱政策,杜绝民间及官场的任何形式的反清苗头动向。文字狱涉及科举考试以及文人日常活动,使得读书人对现实生活无所适从,进而将笔墨投向遥远的过去。在从事经学考据研究的同时,众多学者涉足金石学领域,金石学因而盛极一时,成为一代显学。①参见陈尚君《贞石诠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31-332页。这一时期在继承此前顾炎武(1613—1682)、叶奕苞(1629-1686)、朱彝尊(1629—1709)金石研究理念与成果的同时,出现翁方纲、王昶、武亿、钱大昕、阮元、孙星衍、陆增祥等一代大师,产出了如《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授堂金石跋》《两汉金石记》《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代表当时最高水准的金石文研究著作。
此一时期的金石学者们还将研究触角伸向同为汉字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且不说1805年刊印的《金石萃编》一书中,金石学家王昶(1725—1806)就收入远在朝鲜半岛的《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其拓片来自学生言朝标所赠)。随后董诰(1740—1818)编撰的《全唐文》中,不仅收录上述碑铭,还收录同样出自朝鲜的《刘仁愿纪功碑》。与此同时,随同朝鲜朝贡使臣来到北京的朝鲜学者金正喜、赵寅永、金命喜等人,频繁和上述金石学者翁方纲、阮元、刘喜海等接触,赠送拓自朝鲜半岛的金石拓片。酷爱金石碑志的上述学者欣喜若狂,金石学家刘喜海最终将收集到的朝鲜金石文编辑成册,并潜心研究,《海东金石苑》八卷得以问世,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朝鲜半岛的金石总集类书籍,广受各界的推崇和赞誉。②参见拜根兴《朝鲜半岛现存金石碑志的现状和展望:以七至十世纪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期。
收集东亚各国的石刻碑志,进而著录研究,成为19世纪中叶以后清朝学者乐于从事的事业。继孙星衍(1753—1818)编撰《寰宇访碑录》之后,一些学者纷纷依据自己的所见,对该书加以续修订补。清同治三年(1865)赵之谦(1829—1884)纂集、沈树镛(1832—1873)覆勘的《补寰宇访碑录》刊印出版。据笔者统计,该书在收集清朝各地新见石刻碑志的同时,还收录有65件朝鲜半岛金石碑志,包括此前金石集中未见著录的《新罗武烈王碑额》《新罗文武王陵残碑》等。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卷三还收录了一通日本金石碑志,即著名的“上野三碑”之一的“多胡碑”;不过,赵之谦依据拓片,著录其名为《日本国片罡绿野甘良三郡题名残碑》③碑铭下题小字,云:“正书。和铜四年三月九日甲寅,考为景云二年辛亥。旧题‘多胡郡碑’,传为日本人平鳞得之土中,后藏朝鲜成氏”。,排列于唐景云二年(711)④(清)赵之谦纂集、沈树镛覆勘:《补寰宇访碑录》,见“石刻史料新编本”(第1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可以看出,赵之谦编撰此书之时,“多胡郡碑”拓片已经流入清朝。清人翁方纲(1733—1818)对其字体曾有过精辟的评论。在《平安馆金石文字》中,叶志铣就是依据翁方纲赠送的双钩本,对“多胡碑”多有考辨⑤道光十九年(1839)叶志铣详细考证“多胡碑”的建立年代、上野国位置所在、日本当时的官制及碑文涉及的其他内容等。。有日本学者依据相关记载,认为“多胡碑”拓片在日本桃园天皇宝历年间(1751—1763)已传入清朝①[日]榊莫山著,陈振濂译:《日本书法史》,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6-7页。,至于具体年份,还有待进一步考论。
1877年,鉴于清朝和日本新型外交关系的建立,清朝派遣外交官前往日本。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东渡日本展开工作。②曾民:《清朝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广州研究》1987年第5期。与此同时,作为使馆工作人员,以书法和金石考据享誉学界,精通历史地理的学问大家杨守敬(1839—1915)亦前往日本。到达日本之后,杨氏利用公务之余暇,与日本各界同仁切磋学问、交流心得。因对金石碑志的眷顾,他特别留心日本的金石文状况,故而多有所得。羁留日本四年后,杨守敬返回清朝,居住于湖北黄州。在此之前,杨守敬曾对上述赵之谦编撰《补寰宇访碑录》颇有看法,并收集新见金石碑志,即“书出,则脱漏宏多,而其人高自标置,不受攻错,故余所得拓本出于赵书之外者,已数百事而未入其录中,自是,有别为《三续》之志”③金石学家罗振玉曾撰《补寰宇访碑录勘误》1卷,就是对上述《补寰宇访碑录》所做的勘校。。特别是杨守敬“庚辰东渡,又得日本诸石刻补入之,归后伏处黄州江滨,十年间绝无所得”。也就是说,杨守敬有心续补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④清人刘声木撰《续补寰宇访碑录》25卷,《补寰宇访碑录校勘记》2卷,《再续寰宇访碑录校勘记》1卷。其中前者续补的主要内容为新见南北朝时期的金石碑志,未见对朝鲜半岛及日本金石碑志的收集补录。可能正因如此,亦成为此后罗振玉编《再补寰宇访碑录》,杨守敬撰《三续寰宇访碑录》的重要原因之一。,除过收集国内新见金石碑志之外,还将在日本所见金石碑志,补录于新著。据笔者统计,杨守敬编撰的《三续寰宇访碑录》一书中,收录日本所在石刻共有61通⑤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八册,杨守敬《三续寰宇访碑录·序》,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单从收录日本所见金石碑志看,就比上述赵之谦所著增加很多。除此之外,杨守敬编著《寰宇贞石图》一书,其中书尾“日本”条目下,收有“多胡郡碑”“释迦佛足迹碑”“修造多贺城碑”三碑拓片照片,并有简单的文字说明。《壬癸金石跋》一书中,则对“多贺城碑”撰写长篇跋文,其虽非本稿论述之重点,不妨抄引其文。跋云:
此“修造多贺碑”在日本国陆奥国宫城郡市川村,村即多贺城废址。碑详四至抵界。额有一“西”字,未详其义,或当时立此碑凡有东西南北四碑,此其西碑也。碑称:神龟元年(当中国唐玄宗开元十二年),按察使兼镇守将军,纵四位上,勋四等大野朝臣东人之所置也。按《续日本纪》(四十卷,前二十卷菅野朝臣真道撰,后二十卷藤原朝臣继绳撰,为日本古六国史之一),神龟元年二月,以大野朝臣东人授从五位上,二年闰正月,授从四位下,勋四等。天平三年(当中国开元十九年)正月,授从四位上。其为镇守将军在天平元年九月,其为按察使则在九年正月。其后,十一年四月为参议,十二年闰三月叙从三位,十四年十一月卒于位。碑合其神龟至天平九年之官位书之,而又遗其十一年为参议,十四年叙从三位,何耶?若以置城之时言之,则又未尝为“勋四等从四位上”也。碑又云“天平宝字六年(当唐肃宗宝应元年),岁次壬寅,参议东海东山节度使,从四位上,仁部省乡兼按察使,镇守将军藤原惠美朝四朝獦修造”也者。按朝獦官衔与《续纪》所载多合,惟天平宝字五年(唐肃宗上元二年)十一月丁酉,以朝獦为东海道节度使,不云“东山”。然记载其所管国有上野、下野,东山地所在上野、下野之中,则书“东山”非有异。又据六年十二月《纪》及九月《押胜传》(大师授从一位,后以反伏诛)并云“从四位下。”不载至“从四位上”。是碑为朝獦自署,不容有误,疑日本史为脱漏也。此碑盖东人筑多贺城于前,朝獦复筑于后,记其始末如此。至其官制,多依仿唐代。日本别有《职源》一书,详其品秩。其书庋在黄州,他日当为匋斋尚书详考之。①参见谢承仁主编《杨守敬集》第八册《壬癸金石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30页。
应该说,杨氏对“多贺碑”的探讨全面深入,在当时实属难得。不仅如此,杨守敬还做了另外三项工作:其一,对此前因各种原因输入日本的中国历代书籍如数翻检查询,并写有详细的跋文考辨,编辑完成《日本访书志》《日本访书志补》《日本访书志续补》三书。其二,协助新任驻日公使黎庶昌收集编撰刻印《古逸丛书》26种,将在日本看到的善本古籍编印出版。而其有关金石碑志的学术研究持续进行,使清朝国内更多的人士了解日本,以及日本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其三,和驻日公使何如璋、黎庶昌等人一起,与日本知名学者诗词唱和、切磋学问,在日本学界引起轰动,成为此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
此后,亦曾东渡日本,和日本学者多有交接,撰有《扶桑两月记》(1901)、《扶桑再游记》(1909)的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1866—1940),在日本公务之余,潜心收集日本金石文,并做过一定的研究。罗氏1896年编撰《再补寰宇访碑录》收录日本各种金石文58件②罗继祖:《罗振玉年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罗振玉曾想利用闲暇,将上述孙星衍、赵之谦,以及严銕桥、缪荃孙等诸家所作“汇为一书”。参罗振玉《俑卢日札》,收入《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9页。,上述杨守敬撰集《三续寰宇访碑录》时曾参考过罗振玉所编。另外,因罗氏曾居住日本长达8年(1912—1919),和日本学者多有交集,如内藤湖南1902年曾托人转送罗氏上文提到的松平定信《集古十种》中的《钟铭记》③金程宇:《〈内藤湖南全集〉补遗》,收入《域外汉籍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38-239页。。而日本友人平子铎岭则寄赠“那须直韦提碑”拓片,罗氏在赞许此前狩谷望之《古京遗文》著录并考证精细的同时,指出:
惟碑首署“永昌元年己丑”,掖斋谓当是“朱鸟四年”,系洗者改作。予按:永昌元年下署己丑,为武周年号无疑,且石上并无改刻之迹。盖日本曾奉唐朔,其国《大阪八幡宫钟铭》,亦署“天宝四年”,是其明证。掖斋谓是改洗,盖以奉唐朔为讳也。
即对该碑“永昌元年己丑”纪年,提出自己的看法;不仅如此,他还以另一出自日本的《大阪八幡宫钟铭》纪年为证,阐明日本学者“洗改说”产生的原因,进一步证明自己看法的正确④见罗振玉《俑庐日扎》,收入“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0页。。
清末民初另一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1849—1917),撰有《语石》一书⑤(清)叶昌炽著,韩锐校注:《语石校注》,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其卷二专列“日本”条目,即论及刘喜海收罗朝鲜半岛金石碑志的同时,还著录四件日本金石碑志。叶氏特别提及上述“多贺城碑”,叶氏潜心研究日本金石碑志整体现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还谈及傅云龙游历日本,编撰《日本金石志》一书,因下文将要论及,在此不赘。总之,叶昌炽对日本金石碑志的现状多有了解。
二、傅云龙撰集《日本金石志》
随着西方列强的东来,清政府逐渐开启对外交流的大门,主动采取措施力图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1887年,清政府举办出国考察游历官员考试,浙江德清人傅云龙(1840—1901)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选派出洋考察。傅云龙先后到达日本、美国、巴西、秘鲁、加拿大、古巴六国游历考察,其中在日本游历考察6个月,从北美返回后又在日本居住5个月,即利用一年时间,最终完成《游历日本图经》等著作。对此,有学者评述曰:
十二位考察官员中傅云龙是最仔细、最勤奋的,也是留下游历著述最多的。他每到一个国家,即收集该国地理、历史、政治、风俗、特产等资料,亲自勘察并绘制各种地图和表格,据以编制图经,仅他一人在游历期间就编写了《游历日本图经》30卷、《游历美利加图经》32卷、《游历英属加拿大图经》8卷、《游历古巴图经》2卷、《游历秘鲁图经》4卷、《游历巴西图经》10卷等。傅云龙边考察边撰写考察报告,并以短促的时间里完成各国图经编写、画表、制图,其紧张辛苦可想而知,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是夜四鼓,笔不得休”、“是夜鸡鸣,草犹未脱”①参见张群《傅云龙其人及其著述》,《河南图书馆学刊》2005年第5期。。
单就30卷《游历日本图经》来说,其中包括天文、地理、河渠、食货、兵制、外交、金石、文学、政事等诸多内容,囊括了当时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堪称了解日本的百科全书。该书卷23—卷27中,傅云龙专列《日本金石志》名号,别具一格,成为《游历日本图经》中最受推崇的撰述内容。对此傅云龙自序云:
往无中国人录日本金石嫥书,翁氏方纲仅跋日本残碑,即所谓“建多胡郡辨官苻碑”者,是实未之残,征信不其难欤?日本人松平氏集古而抚之刊之,然求如狩谷望之之能援古,则百不获一。自诩故实者为之,真面目不一传。云龙非好贾余勇也,同文寖微而欲求弊于后,舍金石其奚为哉……
就是说,傅云龙对中国学者罕有专门从事日本金石文著录研究,缺少这一方面的研究著作,仅有的研究竟多有乖舛深感忧虑;日本学者所做工作在他看来又相当基础,这样致使日本金石文的真实状况不为更多的人所知。因而,他想利用难得的游历机会,从事日本金石文的收集研究。至于如何做?他认为“昔欧、赵录金石目,跋尾成帙,洪适《隶释》有续,尝合一编。云龙既广益集思,依欧赵例,箸跋尾文;复参洪续例,续录所见刀剑。然彼系于工,此重厥文,而草䕌剑无文,时尚无文也。彼重神器,以类聚之,难可分见……”也就是说,傅氏参照宋人欧阳修、赵明诚、洪适金石著作的编撰方式,依据日本金石文的现实情况,编撰《日本金石志》一书。
当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大部头的著作,单凭傅云龙一人之力显然难以办到,期间驻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6)提供诸多便利,并多有襄助。特别是身为黎庶昌使馆随员,喜好古书、醉心金石的贵州人陈矩(号衡山,1850—1939),给予傅云龙无私帮助,明治后期日本汉文学家小山朝宏就对陈矩其人大加赞赏,云:陈矩“客岁随星使黎公驻在我邦,署务余暇,广求金石遗文。时傅郎中懋元奉命游历日本等,亦搜索古迹。衡山大赞其业,出平生所聚,且身抵诸州,勿论破驿荒村,幽壑断港,历揭跋涉,探访殆遍。自丰碑片石,佛塔钟铭,至瓦经函识、古印刀剑、铭款系金石文字者,凡四千八百有奇,汇作《日本金石志》,其好古之笃,气力之厚,真可叹服也”。②转引王宝平《日本游历图经·前言(傅云龙及其〈游历日本图经〉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傅云龙自己亦云:“访古之助,赖贵阳陈氏(矩)力居多,生平友益,极不能忘,矧其受多闻益于海外欤!”①(清)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卷23《日本金石志·金石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就是说,傅云龙编著《日本金石志》很大程度上得到在日公务的好古之士陈矩的襄助,至少可以说,《日本金石志》的编撰,凝结着两人共同的心血和汗水,而陈矩于此贡献实大②有日本学者石田肇撰文《傅云龙的〈日本金石志〉与陈矩》,提及该书的著作权问题。笔者同意王宝平教授的观点,即该书为两人合著更接近事实,其中凝结着两人共同的汗水和心血。参见《日本游历图经·前言(傅云龙及其〈游历日本图经〉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而且,对此书的编撰,无论从收录金石的数量,还是考订的详确,傅云龙均有信心满满之感觉。在《日本金石志·金石年表·序》中,他写道:
日本人西田直养《金石年表》所载五百二十有三种,彼人士多之,然如宇治川摩崖即涅槃经摩崖也,刊于宝龟九年,而列之七年,犹可曰拓本不可辨也矣。远江长福寺钟,天宝七年字不一蚀,而列之六年,似此往往而有。以土著之见闻,安问之岁月,犹难详且精如此,况迫不及审。如云龙之游历,而欲无一舛也?虽然畏难,耻也,以避指摘为口实,尤为耻也。赖同志陈氏矩襄嵬讨力,既志厥文矣!余皆录目入表,有年可纪者,得八百九十有余种;无年可纪者,今亦得数十种,合之印文及刀剑款识,不下四千八百有奇。其质有金有银、有铜有石、有瓦有瓷(如伊势大神宫正印筥以木为之,西田入表,类此所不敢沿)。其文有篆有隶,有飞白,有行有正,有梵有日本文。其年以中国为宗,非沿西田例也!③(清)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卷26《日本金石志·金石年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傅云龙与陈矩的勤勉努力,以及日本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保障了《日本金石志》从收录数量到编撰考订水准的超一流,成为研究日本金石学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对于这部所谓外邦人编著的《日本金石志》,当时日本学者好评如云,上述小山朝宏评价此书云:
曩者,自何乐翁侯著《集古十种》,收古碑钟铭等,然不及十六七。市河宽斋聚金石拓本,自附考证,著《金石私志》五卷,亦止二百余种耳。夫乐翁有土贤侯,世称赅博,宽斋好古通雅,用数十年之力。今衡山以外邦之人,淹留不过二三年,而网罗荟萃,以著斯书,不亦伟哉!
日本文学艺术家石川鸿斋为陈矩做《东瀛访碑图》,其题诗云:“蓬岛千年物象移,徐仙遗迹遂难知。当时竹简今乌有,才剥苍苔读断碑。”其诗后题记曰“衡山陈先生大人求东瀛访碑图,碑在上野国多胡郡,和铜年间所树,乃写其胜概,并题小诗”云云。陈氏将日本学者所做此图带回国内,当时十四位中国学者亦题笺祝贺,足见时人对傅、陈二人作为的推崇和认同④参见杜白珣《陈矩辑〈东瀛访碑图咏〉》,《文物》1979年第11期。,以及编撰此书的非凡影响力。上述《语石》的作者叶昌炽对此亦多有评论,云:(傅云龙)“网罗搜讨,做《日本金石志》五卷。内《印文》一卷,《刀剑款识》一卷,其余分前后两卷,前目九十四种,后目百廿四种,又附录十六种,皆有跋尾。又仿欧、赵目录之例,有年可记者八百九十有余种,录其目为表。考日本金石者,于此叹观止焉!”⑤(清)叶昌炽著,韩锐校注:《语石校注》,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无疑,上述评述均符合实际,道出傅氏著作的真实价值。
虽则如此,笔者以为从学术研究及史料的珍贵来看,傅氏《日本金石志》五卷,应该是《游历日本图经》一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为什么如此?其一,书中的其他内容,如实业、教育、政府运营等,同时期出现的著作中均有大同小异的体现,如黄遵宪(1848—1905)《日本国志》40卷(1887),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10卷(1884),叶庆颐《策鳌杂摭》8卷(1887),陈家麟《东槎闻见录》4卷(1887)等。其二,作者的编辑方式亦与其他卷次有明显差异,即第23—卷27卷单独以《日本金石志》命名,并题有“单行五卷”字样,足见作者编撰当时就有将其独立成书的规划,凸显编撰日本金石类总集的必要性。其三,迄今为止,傅云龙、陈矩两人共同编撰的《日本金石志》,从收录金石文数量上看,囊括了当时能够看到所有的日本金石文,并分门别类、条分缕析,撰写题跋论考,堪称日本金石文的百科全书;从研究角度看,作者对所见金石碑刻的诠释探讨,迄今仍然是深入了解日本金石文不可或缺的最详细并具备权威性质的著作。当然,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日本金石志》中收录了日本7世纪末、8世纪初出现的“山上碑”“多胡碑”“金井泽碑”,即著名的“上野三碑”,并有较详细的释文。
三、关于“上野三碑”的著录研究
(一)书体问题
有关“上野三碑”的书体,上述清人学者杨守敬认为“《和铜题名》,最为高古,神似颜鲁公”,“书法雄古,颜鲁公近之”①(清)杨守敬著,谢承仁编:《杨守敬集》第八册,《学书迩言》,《激素飞清阁评碑记》卷3,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作为当时顶尖的书法鉴赏家,杨守敬认定“多胡碑”书体接近颜体,无疑切中要害,只是杨守敬并未进一步说明。而杨氏所说“多胡碑”书体“接近颜体”,应该理解为颜体对此前北魏书法的吸纳发展,并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只是七八世纪当时远离京城的上野地区,其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接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外来移民在文化的传承与表现方面扮演何种角色?其与土著之间是否有一定的文化差异?这些显然均需要冷静并专业化探讨。
田渊保夫从日本书道史发展角度,论证“上野三碑”的书体文化渊源,认为当时相当数量的归化人居住于上野国甘泉郡一带,他们通过海路传来经过朝鲜半岛消化之后的中国北魏文化风尚,其中也带来魏碑所体现的书法风格②[日]田渊保夫:《书道史上からみた“上野三碑”》,《立正大学文学部论丛》第75辑,1983年。。“上野三碑”制作时间前后经过40余年,但碑文书体却表现出难得的相似。追溯其原因,其与此一时期朝鲜半岛移民频繁到达日本居住,特别是百济、高句丽灭亡,新罗与日本交往的频繁,致使朝鲜半岛移民蜂拥而至③[韩]李根雨:《关于日本列岛上的百济移民》,《韩国古代史研究》第23辑,2001年;李婷:《流入日本的高句丽百济移民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度硕士学位论文。,东山道上野国一带成为渡来人重要的移居地,其间身怀绝艺传承北魏书法技艺的书者渡来,并经过他们的再度消化创造,造就了这一时期日本书法碑刻文化的独特风格。对日本书法多有研究的陈振濂先生亦认为“上野三碑”书法有北魏碑刻特点,云:“金井泽碑文、笔迹书风,山上碑及多胡郡碑似为同一人笔迹,颇多相似点。其与北魏石门铭、郑文公碑书风相似”④陈振濂编著:《日本书法通鉴》,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只是其并未提及与朝鲜半岛渡来人的关系。王勇教授亦指出“此碑虽然成于奈良初期,但书风依然六朝传统,还看不出唐朝书法的明显投影。不过书者已经参透六朝书法的奥秘,运其气韵驾轻就熟,象征着飞鸟时代以来修炼六朝书法已近功德圆满,预示着破旧立新时机已经成熟。”①王勇:《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44页。即从另一角度解释多胡碑书法风格形成与发展。
众所周知,“上野三碑”无论从制作形状、石料的选择,以及书体本身,均与6世纪朝鲜半岛某些碑刻保有相似或相同的特点。如果仔细对比其与新罗真兴王管境巡狩四碑,其书体的相似度似更高。鉴于此,前沢和之②[日]前沢和之:《古代东国の石碑》,东京:日本山川出版社,2008年。、田渊保夫,还是亦有研究论著发表的东野治之③[日]东野治之:《上野三碑》,《日本古代金石文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2004年。等学者,均通过大量的史实及缜密的论证,认为“上野三碑”的制作与前来日本的朝鲜半岛渡来人有关。无疑,笔者同意上述学者的看法。而从中国古代增设新的地方行政机构所具备的条件看,某些地方人口剧增,原行政机构不足以很好的行使管辖状况下,往往成为增设新的地方行政机构(州、郡或县)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一点看,东山道上野国增设多胡郡,以及相邻地区扩大交通网络、建立新的驿站,证实当地人口的增多,地域经济人文规模扩大的事实。而多胡郡辖下地名,如织裳、韩级等似与朝鲜半岛关联的地名,其亦可说明问题。对此,应该整理现有研究,发掘新的资料,做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清人学者对“多胡碑”的著录研究
具体到日本设立多胡郡及其建立多胡碑,《续日本纪》卷5记载云:
(和铜)四年春正月丁未,始置都亭驿。山背国相乐郡冈田驿,缀喜郡山本驿,河内国交野郡楠叶驿,摄津国嵨上郡大原驿,嵨下郡殖村驿,伊贺国阿閇郡新家驿。
二月辛丑,从四位下土帅宿弥马手卒。
三月辛亥,伊势国人矶部祖父、高志二人赐姓渡相神主。割上野国甘良郡织裳、韩级、矢田、大家,绿野郡武美,片冈郡山柰等六乡,别置多胡郡。
就是说,因为多胡郡的设立,当时政府才决定在当地竖立多胡郡碑。另如上所述,“多胡碑”16世纪初为人发现,后来逐渐受到关注。其拓片18世纪流传至中国,引起当时著名金石学者翁方纲、叶志铣、杨守敬,以及前往日本考察游历的傅云龙、陈矩等人的注意。“多胡碑”铭文标点断句如下:
弁官苻上野国片冈郡、绿野郡、甘良郡并三郡内三百户,郡成,给羊成多胡郡。和铜四年三月九日甲寅。宣左中弁正五位下多治比真人,太政官二品穗积亲王,左太臣正二位石上尊,右太臣正二位藤原尊。
对此,清人叶志铣依据翁方纲所赠,其可能是来自朝鲜学者的“多胡碑”双钩拓本,详细诠释探讨多胡碑。云:
右日本国残碑凡八十字。按:碑文“和铜”为元明天皇建号,“四年”当唐睿宗景云二年,岁纪辛亥也。日本域地,内有五畿,外有七道。上野国为东山道所属八国之一,本名上毛野,在渡濑河之西,凡隶郡十四,片冈、甘良、多胡、绿野皆其所属。“甘良”,《志》作“甘景”。“中弁”之职有左右之分,当正五位下,秩为朝议大夫,在国为重职,择华族中有才名者居之,执行宫中之事。“太政官”始设于天智天皇十年,至孝德天皇时改为“太师”,后仍复原称,为文官之至极,助理万机。“左右大臣”设于孝德天皇时,奉行诸政,在太政之次。“亲王”以国后子改立者,初叙三品。妃子初叙四品。任国守事者,维上野、上总、常隆三国有之,他国则否。“正二位”秩为特进上柱国。“多治比”岛名。“真人”“藤原”皆赐姓,“石上”亦姓也。此文首尾残缺,似系题名。书势雄伟,类上皇山樵《瘗鹤铭》字。相传日本人平麟(沢田东江)得于土中,拓本流入朝鲜,为成氏(成大中)所藏。
就是说,首先是日本人沢田东江赠送多胡碑拓本与朝鲜人成大中,成氏时为前往日本的朝鲜通信使;成大中回国后将拓片赠与前往清朝的燕行学者某人,这位燕行学者到达清朝后又将拓本赠与金石学家翁方刚;翁氏则将拓片转赠叶志铣①(日)杉村邦彦《多胡碑の朝鲜·中国への流传につぃて》,收入东野治之、伊藤信主编《古代多胡碑と東ろアジア》文集,东京:山川出版社,2005年。,叶氏如获至宝,潜心研究。同治十年(1871),杨守敬在自己的著作中全文转录叶志铣的跋文,并未做进一步的探讨。而傅云龙编撰《日本金石志》一书,其在抄录日本狩谷望之著录文的同时,指出上述叶氏题跋之误,并在一些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此碑盖刻当时符文也。按:碑云九日甲寅,则辛亥为六日,碑、史相差三日。“给羊”字不可读,俗传羊大大之事,不经甚矣!蒙齐曰:应做“半”意粗可通。然文理不稳,不如阙疑之为胜也。“太政官”即知太政官事,庆云二年九月纪云:诏二品穗积亲王知太政官事是也。石上尊麻吕公,藤原尊不比等公也。尊训美古登,古时尊重其人之称。谷川淡斋误以为“朝臣”之省者,可笑矣!二公官衔亦皆与《续纪》合。蒙齐曰:多治比真人,三宅麻吕也。三宅麻吕为左中辨,《续纪》不载,然位阶适合,亦后为左大辨,则或其人也。
云龙按:碑在东山道群马县上野国多胡郡,高三尺九寸,宽一尺九寸。正书六行,第一、第一第二两行□十三字,三行四行五行□十四字,六行十三字。《金石年表》谓之多胡郡碑,今依狩谷箸目。此碑曾流传中国。叶氏双钩刻本翁氏方纲跋云“可与樵山《瘗鹤铭》并峙”诚重之也。呼为日本残碑,实未之残。和铜四年当唐太极元年。“冈”作“罡”,“寅”作“寅(异体)”,“尊”作“尊(异体)”,“穗”作“穂”,它碑字体往往同此。②(清)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卷26《日本金石志·金石年表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可以看出,傅云龙十分了解当时中日学界研究动态,他对多胡碑的一些看法,以及对此前研究成果的指责订正,应该是当时学界最前沿的研究之一。而“多胡碑”文涉及问题,在上述叶志铣、狩谷望之、傅云龙等人的研究中均有体现,进而成为此后日本学界研究的重要基础。
四、清代学者醉心日本金石文的原因
18世纪乾嘉学派掀起考据学问之后,金石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众多知名学者参与其中,产出大量流传后世为人称道的金石学著作。与此同时,学者们将研究的触角伸向更为广阔的边疆地带及周边国家地区,丰富了金石学的研究内容,促进带动了周边国家地区金石学研究的深入。
那么,是什么契机促使清朝学者扩展研究范围,对周边地区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地的金石产生兴趣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从乾嘉学派金石考据学的肇启,到咸丰、同治之时,由于研究人员的持续投入,金石学关联的诸多问题均已涉及,新的金石文的出土面世有限,金石学著作的重复或炒冷饭现象时有出现。这样,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势在必行。其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东亚国家特有的朝贡册封体系的逐渐瓦解,维系数百年乃至千年的宗藩关系岌岌可危,清王朝无论是东南海疆,还是西北陆域,乃至东北数百年封禁之地,均出现此前不曾有的危机,清廷采取措施充实边疆,人们开始不同程度的关注遥远的边境地带,那里不为人知的金石碑志因此得以面世,著名的好太王碑就是一例。而其他金石碑刻也间有发现,这些由于有异域人士参与研究广受关注,进而吸引清人金石学者的注意力,并投入到新的研究领域。第三,国门洞开,和周边国家的来往增多,进而也为醉心金石的清朝学者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且不说在此之前,随朝鲜朝贡使臣前来的朝鲜学者赠送朝鲜半岛所在金石碑志拓片,扩展了这一时期金石碑志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内容,研究朝鲜半岛金石碑志划时代著作《海东金石苑》得以问世;其他金石著作中的朝鲜金石也引起更多研究者的兴趣。而明治维新后,清朝与日本间逆向交往增多(此前文化虽然呈双向交流样态,但中国文化流入日本无疑是主流),双方文化双向交流趋于正常,但师生地位的互换却成为事实;不仅如此,前往日本找寻中国文化遗存成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这种状况随着留学日本的热潮,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初。第四,这一时期日本金石文著录研究,日本本土无论从人员投入,还是研究产出,均呈现相对薄弱景象,这就为清朝金石学者开辟新领域、探讨新问题提供了可能。上述翁方纲、叶志铣、刘喜海、赵之谦因风云际会,接触到少量日本金石文拓片,进而精心考释,做过不同程度的探讨。随着19世纪80年代之后中日实质外交关系的建立,从事金石研究的清人学者有机会到达日本,开始了他们非同寻常的日本金石文收集研究之旅,杨守敬、傅云龙、陈矩等人,以及此后的罗振玉,是当时研究日本金石文最具代表的人物。他们的日本金石文著录研究,特别是傅云龙《日本金石志》撰述,对日本金石学研究来说,无疑是具有里程碑的重要地位,应该引起中日研究者的注意。
总之,19世纪80年代之后,清朝学者对日本金石文的编撰研究,体现出这一时期金石学者研究视野、领域的拓展,研究内容的多样化,周边地域国家的金石文统统纳入他们的研究范围。当然,周边地区国家本土学者的研究,应当是这种研究的基础。虽则如此,这使得东亚各地的金石文字,亦成为组成东亚文化圈举足轻重的必备要素之一①日本西嶋定生教授提出东亚文化圈组成的四大要素有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制度。台湾大学高明士教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古代科技。参见高明士《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台北:乐学书局,2003年,第255-265页。笔者认为,从金石碑刻在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历史、普及程度,以及迄今为止流布研究延续不断看,将其作为一种新的要素补充进去未尝不可。当然,对此还应做进一步的研究。另外,日本学者平势隆郎以东亚册封体制与龟趺碑为题,探讨中国周边国家的“中华观”。参见平势隆郎《东亚册封体制与龟趺碑》,收入高明士主编《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政治法制篇》,台湾大学历史学系,2002年。。清末民初叶昌炽《语石》一书,纵论这一时期金石学研究,涉及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的金石文,其亦可说明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