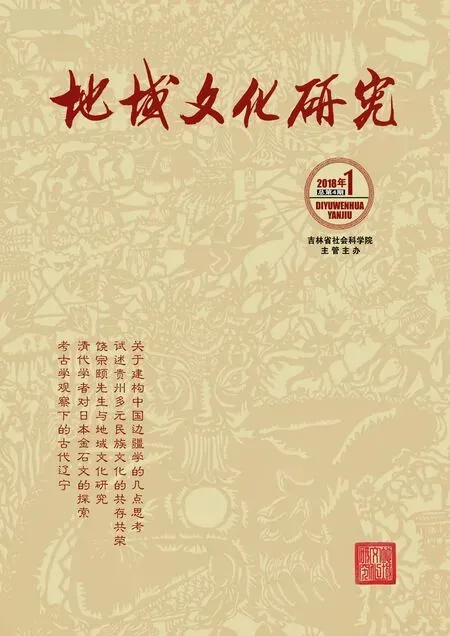明末至雍正朝改土归流之前云贵土司地区的法治
方悦萌
一、明末至“三藩”叛乱结束时的云贵土司地区
明末改朝换代的战争,给云贵土司地区造成极大的破坏,这一情况延续了很长的时间。顺治十五年(1658),云南官吏王弘祚上奏朝廷的《滇南十议疏》,描述了明末战乱以来云贵地区极度凋零的情形。他说:“无艺之征派,每岁加至十余倍,遐荒赤子,皮穿见骨。”①(清)王弘祚:《滇南十议疏》,道光《云南通志》卷203《艺文志·杂著七》,云南省图书馆藏本。所见田野中唯有老弱者耕种,青壮年则被抓丁参加战争,各地的百姓可说是“性命悬于锋镝,青磷白骨,号雨悲风”②(清)王弘祚:《滇南十议疏》,道光《云南通志》卷203《艺文志·杂著七》,云南省图书馆藏本。。云南距离都城遥远,官府的管辖十分松懈。一些官府甚至“趋利如骛,视民如仇,小民疾痛疴庠,置若罔闻”③(清)王弘祚:《滇南十议疏》,道光《云南通志》卷203《艺文志·杂著七》,云南省图书馆藏本。。百姓最痛苦之事,一是官府无尽的摊派,二是人口无端被抽调,“翘首循良抚绥,不啻救焚拯溺”④(清)王弘祚:《滇南十议疏》,道光《云南通志》卷203《艺文志·杂著七》,云南省图书馆藏本。。明代云贵地区凡设置土司的地区,皆奉命自耕自食,上缴官府的钱粮称为“差发银”,通常较汉族编户为轻。但自战乱频发以来,因法纪长期松懈,叛乱之军又随意摊派,“远者派金以养贼兵,近者派人力以驱争斗”⑤(清)王弘祚:《滇南十议疏》,道光《云南通志》卷203《艺文志·杂著七》,云南省图书馆藏本。。各地的土司及其子民因此财力交困,甚至生存都有困难。王弘祚建议普遍审查各地土司履行职务的情形,恢复原先规定的做法,即各地土司照常管理子民,应该交纳的“差发银”仍然交纳,彻底废除一切苛派,如此则“庶土司安,百姓亦安矣”。①(清)王弘祚:《滇南十议疏》,道光《云南通志》卷203《艺文志·杂著七》,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顺治十七年(1660),云贵总督赵廷臣前往晋宁州(今云南晋宁)等处催办粮草。他自曲靖府启程,沿途经过马龙、易隆、杨林、板桥等地,亲眼看到各地的穷苦百姓菜色鸠形,他采集野菜、挖掘蕨根充饥。在道途的河沟、寺庙等处破屋以及山路和田野,随处可见饿死的百姓。甚至听说有母食其子女、子女抛弃其病父的惨状,“闻不忍闻,见不忍见”②《云贵总督赵廷臣揭报请催解部拨协饷折》(顺治十七年二月),载《明清档案》第36册。。
从顺治十六年(1659)吴三桂受命镇守云贵地区,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三藩之乱”被朝廷平定,吴三桂盘踞云南的时间长达24年。在统治云贵地区期间,吴三桂对云贵地区土司的处置,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吴三桂平定云贵地区前后为第一阶段。自清军攻入云南,云贵地区的一些土司发动叛乱,这些叛乱被吴三桂先后镇压,并改设了流官。乾隆四十五年(1780),就史书是否应记载吴三桂擒获南明皇帝朱由榔的问题,朝廷曾发生争议。有馆臣提出:“‘三患二难之议’发自三桂,即后之进兵,檄缅甸驱李定国,降白文选,皆出自三桂之筹画,其功固不可泯也。”③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80《逆臣传·吴三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46页。即认为吴三桂攻取云南的功绩不可泯灭,宜于史载存之。但也有馆臣不同意其看法,认为:“然其筹画岂实为我国家哉?彼时已具欲据滇黔而有之之心。”④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80《逆臣传·吴三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46页。笔者以后论所言为是。吴三桂率兵平滇,已暗具割据云贵地区的祸心,他处理土司造反之事岂能无私?
吴三桂统治云贵地区至“三藩之乱”结束为后一阶段。吴三桂据有云贵地区,暗中拉拢各地的土司,甚至还纵容土司违法乱纪,对朝廷的法纪造成严重的破坏。吴三桂如此行事,目的缘于“益欲揽事权,构衅苗蛮,藉端用兵不休”⑤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80《逆臣传·吴三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36页。。吴三桂盘踞云贵地区后,因眼疾发作,曾上书请辞去云南总管之职。云贵总督卞三元等官吏竞相奏报,称“谓苗蛮叵测,非任三桂,恐边衅日滋,请敕仍总管”⑥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80《逆臣传·吴三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37页。,建议朝廷对吴三桂尽量挽留。以后吴三桂准备造反的情况渐明,康熙帝毅然决定撤藩。吴三桂害怕阴谋暴露,假意上疏请求移藩东北。朝廷为此争论不休,甚至有廷臣说云贵地区非吴三桂镇服不可,由此可见吴三桂的障眼法影响之大。
吴三桂决然发动叛乱,并假意以为明朝永历帝复仇为号召。多年来受吴三桂拉拢的土司纷纷参加叛乱,气焰十分嚣张。吴三桂又在云贵地区滥征士兵,以各种官秩封赏土司,“伪总兵、副将、伪参、游、都、守遍及诸蛮”。⑦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80《逆臣传·吴三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37页。受封为“将军”“监军”的土司“狂逞无忌”。以后吴三桂的叛军失势,跟随叛乱的土司又先后反正,既有震慑于朝廷雄威方面的原因,也反映了存在一些土司被吴三桂裹胁或诱惑参加叛乱的情形。但总体说,一些土司积极参加吴三桂的叛乱活动,则是不争的事实。
《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说:“三藩之乱,重啖土司兵为助,及叛藩戡定,余威震于殊俗。”在吴三桂叛乱的初期,云南、贵州、湖南等省先后被叛军攻占,吴三桂又以滇茶交易西藏的马匹为诱饵,暗中联络西藏的达赖喇嘛。同时勾结一些山地民族反叛,吴三桂在云南私自铸钱,增加赋税,大肆搜刮,为叛乱提供大量资金,“以饵党羽,势日猖獗”①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80《逆臣传·吴三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40页。。吴三桂死后,叛军在贵阳拥立吴世璠继位。清朝平叛的军队到达曲靖府,准备在嵩明州与叛军决战。吴世璠率领万余叛军出战,“列象阵,离城三十里拒战”②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80《逆臣传·吴三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44页。。史载称叛军距城30里布列象阵,可见云南南部的土司率领象军参加了叛乱。在本次战役中平叛的军队五战五胜,在阵上斩杀叛军将领胡国柄、刘起龙以及伪总兵等九人,“贼众自相蹂躏,死者枕藉”③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80《逆臣传·吴三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44页。。所述被杀的伪将军胡国柄、刘起龙与伪总兵九人,均为参加反叛的土司头目。
在吴三桂发动的反叛中,一些土司主动或被动地参加叛乱。清朝的应对之策是积极分化瓦解,力求将追随吴三桂的土司争取过来。康熙帝为此颁诏:“自逆贼煽乱,所在官民多被诱惑,陷身贼中莫能自拔。朕已洞悉情形,屡颁敕谕,广示招徕,开其自新之路。”④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80《逆臣传·吴三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42页。吴三桂的叛乱被平定后,任职云南的官吏蔡毓荣,秉承朝廷的旨意公布告示,规定云贵地区的土司凡是解送参加叛乱的人员30名或八旗军队的逃兵50名到官者,官府允准晋职一级;解送的人数若翻倍,则“递加升赏”。凡土司解送的犯罪之人,八旗军队的逃兵照例归旗,其余人员可免其死罪,⑤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80《逆臣传·吴三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45页。这些规定对瓦解叛军起到积极的作用。
吴三桂纵容并煽动土司参加叛乱,引发了严重的连锁反应。“三藩之乱”平定后,鄂尔泰至云南调查以后指出:叛乱虽被平定,但云贵地区土司严重违法及无视官法存在,主要是自恃拥有“土官”“土目”等名号,相互争斗劫杀,汉族百姓受其摧残,少数民族亦被荼毒,“此边疆大害,必当剪除者也”⑥《云贵总督鄂尔泰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奏事》(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二,云南大学图书馆藏。。鄂尔泰的奏疏还说:云南地区的土司大都属于豪强势力,“苗众”皆听其指挥,这些邪恶势力在各地“残暴横肆,无所不为”。如果土司懦弱无为,下属之土官或土目为害尤其严重。这些人眼中既无府州官府,亦无督抚等朝廷大员。若事情闹大必须呈报官府,或欲求得事件的解决,相关的土官或土目则赴官府行贿打点,甚至捏造事实以求结案,“上司亦不深求”。而官府于刁抗不法、命拘不至者又无可奈何,“唯有隐忍了事”。贵州地区的土司势力单薄,不能有效管辖众人,“故苗患更大”。一些地方“恶苗”有烧杀劫掳,“拿白放黑”的传统,以之为获财的生计。亦有直接至城边捆百姓子女,明说于某处勒令取赎者,地方文武官员则视之为常态,“唯隐忍了事”。受害者虽经赴官府控告得到受理,但凶犯仍不可能抓获。“而原告原报并若干证人等,反被拖累至死。”⑦《云贵总督鄂尔泰为恭谢圣恩、敬陈愚悃奏事》(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二,云南大学图书馆藏。可见土司、“恶苗”严重违法的程度,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广西地区土司势力之猖獗,与云贵地区相比并无差别。雍正二年(1724),广西提督韩良辅在奏疏中说:广西土司之昏愚贪暴与所属子民之困苦颠连,可说是历来如此,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广西土司的职务世袭,子弟多不读诗书,继任以后其所为仍同于前辈。兼之下属的土官或土目为非作歹,习惯于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一些地方苛捐杂税众多,职务承袭须纳税,协助办理须纳税,丧则吊奠须纳税,殡葬入土须纳税,婚姻娶妻须纳税,酬谢亲友须纳税,甚至还债赎田也须纳税。若当事人不照办,抄杀之祸随之而至。“其他荼毒蹂躏之暴尤指不胜屈。”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谕旨汇编》第三册,《广西提督韩良辅奏陈抚绥边民劝惩土司折》(雍正二年八月十三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雍正三年(1725),广西巡抚李绂上奏疏说:“臣查广西猺獞从前素称淳朴,自甲寅(康熙十三年)、乙卯(康熙十四年)以后,地方大吏专事姑息,瑶、僮之凶夷遂渐无所忌惮,而肆行劫夺。臣至粤时稽查旧案,有劫掳大盗而十年、五年未追究者,致使良善之民无所赴诉。”奏疏还说平乐府修仁县的土司“跳梁尤甚”,甚至攻掠邻近的村寨,聚众抗拒官兵的抓捕,使百姓不能外出耕种田地。同年,广西提督韩良辅上奏,称贵州安笼、云南的广罗与广南、广西西部的泗城、镇安等处营盘,为三省交界之地。其地山林绵密,地域广阔。侬人、仲人等少数民族聚居于此,经常与邻省发生争执,当地土司“辄互相仇杀不已”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谕旨汇编》第三册,《广西提督韩良辅奏承整饬滇黔粤西三省界地营汛以绥地方折》(雍正三年五月十三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也应指出,云贵地区的土司中也有一些人顺从朝廷,甚至参加官军对吴三桂叛乱的军事行动。据记载,官军攻下遵义、安顺、石阡、都匀、思南等府之后,于永宁州打败叛军,随后追至铁索桥一带,“土司龙天祜、沙起龙、李廷试各率属助战,筑盘江浮桥以济师”③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80《逆臣传·吴三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43页。。清军攻据北盘江西坡地区后,分路进行搜索,“土司安胜祖等相助协剿”④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80《逆臣传·吴三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43页。。一部分叛军逃往广西方向,“总兵李国棵、土司依朋合围于西板桥”⑤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80《逆臣传·吴三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43页。。但总体来看,顺从朝廷并参加征讨吴三桂的土司仅为少数。
在吴三桂统治的云贵地区,社会数十年间基本上停滞不前。云南官吏蔡毓荣撰写的《筹滇十疏》称:在吴三桂统治的时期,云贵地区的百姓不仅遭受加粮、征兵之苦,还经常被驱赶上阵面临锋镝之灾,“播虐万状,民不胜其苦”。吴三桂发动叛乱后,云贵百姓辗转沟壑者竟达总数的一半。至平叛官军进入云贵地区,百姓又被迫参加筑垒修壕或列营布栅。城郊、道路都变为战场,田地满目榛芜,仅堪牧马放羊。云南、贵州两省之间的驿路阻碍难通,沿途难见桑麻鸡犬。吴三桂兵败叛军逃窜,所过随意杀害百姓、纵烧房屋,甚至掳掠百姓的子女,其状“惨蔽天日”。以后叛乱平定,云贵地区“所余者荒丘蔓草,白骨青磷”⑥(清)蔡毓荣:《筹滇十疏·筹滇第二疏》,载康熙《云南通志》卷29《艺文三》,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三藩之乱”与平叛战给云贵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并长期未能恢复。雍正四年(1726),时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到云南的东川地区巡视。他从贵阳出发,经过威宁至东川地区,据他说沿途360里大致是人烟俱无,亦无鸡犬之声。每隔30余里,仅见负责治安的士兵二三人及数间茅屋。“但所见田皆蒿莱,地尽荆棘,耕种不施,渔樵绝迹。”⑦《云贵总督鄂尔泰为敬陈东川事宜奏事》(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二。一路上唯见近山岭森林茂密,荒芜的土地万顷相连。鄂尔泰感叹“若取用皆为良材,如垦治则皆为美产”⑧《云贵总督鄂尔泰为敬陈东川事宜奏事》(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二。。他认为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所经之地靠近“凶夷”,百姓不敢居住,官府也置之不问。鄂尔泰询问为何近城数十里内的耕地也被荒芜,官府推托说是因受附近乌蒙土司的威胁,而真相则是“地方有司之不用心也”①《云贵总督鄂尔泰为敬陈东川事宜奏事》(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二,云南大学图书馆藏。。
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违法的除土司外,在一些未曾设立土司的地区,“夷霸”“生苗”作乱的情况也很严重.为回答鄂尔泰关于苗疆应否开辟的问题,贵州官吏方显说:“生苗不籍有司,且无土司管辖。”②(清)方显:《平苗纪略》,清同治武昌刻本。“生苗”盘踞的地区治安十分混乱。官民从湖南进入贵州,经过贵州进入云南或广西,都必须绕道而行,不敢从“生苗”盘踞的地区经过。进入土司地区之汉人中的“奸民”,若犯法多窜入“生苗”之地,官府不敢过问。“生苗”地区盛行弱肉强食,弱者饱受欺凌而控诉无门。“生苗”又经常外出,掳掠汉地百姓的财物和人口,“此黔省之大害”③(清)方显:《平苗纪略》,清同治武昌刻本。。广西巡抚孔毓珣则说:广西地区为瑶人、僮人相杂处,“瑶人性颇驯良,亦知遵法”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谕旨汇编》第三册,《广西巡抚孔毓珣为剿除凶獞奏事》(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僮人有良善者纳粮当差,原与百姓无异”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谕旨汇编》第三册,《广西巡抚孔毓珣为剿除凶獞奏事》(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但一些居住山势险要之处的僮人,“不务生业,为匪作奸,绳以严刑,方知警惧”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谕旨汇编》第三册,《广西巡抚孔毓珣为剿除凶獞奏事》(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孔毓珣指出这些人“劫夺良民、聚众拒捕”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谕旨汇编》第三册,《广西巡抚孔毓珣为剿除凶獞奏事》(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主要原因是官府“历年姑息太过,以致养成党羽”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谕旨汇编》第三册,《广西巡抚孔毓珣为剿除凶獞奏事》(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以致酿为长期的祸害。
云贵总督高其倬说:云南地区“不籍有司、且无土司管辖”的“夷霸”,可称为“野贼”。他又说:“云南历来野贼头目,平时皆居元江、新平之间,若一旦生事官兵剿捕,野贼遁入威远土州及普洱茶山等处。”⑨(清)高其倬:《筹酌鲁寇山善后疏》,载道光《云南通志稿》,云南省图书馆藏本。在遭受“野贼”侵扰的地区,地方土司向百姓征收保护费,每年都必须交纳,甚至所产井盐也递日收税,经过的商队则被按驮收银。一些土司强住“倮民”之家,随意支使“倮民”,强迫其供应饮食。待征讨的官军到达,“野贼”早已得知消息逃走,“查拿不易,剿捕更难”⑩(清)高其倬:《筹酌鲁寇山善后疏》,载道光《云南通志稿》,云南省图书馆藏本。。云南的元江、新平等地,普遍流行讨保之风勒索之风。土司、土目每年向百姓成千上百收取“年例钱”,其随从也乘机勒索,下乡一次可各得三四十两银子,称为“鞋脚钱”。“利之所在,趋之若鹜。”11(清)高其倬:《筹酌鲁寇山善后疏》,载道光《云南通志稿》,云南省图书馆藏本。云南鲁魁山的“恶夷”,在各地“夷霸”中最为猖獗。云南布政使李世昌的奏疏称:“鲁魁夷倮性顽,种别从来不入版图。”《清史稿》也说:“鲁魁山者,自国初为盗薮,夷倮杂处,推杨、方、普、李四姓为渠。有方景明者,挟倮夷掠元江。”12《清史稿》卷291《高其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云贵总督高其倬遣兵进讨,擒获方景明并消灭“倮夷”几百人,经奏准朝廷,官府在鲁魁山、普洱等地驻兵,在威远地区进行改土归流,鲁魁山“夷倮”严重违法的情形才得以改变。
由此可知,雍正朝在云贵土司地区进行改土归流,既是针对严重违法的土司,也是针对违反朝廷法治规定的“夷霸”与“生苗”。雍正朝在云贵土司地区施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地区土司、“夷霸”与“生苗”严重违法乱纪、阻挠朝廷的管理与边疆开发的问题,雍正朝改土归流的目的,是将上述地区彻底纳入法治管理的轨道,以服从深入经营及积极开发边疆地区的目标。
二、“三藩”叛乱结束至雍正朝改土归流以前云贵土司地区的法治
在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以前,雍正帝对云贵地区的土司、“夷霸”违法横行的情况有所了解,他在颁布的诏书中痛斥了这些不法行为,同时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百姓表示同情。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颁诏晓谕四川、陕西、湖广、云南、贵州等省的官府:
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朕心深为不忍。然土司之敢于恣肆者,大率皆汉奸为之指使。或缘事犯法,避罪藏身;或积恶生奸,倚势横行。此辈粗知文义,为之主文办事,助虐逞强,无所不至,诚可痛恨。嗣后督抚提镇,宜严饬所属土官,爱惜土民,毋得肆为残暴,毋得滥行科派。倘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经发觉,土司参革,从重究拟,汉奸立置重典,切毋姑容宽纵。①《清世宗实录》卷20,雍正二年五月辛酉条,日本东京大藏株式会社影印本。
在诏书中,雍正帝指出土司敢于放肆横行,离不开“汉奸”的挑拨与教唆。这些外来移民中的不法之徒粗知文义,为土司主文办事,却教唆土司为非作歹,“无所不至,诚可痛恨”。他命令相关各省的督抚提镇,当饬令所属土司令其爱惜子民,不得滥行摊派。若饬令之后仍有再犯,土司必被参革从重处分;对挑唆土司犯法的“汉奸”也将严惩不贷,决不姑息。上述诏书表明雍正帝认识到“汉奸”与土司勾结,是造成土司地区法纪混乱、百姓遭受荼毒的重要原因,决心通过整顿法治的办法改变这一现状。至于雍正帝对受土司欺压的百姓表示同情,也不能简单归于官样文章,实则是清朝统治者具有人本主义思想的表现。在其后施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过程中,雍正帝多次诏令认真调研及从长计议,提醒讲究策略尽量减少损失,务必以实现长治久安为目标,既表明清廷期望通过改土归流对土司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愿望,也反映出当事者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本主义思想。
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颁诏书给户部:“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倘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唯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②《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乙亥条。规定以后南方各省凡有可开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③《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乙亥条。,“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④《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乙亥条。。雍正帝的诏书反映了他真实的意图,即创造条件开垦包括土司地区在内各地荒芜的土地,以满足内地人口急剧增长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改土归流彻底解决土司违法乱纪的问题,切实保证朝廷能支配土司地区的土地等资源,乃成为朝廷的一项重要决策。鄂尔泰就任云南巡抚,对云贵土司地区进行了详细调查。在奏疏中他强烈谴责违法土司的肆意横行,并说乌蒙土司每年向朝廷缴纳的税银仅300余两,向子民收取的数额竟高达十倍乃至百倍。土司在管辖地区“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①(清)魏源:《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纪·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小派以钱为单位收取,大派则直接征收银两。土司若结婚,子民三年不敢娶媳妇,子民若被土司杀害,“亲族尚出垫刀数十金,终身不见天日”②(清)魏源:《圣武记》卷7《雍正西南夷改流纪·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年。。鄂尔泰奏疏所言,与雍正帝的诏书相呼应,两人的思想也大致相通。
从有关记载来看,在土司与“夷霸”严重违法的云贵地区,改土归流之前的情形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大都位于多省地界相连的地区。因各省官府鞭长莫及,难以管辖这一地区的土司或“夷霸”,致使他们的违法行为难以控制,尤其以乌蒙、镇雄、泗城三府的土司最为典型。鄂尔泰的奏疏甚至将这些地区归入“并未归版图”的范围。③《云贵总督鄂尔泰为敬陈东川事宜,仰祈圣裁奏事》(雍正四年三月二十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二。其二是未曾设置土司地区的地区。史籍将这些地区的违法者称为“恶夷”“生苗”或“野贼”。这些违法者经常掠夺附近的百姓与经过的商旅,偷割附近编户的庄稼,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官府也防不胜防。据云贵总督高其倬说,元江、新平地区的“野贼”十分猖獗,经常掠夺作乱。听说官府发兵围剿,随即遁入威远、普洱等地的深山老林。“岁无宁宇。”④(清)高其倬撰:《筹酌鲁寇山善后疏》,载道光《云南通志稿》。鄂尔泰则称在以古州为中心的贵州东南部,“为顽苗盘踞,梗隔三省,遂成化外”⑤《云贵总督鄂尔泰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奏事》(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二。。若欲开由贵州通往云南与广西的驿路,“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⑥《云贵总督鄂尔泰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奏事》(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二。。其三是与缅甸、越南等国接壤的云南南部边疆,这些地区的土司长期游离于官府的管辖之外,“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⑦《云贵总督鄂尔泰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奏事》(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二。这些土司“巢穴深邃”⑧《云贵总督鄂尔泰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奏事》(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二。,尤其以居住在鲁魁、哀牢两地的土司最为活跃。位于澜沧江两岸的土司十分危险。澜沧江以内为相对稳定的镇沅、威远、元江诸府,澜沧江以外是情况复杂的车里府以及缅甸、老挝诸国。一旦边疆有事,暗藏的隐患将发展为严重的祸害。
云贵土司地区普遍存在法制不健全的现象,根源仍在于土司与“恶夷”难以管控。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在奏疏中说:“滇黔大患,莫甚于苗猓,苗猓大患,实由于土司。”⑨《云贵总督鄂尔泰为擒制积恶土官奏事》(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二。他还说明朝的土司虽有职衔,但朝廷疏于考察与管理,大致仍属于消极的“以夷治夷”。“遂致以盗治盗,徒令挟土司之势,以残虐群苗。”⑩《云贵总督鄂尔泰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奏事》(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二。因此百姓长期遭受荼毒。鄂尔泰还说:“苗倮逞凶,皆由土司,土司肆虐,并无官法,恃有土官土目之名,行其相杀相劫之计,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此边疆大害,必当剪除者也。”11《云贵总督鄂尔泰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赋、以靖地方奏事》(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二。在这样的情况下,雍正朝组织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当以全面惩治违法的土司与“恶夷”为施行的重点。
与土司地区、“恶夷”地区存在严重的违法现象相对应者,是地方官府在吏治方面存在普遍腐败的问题。鄂尔泰于雍正四年(1726)赴云南东川府(治今会泽)考察。他得知自康熙年间东川府实行改土归流,至今已达30年之久,但东川仍在土司的控制之下,东川土司的活动十分猖獗,每年秋收必抢割百姓的庄稼。附近的寻甸、禄劝、沾益等州百姓,经常遭受东川土司无端的骚扰,掳掠人口或抢劫牛马是常有之事。被害的百姓到官府控诉,官府行文令下属调查处理,四川省的官衙依例先询问事发地点的土官土目,土官土目因从中获利,便多为隐匿包庇,云南也存在类似的情形。雍正六年(1628)鄂尔泰的奏报称:在云南的车里(今景洪)、茶山、孟养等地,各种“蛮贼”出没无常,他们居住不定,外人难以得知其活动的踪迹。这些“蛮贼”十分凶残。劫人烧寨为平常之事,还经常武力对抗前来围剿的官军。地方官府纵然报告督抚提镇等上级官府,但通常是互相隐讳,以之为安妥之计,“间有建议征缴者,非以为好事,又指为喜功。”①《云贵总督鄂尔泰为窝泥既靖、规画宜周、敬陈管见、仰祈睿鉴奏事》(雍正六年正月初八日),《朱批谕旨》鄂尔泰折五。
在云贵土司地区凡有争执,主要是依靠传统的习惯法审理,对一般争执官府通常并不过问。广西分巡右江道佥事乔于瀛,雍正元年(1723)在上奏朝廷的奏报中说:在柳州、庆远与思恩等地,少数民族占居民总数至七八成。“熟夷”如同汉民一样输赋纳租,但传统习俗仍起很大的作用。若发生争执,多请地方老者调停解决,很少至官府告状。“非趁炮火劫杀,即趁黑夜烧掠,皆因愤有衅隙,循环报复得可完结。”②《广西分巡右江道佥事乔于瀛为奉明奏事》(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雍正朝汉文朱批谕旨汇编》第三册。受害人即便赴官府控诉,官府设法推脱的情况较多,因此很难得到妥善解决。表明国家法律与地方习惯法之间,也存在需要磨合的问题。
可见云贵地区长期存在土司、“恶夷”严重违法,以及法治普遍不健全的问题,前提是当地官府吏治腐败,纵容土司与“恶夷”的违法活动。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朝廷法治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磨合不够的问题。因此,只有全面整顿吏治,处理好朝廷法治与地方习惯法妥善对接等一类的问题,才能改变云贵地区各级官府执行不力的状况,土司、“恶夷”严重违法与法治普遍不健全的痼疾,也才能相应得到有效解决。
综上所述,明末至雍正朝改土归流以前云贵土司地区的法治,大致可分为明末至“三藩”叛乱结束、“三藩”叛乱结束至雍正朝改土归流之前两个时期。
前一时期,明末战争给云贵地区留下严重的创伤,兼之土司违法作歹由来已久,战争创伤延续了很长的时间。吴三桂平定云贵地区,一度镇压反抗的土司并改设流官,但用意与朝廷的改土归流明显有别。出于割据云贵地区准备造反的考虑,吴三桂纵容和滥封土司。“三藩之乱”爆发后,不少土司参加反叛,使原本饱受破坏的地区雪上加霜。除违法土司外,一些地区的“夷霸”和“生苗”也肆意横行,使得道路受阻,耕地荒芜。
“三藩之乱”平定后,土司、“夷霸”“生苗”长期违法涉及的深层问题暴露,官府失职推诿以及吏治腐败,堪称是土司、“夷霸”违法难止的土壤。对云贵地区土司、“夷霸”严重违法的问题,雍正朝之前也进行过一些治理,但收效甚微。经过详细调研,雍正帝与大臣鄂尔泰总结出重病须用猛药,对违法的土司和“夷霸”,以及云贵地区的吏治必须彻底整顿的思路,为以后大规模进行改土归流,彻底解决土司地区法治方面的问题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