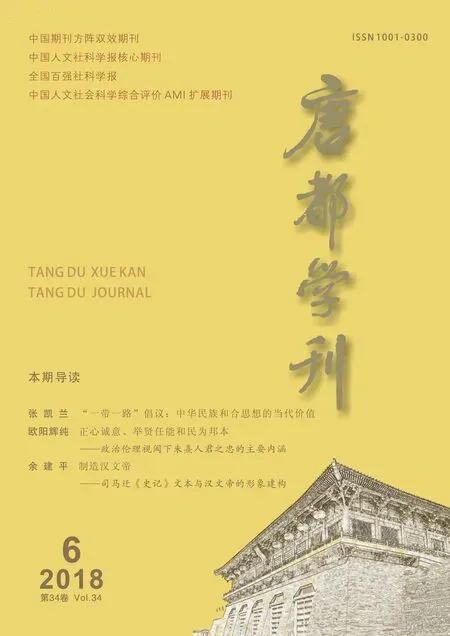本居宣长“物哀”论的学术价值探讨
雷晓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广州 510420)
研究本居宣长的“物哀”论是深入了解日本古典文学、探索日本人精神底蕴的一个独特的视角,也是中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节点。长久以来,中国学者对本居宣长“物哀”论的评价莫衷一是,也有一定的深度,但对“物哀”论的多维度研究以及深层肌理却付之阙如,这是研究日本文学与日本思想的一个盲点,也是学界近十年的一个热点。本文拟从本居宣长“物哀”论的成就、局限性及其启示三个角度解析其成败利钝。
一、“物哀”论的“成就”
本居宣长的“物哀”论之所以能够在日本文学和日本思想领域里熠熠生辉,必有其自身的所谓优点,但它牵扯到了中国文论的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核心论点。本居宣长的“物哀”论批判了中国文论的“克己复礼”观点,他认为:“中国文论注重现实批判性,主人公往往即使心有所怜、所苦,但为‘义’、为‘礼’也要表现得冠冕堂皇,这是缺乏对‘人性的真实描写’、‘实则装腔作势、色厉内茬’。”[1]94本居宣长的这个观点本身就是偏颇的看法,中国文论历来主张文学作品应注重情理和谐且以理节情,基本的文学思想可概括为“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的文学理念。毋庸讳言,中国的有些文学作品的确有克制、压抑,甚至是扭曲人性的表现。本居宣长在比较中日文论时,在批判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道德性偏重方面,抓住这一点,可谓找到了一个“排除汉意”的突破口,不得不说其剖析独到。本居宣长在“物哀”论中强调:“写作要如实把人的内心世界,尤其是脆弱细微之处表现出来,打动读者,使其感受到物之‘真实’。”他的“物哀”论以“真情实感”作为写作的要求和标准,不是没有道理,甚至可以给予积极的评价。
但从公允的角度讲,批判某些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道德性偏重倾向,并不因此就可以对之予以肆意歪曲乃至全面排斥。对于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世界文学界自有公论。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中就有一个很有见地的评述:“中国的‘情感论’包含教化和娱乐,这一点与贺拉斯相似。中国官方的倾向是恪守儒家‘教重于乐’的观念。日本与中国有着同一种前提,即认为诗人乃有感而发,但道德教化观念在日本却很难找到。除了早期有少数的几个例子外,儒家学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新儒家学说,直到大约公元1600年,才因德川幕府把它采用为官方意识形态而获得发展的动力。但即使是到了这个时期,作家们大都还是持抵制态度。因此,中国的情感论正好处于日本和贺拉斯二者之间。”[2]由此可知,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日本文论比较而言,是适中的文学观。厄尔·迈纳的这个观点堪称深刻而精辟。
首先,正是这位所谓的求“真”的日本学者,却在明目张胆地造假。本居宣长杜撰、想象日本历史。其学术思想的荒谬之处在于他无视历史事实,捏造出所谓“皇国创世神话”,通过“日本是世界诸神之祖天照大神所生,是万国之母国,所以日本远胜万国,即更源于此”。而“天皇代替天照大神抚育万邦的现人神”。他的歪理邪说企图证明“无论圣人、神道还是儒教、佛教,日本具有先验性的绝对的优越性”,因日本是“先天地而生”,故具有先验性的真善美品格。“神国善美”“天皇神圣”“神道纯正”,这些被本居宣长杜撰出来的“神话”成为“日本精神”。这些既没有科学根据、又违背历史事实的“想象”,完全出于其为了刻意抬高日本文化的预设目的而导出的伪历史,正如其无端歪曲和批判的,在中国和在日本传播的汉学审美文学完全被拉黑、被污蔑,又堕入历史虚无主义一样。在本居宣长那里,伪造历史与历史虚无主义,正好是不尊重历史和反历史的合二为一。
其次,本居宣长对中国文论“劝善惩恶”的批判。本居宣长认为:“外国(此处指中国)的书,无论是什么书,对待人物喜欢严格论定其善恶是非,喜欢讲大道理,每个人都极力证明自己的贤明。即使是在以风雅为宗的诗文中,也与日本的和歌大异其趣,并不着意表现人情,而是讲道理、显才学。日本的物语则无拘无束、随心所欲、丝毫也不卖弄才学,自然而然地写出了细腻丰富的人情。”[1]29这个观点涉及文学功能的问题。客观地讲,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写作目的。有的人为了疗救的目的即“治愈”功能而写作,有的人为了“寓教于乐”而创作,有人为了追求“崇高”而写作,而有的人为了“狂欢”而写作等等。对于作者的创作目的,这本来就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而本居宣长却认为,“写作的宗旨是为了‘物哀’、为了‘人情’”。他关于写作目的的观点是很狭隘的。这一点,看看他关于“物哀”的评断就一目了然。他认为:“知物哀的就是好人,不知物哀的人就是恶人。”[1]29如此评价“知物哀”,可以说是一家之言。而当他把“物哀”与善恶完全剥离开之时,其推崇“物哀”的恶俗低劣的粗滥底色就暴露无遗。他说“善恶自在人心”,与“知物哀”与否没有必然的关系。在本居宣长看来,“凡是人,都应该理解风雅之趣,不解情趣,就是不知物哀,就是不通人情。”[1]38“知物哀”是一种审美情趣,“仁义道德”也是一种价值追求,二者各有所好,没有孰对孰错的必然选择,因此不必厚此薄彼。世界上哪里有无缘无故的“物哀”呢?中国没有,日本也没有。这些观点与人类的审美经验大相径庭,与日本文学中有价值的成分也背道而驰。剥离善与恶,隔绝情与理,这样荒诞的思想,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本居宣长为什么对中国文论中“善恶观”的批判是那么武断和失真。
第三,作为日本学者,本居宣长提出“物哀”论不失为在文学理论领域里的创新之举。本居宣长认为:“以前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学问,仅仅是学习和研究来自中国的学问。久而久之,我们就对本国古代的事情越来越疏远了。相反,对中国的事情却越来越熟悉。最终在精神上完全汉化了。我们对于本国古代的事情不仅无知,而且连古语古词,听起来也感觉像是外国话了。”[3]297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明确两点:一是日本文学一直深受中国文学的沾溉,尤其是日本文论中的许多文学理论观点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于中国的文论;其二是本居宣长有一种日本文学的自觉或曰觉醒。前者是历史事实,后者是可以理解的日本文坛和学界的民族独立情绪。我们对本居宣长及其日本学界的创新举措也很欣赏,并且乐观其成。需要指出的是,创新有一个国际学界的通则,那就是创制贵其真,求新据其实,进取有其道,协和是其德,舍弃真实与道德的进取,不但行之不远,而且会伤人误己,甚至贻害无穷。
本居宣长“物哀”论的提出,彻底颠覆了日本文学评论史上长期流行的、建立在中国儒家伦理道德学说基础上的“劝善惩恶”论。本居宣长倡导“物哀”论,在摆脱对中国文论的依附方面,可谓敢于有为,勇气可佳;但是在创新求变和日本文论自觉的同时,也披露出狭隘保守而且吝于反思和过河拆桥的行径。
二、“物哀”论的局限性
首先,本居宣长“物哀”论在学理方面有其曲直问题。举凡学术创造,都有一个道理之曲直。理有曲直,道有大小。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从属于大道理。任何学术创新的价值,无不与此有关。如民族自尊,唯我独尊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一脉独张的民族中心主义,这些都是不足取的。本居宣长的局限在于他知其曲,而不知其直;举其小,而忘其大。其所曲就在于拘泥于小道理,而忽略了大道理。
从纵向而言,学术问题需要不断反思,不断提升,不断向更高的人类正道行进。在横向角度,学术繁荣也需要与各国各族各家各派相互切磋,集思广益,以期取长补短。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之间相互交流、互补、互通,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学术主张共同促进了大道。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世界各国文化学术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需要求同存异,相互尊重,学他人之长,适可优势互补,或可异质同构。本居宣长为了彰显日本的“大和魂”,不惜肆意地诽谤和攻击中国文化是令人遗憾的做法。例如,本居宣长认为:“中国不是日本这样的神国,从远古时代始,坏人比较多,暴虐无道之事频繁,动辄祸国殃民,世道不稳。为了治国安邦,他们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寻找良策,于是催生了一批批谋士,上行下效,因此无论做任何事,都一本正经,深谋远虑,费尽心机,杜撰玄虚的理论,对区区小事,也要论个善恶。改过上下人人自命圣贤,将内心软弱无靠的真实情感深藏不露,使他人无法看到其内心的软弱无助。这些都是虚伪矫饰,而非真情实感。”[4]152可以说本居宣长的这种观点是罔顾事实的。此处仅指陈两点:第一点,本居宣长认为中国学者的“克制”“隐忍”都是“刻意为之的装腔作势”,这对伟人辈出的中国学者长河不啻可笑的歪曲。第二点,本居宣长为了确立日本的“大和魂”,就攻击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将中国文化一概否定,全然不顾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对全人类的贡献,这是不值一驳的狂悖行径。本居宣长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言行,可以用庄子的一句话作结:“曲士不可言道,夏虫不可语冰”。
其次,本居宣长“物哀”论只强调“人欲”而忽视“道德”,本身是有偏颇的。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彰显了人的自然属性,注重“真实”,无可厚非。但作为一名创作者,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一味宣泄个人的情感,而无视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是不可取的。例如,本居宣长认为:“《源氏物语》的宗旨是表现‘物哀’和‘知物哀’”。在所有人情中,最令人刻骨铭心的是男女恋情。而在恋情中,最能使人“物哀”和“知物哀”的,则是“背德”的“不伦之恋”,亦即“好色”。《源氏物语》中描写了许多“不伦之恋”,包括乱伦、诱奸、通奸、强奸、多情泛爱。这些恋情在本居宣长看来都是出自真情、都是无可厚非的,也都属于“物哀”。这里面不仅有一个审美趋向的邪正问题,而且有一个文学伦理价值的判断问题。文学事业选择道德底线的坚守,还是选择所谓“真实的物哀”面具下的淫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同的作家、评论者似乎有自由权,但是本质上必须遵守天理的检视和人伦的拷问。在这两种律令面前,所有自认为是人的文人学士都无可逃遁。本居宣长在这里打出了日本天照大神的底牌,他认为:“神只聆听人心之实。而中国人‘凡事都设定大道理’是不被神所接受的。所以,只能以‘物哀’感动神与人。”[4]174-175这个观点非常荒谬,把纵欲和“去道德”的文学归之于神,这是一种虚伪的狡辩。如果以神说事,那么是否可以反问,神难道不要求人们恪守道德吗?神可以教唆文学人骄奢淫欲吗?如果神把文艺引向邪恶,那这个神谕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可信呢?本居宣长的这套借神旨宣扬淫欲的“物哀”论,在这里露出了邪恶的面目。
第三,本居宣长“物哀”论被日本军国主义所利用。由于本居宣长的学术观点无视甚至破坏文学“伦理”与思想文化的道德的底线,故而他的思想学说正好投合了日本历史上最反动、最残暴、最无耻的军国主义分子的胃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居宣长那套歪理邪说,就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狂妄不可一世的理论先驱。二战战犯的所有无耻谰言恶行,诸如“大日本至上”“皇国优越”“日本在世界上没有约束”等等,都可在本居宣长那里找到根据。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们所赞美和利用的本居宣长思想,不仅仅是一种“曲解”,在本质上就是一脉相承的。由此来看,“物哀”论成为近代日本皇国史观的理论资源,大受日本统治者们的青睐,就毫不奇怪了。我们不妨听听本居宣长《敷岛之歌》中的下述言论:“人问敷岛大和心,朝日灿烂山樱花。”回顾日本文化史,把“山樱花”图腾化的始作俑者当中,就有本居宣长其人。人们不会忘记,1944年10月,当时就任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的大西泷治郎组建“神风特攻队”,正是以本居宣长诗中的“敷岛”“大和”“朝日”和“山樱”命名四个大队[5]。本居宣长的“物哀”论标榜无道德无政治,骨子里却渗透着反人性反天理的反动因子及滥杀无辜的军国主义法西斯基因。
三、“物哀”论的启示
上述梳理对我们的启发是深刻的。由之我们不仅看到了本居宣长“物哀”论的长短曲直,而且深切地引发了当今各国文化交流的应取态度。总起来讲,有以下三点发人深思:
首先,本居宣长所构建的“物哀”论,让我们思考如何公允地对待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可以完全封闭起来,不与其他国家、民族、地区联系。而且,客观地讲,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也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为学者在做学问、做研究时,少不了客观评价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问题。
在评价中国文化上,本居宣长无视事实的做法十分不可取。他认为:“日本学者以不知道中国的事情感到很羞愧,很丢脸。对于不知道日本的事情,则会毫不羞耻地回答‘不知道’。”[3]40其实在当时,中国文化在日本的普及,是给日本社会注入了正能量,这一点已经被历史证实,也被许多日本学者和有良知者所肯定。本居宣长对于“日本学者接受中国文化、学术而不了解日本文化”的现状有忧虑之心,全然违背历史真实,全然不思考日本历史上所用的国名“倭”与核心字词“和”也是从中国借鉴,全然不考虑他本人所离不开的一些思想元素,如“道”“文”以及“物哀”等术语,也都是汉语言文化的东传。他的“忧虑之心”,实乃小人心态。本居宣长要确立民族自信、自立、自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忘恩负义,甚至狂悖到无耻的地步,那就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人品卑劣的表现。他号召日本人学习日本文化的愿望没有错,但他抹煞了一个事实,日本的古代典籍,即便他所谓最古老的《古事记》,不但是用汉语写就,而且有不少内容原本就是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改写或模仿。本居宣长为了证明日本文化、学术的独立性,绞尽脑汁割裂其与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实在是与历史开玩笑。
其次,本居宣长要给自己的民族树立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标杆,其精神可嘉,但不可狂妄自大。本居宣长为了确立“大和魂”而歪曲事实、曲解中国儒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而比这种歪曲更可怕的是他已经走得更远。他把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置于世界各民族之上,认定“皇国优越”“大日本至上”,为达此目的,他不惜对历史本真虚无化。同时,又对日本古来历史进行伪造,由此渲染的“大和魂”把日本民族拖向了一条危险的道路。一个人狂妄,是危险的;一个民族狂妄,则更加危险。近代以来,日本在法西斯化道路上的裸奔,已经无可争辩地证实了这一结论。
最后,在学术道德问题上务必守住底线,这一点非常重要。(1)守底线,就必须给人性中的兽性那一面套上缰绳。西方有句谚语说得好: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不能让兽性失去控制,不能让淫欲祸水横流。(2)守底线,就要推崇世界民族之林最起码的立场,诸如,不可忘恩负义,不可过河拆桥,不可面对事实而满口胡言乱语。(3)守底线,就要培植和巩固人类共有的核心价值,如善良、公正、和平等基本准则。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当中,上述三条底线,实际上要求人们具有自我反思意识和民族检讨精神。试看世界上那些伟大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哪一个不是围绕上述底线不断自我批判、自我节制,在自我改造中经磨历劫,由此一天天发展壮大,从而恒久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综上所述,本居宣长曾强烈呼吁彻底排除毒害日本的“汉意”,回归日本“古道”,其目的就是要采取抹煞历史真实和伪造历史的手段,以实现重构日本人的历史记忆,寻求日本人的集体意识。至于历史的真相如何,本居宣长完全忽略了。也正是因为他的“创造”与“发明”,日本社会从天皇、学者到民众都受到了荼毒,甚至被导向了歧途。联系到今天日本政府以及部分普通百姓对二战与侵略他国的错误态度,至少本居宣长及其“物哀”论难辞其咎。面对相当数量的日本人不愿正视二战历史真相的种种现状,深入解析本居宣长“物哀”论后面的东西,对全球化大趋势中如何和平地推进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意义相当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