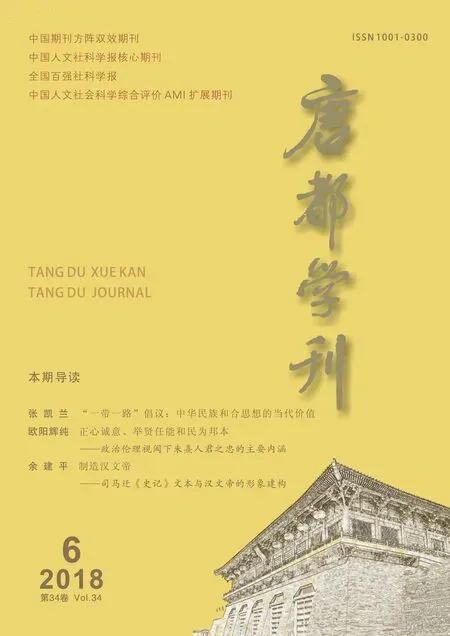正朔与僭闰:东晋的正统认同问题研究
李正君, 黄树林
(1.安庆师范大学 人文与社会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2.广东建设职业学院 学生处,广州 404507)
一、东晋时期的正统认同
“正统性”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概念,而西方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则是“合法性”。法国学者让·马克·夸克对于政治的合法性有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最通俗地讲,合法性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它是政治权力和其遵从这证明自身合法性的过程。它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1]根据让·马克·夸克的定义,合法性首先需要得到被统治者的首肯,同时还要得到社会整个价值体系文化的认同。但是中国古代的情况略有不同,中国古代王朝正统性针对的对象固然有本王朝的被统治阶级,但更多的是针对前代以及敌国而言,其目的是为加强本朝的现实统治。刘靖年等人编写的《中国政府管理创新》一书认为支撑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资源:“首先是自然因素的人格化力量,并集中在‘天’这个特殊的载体和范畴上……其次是宗法的力量……可以说,宗法性的社会结构是伦理政治化的社会基础。第三是巫化圣化力量的合一。”[2]而笔者认为其中的第一点和第三点可以合并在一起,中国古代统治者都自称天子,力图树立内圣外王的神圣形象,把“天”的意志赋予统治者的身上,一方面赋予自然和统治者以超自然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把这种超自然的力量纳入政治体制中来,这样使其合法性和正统性得到宣扬和巩固。
(一)东晋初期江南对其正统观的认知
西晋惠帝时期爆发的八王之乱,使西晋元气大伤走向灭亡的边缘,而胡人的入侵则是西晋灭亡的直接原因。西晋既亡,晋元帝司马睿在南渡士族和江南士族的支持下,建立了江左的小朝廷,史称东晋。而在东晋建立之初,司马睿所代表的东晋王朝并不能得到人们一致的承认和认可,这种阻力既来自北方也来自南方。
首先,北方汉人。《晋书·张寔传》:“元帝即位于建邺,改年太兴,寔犹称建兴六年,不从中兴之所改也。”[3]2230建兴为晋愍帝的年号。另据同书《张玄靓传》:“废和平之号,复称建兴四十三年。”[3]2248由此可见在北方汉族心中东晋的正统性不能完全被认可。
其次,南迁流民帅。据田余庆先生的研究,东晋初年,流民是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流民帅出身背景不一,既有北方高门,也有门户较低的武人。他们长期统领部曲、乡党,经历过战事,他们的南下是迫于生存的压力,不存在效忠东晋政权的必然性,与北方政权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4]330。这些流民帅也许在南渡初期对于东晋政权只保持着观望的态度,并不承认东晋朝廷的正统性,维护其自身利益才是其南渡的出发点。
再次,江南吴人。晋武帝太康元年(280),西晋消灭东吴统一了全国,但是江南的反抗势力依然存在,随着胡人的入侵,西晋的衰落,这股势力不甘心本地割据政权的覆灭,掀起了多次起义,并制造诸多谶语。如《宋书·五行志》载:“晋武帝太康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莫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于时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故窃乱者相继。按横目者‘四’字,自吴亡至晋元帝兴,几四十年,皆如童谣之言。元帝懦而少断,局缩肉,直斥之也。”[5]914可见当时在江南复兴东吴的势力还是有一定影响的,而童谣直指晋元帝,说其性格“懦而少断”,言下之意,望之不似人君,进而对于东晋的正统地位不予认可。
面对两晋之际严峻的政治形势,琅琊王氏对于晋元帝司马睿的扶持之功是不能抹杀的。《晋书·王导传》载:“乃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导患之。会敦来朝,导谓之曰:‘琅琊王仁德虽厚,而名论犹轻。兄威风已振,宜有以匡济者。’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导因讲计曰:‘古之王者,莫不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己倾心,以招俊义。况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草创,急于得人者乎!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帝乃使导躬造循、荣,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3]1745“王与马共天下”开启了江东政局,奠定了东晋一朝政局的基础,而琅琊王氏等世家大族对于东晋政权的扶持对于其正统性的重塑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北朝部分政权对东晋正统观的认知
永嘉南渡之后,中国南北分立,北方曾出现二十个政权,因崔鸿著有《十六国春秋》,因此后世将这一历史时期称之为十六国时期。439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534年,分裂为东魏与西魏。东魏武定八年(550),高洋废孝静帝,代东魏自立,建立北齐。西魏于恭帝三年(557)被权臣宇文护逼迫禅位于其堂弟宇文觉建立北周,北魏历史正式结束。公元581年,隋文帝取代北周建立隋朝,589年灭陈,统一全国。而南方则先后经历东晋、宋、齐、梁、陈等朝,加上之前在江东建立的孙吴政权,合称六朝。这一历史时期北方民族成分复杂,王朝嬗变频繁,新建立的王朝尤其是少数民族政权迫切需要论证其正统性问题,南北双方遂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北史·序志》有载:“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魏‘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6]南北之间相互攻讦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南人称北人为“索虏”,北人称南人为“岛夷”,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东晋正统上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司马睿身上。在历史上,政治的正统问题常常与血统问题联系起来,正如董恩林先生所说:“政治正统的根本是王位正统,王位正统的保证在于王室血缘的纯正。”[7]如《魏书·僭晋司马睿传》言:
僭晋司马叡,字景文,晋将牛金子也。初晋宣帝生大将军、琅邪武王伷,伷生冗从仆射、琅邪恭王觐。觐妃谯国夏侯氏,字铜环,与金奸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马,仍为觐子。由是自言河内温人……司马叡之窜江表,窃魁帅之名,无君长之实,局天脊地,畏首畏尾,对之李雄,各一方小盗,其孙皓之不若矣。[8]
首先这里称晋元帝司马睿为“僭晋司马睿”,说明北魏认为东晋是僭位,北魏才是正统,司马睿是伪帝,北魏皇帝才是天命所归的天子。其次,其上所引的这一段材料已将司马睿的形象丑化到了极点。其出身被描绘成西晋将领牛金与夏侯氏私通而生,并非西晋皇室的后裔。司马睿登上帝位是“窜”的,是“窃”的,是“无君长之实”的,司马睿本人没什么能力的,是“畏首畏尾”的,像李雄那样的“小盗”,是连吴主孙皓都不如的。可见,北朝在史书在极力诽谤攻击南朝,以维护其正统的地位和利益,这也就使得这一时期史学宣扬正统的特征更加突出,但是东晋的正统性也并非完全得不到认可。十六国时期一些割据政权的君主和创始人还是心恋南方的。
其一,前燕。前燕的慕容廆与东晋的关系十分微妙,太兴四年(321),“十二月,以慕容廆为持节、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平州牧,封辽东郡公。”[3]155慕容廆曾接受东晋册封,1992年11月在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与云飞街交叉路口东南发现一前燕墓,出土砖质墓志一方,墓志主人为李廆,不见于史,墓志内容也十分简单。“燕国蓟李廆/永昌三年正月廿六/□□日亡。”[9]永昌为东晋元帝的年号,李廆虽为前燕人,但死后仍然沿用东晋年号,可见东晋的正统影响力在辽东还是相当广泛的。

其三,成汉。割据四川的李雄也曾说:“我之祖考本亦晋臣,遭天下大乱,与六郡之民避乱此州,为众所推,遂有今日。琅琊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国者,亦当帅众辅之。”[10]2992
其四,再如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他经常告诫自己的儿子说:“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3]2961他之后甚至遣使向东晋请降。
而在北朝时期仍有视南方为正朔者,如《洛阳伽蓝记》卷2:“庆之因醉谓萧张等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朝玉玺,今在梁朝。’”[11]又如《北齐书·杜弼传》:“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于高祖。高祖曰:‘天下浊乱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12]347南方王朝统系相承明确,承认梁代是正朔所在,也可说明其对东晋正统性的认可。而当时北伐也与正统性相联系,东晋桓温北伐时,关中耆老就说:“不图今日复见官军。”[3]2571刘裕北伐时,三秦父老也泣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矣,始睹衣冠,方仰圣泽。”[5]1634可见北方身陷胡族政权的汉族士民对于东晋的渴望和认可。日本学者川本芳昭先生认为北方诸胡族政权对于东晋的承认是出于一种现实的考虑,“并不是认识到东晋是继承西晋正统的王朝,而是他们认为吸纳自己所占领的华北地区占据人口多数的汉族的意向,有助于加强其统治,即非汉族的立场与汉族不同,他们是从更现实的观点出发,意识到当前支持东晋是上策。”[13]川本先生的这一观点固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笔者认为由于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的落后,导致其自卑心理具有一定的惯性,想要使其在心理上达到与汉族平起平坐的地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在五胡入主中原的初期,西晋或者以后的东晋的正统性还是极富号召力的。正如姚弋仲所说:“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这种心理在当时也是普遍存在的,正如刘琨在向石勒求援时所说:“自古以来,诚无戎人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3]2715但随着他们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这种文化上的自卑心理被逐渐淡化和克服,使他们敢于与汉族政权分庭抗礼,这一点鲜卑北魏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唐宋时期学者对于东晋正统性的认识
上一节我们讨论了东晋时期的正统认同问题,而对于一个王朝的正统性多是自说自话,站在后人和研究者的角度,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辨别到底谁是正统。但关于东晋的正统性也受到了唐宋以降学者的高度关注。正如洪迈在《容斋随笔》里所说的:“晋魏以来,正闰之说纷纷,前人论之多矣。”[14]隋唐的统一,不仅是地理疆域上的统一,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统一。经过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局面,在隋唐之际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当时的学者思考和总结,而正统思想就是其中之一。下面笔者将介绍唐宋以降几位主要学者对于东晋正统性的看法。
(一)王勃对东晋正统性的认识
王勃,字子安,唐代诗人。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我们熟知的王勃大多是因为他在诗歌方面的造诣,其实他在历法方面也是颇具成就的。“高宗时,王勃著《大唐千年历》:‘国家土运,当承汉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两朝,咸非一统,不得承五运之次。”[15]168这就是王勃所提出的“唐承汉统”论,与汉代的“越秦承周”、东晋习凿齿的“晋承汉统”论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王勃的这一理论在当时似乎没有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史书上称“勃言迂阔,未为当时所许”。直到玄宗时期,“天宝中,上书言事者,多为诡异,以冀进用,有崔昌采勃旧说,遂以上闻,玄宗纳焉。下诏以唐承汉,自隋以前历代帝王皆屏黜,更以周、汉为二王后。是岁礼部试《土德惟新赋》,即其事也。”[15]168另据《新唐书·王勃传》:
(勃)谓王者乘土王世五十,数尽千年;乘金王世四十九,数九百年;乘水王世二十,数七百年;承木王世三十,数八百年;承火王世二十,数七百年,天地之常也。自黄帝至汉,五运适周,土复归唐,应继周汉,不可承周隋短祚。乃斥魏晋以降,非真主正统,皆五行沴气。遂作《唐家千岁历》。武后时,李嗣真请以周汉为二王后,而废周隋。中宗复用周隋。天宝中,太平久,上言者多以诡异进,有崔昌者,采勃旧说,上《五行应运历》,请承周汉,废周隋为闰。右相李林甫亦赞右之,集公卿议可否。集贤学士卫包,起居舍人阎伯玙表上曰:“都堂集议之夕,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矣。”于是玄宗下诏以唐承汉,黜隋以前帝王、废介、酅公,尊周汉为二王后。[16]
又《通鉴》卷216云:
天宝九载八月辛卯,处士崔昌上言:国家宜承周汉,以土代火,周隋皆闰位,不当以其子孙为二王后。……上乃命求殷周汉为三恪,废韩、介、酅公。[10]6899
这里除了不承认东晋是正统王朝之外,干脆把整个魏晋南北朝都排除在五运之次以外,这一意志更是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直接影响了唐代的“二王三恪”问题。
(二)皇甫湜对于东晋正统性的认识
皇甫湜,唐代散文家。字持正,唐睦州新安(今浙江建德淳安)人。十多岁时就漫游各地,投梁肃,谒杜佑;后又结交顾况,师从韩愈,还求见江西观察使李巽,作书献文,希图荐举,未成。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他在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不第。他广为交游,与白居易、李翱、刘敦质等人往来。留有《东晋元魏正闰论》一文,现收入《皇甫持正文集》中。他首先提出“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统,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说明皇甫湜十分重视正统性的宣扬。而对于东晋的正统性问题,他是这样说的:
惠帝无道,群胡乱华,晋之南迁,实曰元帝。与夫祖乙之圯耿,盘庚之徙亳,幽王之灭戏,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义一矣。而拓跋氏种实匈奴,来自幽代,袭有先王之桑梓,目为中国之位号,谓之灭邪?晋实未改,谓之禅邪?已无所传。而往之著书者,有帝元,今之为录者,皆闰晋,可谓失之远矣。或曰元之所据,中国也。对曰:所以为中国者,以礼义也;所以为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17]33
皇甫湜以东晋与北魏对立的角度,认为北魏并非正统,东晋才是承袭西晋正统的朝代。他认为东晋永嘉南渡与商代祖乙圯耿、盘庚迁亳、周代幽王灭戏、平王避戎是同一类型的事件,只是都城位置有所变化,但正朔仍然相传。皇甫湜的夷夏观念在于文化礼义,不在于地域。东晋虽然南渡,但是传承文化的人物也跟着一起南渡了,所以“礼乐咸在,史实存焉”。似乎其与中国传统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的观念不同。事实并非如此,皇甫湜不是没有注意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史实,只是他对这一次改革评价不高。“至于孝文,始用夏变夷,而易姓更法将无及矣。且授受无所,谓之何哉?”[17]34
然而对于这一观点,有人似乎提出疑问,也可能是皇甫湜为了说明自我观点而在文中故意使用问答的形式。“又曰:周继元,隋继周,国家之兴,实继隋氏,子谓是何?[17]34这一发问分量极重,如果回答不准确可能会陷入对方的圈套,这一问难从唐代的正统性入手,唐继隋,隋继北周,北周是由北魏分裂出来的,如果否认了北魏的正统性,也就是否认了唐代的正统性。此一问难不禁让人想到汉初关于黄老学说和儒家革命观点之争[注]《汉书》卷88《辕固传》:“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黄生曰:‘冠虽蔽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大凡牵涉本朝历运正统问题,回答时务必小心谨慎,不可再犯汉初诸儒的错误。而皇甫湜的回答是:“晋为宋,宋为齐,齐为梁,江陵之灭,则为周矣。陈氏自树而夺,无容于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之于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梁而上,以至于尧舜,得天统矣。”由此可知,皇甫湜认为北周的历运接在南朝梁之后,并认为陈代是闰统,由他重新编排魏晋南北朝隋唐统系:尧舜……东晋—宋—齐—梁—周—隋—唐。皇甫湜统系的核心观点在于“陈奸于南,元闰于北”。他似乎对自己的观点充满自信,在文中最后还加重语气重复了两句:“其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以上就是皇甫湜对于东晋北魏正统性的看法。
(三)欧阳修对于东晋正统性的认识
两宋时期对于正统性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正闰之说尚矣。欧公作《正统论》,则章望之著《明统论》以非之。温公作《通鉴》,则朱晦庵作《纲目》以纠之。”[18]97这些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自己心目中的正统观念提出一些看法,我们所关注的还是其对东晋正统性的认识。关于正统论的研究,我们不得不提到欧阳修,因为他最早对正统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苏轼曾言道:“正统之论,起于欧阳子。”欧阳修对“正统”一词下过如下的定义:“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19]267依笔者理解,欧阳修所提到的“正”应该是政权来源上的正当,而“统”指的是国土上的统一。以这样的“正统”观念去审视前代王朝的正统问题,我们所关注的东晋就不在欧阳修所谓的正统王朝之列了。事实也是这样,甚至有人提出欧阳修是第一个否定东晋正统性的人。清代学者周树槐曾说:“晋之东,未有绝之正统者,绝之自欧阳子。”[20]124而欧阳修关于东晋正统性的看法是以东周为类比而阐发的。他认为“自惠帝之乱,晋政已亡;愍怀之间,晋如线尔。惟嗣君继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兴之亡,晋于是而绝矣。夫周之东,以周而东;晋之南也,岂复以晋而南乎?自愍帝死贼庭,琅琊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继世。徒以晋之臣子有不忘晋之心,发于忠义而功不就,可为伤已。”[19]283欧阳修认西晋自惠帝之后,政治几乎就要断绝了,而到了东晋就彻底断绝了,东晋的南渡与周平王的东迁不能相提并论,并提出司马睿“位非嗣君,正非继世”,从“正”的方面否认东晋政权来源的合法性。他进而说:“以宗室子自立于一方,卒不能复天下于一”,这是从“统”的角度来论述的,在欧阳修看来,“晋之琅琊,与夫后汉之刘备,五代汉之刘崇何异?”
(四)刘羲仲对于东晋正统性的认识
刘羲仲,北宋藏书家。字壮舆,号浪漫翁,筠州高安(今属江西)人。刘涣之孙、刘恕之子,史有“高安三刘”之称,著有《通鉴问疑》一卷。刘羲仲在《通鉴问疑》中阐述了其父刘恕的观点。“道原曰:‘晋元东渡,南北分疆。魏、周据中国,宋、齐受符玺,互相夷虏,自谓正统。则宋、齐与魏、周,势当两存之。然汉昭烈窜巴蜀,似晋元。吴大帝兴于江表,似后魏。若谓中国有主,蜀不得绍汉为伪,则东晋非中国也,吴介立无所承为伪,则后魏无所承也。南北朝书某主而不名,魏何以得名吴蜀之主乎?’”[21]道原是刘恕的字,刘恕将东晋与蜀汉政权相提并论,认为与东晋相似的蜀汉政权是“窜”的,提出东晋是非中国的,可见他对于东晋的正统地位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欧阳修的正统观念对后世影响极大,有宋一代备受推崇,其极力推崇者当为苏轼,前所引苏轼言论,言及章望之所著《明统论》,他虽然不赞同欧阳修的“正统论”,而提出了一个“霸统”的概念,但在对于东晋的问题上确实一致的,即都不承认东晋具有正统的合法地位。
(五)张栻对于东晋正统性的认识
到了南宋时期,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对于东晋正统性的认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代表人物就是张栻、李焘、朱熹和周密。张栻,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中兴名相张浚之子。幼承家学,既长,从师南岳衡山五峰先生胡宏,潜心理学。曾以古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以见志。曾作《经世纪年》称“考自尧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岁,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列为六图。”并为其作序,称“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齐后周皆夷狄也,故统独系于江南。”[22]对于十六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权,鲜有承认其正统性者,而争论的焦点在于东晋与北魏之间。张栻在说明北魏是夷狄的同时,认为“统独系于江南”,就是承认东晋的正统地位的。
(六)李焘对于东晋正统性的认识
李焘,字仁甫,宋代著名史学家,学界对于李焘的认识多集中于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而对他的《六朝通鉴博议》认识不够,有学者曾评价此书为“中国传统褒贬鉴戒史学的优秀作品”。其中也有论及东晋正统问题,“王猛丁宁垂死之言,以江南正朔相承,劝苻坚不宜图晋;崔浩指南方为衣冠所在,历事两朝,不愿南伐。苻坚违王猛之戒,故有淝水之奔;佛狸忽崔浩之谋,故有盱眙之辱。虽江南之险,兵不可败,而天意佑华,亦不可厚诬其实。”[23]155-156李焘生于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南宋绍兴八年(1138)中进士,是两宋之际变革的亲身经历者,他所著《六朝通鉴博议》一书也在此背景下完成。清代学者彭元端就认为“仁父(甫)此书,为南宋而发,非为六朝也。与李舜臣《江东十鉴》、钱文子《蜀鉴》同意,欲用襄蜀以规复中原,故借古事以指今势。”[23]263《四库全书》也说:“核其义例,盖亦《江东十鉴》之类,专为南宋立言者。”[24]李焘著《六朝通鉴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阐明六朝的史实,而是为南宋的政治形势提供借鉴。
(七)朱熹对于东晋正统性的认识
朱熹,世称朱子,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著有《通鉴纲目》。他非难司马光修《通鉴》以曹魏为正统,主张以蜀汉为正统。“有始不得正统,而后方得者,是正统之始,而后不得者,是正统之余。如秦初犹未得正统,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统。晋初亦未得正统,自泰康以后方始得正统。隋初亦未得正统,自灭陈后,方得正统,如本朝圣太宗并了太原,方是得正统。又有无统时,如三国、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25]3458在朱熹看来,王朝之前不得正统而后得之的,称作“正统之始”,之后没有得到的叫“正统之余”。其列举的秦、晋、隋和北宋都可算是“正统之始”,对于无统的朝代,朱熹认为是三国、南北、五代,明显中间跳过了两晋,可见朱老夫子也是承认东晋的正统性的。
(八)周密对于东晋正统性的认识
周密,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华不注山人,南宋词人、文学家,著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癸辛杂识》《志雅堂要杂钞》等杂著数十种。在《癸辛杂识》中就有《论正闰》一篇。这篇文章旨在说明中国古代历史上正统有绝有续的情况。其认为“晋武帝平吴亦得正统,此正统之四续也。愍帝亡而元帝中兴,虽在江南,而正统未绝。安帝为桓元所篡,未几返正,以至恭帝禅宋而与魏分注,此正统之五绝也。”[18]98由上可知,周密认为元帝中兴,虽地处江南,但是正统尚未断绝,是承认东晋的正统性的。
(九)郑思肖对于东晋正统性的认识
郑思肖,宋末诗人、画家,连江(今属福建)人,著有《心史》《郑所南先生文集》《所南翁一百二十图诗集》等。此人生活于南宋末年,元兵南侵,眼见山河破碎,却无力回天。宋亡后改名思肖,借“肖”为宋朝国姓赵(趙)字之省。可见其忠贞之志。在其《心史》中有《古今正统大论》:“若论古今正统,则三皇、五帝、三代、西汉、东汉、蜀汉、大宋而已。司马绝无善治,或谓后化为牛氏矣。宋齐梁陈,藐然缀中国之一脉四姓廿四帝,通不过百七十年,俱无善治,俱未足多议。故两晋、宋、齐、梁、陈,可以中国与之,不可列之于正统。”[26]945郑思肖否认东晋正统性的依据有二,其一“绝无善治”,认为两晋不是很好的治世,这也是他否认南朝正统性的依据之一。其二,司马氏出身不好,由前章可知,有传闻司马睿并非司马氏嫡系子孙,而是牛金的后代,这可能是当时攻击东晋政权的人编造出来的谎言,真假莫名。郑思肖也以此来认定其并非正统。而笔者认为可能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郑思肖经历了宋末元初的战火,深知南宋政权的偏安和官员的腐败。而东晋政权也存在偏安的倾向,虽曾有过祖逖、桓温之辈的北伐,但成效不大,尤其祖逖的北伐并未得到东晋朝廷的全力支持。郑思肖痛恨这种偏安的朝廷,也应是其不承认东晋正统性的原因之一。
由以上几位唐宋学者对于东晋正统性的讨论,我们可以大致理清脉络。唐代曾一度出现过“唐承汉统”的思潮,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排除在正统王朝之外,这一思潮还上升到国家层面,成为统治阶级的意志。但同时也曾出现过承认东晋正统性的倾向,认为东晋才是承袭西晋正统的王朝,皇甫湜还重新编排了王朝的统系。认为南朝的统系到梁就断绝了,接着就是北周,之后承接的就是隋唐。而到了北宋时期,否认东晋正统性的观点占主流,支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欧阳修、刘羲仲、苏轼和章望之。他们对于正统的认识虽然不太一样,但是都否认东晋的正统地位,这一点却是一致的。而到了南宋,政治形势与东晋初年有很多相似之处,为了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争夺正统地位以赢得民心,对于东晋的正统性的认识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承认东晋正统地位的倾向,其主要代表就是周密、张栻和朱熹。其中当时的政治形势对东晋正统性的认识影响极大,清人周树槐曾说:“晋之东,未有绝之正统者,绝之自欧阳子。欧阳子宋人也,使其生南宋,欧阳子不绝东晋矣。”[20]124可见两宋之际这种对正统性的认识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然我们强调的是主流思想,在百花齐放的两宋时代,对于正统性的认识不可能整齐划一,南宋末年的郑思肖就是否认东晋正统性的一例。
三、结语
关于东晋正统地位的认同问题,不论当时还是后代都产生过一些争论,这些争论体现出深刻的时代背景。就东晋当时来看,北方的一些汉族士人、南迁的流民以及江南的吴人,都对东晋的正统性持怀疑态度。而十六国时期的一些君主心系南方,他们对东晋的合法性还是予以认可的。就唐宋时代来看,唐代因与东晋无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对东晋的正统性出现过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其中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排除在正统王朝之外的观点一度得到唐朝的官方认可。到了宋代,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北宋一般否认东晋的正统地位,而南宋因其与东晋有诸多相似之处,故承认其正统性的占主流。不管是承认还是否认,都是古人结合政治形势和需要对历史做出的总结和思考,通过对东晋正统认同问题的研究,能让我们更好地梳理古人对这个问题的认知过程,尤其是认知的变化更能体现出特定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