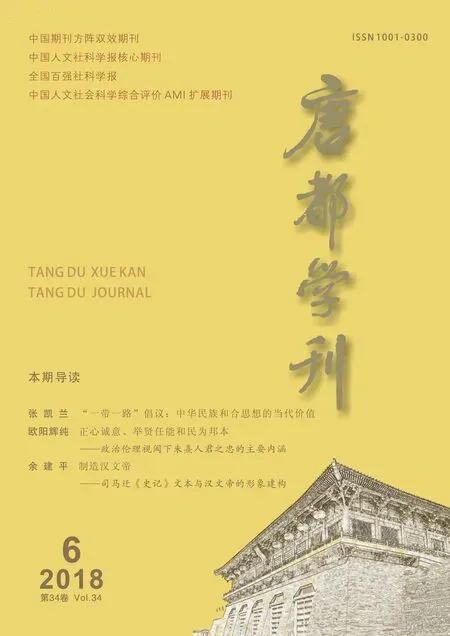试析近代西方文化对云南边疆文化的渗入
李 强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昆明 650504)
一
西方文化对近代云南文化的入侵反映在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是一个十分庞杂的范畴。由于近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显性表现是基督教的扩张,因而由宗教引发的文化间的碰撞损害了云南社会的利益,危害了中华民族的权益。西方文化开始大规模渗入云南的时代是欧洲称霸全球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欧洲人空前自信,在处理与非欧国家关系的问题上,或多或少都带有文化殖民主义的倾向。“他们(欧洲人)深信,上帝创造了不同的人。它将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挥劳动,能指导宽背、低能的劣等种族的发展。因而也就有了‘白人的责任’这一概念——用理想主义的忠于职守的罩衣遮盖当时的帝国主义的一种说教。”[1]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不少欧洲人都以“欧洲标准”来看待非欧事物,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在某些方面扭曲科学的本来面目。近代云南社会动荡,散落民间的历史文物价值极高却不被当地人重视,一些西方人通过各种手段将其据为己有,这同样是西方文化侵略的一种表现。
(一)宗教渗入
梁启超曾谈到,“耶教之入中国也,有两目的:一曰真传教者,二曰各国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权利者。”[2]从某种程度上说,基督教的传播本身就意味着文化渗透,而基督教又往往与西方在云南的现实利益相结合,因而对云南社会造成了一定的破坏。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天主教就在云南设有据点,推行以华制华的宗教政策。光绪七年(1881),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携妻由英属缅甸入大理传教,创办了新教在近代云南的第一个教会。随后,英法等国传教士争先恐后、纷至沓来。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传教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云南的基督教传播较内地而言较为特殊,在三江以内地区,基督教遭遇了儒教伦理文化的强烈抵抗,因而效果并未像西人想象中的那样理想,特别是在传教早期,还引发了大量的社会冲突。如光绪九年(1883)二月十九(4月6日),浪穹县(今洱源县)乡民就曾烧毁该处法国教堂,男女大小十四人毙命。据《清实录》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初七(8月1日),兼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丁振铎奏:“法总领事违约,估运军火入省,绅民遗愤拦查,匪徒乘机焚抢教堂……”[3]当时,民众集结领署前,领事馆开枪伤人,绅民愤怒之余,将藏匿武器的平政街天主堂、主教公署及法国人住宅等建筑全部捣毁。与此同时,陆良、师宗、盐津、镇雄、昭通、永善等县,也有驱逐教士、捣毁教堂的事件发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有英国传教士到双江,先是企图分裂傣汉两族,但未得逞,接着又煽动拉祜族和佤族向傣族和汉族进攻,结果造成了5个月的大混乱,使当地许多人家破人亡,而传教士最终在清廷的保护下逃生。同年,由宗教入侵带来的中西矛盾还有发生在阿敦子(今德钦)的藏、汉僧俗围攻阿敦子教堂事件。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间,昭通的彝、汉各族也时常有捣毁教堂的事件发生。民国年间,西方的传教事业有所进展,且没有大规模宗教冲突的发生,但西人妄图在宗教方面彻底改变云南人信仰的初衷始终未实现。据统计资料显示,1929年大理教区有教友5 038人,预备入教者11 941人;1935年昭通地区有教友5 204人,预备入教者236人;1938—1939年间,昆明教区有教友11 482人,预备入教者4 162人[4]566-567。另一方面,在经济文化较为滞后的三江以外少数民族边疆区,基督教传播则取得了空前的进展。自古以来,云南境内“不同的民族,其对生活、社会和道德的理解迥然有别,而且构成他们自身和确定他们的民族性的价值观也完全不同……它是建立在那些使用文字和不使用文字的人之间的”[5]。“当时政府漠视边区,怒、俅两江流域归土司管理,人民苦于土司、喇嘛之苛索无厌,无处申诉。英帝国主义者乘势派人经营这一地方,设立教堂,实行煽诱。”[6]“外人(这里指英国人)更因傈僳素拜孔明老祖,乃捏造耶稣是孔明的哥哥以投其心理,傈僳相率入教者也有数万人。”[7]一些传教士通过巴结控制少数民族地方首领的方式传教,曾有佤族村寨头人规定:“哪个青年不信耶稣,不唱耶稣歌,就不准结婚。”[8]在教士的努力下,基督教1913年在瑞丽县的登戛寨发展了教徒,1918年在盈江县的邦瓦寨子扎下了根,1929年在梁河县的遮岛盖了教堂,1930年在陇川县的吕良乡扩大了入教人数,接着又发展到潞西县的弄邱寨。这样德宏的各县都有了基督教会。传教士编写景颇文课本,大讲景颇族与帝国主义的关系,编造景颇族的王子是英王乔治六世的谎言。1949年左右全州有教堂30多个,入教户数1 500多户,教徒6 000多人[9]。云南的基督教按国别分布于不同地域,英国教会势力主要集中于德宏、怒江、耿马、双江、孟连等地,法国教会活动区域则主要在滇越铁路沿线,美国主要在西双版纳、元江、墨江一带,基督教按国别的区域分布也间接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在云南的势力划分。
(二)歪曲人种
自19世纪后期开始,欧洲人普遍带有一种空前的民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主要是相对于黑人与黄种人而言的。中国的汉族是黄种人的代表,是一个与欧洲文明截然不同的族群,是那个年代里与欧洲人生存竞争角逐中的失败者,是西方人蔑视的对象,而在他们看来,与汉族疏风易俗的云南少数民族则与汉族(黄种人)有着许多方面的不同,以至于不少西方人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认识一直带有人种学方面的烙印。晃西士加尼曾在其《柬埔寨以北探路记》中写道:“他郎(墨江)居民之中,杂有一种土番,华人呼之为‘浩泥’。所穿服色,略似解思高斯。气体迥异,美秀好武,头面仿佛欧人,额狄面方,眉平目黑,皮铜色。”[10]
他认为彝族“是高加索人的黑色分支”[10]前言第2页。之后,众多的西方旅行家不但没有驳斥这一观点,反而提出种种假设证明以彝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与印欧人的亲缘关系。“那时的中国西南地区并不是黄色人种的出生地。他们可能是从别处迁徙来的,从以前的主人那里夺得了土地。”[10]前言第2页光绪二年(1876)巴伯(Baber)在云南调查马嘉理案期间,在途中遇到了两个彝族妇女,“分别大约是25岁和17岁,立即吸引了我们的眼球。我和我的两个同伴都认为她们无论在哪里都是非常漂亮的。她们比男人要白一些,椭圆形和充满智慧的脸让我们想到了高加索人”[11]3。可见,当时不少来滇的西人都以“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来看待云南的少数民族,这种观点是一种文化侵略的表现,也隐藏着帝国主义国家分裂中国的目的。针对20世纪早期西方学术界疯狂叫嚣的云南某些少数民族是“以色列人的后裔”或“印欧民族”的论调,1934—1937年,凌纯声、芮逸夫、陶云奎等一批中国学者开始深入云南各地州调查研究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历史渊源,同时,国民政府为“泯除界限,团结整个中华民族”,而明令称:“案查关于边疆同胞,应以地域分称为某地人,禁止沿用苗、夷、蛮、猺、猓、獞等称谓”[注]转引自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在战乱频繁的民国年间,这些工作虽然受时局、国力等因素的影响,但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文物掠夺
作为自古与中国内地及东南亚、南亚有着密切经济、文化联系的云南,其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灿烂夺目,留存下来的文物也十分丰富。清末至民国年间,由于云南政局不稳定、经济发展迟滞,本该由政府保护管理的文物没有得到应有的监管,民间则因为社会动荡导致众多家族财富急剧缩水,一些人迫于生计再加上文物保护意识淡薄等原因,将家族中价值连城的珍宝变卖,就这样,不少文物被西方国家的一些组织或个人以抢夺、盗取、“等价交换”等方式窃为己有。20世纪初,以法国少校亨利·马里·古斯塔夫·多隆为队长的中国西南民族调查队曾对包括云南的西南诸省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察,而这次考察的结果,不仅有冠冕堂皇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更是搜刮了“大量武器、工具、陶瓷器皿、货币、绘画等珍品”[12]。《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的作者、美国人约瑟夫·洛克起初来丽江只是采集植物标本,后来见到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字,便开始不遗余力地收集东巴经,据为己有。洛克对有历史价值的文物特别感兴趣,他在永宁得到了一件世代相传的土官小姐穿的黑彝贵族服饰全套,连首饰共三十多件。……他又在德钦藏族农奴主家里得到其祖传的皮盔皮甲一套和镶嵌宝石的古剑一把。这套皮盔甲是乃是用若干小块皮穿成,然后拼成胸甲、背甲、臂甲等大块……元代以后的铠甲都是制成整件,因而这套盔甲应是大理或更早时代的。1941年,另一个美国人在丽江县东北的观音庙里收到一尊铜制观音立像。这尊观音细腰跛足,满身璎珞,制作非常精美……是大理国段政兴在位(1148—1171)时制造的,距今有八百多年[注]参见李家瑞《帝国主义分子盗窃云南文物目击记》,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内部发行,1965年版,第194~195页。。
二
(一)社会风尚的变化
晚清西方开始渗入云南前,云南社会一直较为封闭,民众传统观念非常浓郁。随着中西交往的日益增多,云南人逐渐开始接触不同国籍、身份各异、社会地位“高人一等”的西方人,西方文化的渗入开始发生作用。火车、电灯、电话、报纸等新式科技成果的出现,在方便云南人生活的同时,也逐渐改变着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特别是琳琅满目的舶来品,使云南人的生活开始由单调、慢节奏的农业生活逐步向多元、快节奏的工业生活方式转变。云南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大家互相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它倡导民众生活安定、知足常乐、不重视时间与金钱观念,而近代工业社会则是一个人员、资金、技术、生产、产品等各要素不断流动的社会,它需要人们合理流动、善于竞争、强调时间和财富观念。新式生活方式与旧有习惯格格不入:如火车出行对时间的要求极其苛刻,不仅不允许出现“一袋烟的功夫”,个人哪怕是一分一秒的时间耽搁也只能由自身承担后果;列车、轮船、电影院等场所会把没有买票的人毫不留情地赶出场,这些被赶走的人则往往认为乡里乡亲,人情重于金钱;几乎所有来滇的西方人都反对云南人习以为常的民间巫术、妇女缠足、男性辫子(晚清时期)、包办婚姻、溺婴、卖女等现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无论如何,在西方文化的示范性影响以及云南人模仿、从众心理因素的作用下,西式生活方式逐渐走近了云南人的生活。投资工商业不再被认为是从事低下的职业,官僚带头疯狂逐利。时髦的洋装、洋烟、洋酒、洋火等产品大量进入云南,日用洋货成为云南居民竞相追逐、彰显身份的用品,“当交通不便之时代,滇省人民诚为朴实。今则不然。新人物辈出,或游学自海外归来,或服官他处返里,舍其旧有朴实之风,而沐新学文明之化矣。款客时必用洋酒,非此不恭;故一席达数十元,视为恒事。”[13]从前以等级来区分消费的规则逐渐变为了按金钱多少来区分。在与西方人的接触中,云南人逐渐发现旧礼虽然隆重、正式,但却繁琐、僵化且费钱。日常交往中,不少人很快习惯了脱帽、握手等西式礼仪,婚丧嫁娶活动也受西方文化影响,更加注重内容而不流于形式。《续云南通志长编》载:“近日行新式结婚礼,则多于公共礼堂宣读结婚证书,由男女及主婚人、介绍人、证婚人等以次于证书内盖印,并由男女交换证物,并向主婚、介绍人、来宾行三鞠躬礼或一鞠躬礼,不似旧仪之繁缛矣。”又“近则古礼尽废,往往于柩前饮酒食肉,未期而娶,亦恬不为怪矣。然未满百日,男不薙发,女不插簪。省会则仿西俗,于左臂缠黑纱,亦尚有饩羊遗意焉。”[注]参见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卷66《社会一·礼俗》,玉溪地区印刷厂,1986年版,第132~134页。随着城镇新式照明技术的普及、电影等新式娱乐方式的流行及商贸活动的增多,璀璨的夜生活使越来越多原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沉迷其中。在西方文化渗透下,云南妇女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经济宽裕的家庭开始让女孩子读书,新式社会分工也使妇女可以参与少部分工作。在家庭观念上,“四世同堂”逐渐被“核心家庭”的观念所取代。在一些少数民族边地,社会风气也有很大变化。过去由于巫术的盛行,造成了对生产的破坏,如解放前,陇川县邦瓦寨每年祭鬼支出折合稻谷16万斤以上,浪费惊人!大大小小无休止的祭鬼活动需要从事祭鬼的“董萨”(又叫“魔头”,原始宗教师)。由于杀一头牛或猪,董萨得一只前腿,他们为了多吃多占,于是杀牲祭鬼越来越厉害,而浸礼会来到后,摒弃祭鬼的方法,不与民争利,他们还根据景颇族稻谷新熟全寨人要杀牛宰猪吃新米这一习俗,变大吃大喝为教徒每家拿一箩新谷舂了,全寨摆在一起祷告,表示把初熟的稻谷送给上帝,把基督教的感恩节与景颇族吃新米这一习俗结合了起来。总之,信教户在宗教方面的支出最多占到信鬼户在祭鬼方面支出的十分之一[14]。近代以来,一些传教士进入云南后根据民族语音特点,借用拉丁字母创制了景颇文、载瓦文、拉祜文、佤文、傈僳文、苗文等拼音文字。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传教士博勒德(Samuel Pollard)曾在深入了解苗语的基础上,以苗语滇东北次方言发音为基准,通过拉丁字母及某些苗族符号来拼写苗文。苗族视这套苗文为苗族文化的宝贵财富。此外,西方音乐还部分地影响了某些少数民族的娱乐形式,景颇族的目瑙纵歌中就包含西洋管弦乐的因素,傈僳族的多声部无伴奏合唱也传承着复杂的西方音乐形式。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一些少数民族民众开始变得讲卫生、爱清洁、不酗酒,不少年轻人更加重视感情在婚姻中的作用,开始追求婚姻自由。
(二)专业教育的发展
西方势力渗入云南前,科举制一直是社会中最正统的教育。这种教育与选官制度相联系,使学校的教学内容完全服务于后者,八股文的固定形制,使人们的思想僵化甚至迂腐,一旦科举无望,社会上适合学习者的职业很有限,所以会出现鲁迅先生所塑造的“孔乙己”形象。19世纪后期,西方人的足迹已遍及全球,他们认为“不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势力的人,他们会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15]。既然云南的传统教育不能适应近代世界潮流的要求,西方历史上一直与教育相联系的载体——教会理所当然地承担起这个任务。它们创办了一些学校,尽管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但不可避免地要传播大量西方科学文化知识,除基督教神学外,文、理、工、商、医、农、法等专业都有涉及。“教会学校因受职业之训练,法语之专习,毕业后由教会派遣从事宣教,能得维持一家之生活。华法高等学校毕业生成绩优良者,可升学云南巴维大学,无升学之志望者,可介绍至滇越铁路公司或洋行通译或买办之职务。”[16]在西式教育的影响下,云南的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本土的专业教育问题。晚清文化名人周钟岳曾说:“现在的时代有许多事非专门人才不能办理,我们缺乏此项人才,所以规模稍大的事,都不能办理,即或勉强办理,也容易失败,如锡务公司、东川铜矿公司、个碧铁路公司、电灯公司等无一样不吃亏。”[注]参见董雨苍《东陆大学创办记》,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内部发行,1965年版,第1~2页。晚清至民国年间,云南公派及私学的留学生络绎不绝,像护国名将蔡锷、东陆大学校长董雨苍、云南炼锡公司缪云台等社会名人都曾远赴重洋留学海外,当然,由于条件有限,留学生总数毕竟有限,难以满足云南高等教育的需求。唐继尧主政时期,于1922年12月8日成立了东陆大学(即后来的云南大学)。该大学“以发扬东亚文化,研究西欧学术、造就专才”[注]参见董雨苍《东陆大学创办记》,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内部发行,1965年版,第6页。为宗旨,为云南培养了不少采矿冶金、土木工程、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人才。面对摩登的西式文化,当时不少年轻人都对其充满了激情向往。如在20年代,就有云南人开始接触世界语。1932年6月12日“云南世界语学会”正式成立。学会成立后第三天,即创办了《云南世界语运动》周刊,作为《云南民国日报》副刊出版。同年7月10日,学会在省教育会里开办世界语星期日早课班,原计划招生一百人,但报名截止时,人数竟达一百五十多人,云南世界语学会成立后,定期登记会员。一时登记入会的竟有四五百人之多[17]。近代西方教育无疑影响着世界教育行业的走向,对云南人来说,不论是远赴重洋、留学欧美,还是在本土接受教会教育或新式大学教育,都能够适应近代云南社会转型的要求,获得较大的个人发展的机会,因而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云南教育的发展。
(三)医学的发展
“基督教传道,多借医术之援助;盖鼓吹中国人崇拜基督教,必以广施外国医术之利益,为引入教门之妙策,因而欲为将来之牧师或传道师者,不可不身兼医生;故对于中国青年传播基督教,同时授之医术,即以之充将来传道之任;而教会对于医学教育所以不惜投巨资植势力者,实以此也。”[18]可见,早期的西医治疗是与基督教分不开的。晚清以来,来云南的西方传教士不胜枚举,他们在云南活动短则几日,长则数十年。为了个人健康,这些人往往随身带有一定数量的药物和简易医疗工具以备不测,不少人还懂得西医知识,而西医(特别是西医中的外科)相对于中医甚至是少数民族地方的巫术来说,是很好的医疗互补或替代方法,因而很有医疗诊治市场。云南由于气候的原因,时常会周期性爆发鼠疫。在蒙自,“传教士用大剂量的催吐药,成功地抵制了鼠疫。”[19]新式的科学治疗方法往往令周围百姓大为称奇。《新纂云南通志》也谈到了“路南州:……城外富乡路美邑,距城十五里,设大教堂一处,建自光绪十五年(1889),育婴、施药”,“阿迷州:东乡噜都克寨,距城百九十里,设小教堂一处,建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施药”[4]572。越是边疆地区、越是缺医少药的地区,传教士们就越是在医疗方面下功夫。1949年前,在景颇族聚居的地区,传教士善于在群众患病时伸出帮助之手:生小病吃药不要钱,生大病则送到缅甸南坎医院免费治疗。日常生活中,教士常常对群众进行讲卫生的宣传。在省城昆明,交通便利、人口集中、市场需求旺盛,教会医院以其雄厚的医疗实力成为当地不容忽视的西医力量。光绪二十七年(1901)法国领事署在昆明华山西路创办的大法医院是云南最早的西医医院。《清实录》记载的“法国前于滇省城内设有施医院,滇民就医者众。……光绪三十四年(1908),交涉司高而谦祥称:‘该医院心存济世,不分畛域,甚属可嘉……’”[20]。该院开始时实行免费治疗,后来逐渐收取挂号费、医药费及住院费。由于大法医院院址狭小,无法满足日益增多的病人,1935年法国人又在昆明巡津街设立甘美医院,大法医院改为门诊部,直到1941年由云南省政府接管。宣统三年(1911)昆明高地巷还成立了圣保罗孤儿院,该孤儿院附设贫民诊所,只是知道的人不多,医疗效果不佳。1920年,英国教会在昆明开设了惠滇医院,该院院址在金碧路,成为昆明另一家比较著名的英式医院。这些医院的建立给云南带来了一阵新的医疗诊治之风,加速了云南医疗近代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