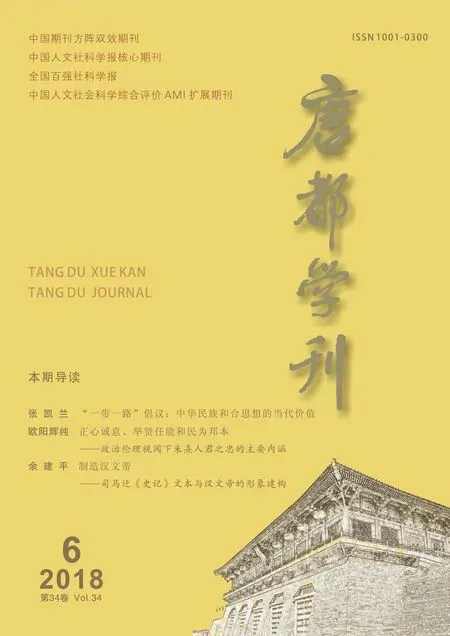唐宋人之“陶王”接受论
张 进
(西安文理学院 文学院,西安 710065)
在宋代以后的人看来,称王维是陶渊明的学习者、后继者,是毫无疑问的。然现存文献资料中,始终未见唐人将王维与渊明相提并论的文字。刘禹锡以王崔(颢)、皎然以王韦(应物)、刘昫以王杜(甫)并举(详见下文),而钱钟书《谈艺录》里说唐人“少陵、皎然以陶谢并称,香山(白居易)以陶韦等类,大拙(薛能)以陶李(白)齐举”[1]卷24,90,皆未及“陶王”之例。唐人为何不并称“陶王”?宋人为何推崇“陶王”?宋人对“王维讥陶潜”有何异议?宋人的“陶王”并称有何意义?很值得探究。
一、唐人为何不并称“陶王”
先说陶渊明。唐人对陶的接受,大致说来,多从渊明为人与处世态度来着眼,较少论及陶诗的文词风格。即如钱钟书说“颜真卿咏陶渊明,美其志节,不及文词”[1]89。以下举几位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来作分析。
孟浩然诗中有三首言及陶渊明。《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云:
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归来冒炎暑,耕稼不及春。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涧滨。因声谢朝列,吾慕颍阳真。[2]卷1,15
此首写诗人自长安落第归来的心情和未来的打算,首尾四韵“嘉陶”“慕颍”,表明他要学“日耽田园趣”的陶渊明和“洗耳于颍水滨”的许由,隐居田园,不再出仕。又《李氏园卧疾》云:“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2]卷4,52又《口号赠王九》云:“归人须早去,稚子望陶潜。”[2]卷4,57都是推赏陶渊明的清闲自适、超脱世俗,并要以此为榜样。
李白心中始终抱有建功立业的理想,虽几入长安,志不得酬,然此心不泯。59岁遇赦后在岳阳作《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抒发了要为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统一而出力的情怀:
……今兹讨鲸鲵,旌旆何缤纷。白羽落酒樽,洞庭罗三军。黄花不掇手,战鼓遥相闻。剑舞转颓阳,当时日停曛。酣歌激壮士,可以摧妖氛。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3]卷180,1838
末两句说,像陶渊明那样拘牵于小节而消极避世,是不值得与之为伍、不值得效仿的。对陶渊明的退隐不予认同。不过他之前也曾在寄好友韦冰的诗中表示过对陶渊明的推许,《寄韦南陵冰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中说:“梦见五柳枝,已堪挂马鞭。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3]卷172,1770
王维对陶渊明也有不予认可之处。《偶然作六首》其四云:“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中心窃自思,傥有人送否。白衣携壶觞,果来遗老叟。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倾倒强行行,酣歌归五柳。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4]卷1,74王维觉得陶渊明弃官归隐,只顾自己饮酒而不问家中生计,无疑是愧对妻子的。当然他的田园诗是颇得陶诗之精髓的。
杜甫《遣兴五首》其三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3]卷218,2291认为陶潜虽然避世隐居,但也并未进入忘怀得失、通达人生的境界。他对五个儿子的不求上进还是很挂怀的。杜甫还以唐人的审美眼光,遗憾陶诗过于枯槁。不过他对陶的诗思、诗才是极为推服的,且以陶、谢并论:“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3]卷226,2443,“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3]卷216,2263。
韦应物是公认的学陶诗人。四库馆臣《韦苏州集提要》称其“五言古体源出于陶,而镕化于三谢,故真而不朴,华而不绮”[5]卷1,78。韦有《与友生野饮效陶体》和《效陶彭泽》两首,写的都是关乎饮酒之事,前首曰“于时不共酌,奈此泉下人”[5]卷1,82,后首曰“尽醉茅檐下,一生岂在多”[5]卷1,83。《东郊》一诗先写拘束于公务,因而案牍劳形。次写春日郊游,快乐无限。再写归隐不遂,越发慕陶,诗末有“终罢斯结庐,慕陶真可庶”之句[5]卷7,139。可见韦诗基本是围绕着饮酒和归隐两点来效陶和慕陶的。
白居易在前期强调“风雅比兴”传统和肯定“讽喻诗”时,对晋宋诗人多有批评,《与元九书》指出:“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6]卷45,490在后期的闲适诗里,对陶多有认同。作《效陶潜体十六首》,序云:“因咏陶渊明诗,适与意会,遂效其体,成十六篇。”[6]卷5,56其中一篇专以咏陶:“吾闻浔阳郡,昔有陶征君。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尝为彭泽令,在官才八旬。……归来五柳下,还以酒养真。人间荣与利,摆落如泥尘。先生去已久,纸墨有遗文。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我从老大来,窃慕其为人。其它不可及,且效醉昏昏。”[6]卷5,59白氏的“效陶潜体”,依旧循着韦应物的“饮酒”和“归隐”两个点展开,窃慕陶之摆脱“人间荣与利”的超然处世态度。晚唐诗人刘驾有《效陶》一诗,说“大恢生死网,飞走无逃处”“我有杯中物,可以消万虑”[3]卷585,6784,表达的也是生死不可逃、以酒消世虑的意思。
柳宗元也被认为是继陶一派的诗人,可惜柳宗元的诗文中并无留下咏陶的文字,他对陶诗作何评价,我们不敢妄加臆测。
晚唐诗人薛能,字大拙,自负过高,说:“李白终无取,陶潜固不刊。”[3]卷561,6521将陶李齐举而又同贬,实为狂傲之徒。
从诗人们对陶诗的接受视角看,或推崇或批评,主要在首肯心折陶之“为人”的精神境界,唯杜甫推服其“诗思”,却又不欣赏其“枯槁”的“诗风”。
再说王维。唐人不仅称道王维“以孝闻”“有高致”的品行,更欣赏王维“诗兴入神”“诗通大雅之作”的境界[7],欣赏其诗“秀雅”“澄澹”“精致”“华彩”的风格。如殷璠《河岳英灵集》说:“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成珠,着壁成绘。”[8]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纪》说:“王维与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9]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说:“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10]刘昫《旧唐书》说:“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若隋珠色泽,无假淬磨;孔玑翠羽,自成华彩。”[11]足见唐人对王维诗的接受视角是全方位的、多视角的。
池洁《唐人应试试题与唐代诗歌审美取向》一文通过对唐人应试诗题中典出六朝诗歌居多情况的分析,指出“崇尚六朝诗歌乃是唐代诗歌审美取向的主流,唐诗正是学习六朝诗歌而结出的硕果”[12];认为陈子昂诗歌理论对唐代诗风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长期以来文学史对此做了夸大描述[12]。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但准确地说,唐人正是接受了陈子昂对六朝诗的批评,在对六朝诗的扬弃过程中,取其精华,为我所用,遂形成了唐代以崇尚典雅华彩、清丽隽永、雄浑高远、自然飘逸为主的诗歌审美取向。这里包含了谢灵运的富丽精工、谢朓的清丽秀发、庾信的清新、鲍照的俊逸等等。王维的边塞诗、应制诗、田园诗、送别诗……正兼具了上述风格,所以与唐人的诗歌审美取向相一致,也与恢宏绚丽的大唐气象相一致。因此唐代宗《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称誉王维为“天下文宗”“名高希代”[13]。
池洁文中还提到唐人应试诗题中,有三个诗题出自陶渊明的诗歌[注]张明华、魏宏灿的《论梅尧臣诗对陶渊明的接受》一文中有数据统计,载于《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作者说:“从中可见唐人对陶诗的喜爱与推崇”,“陶渊明在唐代就已被公认为第一流的大诗人”[12]。这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三个诗题出自两首诗。《拟古诗》之七“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一诗,抒发人生无常、良景易逝之叹;《饮酒诗》之八“秋菊有佳色”一诗,借秋菊抒发忘忧遗世之情。如前所述,唐人对陶王诗的接受视角有所不同,对王主要在其“为诗”的艺术境界;对陶主要在其“为人”的精神境界,而对陶诗的艺术性还未真正发抉。宋人《蔡宽夫诗话》就说:“渊明诗,唐人绝无知其奥者。唯韦苏州、白乐天尝有效其体之作,而乐天去之亦自远甚。”[14]钱钟书也说少陵、皎然、香山、大拙等人“虽道渊明,而未识其出类拔萃”[1]90。
可以说在唐人眼中,陶渊明诗与王维诗的可比性不是很大,故不曾有人将“陶王”相提并论。
二、宋人为何推崇“陶王”
到了宋人,才将“陶王”捉置一处,有了摩诘、渊明并称,辋川、斜川对举的提法。
据笔者对现存宋代文献资料的检索,最早将“陶王”并称的当是北宋的郭祥正与苏轼。郭祥正与苏轼、黄庭坚等人交游甚密,与梅尧臣亦有交集。
在宋人中,梅尧臣(1002—1060)首倡平淡,他在《依韵和晏相公》中说:“微生守贱贫,文字出肝胆。……因吟适情性,稍欲到平淡。”[15]卷28,211道出了他作诗的动机与审美追求。梅公酷好陶诗[注]陶诗入选唐人应试试题的三个诗题:(1)《日暮天无云》,典出《拟古诗》之七。(2)《春风扇微和》,出典同上。(3)《秋菊有佳色》,典出《饮酒诗》之八。其中第(2)题曾被考过两次。见池洁文章第152页。,是他将陶诗风格归为“平淡”,如《答中道小集见寄》说:“诗本道情性,不须大厥声。方闻理平淡,昏晓在渊明”[15]卷24,182,《寄宋次道中道》说:“中作渊明诗,平淡可拟伦”[15]卷25,第1099册,187。他用心研习陶诗,又“学唐人平淡处”,遂以平淡诗风著称,为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郭祥正(1035—1113)当涂(今属安徽)人,《宋史》言他:“母梦李白而生。少有诗声,梅尧臣方擅名一时,见而叹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16]郭亦酷好渊明诗与王维画,诗中屡屡咏及,其《清江台致酒赠范希远龙图》诗中说:“谁展摩诘图,而把渊明杯。”[17]以为王摩诘之画与陶渊明之酒是人间之最美。
苏轼(1037—1101)参加科考那年,梅尧臣是考官。他赏识苏轼的文章,苏轼亦敬慕他的为人与诗文,从此结下深厚情谊。苏轼受梅公影响,加之外任、贬逐数年,对陶诗有深切的体会。又因他也喜欢王维诗画与韦诗,所以当黄庭坚为李公麟(伯时)画的王维像题诗时,苏轼欣然次韵:“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欲觅王右丞,还向五字求。……”[18]唐宋以来,司空图有“王韦”并称,梅尧臣有“陶韦”并举,其《涂中寄上尚书晏相公二十韵》说:“下言狂斐颇及古,陶韦比格吾不私”[15]卷28,212,至苏轼,将陶、王、韦并列,指明三者的承继关系,并强调王维诗的特色在五言诗,这就使“陶、王”诗的关系首次得以确认。苏轼晚年对陶诗以及韦柳的“平淡”诗风做出了精辟的阐释与高度的评价:
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19]
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评韩柳诗》)[20]卷67,2109
李杜之后……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余子所及也。(《书黄子思诗集后》)[20]卷67,2124
苏轼指出陶、韦、柳诗歌,在看似朴质清癯、简古淡泊的文字中,实包含着绮丽细密和深厚韵味,这就与王维诗的平淡、清丽、精致、华彩有了更多的相通。苏轼之论,对宋代尚平淡的诗美观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自苏轼后,“陶王”并论流播开来,成为宋代的时尚话语。黄庭坚在《追和东坡题李亮功归来图》诗中云:“欲学渊明归作赋,先烦摩诘画成图。”[21]王之道在《秋兴八首追和杜老(其三)》诗中云:“摩诘家风非世有,渊明心性与时违。”[22]杨万里在《书王右丞诗后》诗中云:“晩因子厚识渊明,早学苏州得右丞。”[23]卷7,70又在《归来桥》诗中云:“已赓彭泽辞,更拟辋川诗。”[23]卷30,319毛幵在《樵隐词·念奴娇》中云:“追念辋水斜川,有风流千载,渊明摩诘。”[24]汪藻在《跋折枢密锦屏山堂图》诗中云:“便觉斜川辋川,去人不远也。”[25]卷17,156李处权在《翠微堂·为刘端礼题》诗中将王维、陶渊明与汉代郑朴、唐代贺知章四子相提并咏:“子真隐谷口,摩诘居辋川。渊明道上醉,知章井底眠。风味有数子,较量谁后先。”[26]卷1,589陈师道指出:“右丞、苏州皆学于陶,王得其自在。”[27]陈振孙指出:“维诗清逸,追逼陶、谢。”[28]卷16,799舒岳祥在《刘正仲和陶集序》中指出:“自唐以来,效渊明为诗者皆大家数,王摩诘得其清妍,韦苏州得其散远,柳子厚得其幽洁,白乐天得其平淡。”[29]卷10,425
处于两宋之交的汪藻在《翠微堂记》中,对陶、谢、王的“山水之乐”做了精彩的论述。他说:
山林之乐,士大夫知其可乐者多矣,而莫能有。其有焉者,率樵夫野叟川居谷汲之人,而又不知其所以为乐。惟高人逸士自甘于寂寞之滨,长往而不顾者为足以得之。然自汉以来,士之遁迹求志者不可胜数,其能甘心丘壑使后世闻之翛然,想念其处者亦无几人,岂方寄味无味,自适其适,而不暇以语世耶。至陶渊明、谢康乐、王摩诘之徒,始穷探极讨,尽山水之趣,纳万境于胸中,凡林霏空翠之过乎目,泉声鸟咔之属乎耳,风云雾雨,纵横合散于冲融杳霭之间,而有感于吾心者,皆取之以为诗酒之用,盖方其自得于言意之表也。虽宇宙之大,终古之远,其间治乱兴废,是非得失,变幻万方,日陈于前者,皆不足以累吾之真。故古人有贵于山水之乐者如此,岂与夫槁项黄馘、欺世眩俗者同年而语哉![25]卷18,160
士大夫一般多喜欢山林之乐,但在汪藻看来,真正能知山林之乐的高人逸士并无几人,难道是他们“寄味无味,自适其适”,不暇以语世人?至陶、谢、王这样的高人逸士,始能以贴近的心态探究山水之趣,以虚静的胸怀接纳万境之美,林霏空翠、泉声鸟咔、风云雾雨,极尽变化,过之于耳目,感之于内心,借诗酒以抒发,其“自得”于心者,又远非言意所能表现,而更在于其穿越时空局限,超脱世间得失,而从大自然中领悟生命之本真。这才是山水之乐的宝贵之处与根本所在。汪藻之论,将陶、谢、王之“山水之乐”及其所达到的精神境界,给予了精准的诠释。
由上举数条,概知宋人将“陶王”并称,基于三个认可:一是二人所具有的超脱世俗的高人品格;二是能知山水之乐,从大自然中体悟生命的本真;三是王维效法渊明之诗,其风格的主导方面与陶诗接近。这三个认可,与宋朝的政治环境和宋人的审美心理有密切的联系。
宋朝文人主政,北宋政治改革的风云、南宋主战主和的对立,使得宋朝的党争一波接一波,文人士大夫遭贬谪成家常便饭。他们被迫离开政治中心,或外任州县,或赋闲乡村,与自然山水有着比较亲近的接触,对山水之乐也有了自己的体会。如王禹偁(954—1101)《朝簪》诗说:“一戴朝簪已十年,半居谪宦半荣迁”[30]卷10,102,《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文说:“公退之暇,……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30]卷17,166宋人也因此对王维的辋川诗与辋川画拥有了特殊的兴趣,赏玩者仿效者层出。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唐代四大诗人》中说:“宋元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的阶段,社会矛盾日趋复杂。一般有识之士,他们的心情往往是寂寞的,因此向往于一种清高幽寂的境界。……在这种情况下,王维晚年诗中那种幽寂的意境便很自然地与山水画融为一体。”[31]宋代扩大了科举取士的人数,出身寒微的士子所占比例增加,他们一般生活俭素,性不好奢华,易对平淡之美发生兴趣。他们在追慕陶、王的同时,拥有了一种超然物外的品格节操,也形成了有宋一代尚平淡的审美取向。
与唐人不同的是,宋人一方面将陶诗归为平淡,又充分看到陶诗平淡里所包含的绮丽;一方面欣赏王维诗歌的多种题材与风格,又特别偏好其山水田园诗所表现出的闲淡秀雅。这样,在宋人眼里,王维与陶潜在品格与诗风上就非常靠近了。宋人因此将“陶王”作为山水田园诗歌与平淡诗风的代表人物。
三、宋人对“王维讥陶潜”有何异议
王维晚年作《与魏居士书》[4]1088,劝说魏居士走出山林,应朝廷征诏出来做官,以平和、等同的心态对待仕隐问题,不可太在乎隐士之名而废了君臣之义,“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注]“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语出《论语·微子》:“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为此,他先批评了拒仕的许由、嵇康。他说许由“闻尧让,临水而洗耳”,是“恶外垢内”,连一个旷士都算不上,离佛教所说的“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还差得远。他说嵇康自谓“顿缨狂顾,逾思长林而忆丰草”,若消除“异见”,能“等同虚空”(佛教谓一切法在虚空上无差异)、“知见独存”,则“顿缨狂顾”与“俛受维絷”“长林丰草”与“官署门阑”有何差异?接下来,王维也讥讽了陶渊明:
近有陶潜,不肯把板曲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当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按:赵殿成《王右丞集箋注》卷18此处为“恤”)其后之累也。[4]1095
在他看来,陶潜不肯执手板弯腰见督邮,是“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注]参见《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此乃太执着于自我,以至于“忘大守小”,是只顾一时而不恤其后之累的做法。王维最后引孔子“无可无不可”之语,提出:
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仁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4]1095
王维在理想与现实、仕与隐的矛盾冲突中,融通了儒释道三家思想[注]王维提出的“知见独存”“身心相离”“适意”,近于庄子提出的“见独”“坐忘”“忘适之适”。,以“适意”为本,“为亦官亦隐、身官心隐找到了立论基点”[32]。总之,陶选择了遁隐,王选择了心隐。
值得关注的是,王维的“讥陶”,在唐人那里并未引起反对,却在宋代受到非议。
葛胜仲(1072—1144),字鲁卿,官至文华阁待制,气节甚伟,著名于时。他在《次韵良器真意亭探韵并序》中,批评王维、杜甫“不知渊明”。序云:
《晋》《宋》二史皆载陶渊明不肯束带见乡里小儿,遂弃彭泽归,意谓淡于荣利,足名高隐。不知适所以訾之也。古之达人胜士,语默隐显,如固有渊明襟量,如止水,澄之挠之,未易清浊,岂以把板屈腰婴意遽违初心哉。……杜拾遗、王右丞辈固一臭味也。然杜诗云:“渊明避俗翁,未得为达道。观其着诗集,颇亦恨枯槁。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王书云:“陶潜不肯见督邮,弃官后贫,《乞食》诗云:‘扣门言辞拙’,是屡乞而多惭也。一惭之不忍,乃终身惭乎!盖人我攻中之累也。”世人不知渊明类若此。渊明何訾焉?……
诗云:
我爱陶渊明,脱颖深天机。丛菊绕荒径,五柳摇幽扉。……少陵罪责子,颇谓达道非。右丞鄙乞食,更以人我讥。乃知第一流,尚此知音稀。……愿以靖节语,佩之如弦韦。[33]
葛氏认为,陶渊明是有襟量气度的人,岂肯以屈身事奉而改变初心。《庄子·大宗师》说:“嗜欲深者天机浅”。葛氏以为陶渊明正是能超脱嗜欲而天机深厚具有大智慧的人。而杜甫、王维臭味相投,杜甫罪他“责子”,王维鄙他“乞食”,讥他“一惭之不忍,乃终身惭”,是“不知渊明”的一类人!他为渊明乃第一流人品却少知音而抱憾,愿以渊明之语来时时警戒自己。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宋末学者王应麟(1223—1296)力挺葛胜仲的观点,他在《评诗》中引苏轼之语,尊陶潜而抑萧统、杜甫和王维三人:
东坡云:“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求食,饱则具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葛鲁卿为赞罗端良为记,皆发此意。萧统疵其闲情,杜子美讥其责子,王摩诘议其乞食,何伤于日月乎?[34]
在他看来,陶渊明是一位不掩真情的贤人,萧、杜、王三人讥讽、疵议陶渊明,并不能减损其光辉。
陈渊(1075?—1145)为杨时的弟子,南宋著名理学家。他在《答翁子静论陶渊明》中,认为翁氏论王维责渊明“非是精当”,而苏轼论渊明亦未做到“义之尽也”。他说:
所论王摩诘责渊明,非是精当。顷闻之,苏黄门(指苏轼)称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人为嫌。欲已则已,不以去人为高。饥则叩门以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若此语深得渊明之心矣。今公所谓真者,无乃几是乎。虽然此语可谓深得渊明之心,而不可谓义之尽也。渊明以小人鄙督邮而不肯以己下之,非孟子所谓隘乎?仕为令尹,乃曰徒为五斗米而已,以此为可欲而就,以此为可轻而去,此何义哉?诚如此,是废规矩准绳,而任吾意耳。……渊明固贤于晋宋之人远矣,于此窃有疑焉。[35]
陈渊认为,苏轼赞渊明“贵其真”,固然深得渊明之心,但不能说尽到了“义”。《论语·微子》中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在陈渊看来,渊明出仕为县令,把自己应尽之责视为“五斗米而已”,可轻易放弃,何义之有?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存疑义。由此看来,他的观点与王维议陶渊明“忘大守小”说倒有些接近。其实,苏轼并非不尽义。他曾作《灵壁张氏园亭记》说:“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张氏)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20]卷11,369苏轼称道古之君子及张氏子孙,适性而为,顺时而动,能将“仕”与“不仕”“行义”与“适意”两相兼顾,与王维所阐发的“适意”,意思比较接近。
宋人的议论,又引发了后人的议论。明李贽《续焚书》卷3《王维讥陶潜》条说:
此亦公(指王维)一偏之谈也。苟知官署门阑不异长林丰草,则终身长林丰草,固即终身官署门阑矣。同等大虚,无所不遍,则不见督邮,虽不为高,亦不为碍。若王维是,陶潜非,则一陶潜,足以碍王维矣,安在其为无碍、无所不遍乎?[36]540
李贽认为既然王维以“同等大虚”的观点来抹去仕与隐、长林丰草与官署门阑的区别,那么,陶潜不见督邮,亦不为碍,无可厚非。倘若一定要分辨孰是孰非,则如何见得“无所不遍”呢?意谓王维讥讽陶潜,是站不住脚的。明黄廷鹄《诗冶》卷11说:
陶潜《乞食》评:……右丞乃云:“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与腐鼠之吓何异?然“万户伤心”亦为一惭尔,佹两失之矣。[36]862
黄氏借庄子讲的鸱得腐鼠而对空中飞过之鹓雏发出“吓”的怒斥声的故事,讥讽王维不知渊明之清高自守,王维作“凝碧诗”,亦为一惭,他讥人亦为人讥,此两失之矣。可见后人之论,亦比较苛责。
钱钟书论《陶渊明诗显晦》中说:“渊明文名,至宋而极。”[1]卷24,88宋人出于对渊明人格的尊崇,容不得有对他的訾病,故对王维讥陶潜予以反唇相讥,乃在情理之中。但宋人对王维赞誉的声音,远远高出指责的声音。
总起来看,宋人将“陶王”并称,确立了一个诗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继承关系,确立了一种尚平淡的审美理想,这在文学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从陶、王在唐宋时期的接受程度来看,唐代王高于陶,宋代陶高于王,呈现这种不同的接受情况,正是文学接受研究所要关注和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