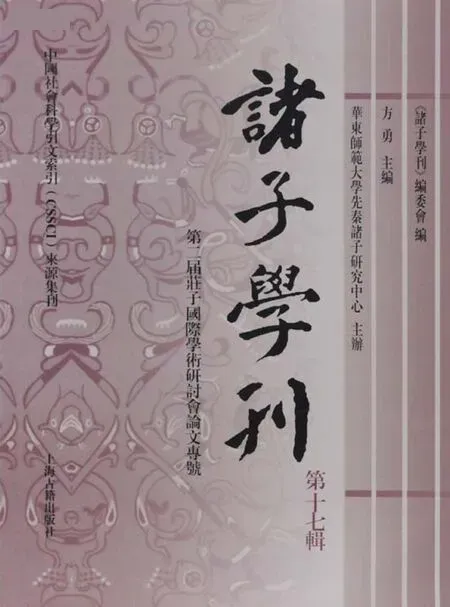纂微與新解
——褚伯秀對《莊子》注解的繼承與補充
(臺灣) 簡光明
内容提要 褚伯秀注解《莊子》而以“義海纂微”爲書名,“義海”正顯示歷代《莊子》義理注解如海洋一般浩瀚,“纂微”則彰顯褚伯秀從衆多注解之中披沙揀金纂輯微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説其書“蓋宋以前解《莊子》者,梗概略具於是”,“伯秀編纂之功亦不可没矣”。其所强調者爲該書“編纂之功”,而忽略褚伯秀“創新之見”。褚伯秀對於歷代《莊子》注解多所繼承,“纂集諸家之説”是其用功之處,諸家解説未能盡洽文本者,亦能提出新解,“斷以己意”是其用心之處。褚伯秀的用功之處,歷代學者多能説明;其用心之處,則尚待完整探究。唯有將褚伯秀的用功之處與用心之處展開,才能説明其爲宋代《莊子》注之集大成。
[關鍵詞] 莊子 郭象 林希逸 范應元 褚伯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前 言
莊子爲先秦重要思想家,影響中國文人的生活,因此在歷代《莊子》注解中,以思想闡發爲主,標音注義與評點爲文爲輔,纂輯歷代《莊子》注解的集解之作則兼包義理、音義與文學。南宋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與明代焦竑《莊子翼》、清代王先謙《莊子集解》、郭慶藩《莊子集釋》均爲纂輯歷代《莊子》注解之作,相較之下,褚伯秀除了纂輯之外,兼評諸家注解的得失,並能提出問題,對於諸家注解未能適切解説處,亦能提出新解,可謂難得。
宋末天慶觀道士褚伯秀,號雪巘,錢塘人(1)見嚴靈峰《輯褚伯秀老子注叙》,《經子叢著》第七册《老子宋注叢殘》,(臺灣)“國立”編譯館1983年版。,以清節苦行著聞(2)鄭元祐《遂昌雜録》,《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7頁。,入元尚在(3)周密《癸辛雜識後集》説:“至元丁亥九月四日,余偕錢菊泉至天慶觀訪褚伯秀,遂同道士王磐隱游寶蓮山韓平原故園。”“至元”爲元世祖忽必烈的年號,丁亥年爲至元二十四年(1287),南宋亡於至元十六年(1279),可見褚伯秀入元尚在。。《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書,成於咸淳元年(1265),下距宋亡僅十四年。褚伯秀纂集郭象、吕惠卿、林疑獨、陳詳道、陳景元、王雱、劉概、吴儔、趙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應元十三家之説,斷以己意,謂之“管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説:“蓋宋以前解《莊子》者,梗概略具於是。其間如吴儔、趙以夫、王旦諸家,今皆罕見傳本,實賴是書以傳,則伯秀編纂之功亦不可没矣。”(4)紀昀等《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提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46,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26頁。謝祥皓《莊子導讀》説:“此書的價值乃在於保存了兩宋各家注《莊》重要資料。”(5)謝祥皓《莊子導讀》,收入《莊子論文集新編》,(臺灣)木鐸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頁。關鋒《莊子内篇譯解和批判》認爲該書:“可謂集宋代注釋之大成,‘管見’亦多有可取。”(6)關鋒《莊子内篇譯解和批判》,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380頁。楊儒賓《莊周風貌》説:“由於唐宋古注完整流傳下來的不多,因此,褚書保存的文獻價值,頗受後人重視。此書可視爲宋人注莊的一個縮影。”(7)楊儒賓《莊周風貌》,(臺灣)黎明文化1991年版,第231—233頁。當代莊學研究者多推崇褚伯秀在莊學史上的編纂之功。
劉振孫《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原序》説:“一日,中都道士褚伯秀持所集《莊子解》且附以己見示余。余喜其會萃之勤、去取之精,而所見之多有超詣也。”學者論“會萃之勤”與“去取之精”者多,“所見之多有超詣”則發揮較少。本論文分别探討褚伯秀的“纂微”與“己意”,説明其對《莊子》注解的繼承與新解,並略作檢討。
一、 纂微: 褚伯秀對《莊子》注解的繼承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指出,伯秀纂集郭象、吕惠卿、林疑獨、陳詳道、陳景元、王雱、劉概、吴儔、趙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應元十三家之説,而吴儔、趙以夫、王旦諸家今皆罕見傳本。褚伯秀對於歷代《莊子》注解的繼承,以郭象、范應元爲最多。若我們將注解的定義放寬,納入歷代士人關於《莊子》的評論,則褚伯秀對於蘇軾《莊子祠堂記》的重視,未必在諸家之下,故以下略論褚伯秀對三家接受與評論,説明其繼承。
(一) 評論郭象《莊子注》
郭象《莊子注》是中國莊學史的權威之作,宋代士人多喜歡徵引其注文,也因其時代較早,褚伯秀將郭象注文置於《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各家注之首。
郭象注《天下》“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句説“揮斥高大之貌”,褚伯秀説:“圖傲乎一句頗難釋,諸解唯郭註近之。”(8)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卷104,第15頁。本文引用《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注文采用此一版本,爲避免繁冗,後僅標示卷數與頁碼。郭象注《逍遥遊》“神人無功”句説“理至則迹滅”,褚伯秀認爲:“郭氏註‘理至則迹滅’,其説盡之。”(卷1,第13頁)《應帝王》“儵忽混沌”寓言,郭象注僅“爲者敗之”四字,褚伯秀説:“右章計七十四字,郭氏引《道德經》一言以蔽之,簡要切當,莫越於此。”(卷22,第6頁)《老子》二十九章説:“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郭象引用《老子》“爲者敗之”一語説明“儵忽渾沌”寓言,褚伯秀認爲既“簡要”又“切當”,宋代注家如吕惠卿、林疑獨、陳祥道、陳碧虚、吴儔、趙以夫、林希逸之説所不及。
《盜跖》“孔子往見盜跖”寓言,郭象將該寓言分爲三章,只在章末加注:“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己,雖盜跖不可御也。”“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内,然後行高而士貴耳。”“此章言知足者常足。”褚伯秀認爲相當得體:“故郭氏於三章之下略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意。”(卷95,第8頁)一般注解者“覩其迹而未得其心”,以人廢言,以盜跖之言爲强辯,不去留意其中有理之處,注解當然不適切。郭象不詳細注解,只於“三章之下略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意”,對《莊子》大意掌握較爲精當。
郭象注解《莊子》,有時整段文本都没有注文,如《説劍》即是。褚伯秀認爲這樣的做法是適切的,在没有注解的地方,反而可以看到郭象對莊子思想的掌握:
蓋南華痛憫世人躭於物欲,失性而不自知,故創爲是論,以明復性者在乎中有所主,防欲如讐,心纔有覺即推理以勝之,不待乎劒士夾門,日夜相擊,然後求夫善説者以止之也。此寓道於技以立言,而解者往往以外象求合,使正大之理爲之久湮,併陷至言於辯者之囿,可爲太息。兹因鑚硏至極,遂悟反流歸源,庶符立言本意云。子玄於是經,得其心髓,雄文奥論,與之並駕争驅,獨此篇不著一語,使人深造而自得之也。恐或者於此乎致疑,故不得不辯。(卷97,第10頁)
《養生主》“庖丁解牛”寓言中,庖丁自謂“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此即莊子“寓道於技以立言”。注解者若不能瞭解莊子“立言本意”,將《説劍》視爲縱横家言,就會導致“以外象求合,使正大之理爲之久湮,併陷至言於辯者之囿”的結果。郭象能够瞭解莊子本意,故對於《説劍》“不著一語,使人深造而自得之”。可見褚伯秀以郭象知《莊子》之深,在在都説明其對郭象之推崇讚譽(9)《天下》“惠施多方,其書五車”以下,郭象不注,褚伯秀引用其師范應元的説法:“郭氏知此而不明言,使觀者自得。”頗爲讚譽,亦是此意。其實,郭象不注未必是想使觀者自得。蘇軾《莊子祠堂記》説:“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讓王》《説劍》皆淺陋而不入於道”,乃“昧者勦之以入其言”,將《説劍》視爲僞作。若依蘇軾的説法,郭象之所以不注《説劍》,可以解讀爲郭象將之視爲僞作而不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常常點出郭象注解不適切之處,如説“郭氏乃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非莊子本意”(卷1,第11頁),“無隱范先生講宗吕注,兼證郭氏小失”(卷65,第8頁),“郭氏以‘中’釋‘督’而不明”(卷5,第7頁),“郭氏從‘顯則明’爲句,後來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卷34,第14頁),“‘覩於泰’非郭氏所謂‘多於本性’也”(卷42,第15頁)。可見褚伯秀對於郭象注文不符合《莊子》思想者,亦能論其缺失(10)簡光明《宋人對郭象〈莊子注〉的接受與評論》,《諸子學刊》第八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4月版,第191—214頁。。
(二) 評論蘇軾《莊子祠堂記》
莊子思想的定位一向是莊學史關注的課題,司馬遷《老莊申韓列傳》説:“(莊子)其學無所不窺,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11)司馬遷《史記》,(臺灣)鼎文書局1977年版。司馬遷依據《漁父》《盜跖》《胠篋》等篇的寓言,而有“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的判斷,此一莊子思想定位的判斷爲後代士人所接受而形成主流觀點。蘇軾《莊子祠堂記》認爲司馬遷判斷莊子思想的定位是“知莊子之粗者”,因而提出莊子陽擠而陰助孔子的新觀點,認爲莊子對孔子是“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12)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二册,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47頁。。蘇軾的觀點對宋代莊學發展的影響甚深,有凌駕司馬遷之勢,成爲宋人論莊子思想定位的新權威(13)簡光明《宋代“援莊入儒”綜論》,《嘉大中文學報》第二期2009年9月,第121—150頁。。
在莊子思想定位上,褚伯秀接受蘇軾的觀點,《南華真經義海纂微》説:
南華以間世卓犖之才而居溷濁之世,時人無足與語,無以發胸中之竒,遂上論皇王,中談孔、老,下至楊、墨、桀、跖,悉評議而無遺,其於察言行之實,判心迹之微,不啻明鑒之燭秋毫也。或謂所談多譏孔子,徒觀其言而不究其意耳!是章結以舉魯國儒服而儒者一人,余謂尊孔子者莫南華若也。請觀東坡《莊子祠堂記》,庶表余言之不妄云。(卷64,第10頁)
莊子一向被列爲道家,並非儒門弟子,《莊子》中多有批評孔子之寓言,莊子“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自漢代司馬遷提出之後成爲主流的觀點,可見褚伯秀所謂“尊孔子者莫南華若也”,則在蘇軾“莊子陽擠陰助孔子”的基礎之上更進一步,主張莊子尊孔子已非孟子與荀子可比。《南華真經義海纂微》説:
唯南華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之,則所謂真者可黙契矣。世人多病是經訾孔子,余謂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所以尊之妙,“正言若反”盖謂是也。(卷98,第9—10頁)
嗚呼!諸子之書曷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卷106,第17—18頁)
昔孟子闢楊墨而聖道明,世世稱之,以爲功不在禹下。余於此亦云: 南華之功不在孟子下。後世必有以爲然者。(卷39,第16頁)
《莊子》中有些寓言涉及批判孔子,褚伯秀認爲那些都應視爲“正言若反”。表面上,莊子批判孔子,“指其迹而非之”就是“反立説”;實際上,莊子尊敬孔子,“得夫子之心”故能“於理無悖”。世人多只看到文字表面,就以爲莊子詆訾孔子,因爲没有掌握“正言若反”的表達方式,未能看出莊子尊敬孔子的用心。這樣的論述與蘇軾“莊子陽擠陰助孔子”如出一轍。
褚伯秀説:“余謂尊孔子者莫南華若也,請觀東坡《莊子祠堂記》,庶表余言之不妄云。”可以看出兩者在觀點上的關聯。蘇軾認爲司馬遷《史記》説莊子“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是知莊子之粗者,提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的新觀點。蘇軾暗用《論語·先進》的意思,孔子説:“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説。”顔回對於孔子之言無所不悦,被孔子視爲非助孔子者;那麽,莊子批判孔子,就可以説是助孔子。褚伯秀繼承蘇軾之説,並推至極致,因有“尊孔子者莫南華若也”之説,而且認爲“南華之功不在孟子下”(14)簡光明《褚伯秀“尊孔子者莫南華若”析論》,《首届海峽兩岸莊子文化論壇特刊》,廈門大學2016年9月13日,第22—27頁。。
蘇軾提出“莊子陽擠陰助孔子”的觀點,褚伯秀頗爲認同,並進一步闡發爲“尊孔子者莫南華若也”。蘇軾提出《讓王》等四篇爲僞作的觀點,褚伯秀則承認四篇文字不淳,卻不認爲應該删除,《南華真經義海纂微》説:
予嘗閲東坡蘇文公《莊子祠堂記》,謂《寓言》篇末當連《列禦寇》篇首,而不取《讓王》、《盜跖》、《説劍》、《漁父》四篇。且二篇合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遭黜,無乃太甚。意其所病者,《讓王》條列繁而義重復,《盜跖》訾孔子若太過,《説劒》類從横之談,《漁父》幾詆聖之語,此所以不爲坡翁所取也。然《祠堂記》中嘗謂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則亦燭其立言救弊之本心矣,又何以麤迹爲嫌?竊考《讓王》等四篇,較之内外部若有間,然其指歸不失大本。蓋立言者不無精粗之分、抑揚之異,或門人補續,不得其淳,所以置諸雜部之末,自可意會,無煩多議,以啓後疑。(卷92,第16—17頁)
蘇軾《莊子祠堂記》説:“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讓王》《説劍》皆淺陋而不入於道”,乃“昧者勦之以入其言”,將此四篇視爲僞作。莊子詆訾孔子的篇章,被司馬遷取爲論證莊子思想的依據,若能加以删除,則更能使莊子陰助孔子之説得到充分的支持。褚伯秀顯然不認同這樣的觀點,《莊子》一書分爲内外雜篇,文字難免有“精粗之分”與“抑揚之異”,而其立言救弊之本心則無二致,故不必以粗迹爲嫌。“不得其淳”,有可能是門人補續,既然其指歸不失大本,置諸雜部之末即可,不必删除(15)方勇認爲,褚伯秀能一反蘇軾主張《莊子》辨僞而删去《讓王》的觀點,表現挑戰權威的勇氣,只是没有完全擺脱蘇軾“助孔”説的影響。見氏著《莊子學史》第六章“褚伯秀的《南華真經義海纂微》”,《莊子學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頁。。
(三) 評論范應元“莊子講語”
范應元的生平事迹,史籍無可考。褚伯秀在《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對范應元有極爲簡要的介紹:“淳祐丙午歲,幸遇西蜀無隱范先生遊京,獲侍講席,幾二載。……師諱應元,字善甫,蜀之順慶人,學通内外,識究天人,静重端方,動必中禮,《經》所謂‘不言而引人以和’者、‘與人並立而使人化’(16)“不言而引人以和”與“與人並立而使人化”二句出自《莊子·則陽》首段,爲對於“聖人”的稱讚。者是也。江湖宿德,稔知其人,不復贅述。”(卷106,第20頁)當時江湖宿德稔知范應元,褚伯秀不復贅述,後代學者則因資料不足,而只能看見其基本資料,無法稔知其人。
明代焦竑的《莊子翼》堪稱是集宋、明《莊子》注之大成,書前之“采摭書目”一向備受研究莊學史者的重視,書目中即有范應元的名字:“范無隱《講語》(應元,字善甫,蜀順慶人)。”(17)焦竑《莊子翼》,(臺灣)廣文書局1978年版,第4頁。既稱“采摭書目”,則范無隱不但曾注《莊子》,而且書成以《莊子講語》爲名。《四庫全書總目》認爲《莊子翼》所徵引的書目過於浮誇:“蓋明人著書好誇博奥,一核其實,多屬子虚。萬曆以後風氣頹然,固不足深詰也。”(18)《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六子部道家類,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247頁。又説:“范元應乃蜀中道士,本未注《莊子》,以其爲伯秀之師,故多述其緒論焉。蓋宋以前解《莊子》者,梗概略具於是。”(19)同上,“范元應”應作“范應元”。《南華真經義海纂微》説:
古語云: 務學不如務求師。至哉師恩,昊天罔極。兹因纂集諸解,凡七載而畢業,恭炷瓣香,四望九拜,儼乎無隱講師之在前,洋洋乎南華老仙之鑒臨於上也。所恨當時同學流亡南北,舊聆師誨,或有遺缺,無從質正,徒深慨歎耳。(卷106,第20頁)
如果范無隱曾注《莊子》,則“舊聆師誨,或有缺遺”就可以與《莊子講語》互相印證,而不致於“無從質正”。正因爲范應元未嘗註《莊子》,褚伯秀雖獲侍講席近二年,聽范應元講完《莊子》,筆記不完整,仍不免有所缺遺,希望求正於當時的同學,同學們卻流亡南北,無從質正起,這是褚伯秀所恨者,也是他深深慨歎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見,范應元曾講授《莊子》而卻未曾注《莊子》;既不曾注《莊子》,當然也就没有《莊子講語》一書的存在。《四庫全書總目》的説法比較可靠。
范應元雖未注解《莊子》,其所講解《莊子》的觀點,卻因收入弟子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中而得以流傳下來。
《田子方》“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句,褚伯秀注云:
無隱范先生講宗吕註,兼證郭氏小失,云:“方矢猶方舟之義,並也,謂並執之矢已寓於弦,非寓杯水於肘上也。”其論爲當。(卷65,第8頁)
范無隱把“方矢”解釋爲“並執之矢已寓於弦”,並且説明郭象所謂“寓杯水於肘上”的解釋有欠妥當。就文義而言,范無隱的説法通順可取。
《逍遥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一段,褚伯秀注云:
詳前諸解,吕、林二公得其端緒,後有無隱講師盡略衍義,直指玄微,發先聖不言之秘,開學人固有之天,恨不能手挈群生俱登姑射,同爲逍遥之遊,其用心可謂普矣。伯秀幸聆慈誨,不敢己私,敬附諸解之末,以弘法施,並推廣餘意。(卷1,第22頁)
褚伯秀先論神人的内在修爲: 體抱純素,守柔自全,因此塵莫能污而害莫能及,這是養神之極,可以自全。次論神人與自然的關係: 絶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故能凌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而與造物者遊,天人爲一。末論神人推己以及物的功效: 足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這是合神不測,契道無方。從而説明范應元對於《莊子》的詮釋確有獨到之處。
《逍遥遊》“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寓言,褚伯秀注云:
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四子喻四大,藐射言其幽眇,謂堯雖治天下、平海内,迹若由爲,心不離道,能反觀四大於幽眇之中,故累盡而逍遥也。”褚氏管見云:“已上諸解四子之論不齊,或大意混成而數不合,或稽數合符而考義差遠,求之近解中,虚齋實爲理勝,范講義數兼該,皆可服膺者也。”(卷1,第25頁)
褚伯秀徵引陳碧虚、吴儔、趙以夫、林希逸、范應元等宋代注家的見解,有些注文“大意混成而數不合”,有些注文“稽數合符而考義差遠”,相較之下,趙以夫的注解“實爲理勝”,而范應元的説法“義數兼該”,都可以服膺。雖然都可以服膺,范應元的講法更勝一籌。
《天下》所載惠施的學説歷來號稱難解,褚伯秀初讀《莊子》終卷,於此覺得莫窺端涯而難以措思容喙,此一難題横於胸臆多年,直至遇見范應元才得到解答。褚伯秀云:
竊謂同學曰:“是經疑難頗多,此爲最後一關,未審師意。若爲發明,度有出尋常見聞之表者。”暨舉經文,衆皆凝神以聽。師乃見問諸友以此論爲何如,衆謝不敏,願開迷雲。師曰:“本經有云: 恢奇譎怪,道通爲一。存而勿論可也。”衆皆愕然,再請明訓。師默然良久,曰:“若猶未悟耶?此非南華語,是其所闢以爲舛駁不中之言,焉用解爲!自‘至大無外’至‘天地一體’,皆惠子之言;‘雞三足’至‘萬世而不竭’乃從學辯者相應之辭,時習佞給,務以譎怪相誇,肆言無軌,一至於此。或者不察,認爲莊子語,愈增疑議,皆不究本源故也。郭氏知此而不明言,使觀者自得。世有好奇之士爲彼怪所惑,遂苦心焦思生異見以求合,其説雖勤,何補於是?”衆心豁然如發重覆而睹天日也。……竊唯聖賢垂訓啓迪後人,義海宏深,酌量隨人,箋註之學見有差等,須遇師匠心傳,庶免多歧之惑,否則死在惠施句裡,無由達南華向上一關,雖多方五車,不過一辯士耳。(卷106,第20頁)
范應元認爲: 由於惠施的學説舛駁不中,本爲莊子所闢;既爲莊子所闢,則就算未瞭解惠施的思想,當不至於妨礙對莊子思想的掌握。反過來説,瞭解莊子當然必須究其本源,若不究本源卻將惠施的學説當成莊子思想,勤於研究辯者之言,始則疑議愈增,繼而爲彼怪所惑,終於死在惠施句裡,豈止是無益,根本就有害。惠施的學説並非莊子的思想,而且是莊子所要批判的對象;既爲莊子所闢,實可不必注解。弟子追隨老師,有一定的默契,開示之前已經預期“度有出尋常見聞之表者”,范應元的説法確實能一新耳目,是以弟子“衆心豁然如發重覆而睹天日”,可見褚伯秀對於范應元講解《莊子》的讚譽(20)詳參簡光明《范應元及其莊子學》,《屏東教育大學學報》24期2006年3月,第351—372頁。《達生》篇“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句,褚伯秀註云:“諸解略而不論。無隱范先生云:‘拔,讀同拂,拂篲皆服役者所執。’解義通而音訓未明,詳玩字形,參之以理而得以説,拔當是帗,傳寫小差耳。”(卷58,第21頁)可見褚伯秀雖然讚譽范應元的講解,並非全盤接受,而能指出其義理可通而音訓未明之處。。
湯漢《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原序》説:“近時釋《莊》者益衆,其説亦有超於昔人。然未免翼以吾聖人言,挾以禪門關鍵,似則似矣,是則未是。余謂不若直以《莊子》解《莊子》,上絶攀援,下無拖帶,庶幾調適上遂之宗,可以見其端涯也。武林褚君伯秀,道家者流,非儒非墨,故其讀此書也,用志不分,無多歧亡羊之失。”《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中,雖不乏“以儒解莊”、“以佛解莊”以及“以道(教)解莊”,主要還是着眼於思想的相應。褚伯秀對於郭象、蘇軾與范應元詮釋《莊子》的觀點多所繼承,即使是恩師的觀點,也並非全盤接受,而其依據則在於是否能適切地説明《莊子》的思想以及正確地標示《莊子》的音義,朝“以《莊子》解《莊子》”的方向邁進。
二、 新解: 褚伯秀對《莊子》注解的補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徵引各家之説,所謂“纂微”當然是采納各注家論述的精微,繼承合理的詮釋,各家注解已經足以説明《莊子》思想,就不多加説明,如“經文大意明白,不復集解”(卷1,第9頁),“餘文平易可通,不復贅釋”(卷1,第23頁),“集解詳明,兹不復贅”(卷2,第16頁),“諸解大意詳悉,兹不復贅”(卷7,第13頁),“諸解已詳,不復贅釋”(卷10,第5頁),“諸解備悉,兹不復贅”(卷17,第8頁),“諸解已詳,不復贅釋”(卷29,第5頁),“經旨坦明,不復贅釋”(卷83,第14頁)。褚伯秀在繼承合理詮釋的同時,也評論各家的優劣,如注《齊物論》“既使我與若辯矣”段:“諸解中疑獨立論最高,自成一家之言,與經文相表裹,非訓詁之學所能及。鬳齋論化聲獨異於衆而無竟,立説尤長。”(卷4,第23頁)指出在諸家詮釋中,林疑獨與林希逸的詮釋較爲適切。本論文所謂“新解”,是指褚伯秀在纂輯諸家解説後的補充,尤其諸家解説未能盡闡《莊子》全幅意藴時,所提出的新解。
《齊物論》“夫隨其成心而師之”句,向來是注家争議不休的論題,尤其“成心”究竟是善或者不是善,注家各持己見。褚伯秀注云:
按諸解多以成心爲善,或以成心爲否,考之下文“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則成心者是非分别之所自萌,不可以善言之也。愚嘗侍西蜀無隱范先生講席,竊聆師誨云:“未成乎心則真性混融,太虚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再衍餘意,輒陳管見云:“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爲難,能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心者性之用,萬法之本原,一身之主宰,不可蔑無,若曰成心,則流乎意矣。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然方寸之所欲爲,未有不因物而生者。……審詳經意,知代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於道,以爲成心者也。”(卷2,第27頁)
范應元的解釋立基於“齊物”的觀點,用全篇的中心思想來解釋字句,再以段落的義理呼應主旨,部分與整體之間的思想能够通貫而一致,確爲有見。未成乎心則真性混融,真性混融則無分别(即無是非、無善惡、無成毁),無分别則萬物齊;反過來説,成乎心則真性鑿裂,真性鑿裂則有分别(有是非、有善惡、有成毁),有分别則萬物不齊。《齊物論》“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物”欲通爲一則須無成毁,“心”亦然。未成乎心則與道爲一,成乎心則道術將爲天下裂。由此觀之,所謂“其論精當,足以盡祛前惑”,實非過論。褚伯秀承其説以批判“諸解多以成心爲善”之非,亦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21)謝明陽從歷代《莊子》注解歸納“成心”的三種詮釋取向: 晉代郭象認爲“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唐代成玄英認爲“夫域情滯著,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心”;宋代吕惠卿則認爲“成心,吾所受於天而無虧者”。其中,范應元的詮釋取向屬第二種。詳《〈齊物論〉“成心”舊注詮評》,《東華漢學》第3期2005年5月,第23—49頁。。
褚伯秀説明范應元的觀點之後,“再衍餘意,輒陳管見”。就心性的關係而言,“心者性之用,萬法之本原,一身之主宰”,對物則心生而念起,師乎成心則流於意,忘物則性現而念止,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22)褚伯秀透過“心”、“性”、“神”的聯結,把“本體論”轉向“心性論”,使《莊子》呈顯出“心性學”的風貌,此爲《南華真經義海纂微》最大的特色。見周豐富《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1996年。。褚伯秀從心性關係切入,以“復性”工夫讓人回到未成乎心之前的善性。
《人間世》“心齋”寓言,褚伯秀注:
按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及氣也者,重舉以釋上文,解者或分析立説,義不貫通。今摭其大意以求印正,云: 聽之以耳,止於聞道而未能盡行;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未能盡忘;至於聽之以氣,則無所不聞、無所不契、彷徨周浹、混合太虚。太虚,何處無之?故待物盡善,而物亦不能逃也。耳之所冥者心,心之所符者氣,氣則静極無爲,虚以待物,孟子所謂浩然充塞者也。觀夫注焉不滿、酌焉不竭、與人而愈有、常應而常静者,則亦何待不待之有哉?通天下一氣,人物太虚之所同攝也。唯虚與氣,非即非離,互顯體用,是以無往而不通。道則非虚非氣,能虚能氣,所以化天下之剛,御天下之實,待物於無待,善應而不窮者也。心齋之妙,亦虚而已。(卷8,第10—11頁)
諸家注中,郭象總括地説“遺耳目、忘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虚以待物者也”,没有詳細論述工夫的層次。吕惠卿説:“無聽以耳而以心,則聽無聞矣。無聽以心而以氣,則心無知矣。聽無聞而止於耳,心無知而止於符,虚以待物,唯氣而已。”從擺脱感官知覺的“聽無聞”到超越心智分辨的“心無知”,然後能達到虚而待物的境界。林疑獨注:“聽之以耳,正聽也;聽之以心,反聽也;聽之以氣,無聽也。正聽以耳,將以窮理;反聽以神,將以盡性;無聽以虚,將以至命也。……《列子》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與此義同。”林疑獨將心齋的層次分爲“正聽(耳)-反聽(心)-無聽(氣)”,相當於《列子》“體-心-氣(神)”(23)《老子》二十五章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既爲本體,則不應該“道”法“自然”,“道”即“自然”。《列子》所謂“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亦應作如是觀,故其工夫層次不應該是“體-心-氣-神”,而應該分爲“體-心-氣(神)”,此一工夫結構才能與《莊子》相應。如果套用褚伯秀的觀點,“神”與“氣”互爲體用,“道”則能“神”能“氣”,可以講得通。如此一來,仍分爲三個層次“形(體、耳)-心(知、聰明)-神(氣、虚)”。的工夫層次,也符應於《易經·説卦》“窮理-盡性-至命”的工夫層次。陳祥道注:“《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陳祥道引《文子》“耳-心-神”的層次説明《人間世》“心齋”,《莊子·大宗師》論“坐忘”,所謂“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形”、“體”、“耳”都是指身體的感官。林疑獨引用《列子》與陳祥道引用《文子》都可呼應《莊子》“心齋”的工夫層次。
褚伯秀對於諸家詮釋並不滿意,而謂“解者或分析立説,義不貫通”,因而“摭其大意”,做進一步的補充。他説:“耳之所冥者心,心之所符者氣。”心齋的層次分爲“耳-心-氣”,對應於體道的層次則爲“止於聞道而未能盡行—止於契道而未能盡忘—無所不聞、無所不契”。《人間世》説:“氣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齋也。”一般注家多未能解釋“氣”、“虚”與“道”的關係,褚伯秀所謂“唯虚與氣,非即非離,互顯體用”,可見“氣”與“虚”是互爲體用的關係;“道則非虚非氣,能虚能氣”,“道”透過“虚”與“氣”來冥契與實踐。
《在宥》“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段,褚伯秀注:
“挈汝適復之撓撓”一句,頗難釋,諸解亦未甚顯明。審詳經旨,與《道德經》“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意同。蓋大人之教,主在動而化物,故遊乎無端無旁而與日俱新,無始終也。頌論,猶議論。議論大人之形容,合乎大同,與道無異,即《道德經》“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之義。諸解多着意於頌論二字,故於下文説之不通。大人則無己,己既無矣,何物足有哉?君子則務學,期造乎道,是以未能忘物而所睹無非有,猶庖丁始解牛,所見無非牛。昔之君子尚然,今之君子又可知矣,故思“睹無”之人而尊之,“睹無”則絶學而至於道,猶庖丁三年之後目無全牛矣!天地生於無者也,能睹天地之所生,則與之爲友非過論也。
“挈汝適復之撓撓”句,郭象説:“挈提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爲之至矣。”吕惠卿注:“故能挈天下而往,以復之擾擾而不必静,是所謂‘萬物並作,吾以觀復’,而‘藏天下於天下’也。”林疑獨注:“挈汝萬物同適乎至静,然後出而應物於擾擾之間,故能與造物者遊乎無端,出入無旁也。”陳詳道注:“‘復之撓撓’與‘鞅掌以觀無妄’意同。”林希逸注:“‘擾擾’,群動無已貌。挈舉世之人,往歸於擾擾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世間,是出世世間非二法。”褚伯秀認爲該句相當難以解釋,諸家注解未能將該句的意涵彰顯説明,即使引用《老子》十六章“萬物並作,吾以觀復”、《莊子·大宗師》“藏天下於天下”與《莊子·在宥》“鞅掌以觀無妄”,一樣未能契合該句的義理。該句意涵與《老子》十五章“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同。此外,“諸解多著意於頌論二字,故於下文説之不通”。褚伯秀以《老子》二十一章“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來説明“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
褚伯秀將庖丁的工夫分爲剛開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的“睹有”階段與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的“睹無”,“睹無則絶學而至於道”是把“未嘗見全牛”的工夫層次歸屬“神遇”的階段。這樣的理解有欠妥當。如果把庖丁解牛的工夫分爲“所見無非牛”與“未嘗見全牛”,“未嘗見全牛”應該包括“良庖”與“庖丁”兩個階段,問題是,“庖丁”的運作主體已經用“神遇”來説明,那麽,“未嘗見全牛”應該專屬“良庖的階段”。而且《養生主》説“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則顯然“三年之後”還没達到“神遇”的境界。“未嘗見全牛”雖然比“所見無非牛者”更上一層樓,但是仍然還在“技”的階段,雖是進階,仍尚未達到“道”的境界。
《列禦寇》“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寓言,褚伯秀注:
“遁天之刑”,訓解不一,詳下文“所安”“所不安”,即其證。或析爲别章,遂至經意不貫。言緩遁逃自然之理,而棄背父子兄弟之天,是“不安其所安”;怨憤而自之於刑戮,是“安其所不安”也。南華以“遁天之刑”一語結緩之公案,所以爲後世不安天理而狠愎自戕者之戒云。
《養生主》中,秦失弔老聃,看到“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認爲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並指出“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人之生死本之自然,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逃遁天理,違背實情,如受到刑罰,故謂“遁天之刑”;順應自然,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才能“帝之懸解”。《列禦寇》:“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褚伯秀認爲應該從“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來理解。所謂“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就像《養生主》中“帝之懸解”,順乎天理,順應自然;“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一如《養生主》中“遁天之刑”,遁逃自然之理,遁天倍情,忘其所受。鄭人緩“棄背父子兄弟之天”,是“不安其所安”;怨憤而自之於刑戮,是“安其所不安”,不安天理而狠愎自戕,正是“遁天之刑”的具體事例,故莊子以之爲後世之戒。有些注家把“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數句從鄭人緩的故事中移出,另成一章,無法用緩的例子來説明“所安”“所不安”,導致經意無法通貫;褚伯秀指出義理通貫之處,用緩的例子來説明“遁天之刑”,莊子勸戒後世之意才有着落。
結 語
褚伯秀注解《莊子》而以“義海纂微”爲書名,“義海”正顯示歷代《莊子》義理注解如海洋一般浩瀚,“纂微”則彰顯褚伯秀從衆多注解之中披沙揀金纂輯微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書,如劉振孫《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原序》所言“會萃之勤、去取之精,而所見之多有超詣也”。學者論“會萃之勤”與“去取之精”者多,“所見之多有超詣”則發揮較少。本論文以郭象、范應元、蘇軾爲例,説明褚伯秀對於歷代《莊子》注解的繼承;以對諸家注解的不滿而提出新解爲例,説明褚伯秀對於歷代《莊子》注解的補充。
在繼承方面,郭象是《莊子》注解的權威,褚伯秀注《説劍》説:“子玄於是經得其心髓,雄文奥論,與之並駕争驅,獨此篇不著一語,使人深造而自得之也。”其他如“簡要切當,莫越於此”,“略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意”,可見其推崇之意。褚伯秀對於郭象注文不符合《莊子》思想者,亦能論其缺失,指出“似與下文不貫”及“非莊子本意”之處。蘇軾《莊子祠堂記》對莊子思想定位的觀點影響深遠,褚伯秀繼承蘇軾“莊子陽擠陰助孔子”之説。褚伯秀説:“余謂尊孔子者莫南華若也。請觀東坡《莊子祠堂記》,庶表余言之不妄云。”可見其推崇與發揚其説;然對蘇軾提出的《讓王》等四篇爲僞作的觀點,褚伯秀不表認同,只承認四篇文字不淳,《莊子》一書分爲内外雜偏,文字難免有“精粗之分”與“抑揚之異”,而其立言救弊之本心則無二致,故不必以粗迹爲嫌。范應元爲褚伯秀之師,褚伯秀承其緒,“舊聆師誨,或有遺缺,無從質正,徒深慨歎耳”,“無隱講師盡略衍義,直指玄微,發先聖不言之秘,開學人固有之天,恨不能手挈群生俱登姑射,同爲逍遥之遊,其用心可謂普矣”。《天下》關於惠施的學説,范應元指出“非南華語,是其所闢以爲舛駁不中之言,焉用解爲”,於是“衆心豁然如發重覆而睹天日也”。褚伯秀對其實多讚揚之語。范應元“解義通而音訓未明”之處,褚伯秀亦能指出並補充。整體而言,褚伯秀對於注家觀點的繼承,能清楚説明其理由,並評論其優缺點,不盲目聽信權威。
在補充方面,褚伯秀有在纂輯諸家解説後的補充;尤其是諸家解説未能盡闡《莊子》全幅意藴時,有提出的新解。《齊物論》“成心”二字,“諸解多以成心爲善,或以成心爲否”,必須加以補充,“再衍餘意,輒陳管見”,褚伯秀從心性關係切入,以“復性”工夫讓人回到未成乎心之前的善性。《人間世》“心齋”工夫,“解者或分析立説,義不貫通。今摭其大意以求印正”,一般注家多未能解釋“氣”、“虚”與“道”的關係,褚伯秀所謂“唯虚與氣,非即非離,互顯體用”,可見“氣”與“虚”是互爲體用的關係;“道則非虚非氣,能虚能氣”,“道”透過“虚”與“氣”來冥契與實踐。《在宥》“‘挈汝適復之撓撓’一句,頗難釋,諸解亦未甚顯明”,“諸解多着意於頌論二字,故於下文説之不通”,褚伯秀因此加以補充,唯其對於庖丁解牛工夫層次有欠妥當。《列禦寇》“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寓言,有些注家把“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數句從鄭人緩的故事中移出,另成一章,無法用緩的例子來説明“所安”“所不安”,導致經意無法通貫,褚伯秀指出義理通貫之處,用緩的例子來説明“遁天之刑”,莊子勸戒後世之意才有着落。整體而言,褚伯秀能够詳細檢視徵引歷代《莊子》注解,指出義理不通貫之處,提出新解加以補充,多能言之成理。
褚伯秀對於歷代《莊子》注解多所繼承,“纂集諸家之説”,是其用功之處;諸家解説未能盡洽文本者,亦能提出新解,“斷以己意”,是其用心之處。本文將褚伯秀的用功之處與用心之處具體而微地展開,説明《南華真經義海纂微》確實爲宋代《莊子》注之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