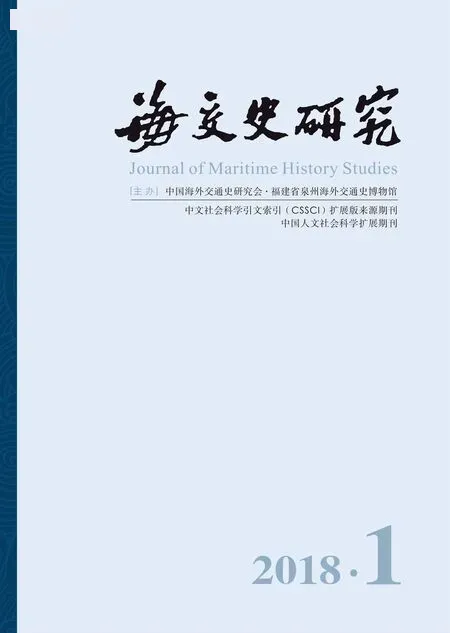博弈与牺牲:近世初期德川幕府海洋政策特点
王煜焜
坂本太郎曾言:“从家康到家光的三代是德川幕府奠定基础的时代,是完善幕府政治的时代。”*〔日〕坂本太郎著:《日本史》,汪向荣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75页。其海洋政策亦然,肇基于此。江户幕府初创时,日本不向海外派遣臣僚,不干预海外日人卷入的纠纷。这并非无可奈何之举,而是幕府宁愿牺牲海外臣民来换取国内之稳定。采取锁国令后,以长崎作为贸易与出入境的管理窗口,逐渐完善成为后世所称的“锁国”体制,将自己封闭在幻想的日本型华夷秩序中*〔日〕荒野泰典:《近世の対外観》,载《岩波講座日本通史·近世3》,东京:岩波书店,1994年,第211-251页。近世,日本创造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对日本而言,通过朝鲜通信使、琉球庆贺使与荷兰商馆长的江户参府来提高其自大感,将自己置于“中华”的位置。西川如见《增補華夷通商考》卷2结束后附有一幅地球万国地图,其将日本置于世界的中心。参见《增補華夷通商考》,载《西川如見遺書第四編》,东京:求林堂藏版,1899年。又如“1672年林春胜父子所编的《华夷变态》,1669年山鹿素行所著的《中朝事实》都已经开始强调,应当把‘本朝’当作‘中国’,这是‘天地自然之势,神神相生,圣皇连绵’”。(引自葛兆光:《宅兹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页。),直至被美国大黑船强行打开国门。
一
草创之期,幕府所忧之事乃是国民于海外之活动。相对,日本国民亦是东南诸国的眼中之钉。帕塔尼国与日本亦为日侨为祸当地之事断交多年,甚至暹罗也介入调停。*《大日本史料》,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第12编第7册,第608-609页。日本商人在安南国还抢夺福建商人的财物,令执政者头疼,很是希望家康可以妥善处理。*《大日本史料》,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年,第12编第4册,第357页。自建府以来,德川家康曾为此事与柬埔寨、越南等国执掌多次通信。《异国近年御书草案》载家康致安南国之信言:“陋邦商客,每岁到其国,不厌海陆远,不畏风浪灾,贪小利轻一身,共非有道辈。于异方者,想是以无族类之亲,不得口舌之便,若吐恶言作恶行,究尽理之正邪,辨别罪之轻重,而可被刑戮。”*《大日本史料》,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年,第12编第3册,第560页。同书又载家康致柬埔寨之信:“自陋国商舟岁岁到贵域商贾者,非高客贤士,所业知重利耳。故尽可作暴恶,其咎无所遁逃,可令囚狱。”*《大日本史料》,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9年,第12编第3册,第484页。以上乃是幕府答复东南诸国要求严惩在当地为恶日人的言辞。家康声称,海外日人若然归国即处极刑,若不归国便任由对方国家处置。然而,即便本国国民有错在先,身为一国执政者亦不应将其舍弃海外。此外,即便日人担任国外官职,幕府也希望他们能安守本分,不要有所僭越。与其说是抱有不干预之态度,毋宁说德川氏是对局势谨慎地关注和避免祸及国内。
江户始,大御所*日本古代、中古时期,通交认知之国颇少,远仅天竺,临近只有中国与朝鲜。近世初期,由于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国际环境为之一变。与日本有往来之国,在欧洲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在亚洲则有中国、朝鲜、琉球、虾夷、吕宋(菲律宾)、东京、安南、交趾、占城、柬埔寨、暹罗、太泥等。江户幕府对固定交往之国的外交权掌握在将军手中,其余则由大御所管理。管理海域相关之事务,其中异国渡海朱印状值得吟味。德川幕府颁发朱印状*其时发放的朱印状数量极为可观。据《长崎实录大成》载:“自文禄初年始,长崎、京都、堺之人领受朱印,为贸易买卖渡海前往广南、东京、占城、柬埔寨、六昆、太泥、暹罗、台湾、吕宋、阿妈港等地。”(见《長崎志正編》,长崎:长崎文库刊行会,1928年,第425页。) 其中,“安南国十四封、东京十封、占城五封、吕宋三十封、信州二封、太泥国五封、暹罗国三十五封、顺化一封、柬埔寨二十三封、西洋十八封、迦知安一封、蜜西耶二封、芠莱二封、田弹国二封、摩利迦一封、交趾国二十六封、高砂国一封、摩陆一封。” (〔日〕川岛元次郎:《德川初期の海外貿易家》,大阪:朝日新闻合资会社,1916年,第25页。)船主七十五人,共一百七十九封,数量极为可观。给合法商人,除了能证明其身份外,还会特地标注商队的航行目的地,可见其制度设置之初衷是为清除在东亚海域上进行非法贸易的倭寇余党*家康颇感大阪、京都商人的经营模式与传统海盗式贸易风格迥异,对其财政似有益处。。然而,若日本商人与海外其它势力发生纠纷时,幕府可能会被牵扯其中。三省其政后,幕府决意改革海域政策,首先隐蔽朱印状上的重要信息。
如斯变化显然是为了规避风险。故而,朱印状领受人中没有官僚、德川一族、谱代大名、朝廷贵族与寺社等统治阶层。*朱印船商人除却京都的茶屋、角仓,大阪的末吉,长崎的末次等外,尚有中国人李旦等十一人,皆为商人阶层。参见〔日〕藤井让治:《日本の歴史·江戸開幕》,东京:集英社,1992年,第133页。遇到纷争时,幕府则直接制裁拥有朱印状的商人集团,他们成为替罪羔羊。例如,在暹罗发生的高木船烧毁事件*1627年,高木作右卫门的朱印船受到西班牙舰队攻击而焚毁,船员被押往马尼拉。,幕府不但未替澳门的日本商人行会出头,反而处罚他们。因为得不到政府的保护,故此出现像类似高木家放弃贸易的负面结果。
一如以明朝为中心的东亚册封体制般,德川家康亦有尝试学习中国天子那般“傲气”,却不得其要领。幕府虽不愿探究海外纠纷爆发之根源,但实藏报复之心,如古拉萨事件*古拉萨事件的概要详见《大日本史料》,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第12编第6册,第789-826页。。1608年时,有马晴信的家臣去占城国购置沉香,一行人在澳门与葡萄牙人起了争执,不仅人员有所死伤,随身财物亦被夺走。史料记载有限,但从现有的文献可知双方实际皆有责任。然而家康却不问缘由,纵容有马晴信恶意报复澳门船只。次年,葡萄牙的古拉萨号从赴日之际就踏入日人所设陷阱,落得船沉之悲惨下场。同年,德川家康接受澳门申请禁止贸易的请求,且下令禁止日人前往澳门交易。*影印本《異国日記》,东京:东京美术,1989年,第9页。1611年,葡萄牙要求赔款,并请求罢免长崎奉行。德川家康拒绝其请,亦恼葡干涉日本国政。*参见《大日本史料》第12编第8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第525-539页。葡萄牙则认为幕府并不追查海外事件的真相,且将政治的博弈舞台限定于日本是一种欠缺国际公平的回应方式。最终,日本坚持的交涉政策始终为不贸易、不回应。然而,葡萄牙究拧不过贸易之诱惑,因长久与日本的贸易中断致使其收入锐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又厚着脸皮要求恢复贸易往来。*《大日本史料》,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第12编第10册,第120-121、129页。显然,在政治上老谋深算的家康是以对方依赖日本贸易为筹码回击的。
幕府于其后颁布的大船持有禁令进而迫使西国大名考虑终结朱印船贸易。*安达裕之认为没收大船的对象为诸大名领内所有的船只。见〔日〕安达裕之《異様の船》,东京:平凡社,1995年,第15-30页。如前所述,由于澳门事件的影响,幕府终止发放前往澳门的朱印状。*〔日〕岩生成一:《新版朱印船貿易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85年,第165-166页。此后,有马晴信毅然决然退出海外贸易的经营,而与其站在同一战线的高木作右门与末次平藏亦紧随其后。显然,澳门事件的恶劣影响间接促使日本商人逐渐退出海外贸易。此外,葡萄牙虽未得到经济赔偿,但日本商人在海上的人数急转直下*《大日本史料》,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第12编第10册,第120-121、129页。则成功使葡萄牙独占海上贸易的利益。
江户时期,日本的“海禁”独具特色。横向比较,东亚三国实行的海洋政策虽然都是“海禁”,但仍有些差异。在中国与朝鲜民间的海外航行虽被严禁,但国家之间的通交不受影响,互相间仍有频繁交往,如明朝会定期接受海外“有诚意”国家的朝贡,并不时向海外派遣使节册封,给予他国在统治上的合法性。*一般认为,海禁政策兼备防止倭寇与抑制私下贸易等两大作用。不过,洪武帝颁布海禁令的直接目的显然是防止倭寇,而不是取缔私下贸易。海外贸易是在市舶司的管辖之下,民间贸易是许可的。(见〔日〕檀上宽:《明代海禁概念の成立とその背景》,《东洋史研究》,第63巻第3号,2004年,第9页。)海禁为朝贡体系发挥最大效用是在永乐时期。对外采取积极态度的成祖于1403年恢复了三市舶司,为诸国朝贡做准备。1405年派遣郑和出海,敦促海外诸国入朝朝贡。(见〔日〕佐久间重男:《日明関係史の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92年,第121-122页。)然而,日本却从政策执行初始便停止向海外派遣使节,有意回避国际交往,有联系的不过寥寥数国而已。不过,德川家康亦曾动过通商的念头,他赐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朱印状“初心”实乃保护来航人员。*〔日〕村上直次郎译注:《增訂異国日記抄》,东京:骏南社,1929年,第24-26页。之后,幕府赐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朱印状条款则增至七条,但其内涵却相差无几。*〔日〕 村上直次郎译注:《增訂異国日記抄》,东京:骏南社,1929年,第184-188页。其源头可追溯到安土桃山时代的布教许可。*〔日〕村井早苗:《天皇とキリシタン禁制》,东京:雄山阁,2000年,第45-46页。德川家康赐予英国的朱印状内容与其大致相似。在丰臣秀吉之前亦有类似许可的先例*约定许可保护传教士在京都居住的有织田信长的朱印状和足利义昭的制札。其后,关白丰臣秀吉发出两封文书,一封给印度、葡萄牙,另外一封给予在日的传教士。其要旨是免除寺院的征课税和赐予传教士居住权。参阅〔日〕村井早苗:《天皇とキリシタン禁制》,东京:雄山阁,2000年,第14-16、27页。,但皆为临时措施。家康颁发保护通商朱印状的真正目标是稳定国内政权后再逐步展开贸易与外交。然而,由于德川家康逝世,日本海洋贸易体制的构建幻想随即破灭,其子秀忠将政治着眼点落于国内,海外的交往则有所保留。不久后,一纸“宽永锁国”令将海外来船限制于长崎一地。显而易见,以海外情势的紧迫为契机,幕府利用锁国政策终结了民间贸易。
二
德川氏得天下颇有偶然因素,一大缘由即是丰臣秀吉将战火引向海外,直接促成其子接受一副烂摊子,政权千疮百孔、内外交困;殷鉴不远,德川氏在处理海外事务之时极为谨慎,故此家康身后的锁国倾向愈发明显。德川家忠于1617年禁止朝鲜使节购买火器*《日本関係海外史料·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中,第186-187页。,此举正是四年后全面禁止武器、技术人员外流的试金之举。*《日本関係海外史料·イギリス商館長日記》,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下,第155页。西方传教士法兰塔因认为这显然是德川幕府放弃海洋的主要征兆。*《大日本史料》,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第12编第38册,第192-193页。因为,武器输出的背景是亚洲的动荡局势,幕府终止武器输出不仅改变了日本自中世以来的贸易惯例,更是表现出德川氏急欲回避海外事务。其后,德川氏锁国的另一缘由即是担心海外贸易家抵受不住利益的诱惑而秘密向海外输出武器。故此,如《宽明日记》*《內閣文庫所藏史籍叢刊·元寬日記 寬明日記一》,东京:汲古书院,1986年,第408页。所见,奉书制度是幕府为了避免日本国民卷入海外而设立的,其核心要点便是“渡航者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还包括“禁止武器输出”和“不得随意航行至指定的地点外”*〔日〕永积洋子:《近世初期の外交》,东京:创文社,1990年,第56-57页。。
荷兰商馆长坎普斯曾记述道:“皇帝*荷兰人认为幕府的将军就是皇帝。的名誉欲仅限于帝国内,不愿对任何人开战。海外臣民给他增添无数烦恼。他绝不允许海外的冲突演变为日本与外国君主间的战争。”*〔日〕幸田成友译:《日本大王国志》,东京:平凡社,1967年,第240页。荷兰商馆长之言一笔点出德川秀忠海洋政策的精髓。德川幕府锁国的本意便是希冀将国际纠纷置于日本领土内处理。故此,即便海外的日本町被当地商人所焚毁,德川氏依旧不为所动,奉行不保护海外民众之政策,更颁布残酷的锁国令使其成为无主弃民。
“台湾事件”是幕府海洋政策的经典体现。*〔日〕永积洋子:《平户オランダ商館日記》,东京:讲谈社,2000年,第37-41页。1625年之际,一艘日本贸易船随同长崎代官末次平藏一起驶入台湾。荷兰商馆为了筹措防御费,在金钱的驱使下,随意将通行的出口税提高百分之十。末次平藏当即认为其税不合规矩,故而拒绝支付,但荷兰方强行没收日船的生丝1 500斤,无比蛮横。归国后,末次平藏将此事上报阁老,然幕府却冷眼旁观,并无作为。荷兰事后有些懊悔,担心事件会发酵,进而引起轩然大波,故而遣使节诺伊兹赴日交涉。然而,荷兰并未提及己方贪财之过,反归咎于日方,认为事件起因是日本船员拐带台湾原居民。吊诡的是幕府同样不做回应,诺伊兹则悻悻离去。次年,末次平藏意欲言和,但诺伊兹并不领情,下令扣押日人且没收财物。末次平藏的船头滨田弥兵卫趁机反击,且获小胜,俘虏人质后同荷兰谈判。经过协商,双方决定各退一步,当日船回国后就放还荷兰人质,而荷兰则返还没收的财物与生丝。但是,日人并未守约,荷兰先后派遣两次使节赴日谈判,皆无果。
与古拉萨事件相同,德川幕府此后不再发放前往台湾贸易的朱印状,日本商人再次陷入困境。大多商人暗中投靠荷兰换取利益,结果却使幕府更为防备他们,演变为恶性循环之结果。对于触及幕府底线的末次平藏被褫夺贸易权尚在情理中,但并非所有商人都站在末次的阵营中,例如亦是经营台湾贸易的平野藤次郎。诺伊兹到达江户时,阁老伊丹康胜曾在宿老集会上表达对平野的谢意,因为藤次郎在台湾经营海上生意时曾拜托荷兰人厚待伊丹的下属。*〔日〕永积洋子译:《平户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第一辑,第133页。并且,身为大阪奉行下属的平野藤次郎却特意前往京都拜访诺伊兹,希望他能在必要时给与日本商人一臂之力。然而,在京都的中层官员却纷纷求见诺伊兹,表示出对平野藤次郎的不满之情。*〔日〕永积洋子译:《平户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第一辑,第116页。此时,诺伊兹唯一能感受到的只是京都官员深恐惹怒荷兰而失去在台湾的贸易利益,甚至毫无差别的归咎于他人。
德川幕府在台湾事件的处理上始终一意孤行,且将商人孤立到底。德川氏之所以毫无回应,显然是不欲为一介商人之纠葛而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双方当时的焦点聚焦在台湾的贸易所有权上。末次平藏原本认为献上台湾的利益后必能换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他尝试将自己同日本最高执政者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新訂增補國史大系·德川實紀》,东京:吉川弘文馆,1990,第二篇,第417页。其愿虽宏,究未成功,结果无疑是与虎谋皮。德川氏在选择国家稳定和海上经济之间有明显的偏向。荷兰的观点则直截了当,日商若要拐带台湾居民等同侵害其权益。虽然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同样不是台湾的主人,与日人多年后的行径一样,皆是非法之举。然而,幕府的世界认知却于此有别,德川氏始终认为非法驻扎台湾的荷兰人是南蛮商人,而爆发的事件仅为同行商人间的纠纷。幕府认定放弃海外市场当可一石二鸟,同时驯服荷兰与末次家族。结果,末次平藏在江户突然暴毙,原因不明*〔日〕永积洋子译:《平户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第一辑,第363-364页。,其子选择屈从一途,不再恋栈海外利益。
末次平藏的薨逝意味着长崎旧势力的消退。平户藩主与长崎奉行水野实乃至交*〔日〕永积洋子:《キリシタン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第二十五辑,第203页。,平野藤次与幕府也极有渊源。*〔日〕永积洋子译:《平户オランダ商館日記》,东京:讲谈社,2000年,第44页。他们读懂时代巨轮的走向,机敏地知晓应当身处何方,沿着幕府的意图前行。但是,末次、竹中与他们不同,在政策上选择错误的事项。*〔日〕永积洋子译:《平户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第一辑,第132-133页。由于海外形势不稳,德川氏加强了长崎一地的管理。进而,德川家光的危机管理模式远超其父秀忠。末次与竹中并不适应如斯局势的发展,最后惨被德川氏肃清。
台湾事件之经纬尽显幕府对海洋事务的冷淡态度。德川氏从未付出丝毫努力去了解台湾事件的发展。与此相对,幕府却容忍末次平藏毫无依据地将荷兰人投入牢狱之中。并且,老中酒井忠世还派人警告荷兰使节,若荷兰在海上或其它地方做出对日本不当的行径,幕府必将处罚囚禁于日本的荷兰人质。*〔日〕永积洋子译:《平户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第二辑,第282、336页。当时,荷兰在世界各地都陷入战争的漩涡中,若然此刻失去同日本的贸易,其苦心经营数十载的平户商馆与耗费巨资建起的台湾商馆顷刻间将化为乌有。权衡再三,荷兰选择妥协一途。最终,幕府通过控制对外贸易与利用人质,成功使荷兰在海上为其服务。此后,雅加达总督也愿意配合幕府的政策,实行共存、守护权益的现实性战略。
三
在近世的东亚地区,荷兰语中的“通行证”多指朱印状,但也包括幕府各种不同机构颁发的许可证,例如渡海通商许可朱印状、渡海许可奉书、长崎奉行的出港许可书等。然而,对于来自“南蛮”的荷兰人而言,官僚的文书有些过于繁琐,以上诸等官方许可证之间似乎并无差异,他们不会考虑文书源于何处。实际上,大御所、将军、老中、长崎奉行等官职皆非一体,职能各异。朱印状的签署人为大御所,而奉书则出自幕府将军之手,两者分别所掌控的是外交和内政。表面来看,两者似乎皆为海上贸易许可证,但其签署出处的变化则深刻体现斯时日本对外政策之转型。
由于海外出现冒用朱印状之事件,德川氏削足适履,迅速收回发行不久的朱印状。不久后,幕府更是禁止日本船出港,但在充分考量形势后勉强允许持奉书之贸易家出海。《谱牒余录》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宽永六年(1629),自日本到交趾国船也。朱印在竹中采女正殿下任奉行时召回。向老中殿下献上奉书而受命出海。奉书为采女正殿下所留。其后,神原飞騨守殿下任奉行之时,日本人被命禁止航行海外。”*《內閣文庫影印叢刊·譜牒餘錄》,东京:国立公文书館,1975年,下,第912页。竹中在担任奉行时的严厉政策使商人即便获得奉书亦得物无所用,其后的趋势更为紧张。由于德川幕府禁止日本船无证出航,原本往东京贸易的角仓和去柬埔寨的按针等贸易家偷偷在长崎奉行管辖范围外的地方上船,荷兰人就是他们的“帮凶”,而荷兰人亦有许多违规行为,不少荷兰船伪装成中国的唐船出港。*〔日〕永积洋子译:《平户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第一辑,第317页。前往东南亚的日商在归航时多乘暹罗国的使节船。*〔日〕永积洋子译:《平户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第一辑,第316、329页。
荷兰商馆长卡隆曾提到:“从皇帝处得到七封旅券,即航海通行证。可渡海至东京、柬埔寨、暹罗和台湾。旅券上记载的条款中有一条为旅客行至外国须当遵守当地的律法。”*〔日〕幸田成友译:《日本大王国志》,东京:平凡社,1967年,第174页。可见,即便勉强颁发许可证,幕府依旧担忧日商在海外引发纠纷,故此在源头处便灌输遵纪守法之顺从理念。获得许可的商人并不多,仅七大家族获得老中的奉书,分别为角仓、平野、末吉、茶屋、末次、桥本、三浦按针等。*〔日〕永积洋子译:《平户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第三辑,第103页。然而,由于日本在海上的影响力有限,且幕府不愿发展海洋势力,结果只能依赖身为南蛮的荷兰人来保障日商在海上的航行。
在幕府连年的严厉政策下,荷兰人逐渐成为日商海上航行的保障者。荷兰商馆长曾接受平户藩主的请求,并发放通行证。不过,即便日人“沦落”至需要接受南蛮化外之人的保护,德川氏却依然选择视而不见。荷兰商馆员在书信上提及:“皇帝或阁老的朱印状”仍未发行。*〔日〕永积洋子译:《平户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第三辑,第517页。显然,这里指的是幕府所发放的允许商人出海贸易的奉书。商馆长也说:“彼等特为等候此信。因为无法从皇帝处得到朱印状。”*〔日〕永积洋子译:《平户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第二辑,第505页。由于幕府不再发放朱印状,所以“彼等”所指的必为原来经营朱印船的贸易家,即前文所提及的角仓等家族。面对禁令,诸位贸易家仍意图开展海外贸易,因此在和政府的诸多博弈中,思考别样的经营方法。一方面,他们同长崎奉行竹中等保持良好的私交,另一方面则在海上利用荷兰人的势力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于外交与经济的夹缝中汲取那一点点带着危险味道的利益。
如前所言,执政者的变化促使局势更为紧张。德川家光的政治素养远逊祖父,更为惧怕海外远洋所隐含的政治风险。日本贸易家总在政策上同幕府的意图相左,诸如雇佣荷兰水手、申请荷兰商馆的通行证都在暗地里刺激德川氏的神经。问题的实质是政府与民间商业阶层间的博弈。然而,政府内部充斥为了利益而背叛幕府将军的官员,如江户阁老们大多身兼海外贸易家的身份,他们利用政策的便利来谋取私利。故此,他们在台湾事件尚未恶化前就暗中维护荷兰,且偷偷签署朱印状,希冀能维系原有的海上贸易格局不变。荷兰商馆长之言成为有力的证明。*“仅获得皇帝朱印状的贸易家能出海,并会准备需要远航的中国式帆船……不过,现在有效的是阁老的书信。”见〔日〕永积洋子译:《平户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第二辑,第80页。例如,角仓与平野为去东京与交趾,求助荷兰商馆,并获得其舵手的助航与通行证。*〔日〕永积洋子译:《平户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第三辑,第517-518页。老中酒井忠世允许曾被禁止访日的荷兰人克库德鲁多德乘坐末次平藏驶往鸡头国*鸡头国就是东京。〔日〕桜井·菊池編:《近世日越交流史》,东京:柏书房,2002年,第23页。的海船。相应地,荷兰商馆则为前往东京与交趾的角仓和平藏提供便利。东京与交趾是角仓、茶屋氏对外通商之根基所在,如若未能获取阁老之援助,不仅利益将大幅减少,更是随时丧失海外贸易的经营权。因此,家光时期的海外贸易家皆暗里与荷兰商馆及日本权要集团勾结。幕府禁止日人海外航行是无视少数集团之利益,然而被牺牲的少数集团却心有不甘,在数方势力的博弈下继续用独特的方法赚取金钱,东亚地区同日本相关的贸易模式转而以如斯的形式继续推进。
即便如此,荷兰依旧希冀得到日本官方的支持,以免招致毁灭的打击。荷兰商馆长在日记上言及,日荷双方合作之基础是日方“持有皇帝朱印状”,从而荷方亦可向领受朱印状的船只发放通行证,保障其海上航行安全。*〔日〕永积洋子译:《平户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第三辑,第28页。据《热兰遮城日志》所载,1634年有两艘前往交趾的日本船“获得朱印状”*〔日〕永积洋子:《朱印船》,东京:吉川弘文馆,2001年,第89页。。这两艘船应该是茶屋与末次家的船只。同时,荷兰商馆长亦提及商馆无法拒绝“将军的请求”,向预备前往印度支那的五艘日本船发放了通行证。*〔日〕永积洋子:《朱印船》,东京:吉川弘文館,2001年,第95页。这意味着,江户幕府的默认是荷兰商馆与七大贸易家合作的基础。德川幕府的政策显然是企图将荷兰商馆纳入日本的内政管理中,进而压制其异心。幕府暗地雇佣荷兰人为其服务则从不同角度证实了它的海上意图。一方面,海上的航行乃至海外的安全问题可以委托更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在发生海外冲突之际能使日本抽身而退;另一方面,幕府能间接控制荷兰商馆,将其纳入日本国内的行政管理中。然而,随着幕府锁国政策的逐渐推进,压在商人身上的枷锁不断厚重,许多贸易家放弃“从皇帝处得到的朱印状”*〔日〕永积洋子译:《平户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东京:岩波书店,1969年,第三辑,第202页。,不再经营海上生意。
实际上,由于高木船事件的影响,幕府对海外航行的控制愈发严厉,已然颁发的朱印状亦被召回,不再发放。不久后,长崎奉行着手管理船只出入港的事务,旋即禁止日本船出航。为此,许多贸易家不甘就此放弃多年的海上贸易成果,在国外势力与幕府间斡旋。他们伪装成唐船出海,而海上的安全便交由荷兰的舵手与商馆长的通行证来保障。面对新时期的问题,幕府亦在尝试解决。禁航的两年后,德川氏向七大海外贸易家发放奉书,规定只有手持奉书之商才能出港航行。某种程度而言,这是幕府对私家贸易的妥协。此时,原本为大御所管辖的朱印状未能再度刊行于世,而海外的渡航事务则逐渐移交将军与老中所管理。以奉书为海外贸易媒介的出现意味着大御所控制的对外关系纳入幕府将军的内政中。另一方面,由于德川家的影响极为有限,奉书能力所及的仅限于日本领土,对于保障海上的安全毫无作用可言。结果,家光政权将原本应由朱印状行使的保障海上安全的职能托付给荷兰商人,而朱印状管理日本海上贸易家的功能则由奉书制度所代行。
然而,奉书制度是德川家光政权为纠正江户幕府在海洋政策上存在的扭曲,亦是其应对海外紧张局势的措施之一。对于日本而言,同属南蛮的荷兰与葡萄牙围绕澳门的利益反复纠缠,大有誓死不休之态势。同时期,马六甲海峡被截断,摩鹿加群岛至台湾海峡都处于燃烧的战火之中。此外,由于吕宋与暹罗不和,南海的局势也岌岌可危。印度支那半岛则进入动乱期。在越南,阮、郑两家交恶互战,无一日停息。暹罗则由于政局不稳而出现日本町被焚毁的事件。明清鼎革的中国可谓局势动荡,沿岸各处海盗横行。朝鲜境内的形势则不遑多让,政权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可以说,日本的宽永时期是天下动荡之际,海外局势的恶化促使德川家光推出更加严厉无情的海洋政策,幕府对海外贸易的管理亦趋于苛刻。
不仅对商品贸易管理严苛,幕府更不希望由于商人偷偷出口武器的缘故而陷日本于海外的军事危险中。例如,越南与其邻居交恶,而日本商人在两个地区都有贸易往来,异国对峙的局势本应使日本的商人面临退出的选择。吊诡的是,日本的贸易家反将这种恶劣的战争环境当作商机来把握,这使幕府掌权人哭笑不得。恶劣的日本商人希冀邻国有难,可趁此机会贩卖武器军需给他们,大赚国难财。卡隆曾言及:“锁国之事乃出于皇帝不欲外国人损伤其无比高尚的声誉。暹罗事件与台湾事件是令人难以容忍的。锁国之意图是为了不让武器秘密出口和控制基督教的传播。”*〔日〕幸田成友译:《日本大王国志》,东京:平凡社,1967年,第174页。显而易见,其分析一语中的。
结 语
江户初期,由于前任关白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且日人为祸亚洲诸国,幕府面临颇多外交问题。而德川氏势力未稳,无力兼顾内外,遂不欲干涉海外纠纷,弃日本国民于外,无视其生死。秀忠承袭乃父做法,并有所巩固。至家光时,亚洲大环境的变化使其进一步加强海禁,不允许国人出海。最终,幕府将自己封闭在幻想的“日本型华夷体系”中,视自己为天下之“中心”,希望一切外来事务都在日本解决,从而确立了海禁锁国政策。然而,正是日本政府与民间利益的博弈,不仅使国民在贸易上有所损失,更易使贸易家为了私下贸易而伪装出海,甚至流为倭寇,为祸海域。
近世初期德川幕府海洋政策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幕府不干涉海外的纠纷,以及任何可能会将日本卷入其中的事件,德川氏竭力将交涉地点置于日本国内。其二,不干涉它国内政。其三,仅接待来日人员,不向海外派遣幕府使节。为了鼓励他国使节来日,幕府更是优待赴日之人。其四,德川将军不再演绎外交主角,而由幕府臣僚处理实务。宽永锁国貌似是突然间对外政策的转变,实际却是德川幕府自家康以来海洋政策发展的结果,是对亚洲各地紧张局势的一种政策回应。以回避国际纷争为主旨的幕府强行迫使民间集团牺牲利益,遵从其政策。在此过程中,大御所外交逐渐成为将军内政的一部分,而行政上的变化恰巧完美诠释了日本海洋政策的收缩。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日本海洋政策完全转向危机管理,政府深恐民众在海上犯下丁点错误。在同民间集团的博弈中,幕府浓厚的“孤立”味道不仅伤害了本国人民的权益,更使他国增添对日本的不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