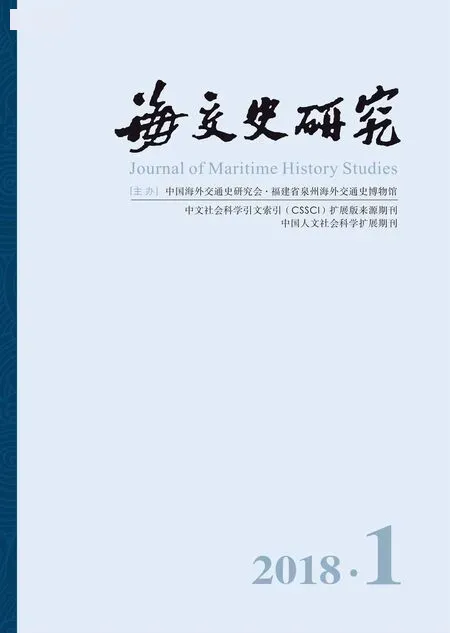陈志明主编:《东南亚的华人饮食和全球化》
孙梦迪
(公维军、孙凤娟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299页)
刘东意味深长地将这样一段话作为“海外中国丛书”的序言:“在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我们不仅必须放眼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认识中国;不仅要向国内的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这种认识体现出国人面对国外学术繁荣的紧迫感。在上世纪80年代的译介热潮中,饮食——这个国内学界鲜少有人关注的话题成为一个时髦的话题,而这种热度持续了30余年,依然活力不减。关于饮食,中国学者翻译了大量西学名著,如叶舒宪所翻译的马文·哈里斯《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一书,即试图从文化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各民族的饮食禁忌问题的来由;而在马孆、刘东共译的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一书中,介绍了海外学者对中国的饮食文化从古至今的梳理、分析工作。
饮食何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这无疑与早期人类学家对特定族群的饮食习俗的记录、研究有关。可以说,正是通过人类学,饮食成为一种“文化表达,并置于文化象征主义的语境之中”*彭兆荣:《饮食人类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1页。。从早期的功能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文化研究,在人类学的每次转向中,饮食的方式、作用和意义都会被特别提及。在全球化背景下,“饮食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一种特殊的联系方式和表达风格,人类学家可以通过对食物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考虑、了解进而分析某种文化系统的复杂关系和社会情形。”*彭兆荣:《饮食人类学》,第31页。
中国饮食已然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切入口。诚如前文所述,西方学者已经对此做出了非常系统的研究。作为一种“探寻作为食物‘形而下’中‘形而上’的文化符码以及表述”*彭兆荣:《饮食人类学》,第32页。,我们惯常的饮食习惯在西方异样眼光和学术思维体系中被重新审视。中国人自然是喜爱美食的,但美食抛开它的味觉意义,似乎从来没有被认真研究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当然这种重新审视必然伴随着某种不适。叶舒宪在《文化模式方法论》一文中指出,“按照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对于文化做主观上的价值判断是没有什么科学意义的。……研究者要做的不是‘优劣取舍’和‘应当如何’之类的判断,而是解答所以然即‘为什么’的问题。”*叶舒宪:《文化研究中的模式构拟方法——以传统思维定向模式为例》,载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编:《文化研究方法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11页。这些都是我们借鉴外国人类学经验反思我国学术研究的经验之谈。
今天,当学者们都可以平心静气地面对中外文化研究进行“所以然”的研究之时,我们或许可以消除那种狭隘的不快感。张光直认为:“中国的饮食史……第一个这样的转折点,是农耕的开始……第二个转折点,是一个高度层化的社会的开始,也许发生在夏王朝时期……第三个转折点,如果信息证明是准确的——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美]尤金·N·安德森,《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第261-262页。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放眼自身所处的时代,走出国门去体认中国饮食文化在世界各地的样态,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移民在这个过程中有着非凡的适应性和创造力,他们将中国饮食文化带向世界各地,并保持着独特性。一份米粉,一份春卷,一份传承至今又在全球化、地方化过程中不断变化的食谱和烹饪经验,正如陈志明所言:“既值得品尝一番,又值得好好研究。”
陈志明主编、公维军和孙凤娟翻译的《东南亚的华人饮食与全球化》一书,正适时迎合了这样一种阅读期待。作为一名马来西亚华裔人类学家和东南亚研究专家,这本书既能体现“去中心化的多元学术研究视野”(译序),又因为东南亚华人饮食的大量鲜活例子而显得格外生动有趣。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海外华人饮食的概述,涉及到理论性的华人饮食的全球化议题和描述性的全球性华人饮食的游历情况;第二部分描绘了华人饮食的情况,包括印尼、菲律宾、缅甸(以曼德勒为例)和越南的华人饮食;第三部分则具体阐述东南亚周边地区的华人饮食文化,包括拉斯维加斯的华人饮食、澳洲华人饮食和香港华人饮食问题。整体显示出从理论前沿到人类学民族志的调研经验,从全世界到东南亚再到全世界的一种研究思路。
正是由于东南亚华人饮食产生于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所以才与中国本土饮食截然不同。陈志明先生专门提及在饮食方面的“涵化”问题,即“异质文化接触而引起原有文化模式的变化”,显然,这涉及到人类学研究文化变迁的一种模式。当东南亚华人饮食与当地饮食相遇的时候,东南亚美食本身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就开始了“涵化”的过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饮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计方式,体现出个体(比如厨师、家庭主妇)极大的创造性和适应性。比如中国福建南部常见的蚝煎,在东南亚地区会选择使用更多煎蛋和更小的牡蛎;在中国广州,人们偏爱新鲜春卷,而在东南亚地区,炸春卷则更为流行。“总而言之,华人饮食在全球范围内的贡献是中国不同区域发展形成的一个核心饮食传统再生产而来的,而这种再生产是本土化创新或者从当地人那里采纳来的食品添加行为。”(第28页)这个结论看似是显而易见的,但却让我们不得不认真反思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中国本土所吃到的美食或许并不来自中国某个区域,而是更直接地来自东南亚华人饮食传统?比如说春卷,在上海的春卷几乎都是油炸的,有很多小吃店都只是笼统写着“炸春卷”,但也有店铺直接标明是“越南春卷”或者“泰式春卷”。中国本土饮食固然是东南亚华人饮食的来源,但东南亚华人饮食如何影响中国本土饮食,并形成一种互动和融合,也可以从中找到线索,正所谓“不要在上海寻找上海春卷,不要在广东寻找广东面条”。
中国饮食中的“饭/菜”组合、共享原则、食物保存技术等,经由东南亚饮食文化的传播发展,对太平洋地区的饮食也影响颇深。这种影响只有等到“中国学者使英语读者越来越深入理解中国早期社会生活,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之间饮食学联系的证据、考古发现和史前农作物的重建也都一一开始呈现出来”(第54页)的时候才能更为深入。而包括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微生物学等多重学科的证据组合寻求联系的过程,正体现了人类学对于跨学科研究的尝试。如何统合这些跨学科的材料,找到中国和东南亚饮食与太平洋饮食的关系,既涉及到一个证据条件具备的历史过程,又涉及到一个对证据组合、利用的认知和操作过程。南希·波洛克受到阿帕杜拉的“文化景观”建构全球文化流动的研究方法,通过四道食物景观:饮食资源、文献证据、食物共享、当代影响来描述并证明这种影响所在。更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将华人饮食文化这条线索与西方饮食文化对太平洋的影响进行对比,以此说明华人饮食文化的独特性。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研究方法和思路是在人类学的启发下,对文化研究运用多重证据阐释文化现象,并积极参与世界对话的文化理论。
吃饭不仅仅在于吃,在饮食人类学中,“吃什么”“如何吃”都会成为一个个研究问题。因为在某种无意识的层面上,它能够体现出我们自身的一种超越国界,从而形成一种比政治意义上的国民更为强大和持久的文化身份认同。对于印尼华人而言,“越是适应印尼文化,他们就越喜欢辛辣的印尼食物,而那些更倾向于中国文化的家庭,则喜欢更加正宗的中国食物”(第150页)。至于曼德勒的华人饮食,如家庭聚餐和庆典仪式中饮食文化,同样承载着族群互动和身份认同。
东南亚华人饮食很容易被单纯理解成为中国饮食的延续和扩散,这样的说法也许并不准确。因为当我们真正关注到国家边境两端两种相似的小吃时会发现,不同的国家在处理食材上的创造并不一定非要做到“谁影响了谁”。从文化整合视野来看,中国广东和越南的蒸粉卷都是“稻米文化”“稻米经济”下的产物,也都体现出一种自觉的创造。因此,小小的蒸粉卷成为重新反思“文化边界和国家边界联系在一起的惯性思维”(第206页)切入口。
当中国移民和东南亚的华人走向全世界的时候,饮食作为一种最具适应性的主题,成为我们理解跨国移民和全球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拉斯维加斯泰式中国菜是怎样的?东南亚华裔、澳大利亚饮食教父做出的“海洋四重奏”有着怎样的独特灵感和故事?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为我们通过饮食理解文化、全球化和世界主义提供了极其富有新意的视角。
民以食为天,对于吃的偏好成为我们理解自己的又一个角度,同时,也是“求解人与文化之谜的新途径”*[美]马文·哈里斯,《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户晓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译本序。。从一份小吃能够看到一个世界,从一种饮食习惯则能看懂一个人的文化和信仰,这并不是言过其实。不论是中国、东南亚还是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与地区,文化的流转往往是非常微妙、顽固而又富有活力的。而饮食作为适应性与创新性的主题,在这种流转中所传达出的诸多信息都有待深入发掘。本书较少在理论上进行梳理,但却通过丰富的实例——正如一份份在世界各地餐馆、普通家庭、庆典仪式的餐桌上进行的民族志调研一样,试图为“我们自己时代”的饮食文化增添新的材料。相信读者读罢此书,自然也就愿意相信,所谓的“中国菜”也不再是一种国别的区分,而是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时时启发我们对自身文化乃至所处的这个时代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