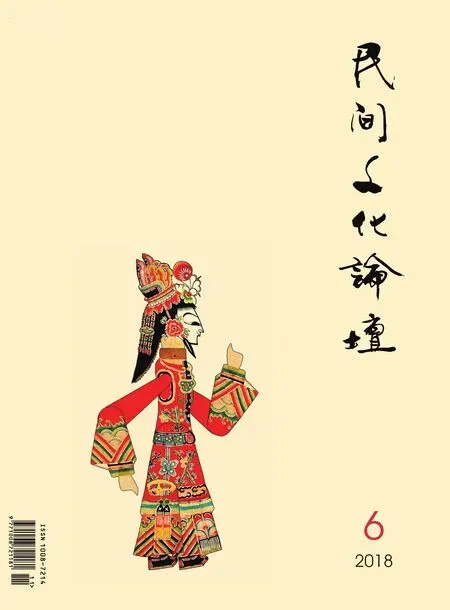在历史的掌心中反思
任何文化事象都是历史的产物,这似乎是所有文化研究者都明白并经常挂在嘴边的道理。然而,在实际的行动中,人们却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一点,“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等等之类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的大量存在,就是这方面的证明。它们也从反面的角度不断提醒大家,思考和探讨一切文化问题,都应该结合历史的视角。近年来,包括民俗学在内的许多人文社会学科当中,出现了大量有关回到元典(或原点)的呼吁,正是基于对当前研究中欠缺历史维度现象的警觉,并为了告诫同人要始终立足于学术史来展开相关研究。
拿作为民俗学之根本的“民俗”概念来说,从这个概念被发明以来,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有关其内涵与属性的讨论,就始终是民俗学界持续不断的重要话题,由此也推动了学科基本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完善。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其中不少讨论,主要是根据研究者所处时代的学术状况或需要,依据对概念字面意义的理解来进行,而较少结合它产生的背景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所指对象之间的互动,以及因此而发生的调整和改变来展开全面的探究,即使对其起源有所涉及,也只是简单列举它在1846年由威廉·汤姆斯发明的事实而已。这势必会严重削弱讨论的深度,也制约了学科本身的发展。
作为一个被创造的概念,“民俗”已经成了人们概括生活中各种以往只能用各地不同的说法来分别指称的文化现象的通用词。就这一点来说,这个概念的发明者、尤其是围绕这一概念而形成的学术共同体也即民俗学界,实际上为在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世界文化之间搭建理解的桥梁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尽管只是一个概念,但它的发明以及基于学术研究的推广,使得对于任何一个特定地区的人们而言看似千奇百怪的其他地区的生活文化传统,都因“民俗”这个相同的名称而同自我文化具有了相似性、通约性、一致性,从而为进一步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乃至相互接受、相互欣赏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这个概念对以其为核心而形成的学问民俗学,也具有基本的形塑作用。无论是把“民俗”看作“民”与“俗”两个独立概念的有机组合,还是视之为一个与“风俗”“习俗”“惯习”等相类似的更具内聚性的独立词,任何一种理解,都会对一段时期民俗学的学科属性与任务造成本质的影响。众所周知,其英语概念“folklore”是由“folk”(民众)和“lore”(知识)两个原有的现成词构成的新词。但这个新词,并不是对两个已有概念的简单组合,而是包含了更加复杂、更为丰富的意义,并预示了有关它的学问——民俗学——的根本使命。这一认识,以及基于这一认识的深入讨论,正是本期前沿话题的核心主题。其中的三篇文章,立足于“folk-lore”这一概念发明的历史,在全面梳理其深刻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民俗学的学科属性与学术方向,文章突出地体现了一种从历史出发、或者说“在历史的掌心中”反思学术概念与学科属性的特点。
当然,从国际学界的情况来看,由于不同国家历史文化与社会基础的不同,民俗学者有关民俗的理解,在侧重点上也存在着民族、地区或时代的差异。这些具有差异性的理解,自有其特殊的适应性。但无论如何,只有那些真正立足于过去的历史并密切结合当下需要的阐释,才是最接近对象的本质、最有益于学科自身建设的研究成果——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