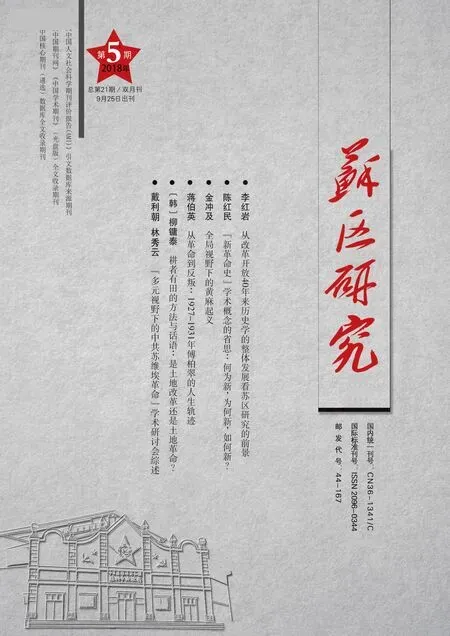“他们为什么获胜?”的追问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之方法论
提要:中共革命何以成功以及中共与农民的关系是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核心命题,马克·赛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深入研究了这一问题。在问题意识方面,该书受到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人生经历、学术史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最终促使作者进入中共革命史的核心命题;在文章结构上,该书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相结合,探究了“延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史;在结论上,作者运用了“延安道路”这一宏观性的概念,呈现了作者的鲜明主张。当然无论在文章结构、叙述和结论上,该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他们为什么获胜?》是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以下简称赛尔登)1991年8月在南开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文章,文章追问中共革命胜利的原因何在,并围绕中共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对以往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文章谈到,中共经历游击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基本事实一清二楚”[*][美]马克·赛尔登:《他们为什么获胜?——对中共与农民关系的反思》,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605-615页。,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这一事实,人们的解释与评价却很不一致。中共革命胜利之因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难题。《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以下简称《延安道路》)[*][美]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凡引自该书者,仅在文中标*页码。一书的出版,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里兹大学班国瑞教授认为这本书“开创了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局面,影响了整整一代研究中国的学者”[*]魏晓明、冯崇义:《〈延安道路〉的反思——译者序》,《历史教学》2003年第2期,第76页。。学界很多相关评论都涉及此书,这些评论将《延安道路》中的观点置于美国中共革命史的学术脉络中进行梳理,并对其观点和论证进行了一定的商榷。[*]如[美]范力沛:《西方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95-107页;陈永发:《“延安模式”的再检讨》,(台北)《新史学》第8卷第3期,1997年9月;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0),1990年版;陈耀煌:《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8期,2010年6月;陈耀煌:《政治、史学与史家:从〈汉学的阴影〉一文来看1950-1980年间美国中国共产革命史研究的转变》,《政大史粹》2002年第4期;李金铮:《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魏晓明、冯崇义:《〈延安道路〉的反思——译者序》,《历史教学》2003年第2期。不过,对于这样一部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经典著作,它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观点上的研究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在方法论层面的诸多启示。因此,本文拟从方法论的角度梳理出一些问题,以全面了解此书的贡献,也为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继续发展寻找问题的基点。
一、问题意识:“他们为什么获胜?”
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延安道路》一书问题意识的形成,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如政治和社会环境、个人经历、以往的学术研究、学术传统等方面。
本书虽出版于1971年,但据赛尔登所说,“这本书还是1960年代一批大事件的产品”(前言第1页)。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越战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左’翼观点开始为美国学者所青睐,逐渐成为美国中国研究圈中的主流典范”[*]陈耀煌:《政治、史学与史家:从〈汉学的阴影〉一文来看1950-1980年间美国中国共产革命史研究的转变》,《政大史粹》2002年第4期,第118-119页。。赛尔登就属于其中被影响的一员,1968年部分左翼学者成立了“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赛尔登就是其中的成员之一。左翼观点的影响使得赛尔登“从占优势的集权主义理论模式和国际共产主义理论模式中脱离出来,转而探究革命变革中的创造性和民粹主义来源”(第1页)。在此情况下,对这位左翼学者而言,中共革命何以成功成为一个需要重新解释的问题。
另一方面,赛尔登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为他的继续探讨留下了空间。在赛尔登之前,美国学术界对中共革命何以胜利的原因解释主要分为四种观点:社会经济纲领说、民族主义说、民主说、组织武器说。这四种观点在抗战时期赴根据地访问的记者和美国外交官中就已形成;到20世纪60-70年代,学术界接过这些命题重新进行探讨,本书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20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就是詹姆斯·约翰逊于1962年出版的《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1937-1945年间革命中国的浮现》一书。约翰逊支持了民族主义说,这成为赛尔登要对话的重要学术命题,“约翰逊的著作为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跳板,激发我去写作《延安道路》一书”。他认为约翰逊的观点忽略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第280-281页),他进一步指出了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说的缺陷:“侵略、战斗和恐怖并不一定激发民族主义激情。众所周知,对侵略战争的反应还有恐惧、逃亡、逆来顺受,甚至于还有迁怒于抵抗运动、指斥抗战激怒了敌人等等,这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区别。”(第284页)[*]对农民民族主义与中共革命的关系,可见李金铮:《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34-151页。[瑞典]达格芬·嘉图著,杨建立等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8-81页。[美]胡素珊著,启蒙编译所译:《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再版前言,第1-16页。对于“组织武器说”赛尔登也并不同意,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组织与那些解决农村问题的社会经济纲领之间的紧密联系”(第286页)。这些学术研究的基础促使赛尔登重新确立自己的观点。
影响赛尔登问题意识确立的另一个因素是美国学术界的传统,即重视学术史梳理,善于将自己的著作纳入到学术史之中,并对学术史的发展有所推动[*]参见王笛:《从历史的最底层往上看》,《南方都市报》2013年7月25日,第B15版。李金铮:《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121-133页。。赛尔登将自己的学术研究纳入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对中共革命胜利之因的追问上,并通过对陕甘宁边区的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
那么,问题意识确立以后,为何选择陕甘宁边区作为研究对象呢?
这部书提供了“第一批关于单个根据地的‘微观社会’”(第1页)的研究,这一研究对象的选择与美国中共革命史从中央到地方研究路径的转变是一致的。班国瑞指出:“自1970年代末期以来,研究中共党史的西方学者不再拘泥于追求‘大理论’(grand theory),转而从事以根据地为中心的地方研究。”[*]转引自陈耀煌:《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第144页。
对于陕甘宁边区的选择,赛尔登指出“这倒不是因为陕甘宁根据地在所有根据地中有代表性”,而在于陕甘宁边区有自己的特点:“它是最穷的根据地;它的大部分地区在建立统一战线以前已经完成了土地的再分配;它虽然曾经遭受日军的轰炸并发生同国民党军队的冲突,但它幸免于日军的侵略,因而这里的游击战争远不如敌后根据地中那样重要;最后,它是党和军队的总部,也是数以万计知识分子投奔的圣地。”(第265-266页)他还认为这一地区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了最差地区转变和发展的可能性”(第122页)。在这些特点之外,各个根据地在动员民众和社会政治制度等方面大同小异,因此“陕甘宁既是中国革命的缩影,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中心环节”(第266页)。
总之,《延安道路》一书问题意识的确立是多种因素汇合的结果,因势而异、因人而异,但像政治社会环境、个人经历等方面,对中西研究者来说是相同的。
二、问题的展开: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
问题意识的展开和落实最终要通过著作的结构来实现,一本著作的结构会受到作者的思路、材料的多寡、研究的题目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结合本书的内容可以看到,本书的结构展开呈现出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的特点。除前言、结论、后记外,按时间顺序分为六章;而各章的叙述以专题进行展开,横向拓展,显示了作者宽广的研究视野。笔者将六章的内容整合为五个方面的问题,兹分述如下:
1.寻找革命的源流
作者通过西方人在西北的游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农村调查资料证明:陕北地区贫穷、偏远、交通不便、自然灾害、军阀混战、土匪横行,这成为传统的武装流寇的理想之地。(第11-12页)在此情况下,农民面临的苦难呈现复杂性,包括“饥饿、战争和土匪的破坏、长期恶化的债务、租佃增多、离乡城居地主的出现、沉重的税收和土壤干燥”(第13页)。周锡瑞也在关*陕北的早期历史,对于陕北地区的社会环境,他也给出了类似的看法。[*]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38页。不过,这里对革命源流的追寻只分析了陕北地区的自然和政治环境,需要在其他方面继续发掘中共革命的源流。[*]关于中共革命源流的分析,可见李金铮:《农民何以支持与参加中共革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34-151页;黄道炫:《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源流》,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89-321页。
2.大革命时期的中共革命
在赛尔登看来,陕北地区的共产主义起源路径与其他地区并无二致,亦是五四时期通过学校、学生进行思想的传播,不过在传播源上,陕北地区受北京比受西安的影响大。在传播地区上分布不均,在渭河平原传播较广,而在陕西北部影响较小,(第28页)[*]周锡瑞也持此看法,见《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39页。这与陕北长期被地方军阀井岳秀控制有关。在革命思想传播的过程中,一大批地方领导人逐步成长起来,如刘志丹、高岗、谢子长等人。国共合作以后,中共在渭河平原地区发展迅速,在陕北地区发展缓慢,且发展对象限于学生和知识分子。冯玉祥1926年主政陕西之后,中共力量在渭河地区得到更大发展,1927年冯玉祥清党,中共势力衰弱。中共在陕北由盛转衰的历史再次诠释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
1927年和1928年中共先后发动了三次起义,均告失败。在这些起义的过程中,作者发现了革命者与反叛者的相似性:“特别是早期阶段,游击运动与陕西山区其他武装土匪极为相像。”(第40页)在这些起义中,渭华起义是最有影响的。渭华地区在大革命时期风起云涌,而中共的武装起义却遭遇失败,实是匪夷所思。作者提出了对两个假设的质疑,第一,“农村革命由农民的不满直接引起,特别是高租佃率和农民运动兴起高度相关”。渭河平原地区租佃率低却成为大革命时期的活跃地区,陕北地区租佃率也不高,却成为革命的重要据点。第二,“革命和农村‘现代化’高度相关”。而实际情况是“从1927年开始,运动的发展朝向农业中国最落后的地区”(第42-43页)。起义失败后,“以刘志丹为首的一派赞成打游击和农民起义,最终在陕北发展出一种可行的游击战略”(第44页),刘志丹回到陕北,以民团司令的身份继续进行革命活动,这种革命形式体现了革命与传统的延续性。
1928-1935年以后中共在陕北的斗争史,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有着大致相同的路径。陕北的斗争中也存在着进攻城市和进入乡村的党内斗争,而对于刘志丹等地方领导人来说,由于他们本地人的身份,陕北成为中共活动的重点区域,“上山”成为陕北中共力量的选择(第49-55页),这种选择使作者发现了革命与地方社会传统的延续性:“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游击队与陕北山里众多反叛和秘密社会小团体,不仅仅在不满军阀和地主权势上一致,特别是在较早年月,他们经常从事绿林好汉行动——劫富济贫。他们的突袭策略和撤返山区与其他反叛团体并无二致”(第50页),而其中的关键在于二者的转化。[*]由传统的反叛到革命的转化,可见[美]裴宜理著,池子华、刘平译:《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在陕北地区,促成这种转变的关键人物是刘志丹,但作者并未过多着墨转变的过程(第64页),事实上,由传统到革命的转变应是一个全方面的复杂的变化,此处不展开,拟另文探讨。1934-1935年中共进行了土地分配,作者评论道:“1934-1935年的土地革命,是陕北游击队获得农民支持的杠杆。农民长久积怨的爆发成为农民积极赞成土地革命的基础,也是扩大和加强军事、政治组织的手段。最初一度是绿林好汉式的小股游击军事行动,到1935年已发展成为全面的农村革命。”(第70-71页)最后,作者通过比较陕北的农村革命和江西的井冈山斗争总结了中共农村革命的基本特征,认为“在本质上,毛和朱德的游击队在井冈山面对的问题与陕北游击队面对的问题相似”(第80页)[*]作者指出唯一的不同点在于刘志丹和他的人员是本地人。,所采取的策略也是相似的,整个发展过程都体现了革命与传统的延续性。
3.从土地革命到抗战的过渡
在赛尔登看来,土地革命的主要经济后果是“打破了财富大量集中,通过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和财产分给穷人,大大增加了中农”(第84页)。土地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经济方面而且在于政治方面,作者引述了《西行漫记》中所描述的年长者和年轻人的评述,指出土地革命的开展对二者的吸引力是不同的:前者更*目于土地,后者则*目于土地革命带来的希望。作者对于土地革命对不同年龄人的触动的探讨令人深受启发。(第96页)
同时作者认为,仅仅将“民族主义”视为中共与农民联系的纽带是片面的,这种观点“忽视了战时抵抗运动的主要特点”,因此“要确保农民的支持则只有联系到农村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共产党使农村革命的实践适应统一战线的战时迫切需要,同时领导民众大胆地、创造性地解决农村在多重压迫下解体的问题,正是延安时期的重要标志”(第121页)。
4.抗战时期的中共革命
1937年以后,新民主主义在陕甘宁边区逐步实施,作者首先评述了1937年的根据地选举,他称这次选举是继土地革命之后的第二次大动员。(第128页)他称赞1937年5月12日形成的选举法“有西方自由民主的味道,不带有阶级斗争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色彩”。这样的立法,“国民党的政策制定者自孙中山时代以来从未实行过”(第129页)。选举运动的另一个意义在于激发人们对新的社会、经济等机构的兴趣和参与。不过,在选举运动实行过程中也呈现出了统一战线政策下的紧张性,即如何再次动员农民接受地主、富农的选举权和参与选举权成为中共党组织面临的难题。尽管中共一再动员,但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
经过选举运动,边区的政治系统初步形成,边区形成党、政府、军队、群众组织、参议会等组织的联动系统。政府部门逐步建立起来。与1937年前、1942年后都不同,这个阶段政府的特点是行政趋于正规化,行政风格高于动员风格,“当地革命者地位下降,相对上升的是较有经验的行政官员,他们的技巧在正式职能机构中备受重视”。在参议会方面,表达和实践出现落差,“实际上,起草和执行法律,参议会被都(应为都被——引者*)较小而更有效率的政府委员会和职能机构所遮掩”(第146-147页)。政府纵向结构为边区、分区、县、区、乡,在领导方式上实行纵向领导,其结果是“集权且自成体系的职能机构渗透到县级。相当程度上不受党或民选政府官员诸如县长等人的控制”(第150-151页),官僚系统中实行的薪水制度也体现了延安时代的俭朴和平等精神。(第155页)群众组织是迎合全民的机构,但赛尔登也指出,1938年以后群众组织工作的资料很少,因此“有人怀疑,这些组织大多呆滞,其作用主要由政府和党取代”,具体事实如何,需要进一步研究。作者描述了这些机构的基本情况,但对实际工作的情况未予更多*意。(第142-143页)
在统一战线方面最明显的标志是三三制,三三制在选举运动中的实施增加了其复杂性,这在不同性质的地区呈现的情况不同。在老区,“‘三三制’产生了与‘左派’的摩擦,主要是农民革命者不愿与以前的阶级敌人合作”;在新区,“共产党对‘三三制’的兴趣最强烈”(第164页)。“三三制”的实施主要体现在参议会上,在其他部门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实际上非共产党人很少握有县长这样的实权职位,特别是在共产党权力已经巩固的地方”。尽管如此,“三三制”对抗战时期中共的生存和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赛尔登总结道:“共产党通过‘三三制’表明他们有能力与无党派人士分享权力和共同有效地工作”,而“三三制”在其他根据地的作用更大,它“帮助建立了稳定的政府”(第166-167页)。然而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国共统一战线面临危机,在此情况下,中共应如何作为?(第172页)[*]在赛尔登的叙述中,他区分了发动式和治理式的革命政策,他认为1937-1941年之间中共的治理模式逐步由动员式向治理式转变,1941年危机状况下,中共的治理模式又返回到激进动员式。
5.“延安道路”
1941年开始,中共面临多重压力和危机,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形势迫使中共做出反应,边区政府改变税收政策,征收救国公粮,降低免征点、增收饲料税等新税种,民众负担增大。(第177-182页)
在此形势下,中共发起了整风运动。赛尔登谈到开展整风运动的原因在于“由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所引发的危机”,危机的出现使得中共内部关于政府及领导方式的不同意见表面化。(第183页)[*]两种主张指“一种是革命倾向,强调斗争及大众参与。另一种是官僚倾向,强调政治的稳定性及统一战线”。因此整风运动的目标在于:“建设一个在思想、方法和方向等方面都一致的统一政党”(第184页)。他解释到,“整风运动不是一场清洗运动”(第188页),其意义在于“找到了解决个人冲突、矛盾、政策上的争论以及党与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的方法”。在他看来,整风运动最进步的发明在于方式和手段,即采用了组织和教育的方式而不是开除、逮捕或处罚的方式,其具体方式在于强化教育、小组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改造等方面。其中赛尔登对小组学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赞誉有加。(第189-191页)[*]他运用小组互动的研究理论指出这种学习方式有助于思想上的统一,其实从读者阅读的角度也可以看到这种互相讨论方式有助于增强学习效果,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能够反映中共性格的政治文化,值得深入研究,可见黄道炫:《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的养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39-43页。1995年本书再版时,赛尔登对整风运动有了新的思考,他认为:“延安整风不仅是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至尊地位、特别是理论上的霸权关键的一环,而且是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抑制知识分子及党内积极分子的思想独立性关键的一环。”(第302页)但他同时也认为:“我们也不应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开放、最富有创造性时期的一些特色视而不见。”(第304页)
1942年以后中共采取的新政策和新措施构成了“延安道路”的具体内涵。在简政方面,赛尔登谈到,运动达到了两个目标,即缩短开支和充实了基层机构。(第205页)下乡运动在整风运动时期发起,其中干部的下放更具改革意义,“干部的下放有助于改善农村的孤立状况,有助于加强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的联系,有助于引进整风运动中所创造的新的领导方式”(第218页)。不过,下乡运动也使一些干部视其为降级处罚,并引发与本地干部的冲突。在政府权力结构方面,又从纵向领导转变为纵向双重领导,基层党和政府的权力得到加强。(第212页)
随着中共遇到危机,土地问题重新登上日程,因此中共到1942年才发布决议开始减租,1942年1月的减租斗争不断激进化,但仍被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减租运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推动生产的一面,更在于为合作运动提供了一定基础。(第225页)为推动农业生产,中共采取了两项办法:一个是互助合作,一个是大生产运动。中共在互助合作的形式上受制于传统的模式,在自愿原则与组织纪律性方面纠结,最终以改造的变工形式推动互助合作。他评价道:“互助组是农民大众们所熟悉的一种合作方式,是对土生土长的传统的一种创造性的利用。”(第237页)
步骤3:并行运行降阶和全阶自适应交互双模算法。当采用降阶估计值保障系统实时性时,在计算耗时较长的全阶算法运行完成一次后修正一次降阶估计值,以提高测速精度。若返回步骤2;若重复步骤3。
接着作者论述了互助合作运动在1943年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大生产运动(机关团体生产),一是向劳动英雄的学习。赛尔登认为这种生产运动已经超出了一般的经济意义,而是“旨在通过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相结合来增强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干部与人民之间的团结”(第239页)。另一个刺激农业生产的手段是劳模的树立,给予精神和物质的鼓励,赛尔登认为这些被发现的劳动英雄不仅在经济上有其意义,在乡村政治结构的变化上也有其价值。赛尔登将这些经济发展的路径概括为延安模式,这一发展模式的特点就是走一条劳动密集型发展道路,而这一道路之所以能够完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共革命与传统的延续和妥协,这些努力均是整风之后中共扎根基层的努力实践。(第250-258页)
在赛尔登看来,整风运动中的各项措施最终都落在群众路线上,理解群众路线要*意两方面的特征,“群众路线是针对农民社会的问题与缺陷而提出的。但是,它也同时考虑到了农民积极分子潜在的创造性和社会基层的创造性等因素”(第259页)。不过,随后赛尔登反思了自己对群众路线的认知,他认为“延安道路”中忽略了群众路线中的政治动员的阴暗面,但他同时也强调《延安道路》一书所做出的判断“是与国统区、军阀统治区和日本占领区比较而言,也是与当前贫穷落后的国家比较而言”(第300页)。
三、问题的落地:“延安道路”
赛尔登通过本书六章的论述之后,最终将问题落地为一个大理论的概括中,即他将书中所描述的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和成长模式称为“延安道路”,并将其视为中共抗战时期成长发展之路。
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作者对“延安道路”的历史内涵进行了分项评述,使我们了解了“延安道路”的具体内容。赛尔登并未对“延安道路”做出一个总体性的定义,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表述中总结出一些共同性特征。赛尔登谈到,他是在两种含义中使用“延安道路”这一概念的,第一个“表示在中国西北的黄土地区政治经济条件下,共产主义统治下出现的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风格及它的综合制度,它们最终构成了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第二个层面则“关*20世纪革命变革的理论和实际,以及后殖民时期的发展”(第4-5页)。也就是说“延安道路”是一个囊括中共抗战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双重办法的概念。
他进一步指出:“‘延安道路’是一个松散的概念,指的是使党、农民和地方精英形成新的关系的革命思想与实践。它既指民族解放战争的道路,也指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化。”(第266页)在第六章中,他谈道:“‘延安道路’是关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人民战争的别具一格的方式。其特色包括民众参与、简放政权、社区自治等。”(第202页)综合以上作者的说法,“延安道路”似可以这样表述:“延安道路”是中共走向成功与发展之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的综合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整风运动、精兵简政运动、减租减息、互助合作运动、大生产运动、大众教育运动等,这些政策是中共革命的创造和贡献,也是中共革命胜利的原因所在。
那么,如何认识“延安道路”这个概念?
首先,这体现了赛尔登对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理论贡献,从其问题意识的提出过程可以看到,赛尔登在写作本书时始终将自己的主张置于学术史的脉络之中,在梳理中共陕甘宁边区历史的基础上与以往的学术研究进行对话,从而提高了本书的价值。
其次,通过对“延安道路”的梳理可以看出,这个概念抓住了中共革命史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中共与农民的关系,可以说这也是“延安道路”的核心。但是,“延安道路”是一个囊括性很强的概念,作者只是在第六章中按专题进行了探讨,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这种“大理论”模式因包含内容过于宽泛而导致各项内容的分析不够深入,从而容易致人诟病。陈永发在其长文《“延安模式”的再检讨》对“延安道路”中所“未言之意”进行了商榷,不过从其叙述中可以看到,他的对话无法找到一个明确的靶子。
最后,是“延安道路”概念的普适性问题。范力沛即称赛尔登的研究方法属于“山头主义”的研究方法,即“集中研究一个根据地,通常是陕甘宁根据地,然后将研究这一根据地的结果推及所有根据地甚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美]范力沛:《西方学者对抗日根据地的研究》,《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96页。。因此,这一概念是否具有空间上的普适性,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余论
不过,在看到这本书贡献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兹列举如下:
第一,从本书的结构来看,赛尔登谈“延安道路”的起点是“陕西省:革命的环境”。与一般意义上党史的讲述方式并不一样,本书深入挖掘了陕北地区的革命环境和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部分内容稍显不足,一些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如第二章应该着重回答为什么陕甘宁根据地能够生存下来;文章开端虽然对陕西的革命环境进行了挖掘,但后面几章的内容并未深挖陕北地区的“社会”特质,而使读者看不到中共政策与地方的复杂互动过程。
第二,从本书的材料来看,据赛尔登自己所讲,所用的“关于共产党的情报档案文件来自台湾、日本和美国”(第1页),这与作者所处的60年代的环境有关。(第265页)也因此,根据地详细资料的缺乏,影响了作者探讨问题的深度。
第三,要更好地理解“延安道路”,就要对其中的各个要素分别进行深入研究。“延安道路”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在本书中作者研究了中共的各项政策的制定,但各个方面都未来得及深入探究,这就给相关议题的继续探讨提供了空间。而且还要深入研究其他根据地的情况,对赛尔登所谈的“延安道路”这些组成要素在其他根据地的实施情况进行探究,从而更好地理解“延安道路”对中共革命胜利所起的作用。
通过阅读此书,笔者也有一些关于中共革命史研究的体会:
第一,提出研究的问题要从学术史中来到学术史中去。赛尔登写作《延安道路》是在充分梳理以往关于中共革命胜利原因探讨之后提出问题的,即问题本身是从学术史中来;但更为关键的是赛尔登通过研究,最后运用“延安道路”的概念使自己的研究回到学术史中去,确立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地位,从而进入到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核心命题”。
第二,提问方式和问题意识会影响研究者的“*意力”,“*意力所及的地方才有历史”[*]王汎森:《“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层”——对“地方的近代史”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6期,第126页。。陈永发、陈耀煌对“延安道路”的批评是最猛烈的,他们集中指出了“延安道路”中所谈不多的一些问题,即陈永发所说的“并不是令人感觉愉快的课题”[*]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60),1990年,序文第4页。。但据我的理解,由于赛尔登的对话对象是农民民族主义,他的提问方式是“想弄清一个贫穷而技术落后的农业国家是如何在15年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抗战的”(第2页),陈永发与赛尔登所指向的问题并不完全一致。因为“*意力”的不同导致焦点的不同,这就提醒研究者要不断变换提问方式和问题意识,调整问题的聚焦。
第三,中共革命史研究中的“倒放电影”现象。在陈永发的批评观点中可以看到“倒放电影”的某些痕迹,即通过中共建国以后出现的现象来评估建国前的问题,这样做有其合理性,能够以贯通的方式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但是这样的思考路径有时也会影响研究者的“*意力”。如何面对结果与走进历史现场之间的张力仍是一个值得*意和需要探索的问题。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史学研究总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之中前进的。《延安道路》一书无论从问题意识、文章结构、理论解释等方面对今天的革命史研究仍然有其价值。只有不断地“追溯先辈之识见”[*]李金铮:《追溯先辈之识见: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与“旧”》,《史学集刊》2012年第5期,第25页。,才能真正实现学术进步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