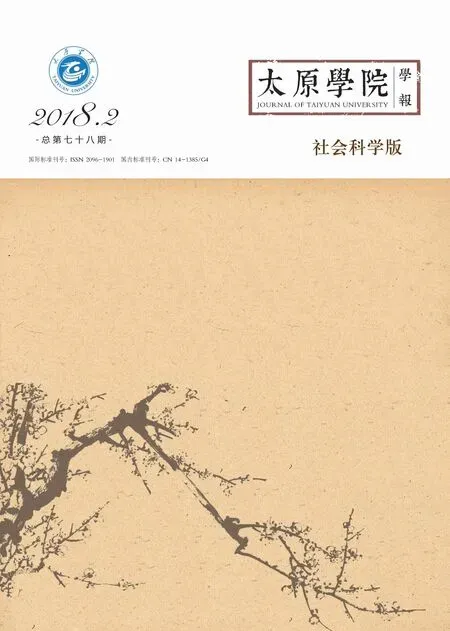唐代非实用性挽歌诗考察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学报编辑部,安徽 滁州 239000)
唐代献赠挽歌诗是一种配合葬礼出现的礼仪诗歌,主要是献赠给去世的皇族成员和具有一定品阶的官员,经过选择之后由挽歌郎在丧礼上反复咏唱,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倡哀挽,其次颂美,形式上大多为五言律体。其实用性决定了诗歌内容要符合礼仪的需要,然而抒情毕竟是诗歌的特质,言志从《诗经》时代就已经成为了诗人创作的内在要求,这使得唐代诗人在创作挽歌诗时有可能突破悲悼与颂美的固定格式。唐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相对宽松的思想环境也使得有些挽歌诗与献赠挽歌诗的实用性有所疏离,出现了少量不是以实用为创作目的的挽歌诗。
一、借哀挽诗之名行讽谏之实的挽歌诗
李商隐在他仅存的3首献赠挽歌诗中,对作为丧者的武宗皇帝没有一味地颂美,在承认武宗皇帝“武治”成就的同时,对他晚期的迷信神仙道教、妄求长生的荒谬之举,也给予了揭露和讽刺。下面看他的《昭肃皇帝挽歌辞三首》:
九县怀雄武,三灵仰睿文。周王传叔父,汉后重神君。玉律朝露惊,金茎夜切云。箫笳凄欲断,无复咏横汾。
玉塞惊宵柝,金桥罢举烽。始巢阿阁凤,旋驾鼎湖龙。门咽通神鼓,楼凝警夜钟。小臣观吉从,犹误欲东封。
莫验昭华琯,虚传甲帐神。海迷求药使,雪隔献桃人。桂寝青云断,松扉白露新。万方同象鸟,舆动满秋尘。[1]598
李商隐是一个关心现实政治和国家命运的诗人,他创作了有现实政治指向的政治诗、咏史诗多达一百一十首。从他的全部诗作看,那种关注现实政治、国家命运的精神和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抱负确实是一贯的,而利用献赠挽歌诗来反映现实政治,并对丧者(一个皇帝)进行讽刺和揭露,这可以说是献赠挽歌诗的一种“破体”,其价值当然高于同时代的那些所谓符合“臣下之旨”的同类诗作,刘学锴和余恕诚两先生在《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对这3首挽歌诗有一段按语,评析甚为精当,现录述如下:
帝王挽歌,哀挽而外,例皆颂美之词也。此三章独于颂美哀挽之同时,托讽寓慨,直似盖棺定论之史赞。唐后期诸帝中,宪宗而外,惟武宗在位期间政治、军事略有起色,其治绩不仅远胜穆、敬,亦超越文、宣。义山于其武功,备极推崇,诗中一则曰“九县怀雄武”再则曰“玉塞惊宵柝,金桥罢举烽”,极称其讨回鹘、平刘稹之功。本以为太平有望,东封有日,不意其因耽于神仙方术而遽死,故诗中於其求仙再三托讽致慨。讽之正所以深惜之也。要之,颂赞其雄武英达,伐叛平乱,深惜其迷信神仙,年寿不永,为三章大旨。其中首章赞、讽并寓,而笔意较虚;次章侧重于赞其“雄武”,而深慨其年寿之促;三章侧重于其“重神君”,耽于神仙方术。似是首章总提,二、三分承。程氏不明作意,力主首章为颂扬冠冕之词,于“周王”联别生曲解,求深反凿。姚笺谓三章以时间为先后为序,亦非。[1]606
由此可见,李商隐这一组挽歌诗的创作动机与通行的献赠挽歌诗大相径庭,具有“史赞”的性质。也就是说作者以“史”的观点对唐武宗的功过是非做客观的评价,而这样做的出发点是对国运民生的深切关注。程梦星和姚培谦之所以对本诗“作意”产生误解,就是因为古代的诗评家们还是囿于传统献赠挽歌诗的创作思路,用虚饰哀挽的俗套写法来匡囿义山之诗,他们无法想象挽歌诗体也能用来表达讽慨之旨。倒是在义山另一首题为《茂陵》(汉武帝的陵墓)的诗里被很多前代的学者看出了是对唐武宗的讥刺。诗曰: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偏近郊。内苑只知含凤嘴,属车无复插鸡翘。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1]607
这是一首托名汉武帝实刺唐武宗的作品,清代李商隐诗歌的研究者大多意识到了这一点。冯浩的评语较为切合题旨,他说:“武宗武功甚大,故首联重笔写起,不仅游猎武戏也。推之好仙好色,而仍归宿边事,武之所以为武也。”[1]611刘学锴和余恕诚两先生明确指出此诗内容与《昭肃皇帝挽歌辞三首》的异同:“挽歌辞於颂其武功外,仅讽其耽於神仙方术,此则兼及游猎、女宠;挽歌辞仅於哀挽中托讽寓慨,此则讽意较为显露。然其赞扬武功则同。”[1]612笔者以为讽意的“显”与“露”的程度变化与两首诗的体裁有关,相对于用挽歌诗直面本朝天子而言,借古代君王以寄寓就会显得方便和自由得多。
李商隐《昭肃皇帝挽歌辞三首》以挽歌诗为讽寓实是献赠挽歌诗中的“别体”,同时诗人顾非熊的《武宗挽歌词二首》才是中规中矩的献赠之作,这二首诗也极力颂扬了武宗的武功,如“静塞妖星落,和戎贵主回。”并且对武宗抑废佛教一事也大加褒词,诗中写到“国用销灵像,农功复冗僧。”[2]5788可是他对武宗抑佛同时大肆地崇道,并且因此误信方术神药而身亡的事却只字不提。
二、唐代拟古的挽歌诗
在唐代,除了主导的五言律体的献赠挽歌诗以外,还有一种古老的挽歌诗体存在,那就是一些题名为“挽歌”或者“古挽歌”的、不针对固定丧者的泛咏之作,但这一类诗所留存的作品数量很少,参与创作此类挽歌诗的作家也不多,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二》收录了孟云卿、赵微明、于鹄、白居易4人的5首诗,《全唐诗》又增加了于鹄的2首,张之象的《唐诗类苑》中另录沈千运1首,题名亦为“古挽歌”,这首诗在《全唐诗》里题名为“古歌”,考其诗意,当亦属于此类挽歌诗。
这类挽歌诗远绍《薤露》《蒿里》,近法陆机。在唐代献赠挽歌诗主要为实用哀挽诗体的时期,这种泛咏挽歌诗的实用性进一步弱化。
到唐代,魏晋时期葬礼挽歌与文人拟古挽歌诗分流并行的局面被五言律体献赠挽歌诗一枝独秀所代替。拟挽歌、自挽歌创作已退出了大部分诗人的创作视野。唐代仅有的这几首拟挽歌诗与魏晋六朝的拟挽歌虽然同样以泛咏生死悼挽为主题,但是却没有了那一时期普遍存在的“自挽”的情调。对于死亡悼挽主题,魏晋时期的诗人比如陆机等人大多采用代言体的形式去表现。诗中所写的是一种为死者设身处地之语,诗中的情景,是以死者亲身感受道出的。而唐代诗人则与诗中所写的丧者及丧葬情事拉开了距离,而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抒发自己的感情。试举两首做简单比较。
重阜何崔嵬,玄庐窜其间。磅礴立四极,穹隆放苍天。侧听阴沟涌,卧观天井悬。圹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返岁,我行无归年。昔居四民宅,今托万鬼邻。昔为七尺躯,今成灰与尘。金玉素所佩,鸿毛今不振。丰肌飨蝼蚁,妍姿永夷泯。寿堂延魑魅,虚无自相宾。蝼蚁尔何怨,魑魅我何亲。拊心痛荼毒,永叹莫为陈。[3]654(陆机诗)
寒日蒿上明,凄凄郭东路。素车谁家子,丹旐引将去。原下荆棘丛,丛边有新坟。人间痛伤别,此是常别处。旷野多萧条,青松白杨树。[4]309(赵微明诗)
从上引两诗可以明显发现两首诗的叙述角度的区别,陆机以一个已死将葬者的口吻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其实这些都是已死者所不能的),而赵微明诗的作者却是一个连丧者是“谁家子”都不知道的“旁观者”,似乎只是一个偶然经过的路人。从表现手法上看,陆诗具有一定荒诞性,赵诗则遵循现实再现的原则。这两首诗可以说是魏晋和唐代拟古挽歌诗的代表作品。陆机为代表的身处乱世的魏晋诗人,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从而形成文学的悲剧性基调。而生死问题自然成为其中重要的主题,表现在拟挽诗中的“自挽”情调,看似放达之举,其实是难以化解心中的“大悲大惧”而故作通脱的做法,这一时期的拟挽歌诗更多是表达了悲凉、无奈的情感(真正做到以达观的态度对待生死的大概只有陶渊明一个人)。[5]77-78
到了唐代,大一统的王朝赋予文人的精神风貌当然与终日忧惧生死的魏晋文人不同,所以唐代拟古挽歌诗作者没有采用那种近乎荒诞的自挽表现手法,只是从形式上学习了魏晋的五言体例,情感表现上对生死持一种相对冷静的态度。虽没能达到陶潜的彻悟境界,倒也不至于如魏晋其他拟挽歌诗人那样始终缠绕着难以释怀的死亡情结。在唐代这种拟作只是一小部分诗人尊古仿古的模拟之举。在5位创作了拟挽歌诗的作者中,沈千运、赵微明、孟云卿都是入选元结《箧中集》的作家,元结论诗提倡淳古淡泊、质朴自然之诗风,所编《箧中集》体现了自己诗学之宗旨。他说:“风雅不兴,几及千载,溺于时者,世无人哉。……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4]299赵微明、孟云卿的拟挽歌都收在《箧中集》里。这些作家主要是对初盛唐时期兴起的格律诗不以为然,专以拟古为宗旨,故所创作的诗歌多以五言的古体诗为主,在当时五言律体献赠挽歌诗日趋主流的形势下创作拟古挽歌诗实际上是一种复古倾向的表达,实用的可能性极小。沈千运的《古挽歌》:“北邙不种田,但种松与柏。松柏未生处,留待市朝客。”[2]2888诗中没有对死亡的哀惧,流露出即使是那些现世在争名夺利的“市朝客”最终也难免一死而坟植松柏的情绪。这种哀挽情绪淡到几乎看不见且不针对具体丧者的拟挽歌诗远离现实丧葬礼仪是不难理解的。
如果说魏晋时期的文人拟挽歌诗交织着抒情和实用两种目的的话,唐代的拟挽歌诗的实用性在五言律体兴盛与诗人复古目的双重作用下已消失殆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抒情诗歌了。
三、仕进之资和游戏之笔的挽歌诗
唐代挽歌诗是丧葬礼仪的组成部分,因此绝大部分献赠挽歌诗的创作目的都是配合现实丧礼。但也有一小部分的献赠挽歌诗的创作缘起与现实葬礼脱离了关系,把挽歌诗或作为仕进之资本,或变成游戏的笔墨。
在唐代,读书人除了参加科举博取功名而外,以自己的诗词歌赋投刺当途或朝廷,显示才华以期获得援引提拔也是他们成功的另一“捷径”,很多著名的文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如大诗人杜甫、李白、孟浩然等。那些献赠当途或朝廷的作品题材、体裁多样,然而以挽歌诗作为投献手段倒是相对比较独特的做法。代宗宝应年间有一位叫郑丹的人便这么做了,并且取得了成功。在唐人高仲武编辑的《中兴间气集》中记录了郑丹的两首献赠挽歌诗:《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挽歌》和《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挽歌》,诗前有一段编选者所加的关于这两首诗的写作缘起,其词曰:
丹诗剪刻婉密。宝应中,献二帝两后挽歌三十首,词旨哀楚,得臣子之致,虽不及事,朝廷嘉之。解褐任蕲州录事参军。今选尤者,列于此集。[4]470
《唐诗纪事》卷二八有类似的记载,《全唐诗》郑丹条下亦仅录此二诗,诗题较简,分别为《明皇帝挽歌》和《肃宗挽歌》,并记郑丹为大历时诗人。玄宗卒于宝应元年四月甲寅,同月丁卯肃宗卒。则丹此二诗,必当玄、肃父子二人先后去世不久而作,时当宝应。故此文中说他“不及事”,那么郑丹的这两首献赠挽歌诗就与当时二帝、两后的丧礼就不具有一般的挽歌与丧礼之间的共时性特点了。实际上郑丹的创作目的本来就不在此,而是以此作为自己获取官阶的“敲门砖”,所以他一口气进献了三十首之多,(高仲武仅从中选了两首,而郑丹也就只有这两首诗传世)而且都是“合体”之作。即文中所谓“词旨哀楚,得臣子之致”,可能正是他的这种“忠”打动了朝廷,或者是朝廷正需要这样的文人来宣扬道统,因此“朝廷嘉之”,授予他蕲州录事参军的官职。郑丹之所以成为一个幸运儿,是因为他选择了一个一般士人没有想到的捷径。
郑丹以挽歌诗登上仕途看起来是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但在唐代挽歌诗大行其道的环境下,在纯粹悼挽目的以外创作挽歌诗是有可能的,不过未必都像郑丹那样的露骨。一些士子很有可能在向达官显贵献赠挽歌诗的时候借机显露才华,以图汲引。另外,在唐代挽歌诗大行其道,朝廷经常征召百官进献挽歌诗,而百官并非个个都具诗才,就有可能请别人代作,这也给一些士子提供了展露才华,结交豪门的一个机会,这种动机的羼入就与挽歌诗悼挽实用功能产生了偏差。
《全唐诗》八六八卷著录了两首分别署名王炎和沈亚之的挽歌诗,丧者一为西施,一为秦穆公女弄玉,且均为记梦之作。其实这两首挽歌诗的故事本事在《太平广记》(成书于太平兴国三年即978年)和《沈下贤集》(刊刻于元佑丙寅即1086年)都有著录,只不过在《太平广记》里《葬西施挽歌》的作者署名“王生”,而在《沈下贤集》里署名“王炎”,故事情节基本相同,都以沈亚之为串联故事的线索人物。另外,两诗在两书中所属故事篇名也有不同,在《太平广记》里《葬西施挽歌》属《邢凤》篇,出自小说集《异闻录》,《弄玉挽歌》属《沈亚之》篇,出自《异闻集》。在《沈下贤集》里西施和弄玉的挽歌诗分属《异梦录》和《秦梦记》两篇“杂著”,此种错讹,《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有考辨说:“考《秦梦记》《异梦录》二篇,见《太平广记》二百八十二卷,……均注曰出《异闻集》,(此处《总目》记录有误,见上述不云出亚之本集)然则或亚之偶然戏笔,为小说家所采,后来编亚之集者,又从小说摭入之,非原本所旧有与?”[6]2016综合以上,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不论“王炎”与“王生”的不同,还是所属篇名的相异,这两首挽歌诗的作者实际上都是沈亚之一个人。《全唐诗》的诗前序文就是这两个故事的梗概:
元和初,太原王炎梦游吴,闻吴王宫中出辇,吹箫击鼓,言葬西施,诏词客作挽歌,炎进诗,王甚嘉之。——《葬西施挽歌》前序。
诗曰:西望吴王国,云书凤字牌。连江起珠帐,择地葬金钗。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
太和初,亚之客橐泉邸舍,梦入秦,见穆公,尚始平公主弄玉。所居宫曰翠微宫。公主芳姝明媚,笔不可模画。每吹箫,声调远逸悲人,闻者莫不自废。约一年,公主卒,葬咸阳原,公命亚之作挽歌并墓铭。后公辞亚之令归,又为歌一章,仍至翠微宫,与公主侍人泣别。有题宫门诗。已而公命车驾送出函谷关,为别语未卒,惊觉。橐泉,秦穆公葬地也。——挽弄玉诗序
诗曰: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佃坠芳草,香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2]9831
沈亚之(约781—约832)是中唐时期一位重要的文学家,他工诗善文,尤长于传奇小说。李贺称之为“吴兴才人”,鲁迅先生称其传奇小说善“以华艳之笔,叙恍惚之情,而好言仙鬼复死,尤与同时文人异趣”。[7]48上述《秦梦记》即是他的传奇名篇。运用诗歌成为“文备众体”的唐传奇创作的一个常见表达模式,许多优秀小说家往往把诗笔的妙用发挥到极致。他们非常自觉地运用诗笔来表达情感,营造意境。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沈亚之的传奇善叙仙鬼恍惚迷离的情事,有华艳的文风,这是其传奇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挽歌诗体入传奇小说也可以说是他的独创之举,将板滞无趣的挽歌诗写得凄婉缠绵,俨然是以挽歌诗之名,行情诗之实。
《秦梦记》是沈亚之以春日昼寝橐泉(秦穆公葬地)邸舍梦入秦为缘起而敷衍出来的一个故事。小说中写他因军功得尚始平公主(时当寡居的弄玉),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好景不长,弄玉的死去使沈亚之也渐渐失去了秦穆公的恩宠。《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说这篇传奇:“大抵讳其本事,托之寓言”。[6]2016或许沈亚之钟情贵主而无缘遇合,借小说家言寄托情思。然而,作者在这篇小说中刻意逞现的是自己的文才诗笔,小说中三处用诗,一处用楚辞体铭文。而且这几处用诗与一般传奇小说中常见的或以诗代话,或以诗为戏不同,三首诗题材各异,一为挽弄玉,一为别穆公,一为题宫门。体裁也尽不相同,有五言律体,有七言绝句,还有杂言体格,从此便可看出作者刻意出奇、精心结撰之功。贯穿这几首诗的内在线索便是一个“情”字,在情的统摄之下,挽歌诗变成了凄艳缠绵的伤情之作,又仿佛是可与潘岳媲美的悼亡佳构,脱尽宫廷官宦挽歌诗的俗套,夫妻的生离悲怀代替了君臣同僚的虚饰哀情。
与唐代的拟古挽歌诗不同,沈亚之穿插在传奇小说中的挽歌诗,既有了明确的丧者,也成为一种卖弄文才的炫技之作。
参考文献:
[1]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5]范子烨.永恒的悲美:中古时代的挽歌与挽歌诗[J].求是学刊,1996(02):77-81.
[6]四库全书研究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7.
[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