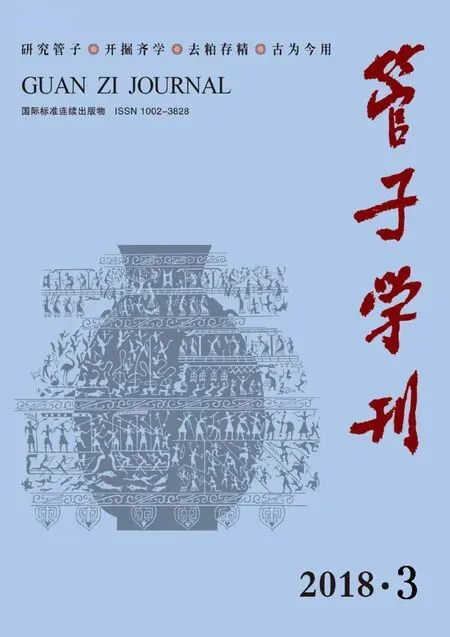齐“雍廪杀无知”考辨
——兼论齐国雍氏的问题
张淑一
(华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在春秋时代齐国的历史上,发生过齐襄公十二年(公元前686年)齐僖公之侄公孙无知联合两位大夫连称和管至父发动叛乱,弑杀齐襄公而自立为君,但很快又被“雍廪”所杀的事件。这一事件因为与齐襄公之弟公子小白先出奔莒而又归国、最终成为春秋首霸之齐桓公的历史有直接的关联,因而是齐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但是就本段史事的记载来说,先秦时代的主要文献《左传》《国语》《管子》等都对公孙无知因何杀齐襄公,无知与连称、管至父是如何作乱的记载甚详,但却又都对公孙无知被“雍廪”所杀一笔带过,这就使得“雍廪杀无知”成为齐国历史上的一个迷团,“雍廪”究竟是人名还是地名始终含混不清,令人不明所以。
一、“雍廪”谜团的形成
有关公孙无知被杀的基本史实,《左传》分散在庄公八年、九年两年的记载当中,但两年的内容全部加起来,也不过两句话:“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春,雍廪杀无知”。《管子·大匡》亦记载了此事,但也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只作“公孙无知虐于壅廪,壅廪杀无知也”。“壅廪”即“雍廪”,“雍”“壅”同音通假。
由于《左传》庄公八年、九年与《管子·大匡》均未说明“雍廪”为地名还是人名,而《左传》昭公十一年又将公孙无知被杀表述为“齐渠丘实杀无知”,《国语·楚语上》也作“齐渠丘实杀无知”;《国语·楚语上》又说“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弁、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徵、衙”,将渠丘与郑之京、栎,宋之萧、亳,晋之曲沃等城邑并列,明确显示“渠丘”为地名,因而很多史家便把“雍廪”视为人名。
例如,班固就把“雍廪”列入《汉书·古今人表》的“下中”档次,写作“雍人禀”,“禀”同样是“廪”的通假;应劭的《风俗通·姓氏》篇也把“雍廪”当作人名,以之为“雍氏”的人名例证之一,曰“周文王第十二子也,雍伯之后,以国为姓,今或音雍州之雍。郑大夫有雍纠,楚有雍子,齐有雍廪,宋有雍鉏”。此后贾逵注《史记》,又将“雍廪”与“渠丘”建立联系,谓“雍廪”为“渠丘大夫也”(《史记·齐太公世家》裴骃《集解》引)[1]1485,之后三国吴韦昭的《国语·楚语上》注[2]498,晋杜预的《左传》昭公十一年注[3]1344,南朝郦道元的《水经注·淄水》,都纷纷沿用贾逵之说,谓“渠丘,齐大夫雍廪之邑”。至唐朝,张守节为《史记·秦本纪》作《正义》,也以“雍廪”为人名。到清朝,高士奇作《春秋地名考略》,虽然注意到了《左传》昭公十一年唐孔颖达《疏》引郑众谓渠丘为公孙无知之邑的说法,意识到如果雍廪也是渠丘大夫,那么两者便相抵牾,但他仍然左右弥缝,以晋国封桓叔于曲沃而以栾宾傅之、郑国使许叔居许而以公孙获佐之、楚国使太子建居城父而以奋扬助之为之疏通,认为一个邑可以同时有两位主脑,仍然将“雍廪”看作人名(《春秋地名考略》卷之三齐国葵丘条)。此后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传诂》(《春秋左传诂》庄公八年),也认同“雍廪”为人名。
文献中也有把“雍廪”当作地名的,但此说仅见于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记述,司马迁将“雍廪”写作“雍林”,谓“桓公元年春,……雍林人袭杀无知”,唐司马贞《索隐》将此解释为“盖雍林为邑名,其地有人杀无知。”不过因为在《史记·秦本纪》中,司马迁又将此事记述为“齐人管至父、连称等杀其君襄公,而立公孙无知。……齐雍廪杀无知、管至父等,而立齐桓公”,此记述又与《左传》的记载相近,而与《齐太公世家》的说法有区别,因而又让人生出困惑,张守节于是兼采两说,谓“雍廪”“是雍林邑人姓名也”(《史记·秦本纪》张守节《正义》)。
由上述梳理可见,所谓“雍廪杀无知”,究竟是名为“雍廪”的人杀了公孙无知,还是“雍廪”这个地方的人杀了公孙无知?两说皆有,莫详谁是,但人名说在其中占上风。
二、“雍廪”应为地名
然而笔者以为,虽然“雍廪”为人名的说法一直占上风,但“雍廪”为地名说更不容忽视,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的记述更值得我们关注,原因有这样两个方面:
首先,在所有对公孙无知被杀这一史事有过记载的先秦秦汉原始文献当中,都没有言及“雍廪”为人名者,这些文献除了上文已经列举的《左传》《国语》《管子》《史记》之外,还有《春秋》庄公九年、《谷梁传》庄公九年、《公羊传》隐公元年和庄公九年、《吕氏春秋·贵卒》篇以及《春秋繁露·王道》篇四部。这四部文献对于公孙无知被杀的记述都只作“齐人杀无知”,或“国杀无知”,均不曾言及杀公孙无知的人名叫“雍廪”。上述文献在记载这个事件时所表现出的如此高度的一致性,显示出从先秦直到西汉时期,都没有“雍廪”为人名的说法。而本文前述梳理的“雍廪”为人名之说法的形成过程也显示,以“雍廪”为人名,其实起源于东汉以后的注家对于上述原始文献的注释。
其次,虽然东汉以后的注家将“雍廪”解释为人名者颇多,然而各家对于“雍廪”因何而为人名,却又都是出于对《左传》《国语》等原始文献所语焉不详的内容的推测,各家都没有就“雍廪”为何是人名给出过积极的证明。而与之相反的是,虽然以“雍廪(林)”为地名者仅有《史记·齐太公世家》一家,但是《齐太公世家》对于这一事件却有比较清晰的记载,谓:“桓公元年春,齐君无知游于雍林。雍林人尝有怨无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袭杀无知,告齐大夫曰:‘无知弑襄公自立,臣谨行诛。唯大夫更立公子之当立者,唯命是听。’”并且在接下来关于公子小白被立为君的记述中,又重申了“雍林人杀无知”的说法,谓:“小白母,卫女也,有宠于僖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杀无知,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
“廪”和“林”,上古音皆为来母侵部字,中古音都属于开口三等,两者只有声调的差别,《管子·戒篇》:“桓公明日弋在廪”,郭沫若《管子集校》引张佩纶《管子学》便说“廪,林之借字”;《文选》卷九晋潘岳《射雉赋》有“越壑凌岑,飞鸣薄廪”句,其中的“廪”亦当读作“林”,“飞鸣薄廪”就是指雉鸟飞集鸣叫于丛林。因而“雍廪”、“雍林”互相通假,《左传》等文献中的“雍廪杀无知”,就是《史记·齐太公世家》中“雍林人袭杀无知”的简化说法。
所谓“雍林”,或即齐国都城临淄城门之一雍门周围的树林。《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齐国的陈逆“以公命取车于道,及耏。众知而东之,出雍门”,《韩非子·难三》记载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都显示临淄的城门中有一个叫雍门;而《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晋人伐齐,“伐雍门之萩”,“萩”即“楸”,《说文·木部》:“楸,梓也”;《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记载齐景公“登箐室而望,见人有断雍门之橚者,公令吏拘之”,以上材料都反映了雍门附近树木很多,即雍门有林。
三、“雍廪”与“渠丘”“齐”的关系
以“雍廪(林)”为地名,还有一个“雍廪(林)”与“渠丘”及“齐”之间的关系问题需要解决。前文已述,《左传》昭公十一年和《国语·楚语上》都把“雍廪杀无知”表述为“渠丘实杀无知”,“渠丘”为地名无疑。而如果“雍廪(林)”也是地名,那么它与“渠丘”的关系该如何解释?笔者以为,两者可能是大地名与小地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春秋时代有两个渠丘,其一属于齐国,另一属于莒国,《左传》文公八年:“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与渠丘公立于池上”,以及文公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丘。渠丘城恶,众溃,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这个就是属于莒国的渠丘,与公孙无知被杀无涉。
属于齐国的渠丘又作“葵丘”,即齐襄公派连称与管至父戍守、驻扎期满却不派人替代而引起二人叛乱的地方。《左传》孔颖达《疏》引郑众说谓渠丘为公孙无知之邑,或为有据,因为无知所封与连称、管至父所戍同在一地,几者更有机缘互相勾连作乱。渠丘为齐国的大邑,前引《国语·楚语上》和《左传》昭公十一年都记载楚灵王问申无宇曰:“国有大城何如?”申无宇回答“郑京栎实杀曼伯,宋萧亳实杀子游,齐渠丘实杀无知,卫蒲戚实出献公”,将渠丘列为“害于国”的大城之一。渠丘与临淄相邻,郦道元《水经注·淄水》:“时水又西北迳西安县故城南,本渠丘也”,“西安”为西汉所置县名,属齐郡,位于临淄西三十里处,郭守敬注:“《续汉志》西安有蘧丘里,古渠丘”。
而“雍门”恰为临淄的西门,《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晋伐齐,“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列子·汤问》有“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均说明雍门在临淄之西;而《战国策·齐策一》孙膑谓田忌“使轻车锐骑冲雍门”,高诱注更是直接说:“雍门,齐西门名”。雍门既然位于临淄的最西面,作为雍门附近之林的“雍林”亦自然在西,正合于渠丘的地理方位,因此雍林极可能是隶属于渠丘的某个小地名。雍林属于渠丘,两者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雍林人”同时也是“渠丘人”,因而文献上无论是写作“雍林(廪)杀无知”,还是作“渠丘杀无知”,于地理关系上都不成问题,逻辑上均能说得通。
而“雍林(廪)杀无知”在《春秋》庄公九年又写作“齐人杀无知”,这要从《春秋》的“笔法”即地名书写义例上找原因。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中曾总结过:“《春秋》之例,通都大邑得以名通,则不系以国;……若小邑不得以名通,则但书其国而不书其地,如‘盟于宋’,‘会于曹’,必有所在之地;而其地小,名亦不著,书之史策,后世将不知其所在,故以国书之”(《古书疑义举例》卷三“以大名代小名例”)。雍林正符合“小邑”的情形,虽然在该地发生了弑杀国君的大事件,但因其地小,声名不为人所知,所以《春秋》仅列国名,作“齐人杀无知”。其后《谷梁传》《公羊传》《吕氏春秋》《春秋繁露》等也作类似的记述,当属于对《春秋》的沿袭。
综上,“雍廪”并非人名,而是地名“雍林”的同音假借。《左传》《管子》等文献的“雍廪杀无知”,其实是《史记·齐太公世家》“雍林人袭杀无知”的简化表述。“雍廪”与“渠丘”是大地名与小地名、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于《春秋》等文献中又作“齐人杀无知”,则是由《春秋》的地名书写义例所致。
需要说明的是,先秦文献的作者对于将“雍廪”“渠丘”“齐”三个概念交互使用,可能并不觉得有何不妥,因为作为当时人,他们熟知其中的内在联系,以之为无需赘言的常识。就如我们同现今记述某个人,可以说其是“临淄人”,也可以说其是“淄博人”或者“山东人”一样,因为临淄区属于淄博市、淄博市属于山东省是当今地理上的常识,所以人们并不会特别地对三者间的关系加以解释。只是随着时代久远、记忆模糊之后,常识不复为常识,当时无意间的混用,却给千载之下的读史者造成了困惑。
顺便提及,齐国确实有“雍氏”,但不过与“雍廪(林)”并无瓜葛,也与应劭所谓的“周文王第十二子也,雍伯之后,以国为姓”没什么联系。《左传》僖公十七年记载齐国有“雍巫”,也就是齐桓公的宠臣易牙,根据当年《左传》的记载:“雍巫有宠于卫共姬,因寺人貂以荐馐于(齐桓)公”,以及《战国策·魏策二》的记载:“齐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之而饱”,则“雍巫”本为掌管饮食料理的庖厨之人。而《周礼·天官·冢宰》有“饔人”之官,谓:“凡王之好赐肉脩,则饔人供之”;“内饔掌王及后世子膳馐之割烹煎和之事,辨体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外饔掌外祭祀之割烹,供其脯脩,刑膴,陈其鼎俎实之牲体鱼腊”,《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也记载:“公膳日双鸡,饔人窃更之以鹜”,则雍巫的职守正与饔人之官相同,“饔”“雍”字通,齐“雍氏”属以官为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