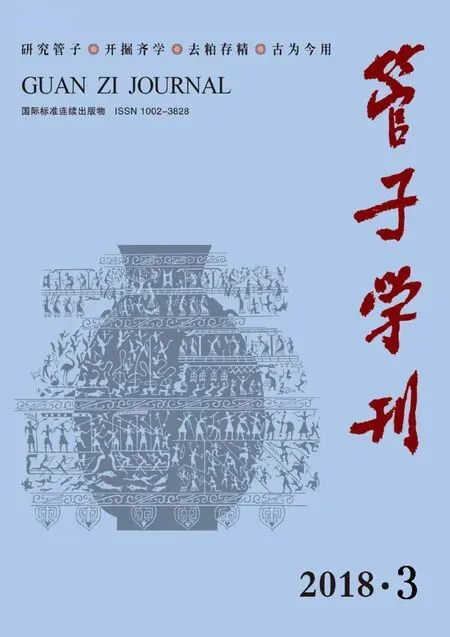刘秀“柔武”思想对《孙子》兵学理论的贡献
姚振文
(滨州学院 孙子研究院,山东 滨州 256603)
刘秀(前6年—57年),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人,出生于陈留郡济阳县(今河南兰考)。他在新莽政权危机、社会动乱之际,顺应历史潮流,起兵反莽,重建汉政权,史称东汉。之后,他剿灭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并开创了“光武中兴”的局面,被后人评价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刘秀是否读过《孙子》或是否熟悉了解《孙子》思想理论,寻诸史籍,未见明确的记载。然而,其军事实践活动及军事思想与《孙子》思想理论之间却有着明显的共通性。刘秀经国治军活动的总体特点是“以柔道理天下”,他将中国的柔武战略思想发展到了一种高层的境界。王夫之在总结光武帝成功的经验时说:“乃微窥其所以制胜荡平之者,岂有他哉!以静制动,以道制权,以谋制力,以缓制猝,以宽制猛而已。帝之言曰:‘吾治天下以柔道行之。’非徒治天下也,其取天下也,亦是而已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6光武)而就整体而言,《孙子》的兵学思想理论也是主要体现了柔性的风格,他虽然不像老子那样过分地推崇“柔弱胜刚强”的意义,但其强调慎战、先胜而反对激进冒险,强调以道制胜、上兵伐谋而厌恶武力拼杀,包括他提出的许多用兵原则,诸如避实击虚、出奇制胜、以迂为直、因情用兵等等,都是体现了以智克力的柔武思想特点。鉴于此,刘秀在战争实践中是如何践行《孙子》思想理论的?其柔武为特色的军事思想又如何发展和完善了《孙子》的兵学理论体系,这一课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宽仁恤民,注重教化,深化发展《孙子》道胜思想
《孙子》将“道”置于战略要素的首位,并在《计篇》中明确阐释“道”的内涵为:“道者,令民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诡也。”《形篇》中又谈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正。”这说明,孙子视“道”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孙子》一书,“舍事而言理”,“道”为什么重要?其根本性的原理何在?孙子并未从政治与军事关系的层面作出深入的阐释。
比较而言,儒家学派在这一问题上有着更明确的指向。亚圣孟子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孟子·公孙丑下》)荀子作为儒家兵学的集大成者亦指出:“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荀子·议兵篇》)在儒家看来,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至于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术谋略等都是次要的。这是否是“迂阔迂腐”之论呢?晚清胡林翼曾说过:“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及也。”[1]653言外之意,儒家学者颇能悟透兵事之精髓。那么,这个精髓或根本的道理是什么?有学者根据冷兵器时代的战争特点予以解释说:“儒家认为道义上的‘仁’是战争之纲,纲举目张,落实到政治层面,要‘施仁政’‘行王道’,以赢得人心,心悦诚服才能四方来归,人多势众,天下皆为我所用。”[2]45-53这番话是颇有道理的,它有力地阐明了中国古人关于战争问题的一个基本观念,即人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
刘秀作为杰出的军事家,正是站在儒家“仁为兵本”观念的立场上,紧紧抓住“民心”这一影响战争胜负的根本问题,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孙子》的道胜思想。
新莽之际,之所以“暴乱”四起,正是因为统治者“暴兵累年,祸弩未解,兵连不息,刑法弥深,赋敛愈重”(《后汉书·冯衍列传》)。所以刘秀自起兵反莽之日起,就十分注重争取民心的问题。最初,他北上经营河北之时,当地豪雄多拥兵割据,农民起义军首领也自立称雄,他兵微将寡,力量最弱,极为被动。然而,他采用了高明的政治手段,争取各方力量的支持。《后汉书·光武帝本纪》有载:“所到郡县,辄见二千石、长吏、三老、宦属,下至佐吏,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迎劳。”《后汉书·耿纯传》也说:“窃见明公单车临河北,非有府藏之蓄,重赏甘饵,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怀之,是故士众乐附。”这不仅使刘秀建立起自己的一支武装,还消灭了割据势力王郎,最终在河北地区站稳了脚跟。
为了更好地收揽民心,他严明军纪,训谕诸将“禁制士卒,不得掳掠百姓”(《后汉书·朱佑传》);“虽发师旁县,人马席荐羁绊,皆有成贾,而贵不侵,民乐与官市”[3]14。建武元年(25年),刘秀派侍御史杜诗巡视洛阳,“时将军萧广放纵兵士,暴横民间,百姓惶忧”(《后汉书·杜诗列传》)。杜诗在多次诫谕无效的情况下,将其处死,并上报朝廷。刘秀为此大加褒赏杜诗,“赐以启戟”,授其惩治不法将领的专权。建武十二年十一月,吴汉打败公孙述,攻入成都,放纵士兵大肆抢掠财物,并焚烧宫室。光武帝闻讯后对其痛加斥责: “城降三日,吏民从服,孩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日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尚宗室子孙,尝更吏职,何忍行此?仰视天,俯视地,观放麂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斩将吊人之义也。”(《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
另一方面,刘秀又结合儒家的思想,教化民众,稳定民心。孙子在《火攻篇》有言:“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就是说,取得了战争胜利而不注意巩固战果,就好比财物白白流失了,这是很不好的事情。为了巩固战果,刘秀在战后多采取以教化为主的安抚政策,如修庙堂、建太学、立五经博士、完善法令制度等等,特别是注重选拔任用“重厚之吏”,以改造民风。同时,为了更好地安抚人心,刘秀又非常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任用与扶植。他说:“今天下散乱,兵革并兴,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梦想贤士,共成功业,岂有二哉!”[4]5故所到之处,“未及下车,先访儒雅”(《后汉书·儒林列传》);他属下的开国功臣,也多文吏,颇具“儒者气象”。正所谓“群雄崩扰,旅旗乱野,东西诛伐,不惶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后汉书·樊宏附族曾孙准列传》)。儒家及儒学的优势在于教化民众,如此以来,便收到了人心稳定,天下晏然的效果。
上述内容集中体现了刘秀将政治问题与战争问题有机结合的高明艺术,他将《孙子》论及的道胜内涵上升到了一种新的高度,也从实践上证明了其在战争领域的特殊价值。战争制胜不是单纯以武力拼胜负,而是要从政治的高度,重民心所向,施宽仁之政,最终以仁德取天下。同时,此种战略思想又可以“柔道”释之。刘秀曾言:“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后汉书·藏宫列传》)这说明,在刘秀看来,“柔道”的实质乃是以“德”“仁”为本,要运用德化的手段,以达成军事胜利之目的。王夫之极为赞同刘秀这种经国治军政策的智慧与高明。他说:“柔道非弱之谓也,反本自治,顺人心以不犯阴阳之忌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6光武)总之,在战略上坚持重民思想的主旨,在策略上实行以柔克刚的方针,这可以视为刘秀取天下的全部经验总结,也可以说是刘秀对孙子道胜思想与战争观理论做出的一种杰出贡献。
二、远交近攻,不战屈人,完美诠释《孙子》全胜思想
《孙子》之全胜思想是战争的最高理想境界。然而,能否真正领会孙子全胜之精神,取得全胜之效果,却并不是每一位战争统帅或将领能够做到的。刘秀以其柔武思想为根基,将孙子的伐谋、伐交思想融入其中,从不同角度探索了实现全胜的途径与方法,这是其对孙子学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贡献。
首先,活用《孙子》伐交思想,实施“远交近攻”策略。这一策略,在平定各地割据势力过程中,运用的最为充分。其基本思路是先取关东,后收陇蜀。当时,隗嚣、公孙述等占据陇蜀之地,虽实力强大,但相距较远,威胁不大。所以,刘秀对隗嚣采取拉拢政策,“赞以文王三分,许以计功割地”,使其成为汉军联盟,遂“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5]215。第一步,先集中力量剿灭关中的刘永。建武二年,刘秀出兵攻打刘永,次年杀之。第二步,先后平定张步、董宪、李宪、秦丰等东南割据势力,同时击败逼降了绿林、赤眉等起义军力量,然后又消灭渔阳的彭宠割据势力。在最后剿灭隗嚣、公孙述之时,也是采取了先陇后蜀战略,先灭隗嚣,再灭公孙述,此种伐谋伐交、各个击破的战略思想,完全符合孙子之易胜、全胜的思想宗旨。
其次,威慑与教化并用,达到“不战屈人之兵”的目的。瓦亭之战是剿灭隗嚣势力过程中的关键战役,敌方守将是牛邯。光武帝得知王遵和牛邯是老朋友,遂命王遵修书牛邯:“今车驾大众,已在道路,吴、耿骁将,云集四境,而孺卿以奔离之卒,拒要厄,当军冲,视其情形何如哉?”(《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这是典型的战略威慑,然又与教化手段结合使用,“今孺卿当成败之际,遇严兵之锋,宜断之心胸,参之有识,毋使古人得专美于前,则功成名立,在此时矣。幸孺卿图之!”(《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此种柔武策略,使牛邯最终倒戈归附。牛邯的归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不仅使汉军顺利攻占瓦亭,而且大大动摇了隗嚣的军心士气。此后,隗嚣手下的大将十三人及兵士十余万,皆降顺归附汉朝。此诚可谓真正的“兵不顿而利可全”(《孙子·谋攻》)。
第三,广泛采用劝服、离间、利诱、威逼等多种策略方法,以求全胜。公元25年,刘秀命冯异屯兵孟津,命寇恂进兵河内,旨在对洛阳形成包围之势。但洛阳兵多势众,城池坚固,攻克异常艰难。于是,刘秀命诸将围而不攻,大施反间计,离间其守将朱鲔与李轶的关系,使朱鲔杀死李轶,继而又派人说服朱鲔投降。最终,刘秀兵不血刃,占领洛阳。在平定西北格局势力过程中,招降纳叛的分化策略也得以充分运用。隗嚣大将高峻拥重兵占据高平,成为汉军攻取陇右的重要障碍。光武帝曾命马援劝降高峻,但其后又反复。光武帝亲征之时,高峻率重兵阻挡汉军,强攻必然造成巨大损失。刘秀再派寇恂前往高平劝降,寇恂机智果断,怒而斩杀“辞礼不屈”的军事皇甫文,并告高峻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后汉书·寇恂列传》)最终,高峻慑于汉军声威,开城投降,高平不战而下。
最后,通过政治手段的使用,实现全胜。如在统一战争之时,刘秀大赦天水、陇西、安定、北地等地为魄嚣所诱迫的官员;大赦乐浪谋反株连的下属;废除边郡“盗谷五十斛罪至于死”的严苛法令;释放陇、蜀、凉、益的奴婢为庶民等等,这些都是刘秀执行“柔远以德”政策的典型事例。在执行这种仁德政策的同时,刘秀又尽力避免因处理各族事务不当而引发的矛盾与战争。建武二十一年,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遣子入侍,自愿请求都护。刘秀以“中国初定、未逞外事”为由加以拒绝,最终不仅遣还侍子,而且对其大加赏赐,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战乱,而希望对各族都能以恩德怀之。更值得肯定的是,刘秀性“谨厚”的性格特点,使他绝不会为了自己的所谓“万世功业”而穷兵黩武。建武二十七年, 藏宫、马武等将领曾建议乘“匈奴饥疲,自相纷争”之机进击匈奴,并预言“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而刘秀的回答是:“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今国无善政,灾害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后汉书·藏官列传》)自此之后,诸将莫敢轻言战事,守边之将也以固守为本。于是,边疆遂宁,民众生活得以安定。
三、以智克力,以谋胜敌,灵活运用《孙子》战术思想
刘秀的“柔道”,突出表现在一个“智”字上,讲求“以智克力”“以谋胜敌”,而其核心内容则在于对战场复杂形势的从容应变及对兵学原则的灵活应用。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孙子说过的那句名言:“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成势,无恒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下面我们先以昆阳之战为例进行分析。
昆阳之战发生于公元23年,是绿林军与王莽军队之间进行的一场战略大决战。此役可谓是中国战争史上典型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刘秀军队合计不过2万人,莽军四十二万人,双方兵力对比20: 1。在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刘秀是如何指挥这场战役取得胜利的呢?其中又体现了哪些《孙子》的基本思想呢?我们从《后汉书·光武帝纪》的相关记载中,可以找到答案。
其一,临危不乱,智勇结合。昆阳之战,充分展示了刘秀作为一名贤能之将的基本素质。孙子讲:“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孙子·作战》)将帅是战场上最活跃的变量,其组织指挥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战争的成败。当时,在昆阳城突遭敌人大军包围、“诸将皆惶恐”的情况下,刘秀作为一名偏将,临危不乱,先是力劝诸将坚守,“复为图画成败”,后又率十三骑突围出城搬回救兵,最终化解危局。从具体过程看,刘秀能够彻底扭转战局,不仅在其“智”,更在其“勇”,他先是敢于“夜自与骠骑大将军宗佻、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出城南门,于外收兵”,后又能“自将步骑千余,前去大军四五里而陈”,最终带动起全体将士投入作战,“诸部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 且复居前, 请助将军! ’”今人评价孙子之将帅五德理论(智、信、仁、勇、严),常常盛赞“智”而忽略“勇”,其实“智”与“勇”譬如“将”之双翼,缺一不可,偏其一端,实为对《孙子》的缪读。
其二,并力御敌,励军士气。昆阳被围之初,诸将“忧念妻孥, 欲散归诸城”,光武议曰:“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后来,在“既至邸、定陵, 悉发诸营兵”之时,诸将又“贪惜财货, 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敌, 珍宝万倍, 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余, 何财物之有!”乃悉发之。这其中,刘秀两次运用孙子“我专敌分”的理论,打消了诸将的分兵之念;同时又借用孙子“深入则专”的理论,激发了其他将士的士气,充分体现了刘秀作为杰出军事家的大智慧。孙子思想高深莫测,玄机重重,而大智之人用兵颇能与之暗合,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孙子兵学的实践价值。
其三,“阳堕其书”,巧妙“示形”。孙子有“兵者诡道”理论,而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手段又在于“示形”,“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孙子·计》);“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孙子·虚实》)。昆阳之战中,刘秀对“示形”思想的应用是主动而又巧妙的,“时伯升拔宛已三日, 而光武尚未知,乃伪使持书报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阳堕其书。寻、邑得之不熹。诸将既经累捷,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这其中,“寻、邑得之不熹”,说明此计起到了打击敌方统帅作战决心的作用,而我方诸将“胆气益壮”说明大大激励了我军士气,而如此一箭双雕的效果,又诚可谓孙子“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孙子·虚实》)的理想境界了。
其四,“夺其所爱”,攻敌“中坚”。从战场发展的形势看,刘秀军队虽然取得小胜,但欲以2万人彻底击败敌人之四十万大军,并非易事。所以,刘秀最后采取的是出奇制胜、避实击虚的战法。“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以少数兵力突然进攻敌方统帅居中指挥的指挥部,这无疑是大胆的出奇制胜之举,同时它又符合了孙子避实击虚理论的思想要旨。避实击虚的关键在于“夺其所爱”,即攻击敌方部署中既要害而又虚弱的地方。指挥部自然是敌之要害,而“寻、邑易(轻视)之,自将万馀人行陈,敕诸营皆按部毋得动,独迎与汉兵战”,就使得其指挥部又成为虚弱之处。如此以来,刘秀之攻敌“中坚”,就完全符合了孙子“避实击虚”“夺其所爱”的理论原则,从而成为义军取得昆阳之战胜利的最关键环节。最终的结果是:“寻、邑阵乱,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追杀之意)百余里间。”
昆阳之战,刘秀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其指挥风格可谓是勇有谋,刚柔并济。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在严重的危机关头,他坚定信念,身先士卒,以其过人的胆略和魄力,组织力量进行反扑,赢得了战争胜利。如果说,昆阳之战是在特定形势下更多地体现了刘秀指挥风格刚性的一面,那么,此后的几次大战指挥则主要体现了其柔性、柔武的特点。
比如,刘秀平定赤眉军之战即是以逸待劳、以柔克刚的典型战例。建武二年九月,当赤眉军打败邓禹,复入长安之后,刘秀就将邓禹召回,而派冯异率兵讨之,并告诫说:“慎毋与穷寇争锋,赤眉无谷,自当东来,吾以饱待饥,以逸待劳,折棰笞之,非诸将忧也,卿其速归,无得复妄进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1)此后,赤眉军果然受当地饥荒所迫,引兵东归,刘秀遂遣大将侯进屯兵新安,派耿算屯兵宜阳,截断赤眉军退路。建武三年,当赤眉军向东退往宜阳之时,刘秀亲率大军截击,最终将其全部歼灭。刘秀对这一战役的指挥灵活运用了孙子“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用兵思想,更充分体现了其以柔克刚的作战指挥风格。王船山对此评价说:“帝以持重而挫其方决之势,禹以持重而失之方溃之初。相对之变,定几于倾刻,非智之所能知,勇之所能胜。”(王夫之:《读通鉴论》卷6光武)
再如,刘秀剿灭公孙述的战役也是执行了“以智克力、以逸待劳”的作战思想。建武十二年,刘秀派吴汉率兵讨伐公孙述。大军临行之前,特意叮嘱其说:“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3)然吴汉大意轻敌,在攻占广都以后,即出兵二万人进至成都附近屯兵扎营,另分兵一部于刘尚屯于江南。光武闻知后,立即斥责吴汉进兵之误:“比敕公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以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3)后来战事发展果如刘秀所料,吴汉与刘尚军很快被吴汉大军层层包围,幸而乘夜偷袭突围,合兵一处,方得以引兵还广都。此后,吴汉坚决执行刘秀“以逸待劳”的方针,谨慎用兵,稳中求进,历经八次战役,终于大败公孙述。这正符合了孙子“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用兵思想。从理论层面讲,刘秀之柔武用兵策略与孙子之“先胜”理论,在本质上是会通的。
四、“文吏典军”“泛爱容众”,补充完善《孙子》治军思想
刘秀不仅善于用兵,也善于治军,而且其性“谨厚”“以柔道理天下”的风格,在他的治军思想和实践中得到鲜明的反映。史称其“官属将兵法度不与它将同”(《后汉书·任李万邳刘耿列传》);“上下相亲,天下之势乃固”(王夫之《读通鉴论》卷6 光武),以至于出现了“今称天子者数人,唯洛阳甲兵最强、号令最明”[4]52的局面。概括起来,刘秀治军有以下几个特点:
1.文吏典军,“倚为干城”。刘秀建军之始,主要与河北的王朗对峙。为了战胜王郎,刘秀将信都、和成二郡之兵力交由邓禹指挥,“发奔命,得数千人,令自将之”[6]130,同时,又任命随其北渡的文吏王霸、冯异、藏宫等人为偏将,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主干部队。此后,刘秀部下许多重要将领也多出自文吏,“征之史册,刘秀的开国功臣二十八将中,确切不疑地判明为文吏出身者有二十三人,被倚为干城”[7]97-102。
文吏典军,形成汉军与众不同的特色,相较于专横跋扈的武将治军而言,在诸多方面出表现出特定的优势。首先,典军文吏政治素养高,较少出现贪恋财物、虐待士兵、残暴害民的行为,如祭遵能“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后汉书·祭遵列传》);朱佑“以克定城邑为本,不存首级之功”(《后汉书·朱佑列传》)。其次,典军文吏通晓法制纲纪,能够自觉执行君命军纪,较少有武将的骄横专断行为。如刘秀总揽军权,指授方略,“诸将亦以绳墨应之”(叶适:《习学记言》卷二四),每遇大事,则“遣吏奏状”“委决于中”。再者,典军文吏多出自基层,干练多能,绝无宿儒之迁阔空谈之陋习,在军情危机面前,能够临阵不乱,果敢决策。最后,典军文吏有大局观念,较少有门户之见,关键时刻能精诚团结,相互支援,共赴危难。
刘秀“文吏典军”是中国建军史上的一个创举,其与《孙子》治军思想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对后世治军思想的发展却影响深远。自宋代开始,重文轻武,文臣统兵成为重要国策,明、清两朝沿袭此制,不断出现文职兼任武将的实例,这就催生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兵家群体。如宋代的范仲淹、明代的王阳明、清代的曾国藩等著名将帅,都是文臣统兵的典范,他们以儒家忠义观念作为治军的核心思想,既有利于提升将帅的政治品格和道德素养,也有利于凝聚军心士气,提高士兵战斗力,这是中国古代治军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对《孙子》治军思想的一个有益补充。
2.以诚待将,以信治军。将帅是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宝贵财富。孙子有言:“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孙子·谋攻》)所以,君主如何处理好与将帅的关系,是经国治军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时期专职武将出现以后,君将关系的处理就变得异常复杂。一方面,由于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在古代通信不发达的条件下,将帅需要战场临机决断权。如孙子就强调,“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而且他还特别总结了君主对军队乱加干预的三种情况及严重后果:“故君之所以患於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孙子·谋攻》)然而,从另一方面讲,有些将帅被授予军事大权之后,拥兵自重,专横跋扈,甚至谋反自立,也使得君权受到严重威胁。所以,自古君将关系是一种两难困境,处理起来既充满着权术欺诈,又伴随着暴力血腥,而刘秀以柔道处之,以一个“诚”字赢取人心,对后世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例如,刘秀麾下大将冯异,战功卓著且“能御吏士”,在镇守关中之时更是“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当地百姓以“咸阳王”称之。这引起朝野之臣的怀疑和警觉,担心其拥兵自重,图谋不轨。冯异闻知此情后,非常害怕,立即上书请求调离关中,以证清白。然而刘秀对其的答复是:“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后汉书·冯异列传》)如此坦诚之语,让冯异疑虑顿消、感激涕零。君臣之间能够如此肝胆相照,推心置腹,这在封建社会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实属罕见。
刘秀不仅以诚信待将,亦以诚信治军。更始二年,刘秀在击败、招降铜马农民起义军之后,封其首领渠帅为列侯,然降者兵众“犹不自安”,刘秀为赢得他们的信任,竟然出人意料地“敕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按行部陈”(《后汉书·光武帝纪》)。此举令降者大为感动:“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此外,刘秀在攻破王郎后,将缴获的部下与王郎私通勾结的书信,看也不看便当众销毁,同样体现了以诚信待人的治军作风。孙子将帅五德中,曾将“信”置于第二位,可见其对“信”的重视。这个“信”很大程度上讲的就是诚信,它突出的是可贵的公平公正理念,在本质上是一种上与下之间的高层次的精神互动,能够起到“士为知己者死”的感化效果。
3.公正严明,重赏轻罚。严明赏罚是中国古代治军思想的重要内容。管理一支军队,能否做到有功必赏、有错必罚,是保证军队令行禁止进而完成作战任务的关键所在。正如孙子在《行军》所言:“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刘秀治军,特别重视这一点,对于作战立功的将士,不论亲疏贵贱,他一律“厚与之赏”;而对于违令将士,即使是自己的亲信爱将,也严加惩处,绝无例外。如寇恂作为刘秀的心腹爱将,在河内任职时,违备命令,系拷上书者,即被刘秀撤职免官。然而,刘秀治军虽然严明,但却不以刑杀为主,而是代之以训导教育的方式。比如,即位后大封功臣之时,他就下诏告诫群臣:“人情得足,苦干放纵,快须臾之欲,忘慎罚之义。惟诸将业远功大,诚欲传于无穷,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日慎一日。”(《后汉书·光武帝纪》)
刘秀治军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重赏轻罚。东汉建立之初,他对功臣的赏赐可以说是非常丰厚的,“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余各有差”(《后汉书·光武帝纪》)。这就突破了“功臣食邑不过百里的古法”,并由此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今封诸侯四县,不合法制。”然刘秀却说:“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后汉书·光武帝纪》)在惩罚问题上,刘秀则坚持尽量从轻的原则,几乎很少诛杀将士,更无随意诛戮的情况。刘秀重赏轻罚的目的在于恩结将士,加强内部的凝聚力,这是其以柔道经国治军思想的体现。
4.“泛爱容众”“广施恩德”。情感管理是中国古代治军的一个优良传统。战争是死生之地,将帅的功绩和事业要靠下属的英勇作战来完成,那么下属凭什么要为你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生命?这除了靠严明的纪律及必要的奖赏以外,更需要以情感赢得下属的忠诚、信任和支持。故孙子在《计》中将“仁”列为将帅的基本素养之一。在《地形》中,孙子更强调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刘秀是一个宽厚、仁慈、重感情的人,这使他更容易明白“以情治军”的道理,而其实际的表现总体上可以用“泛爱容众”“广施恩德”来概括。
将领贾复受重伤,刘秀诚恳地表示:“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后汉书·贾复列传》);李忠母亲及妻子为敌所捕,刘秀指示下属不惜钱财营救,“踢钱千万,来从我取”(《后汉书·李忠列传》);征虏将军祭遵去世,刘秀“车驾素服临之,望哭哀恸”(《后汉书·祭遵列传》);中郎将来歙征蜀时被刺身亡,刘秀“乘舆缟素,临吊送葬”(《后汉书·来歙列传》)。此外,刘秀也懂得关爱普通的士卒。手下将领王霸是善抚士卒的典范,以至于“死者脱衣以敛之,伤者躬亲以养之”(《后汉书·王霸列传》),刘秀因此对其大加褒奖,擢升为偏将军。从上述内容看,刘秀关爱将士的行为和表现,绝非个案,也非一时的虚伪或冲动之举,历史上帝王优抚将士的实例不少,但像刘秀这样能做到真诚自觉、一以贯之的,却非常罕见。
刘秀对于将帅的仁德,还表现为宽容爱护的一面。即能够用人之长,避其所短,即使有性格缺陷也不求全责备。如邓禹足智多谋,骁勇善战,但却在进兵关中时犯下轻敌数败的错误,刘秀并没有因此而降罪处置,而是将其召回专主谋议。再如,贾复是员猛将,有万夫不当之勇,但刘秀考虑到他这种性格容易轻敌致败,就让他负责京师的守卫工作,而不让其率军出征,独当一面。同时,对于犯下错误的将士,刘秀也能宽容处之,在其改过立功后重新提拔任用。如王梁曾因擅自调军而犯下重罪,几乎被处死,但后来能在击王校、破庞萌的战争中立下大功,刘秀便又重新择其为将。另外,对于一些性格直爽、屡屡犯上的将士,刘秀也能容忍不责,理性处之。
刘秀的“广施恩德”,更表现在对战后功臣的处理问题上。自古君主与功臣能够“同患难”,却难以“共富贵”,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刘秀是中国历史上没有杀过一个功臣的开国皇帝,他吸取了西汉初年对功臣能将不教而诛的深刻教训,代之以“经济上予以优厚待遇而政治上加以防范、限制”的策略,使得大多数功臣最终能“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后汉书·马武列传》)。这可以说是第一次以和平方式成功地解决了战后君臣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从而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优待开国功臣的范例。
总体而言,刘秀的治军思想与实践有很大的独特性,它以“柔道”为基础,以“文、诚、赏、仁”为核心,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非有府臧之蓄,重赏甘饵,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怀之,是故士卒乐附。”(《后汉书·任李万邳刘耿列传》)值得强调的是,此种治军风格与中国古代以法从严治军的主流思想是不同的。比如,中国历史上“司马穰苴斩庄贾”“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周亚夫治军细柳营”都是从严治军的范例,孙子虽然主张刚柔并济、“令文齐武”,但总体上也是以“严”为主,其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为贯彻自己的治军理念而“演兵斩美姬”。治军之道,关键就在“文”“武”二字,何者为先,何者为重,乃是不同的将帅性格和治军风格使然,如何融通此理,实在是一门高深的艺术。从这一角度讲,刘秀的治军思想及成就是对《孙子》治军理论的一种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