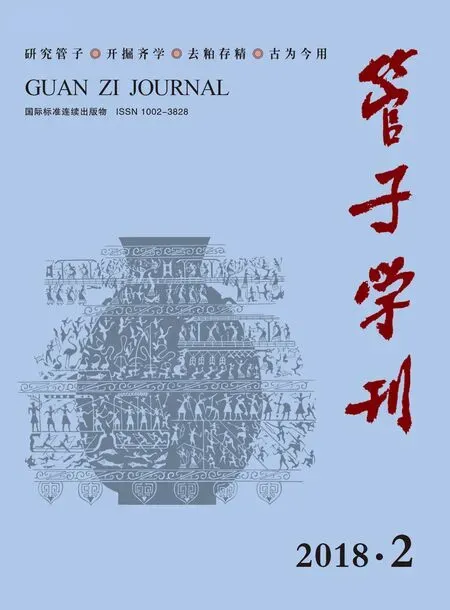鲁国出土异地商周金文通释绎论
孙敬明
(潍坊市博物馆,山东 潍坊 261021)
从史前至商代海岱区域的地方土著传承延续发展的历史文化似是未曾发生大的变化,尽管有所谓的五帝时代的征战与冲突。可是历史的步履迈进到商周之际,则横跨较大区域间的部族矛盾之冲突,原有部族的被征服与迁徙,新来部族的入驻与开拓,凡此诸种变化急剧。正如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所谓:“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并谓:“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故夏殷间政治与文化之变革,不如殷周间之剧烈矣。”试想海岱间原有数千年的部族之文化格局,适逢殷周间之鼎革,故部族文化历史潮流皆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变。当周王的雄师扫灭殷纣的倒戈徒卒之后,即在新占领的东方区域实施肇封诸侯之政治武略布局。鲁是西周初年所新封之诸侯,而海岱区域间由于鲁与齐的新封,由此开始则彻底冲击裂变东方的历史文化之原有格局。所以对鲁国就封之初,其地原有方国部族的历史或应有所顾及。文献所谓鲁国就封于少昊之虚,而少昊时代距鲁国就封岁月遥远。而典籍所谓成王践奄肇封鲁国,或应近乎历史之真面。所以此篇就从商周之际的奄国青铜器谈起,但是,若就当地土著古国族之传承发展,而鲁国则属于其后之外来者,当地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则是旧有的主人所作,又非同如两周时期外地国族所铸而在鲁国封地书出土者,为示别异,故将这些商代青铜器酌作选择,且以国族为单位编号。
(一)奄国
奄尊、鼎、簋、觚、爵(4件)(《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集》2732、2736、2737、2738、2739—2742)
凡尊鼎簋觚爵等八件带有奄国铭文的青铜器,时代始于商代晚期,其中尊为1975年山东省泗水县张庄公社(今泗张镇)窖堌堆村出土。这个铭文作一把刀刃与仰豕腹部平行的样子,属于会意字[1-2],或释之为“解”;殷商甲骨文中有作刀在豕后背的字,或释之为“牝”,闻一多先生释之为“剢”,以为是阉割。金文中的与甲骨文所不同的是,金文的刀正切向豕腹部,而甲骨文的刀则在豕之背后。窃以为金文中的应该就是“阉割”的“阉”字,也就是“奄”。奄地都说在曲阜,但是曲阜一带考古所见商代的青铜器较少,而周近的泗水、平邑、邹城、苍山等地出土商代带铭文青铜器较多。并且传世的与之铭文相同的数量也不少。或许商代奄地就在泗水泗张镇一带。与奄尊一同出土的还有铭文为“母乙”或“母癸”的两件铜爵、一件铭文为“史母癸”铜觚。
(二)薛国史母觚
此件铭文为“史母癸”的铜器与带“奄”字的铜器同时地出土,内在关系密切。上揭之“母乙”“母癸”,或同属于“史”所作器。山东集中出土带铭文“史”字的青铜器,地点在今滕州前掌大。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1998年以前发掘的一百多座墓葬中即出土带有“史”字铭文的60余件[3]581。冯时认为:“‘史’为承官之氏,‘薛’本地名。”[3]590滕州博物馆发掘的前掌大墓葬也出土数件带有“史”字铭文的青铜器,当地公安机关也查获当地出土的带“史”字铭文的青铜器[4]227-375。旧所传世的青铜器中,以及商代甲骨文中均发现带“史”字铭文或刻辞。经由科学考古发掘,积累十数年的资料,可以确定“史”是薛国商代世代传承的官名,同时又演变为其氏名。前掌大墓地同时还出土带有曾、宋、举、冉、戈等国族名的青铜器,证明薛国与这些古国族存在交往关系。而鲁国就封奄地,其与薛国地理密迩,由商代铜器铭文证明,在商周之际鲁国或奄国与薛国有密切交往关系[5]311-317。
(三—九)大保簋
梁山七器之一,陈梦家先生指出:“梁山七器的出土,或以为在道光年间(1821—1850年,《颂·续考释》9),或以为在咸丰年间(1851—1861年,《缀遗》4·2)。梁山在今山东梁山县,在寿张县东南、郓城县东北、东平县西南。此一地区内,在殷周之际颇多小国。《涵清阁金石记》说:‘济宁钟养田(衍培)近在寿张得古器七种:鼎三,彝一,盉一,尊一、甗一;此(指《鼎》)其一也。鲁公鼎、牺尊二器已归曲阜孔庙’。《缀遗》4·2说:‘咸丰间山左寿张所出古器凡三鼎、一簋、一甗、一盉,其铭皆有大保即召伯等文,许印林(瀚)明经定为燕召公之器,而以出山左为疑’。两种记录,大致相同,而后者少录了牺尊一,即大保鸮卣。梁山七器应是:
1.大保方鼎,本书①敬明按:此乃为《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重作整理出版者,下同。68,钟、李、丁彦臣、端方;
2.太史友甗,本书 72,钟、李、住友;
3.伯盉,本书 71,钟、李、钱有山、溥伦、端方、容庚;
4.鼎,本书 70,钟、李、陶祖光、清华大学;
5.大保簋,本书 23,钟、李、溥伦;
6.大保鸮卣,《遗宝》附24、《遗宝》36;
7.鲁公鼎。
最后一鼎,可能是周公作文王鼎,清世学者多误读‘周’字为‘鲁’。”[6]45
梁山七器铭文为:
(1)大保簋铭文曰:“王伐录子取,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哌大保,赐休余土,用兹彝对令。”
(2)太史友甗铭文曰:“太史友作召公宝尊彝。”
(3)伯盉铭文曰:“伯作召伯父辛宝尊彝。”
(4)鼎铭文曰:“唯九月既生霸辛酉,在匽。匽侯赐贝、金。扬侯休,用作召伯父辛宝尊彝。万年子子孙孙宝。光用大保。”
(5)大保方鼎铭文曰:“大保铸。”
(6)大保鸮卣铭文曰:“大保铸。”
(7)周公作文王方鼎铭文曰:“周公作文王尊彝。”
以上所揭列所谓梁山七器,由于出土时间在清代,具体情境各家著录或有出入,但基本情况可以确定。从铭文所见大都与召公燕国相关,并且铭文中的官职“大保”,陈梦家先生认为就是召公,应该可信。西周初年,王室辅弼主要有周公、召公,而太公在伐灭殷商之后即就封营丘,虽然远在东方,同样是与周室诸公在各自位置辅佐王室。梁山七器的出土,不仅可以看出西周初年王室对东方的极为重视,周公帅兵三年靖东国,而召公燕侯同样付出巨大贡献;而且有梁山七器的铭文内容与器物组合,可以推定铜器出土的地点属于鲁国境内。数量如此之多、内容如此之重要的青铜器群组在鲁国境内出土,不仅可以证明当时鲁国在周王室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而且还可看出西周初年周公、召公以及相关的鲁国、燕国在捍卫周王室而绥靖东方局势中的关键作用。从此七件铜器,其中有鼎三、簋、甗、盉、卣各一件的组合;以及周公作文王鼎一件、大保即所谓召公作鼎、簋、卣共三件、伯作盉、鼎共二件、太史友作甗一件。可见数量以召公为最多,伯居其次,周公与太史友各一件。根据器物铭文还可推断,作器的伯由于铭文暂时隶定作“”,其与原篆尚有出入,或可认为这位伯寈就是周公之子鲁国国君伯禽。由于器物出土的年代久远,属于墓葬抑或窖藏已经不可知悉。从器物的时代与周初的形势,以及种类组合与相关人物和出土的大致地区,似可推断这组铜器就有可能是出自窖藏,这与辽宁大凌河流域喀左等发现的西周初年的窖藏颇多相似②参见孙敬明:《考古发现与史寻踪》,《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一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后收入《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考古发现与史寻踪》,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418—429页。,应该是用于祭祀而瘗埋的。
鲁国境域出土周王室成员所作青铜器,而与之相应在周原也发现鲁国贵族所铸铜器。如1981年陕西岐山县京当乡出土鲁国人名鲁者所作铜彝,但是器身已经缺遗,仅存彝盖,铭文曰:“唯八年十又二月初吉丁亥,齐生鲁肇贾休多赢,唯朕文考乙公永启余,鲁用作朕文考乙公宝尊彝,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7]9896从铭文内容、辞例与书体推断,这件铜彝的铸造时代应属西周中期。这位作器者名“鲁”,并且还是齐国的外甥。林沄先生指出:“金文人名中‘某生’之‘生’均当读如典籍所见人名中‘某甥’之‘甥’。”[8]120-135张亚初先生亦指出:“某生之某,是国族氏名。翏生之翏、周生之周、陈生之陈、蔡生之蔡、虢生之虢、鲁生之鲁、生 之、微生之微,都是比较明显的例子。”[9]由此铜彝铭文足证鲁国与周王室的交往关系,可以认为从西周初期到中期鲁国与周室的关系一直密切,而不像齐国在西周中期,哀公被周懿王所烹杀。
还有山西绛县横水坡M2158倗国君墓葬中出土的西周早期鲁侯鼎,铭文曰:“鲁侯作宝尊彝。”据谢尧亭先生称:“M2158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记录,墓主倗伯与‘王姊’联姻,芮国国君制作了青铜器作为媵器,鲁国也赠送了青铜器,另外M2158还随葬‘大保’铜鬲等等。我们知道按照周礼,诸侯一娶九女,同姓诸侯国需要陪嫁,芮国、鲁国和燕国都是姬姓国家,我们推测媿姓倗伯与姬姓王姊联姻,与周室同姓的鲁、芮、燕三国为‘王姊’陪嫁,这件鲁侯鼎或者就是鲁国国君的陪嫁媵器,它更是这种婚姻制度的见证物。”①谢尧亭:《新出土的鲁侯鼎及相关问题》,《青铜器与山东古国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2015年12月。
由此绛县倗国君墓葬出土的鲁侯鼎与燕国太保鬲,足证西周早期鲁国与周王室以及燕国的密切关系,而且也可与山东梁山七器互为通证。
到春秋时期鲁国与燕国仍有密切交往,据《文物》1985年第6期载,王敏之先生《河北唐县出土西周归父敦》文称,河北省沧州地区征集到西周铜敦一件,据其了解,是唐县东崮龙村社员在村东北挖土时发现的。依据铜敦的形制、铭文内容与辞例和书体,可以推断这件铜敦的时代为春秋时期。铜敦铭文曰:“鲁子仲之子归父,为其膳敦。”《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2):“公子慭遂如晋。”“南蒯谓子仲”,杜注:“子仲,公子慭。”昭公二十七年:“子仲之子曰重,为齐侯夫人”,杜注:“子仲,鲁公子慭也。十二年谋逐季氏,不能,而奔齐。”唐县出土的鲁子仲之子所作铜敦,凡此“鲁子仲”若与《左传》所记为同一人,则其时代当春秋晚期。唐县位于战国燕下都所在今易县之邻,而北距北京琉璃河也不远②孙敬明:《鲁归父敦小识》,《先秦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2期;后收入《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商周金文七解》,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 115-124页。。
(十—十一)陈侯壶
1963年山东肥城小王庄出土铜器一批,计有:鼎、鬲、壶、簠、勺各二,盘、匜、穿带壶各一,共十三件。陈侯壶两件同铭,铭文曰:“陈侯作妫苏媵壶,其万年永宝用。”从铭文篇章与书体及铜壶形制可断其年代为西周晚期。陈国在今河南淮阳。由此可知陈国与鲁国通婚,《春秋左传》中记载鲁与陈国交往的内容较多[10]。
(十二—十三)楚国睽士父鬲
睽士父鬲两件同铭,与陈侯壶同时地出土,铭文曰:“睽士父作蓼妃尊鬲,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睽士父鬲时代同为西周晚期。关于“睽”字,清华简《楚居》主要讲楚王、楚公居处迁徙,其中一地名之书体结构与这两件鬲铭文相同,李学勤先生认为即《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 633)的“睽”[11]188。《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杜预注:“睽,楚邑。”杨伯峻注:“子文,前令尹。治兵,又详庄八年《传》注。睽,楚邑,不详今所在。”睽士父或为楚国公族;蓼为先秦古国,在今河南唐河县境。由《左传》所记楚国令尹治兵于睽,推考此睽地与蓼国相距不远,当同处江淮流域。两件鬲的铭文,即可解释为睽士父为其夫人蓼妃所作;亦可解释为睽士父为蓼国出嫁女儿所作的媵器,当时一国嫁女,数国为之作媵器是社会习俗。如作此解,则蓼妃最有可能是嫁与鲁国贵族为夫人的。或者是为陈侯所嫁女“妫苏”陪媵,一同嫁归鲁国的。铭文“蓼妃”之“妃”所从“女”位于右侧,金文中所从“女”往往左右无别,如新见首都师范大学近年新征集西周晩期妟生之孙鼎,器盖对铭,而名文中“妃”所从“女,”即分位左或右[12][5]298-300。再者,金文中所从之“女”,左右无别,如“姬”“姞”“妘”“妇”等,而相同之字,如番匊生壶、稣甫人盘、匜与虢文公鼎等铭文所从之女均位于“己”之右侧。
(十四)姊仲簠
1977年曲阜鲁国墓地M48出土,铭文曰:“姊仲作甫(郙)媵簠,子子孙孙永宝用。”此墓同时还出土鲁司徒中齐鼎、甗、盘、匜、盨以及侯母壶等多件带铭文青铜器。《诗·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甫国在今南阳市境。
(十五)莒侯母壶
1977年山东曲阜鲁国墓地出土,器盖对铭,与习见铜器铭文不同的是,器身铭文铸在口沿的外侧。铭文曰:“侯母作侯父戎壶,用征行,用求福无疆。”[1]2578此墓同时还出土鲁司徒中齐鼎、甗、盘、匜、盨以及姊仲簠等多件带铭文青铜器。“侯母”“侯父”之称谓罕觏,而此壶的国别颇费斟酌[13]145-151。
侯母壶通高38厘米、腹径28厘米,凡此器形尤为少见。1976年日照崮河崖西周1号墓葬,出土鼎、壶、鬲、盆、盘、匜等共12件。其中4件鬲铭文相同,曰:“釐伯媵女子作宝鬲,子子孙孙永宝用。”两件铜壶形制花纹完全相同,通高42厘米、腹径30厘米。当时报道者指出:“出土的壶(M1:1、2)与《曲阜鲁国故城》一书中的M48:16器形大致相同。”[14]比较曲阜鲁国故城出土侯母壶与日照崮河崖两件铜壶,形制花纹几乎完全相同,而且通高相差4厘米,腹径相差2厘米,三件铜壶如出一手。稍微有别的是,侯母壶盖顶捉手为立体雕蟠龙,崮河崖者为盘形。
侯母壶的蟠龙形,在曲阜鲁国铜器中极少见,而与之形制相同或相近者,多见于莒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如沂水刘家店子莒国1号大墓出土6件铜壶,均带铭文“公铸壶”,盖捉手均为蟠龙形;2号大墓出土的两件铜醽,盖捉手亦作蟠龙形[15]。还有1974年莒县老营村出土的西周铜罍,通高33厘米,形制与侯母壶相近[16]55。该书谓铜罍的年代为春秋,从花纹形制看应属西周晚期,与侯母壶世代相近。侯母壶铭文“求福无疆”在同时期的金文中少见。而1980年莒县韩家村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铜铍铭文曰:“承禄休德,永岁寿福。”[1]3853并且“福”字形体与侯母父相近。所以结合器形、花纹以及铭文辞例与形体,我们初步推断,侯母壶应该是莒国所铸造。
(十六)乘父士杉簋
1956年山东泰安徂徕乡(今属泰安市徂徕镇)黄花嶺出土。铭文曰:“乘父士杉,其肇作其皇考伯明父宝簋,其万年眉寿永宝用享。”[1]1911此器形制为盨,但是自名为簋,应名从主人。时代为西周晚期。齐国地名千乘,地在今山东广饶一带。此器主名乘父士杉,或属于齐国所铸造器物。
(十七—二十七)杞伯诸器
据《山东金文集存》中册第七页称:“杞器计鼎二、簋五、壶一、匜一、盆一,均道光光绪间出土于新泰县。”
(1)杞伯母匕鼎 1件(器、盖对铭):(盖铭文)“杞伯母匕作曹宝鼎,子子孙孙永宝。”(器底铭文):“杞伯母匕作鼄曹宝鼎,子子孙孙永宝。”(《三代》3.34.1-2)此为带盖鼎,盖铭文邾国名作“”;器内壁铭文则做“鼄”。杞伯母匕所为鼄曹作器凡二十余件,时代均乃西周晚期。可见当时杞国人作器,同时可将邾写作“”或“鼄”。
(2)杞伯母匕鼎1件:“杞伯母匕作鼄曹宝鼎,子子孙孙永宝用。”(《三代》3.33)道光、光绪间出土新泰。
(3—7)杞伯母匕簋5件:“杞伯母匕作邾曹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三代》7、41.2、7.41.3、7.42.2、7.43.1、7.43.2)
(8)杞伯母匕壶1件:“杞伯母匕作鼄曹宝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三代》12.19.1-2)
(9)杞伯母匕壶1件:“杞伯母匕作鼄曹宝壶,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三代》12.19.3)铭文简率,宝从“宀”“缶”。
(10)杞伯母匕盆1件:“杞伯母匕作鼄曹宝盆,其子子孙孙永宝用。”铜盆带盖,形体样式较晚,似是与相同铭文之鼎、簋诸器,作于不同时期(《三代》18.18.2)。
(11)杞伯母匕匜1件:“杞伯母匕铸鼄曹宝匜,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三代》17.30.1)
以上诸器,道光、光绪间新泰出土。
以下杞伯母匕卣、鼎、簋盖、簋等四件铭文铜器,或不在鲁国境内出土,但对研究杞、鲁、滕、邳等国之间文化交流多所裨益,故附录如此。
(12)杞伯母匕卣1件:“杞伯母匕作鼄曹宝卣,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杨树达谓此卣见载《愙斋集古录》第十四册十二叶下,谓:“杞伯每匕之器至多,今存者有簋、有鼎、有匜、有壶、有卣……每匕之名不见于经传,余疑其即杞孝公也。《春秋》襄公二十三年书杞伯每匕卒,即孝公也。”[17]173敬明案:杞伯母匕所作器:鼎、簋、壶、卣、盆、盘(例应有之)、匜等十四件,皆为邾曹所作。然由器物形制花纹与铭文比较推考,尽管同属于西周晚期,但是并非一次所铸造,似是作于不同的时间段。饶为有趣的是:杞伯母匕为邾曹铸造铜器十四件,这位邾曹应该是嫁归杞国为夫人。
(13)杞伯母匕鼎1件:“杞伯母匕作鼄曹宝鼎,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享。”①1966年山东省滕县木石公社南台大队东台村西南薛河故道旁出土。
(14)山东滕州后荆沟1980年出土不(邳)其簋[18]302;簋盖为后配,簋盖铭文记载杞伯母匕为邾曹作器。此为笔者2004年冬出席小邾国文化学术研讨会间,承林沄师面告。这件簋盖,极有可能为以上簋之盖,而后与不(邳)其簋相配。
凡此十五件杞伯母匕所作邾曹宝器,铭文篇章,大致相同;唯独滕县出土的鼎,铭文篇章书体风格迥异。应是出自不同的书家手笔。
(15)杞伯母匕簋1件(器、盖对铭):“杞伯母匕铸鼄曹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享。”[19]应为西周晚期。此簋1962年由湖北省武汉市文物店收购。凡此对楚国灭邾而迁徙之于今黄冈有意义。
(二十八—三十一)邾叔豸父簠
1976年山东平邑县东阳公社(今东阳镇)蔡庄春秋墓出土,铭文曰:“邾叔豸父作杞孟姒饆簠,其万年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时代为春秋早期,与以上所列杞伯母匕诸器时代大致相当[1]3087。同铭文簠四件,铭文锈泐难拓。邾国与鲁国地域密迩,历史上长期互为姻娅,鲁国境内出土邾国器;邾国境内亦出土鲁国器。
(三十二)铸大司□盘
1976年临沂平邑县东阳公社(今东阳乡)蔡庄村出土。铭文曰:“铸大□□用。”[1]1928文献记载铸妊姓,关于春秋时期铸国之地望,有关诸家参照《左传》等文献所载,均认为在今山东肥城县南大汶河北岸之铸乡。
(三十三)邿季鼎
济宁出土,铭文曰:“邿季肇作孟妊宝鼎,其万年眉寿子孙永宝用。”[18]170邿国都在山东长青,或后又南迁济宁。从铭文篇章与语词推断,这件鼎之时代应为西周晚期。应是邿国与鲁国通婚的证物。
(三十四)邿造遣鼎
清光绪间出土于山东东平县。铭文曰:“邿造遣作宝鼎子子孙孙用享。”时代为春秋早期[18]195。
(三十五)邿遣簋
清代斌良得之于曲阜,铭文曰:“邿遣作宝簋,用追孝于其父母,用锡永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时代为春器晚期[18]439。济宁境内出土邿国鼎、簋,证明鲁国与邿国有所交往。
(三十六)史显簠
1940年山东肥城乔家庄出土,器盖对铭,铭文曰:“史显作旅簠,其永宝用。”时代为西周晚期[18]377。本节编号(九)为商代晚期薛国史母癸觚,由此簠可证直至西周晚期鲁国与薛国存在密切交往关系。
(三十七)宋戴公戈
清代出土,《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谓:“自曲阜土中掘出者。”铭文为凿款九字,曰:“朝王赏戴公之造戈。”旧或以为戈年代为西周。从铭文格式以及书体,其当为春秋早期,这与宋国戴公所在位时间相合。宋国都在今河南商丘,宋乃孔子古国,春秋早期鲁国与宋国多所交往。
(三十八)宋公差戈
应为清代济宁出土,曾归潍县陈介祺收藏。铭文于胡上,曰:“宋公差之所造不阳族戈。”[1]3561时代为春秋晚期。1980年,北京市从废品收购站拣选出宋公差戈一件,铭文曰“宋公差之所造柳族戈”,考释为春秋时代宋元公(佐)于公元前531—517年之间所造[20]。
(三十九)鄫子戈
据载此戈1943年出土于山东汶上,铭文在胡上,曰“鄫子良之造戈”,初云五字,实际六字,首字左从“阜”部,右从迭“曾”,于思泊先生释之为“鄫”,至碻。黄盛璋先生《燕齐兵器研究》中论证至详,认为此戈铭之“鄫”国,地在今山东。《左传》襄公四年(569):“邾人、莒人伐鄫,臧纥救鄫,败邾于狐骀。”鄫国处于邾、莒、鲁诸国间,皆利其土地、人民赋乘,取为己有,襄公四年鲁襄公如晋,曾请以鄫赋属鲁,故邾、莒伐鄫,鲁臧纥救鄫。《春秋》经传记载曾国最初为莒国所灭,《春秋》襄公六年(前567)“莒人灭鄫”。襄公八年(565)“莒人伐我东鄙,以疆鄫田”。尽管莒国灭鄫,但是鲁国仍未甘心鄫地失之与莒,故鄫又为鲁国所取。《春秋》昭公四年(前538)“九月,
①滕县文化馆,万树瀛,杨孝义:《山东滕县出土杞薛铜器》,《文物》,1978年第4期,第95页图2。取鄫”。杜注:“鄫,莒邑。”《公羊传》云:“其言取之何,灭之也。灭之则言取之何,内大恶,讳也。”《左传》云:“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乱,著丘公立而不抚鄫,鄫叛而来,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黄先生指出:“汶上属鲁地,此戈出此或即鲁救鄫因战争而遗于鲁地。”[21]57-59
(四十)齐国赒子叔子盘
1981年山东诸城都吉台出土,铭文曰:“赒子叔子,保为子孟姜媵盥盘,其万年眉寿,室家是保,它它熙熙,匄寿考无期。”何琳仪先生指出:“‘子某子’是齐铭中特有的称谓。”齐国金文陶文中人名,如“子禾子”“子阳子”“子逢子”“子栗子”等[22]91-92。齐国姜姓,此地为鲁国之诸邑,《春秋》庄公二十九年(前667)“城诸及防”。杨伯峻注谓在今诸城西南吕标境内。考古调查此地为汉代诸国城邑,而都吉台为商周遗址,王献唐先生认为此地即商代的诸国都邑。进入西周鲁国疆域逐渐扩大,诸国并入鲁国所辖,至春秋早期东方局势发生变化,鲁国需要防备莒国与齐国的侵扰,而加固诸之城邑的防御。这件盘的时代应为春秋中期,当时此地还属于鲁国,后来则归属莒国,战国早期最终属于齐国。
(四十一)平阴戈
清代山东济宁出土,《山左金文集存》谓:山东济宁黄司马得之虞山[1]2370。此戈时代为春秋时期,当时该地属于鲁国。而戈之铭文曰“平阴戈”,据其时代而不由人联想《清华简·系年》第十七章:“晋庄平公即位元年……平公帅师会诸侯,为平阴之师以围齐,焚其四郭,驱车至于东亩(或释之为‘海’)。”事见《左传》襄公十八年(前555)冬十月,为抵御晋等十二国诸侯联军,“齐侯御诸侯于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阴,遂从齐师……十二月……己亥,焚雍门及西郭、南郭……壬寅,焚东郭、北郭……甲辰,东侵及潍,南及沂。”从十月齐侯堑防门而守之广里,至十一月丁卯晋军等人诸平阴,至十二月己亥焚雍门、西郭、南郭;由此丁卯至己亥凡三十三天;己亥至壬寅四天完成包围齐都之战;壬寅至甲辰三天由临淄而抵达潍水。多国军队从十月到十二月才由平阴进攻到临淄,从临淄到平阴百数十公里;由包围临淄而挥师潍水仅仅七天,而防门之攻取则用一月多时间,由此可见当时晋军等在齐国平阴防门一带战事所用时间最长,显然是由于齐国防门一带军事防御体系完备,故能使战事绵延阅月有余。至此,我们自然联想到当时该段长城的军事防御作用。这件平阴戈或许为鲁国攻打齐国世所获欤?
(四十二)徐子汆鼎
上世纪八十年代临沂地区文物收集组在文物拣选中发现,出土于临沂地区费县城北上冶公社的台子沟。铭文曰:“徐子汆之鼎,百岁用之。”[23]春秋时期曲阜东境有地名“徐”,或称为邾国下邑。从铜鼎形制与铭文书体,可以判断该鼎应为江淮流域的徐国所铸造。而考古发现,在今江苏北部徐州区域发现不少徐国春秋时墓葬,邳州戴庄镇九女墩3号墓即出土徐王之孙钟[1]3612。
(四十三)蔡侯戈
兖州博物馆藏,春秋中晚期,铭文曰:“蔡侯□□。”①1995年春笔者参加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赴济宁博物馆文物定级所见。
以上揭列鲁国境内出土商代奄、薛诸器,证明鲁国就封之前的历史。降至两周时期的则有周公、周王太史、召公(燕)、陈、楚国睽士父、郙、莒、齐乘父士杉、杞、邾、铸、邿、薛史显、宋、鄫、徐、齐赒子叔子、蔡等大致十八国族带铭文青铜器五十余件。似是看出,西周早期鲁国与周王室的交往关系密切,如所谓梁山七器数量之多、作器者规格之高这在其他同时期的方国之中是难得一见的。西周中后期则与海岱区域的古国交往普遍,如莒、齐、杞、邾、铸、邿等国族,尤其与之疆域相近者交往更属频繁;而到西周晚和春秋时期则与江淮流域的古国族如陈、楚、郙、鄫、徐、蔡等进行文化交流,同时与周近的宋国、齐国、薛国等亦是交往密切。
通过比较还可发现,莱国和鲁国与西周王朝的交往从西周早期就已经开始,而且以鲁国最为密切;而邾国与西周王畿之内的诸侯国发生文化交流则主要在西周中晚期,这与文献记载也相契合。但是,海岱区域间古国至春秋时期与江淮流域古国族的文化交流频繁而普遍则是共同现象。
岁次乙未十月既望草讫丙申三月初吉修订于山左潍水之湄知松堂南牖下
参考文献:
[1]陈青荣,赵縕.海岱古族古国吉金文集[M].济南:齐鲁书社,2010.
[2]解华英.山东泗水发现一批商代青铜器.考古[J].1986,(12).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4]滕州市博物馆.滕州前掌大村南墓地发掘报告(1998~2001)[C]//海岱考古:第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5]孙敬明.潍水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4.
[6]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M].北京:中华书局,2004.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87-1994.
[8]林沄.琱生簋新解[C]//古文字研究: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
[9]张亚初.西周金文所见某生考[J].考古与文物,1983,(5).
[10]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J].文物,1972,(5).
[11]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壹)[M].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上海:中西书局,2010.
[12]马保春,袁广阔.妀善鼎铭文考释[J].文物,2012,(10).
[13]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济宁文物组,曲阜文管会.曲阜鲁国故城[M].济南:齐鲁书社,1982.
[14]杨深富.山东日照崮河崖出土一批铜器[J].考古,1984,(7).
[1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4,(9).
[16]苏兆庆.古莒遗珍[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
[17]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18]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金文集成[M].济南:齐鲁书社,2007.
[19]蓝蔚.杞伯簋[J].文物,1962,(10).
[20]程长新.北京发现商龟鱼纹盘及春秋宋公差戈[J].文物,1981,(8).
[21]黄盛璋.燕齐兵器研究[C]//古文字研究:第十九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
[22]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9.
[23]心健,家骥.山东费县发现东周铜器[J].考古,19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