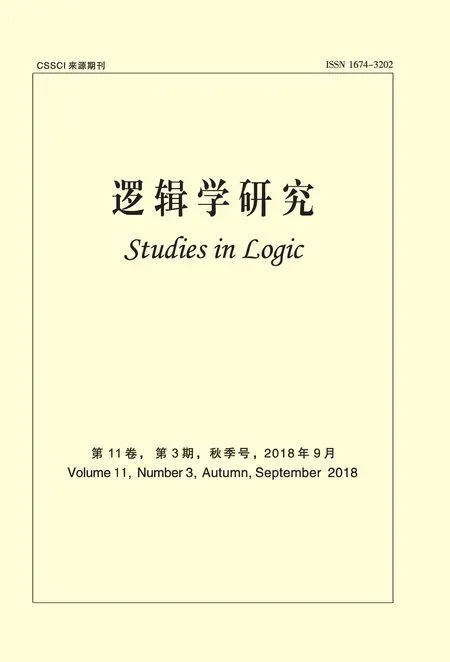先秦哲学对属性与本质的思考
——以“白马论”为中心的讨论*
匡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kuang.sscp@foxmail.com
1 前言
自以现代学术语言讲论中国哲学以来,对先秦名家诸种言说的解释始终是无法回避的疑难,胡适、冯友兰以降虽言者甚众但至今似仍未达成理解上的共识,此种情况,尤以对《公孙龙子》中“白马非马”怪论的解释为代表。此论从来被视为名家的标志性话题,亦或为解决名家理论问题的症结所在,至今也已经出现多种均在一定程度上可自圆其说的解释方案,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小研究传统,几乎成为某种“专门之学”。但无论将此问题直接置于逻辑学的范畴之下,还是注重发掘其背后哲学意义的努力,尚难获得普遍认可的理由,往往在于现代解释者所具有的某些不言自明之“前见”或其理论预设,对于其他不同立场的研究者来说包含了太多的困难,比如我们难以认同先秦名家具备一种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观,而同样也难以接受其在通过上述怪论尝试讨论某种类似于柏拉图的共相或理型论。在此意义上,对“白马论”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展现出论者判别何谓“中国哲学”的潜在标准。认为中国古人具有某种不同于西方的“思维方式”(这包含了目前即使在认知科学的范围内似乎也无法得出的对于心灵或心智的本体论理解),或主张先秦的确存在一种至今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不同于西方样本的说理方式(这种方式既不是逻辑学的——不涉及特定人工语言系统的存在及其对某种自然语言在解释上的回溯效力,也不能直接诉诸现有的语言学知识——即便现代汉语也不完全符合现代语言学的诸多假设),将引导论者针对“白马论”展开完全不同的解释策略。陈汉生认为:“中国人的思维在其哲学传统的焦点在语言以及它在文化中的作用这两方面,与西方人的思维是相同的;而在阐释(says about)语言与文化方面,中国人的思维与传统的西方人的思维,正像中国人的语言一样,是有根本区别的。”([3],第1页)笔者虽不能苟同上述中国哲学的焦点在语言的看法,但亦以为在先秦哲人在讨论内容方面非常不同于西方的哲学论说当中,包含着其对一般意义上哲学问题的思考,即如金岳霖在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所谓“哲学有实质也有形式”,后一种哲学的“形式”或“思想的架格”([6],“审查报告二”),便是无问东西的基本哲学问题,而针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首先也就是如冯友兰所希望的那样,重新钩沉出中国哲学“实质的系统”之中蕴藏的“形式的系统”。就“白马论”而言,笔者所欲论者即其说理方式当中所呈现的哲学问题意识,而更为重要的是,此种问题意识并不局限于名家,更涉及其时先秦诸子多关注有加的哲学基本问题,这意味着,发现“白马论”的特殊意义需将其置于先秦哲学论辩的总体图景当中,而这亦是迄今为止诸种研究常用力不足之处。
2 “白”:物之属性的断定
无论如何理解公孙龙所操“白马论”的理论意图,该怪论在现代中国和先秦语境中均是违反常识的,且这种常识并非受到“西方影响”的后果而实有延绵不绝的历史渊源,如桓谭《新论·离事》载公孙龙操“人不能屈”的“白马为非马”之论乘白马“无符传,欲出关”,而“关吏不听”,“大概当时有规定,马匹出关必须有通行证。”([18],第80页)无论故事之真伪,想必此处桓谭笔下关吏所遵循的亦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白马是(或属于)马”的常识。《墨子·小取》言“白马,马也”,或可被视为对此种常识的理论表达。《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谓:“儿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故籍之虚辞则能胜一国,考实按形不能谩于一人。”此段记载或为桓谭故事的前启,其中所表达的亦是上述有关白马的常识。如借用现代术语陈说此种常识,则其成立的根据或在于“白马”与“马”两语词所涵盖外延虽不同,但前者在经验中实落入后者的范围之内。无需想象公孙龙的“白马论”是欲与此种常识对抗,毋宁说他是在尝试从不同于常识的角度借“白马论”提出一个哲学问题,即我们应以何种恰当的方式以“名”命“物”。这个问题关注的是语义层面的内容而非仅仅欲对语词的外延范围加以讨论,通过怪论的形式,公孙龙为“白马论”的可接受性所作出的辩护与此种辩护当中具有的诡辩性质,或均来自他对“名”如何命“物”的某种洞察和支持常识之成立的那种理论构想之间的差距。
抛开传统上认为公孙龙诡辩的立场不谈,对“白马论”的现代解释,往往致力于发掘公孙龙所提出辩护的“合理之处”,或利用现代逻辑学及相关学科的知识说明“白马论”的辩护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何种程度的可接受性1对于“白马论”较早的逻辑重构,如[1,5]。较新的对于其论证上的可接受性的讨论,如[23,28]。曾昭式文的前一部分同时提供了一个关于“白马论”讨论状况的简单综述,并主张“中国逻辑史研究有两种视角:‘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现代主义”’与‘了解之同情’”,前一种视角或研究范式重在“采用现代逻辑来揭示隐藏在中国古代文献背后的逻辑结构和逻辑原理”,而后一种视角则重在“从文本概念自然演绎出文本义理”,只是出于各自局限尚未能完整把握公孙龙“白马非马”论之含义。,或利用哲学知识对其蕴藏的思想内容在特定语境(可能是以某种西方哲学为背景的解释语境,也可能是强调中国思想之独特性的解释语境)中的可理解性加以解释。笔者无意从前一方向再对公孙龙“白马论”在论证上的可接受性加以现代重建,而更关注其辩护背后的思想立场以及对这种立场的哲学解释可能带来的关于先秦哲学的新知。要而言之,对公孙龙“白马论”的哲学解释,约略有如下三种经典进路:其一如冯友兰的见解,引入柏拉图式的共相观,在“马”之语词指称“马性”(horseness)或马之共相(unversals)的意义上,说明“马”与“白马”所指不同。([7],第257–258页;[8],第144–145页)其二如陈汉生的看法,引入“物质名词”假说,认为“所有真实的复合词项是由各个组成词项所命名的质料总和的名称”,在此意义上,“白马”“应被理解为白质料和马质料的物质和”,甚至“马”在复合词项“白马”中“只是命名为白的马质料”,与单纯的命名马质料的“马”“不是同一名称”,因此公孙龙的论点是可理解的。([3],第190–191页)其三如劳思光的主张,“白”与“马”“各表一属性,因之即各表一‘类’。此二‘类’皆有实在性,故视为同级之实在”,至于“白马非马”在逻辑上的意义,在于“表‘包括关系’与‘等同关系’之殊异”,“白马”与“马”“为不相等之二类。其(公孙龙——引者注)所谓‘白马非马’,即指‘不等同’而言,甚为明显”。([14],第292–293页)冯友兰的见解,实际上预设了先秦哲学中存在某种类似西方柏拉图的哲学观,且公孙龙承认对“普遍与特殊”的划分。此种假设已遭到的典型批评,如陈汉生从语言层面指出;“在中国并未发现说明在语言哲学中柏拉图主义的原动力的印欧语言的语法特征。缺少这些动力,我认为就没有理由去假设中国的思想家们已经设定那些形而上学的奇迹,如抽象的或心理的对象。”([3],前言第3页)笔者同意,先秦哲学语言上的特征,确如葛瑞汉所言,不足以为中国存在“共相的实在论学说”提供支持([9],第99页),且如劳思光对冯友兰坚持柏拉图式立场的判断,此种立场的缺陷在讨论名家之时或不能完全暴露,但形而上学的研究进路并不足以覆盖中国哲学思考之全局([14],第307页)。冯氏对于“白马论”的辨析,对特定构造的西方哲学理论依傍过强,从后来者的角度实难以坦然接受,更为重要的是,笔者不同意将名家作为中国哲学的特例加以处理的讨论方式,似乎公孙龙等人关注一些未得到同时多数思想家认可的特殊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可以抛弃广阔的先秦哲学背景。从这个角度来,冯氏的解释方案的确难以与中国哲学的全幅理论图景相融贯。2最近亦有学者从弗雷格涵义(sense)和指谓(reference)相区别、概念词(concept word)与客体词(object word)相区别、且概念词存在不同等级等角度分析“白马论”的可理解性([32]),此种思路虽然不失为“白马论”增加了一个新的解读方式,但其弱点与冯友兰相同,均在于对特定西方哲学思想依傍过甚。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基于各种不同的西方哲学系统,可以设计出对于“白马论”的多种不同解释方案,这正如基于不同的逻辑观,可对其论证作出多种逻辑重构。由致力于提供对于先秦哲学的更融贯的解释和对冯友兰的不足的批评开始,陈汉生对“白马论”的观点为深入辨析问题提供了新的养分,但其讨论问题的基本假设和某些结论亦无法获得充分支持。他所依托的“物质名词”(mass noun)假说,源于对汉语中缺少表明名词是否可数的语形学(syntax)标记的观察,此种对汉语语法的论断或许源于赵元任较早提出的汉语名词分类方式,([30],第234–235页)赵氏的论点虽来自对现代汉语的观察,但亦可被认为部分适用于对古汉语的讨论。不过,赵元任并未主张全部汉语名词均是不可数的物质名词,而较新的研究也认为现代汉语实际上存在可数/物质名词的区别,并可由一系列语法特点加以识别(如是否能加个体量词等),且此种判断同样适用于古汉语,即无论现代汉语还是古汉语中,可数/物质名词的区别都能从句法和语义层面上被识别出来。([31])实际上仅凭常识判断,即使汉语名词缺少语形上的可数标记,亦不能由此推断在语义上汉语使用者无法区别名词的可数与否,如在计数时将可数的“马”和不可数的“水”同等看待。因此,陈汉生的基本假设:“汉语,从古典时期开始,趋向于一种物质名词的语形学”是不能成立的,而后续推断:“物质名词暗示着一种质料本体论(stuff ontology)以及我称之为关于语词(words)(词项和谓词)的语义功能的区分或辨别的观点”([3],前言第3–4页)亦无法获得支持。他由此认为,在中国人眼中“世界是一个质料或实体相互交迭、相互渗透的集合体”([3],第37页)的论断,充满了早期西方人类学面对异文化且意欲以假想的“非西方方式”对其加以说明时表现出的那种误解与迷茫。陈汉生虽然正确指出,“批判的、分析的、逻辑的和一致性的标准应该用来解释中国人的思维”([3],第30页),但他对中国哲学的思考仍然过早滑入了某种诉诸中国特殊性的西方立场(“他们”和“我们”在某些重大方面不同——虽然这种特殊性并未出现在对中国式思维的元层次判断中,但仍然包含了太多的语义内容)。这导致他在对“白马论”的可理解性的解释当中,最终结论:“中国人思想未曾产生抽象或精神实体的理论”([3],第201页),而这对于任何针对中国哲学从事严肃思考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如果说冯友兰较早的对于“白马论”的分析涉及对某种特定西方哲学构造的直接运用,那么陈汉生在相反的方向上,预设了中国存在某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语义学理论,而此预设同样包含了太多的理论难度。
劳思光解读“白马论”之可理解性的进路,在笔者看来最为朴素可取,白作为一种事物“属性”(attribute),在中国哲学语境中不待对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有所了解后才能为学者所知所论,名家所论物之“实”便是一个等效的术语。参考《公孙龙子·名实论》开篇“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的说法,确如劳思光以为:“‘实’指每一物所以为此物之属性或意义。”([14],第297页)3相关讨论亦可参见[4]。在对“白马”的解析中,将“白”之名作为对白马白色之属性的命名与揭示,更多将问题引向形而上学而非逻辑学方面。劳思光进而对“白马论”的深层意义有所阐发,即他主张在形而上学的问题域中,公孙龙认为“白”与“马”“为同级之实在”的观点将引出“实体”与“属性”之问题。此“实体”即“亚里士多德所谓‘Substratum’”,其与属性“在认知活动中之呈现,显有先后之殊”,“吾人认知‘白’时,必通过一知觉;而在此知觉中,‘白’必呈现为‘某物之白’,否则即不能被知觉。而此时之‘某物’,本身乃成为‘某物之白’被知觉时之预设条件,本身又不被知觉。”如是可知,白乃马“实体”之属性,“白马”之名即如伪《孔丛子·公孙龙》记子高(孔穿)答平原君所言“若以丝麻加之女功,为缁素青黄,色、名虽殊,其质故一”;“先举其色,后名其质”云云,正如《公孙龙子》中“实”为指属性的术语,则《孔丛子》此处“质”即为指“实体”的术语。4参见[14],第294页。劳思光此论,远有溯源,近有后承。谭戒甫谓“名家视马为实,色特其所属者”([21],第392页),已包含类似的实体与属性对比的意思,不过此处谭氏所言“实”未必即Substance;近有江向东析“白马论”,亦明确从“实体”(substance)与“属性”(attribute)角度看待其意义([12])。劳氏上述理解极具启发性,尤其参照《公孙龙子·坚白论》中“坚白石”是“二”而非“三”的论断,即文本在确认白与坚两种可感属性的同时,将石作为不可感但亦不可化除的因素看待(石虽然“藏”,但坚、白仍“在于石”),似乎公孙龙确有对于上述意义上的实体的猜想。但笔者以为,此猜想对于中国哲学的语境而言仍然太“强”了,此处对于实体的推断,与冯友兰对共相的假定可谓处于同一层面,也同样面对古汉语与印欧语言特定主谓式语法特征之间差异的问题,且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公孙龙子》还是名家乃至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均找不到对等于“实体”(substance)的术语,则此问题是否能以完全潜在的方式存在值得存疑。伪《孔丛子》所谓“名其质”的“质”字,可以有其他的解释(详下文),而“坚白石”的论断所推出的,仅是“石”所命名的内容不可感且与“白”或“坚”命名的内容不在同一层面,但并未进一步追问这种内容“是什么”,此与亚里士多德在对entity的追问中发生substance的问题仍有根本的构造上的不同。
在迄今为止与“白马论”相关的哲学解释中,我们应可断定《公孙龙子》对物(“天地与其所产焉”(《名实论》))的属性有明确了解,且此种属性不但是可命名的,亦是在经验中可感知的。参考“坚白论”,可知《公孙龙子》并非将物的一切可命名的方面或特征均等同地视为属性或与其同层次的“名”,那么“白马论”中的奇怪之处就可以被显露出来了:“马”之名命名的内容,是与“白”之名命名的属性同层次的内容,还是与“坚白石”之“石”字所命名的内容同类?“白马论”的诡辩之处即是将“白”与“马”命名的内容同等看待,而实际上“马”与“石”所命名的内容才是同类而与“白”所命名的属性层次不同,劳思光已经看到《公孙龙子》的上述诡辩之处,但他对“马”与“石”的后续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公孙龙子》是否如此看待上述马与石之不同于白,将引出先秦哲学对于物之不同于可感属性的某些方面或特征的理解,而后一种理解实与对物的恰当命名紧密相关。
3 “马”:物之本质的命名
支持“白马是马”的常识成立的理由,如前引伪《孔丛子》中子高言论所主张,暂不深究“质”字之意义,大体可由其对丝麻、牛马的基本看法得出,颜色只是对物的修饰,作为属性附丽其上,而物之名的确定因其“质”而非颜色或其他的修饰、属性(如“楚国”)。于是后文言“凡言人之者,惣谓人也,亦犹言马者、惣谓马也”,“惣”即“揔”,“人”、“马”之名的成立,是来自对人或马这类物之“质”的分辨。公孙龙与子高所代表的常识均同意白色是直接可感知的,《公孙龙子·坚白论》谓“视……而得其所白”,《孔丛子·公孙龙》则引子高言语谓“覩之则见其白”,可见双方的差异主要在于对“马”的理解。在子高看来,“马”作为由其“质”得到的物之名,是可以“察知”的:“察之则知其马”,但公孙龙则将“马”之名所命名的内容,视同于附丽于物的颜色属性,《白马论》谓:“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则“马”之名来自对“形”的把握,而由此处上下文或可推测,“形”如“色”一样,均为直接可感知的对象,也就是说,“形”亦类似于物的属性。上文子高所谓“察”,并不是直接的视觉可感,其虽然包含“视”的意思,但其扩展的用法在先秦多指抽象意义上的辨别,如《孟子·尽心上》:“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吕氏春秋》《本味》:“察其所以然”、《察今》:“故察己则可以人”、《察传》:“夫传言不可以不察”;均涉及思辨意味的分析、辨别而非仅做视而可感。子高“覩”、“察”对举,所强调应为其抽象的扩展意义。至于公孙龙所谓“形”,应指事物之形状样貌,如“牛有角”、“马有尾”、“人二足”等等,此为先秦通行用法,而此种意义的形亦可直接目视可感,此即公孙龙“形”、“色”对举的用意。如此,公孙龙“白马论”的深意便可显露出来,“马”若命名的是类似于“白”之属性的“形”,则此“马”之名,何以能够成为对某一物类之总体的命名呢?
公孙龙以“马”命名马的“形”之属性,正是其怪论的关键,而其在论证中或涉及葛瑞汉所谓“同一性(identity)与类从属关系(class membership)的基本混淆”([9],第99页),而他的论辩对手“一旦被最初的分析欺骗而接受‘马’是形状的名称”([9],第109页),则难免陷入语词使用、属性认定与物类命名之间的困惑。上述问题劳思光亦有所见,但葛氏受困于陈汉生“物质名词”假说,劳氏又在推理中走的太远,均未能对名家的此一关键的“形名”问题加以清晰解释。在对“白马论”加以分析的现有解释空间中,笔者(一)不认为公孙龙此说的意图是在现实中具体的白马是否作为马之物类的成员的意义上欲与常识对抗(后者如庞朴所谓“个别”与“一般”的关系([18],第83页),或如周云之所谓种属关系([33],第86–95页),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在现代哲学语境中欲对古代常识加以分析的方式,同样如冯友兰一样带有明显的受到特定西方哲学范式影响的痕迹);(二)也不认为目前多数欲使公孙龙的辩说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合理”的解释策略所采用的那种A+B不等于A(或B)的说明方式(如同时描述颜色与形状的复名在指称对象方面不同于单独描述颜色或形体的单名5两名结合之复名不同于其中之单名思路,可在《公孙龙子·白马论》本文中找到根据:“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从类似于复名的角度讨论“白马论”合理性的研究情况,参见[11]。)已经充分解决问题;(三)亦不认为目前对“白马非马”中“非”字的理解(“不等于”或“有异于”而非“不属于”6参见前揭劳思光、江向东观点。)对分析公孙龙的思想有实质性推进。以上(二)、(三)将公孙龙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化的努力,只是从表面上取消了问题,且如劳思光所言:“此种讨论,就逻辑要求言,实未足为严格,且所涉问题亦至浅”。([14],第293页)正如《公孙龙子·白马论》的关键语句所言:“命色者非命形也”,他在表面上将色、形同等看待并诱使读者亦做如是观的之时,却又尝试指出上述两者间存在某些关键的不同——若非如此,此句几近废话。如是,色、形之间的同与不同,引发了公孙龙觉察到的一个原有的基于常识的命名理论的关键缺陷:“马”之名作为对形的命名如何能够被直接用来命名马之物类。
对“形”与物之命名之关系的关注,实际上是先秦名家与黄老学当中被广泛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公孙龙个人的特出之见,且在《尹文子》7《尹文子》之真伪存疑,但据曹峰研究,“不能否定其主要思想是以战国中晚期、秦汉之际……为背景的”,“但从这部书对道(黄老)、名、法诸家高度的思想整合性来看……显然有汉以后人加工整理的痕迹”([2],第206–207页)。中曾得到结论性的表述。《战国策·赵策》中苏秦称操“白马论”者为“形名之家”,《列子·仲尼》称“刑【形】名之家,皆曰白马非马”8《列子》虽被近人目为“伪书”,但考虑到现代对于古书形成的种种知识,实尚不足以完全否认其中包含先秦思想材料。对《列子》书辨伪情况的简单讨论,参见[26]。,鲁胜《墨辩注叙》亦称“惠施、公孙龙……以正形名显于世”,可见形名问题被广泛视为名家辩者的代表性问题,而此一传统也在黄老学和法家当中得到延续。“形”通“刑”,黄老学亦道“形名”,如《黄帝四经·经法》:“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必审观事之所始起,审其刑【形】名”;《道法》:“秋毫成之,必有刑【形】名”;或称“名形”,如《经法》:“正、奇有位,而名刑【形】弗去……名刑【形】已定,物自为正。”相关思考继续在韩非子处得以接续,如《韩非子》之《主道》《扬权》等篇专论“形名参同”(《扬权》)、“审合形名”(《二柄》)等。稷下学宫为名辩家和黄老学家共同的活动舞台,而韩非子承继黄老学之思想,则上述围绕“形名”的思想脉络何以形成不难想见。只是前后论“形名”者关注重心有所不同,名辩家首先重在辨物之形名,主要兴趣在知识论方面,而黄老学以降,思考重心已经由物转向人事,以名家辨物之形名为基础,更多延伸出政治学方面的考虑。9曹峰分名家为“知识型名家”和“政论型名家”,亦可与此处所论相参照([2],第60页)。司马迁从后一种角度统称上述围绕“形名”的讨论为“刑名法术之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商鞅、申不害、邓析等人均被认为可归于此学统之下,《史记·商君列传》:“鞅,少好刑名之学”,刘向《别录》:“申子学号曰刑名者”,《邓析子·书录》:“邓析者……好刑名,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在上述“形名”之学的传统中,主张在对物加以命名之时,因其形而定其名,或者说物之形是物之名得以确立的关键,大约是其最基本的观点,否则何来“形名”之说?此种论点,集中见于《尹文子·大道上》的种种论述。
《尹文子·大道上》中最典型的对于形名关系的说法如:“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这是直接将物之形与物之名联系起来,而更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名”作为“命物之名”,是对物之究竟所是为何的指称,即由物之形可以断定物之为物的“名”。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判断词“是”,但不能因为认为古人无法对物之究竟所是做出判断,如“……者……也”的句式10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此句式之末缀上一个空的判断词从形式上补充其语法结构,则可以让补充后的句式类似于现代日语和古希腊语的判断句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认为是等效于包含判断词的语句,如因缺少语型学的标记就认为古人不能在思想中清晰知道“牛是牛”、“马是马”,笔者认为是非常荒唐的。称呼或描述物,可以有多种角度,举现实中的牛为例,可称其究竟为何物之本名为“牛”,称其色名“黄”,称其主观评价之名(毁誉之名或况谓之名)“好”,甚至可以数名连用以描述对象,如称“黄牛”或“好黄牛”。对于各种称呼角度之间的区别,《尹文子·大道上》有一段专门讨论:
语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设复言“好马”,则复连于“马”矣,则“好”所通,无方也。设复言“好人”,则彼属于人矣。
“牛”作为某物的本名,是对其“定形”的称谓,而“好”作为评价,则是可用以评价不同物的“通称”,可以用来描述牛,也可以用来描述马或人。此处“通称”与“定形”的对比,类似于前文引子高对“色”与“质”的对比,可以设想,“白马”之名如在《尹文子》中加以分析,亦与“好马”的模式相同。据此可以进一步推测两个文本均支持区分两种不同的“名”:只能用来称呼现实中的牛的牛之“本名”和可以用来称呼现实中任何对象的“通称”,“本名”被认为直接关联着或指称了确定的物之形或其“质”,而“通称”可以是对物之颜色、评价等等的描述。不过《尹文子·大道上》中对于“名之三科”的划分较为混乱,未能凸显上述意思,如其所谓“命物之名”,实际上包括了我们上文所说的“本名”与颜色名,而后者实际上与毁誉、况谓之名同属于“通称”。
以上《尹文子》的“形名”观,同样获得了来自其他黄老学作品的佐证,如《鹖冠子·环流》:“有图而有名,有名而有形。”《黄帝四经·称》:“有物将来,其形先之。建以其形,名以其名。”《管子·心术上》:“物固有形,形固有名”;“以其形因为之名。”种种说法,均可被认为也同意将物的形状样貌与其本名的命名联系起来的主张。上述“形名”观可被视为战国中晚期从名家到黄老学的通见,或可被视为他们对“白马是马”的常识作出的某种理论说明,此种通见在《尹文子·大道上》里获得了比较好的总结,但无需认为其属于《尹文子》提供的新见。此种“形名”观所涉及的物,最低限度推断起来(一)仅涉及具体实存之物,如牛、马、石之类,而不涵盖对于抽象对象或不存在对象,如“仁义”或“龙”之类;(二)其之所以成立的核心理由在于,物之形标志了此物作为此物且不同于彼物的关键方面,如是对形的称谓才可被作为物之“本名”;同时,(三)可以认为物之“本名”标识出某一物类,但对此“本名”和“形”之间关系的考虑,或涵盖了现实中物类的个体,但不涉及物类之层级。对名家上述看法,谭戒甫亦曾有总结:“因为凡物必有形,再由形给它一个名,就叫‘形名’。由是得知:形名家只认有物的‘形’,不认有物的‘实’。他以为‘形’即是物的标识,‘名’即是形的表达,物有此形,即有此名”。([22],第1–2页)此处谭氏所言“实”,并非公孙龙本来的意思,考其后文,似应指物之质料(material/stuff),此一论断虽不知所据,但谭氏对“形”与“名”(本名)之间关系的发掘符合我们上述对名家思想的讨论。如果物之本名所指称的,确为某物之为某物且与他物相区别的关键,或可利用“本质”这个术语来代表上述内容,如前文引入“属性”以称呼名家对物之某些特征的理解,“本质”所指出的内容,即使某物之为某物的关键,亦不待西方哲学的进入方可为中国人所知,如前引子高语所言“质”,就是一个大体等同的术语(其他先秦诸子亦有不同的用以指称物之本质的术语,详后文)。于是,上述名家与黄老学对于“形名”关系的通见可表述为:本名指称物之本质,而其如此命名的依据,即本名为什么可以指称本质的依据在于本名亦是对物之形的刻画,由此可以推知,以上对“形名”的理解中,实际上蕴含着一个物之形即其本质的看法。11贡华南对名家“以形为本质”的见解亦有所见,参见[10]。不过值得注意的,在名家的术语体系中,并没有一个术语对等于“本质”,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对“形”和“实”的强调已经足够说明问题,物之为物可以辨别出多种“实”,而其中最关键的方面,或者说决定着物之为物并区别于他物的“实”便是“形”,此种特殊的“实”即物之本质,而其他不同于此的“实”即物之属性。
问题在于,公孙龙是否同意上述名家与黄老学均承认的对于物之本名的命名原则的论断,即马之本名所命名的是表现为马之形的马的本质。笔者以为,公孙龙恰恰不同意此种看法,故而才有“白马论”的论辩设计。如前文所言,公孙龙试图指出“形”实际上与“色”一样,仍然只能被视为物的属性,“马”之名如命名现实的马之形(四足有尾无角)的属性,便与“白”对马之色的属性的命名同位阶,如是则不足以命名马之为马的本质,亦即,命形之“马”作为名,也只能被视为“通称”而非物之本名。这显然与“马”始终被作为命名了其本质的、现实中马之物类的本名相冲突,且如以“马”命“形”属性,则可以允许“马马”这样的说法,但《公孙龙子·白马论》明确指出后者在实际上违反语言日常使用并不可接受。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公孙龙的“白马论”可能是针对集中出现在《尹文子·大道上》中的有关“形名”的说法而发12如汪奠基、崔清田等观点,参见[2],第213页。但曹峰认为《尹文子》中的“形名”观不应在公孙龙之前却也未必,这种观点完全可以是对公孙龙之前或同时代的名家主张的后期总结。,但未能揭示出其间差异的真正意义在于公孙龙发现了此种“形名”学说中可能包含的对于本质与属性的理解和命名当中存在的潜在冲突。13在解释“白马论”时,温公颐([25],第46页)、庞朴([17],第75–76页;庞氏此处观点与其前引观点不同)均已经注意到问题可能与属性和本质的异同相关,但均未能予以系统说明。
4 德与性:先秦哲学对物之本质的再反思
如果“白马论”实际上体现了某种对于“形名”之学的反思,则此种反思也并非《公孙龙子》所表现出的独见,实际上大体同时或较早,已经有来自道家和儒家阵营的对于形名关系的深入反思。道家反思上述主张的关键,在于指出“形”的存在之上,尚有决定其为形的“形形者”,后者即如《老子》所论的无形之道,而《庄子》与其他道家黄老后学乃至《易传》均认同并以自己的方式发展了此种反思。14详细讨论亦可参见[10]。
在道家系统中,对于道优先于形名的看法可以引出两种不同的针对“形名”关系的态度。一种是《庄子》式的,如《庄子·天道》批评名家“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并主张“形非道不生”(《天地》),其最终用意在于否定“形”可作为物之本质的标志,将其还原为一种经验中的物之属性。《庄子·德充符》刻画了一系列形貌残缺的得道之人的形象,如“兀者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等,都是为了说明“德不形”的道理,这些人“形”虽然不足,但却都是有道德之人,并在后一种意义上拥有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德”作为与“道”同一位阶的观念,体现了道生成万物的“效果”,并具体化为物之为物的“物德”15“物德”的问题,参见[27]。,就《庄子》所举人的例子而言,德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真实本质,“全德之人”不见得具备一般经验中的人之形,更极端如《人间世》中对“支离疏”的描写,“支离其形”并不意味着“支离其德”。可以由此推测,《庄子》主张对物之本名的命名仅与其德相关,而与其形的改变无关,即对物之为物的本质断定在于对其德的把握,而与经验中的可感属性之具体呈现无关。
另一种对“形名”的反思则是黄老式的,前引《管子》《尹文子》实际上均在此思想路径当中,其思路的实质是为形的成立增加了一个前在的支撑,但未由此进一步反对仍可将形视为标志物之为物的本质与物之得以命名的依据。典型如《尹文子·大道上》言:“大道无形,称器有名。”虽然此论同意无形的道对一切有形之器的优先性,但如前文所言,其在此条件下仍然坚持“形名”对应于某种本质-命名观,以曲折的方式通过申明道的先决地位重新证成形的本质意义。黄老学作品《黄帝四经》中贯穿的“刑【形】德相养”之观念,或即代表了对上述内容的另一种表述。后一种有条件地认为对物之形的把握仍然关乎对物之本名的命名和对物之本质的了解的思路,应当继承了较早时墨家后学的经验主义传统,且在稍晚时的数术中蔚为“形法”家之大观。《汉书·艺文志》中多有讲“相术”的书,涵盖了从阴阳宅风水、人畜物之品鉴到农业经验等多方面,马王堆帛书与居延汉简等亦出土《相马经》《相狗方》《相宝剑刀》等书,仍然同意通过观察对象的经验特征或通过对其形态方面的可感属性的把握,可以了解物之为物的本质所在。16讨论参见[15],第84–87页。
上述思路大体更贴近常识,且以形态特征对物加以某种判断,在现代动植物形态学当中也仍然是可以接受的且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辨别物种的方法,只是其若接受哲学追问难免显出不足,比如因基因变异长出六条腿或者因为意外残缺一条腿的马,还是马(具有马的本质)并可被称为“马”吗?而如面对诸如石头、水或铜这些无定形的对象,又凭什么对其加以命名呢?类似问题《尹文子·大道上》或已经想到:“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而诉诸道的存在解决上述困惑虽不失为符合道家传统的解决方案,但对问题的细节,却犹有“未辩”之处。
对“形名”问题所包含的对于物之本质和据此作出的物之命名的反思,亦出现在儒家孟子与荀子那里。《孟子·告子上》中著名的孟子与告子围绕人性的辩论,所涉及的核心内容不外亦是对人之属性与本质的判断。孟子辨明人性,仍举白色作为论辩的关键部分,这一点与《公孙龙子》的“白马论”无论在材料选择还是内在问题意识等方面均有共同之处,此或是由于颜色乃一般物最易于被观察到的属性,如鲁胜《墨辩注叙》:“名必有形,察形莫如别色”,只是名家展现为“形色”的本质与属性问题,在孟子这里转换为“性色”问题。17非常有意思的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论属性时,亦常举白色为例,并屡次言及“白人”、“白马”。孟子与告子论辩之时,对于“性”有专门的术语化用法,张岱年先生对此早有所见:“孟子所谓性者,实有其特殊意谓。孟子所谓性者,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之特殊性徵。人之所同于禽兽者,不可谓为人之性;所谓人之性,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实即是人之‘特性’”。([29],第185页)此处“特殊性徵”或“特性”即我们所谓“本质”,亦即孟子以“性”专指本质言,而传统意义上表生命禀赋的“性”,孟子称为“天性”,划归属性范畴,如所谓“形色天性”(《孟子·尽心上》),这里孟子不但如公孙龙“白马论”开头所主张的,将形色等同看待,还将这两种属性特征均归为天然的生命禀赋。《尽心下》中著名的“口之于味”章可被视为对上述术语区别的一个说明,“口之于味”、“目之于色”等等传统意义上生命禀赋之“性”,可称为“命性”或“天性”,但却不是“性”这个指称本质的术语所应指称的对象,这个术语应被保留下来,如就人而言,专指仁义礼智这样的人的本质。但告子仍将“性色”同等看待,均视为人的天然禀赋之特征,而未能看出如以“性”指称人之本质,则其必然有别于可视为属性的“白羽”、“白雪”、“白玉”、“白人”、“白马”之“白”。18孟子以“性”指本质,参见[13]。
孟子所关注和谈论的人性,是回答人之所以为人的关键,即其本质所在,孟子进一步指出,人的这种本质就在于可成就德性,并因此点而区别于禽兽。与《公孙龙子》相比,孟子同样视形色为同位阶的属性,并以“性”字作为指称本质的术语,如以为人的本名来自对这种本质的分辨,即人因其性而为人,则实际上解决了“白马论”所提出的有关物类之本名的命名难题。就马之为物而言,其名为马是对其本质而非形的命名,且此本质为马之性而非马之形。孟子与告子的论辩中,没有出现专门用来指称属性的术语,他所谓“白”,也与公孙龙等的用法一样,笼统言是指事物的“属性”,但某物具有这样的属性,是偶然的,即“偶性”(accident),还是恰恰显示了其“特性”(property),孟子与其余先秦诸子均未有所论及。在孟子这里,还发生了如何将此种人的本质识别出来的问题,其不像物的色、味等属性,可由目、口等感官加以直接把握,如何识别出作为人的本质的、不同于禽兽的人性,则成为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此问题在主“形名”论的名家和黄老学者那里并不存在,如果“形”即本质,那么物的这种本质可由感官经验加以认知;这个问题在《老子》《庄子》处亦不曾得到彰显,他们从道的立场均倾向于取消对个别物类之本质或物德问题的具体讨论,甚至可以认为他们有将道或与之对应的德作为万物之共同本质的倾向,如《庄子·齐物论》中“道通为一”的极端主张,相对而言,各种具体的对于万物的命名都是可以取消的。
对于如何识别本质,孟子以人的本质为例,在《告子上》中实际上提供了两个递进的步骤:其一是主张诉诸心的天然能力,通过将“心之官则思”与“耳目之官不思”的大、小体之对照,直接给出了一个即心言性的揭示人之本质的通道;其二是进而主张“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步骤一,认为心具有特别的思知能力,并因此而超出其他感官经验之上,是从稷下黄老学到郭店简书为代表的孔子后学再到孟子乃至荀子均同意的某种共识,如《管子·心术上》开篇即谓:“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郭店《五行》谓:“耳目鼻口手足六者,心之役也”;《荀子·正名》谓:“心有徵知”。如认为此种心与其他感官之间的对照,也出现在对于本质和属性的分辨中是完全可能的,正如颜色、形状等物之属性可由感官加以识别,人性作为人的本质,可由心加以认知。但是,心如何认知本质尚需第二步的追加说明,此即所谓“举相似”。
此主张应是对墨家所坚持的那种经验化原则的继承,即通过分辨某一物类,比如人之个体均具有种种相似之处,最终找到为全体人类成员共享的相似点,而后者便可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如果认为在儒家传统中,圣人代表了人性的理想状态,则一定最好地体现着人的本质,那么通过比较任何人与圣人之相似点,便可以识别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孟子判定“圣人与我同类者”的理由如下: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
这里似乎是在主张味、声、色与理义均是普通人与圣人的相似点,但如考虑到上述第一步心与感官的对照,则此处前三者均为人所共有的属性,仅心所悦之理义方标志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孟子所言“举相似”的原则,或即《墨子·小取》所谓“效”:“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法”即标准、法范,中国古代没有亚里士多德式的通过定义来揭示事物本质的方法,判定某物是某物的方式,或即判断其“符合(某特定事物之样板所给出的)标准”,我们为古文献原文增加的“是”而拟构出带有判断词的现代语句,所表示的也就是“符合(某特定事物之样板所给出的)标准”的意思。举人为例,如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是他们同为人类的关键,那么在追寻相似性的过程中,我们必然能够回溯到某一个最标准的原型或样板,比如儒家便根据三代文化的传统,回溯到所谓尧舜等圣人作为人的样板。如此会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样板所给出的标准可能是多样的;其二,在多种标准中可能有一样或若干样是最为关键的。如孔子之为圣人,不是由于他比别人高、会赶车或者射箭(这些特征其他人可能具备也可能不具备),也不是由于他对于饮食或音乐有良好趣味(这些特征可能任何人都同样具备),而是由于孔子具备以仁义为核心的德性。后者是孔子之为圣人的关键,圣人与我同类,普通人(无论是否会射箭、是否善于欣赏音乐)之所以为人的关键也就在于此,也就是说,此关键标明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所在——这种相似之关键,亦如亚里士多德对本质的看法,其必定为同类事物的所有个体所分享。古人言“推己及人”、“以己度人”,所遵循的亦是上述“效”或“举相似”的原则。
以上孟子的思路,并不同于我们熟悉的西方哲学揭示本质的方式,但却与现代语言学对“实体”(entity)的范畴化研究相协调。受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理论的启发,一些语言学家通过对颜色词和英语“杯子”的个案所指范畴的研究发展出某种自然范畴理论,主张:(1)实体是根据它们的属性加以范畴化的;(2)实体的范畴化是建立在好的、清楚的样本(exemplar)之上,然后将其他实体根据它们与这些好的、清楚的样本在某一组属性上的相似性而归入该范畴。这些好的、清楚的样本,就是“原型”,是非原型事物的参照点;(3)范畴内的成员地位并不相等,有较好的样本和较差的样本之分。([16])以上语言学家的主张,为了显示与西方传统观点的差异,具有明显的取消某一类实体范畴的本质的倾向,但整体的运思路径则与孟子和墨子后学大体相当,如果认为实体的诸属性当中的确有某些或某个最为关键,则称之为其本质并不为过。在本文前面的叙述中,为了更清楚表明问题,始终坚持将本质与属性对立起来,但如亚里士多德所见,某物之本质只不过在于其具备的那些以某种方式支持其余依附性特征存在的优先特征([19],第99页),在此意义上,物之本质与属性并没有绝对的鸿沟,我们强调前文中的对立,只是为了更方便揭示先秦哲学对此问题的思考。
荀子对物之本质及其本名的探讨,可以说是始于《非相》,终于《正名》。《荀子·非相》的核心意思,或即是反对主“形名”论的名家与黄老学者以为由形可通达对物之本质的把握的主张。荀子也举人为例,反复说明“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如果说“二足无毛”是对人之形的一个描述,那么荀子说“狌狌形相,亦二足无毛也”(遵俞樾改字19参见 [24],第 78–79 页。),显然是反对人的本质在于其形的主张。而他所言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有辨”,在《正名》中便发展为“心有徵知”的判断,人据此方可“缘天官”、“别同异”。可以推测,在荀子看来正是人具有的有辨有知的特征,如孟子所以为的德性一样,标明了人的本质,只不过他并未如孟子般用“性”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本质。参考《正名》后文,荀子用来称呼本质的术语,大约是“类”字,即所谓“徵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知类”之后,“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即有万物之名的确立。在批评“形名”方面,荀子与庄子类似,他所谓“非相”,也一定不同意当时或稍后“形法”家相人、相物的主张;在积极的方面,荀子与孟子一样,也认为我们实际上可以并有必要认识人或万物的本质,只是在对人的本质的判定方面,他更看重辨知而非孟子所推崇的德性,但如果可以认为德性的成就是辨知活动的某种后果,那么荀孟之间的差异就会迅速缩小。
回到“白马论”中公孙龙所觉察到的冲突,根据上述儒道两家的反思,“马”作为现实中马之物类的本名,所命名的无疑是马之为马的本质,即马之性或马之德,但绝非“形名”家所认为的马之形。可以推测,如果人的本质被认为在于德性或辨知,那么马的本质或在于善跑,所以伯乐所寻找的乃是“千里马”,而非具有某种特殊毛色或体态的马,如果按图索骥的人不理解这一点,那么他寻找良马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5 结语:共同的哲学问题,不同的解决方案
由“白马论”为发端所引出的先秦哲学当中对于事物本质与属性的分辨,实际上为多数先秦哲人共同关注的话题,而非公孙龙或少数名家的独见。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古希腊哲学中,而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解说最为我们熟知。主张中西均曾在哲学讨论中关注事物的本质与属性问题,并不意味着双方思考问题的路径一定会发生重合,比如先秦就没有希腊式的通过定义的手段来确认本质的方法,而先秦那种通过“举相似”寻求物类之共同点的方式,似也并不曾进入早期西方哲学家的视野。面对事物和人自身,在高于常识并意图解释常识的意义上,无论东西均曾尝试对物所展现或具备的一系列特征加以把握与判断,并且都发现其中某些特征较为关键,甚至直接决定了我们对于物的命名,进而尝试对此种探究加以反思和说明的努力,构成了基本的金岳霖所说的思想的“架格”,围绕这种“架格”发展出了一系列一般意义上的、对于东西方均有意义的共同的哲学问题。对于呈现给我们的哲学问题,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案,比如使用不同的术语系统、采取不同的论证策略,而不同语言的形态特征,的确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对问题的解决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但上述差异,在对共同的架格的探讨之下,实际上都可以得到恰当说明,而笔者以为由“白马论”引发的问题,恰好可说明此点。前文曾认为劳思光提出了潜藏在“白马论”当中的问题关乎“实体”与“属性”,而“实体”的哲学判断显得太“强”,之所以有如此判断,正是由于“实体”概念之出现,应与西方语言充分语法化之后的主谓结构密不可分。没有对象的述谓在西方语言中不可能独立存在,而汉语恰恰允许无主语的“零句”存在,在此意义上,西方语言中的主语只是句法化之后出现的范畴,汉语虽然允许“零句”,但不可想象汉语句子中不包含“话题”。20此亦为赵元任观点,讨论参见[20]。正如西方语言在语法上要求句子必须有主语一样,哲学中的种种对于数量、性质、关系、地点等等的判断也必须围绕或针对一个一定要预先出场的实体,但是在没有相应句法要求的汉语中,哲人们大概也不会自然地设想出实体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有时会将实体与本质等同看待,并因此发生了实体的“双重意义”的困难:既是个别事物,又是个别事物的本质。这样的问题在先秦哲人中间则不会产生,仅确定某一物类的本质将实现于此类事物的所有个体当中就可止步于此而不会陷入进一步追问可能出现的困难当中。基于此种观察,笔者认为“白马论”所引发的乃是本质与属性的问题,在此问题的架格中,先秦哲人对于事物之本质的探寻,具有与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教导的相互可理解性,而无需一定诉诸涉及特定语法构造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