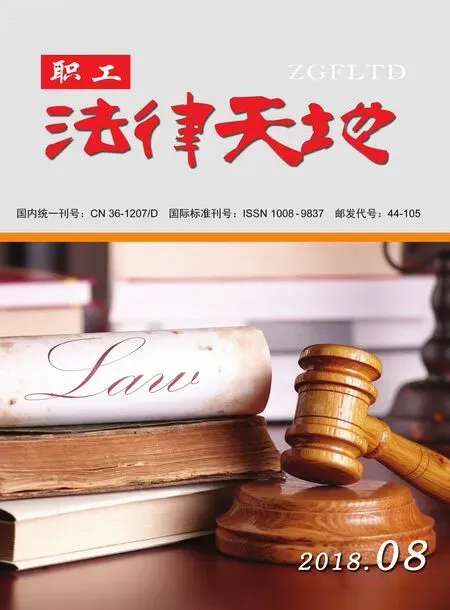论“盗”“骗”交织行为的定性
——以李某骗借手机一案为例
江星如
(201620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本文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对李某骗借吕某手机一案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展示了本案的关键信息和重要部分。
第二部分:联系控辩角度,对案件争议焦点进行归纳。
第三部分:区分了诈骗罪和盗窃罪,论证本案构成诈骗罪和对盗窃罪的否定。
第四部分:总结了本案的定性,结合涉案金额提出建议。
一、案情简介
2017年3月11日下午四点半,李某在上海市某路公交站台处,以手机没电需为朋友筹钱为由向吕某借用手机,并提出在其身边开免提使用,吕某遂将其随身携带的苹果7plus手机交与李某。李某使用该手机与黄某通话,谎称需要购买水果看望病人,提出持手机前往附近一百米的便利店的要求。吕某确认便利店位置后,点头表示同意,李某遂前往便利店,买了两袋苹果后,乘上由黄某驾驶的汽车离开。吕某在公交车站一直看着李某,等待十几分钟后察觉不对劲,前往便利店后发现李某早已离开,遂报警。
二、争议焦点
传统意义上,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区分界限明晰,在行为手段窃取和骗取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但随着作案手法的不断变化,“盗”“骗”交织的案件发生率不断提高,本案就是典型。
行为人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被害人的信任,进而使被害人同意其使用手机,并最终同意其单独将手机带至一百米之外的便利店使用,最后行为人乘黄某汽车离去。既存在虚构事实之骗,又存在离开现场之窃,要判断此种盗窃与诈骗交织的行为,应当关注行为人真正获得手机的手段。
检察院以行为人犯盗窃罪起诉,认为其取得手机是通过趁被害人不备,坐车离开现场的窃取行为。
站在辩护的角度来看,行为人通过谎言加深被害人信任,从把手机“骗到手”,到把手机“骗到走”,起关键作用的是行为人的花言巧语,应当评价为诈骗行为。
因此,行为人获得手机的手段是本案定性的关键。
三、相关法理分析
(一)诈骗罪之肯定
我国刑法对于诈骗罪构成的规定并不明确,理论界普遍认为诈骗罪的基本构造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使得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做出了处分行为。被害人的意志与行为涉及到了诈骗罪和他罪的区分问题。在本案中,对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以及被害人的错误认识是没有争议的,对李某的行为中存在“骗”和吕某的意识里包含“被骗”都持肯定态度。因此重点在于被害人是否具有处分行为。
何为处分行为,是存在争议的。有学者要求诈骗罪的处分行为应当为处分所有权,即被害人将财产的所有权移转给行为人。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将处分限制在所有权是对诈骗罪成立的一种限缩,也与立法目的相违背。首先,采用所有权转移,就意味着只有在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之后,低价卖给、送给或者直接放弃财产时,才成立诈骗罪,这就排除了以借用为手段的诈骗罪。因为在行为人谎称借用时,被害人是很难直接产生出处分所有权的意思①。但是,以借用为手段的诈骗罪是广泛存在于司法实践中的。例如,A没有返还的意思,却隐瞒其意图向X借用汽车,得到汽车后逃匿。X只有转移占有的意思,但A的行为也成立诈骗罪②。其次,当被害人没有处分所有权但实际上行为人已经通过实际支配财物的时候,被害人对行为人销赃、毁弃财物的行为无能为力,仍将该行为评价为盗窃罪,不但不能评价此前的骗取,更突破常理。再者,当涉案财物系违禁品时,对于私人是否能成为其所有权人,本身就是存在争议的,如果以处分所有权为限,难以进行定性。最后,当被骗人本身不是所有权人,而是通过借用、租赁等手段获得占有,他难道就无法成为诈骗罪的受害人呢?这也是不符合常理的。
所以不应当局限在是否处分所有权,而是被害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会失去对财物的控制,却仍然做出了同意的表示,并不采取有效措施保持支配。
实践中也存在类似案例,比如,在丁晓君犯盗窃罪一案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被告人丁晓君冒充帮助警察办案的工作人员获得了被害人的充分信任,从被害人处骗得了手机等财物,又以去拍照、开警车等欺骗手段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同意其带着手机等财物离开现场,并在原地等候财物的归还。丁晓君获取被害人财物的主要方式是欺诈而非窃取,其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被害人处分时意识到财产从自己的支配下转移到对方的支配下,就应该认为有交付处分的意思③。意识到失控和支配转移是处分意思的关键,但是立法上并没有明确的标准。在日本,刑法的占有是指对财物以支配的意思进行事实上的支配。就事实上的支配而言,它不仅仅是单纯物理的、有形的支配,对财物的现实握持和监视也不是占有的要件,占有的存在与否应当根据物的性质、时间、地点和社会习惯等因素,按照社会上的一般观念来判断④。这表明,虽然刑法中的占有是一种社会概念,但也并非完全脱离物理学的判断,司法实践仍然要考虑物的性质、地点等因素。同一个物,在不同场所,即使与所有权人相隔距离相等,也存在控制与失控两种状态。比如同样是相距50米,在私人住宅的领地与体育场,控制的能力有强弱之分。不同的物,在同一场所,根据所有权人的支配方式也会出现不同的占有状态。林山田先生借鉴德国学说与判例,认为可以根据客观情况推定主观支配意思的存在,我国刑法理论中也有学者提出,可以将空间场所区分“公民可以自由出入的公共活动空间”和“与公众隔离的单位内部或个人活动场所"两种情形,分别把握人对财物的控制意识的有无及程度⑤。
回到本案,结合客观环境可以推断出一个普遍的社会观念。现场勘验显示,行为人前往的便利店和被害人停留的公交车站相隔一百米,且位于同侧;案发时间为下午四五点,根据笔录显示当天人流量较大;当天为3月11日,案发时天色较暗,可视范围缩小;便利店与公交车站之间不但有其他建筑物的阻挡,也有人群的迷惑。在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后主动将手机交给行为人时,她已经丧失了事实上的支配。在行为人继续行骗,巩固被害人信任,询问其能否单独带手机去便利店使用时,被害人对自己丧失占有的结果是有预见的。因为按照社会观念来看,客观环境使得无法对手机进行有效控制,显然被害人也预见到了这种失控状态,所以一直紧密注视着行为人。而正是因为客观环境和已经丧失占有的结果,才使得被害人那么密切的注视也没有牢牢锁定行为人。无论是客观第三人的视角,还是被害人的控制,抑或是最终的结果,都足以证明失控的预见和事实。
当被害人基于处分意思,将手机移转给行为人支配时,自然存在处分行为。因此本案中被害人具有处分意思,也做出了处分行为,正是行为人此前的欺骗行为使被害人处分财物,最终导致其财物损失。
(二)盗窃罪之否定
传统意义上的盗窃罪和诈骗罪“泾渭分明”,盗窃罪是指窃取财物,是违背被害人意志的,而诈骗罪是基于被害人的自愿处分,一般情况只要区分导致财物损失的行为由谁做出即可。但在“盗”“骗”交织的案件中,区分的关键则着眼于行为人实际占有财物的时间和行为。
本案中,是被害人的行为导致其丧失占有,被害人基于自愿,做出了处分行为。在行为人借得手机后,将手机带离现场,被害人不加阻止的,则应当认为财物的占有、支配关系已发生变化,被害人实际已因受骗而对财物做出错误处分。就本案而言,被害人将手机交给行为人,只是财物的交给行为;行为人将手机带离现场,被害人未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持对财物的支配,此时才完成了财物的处分行为。
之所以认为被害人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是从两方面来看。其一,被害人采取的眼神控制是无效的。首先,眼神控制本身是具有较大个体差异的,在司法实践中难以衡量和定性;其次,我们不能夸大眼神控制的能力,如果无限延伸,是否眼神所及就是控制所及呢?这与常理不符,也难以形成稳定的标准。本案的结果已经强有力论证了眼神控制之无效。其二,客观环境使得停留在原地的被害人不能有效控制,这一部分已经在诈骗罪之成立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有支持者认为既然被害人交付手机的行为没有导致丧失占有,之后也没有积极的处分行为,那么应该将被害人财物损失的后果归因在行为人离开现场的行为。这其实是狭隘地限定了处分行为。犯罪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处分财物的行为自然也不限于作为,还包括不作为和容忍。正是被害人容忍行为人去远距离、长时间单独使用手机,使得被害人丧失了占有。同时,这也是对行为人离开现场的误解,绝大多数侵财犯罪中,行为人都不会在取得财物后留在案发现场;诈骗罪的行为人更不会一直留在被害人身边,因为被害人时刻都有意识到被骗的可能,也有追回财物的空间。
四、案件结论
在本文引用的案例中,李某虚构了事实,利用吕某的同情心,使其将手机自动交付给李某;并与黄某在免提过程中谎称要买水果,吕某同意李某独自一人前往百米之外的便利店。通过还原客观环境并结合吕某的客观行为,足以证明社会第三人和吕某都能意识到同意的后果——丧失对手机的占有,但是吕某仍旧点头同意,并且除了停留在原地注视李某,没有采取其他措施。李某通过花言巧语将手机“骗到手”,最终达到“骗到走”的目的,无论是案件的起点,还是获得手机占有的时间节点,起到关键作用的都是李某的花言巧语和吕某的错误信任,所以本案应当认定为诈骗行为。
注释:
①蒋铃.论诈骗罪中处分行为的内涵.法治研究,2012年第9期.
②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第891页.
③刘明祥.论诈骗罪中的交付行为.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
④周光权,李志强.刑法上的财产占有概念.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⑤王玉珏.《刑法中的财产性质及财产控制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