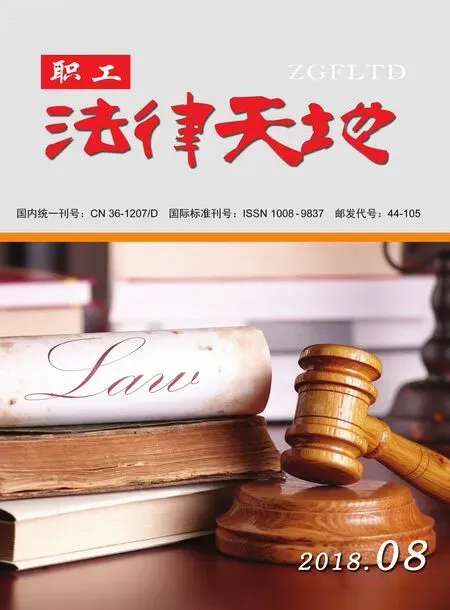论行政诉讼的权利保护必要性
崔友生
(710054 西安市碑林区城市管理局 陕西 西安)
正所谓有权利必有救济,不管对权利如何进行界定,如果说只要是存在权利必然会有司法救济制度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可是对于具体的权利侵害,究竟是否一定要启动司法救济制度也是存在疑问的。即便说存在原告资格,还是要取决于是否存在权利救济亦或者是权利保护的必要性。我国在实施立案登记制之后,行政诉讼案件受理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自从2016年开始,法院也针对频繁使用权利保护必要性的说理来对一些不值得保护的诉讼请求进行驳回。
1 刑事诉讼中权利保护必要性产生于功能
权利保护必要性这一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是在将来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得到承认之后才出来的概念。众所周知,行政诉讼脱胎于民事诉讼,最开始的民事诉讼只存在给付诉讼,而那时的诉讼意义则仅限于变更私人之间现实的利益必要情况,为此,诉讼也是以强制执行为作为首要前提。在经过不断实践之后,我们发现只要对权利关系进行确认才能很好地解决纠纷,而对将来不改变的利益进行明确也存在一定的意义,所以确认之诉也就因此而得到了认同。可是,假设我们没有在法律上对可请求确认的对象进行限制,当事人不管是任何请求都能够起诉到法院,让法院进行确认,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对利益来进行确认,以此来限定确认之诉对象。在我国司法实践之中,权利保护必要性所存在的功能大多是消极意义上的,假设原告的起诉缺少权利保护必要性,法院也就会将其起诉判定为驳回,这也是权利保护必要性的传统功能之一,即指的是产生排除效果,也可以将其称之为消极性程序利用规制,这一功能的存在能够避免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也能对原告起诉要求判决权能进行限制。除此之外,权利保护必要性也具备积极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能够存在权利保护必要性者,法院都会对相关案件进行受理同时做出裁判,这样就能切实的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2 行政诉讼中权利保护必要性审查与限制
权利保护必要性本身就存在诉讼的排除效果,而对于缺少权利保护必要性在现实之中的审判实践中本身就存在多样化表现,所以在审查以及适用上也就不得不慎重。
2.1 权利保护必要性的审查
在其他国家对于缺少权利保护必要性者,法院大多会以诉讼判决的方式来进行驳回。对于究竟是否存在权利保护的必要性,法院需要按照自身职权来进行调查,结合所提供事实资料来进行相关判断,而判断的基准时间则是以事实口头辩论终结为准。可是,在我国法院上则是以裁定的方式来对起诉进行驳回,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所谓的驳回起诉其本身就是为了能够让那些不符合法定条件,亦或者是说不存在权利保护必要性的起诉进入到实体审理。这一种裁定方式满足于权利保护必要性之诉讼要件的基本定位,可是事实上来说即使是适用裁定的方式,在原则上来说也应该要做好开庭审理,特别是对于初审法院而言,不能只是以书面审查的方式来对其进行驳回裁定。在《行政诉讼法》之中的第 51 条明确的提到过,对于满足起诉条件的案件一定要登记立案,换而言之,也只有满足于起诉条件的才能真正进行登记立案。另外,在我国对于起诉条件其本身就包括了起诉要件以及本案要件的具体内容,这也促使起送条件高阶化与实质审查封闭化,从某些方面来说弱化了立审分离这一功能,从而也就无法确保诉讼要求得到充分的保障。
2.2 权利保护必要性的适用界限
权利保护必要性从某些方面来说,本身就是为了能够确保行政诉讼制度能够作为可靠、简易的权利保护方式实现有效运用。可是,值得警惕的是,权利保护必要性本身存在泛化、不明确等问题,假设适用不当还有可能会影响诉权的实现。因此,为了能够有效地避免要件被滥用,法院一定要坚持给予而不是拒绝权利保护,并且在适用时还需要具有一定的限制。而对于适用界限其主要包含了补充适用、有限适用以及说理适用这三种,其中,补充适用则是属于权利保护必要性项下的制度已经被明确的专门制度,像是一事不再理,在专门化制度不能实现适用的时候,才能适用概括性的权利保护必要性要件;而有限适用则不仅体现在权利保护必要性与其他诉讼要件关系上,同时也表现在诉讼要件审查和本案审查的关系上;说理适用则是鉴于权利保护必要性属于不够明确的概念而衍生的,在适用的时候需要进行充分的说理,这从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法院利益衡量的一个过程,能够起到限制法院裁量权,让司法具备较为良好的公信力以及公正性。
3 结语
综上所述,权利保护必要性这一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就是确定有效率、实益、适时、正当的权利救济契机,就我国行政诉讼实践情况来看,因为权利保护必要性经常会和诉讼的排除效果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对其进行判断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最好是以原告诉讼实施利益作为基础进行详细的斟酌,之后再进行适当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