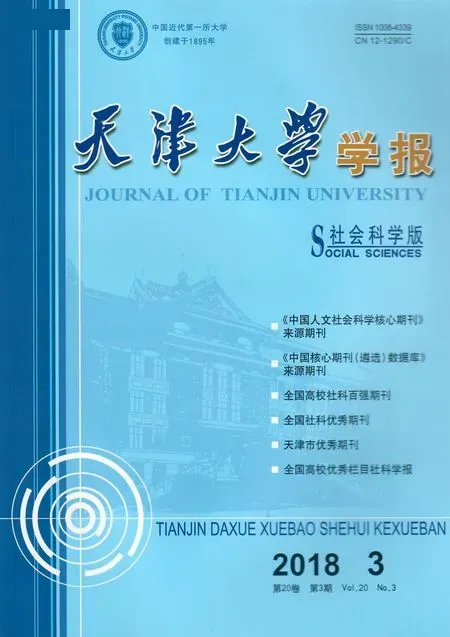近代家庭教育与儿童性别认同探析
侯 杰, 常春波
(1.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天津300350; 2.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300350)
费孝通将家庭的抚育分为社会性抚育和生物性抚育两种。其中,社会性抚育作为社会知识的传递过程,对儿童的成长十分重要:“因为人不能个别地向自然去争取生存,而得在人群里谋生活。一个没有学得这一套行为方式的人,和生理上有欠缺一般,不能得到健全的生活;他也就没有能为人类种族绵絮上尽力的机会。”[1]因此,家庭对儿童的意义不仅在于物质供养,更在于对其思想的塑造和人格的养成。在性别认同方面,家庭对儿童的影响经历着其身体和思维成熟等一系列重要过程。学界目前虽然对近代不同地域、阶层的家庭教育内容及其时代变化,已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尚缺乏性别视角的观察和分析。本文拟根据报刊、自传、日记等资料,从不同方面分析近代家庭教育对儿童性别认同的影响,以及伴随时代变化,家庭性别教育理念等所产生的更新和变化。
一、 知识技能培养中的性别分工
家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一项内容是帮助儿童学习、掌握特定的知识技能,如读书、习字、手艺、武功等。士绅之家的男孩在入学之前多有接受启蒙的经历。一般情况下,这种知识的传授往往是由祖父、父亲、叔伯或兄长等男性长辈进行。曾国荃5岁即进入家塾学习,17岁时又随父进京,接受时任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教导1年有余。曾国藩在日记中留下许多指导九弟曾国荃学业的记录,其中不乏因其进步而感到格外欣慰:“进境不少,可喜。”[2]即使生病,曾国藩亦不敢有所懈怠:“九弟悔从前读得不好,若再不认真教他,愈不能有成矣。余体虽虚弱,此后自己工夫尚可抛弃,万不可(不)教弟读书也。”[2]110在一些男性长辈早逝或在外谋生的家庭中,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母亲亦可代行必要的启蒙工作。胡适、黄仁霖、黄炎培、赵元任等人幼时均有接受母教的经历。
女孩在出嫁之前,要在家庭中学习针黹、蚕桑、纺织、烹饪等技能以应对未来的婚姻、家庭生活。《礼记·内则》中指出未婚女性需要培养的技能包括:“女子十年不出,姆轿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4]清廷颁行的癸卯学制,亦将女性教育归为家庭教育之类,而否定其入学接受教育的权利:“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对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故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或受母教,或受保姆之教,令其能识应用之文字,通解家庭应用之书算物理,及妇职应尽之道,女工应为之事,足以持家、教子而已。其无益文词概不必教;其干预外事、妄发关系重大之议论,更不可教。故女学之无弊者,惟有家庭教育。”[4]除许多学校排斥女性外,一些民间工艺的传承更严格遵守“传男不传女”的规矩。
近代来华传教士发现中国女性在教育等问题上所遭受的不平等对待,创设了一批教会女学。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兴女学的重要性。主张维新的知识分子纷纷在报刊发文,为女性教育摇旗呐喊。在教育实践上,一批中国人自己创设的女学堂在江浙、天津等沿海地区相继出现。1907年的《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正式承认了女性教育的合法地位。民国以后,北京及南京政府亦承认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教育权利。但是在家庭生活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等性别观念依旧阻碍着许多女童迈向学堂的脚步。1906年《大公报》报道,南京“风气虽已日渐开通”,但“奈何人心固蔽,仍不免多所疑阻迂拘之士,每不肯遣其妇女入学堂”[5]。毛彦文幼时在学塾中遭先生体罚,向祖母哭诉,祖母却勃然大怒:“女孩子不能考状元,读什么书?”祖母命毛彦文的父亲将老师辞退、停办家塾,毛彦文因此而失学[6]。遍观20世纪初流传于中国各地的儿歌,亦很难发现女性在学校中的身影和支持女性教育的声音。河北儿歌《栀子花》勾勒了一幅符合主流价值观的生活图景:“栀子花,靠墙栽,男儿聪明女儿乖;男儿聪明读书好,女儿聪明做花鞋。”[7]女性只能将人生的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月奶奶,明晃晃,开开后门洗衣裳。洗的净,浆的光,打发哥哥上学堂。红旗插在俺门上,看看排场不排场。”[8]
由于男孩被视为家庭血脉、财产的继承人,所以父母多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并对其严加要求。男孩因此而背负着沉重的压力。流传于江苏南京地区的儿歌《先苦后甜》就描写了一个下层读书少年理想的人生路径:“一事无成实可怜,二八青春正少年。三餐茶饭常常缺,四季衣裳不周全。五更想到天明亮,六亲无靠向谁言。七篇文章中何用,八字生来颠又颠。久想后来无好处,十样倒有九不全。八月初八头场进,七篇文章赛金钱,鹿鸣宴摆归家转。五凤楼前结綵簷。四方齐看游街客,三尺红罗披在肩。两朵金花头上插,一举成名中状元。”[7]3-4男孩时常会因为行为举止不当而遭受父母的体罚。陈翰笙在回忆录中提及,5岁时曾因念书走神而被父亲扇了耳光[9]。可见,重男轻女的性别偏见不仅损害了很多女孩的权益,也让男孩背负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儿童活泼的天性和创造力往往因为不符合长辈的意愿而被冠以“不务正业”的帽子,遭到遏制和打压。丰子恺幼年时因画画而遭到父亲的责打:“第二天上书的时候,父亲——就是我的先生——就骂,几乎要打手心。”[10]尽管图画在清末的教育改革中被列为小学课程之一,更在蔡元培倡导的美育教育中占重要地位,但在以科举功名为导向的传统教育序列中,丰子恺绘画的兴趣和天赋并不能得到父亲的认同。拜重男轻女观念所赐,不仅女孩的诸多权益惨遭践踏,男孩也遭受不亚于女孩的各种束缚。由此可见,性别歧视造成的是对男女两性儿童的损害。
二、 性别气质的塑造
家庭教育的另一项内容是社会经验的习得和思想意识的塑造。父母等家长在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对儿童思想意识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林语堂认为童年时期家庭生活对自己成人后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为最大。我对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力。”[11]
受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的影响,传统家庭教育认为人际交往、社交礼仪以及与社会现实有关的经验是男孩成长过程中需了解的内容。这些经验往往由男性长辈向孩子们灌输。包天笑回忆童年时父亲的教育方式:“父亲对于我的教育,主张开放,不主张拘束。”因此,他曾被父亲带到“花船”、鸦片馆中,虽然只是走马观花式的观察,也算得是一种特殊的启蒙,粗略体察了世间百态。他还经常被父亲派出去给亲戚拜年,学习社交礼仪[12]。与男孩自幼参与社交生活相比,女孩所受到的教育则是要安守本分,生活在有限的家庭空间内。唐代宋若昭所著《女论语·学礼章》即对女性在外抛头露面的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当在家庭,少游道路。生面相逢,低头看顾。莫学他人,不知朝暮。走遍乡村,说三道四。引惹恶声,多招恶怒。辱贱门风,连累父母。损破自身,供他笑具。”[13]在传统女教的训诫下,女性只有固守在闺房的方寸天地之间方能保全自己和家族的声誉。王映霞对童年时祖父的训导始终不能忘怀:他“对于我,有时只顺口说一句:‘少跑少跳,女孩子要文静些。不然会给别人说闲话,说你不懂规矩的’”[14]。
除交往礼仪、行为举止外,家庭教育对儿童更重要的影响在于品格之养成。在各种回忆录、自传中时常可见童年时父母之谆谆教诲对个体生命轨迹的深刻影响。黄炎培对幼年时母亲的训斥记忆犹新:“记得还有一次,受到病里的母亲大大的训斥。她说:‘奎(我的小名),你看!谁在那里闲荡过日子?公公怎样?婆婆怎样?爹在外边怎样?农民一个个忙得怎样?只有你既不读书,又不做事,怎么对人得起?’这一场病中大训斥,使我直到老年,永远忘不掉。”[15]陈香梅亦在回忆录中对母亲之耐心教诲有所记述:“母亲认为,女人应该有女人的气质,随时随地像个淑女。记得有一次我在母亲面前说一位穷酸表兄的坏话,她当即告诉我:‘淑女应该居心仁厚。’”[16]可以发现,父母对儿童之教育内容,会因性别而存在差异:对男孩强调责任心、上进、拼搏,对女孩则要求温柔、宽容、忍耐等。父母对于男女儿童教育方式之不同,反映出家庭及社会对男女儿童的未来期望也存在巨大差异。
父母、祖父母等长辈对于男童、女童的态度差异亦会对儿童造成一定的影响,形成心理定势。从陈香梅之回忆中可以看出,父亲无意中流露出来的重男轻女观念对她的影响:“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又患大感冒,父亲跟母亲说:‘这孩子真麻烦,三天两头病,干脆把她送人算了。’也许父亲说话无心,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却留下了阴影,我想父亲不爱我,因为我不是个男孩。”[16]10陈香梅父亲少年时出国留学,获得牛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并在北京大学教授英文,思想尚且如此保守,当时普通中国人重男轻女观念之根深蒂固亦可想而知。因重男轻女而导致的家庭内部矛盾,在女童心上留下的阴影更是挥之不去。苏雪林认为童年时的不幸经历,对其忧郁性格的形成有直接联系。她坦言:“我自幼性野,又不善服勤,祖母最憎恶我,常叫我母亲骂我打我,所以我幼时并无生趣可言。”不仅如此,“我生有一种忧郁病,始自童年,至老不衰”,“想必就是不愉快的童年所贻留给我的唯一礼物”[17]。
毋庸讳言,家庭环境因人而异,儿童成长的经历也不完全相同。在一些较为开明的家庭,女孩也能获得与男孩同等的地位和权益,男孩也能够有自由成长的空间。杨步伟的祖父杨仁山提倡废缠足,因此自己就未曾缠足,被家中亲戚嘲笑“大脚片”。自幼极受宠爱的她在顽皮程度上不亚于男孩,还曾跟随叔叔、哥哥到秦淮河上的花船上叫局。父亲以“儿子”称呼她,到10岁时她的性别认同仍旧十分模糊:“因为那时我自己不太清楚我是男子还是女人,我还穿男装,所以自己莫名其妙,新女衣我一点不想要。”[18]军人家庭出身的冰心自幼在比较开放的氛围中长大,并未受到传统女教的束缚:父亲不仅让她从小穿男装,使她免于缠足、穿耳之痛,还教她骑马、打枪[19]。汪曾祺认为父亲很随和,对自己的学业关心而不强求,“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十几岁时常与父亲对坐饮酒、抽烟,父亲总是先给他点上火,还开玩笑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认为父亲的教育方式对自己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后辈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20]但这种开明的家庭毕竟属于少数,大多数儿童依旧在传统家庭中忍受着性别不平等所带来的痛苦。
与学校教育相比,家庭教育对儿童的影响更多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的,其对儿童性别观念的构建作用巨大。近代中国人对传宗接代一事极为重视,认为多子多孙是福气,并不代表儿童可以在家庭中接受良好的养育和教育。
三、 情感教育和性启蒙
传统中国社会有关儿童情感和性的教育是缺失的,特别是程朱理学对人的欲念采取压制态度,将性与道德品行捆绑在一起,使其成为无法启齿、避之不及的事。但儿童随着自身生理、心理的逐渐成熟,自然会对男女之情产生好奇。在缺乏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儿童只能通过各种途径获得朦胧、片面,甚至是不健康的认识。赵元任在回忆录中坦率地承认自己幼时曾偷读过家中大人的书,并从电影的亲密镜头中了解了一些性知识[21]。陶钝回忆,当父亲知道自己能背诵《西厢记》后,认为“我的性知识已经很发达了,对于男女情爱很能理解”,便为其订了婚[22]。除书籍、电影等途径外,性知识还在同龄人之间口耳相传。梁实秋回忆幼时学校:“有些人各自秉承家教,不只是‘三字经’常挂在嘴边,高谈阔论起来其内容往往涉及‘素女经’,而且有几位特别大胆的还不惜把他在家中所见所闻的实例不厌其烦的描写出来。讲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津津有味……性教育在一群孩子们中间自由传播,这种情形当时在公立小学为尤甚,我是深深拜受其赐了。”[23]
20世纪以来,西方、日本科学著作被大量翻译、引入中国,其中介绍性知识的书籍亦为数不少。这些书籍从卫生医疗的角度对性和身体进行科学解析,打破了国人对性讳莫如深的禁忌,并进一步为知识分子批判传统礼教提供了依据。谭嗣同在《仁学》中曾提出,对于性应像治水一样采取疏导的态度,而非盲目压制,“且逆水而防,防愈厚,水力亦愈猛,终必一溃决,泛滥之患,遂不可收拾矣”。在他看来,“遏之适以流之,通之适以塞之,凡事盖莫不然,况本所无有而强致之,以苦恼一切众生哉”。中国人不应对性抱有羞耻的态度,“男女构精,特两动之机,毫无可羞丑”[24]。加之近代以来女权运动的开展和男女平等观念在学校教育等领域影响的扩大,传统贞操观和男女大防遇到了挑战。基于“强国保种”的现实需求,在传统礼教的道德枷锁逐渐瓦解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对性教育愈加重视,并在民国以后掀起了一股大力提倡性教育的浪潮。在学校教育方面,性教育被纳入课程之中。1913年《教育部公布中学校课程标准》中规定中学第2学年的教学内容须包括“生理及卫生”,即“人身之构造”“个人卫生”和“公众卫生”,每周3课时[25]。
这一时期的教育者认为,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家庭对儿童性教育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孩子的好奇心,父母应给予耐心和坦诚的指导,不能故意回避和打压:“在我们中国,谈到性的问题,一般人往往认为玄妙,神秘。年老一辈的人,会摆出严肃,森严的架子,不屑谈起;年轻的人要想讲而不敢公然谈论,酝酿在胸,莫明所以,往往在同伙中窃窃私议:这样,便把这问题愈弄得神秘玄妙了。”他们提出,父母及早对儿童进行性教育,将会对其以后的性别观念产生积极影响:“毫无隐讳地实施性教育,这不仅可以做儿童将来结婚的指南针,更能使儿童在将来全部生活中,对于异性抱着一种好的观念。”同时,父母亦应注意自身言行对儿童的影响:“母亲或其他保护者之间,若在儿童面前不加留意地交换了些猥亵或不经心的行动,都能损坏了柔美的儿童的性情,或称为终世的疮痍,永远不得平复。”[26]
与学校性教育不同,家庭性教育是伴随儿童整个成长阶段的。教育者认为,父母需要时刻注意,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1934年《现代父母》中《爱情及其指导》一文指出了儿童性意识觉醒的几个阶段。一是儿童七八岁时,会迎来第一次的性爱发动,将对父母的爱转移到同龄人身上去。如果是独子,或是家中没有异性兄弟姊妹,父母“一定要使他和亲戚或邻居的异性朋友交际,来补足这种缺陷”。二是在儿童后期,儿童对异性的态度又会发生转变,“男女互相反拨着,男孩讨厌女孩,女孩惧怕男孩”,即所谓“同性爱的时期”。三是从少年少女期的末期到青年期的初期,为第二次性爱醒觉的时候,“女子注目男子,而男子也想亲近女子”。父母对儿童的性教育“在第一次的性爱发动时,即幼儿期和儿童期,就应该加以根本的指导了”[27]。
对于父母在儿童性教育中的不同分工和角色,教育者也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在幼年时,母亲是进行儿童性教育的最佳人选:“我们感到母亲对儿童的关系最是密切,她们对于全人类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26]16及至青春期,“女子固然可仍由母亲教导,男孩子则须由父亲教导。”[28]因为此时个体正处于从儿童向青年的过渡时期,生理、心理皆发生很大变化,父母需要给予特别关注。对于女童,母亲要向女儿讲解月经的知识以及如何在月经期间保护身体,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在解释过程中“应特别指出月经的效能和性质,使她明了这种现象的目的和意义,那末,一个寻常的女子对此便不致有紧张惶恐的情绪,即有感觉不便之处,也必能乐于接受了,因为这于她成立家庭和生育子女的计划,是极有关系的”。对于男孩,父母亦应使其了解女性的生理知识:“我们要对于一般父母进一言:今日的男孩子对于女孩子的事,决不是毫无所知的,他的朋友不像女孩们之能保持缄默,他们喜欢谈论女人。作父母的,必须察看他们的儿子在这方面所得到的智识是否健全,不能纯取放任态度。”[29]
可以说,民国时期知识界对儿童性教育的讨论大多汲取了西方教育学、医学及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虽然在理论上已达到一定的深度,但未免过于理想化,传播范围也不够广泛。这些知识主要通过书籍、报刊方式传播,而能够接触到这些媒介并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和经济能力的家庭十分有限。
四、 结 语
近代中国儿童自孕育至成婚这一时期所经历的性别社会化过程,在学校和家庭中既不同步,也不均衡。在近代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主张维新变法的男性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意识到“男强女弱”、“伸男抑女”的传统性别文化使占中国人口一半的女性在身体和思想上受到了极大束缚,因此兴起了废除缠足、创办女学的新潮流,以培养“国民之母”,追求国家富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男女社交公开和男女同校的潮流再次对传统礼教形成了巨大冲击。因此,近代女性解放起步较早、进展较快的领域之一当属新式学校。
反观家庭教育,男尊女卑的性别制度,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和严男女之大防的性别区隔依旧在大多数家长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贯穿于近代儿童的成长过程之中,影响着儿童的性别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批知识分子提出应关注和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即所谓“儿童的发现”。在反抗父权专制的社会浪潮中,女性和儿童成为近代知识分子关注的两大弱势群体:“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30]但与蒸蒸日上的学校教育相比,家庭教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不显著。由于时局、经济及文化等因素的限制,能够自觉改变传统性别观念、尊重儿童人格的家长还属少数。家庭本是儿童成长的港湾和保护伞,可是在传统观念依然强大的近代中国,儿童从家庭中感受到的除了温暖外,还有不尽的心酸。
[1]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50.
[2]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一[M].长沙:岳麓书社,1994:80.
[3] 郑 玄.礼记正义[M].孔颖达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169.
[4] 佚 名.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M]//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395.
[5] 佚 名.女学堂之大阻力[N].大公报,1906-05-08.
[6] 毛彦文.往事[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5.
[7] 黎锦晖.中国廿省儿歌集[M].中国台北:东方文化书局,1974:7.
[8] 佚 名.重修信阳县志[M]//丁世良,赵 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232.
[9]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4.
[10] 丰子恺.车箱社会[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39.
[11]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1-3.
[12]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中国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48-57.
[13] 宋若昭.宋尚宫女论语[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68.
[14] 王映霞.王映霞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10.
[15] 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7.
[16] 陈香梅.陈香梅自传[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15-16.
[17] 苏雪林.苏雪林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5.
[18] 杨步伟.一个女人的自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7:35-47.
[19] 冰 心.童年杂忆[M]//范伯群.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62-63.
[20] 汪曾祺.汪曾祺自述[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6-40.
[21] 赵元任.赵元任生活自传[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65.
[22] 陶 钝.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50.
[23] 梁实秋.梁实秋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22.
[24] 谭嗣同.谭嗣同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2:326.
[25] 佚 名.教育部公布中学校课程标准[M]//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730.
[26] 青 山.妈妈!我是怎样来的[J].现代父母,1933(6):16-18.
[27] 雪 影.爱情及其指导[J].现代父母,1934(9):28.
[28] 朱江萍.儿童性教育的探讨[J].现代父母,1937(4):13.
[29] 沈秋宾.青春期的少女[J].现代父母,1934(10):7-8.
[30] 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1918(6):574-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