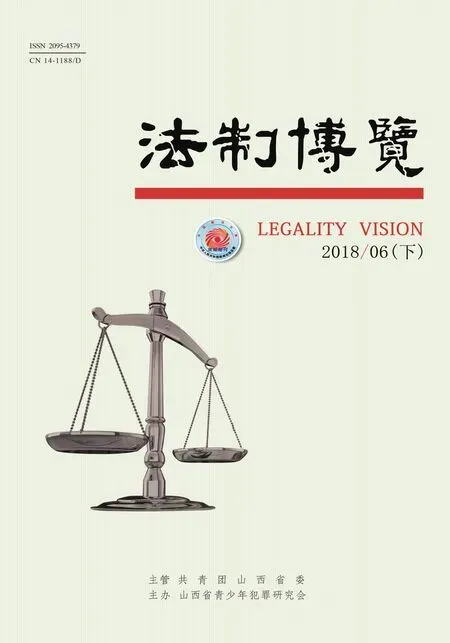《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认识论思想的研究
芮培松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一、“现实的个人”的内涵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1]这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有关实践问题的经典表述,这包含了对以往哲学家的批判,是马克思对“只用词句来反对词句”的不满。无论是老年黑格尔派还是青年黑格尔派,他们都看出了以往的宗教观念对人的束缚。尽管老年黑格尔派将这些宗教观念思想看作是社会的毒瘤,但更愿意将这些纳入无所不包的黑格尔体系当中去解释说明,这无疑透露出老年黑格尔派的保守性。而青年黑格尔派虽然对固有的宗教体系深恶痛疾,却无非只是“词句”上的斗争。因此,马克思写到:“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做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
相对于马克思来讲,他更愿意从人出发,确切的来讲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或是从实践出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明确写到:“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1]这是基于以往认识论基础上的新的起点,是对以往认识论的扬弃。“现实的个人”不再是孤立不变的个人,而是运动中的个人,他与现实世界互为对象,共同构成了一对矛盾综合体,正是这样一对矛盾的辩证运动,才构成了千变万化的物质世界。在这里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的个人”实际上是将以往旧唯物主义中一般意义上的人引入到实践当中来,与现实的客观世界发生关系,从而能够进行现实的物质生产劳动的人。而这也就是与以往旧唯物主义的最大不同之处,“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1]因此我们分析“现实的个人”必须上是既具有对象性又具有能动性的个人。第一,对象性是确保“现实的个人”得以确立的首要前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到:“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人不再是局限于普通直观而无所作为的人,人是处在现实世界当中的人,是处在现实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马克思抛弃了旧唯物主义的感性直观,将人看成是对象性存在物,更否定了唯心主义的精神主体,将人纳入到现实体系当中来。首先,“现实的个人”以自然界为直接对象,人产生于自然界,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其次,人类以人类社会为间接对象,这是因为人在以自然界为直接对象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人类社会,并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第二,能动性是确保现实的个人得以确立的必要前提。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出现,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就在于发挥了能动性,使自然之物为我所用。而人类社会则更加充分的打上了人的足迹。所以,马克思在评判费尔巴哈时曾提到,如果人类停止了能动性的发挥,停止了物质生产的劳动和创造,那么自然界以及费尔巴哈自己生活的物质世界将很快发生改变直至消失。但由于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出现,所以人类发挥能动性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必然受到自然力量的制约,因此能动性中又隐藏着制约性。如果我们说对象性确保了人不是孤立的个人,那么能动性则确保了人为了需要而改造自然的能力。
也正是在“现实的个人”的基础之上,人的现实的认识能力得以展现。人在从事现实的物质生产从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不断的发现着现实世界的规律,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驱使人们去发现更多的未知领域,因而也就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因此我们说,“现实的个人”在物质生产当中表现出来的实践能力成为了人的认识能力的基础。马克思的实践观念区别于以往唯心主义实践的普遍性,也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对实践进行感性直观层面理解的局限性,实践开始与现实相融合,表现为一个横向上认识水平的不断扩充的过程,以及纵向上历史的现实发展过程。
二、人类社会生活的四个方面
实践是人的实践,人在实践中获得了认识,规定了人的本质。所以对实践问题的深化就势必要对“现实的个人”展开一番研究。“现实的个人”是有生命的个体,这必然要求要满足生存的需要,“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但人类的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人的需要也是无穷无尽的,生产力的发展又会引发新的工具的出现,这一切又会不断的促使新的需要的出现。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实践的角度出发去解释历史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这也就否定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对历史发展的“合理”解释。这种“合理的解释”在黑格尔那里是一种抽象思辨,黑格尔的历史是精神发展的历史,而在费尔巴哈那里,则是一种抽象现实,历史更加表现为一成不变的历史。“他们的历史思辨所以特别热衷于这个‘史前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他们不会受到‘粗暴事实’的干预,而且还可以让他们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创立和推翻成千上万的假说”[1],因此马克思说:“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马克思坚决否定思辨哲学对于人的现实活动的理解,思辨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不过是处在虚假历史中的自我演绎,它脱离实际,脱离物质生产生活,因此也就无法真正说明现实历史的发展。人在满足自然需要的基础上,需要进行人口生产,历史是“现实的个人”的历史,历史的发展必然由人来推动,没有“现实的个人”也就无所谓人的历史。马克思认为生命的生产表现为“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两个方面。“自然关系”下的生命的生产是一种正常的生理活动,它保证了为了满足生活需要不断与自然发生交换关系的主体的存在,也进而保证了物质生产的顺利进行。“社会关系”下的人口生产表现为人口共同活动下的生产力的发展,这因为社会关系来源于人类劳动过程中的相互交往,这就表现为一定的生产方式,反过来生产方式又与共同活动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将这种共同活动方式称为“生产力”。生产力表现着社会的发展状况,人类历史也就必然表现为人类活动的历史。
马克思对于物质生活需要、物质生活的再需要和人口生产的分析,实际上描述了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三个基本方面,进而马克思又发现了社会关系当中最基本的交往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第四个方面。马克思结束了对这四个方面的考证之后,又重点考察了意识的产生问题。马克思指出:“意识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社会的产物也就是人在与他物的对象性关系中获得的认识,因此意识的产生来源于物质生产关系当中的交往关系。但一开始意识总是带有简单的性质,直到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以及分工的出现,意识才摆脱了现实的世界,开始涉猎形而上的领域,也正是由于分工,精神生活从物质生活中分离出来。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的最大特点就在于用“物质生产”、“物质交往”去解释思想、观念、意识等认识活动的产生。这也就必然的对黑格尔“自我意识”外化的观点进行了否定,意识不是物质乃至历史的起点,更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与此相反,意识是依赖于物质条件而产生的,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意识没有自我的形成历史,它只是物质活动的附庸产品,因此人们在改造自然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同时,也推动着人类意识的发展。不过与此同时马克思也高度赞扬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对于自我外化的推动作用,只不过黑格尔的劳动只是局限于精神范围内的抽象劳动。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这正如“非对象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一样,人的活动的存在决定了意识的存在。所以无论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对上帝是否存在的论证,还是到近代唯理论者将知识的最终诉求归结为上帝的恩赐,这所有的一切不过是自我的冥想,思想观念上的新的产物不过还是要以现实经验为依据的。所以马克思说:“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1],马克思否定了意识的先验存在,也就颠覆了以往理性哲学家的理论起点。
马克思从现实的生产实践的角度去理解意识的本质问题,也就是说离开了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物质交往关系,意识也就无法形成。它不是费尔巴哈所讲的人仅仅是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而与外在自然界有着一条鸿沟,而是以其能动性沟通了人与自然从而促使意识的产生;也不是如黑格尔将自然看作是“自我意识”抽象劳动的结果,而是将抽象的精神劳动看作是与自然界相对应的现实的生产劳动。以此为基础,马克思通过引入实践的感念解决了二元论和物质与意识本末倒置的问题,他承认了实践与意识的相互统一的关系,也就解决了意识的产生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历史领域的运用
马克思对认识论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引入历史领域,解开了“人类历史之谜”。马克思在评价费尔巴哈的哲学时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1]在前文的分析当中我们实际已经提到了费尔巴哈最为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否定了人的能动性,从而否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仅仅赋予了人的直观世界的能力,而对于外在自然费尔巴哈则认为那是“始终如一”的东西。马克思反驳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费尔巴哈强调的“感性对象性”是对黑格尔唯心历史观的克服,但他也仅仅局限于“感性对象性”而没有任何发挥,也就陷入了与黑格尔的“精神抽象”相对的“现实抽象”,这根本无法解决现实历史的运动。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的同时却丢掉了黑格尔身上最为宝贵的财富——辩证法。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时曾说:“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成果。”[2]发现了历史发展的奥秘,只不过他所发现的奥秘是应用于抽象的精神领域,他将人的发展看作一个过程,人的历史是其劳动的历史,更加确切的说是精神劳动的历史。黑格尔从绝对精神入手,进而通过外化为自然界,再进入人类社会,解释整个历史过程。费尔巴哈由于批判黑格尔的需要,过分的强调了认识主体的客观性,而忽视了他的能动性。因此费尔巴哈在无法解决现实矛盾的情况下,便只能求助于“普通直观”和“高级的哲学直观”的“二重性直观”。
可是我们不得不说,费尔巴哈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是前进了一大步的。费尔巴哈不满足黑格尔所说的自然乃至人的历史只是“自我意识”外化的产物,他力图将自然界和人的历史“现实化”,试图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在他看来,哲学的真正出发点应该是自然与人,这样的人是实际的存在而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但费尔巴哈的人并非是“现实的个人”,好像只是具备人的生理特征而已。他的人只是“感性对象”,而不具备“感性活动”的能力。他没有关切人的正常生产生活,没有关切生产生活基础上的交往活动,更没有从周围的环境出发去考察人。也就是说费尔巴哈依旧没有摆脱旧唯物主义的真正束缚,不了解实践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作用,将认识理解为一种既成的“感性直观”,对于社会生活的本质也就无法真正的理解,因此在解释历史运动时就会陷入唯心主义。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基础上借鉴黑格尔的“劳动”,从而引入实践概念,真正的解释了现实的历史的运动。黑格尔最为积极的地方就在于他把世界看成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自我意识”外化为自然界,然后进入到社会,最终在精神层面实现了对自身的认识。马克思把握住了这个辩证否定的原则,这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是推动“自我意识”逐渐完善的真正奥秘。马克思将辩证的否定引入进唯物主义,将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改造为现实的人。黑格尔实际上颠倒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他将绝对精神上升为主体,而人只不过是从属物,是一种主观的设定,这样他也就无法真正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费尔巴哈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把人从绝对精神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但是他的人只具有受动性,人与自然处在此岸与彼岸。马克思结合他们的优势,将人理解为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体,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能动性绝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领域的能动性,而是现实领域的能动性。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无疑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在实践的基础上获得认识。这种认识首先表现为对对象性存在物的认识,其次表现为对运动中的对象性存在物的认识。而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促使对象性存在物运动的重要外在条件之一依旧是人类的实践活动,而反过来运动中的对象性存在物又需要再实践去重新认识。实践在这里就既表象为获得对对象性存在物初次认识的基础,又表现为对在经过实践本身改造发生变化的对象性存在物进行重新认识的基础。实践促使对象性存在物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自然和人类社会便是现实的发展过程即历史的过程,而实践的发令者又是“现实的个人”,同时对象性存在物又指向的主体也是“现实的个人”,所以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人的历史发展的过程。
因此实践不仅是认识世界的基础,也是改造世界的基础。人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改变了周围的世界,创造出了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资料。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人摆脱了自然的束缚,人不再是对自然无能为力,相反自然成为了人活动的产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成为了主客体的关系。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引入“工业命题”来说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对客观自然界产生的影响,工业的存在才使得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成为满足人需要的自然。实践沟通了主体与客体,主体因为客体成为了主体,客体因为主体成为了客体。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因此,实践具有主体性、对象性、能动性以及目的性。人是“现实的个人”,那么通过人的劳动而形成的现实的自然也就是人化的自然,人的历史也就存在于“现实的个人”改造自然的过程当中。马克思通过引入实践既弥补了黑格尔的劳动只存在于精神领域的局限性,又解决了费尔巴哈无法沟通人与自然的现实问题。所以马克思的认识论不仅仅只存在于自然领域,而且也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这样就把唯心主义在历史领域的最后一个大本营拔除了,构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认识论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更是与现实的历史息息相关。马克思的实践是以人为基础的实践,人的实践活动必然与现实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如果认识仅仅停留在感性层面是无法认识到马克思认识论的深层内涵的,因此只有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才能更准确的把握马克思认识论的真正革命内涵。
[ 参 考 文 献 ]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3]杨河.马克思认识论基本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2002.01.
[4]徐双溪.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研究[D].华侨大学博士论文,2017.
[5]武晓亮.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研究[D].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