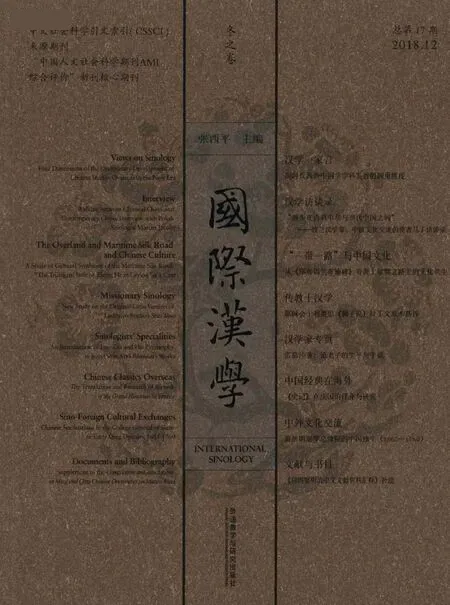日本平安初期汉文《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九首初探
一、《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九首的作者与创作背景
日本平安初期唐风盛行,有日本学者将其称为“国风暗黑时代”①小岛宪之:《国风暗黑时代の文学》(补篇),东京:塙书房刊,平成十四年,第3—4页。,小岛宪之指出这个说法最初由学者吉沢义则在其讲义中提出,而他的学生误读了“暗黑”之意,以致后来一些日本学者将此理解为汉唐文化对日本本土文化的遮蔽。小岛宪之认为将其称之为“汉风赞美时代”更为妥帖。在外来文化和固有文化的融会贯通方面,这个时代比前一时代有更大进步。②坂本太郎著,汪向荣等译:《日本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3页。从天皇到朝臣、贵族乃至整个知识阶层都热衷学习汉文化,通过多种渠道接受大量汉籍和汉唐思想,对汉唐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效仿与借鉴。内藤湖南在其演讲稿《平安朝时代の汉文学》中提到这个时期大部分的日本文化受汉文化的影响而发展。③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全集》(第九卷),东京:筑摩书房,1969年,第89页。在文学方面,贵族文人普遍使用汉字,创作了数量惊人的汉诗文作品,形成日本汉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光辉时代。④川口久雄:《平安朝の汉文学》,东京:吉川弘文馆,平成八年(新装版),第26页。从公元814年到827年,短短13年间完成了三部敕撰汉诗文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和前两部纯粹汉诗集相比,《经国集》在内容和文类上都有很大的扩展,此总集共20卷,仿《文选》体例,分体辑录赋17篇、诗917首、序51篇、对策38篇。其所录年限从庆云四年(707)至天长四年(827),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多年,作者也多达178人。《经国集》之名源于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集中所录作品之丰富显示出彼时日本文学的繁荣,而通过对此集所收作品的分析,亦可大体了解奈良至平安初期的汉文学全貌。
很多时候人们关注和研究平安初期的汉诗,往往忽略了赋这种与诗并存的古老文体。王晓平指出:“从现存的文献来看,辞赋传入日本并对日本文学产生影响,最迟不晚于7世纪后半期……对日本奈良平安文学研究的结果,已经无可争辩地证实,七八世纪的日本贵族文士通过传入日本的《文选》等中国书籍,曾孜孜不倦地钻研秦汉以来的中国辞赋。”①王晓平:《亚洲汉文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8页。《经国集》中赋类的出现,说明当时人们已经熟练掌握这种文体。赋在《经国集》中位于卷首,这是受《文选》编排的影响,同时也表明日本接受者对赋这种文体的重视。肖瑞峰认为,以诗赋取士的制度曾在平安朝短暂实行,“将诗赋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始于嵯峨天皇弘仁十一年(820)”。②肖瑞峰:《中国文化的东渐与日本汉诗的发轫》,《文学评论》1998年第5期。按照肖氏的说法,在《经国集》诞生前七年,日本已经开始实施“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日本是否实行过科举制度值得商榷,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官吏录用考试中加入了诗赋科目内容。《本朝文粹》卷第二《应补文章生并得业生复旧例事》记载:“今须文章生者,取良家子弟,寮试诗若赋补之,选生中稍进者,省更复试,号为俊士,取俊士翘楚者,为秀才生者。”③大曾根章介等校注:《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朝文粹》,东京:岩波书店,2003年,第145页。汉文诗赋创作成为录用官员的一种必备技能,无疑凸显了赋这种文体在当时的重要性。现存《经国集》中收录赋17篇,虽在数量上无法与汉诗相媲美,但作为一种独特且创作技巧要求很高的文体能在异邦流传生存下来,无疑具有非凡的意义和价值。
在《经国集》卷一辑录的“赋”类中,有九首同题的《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以下简称《赋秋可哀》)。重阳节是日本平安时期的一个重要节日。天皇亲自举办重阳宴,始于天武天皇十四年(685),而将其发展为重阳诗宴,则始于嵯峨天皇弘仁三年(812)。④陈巍:《日本平安时期重阳诗宴的来源及其仪式》,《文化遗产》2014年第3期。嵯峨天皇时期经常在重阳日举行诗宴,彰显君臣同乐之精神,也用这种方式沟通君臣、贵族之间的感情。这类重阳唱和的作品在敕撰三集中颇多,如《重阳节神泉苑赐宴群臣》《九月九日侍宴神泉苑》等。这种以天皇为中心的酬唱活动,必然导致《赋秋可哀》九首带有一定程度的颂圣色彩,如“皇欢爰发,叡兴自生……钧天奏乐,罄地寿祯”(菅清公)之类,这是应制之作的共同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核心内容还是述写秋天的哀愁。这一组作品由太上天皇(嵯峨天皇,809—823年在位)牵头倡导,另八位作者应和而作,他们分别是淳和天皇(时为东宫,823—833年在位)、良安世、仲雄王、菅清公、和真纲、科善雄、和仲世、滋贞主(平安初期一些崇尚唐风的臣子模仿汉人,将名字改为三个字,如良岑安世改为良安世),均为皇族或朝廷显要。
为分析的方便,兹选其中两首照录如下:
秋可哀兮,哀年岁之早寒。天高爽兮云渺渺,气肃杀兮露团团。庭潦收而水既净,林蝉疏以引欲殚。燕先社日蛰岩岭,雁杂凉风叫江洲。荷潭带冷无全叶,柳岸衔霜枝不柔。寒服时授,熟稼杂收。
秋可哀兮,哀草木之摇落。对晚林于变衰兮,听秋声乎萧索。望芳菊之丘阜,看幽兰之皋泽。年华荏苒行将阑,物候蹉跎已廻薄。楚客悲哉之词,晋郎感兴之作。
秋可哀兮,哀秋夜之长遥。风凛凛,月照照,卧对风月正萧条。窗前坠叶那堪听,枕上未眠欲终宵。到晓城边谁捣衣,冷冷夜响去来飞。不是愁人犹多感,深闺何况怨别离。□蹉四运易行迈,惆怅三秋绝可悲。⑤與谢野宽等校注:《日本古典全集:怀风藻 凌云集 文华秀丽集 经国集 本朝丽藻》,东京:现代思潮新社,2007年,第118页。
(太上天皇)
秋可哀兮,哀秋候之萧然。潘郎可哀之叹,楚客悲哉之篇。虫惨悽而声冷,露咄咜而泣悬。班姬酷怨因轻扇,青女微霜以旻天。却细絺于云匣,授寒服于香筵。
秋可哀兮,哀卉木之洒落。具物缩悴,爽气辽廓。烟断崇岭,云抽幽谷。淮南木叶声虚散,上苑枫林阴未薄。幕下巢空燕早辞,湖中洲喧雁始归。节灰尚如此,情人谁不悲?
秋可哀兮,哀秋晖之易斜。岩莚扫叶,藤杯挹霞,朗吟听竹树,夕照倒水砂。脆柳暮兮观疏星,蓻兰蔚兮闻浓馨。物色蹔虽使人戚,潭花但喜益仙龄。⑥《日本古典全集:怀风藻 凌云集 文华秀丽集 经国集 本朝丽藻》,第121页。(滋贞主)
这种君臣唱和的文学活动滥觞于中国汉代的柏梁列韵,并在曹魏、南朝发展成君倡臣随、同题共作的文坛风习。嵯峨天皇等人依循此例,表现出对汉唐文化传统的衷心钦慕。《重阳节神泉苑赋秋可哀》九首在结构、句法、意象等方面,亦全方位沿袭摹写汉晋诗赋,而其直接模仿的范本则是西晋夏侯湛的《秋可哀》。
二、形制表现的模仿与创新
毋庸置疑,《赋秋可哀》九首是作为“赋”收录于《经国集》的,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文人将此类作品认定为“赋”而非诗。这一文体观与早期中华文化在日本的传播途径密切相关。平安初期日本文人对汉诗文的学习,主要是通过《文选》和唐类书来实现的。“那时的贵族文士便学会了利用《文选》、类书中收载的赋以及有关事物典故语汇,以作为制赋的材料。”①王晓平:《亚洲汉文学》,第319页。《文选》未录夏侯湛《秋可哀》,但《艺文类聚》载其全文,《初学记》亦予以摘录。更为重要的是,两书均将其归入“赋”类,且《初学记》还辑录了夏侯湛的另一篇作品《秋夕哀》,称名为《秋夕哀赋》。显然,当时日本知识阶层就是通过这两部类书接触到夏侯湛的《秋可哀》等作,从而将其作为“赋”来接受和摹写的。夏侯湛《秋可哀》全文如下:
秋可哀兮,哀秋日之萧条。火回景以西流,天既清而气高。壤含素霜,山结玄霄。月延路以增夜,日迁行以收晖。屏絺绤于笥匣,纳纶缟以授衣。
秋可哀兮,哀新物之陈芜。绸筱朔以敛稀,密叶摵以陨疏。雁擢翼于太清,燕蟠形乎榛墟。
秋可哀兮,哀良夜之遥长。月翳翳以隐云,时笼笼以投光。映前轩之疏幌,炤后帷之闲房。拊轻衾而不寐,临虚槛而褰裳。感时迈以兴思,情怆怆以含伤。②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3页。
全文分多章、每章以骚体的“兮”字句领起,此格式由张衡《四愁诗》开创;晋初傅玄《历九秋篇》在继承此格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共十二章,形成“九秋三春”的历时结构;夏侯湛此作亦由“兮”字句领起,分为三章,依次写秋日、秋物和秋夜,其主要句式则为六言的赋体句,而非《四愁》之七言、《历九秋》之六言的诗体句,形成一种亦诗亦赋、非诗非赋的特殊体式,其《春可乐》等作亦同此类。正是因为这种文体的兼综性与边缘性,造成了其文体界定不像《四愁诗》《历九秋篇》那么简单清晰,而显得非常困难,故《艺文类聚》《初学记》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视之为“赋”,而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则将其作为“诗”辑录其中。曹道衡论此篇曰:“从文体上说,和赋基本相同。但没有铺张的笔法而着重于抒情,又有点类似于杂言诗……这类作品在辞赋史和诗歌史上都有重要意义。”③曹道衡:《汉魏六朝辞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I989年,第138页。
当然,最能代表汉唐赋体文学的应该是《子虚赋》《二京赋》《三都赋》等描写京都宫苑的大赋,但平安时期日本文人有关中华文化的知识储备和语言表达能力,尚不足以驾驭需“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后汉书·张衡传》)、动辄数千言的宏大赋篇。夏侯湛的《秋可哀》作为西晋诗赋杂糅合流的新体,运用短小的篇幅、精巧的结构、轻灵错落的句法和疏朗飘逸的意象,描写秋天的各种景物,并抒发因季节更替、时光流逝而引发的惆怅与轻愁。此类作品去除了汉晋大赋的雕琢堆砌之弊,却兼有赋的整饬与诗的灵动,也极大地降低了撰写的难度;同时,那种写秋景闲愁的清逸雅致,非常契合彼时宫廷化、贵族化之日本文人群体的审美情趣。因此,嵯峨天皇君臣九人,“想‘拊衾’于湛词”(淳和天皇《赋秋可哀》),满怀热情地对夏侯湛此作进行认真的摹写,从而给人们留下了这一组在日本汉文学史早期称得上优秀的诗赋作品。
《赋秋可哀》组赋对夏侯湛《秋可哀》的模仿首先表现在篇章结构上。这九篇赋作尽管篇幅有长短之别,描写内容也围绕秋天而各有侧重,但除两篇外,其他七篇均与夏侯湛之作一样由三章构成,每章以骚体句“秋可哀兮”领起,通过此句一定间隔后的重复,形成鲜明的节奏和一唱三叹的吟诵效果。而且《赋秋可哀》九篇大体遵循夏侯原作每章各述一事、彼此内容基本上不交叉的原则。如嵯峨天皇所作,首章写“年岁之早寒”,集中铺叙天高气肃、水瘦山寒、露重霜降的气候;次章写“草木之摇落”,侧重描绘草木摇落、晚林变衰、秋风萧索的景物;末章写“秋夜之长遥”,则着力刻画抒情主体在秋风秋月中卧听坠叶、感离思亲的惆怅忧伤。又如滋贞主首章写“秋候之萧然”,次章写“卉木之洒落”,末章写“秋晖之易斜”;和真纲先述“岁时之如流”,次述“物候之凄清”,末述“短景之微阳”。除良安世之作按初月、仲月、季月的“三秋”时间顺序外,作者们大抵都遵循夏侯湛《秋可哀》先秋候、次秋物、末秋夜的叙事结构,层次非常分明。其次,夏侯湛之作先述秋候秋景、后抒感秋叹秋之情的书写脉络,在《赋秋可哀》组赋中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虽然其中所抒之情多有“献千秋之寿爵,荷万代之天休”(仲雄王)之类的谀上颂圣之意,或“虽对秋天之凄景,何异冬日之可爱”(科善雄)之类的反悲为喜之志,但都承袭了夏侯湛原作先景后情、卒章显志的抒写模式。
《赋秋可哀》对夏侯湛原作的模仿也表现在语词意象的选择上。夏侯湛描写秋天萧瑟悲凉,主要通过选用中国先秦汉魏诗赋中最典型、最常见的传统意象来表达和渲染,如火星西流、天清气高、壤含素霜、天凉授衣、密叶陨疏、大雁南飞、月夜遥长、感时兴思等等,而这些传统意象,也构成《赋秋可哀》九首状景抒怀的基本要件。其中以天气高爽、霜露降临、草木凋零三类意象的运用最为普遍,九篇作品无一例外予以描写;而流火、授衣、大雁、夜长等,亦在各篇频繁出现,只不过有的是对原作直接沿用,有的略加改造,表现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
《赋秋可哀》组赋在形制与表现上对夏侯湛原作进行了刻意而全面的模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平安初期的贵族作者们全然缺乏创新的意识。事实上,他们突破原作的意愿和努力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从句式方面看,明显突破了原作除每章起首为骚体外,全篇皆用六言赋体句的局限,而增加了相当数量的诗体句和《九歌》型的骚体句。九篇作品计有七言诗28句、除领起句“秋可哀兮”之外的骚体22句,同时还运用了少量三言、五言和六言的诗体句以及四言的赋体句。多种句式特别是五、七言诗和骚体的介入,使夏侯湛原作全用六言赋体句的单调之弊得以大大改善。如滋贞主之作,篇中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交错而出,赋体、诗体、骚体杂糅而成,句法参差灵活,音韵流转优美,将赋体的铺陈、诗体的流利和骚体的韵致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特殊的美学品格。这种写法与南朝谢庄《山夜忧吟》、沈约《岁暮愍衰草》、萧绎《鸳鸯赋》等作如出一辙。显然,《赋秋可哀》的作者虽沿袭了西晋夏侯湛《秋可哀》的题材、结构和主要意象,但在句式方面却又借鉴了南朝诸家诗赋“新变”的路数,从而对原作有所超越。
从表现手法上看,《赋秋可哀》组赋对典故的频繁运用,亦可视为作者们创新求异思维的一个表征。语典如“庭潦收而水既净”“哀草木之摇落”(太上天皇),出自宋玉《九辩》“寂寥兮收潦而水清”“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却暑絺于匣里”(和真纲)、“却细絺于云匣”(滋真主),出自夏侯湛《秋可哀》“屏絺绤于笥匣”;“气肃杀兮露团团”(太上天皇)、“望朝露之团团”(菅清公),出自江淹《四时赋》“秋风一至,白露团团”。事典如“潘郎可哀之叹,楚客悲哉之篇”(滋真主),分别用潘岳作《秋兴赋》、宋玉作《九辩》事;“伤曹子之恻怛,叹淮王之感忧”(和真纲),前句用曹植作《秋思赋》事,后句取《淮南子》“木叶落,长年悲”①萧统编,李善注:《文选·文赋》:“《淮南子》曰:木叶落,长年悲。”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上册),1983年,第240页。之义。他如“秋夜捣衣”“班姬秋怨”“九月授衣”“万物迴薄”等等,汉魏六朝诗赋中不少与“秋”相关的典故,被用于《赋秋可哀》九篇之中,这与夏侯湛原作基本不使用典故的情况大不一样。嵯峨天皇等贵族文人喜用典故的热情,一方面验证了他们对汉唐文化的钟爱;另一方面也说明,通过认真研读《文选》和《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典籍,平安初期日本文人中的先行者,在汉文化知识的积累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三、生命悲感的相通与相异
任何民族之文学母题的形成,都必然有其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认知作为基础。在中国传统的阴阳二元哲学体系中,春天被视为阳气萌生、万物勃发的季节,而秋天则为阴气渐兴、万物凋零的节候,故“秋”在方位配置上属西方,在五行属性上为“金”,主杀;而在人们生活经验的感性范围内,入秋则天气转凉、植物衰败,动物脱毛、大雁南飞,且年岁将尽,呈现出一种肃杀凄冷的氛围,与春天之温暖和煦形成鲜明的对照。《礼记·月令》云孟秋之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仲秋之月“盲风至,鸿雁来,玄鸟归”,季秋之月“霜始降”“草木黄落”,①《礼记·月令第六》,选自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以可感的特征性景物作为秋季的标签。古代诗赋中常见的“悲秋”母题,便是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
中国文学作品对秋的表述,可追溯到《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七月》)、“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四月》),以及《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兮木叶下”等简单的描写,但真正成为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母题,则是在宋玉的《九辩》中完成的。《九辩》起首以一大段篇幅,通过细致描写草木摇落、天高气清、燕归蝉寂、大雁南游、蟋蟀宵征等富有秋季特征的景物,以及登临送别、薄寒中人、羁旅无友、惆怅自怜等凄苦的心理感受,表达作者贫士失职、年华消逝却老大无成的忧伤和悲怆,因而被后人称为“千古言秋之祖”②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页。。此后在魏晋南朝,以“悲秋”为主题的诗赋大量出现。《艺文类聚》卷三“岁时上”辑录此时期写“秋”的诗赋共35篇,而曹丕《燕歌行》《感离赋》,曹植《秋思赋》《遥逝》,陆机《叹逝赋》,陆云《岁暮赋》等名作尚未涉及,可见实际的作品远多于此数。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哲人思考的重要问题。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日渐兴盛,《易经》“立象尽意”的方法被普遍地运用到文学创作领域。陆机《文赋》曰:“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③陆机:《文赋》,选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2013页。成公绥《故笔赋序》曰:“举万物之形,序自然之情,即圣人之心。”④成公绥:《故笔赋序》,选自《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796页。流转更替的四季、落叶柔条等自然万物,都成为人们叹逝兴感、明志阐理的触媒和载体。这种以“象”表“意”的写法在西晋文坛成为一种流行的模式,尤以“悲秋”主题的诗赋最为典型。而魏晋“因物兴悲”的抒情方式,与日本古代的“物哀”传统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物哀”作为文学理论是日本江户时期国学家本居宣长在其著作《紫文要领》中提出的,同时又在《石上私淑言》中指出和歌是因“物哀”而产生。⑤本居宣长著,子安宣邦校注:《排芦小船·石上私淑言》,东京:岩波书店,2003年,第192页。他将“物哀”看作是日本传统文学独特的追求目标,无论是物语还是和歌都以“物哀”为宗旨。本居宣长认为凡是从根本上涉及人的情感的,都是“あはれ”(哀);人情的深深感动,都叫做“物のあはれ”(物哀)。⑥本居宣长著,王向远译:《日本物哀》,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第160页。不过,这些“物哀”的论述是在对中华文化排斥和抗衡的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学者姜文清认为,“物哀”是“平安时代以来日本民族的一种对客观外界做出的以情感反应为主导的认识方式,是一种文艺创作和欣赏中的审美感情的表现”。⑦姜文清:《东方古典美:中日传统审美意识比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2页。叶渭渠明确指出:“古代文学思潮从哀到物哀的演进,是经紫式部之手完成。”⑧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1页。实际上,平安初期日本贵族创作的汉文学,与和文学一样是日本文学的组成部分,其中所蕴涵的“物哀”意味,比《源氏物语》要早约两百年。“物哀”作为日本民族的审美传统,其出现是诸多因素促成的。他们对生命的短暂与无常感受尤为深刻,自然界的每一细微变化都会给他们带来心灵和情感上的颤动。反映在文学上便是对具有季节性和流动性特征的物象格外关注,“秋季在四季中最短,且最富有微妙的变化,同时秋的物景最适合日本人情绪性、感伤性的抒发,最适合寄托人的忧郁和寂寞之情,宣泄悲哀的情绪”①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5 页。。因而秋季常常是催生人们物哀之情的季节,正如本居宣长引用的和歌所说“想要知物哀,须等秋天来”。②《排芦小船·石上私淑言》,第187页。
“哀”是人的主观情绪,“物”是外在的客观形态,借助“外物”来表达、寄寓或烘托“哀情”,“物哀”的审美理想才能完成。西晋的夏侯湛,才高位卑,在混乱流离的时代仕途不顺,“以人当秋则感其事更浑,亦人当其事而悲秋逾甚”③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960页。,乃循潘岳“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秋兴赋》)之意,作《秋可哀》篇,由“哀新物之陈芜”到“感时迈以兴思,情怆怆以含伤”,时光的飞逝、季候的变化使作者联想到生命之短暂、命运之不济、功业之难成,由此发出生命的悲叹和情感的“哀伤”,而其悲叹和哀伤之情,则主要是通过对天清、素霜、疏叶、大雁等富有秋季特征的外物来抒发的。这种以外物写哀情的手法,与本居宣长提出的“物哀”美学理想的实现路径——“将心中感情寄托于目之所及,耳之所闻之物,是物哀的表现,是托物言情之作”④《日本物哀》,第167页。完全一致。
与夏侯湛原作一样,《赋秋可哀》九首的共同主题是时光消逝的生命之悲。为了表达这种“哀情”,作者们借助从汉晋以来的“悲秋”诗赋和《艺文类聚》等类书提供的素材,精心选择与秋天相关的各类意象,如燕、雁、蝉、蟋蟀、文鱼之类,而尤其偏好植物,兰、菊、柳、枫、竹、桐、芦等花卉草木,是《赋秋可哀》九首使用最为频繁的意象。以“菊”为例,这组作品中有七首出现了此意象:
望芳菊之丘阜,看幽兰之皐泽。(太上天皇)
粤采萸房之辟恶,复摘菊蕊之延期。
(淳和天皇)
兰幸佩以擢秀,菊忆杯而含馨。(菅清公)
霜凝菊兮萧萧,露留荷兮冷冷。(和真纲)
窈窕採萸兮鸳鸯席,簪缨饮菊兮翡翠楼。(良安世)
菊方新而欲暮,兰虽败而犹芳。(科善雄)
柳敛眉于天苑,菊映色于故栏。(和仲世)
屈原《离骚》云:“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潜《饮酒》其五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于季秋九月开花,“百卉凋瘁,芳菊始荣,纷葩晔晔,或黄或青”(钟会《菊花赋》)。菊花是秋天特有的物象,形态缤纷,凌霜华茂,又可作为饮品,使人延年益寿,而且被人们赋予了高贵、正直等美好品格。其突出的季节性、涵容的丰富性,以及汉唐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特殊钟爱,很容易引发平安初期热衷于汉文化的皇室贵族文人的浓厚兴趣,从而在他们的诗赋中得以频繁运用,在借菊花(物)表达迁逝之感、生命之悲(哀)的同时,也寄寓其某种高于世俗的心志与情怀。九月九日重阳节在日本被称为菊花节,嵯峨天皇还专门写过咏颂菊花的《重阳节菊花赋》。此后,菊之高贵禀性又衍生出威严的寓意,成为日本王室的象征,乃至渐次融入日本国民之文化—心理结构,被当作其民族性格的形象写照。
正如川端康成所述,“大约一千年前的往昔,日本民族就以自己的方式吸收并消化了中国唐代文化,产生了平安王朝的美”⑤川端康成:《日本文学之美》,载叶渭渠译:《川端康成谈创作》,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303页。。《赋秋可哀》九首虽全面继承了汉唐“悲秋”题材写景抒情、借物表哀的传统手法,然细加分析,二者亦略有差异。汉唐以“悲秋”为主题的诗赋,通常都不是单纯地抒发迁逝之感,往往兼有怀才不遇、命途多舛、思亲念乡、叹逝悼亡等多种情绪。如潘岳《秋兴赋》以宋玉《九辩》悲秋起兴,将送归怀人之恋、远行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之叹逝、登山怀远之悼近的人生“四戚”糅合其中,再加上仕途失意的忧伤、超越尘俗的幻想,使赋作以“悲秋”为主线的情感增添多条副线,显得极为复杂。《赋秋可哀》九首则不是这样。淳和天皇之作因当时在惨烈的宫廷斗争“药子事件”后,面对暗藏的危机焦虑不安,故用班婕妤“秋凉团扇”典故,借女子失宠的幽怨喻指宫廷斗争,并希望“粤采萸房之辟恶,复摘菊蕊之延期”,通过佩戴茱萸以驱邪恶、服食菊蕊以安寿命,在“悲秋”的同时抒写了较为复杂的情感。除此篇外,其他八首所抒之情皆为相对单一的时光流逝之叹,充其量掺杂一点“钧天奏乐,罄地寿祯”(菅清公)、“虽悲零落之序,欣奉名辰之昌”(和真纲)之类对君主的感戴颂谀之意,或有意无意透出的不同于普通人的闲淡雅致。这种情感的单一和闲雅源于作者们皇室贵族的特殊身份,以及奉诏应制的创作动机。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上层,世袭制保证了其政治上的稳定特权和经济地位,因而罕有普通文人仕途、物质生活等世俗忧虑;发起酬唱的核心人物嵯峨天皇,既是君临天下的至尊,也是醉心中华文化和魏晋风流的热情追随者。参与唱和的其他作者不能不遵从天皇之作的主旨和模式,很难有太多的发挥与扩衍。
抒情的单一性也决定了《赋秋可哀》九首与汉唐“悲秋”诗赋在审美风格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后者因“悲秋”涵容的政治性与社会性而充满着痛苦、焦灼乃至愤懑等趋于激烈的情绪;前者则哀而不伤、悲而不痛,其哀情非常轻淡,甚至透出一种闲雅与雍容的气息。王向远认为“物哀”排斥了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抽象说理这三种因素,而只是面对单纯的人性人情以及风花雪月、鸟木虫鱼等大自然。①王向远:《日本古代文论的千年流变与五大论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如嵯峨天皇之作,先用秋露、秋蝉、秋霜、秋草等景物渲染肃杀凄苦的氛围,后用秋夜、未眠、捣衣、深闺等意象抒写年华老去的叹惋。作品虽在音乐般的优美吟唱中明确传达出了作者对时光消逝、青春短暂的不绝哀情,却几乎没有不满、怨愤和抗争,“日本的‘物哀’的情感表现是发乎情、止乎情”②王向远:《“物哀”是理解日本文学与文化的一把钥匙》,载《日本物哀·序》,第19—20页。,不会对情感的善恶加以区分,只是写出人的真实情感并将这种情感表现出来,③本居宣长著,子安宣邦校注:《紫文要领》,东京:岩波书店,2010年,第156页。自然也无意通过某种方式去转移或消解这种似乎注定与生俱来的生命之哀。这与同为君王的汉武帝“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秋风辞》)的慷慨抒怀迥然不同,即使与汉晋“悲秋”诗赋中情感最为平淡的夏侯湛《秋可哀》相比,也少了几许厄于世情的抑郁和沧桑。平安早期的日本崇尚儒学,圣德太子时期的《十七条宪法》中,就提到“以和为贵”,显然儒家中和温雅、“哀而不伤”的诗教对此时期贵族文人平淡冲和的哀情表达是有很大影响的,同时日本民族文化中特别突出的唯情传统和实际上已经基本形成的“物哀”审美理想,也在《赋秋可哀》九首这种风格中得到了足够的体现。笔者认为,物哀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表现时光消逝的生命之哀时,因为将生命易逝视为一种不可违逆的宿命,故抒情主体不仅把“哀”情融入物象之中,淡化了“我”的主体身份,而且也消弭了世俗化的功利之心和与命运抗争的激烈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说,《赋秋可哀》九首深情哀婉而又平淡冲和的风格既是中华汉唐文化与日本民族文化结合的产物,也是日本早期“物哀”美学初步形成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