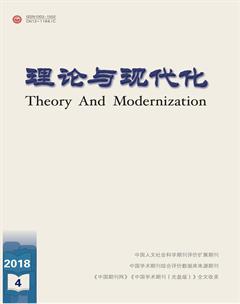通往程序之治
摘要:自主的程序理性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程序是现代社会具有基础性作用的正式调节机制,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程度与程序化程度正相关。中国古代重视程式步骤,现代程序观念形成演变则跌宕起伏,程序化建设与现代化进程大致同步:20世纪头20余年第一次现代化高潮中诞生程序观念,但混同于程式和手续,受制于权力和道德;20世纪后20余年并延续至今的第二次现代化高潮中再次生发程序观念,在科学技术程序、经济管理程序的推进下,政治法律程序注重从中国的实然状态出发,尊重科学理性,保障公民权利的正当程序获得较广泛认同,有效提升了国家社会治理能力。接下来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程序化建设,要在程序表达中更好协调权利、权力和道德三者之间的系统关系。
关键词:程序化;程序观念;现代化;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8)04-0046-07
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范畴,中国的程序观念在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从无到有,日益具有现代性,但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应具有的程序观来要求,则还力所不逮。本文在简述程序化与现代化呈正相关关系的基础上,简析中国程序化建设与程序观念现状,概览其跌宕起伏的演变过程,冀望裨益于中国的程序化与现代化进程。
一、程序化与现代化正相关
人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一直都与基于程序理性的程序行为、程序方法、程序观念息息相关。经过长期的进化,某些动物的行为具有了一定的步骤性,即能够有次序地重复某些行为,这是自发的、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的某些特定行为,比如马克思主義所说的利用工具的劳动,不仅具有次序性和重复性,而且有意识地、理性地将这种步骤和机制固化下来,并根据不同环境选择不同的行为机制、程序方法去改造世界。早期人类之所以形成原始社会,不仅是因为人能够像蚂蚁、蜜蜂[1]、狼群一样相互协作,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更是因为人能够借助语言有意识地、理性地将社会性的实然协作机制固化下来,形成具有一定约束力和指导性的社会规范(如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制度主要体现为程序行为)。我们将人和人类社会起源就具有且必须具有的这种理性称为程序理性,它是人以其自主意志对有次序的可重复行为的有意识提炼和升华,体现在人的劳动和语言中,与之相伴而生、互补互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从动物界中脱颖而出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人类自主的程序理性及其所决定的具体的程序行为、具体的程序性劳动。这是人的第一次飞跃。
人的第二次飞跃是进入轴心文明。所谓轴心文明,现代化理论重要代表人物艾森斯塔特认为是“超越秩序”对“世俗秩序”的积极构建,即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出现了一种新类型的知识精英,他们意识到必须按照某种“超越的”(用史华慈和张灏等人的话来讲是“退而瞻远”,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跳出来看自己、看人、看人类社会”)观念积极建构世界[2]。这种超越观念的制度化,导致对社会内部的关系结构进行广泛地重新安排(如孔孟用仁义等儒家道德观念对周礼的重新赋义及其内部关系的重新排序)。正是这种超越理性所重新安排的结构和程序,形成了中国、印度、希伯来、希腊四种文明型态,人类进入轴心时代。人类文明初步成型、成熟的关键,是人用更具自主性的超越理性构建了新的制度程序,人的意志更积极地参与到了程序的构建当中。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皇帝君主和宗教权力对人的自主性的压制,轴心文明兴起之初人的程序理性并未得到充分发挥。无论是中国的礼法一体化宗法礼治制度体系,还是西方的罗马法、教会法,都在实现皇权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时过分强调了权力意志的强制性,而被统治者的自主性空间非常小,所以只能称之为程式强制,而不能称之为程序治理。到了近现代社会,人的个性与自由得到尊重和彰显,而人以其自主性、反思性进一步解放自我,通过科学的受控实验程序改造自然,通过自然法的法律程序改造社会,人类进入现代文明。这是人的第三次飞跃。据《大英百科全书》载,英文的程序(procedure)一词大约产生于1611年[3]。这正是现代性如朝日般破晓而出、冉冉升起的年代。在现代性三大要素中,科学理性的具体体现,是科学实验程序;公民权利的实现,也要靠具体的程序,比如经济权利的实现要程序性地履行合同契约;政治权利的实现要程序性地制定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程序理性的种子在现代性中才真正破土而出,现代性与程序可谓两者交相辉映、交互融合。
如果把17世纪的现代性和程序理性比喻为花蕾,那么接下来的现代化和程序化就是花朵绽放的过程。18世纪以来,以现代科学和法治为载体,程序精神随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程序化对于推进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程序、法制程序的深化和普及,工业发达国家形成了制度化管理并启发泰罗于19世纪末提出了科学管理程序即“泰罗制”。1889年,作为形容词的procedural一词产生,标志着现代程序观念已经确立,并已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我们把程序观念的普及过程,把社会程序性程度提高的过程,称为程序化。研究表明[4],泰罗科学管理的实质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对实然机制的程序化、具体化、系统化,它对现代社会影响深远,极大地推进了经济政治管理能力的提升。从20世纪初福特的流水化生产线到ERP(流程再造),乃至21世纪德鲁克的知识管理,都坚持程序化科学管理的精髓[5];从韦伯的理性化科层制政府到熊彼特的程序民主,到今天以新制度主义为重要方法论基础的治理变革,作为正式机制的程序日益受到重视。由上,我们可以说,现代文明展开的过程,即现代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程序理性在科学、经济和政治等各领域展开的过程,即科学程序化、管理程序化、治理程序化的过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程序化程度,体现了它的现代化程度,程序化与现代化正相关。
应当承认,程序化在伴随着现代化开疆辟土的过程中,也曾被偏颇地理解为形式理性乃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并借助科学主义形成了对现代社会的形式强制,从而在管理实践上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并受到各种批评。教训和批评一定程度上矫正了程序化的航向。二战后现代社会的自我改善,不仅汲取了第一次现代化的程序化管理经验(比如,在1952年形成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这一新词组,帮助实现战后经济腾飞),而且通过计算机技术的提高和普及,使程序成为现代科技、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础平台。20世纪下半叶,形容词procedural又多了名词的属性。西蒙有限理性下的满意决策(主要是程序性决策)观念浸人经济管理和公共管理理论;布里奇曼操作观被重新定义为收敛的操作主义[6];罗尔斯条件契约论的程序化条款提供了新的思路[7]。在又一个千年之交,哈贝马斯提出了程序性协商的理性重建方案[8]。亚洲学者、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最新潮流,如我国学者季卫东提出了程序和契约收敛于动态平衡的新程序主义。把这些不同领域中的思潮综合起来考虑,或许表明了程序理性的一种雄心,即要想把人类从无思想和道德虚无感中解救出来,要想重振理性雄风,还是要回到现代性的原点,乃至人类文明的原点去重建程序理性。而这雄心的哲学基础,就在于程序理性拒绝预设真理或终极价值,但又相信相对真理和情境道德,它通过程序与规律(真理)的相互论证以及实然机制与应然程序的良性互动,收敛于某种动态平衡的社会稳态。
综上可以得出两点初步结论:1.现代程序观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它与(科学)理性、个人权利和契约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2.现代程序与现代社会的发展休戚与共,它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理性的科学、政治的民主和程序化管理这三种形式分别呈现于文化、政治和经济这三个社会子系统中。了解上述观点,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按照西方中心主义去模仿或者采取东方主义式的拒绝,而是为分析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明确了一个程序化的参照系。事实上,它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与我们存在距离的参照系,而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和程序化进程产生过、并正在产生着切实而深刻的影响的参照系,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甚至可以说,我们必须认真研究。
二、中国程序命题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搜索电子版的《四库全书》发现,古代有“步骤”“程式”“程规”等词,但没有“程序”。同西方在现代性初生之时出现procedure一词一样,中国也是在现代性刚刚开始萌芽的20世纪初(1907-1913年)出现“程序”一词。这似乎表明中国的程序观念在一开始就具有现代属性,也似乎昭示着我们的程序化将随着现代化的演进而演进。
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中国程序问题的特殊性马上就会凸显出来。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性源起和现代化历程,相对世界其他许多国家来说要特殊和复杂得多,与其紧密相关的程序和程序化问题,想必不会单纯和简单,必然会存在许多特殊而复杂的细分问题。比如,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程序一词,但是否一定没有程序治理的传统?如果有,这种传统在哪些方面与现代程序观念类似?哪些方面可以作为程序资源予以继承和光大?又有哪些方面与现代程序观念存在本质不同?哪几个关键词可以代表中国古代的类程序观念?这些关键词在第一次现代化之前的1830-1900年,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是如何应对的?其内涵有无变化?再比如,1900年后的第一次现代化高潮中出现了“程序”这个词,是否表明中国的现代程序观念就此诞生?这个时期的程序观有多少现代属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哪些方面与现代程序存在隔膜?当时的人们对程序观念有清晰的自觉和深刻的反思吗?还比如,在随后的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进程中,我们的程序观念受到哪些影响?最后,在20世纪后20余年兴起的第二次现代化高潮中,我们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如何看待计算机程序?它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法管理程序有影响吗?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程序化建设有什么样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与现代程序是一种什么关系?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我们的程序观念是一种什么状况和水平?
对于上述许多问题,学术界并不能给出一份清晰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对于复杂的程序观念及其演变历史,我们还缺乏应有的重视,缺少系统的研究,这使得我们对程序的认识不仅相对肤浅,而且比较混乱。比如,在什么是“程序”这个基础性的问题上,人们都还缺乏清晰的认识。普及度很高的《辞海》对程序的解释是“按时间先后或依次安排的工作步骤。如工作程序;医疗程序。”[9]200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也基本类似:“行事的先后次序;工作步骤。”[10]综合看来,程序就是做事情的“步骤”。这个解释似乎没有问题,但值得深究的是,两本辞书对“步骤”又是如何解释的呢?居然又都回到了“程序”上。如《辞海》说步骤“今指事情进行的程序、次第”[9]48;《汉语大词典》说步骤是“事情进行的程序、次第。《后汉书·崔寔传》:‘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随显然,在中国颇有影响的这两本辞书中,关于“程序”和“步骤”都形成了一个同意反复的循环解释。对程序的科学属性只字不提,对程序主体的自主性浑然不觉,对程序的应然性及其与实然机制的关系茫然不知,从而将具有现代中国才有的“程序”混同于中性的、古代就有的“步骤”,说明作为程序最基本属性的现代属性基本上被作为语言权威的词典编撰者所无视。这大致体现了国人当前对程序的认识水平。
基本概念不清晰,其运用必然混乱。比如,季卫东在1993年就提出了“新程序主义”,并认为“程序的重要性已经达成跨学科共识”,但他在十几年后也不得不承认“批评的言论也很强劲”[11]。而且批评者的队伍还很强大,既有人以“实质非理性”反对程序正义[12],也有人宣称“‘情理法并重的正义”[13]更符合中国国情。以上争议大多发生在对程序、对法律程序必须有清晰认识的法学领域,这显然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不禁要问: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法程序观?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现代程序观?而声称“理”比“法”高明,“情理法”比现代组织理论高明,要以中国传统“超越”西方文化的局限性的《中国式管理》一样[14],在比法学界更接近日常生活的管理实务界和学术界受到热烈欢迎,同样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不禁要问:变革中的程序观念必须秉承何种中国传统,才能够为国人所接受?它同时又必须坚持哪些基本特征,才能被看作是现代程序而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认可?显然,目前学术界对程序肤浅而混乱的认识状况是不可能提交一份令人满意的答案的。
作为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对程序的认识尚且是如此状况,我们显然不能指望为官或为民的普罗大众对程序概念有更清晰的认识,对程序与传统程式有更明确的区分,对程序的现代属性有更清醒的自觉。2016年“雷洋涉嫌漂娟被民警采取强制约束措施后死亡”及其相关的“邢某某、孔某、周某、孙某某、张某某等五名涉案警务人员玩忽职守案”[15]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引起巨大争议,正说明程序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人们对程序存在巨大争议。当然,争议未必就是坏事,虽然没有见到对该事件(从涉嫌嫖娼到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整个事件)的民意调查分析文件,但如此高的关注度已经使它成为中国程序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该事件的关键是程序问题。
三、中国程序观念的主要线索
上述種种问题,凸显了程序化对治理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重要性和理论复杂性。要想从学术上廓清这一问题,必须要对中国的程序观念史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要有中西比较的现代视野,在认识程序化与现代化存在正相关性、认识到程序性调节机制是现代社会之存续的正式组织力量的基础上,考察中国程序观念如何从旧观念中产生,如何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演变的历史过程和内在逻辑,考察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组织机制和调节机制的程序性蕴含,考察程序观念群如何随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组织机制的变迁而变迁的思想根源。通过对专门为思想史研究而开发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以及一般性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数据库、“四库全书”“中国知网”“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等数据库中程序及其相关名词的检索,我们捋清了中国程序观念演变的主要线索。囿于篇幅,概述如下:
1.传统中国是以程式理性为社会正式调节机制的宗法一体化社会,中国古代存在忠孝同构、家国同构的程式资源,但有其局限性。通过检索“四库全书”中程式及其相关关键词,我们发现儒家伦理一开始就有很强的礼的程式要求,而汉所开启的“阳儒阴法”“儒表法里”的实质,是将更为严苛法家之法的程式要求纳入了儒家之礼;经过宋明理学的理性化之后,礼法程式的道德化和情理化更趋自洽。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具备计划性、步骤性、公开性、严密性等诸多程序性因素,为朝廷选拔官员、为寒门通过相对公平的竞争进入国家治理阶层、为社会流动作出了极大贡献,也为基层社会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族治理培养了人才,但由于皇权和儒教的主导地位也导致了儒生的思想和行为僵化。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中发挥着枢纽作用,是其典型代表;科举程式的价值及局限,集中体现了古代官僚制度的价值与局限,体现了礼法一体化程式的价值与局限。
2.20世纪头20余年,中国在第一次现代化高潮中诞生了程序观念。通过检索“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我们发现,1840年以后,在西方军事、技术和国际法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程式观念略有松动,开始选择性吸收西方程序观。清末新政前,中国已经实质上接受基于世界公民预设的国际法程序,但欠缺保障国民权利的程序意识。1905年彻底废除科举程式[16]1907年“程序”一词就首次出现[17],但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人们谈到民主选举时并未用到“程序”一词,而是受日文的影响用的是比较具有中性色彩的“手续”。在建立现代宪政国家的实践推动下,1913年到1916年间,程序及其相关观念(简称程序观念群)出现第一个使用高峰,程序以与程式混同的形式成为中国政法领域的重要概念,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更多的是受制于权力和道德。新文化运动重构了上一时期学习到的程序观念,但对程序的界定并不明确统一,将程序泛化,对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治理助益不大。比如,胡适为代表的中国式自由主义用进化论继承理学循序渐进思想,其讲求具体道德的关系网结构作为吸附在正式组织上的寄生机制,一直对中国社会发生广泛而深刻影响。
3.20世纪中叶,中国出现过一次程序化建设的小高潮。国共合作的革命党机制恢复了道德程式一体化的结构;中国共产党向来注重纪律建设,它类似理学的规矩,很少使用程序一词。国民党尚“行”而缺乏统一道德,无法以托训政程序之名的“手续”抵御个人关系网的侵蚀。通过检索分析“中国共产党基本文献库”“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和“中国知网”发现,新民主主义建设纲领和社会主义改造不乏现代性初生国家和苏联模式的理学准程序性,“程序”及其观念群的使用量位居历史第三位,掀起了两次现代化高潮中的一个程序化建设小高潮。通过对惨痛教训的反思,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期认识到实然机制和科学规律不可违背,尝试在经济领域播种程序理性。
4.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第二次现代化高潮再次兴起了中国的程序化建设高潮,虽略有起伏,但总体上呈持续上升态势。改革开放树立起科学的至上权威,程序理性中中性的循序渐进因素在大多数时间段里都居于主导地位,而其现代性因素也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自主性扩张而扩张。1978年,科学真理和科学革命突破程式性的“两个凡是”。尊重科学知识,尊重中国国情的实际状况和运转机制,20世纪80年代“系统热”中控制论的试错性反馈调节机制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论”[18]极为契合,计算机、自动化、信息技术、经济管理、政法程序的使用量迅猛增长;“系统的哲学”已经蕴含了超越西方程序理性的零散想法,但由于整个社会程序实践基础薄弱,呼之欲出的系统论程序理性并未形成气候。90年代以后,启蒙自我瓦解[19],普通民众的革命意识和政治热情有所衰减,程序理性在两种科学主义——一是在经济学帝国主义下获得政治哲学上的渐进主义内涵,二是在依法治国中强化其制度化、规范化诉求。简而言之,尊重实然机制、尊重科学规律,开放的市场经济使经济管理程序与世界接轨并推进政法程序进程,程序化与制度化、规范化一道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21世纪多元的价值冲突中,虽然情理化政策和道德化權力也开始回潮,但具有定息止纷的程序正义价值开始从知识分子普及到普罗大众。当然,依然有不少人习惯于用实质理性对程序进行道德化评价,并习惯于把程序看作形式予以负面评价。不过,经过调研发现,基层,尤其是农村的干部群众不仅经常将“认程序不认人”挂在嘴边,而且也确实用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20]。据此我们认为,程序正义已经获得相当的社会认同,具,有了相当的社会基础。
综上,程序是一个重要的现代观念,程序化与现代化正相关。中国程序观念的发展跌宕起伏,大致印证了国家社会的现代性与程序性的正相关性,其程序化建设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大致同步。中国程序观念现代化的关键,是要在程序表达中处理好权利、权力和道德三者之间的系统关系;中国程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要处理好应然程序与实然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1]Andreagiovanni Reina,Thomas Bose,Vito Trianni&James A.R.Marshall,Psychophysical Laws and the Superor-ganism[J].Scientific Reports 2018(8):4387.
[2]“轴心文明与二十一世纪”专题讨论[J].21世纪,57,58.
[3]大英百科全书[EB/OL].[2018-01-10].http://www.m-w.com/dictionary/procedure.
[4]涂明君.程序化的哲学阐释[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8.
[5]Drucker,P.F.Management:tasks,responsibilities,prac-tices[M].New York:Harper&Row,Publishers,inc.,1985(ori-gin worked 1972).
[6]Green,C.D.,Operationism again:What did Bridgmansay?What did Bridgman need?[J].Theory&Psychology,2001,11(1).
[7][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8][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532.
[9]夏征农.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音序[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10]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八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87.
[11]季卫东.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3(1).
[12]朱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3]冯象.正义的蒙眼布[J].读书,2002(7):100-103.
[14]曾仕强.中国式管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5]雷洋[EB/OL].[2018-01-20].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B7%E6%B4%8B/19658789?fr=aladdin.
[1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249.
[17]刘式训.使法刘式训致外部法日协约似有干涉我边务意电[A].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三·二[M]//刘青峰,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9.
[19]許纪霖,罗岗.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20]涂明君.通往善治之路:互补系统论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求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48-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