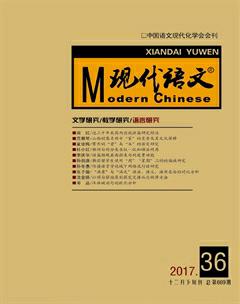中外译者合译的“三美”优势
高雅蓉
摘 要:随着海外国家对中华文化的重视,汉译英工作者与日俱增,中外译者合作的现象也悄然风行,最著名的此类译者当属翻译界泰斗——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为探析该翻译模式的效果,以《离骚》三个著名译本为例,将杨氏夫妇译本分别同英国译者霍克斯及中国译者许渊冲的译本进行对比。在“三美”原则的基础上,得出前者在意、形、音三方面具有更强的综合优势,这说明中西合璧的翻译方式能够较好地再现源语文本的风格和内涵,且有助于目标语读者体会中国文学的古韵之美,为改善汉英文学翻译提供借鉴。
关键词:合译 中外译者 《离骚》
一、引言
经过数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与日俱增,在当今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新时代,推介精神文化并鼓励中国文学走出国门是提高本国文化竞争力、丰富和繁荣世界文化的重要手段。翻译在加速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越来越多的语言专业人士从事翻译工作。翻译模式可大致分为两种:独译与合译。纵观我国翻译史,不仅合译这一模式常被使用,且中外译者合译的现象也在近几十年广泛流行。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从译作可接受性的角度出发,发现“近年来,国际上知名度比较高的译本都是中外合作的结果”,认为“中译外绝对不能一个人译,一定要有中外合作。”[1]Kristeva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由于在一门新语言环境下外语学习者容易出现过度泛化以及负迁移等现象,以致于他们难以完全掌握和本族语使用者同水平的语言技能[2]。因此,源语言使用者和目标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互相协作能够创造出高效率、高水准的翻译条件,以此来充分利用双方译者的母语知识储备,在互帮互助、相辅相成的状态中创作出更令读者满意的译注作品。著名译者聂华苓与她的丈夫美国诗人和翻译家保罗·安格尔[3]对此观点深表赞同。
国内耳熟能详的中外合作译者当属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他们是最早致力于将中华古典文化之精髓引入西方的合译者之一。自上世纪40年代起,杨宪益与其夫人译出大量的经典名著。本文以杨氏夫妇的译著——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为例,对比参照英国汉学大家大卫霍克斯和中国资深英汉译者许渊冲的译本,从“意美”“音美”“形美”三个特征入手,分析中外译者合译的优势,为如何提高古典文学汉英翻译水平,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做出一定的贡献。
二、《离骚》三译本简介
《离骚》代表了“楚辞”的最高艺术成就,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眾多译者为了传播中华经典文学对此进行了谨慎的汉英翻译。本文以三种译本为例,对中外合译进行比较分析。
第一种译本由精通中国语言文化的英国著名汉学家大卫?霍克斯所译,已有学者通过对其《离骚》译本的详尽探析,总结归纳了西方学者如何向欧美受众展示我国南楚文化的特点。[4]
第二种译本由长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许渊冲教授所译。关于该版本的分析主要与“三美论”相关。“三美”原是徐渊冲教授基于西方和中国诗歌特点的全面分析,以及他本人丰富的翻译实践而提出的一项古典文学翻译标准。该原则受鲁迅先生关于“习字”与“著文”论点的启发,具体指“意美、形美和音美”,借用鲁迅的话即为:“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5]
中国古诗歌常常借物言志,即“比”的手法,通过拟物手法表达诗人的情感。一般来说,用来做比的事物较之于被比的本体更加生动具体且为人们所知,便于联想,从而营造出一种意境。这就是中国诗词中“意美”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形”一般是指物体的形状和构造,而诗歌中的“形”包括每首诗的句数、每句诗的字数、每行诗的长度以及总体对仗情况,中外诗歌的“形美”都是由这些因素构成的。中国古代的诗、乐、舞是合为一体的。《礼记·乐记》记载:“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因此,诗歌除了有优美的诗意,还需要琅琅上口的音律。诗歌的“音美”即节奏、韵律和音调。许渊冲所谓的“音美”,就是要保持原诗的神韵,使译文“有节奏、押韵、顺口、好听”[6]。
第三种译本出自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这对伉俪的翻译生涯从《离骚》的英译正式开始,创造了中西合璧的独特范例。已有的研究显示,由于中国古诗词言简意丰的特点以及中西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致使中国古典文学难以实现对等的翻译,从而也有了“诗不可译”的说法在学术界流传[7]。即便如此,杨氏夫妇仍然在文学翻译的“意美、音美、形美”三方面找到了平衡点,使得译文既传递了原文的含义,又具备琅琅上口的优美音律。禹一奇(2009)深入研究了杨氏夫妇的合译模式,并以其《离骚》的翻译为例,分析了他们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时的主要思想和宗旨[8]。
除了对以上三种译本相对应的单独研究,还有一些基于美学、阐释学、炼词造句、功能对等和翻译风格等方面的对比分析,但均未涉及中外译者合译所具备的比较优势。纵观国内外学者对合作翻译的研究,从中外译者合作这一角度的解析可谓寥若晨星。本文将针对以汉语为母语的译者和以英文为母语的译者之间的合作翻译效果进行探索,尝试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译入手,分析中外译者的比较优势,旨在推介汉语言文化、促进汉英文化交流与合作。
三、《离骚》三译本的比较优势分析
(一)意美
根据柯林斯英文字典,当提及诸如书籍、电视节目或网站等内容时,主要是指它们所处理的主题、所讲述的故事、或所表达的想法。奈达(1993)曾指出,翻译的工作主要是翻译源文本所传递的“意思”,字面意思和言外之意都要考虑在内[9]。《离骚》作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其中一些词句对中国读者来说也会有晦涩难懂的情况,对外国读者而言更是如此。下面是对三种翻译作品在“意”传达方面的对比分析。endprint
(1)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大卫·霍克斯:Scion of the high lord Gao Yang,
Bo Yong was my fathers name.
When She Ti pointed to the first month of the year,
On the day geng-yin I passed from the womb.
杨宪益和戴乃迭:A prince am I of ancestry renowned,
Illustrious name my royal sire hath found.
When Sirius did in spring its light display,
A child was born, and Tiger marked the day.
许渊冲:Descendant of High Sunny King, oh!
My fathers name shed sunny ray.
The Wooden Star appeared in spring,oh!
When I was born on Tigers Day.
原诗中许多生僻的名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而不同的译者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也截然不同。霍克斯选择使用和汉字相对应的拼音直接音译,外加注释以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音译这一办法有较为明显的缺点,即汉字和英文单词本身存在巨大差异。在汉语里,同音异形和同音异义的字不胜枚举,几乎每个拼音都有不止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汉字,直接音译极易造成误解。虽然注释能有效地帮助读者理解原文意思和了解其语言文化,但同时也使读者在赏析时驻足停留,花费大量精力琢磨怎样理解注释,从而降低了诗歌“意美”的质量,可谓得不偿失。
许渊冲采取了释义的手法,将其中带有丰富文化色彩的名称以具备相似意义的英文单词代替,这样虽留有一定诗意,但不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外国读者可能无法正确理解该名词的意思;再者,并非所有中文名词都有相对应的英文单词可以代替,比如第二行的“伯庸”,在这种情况下,许先生将其译为“name shed sunny ray”可谓是对原文的“再创作”,并未能做到对原文的忠实。
杨氏夫妇则直接选用更通俗易懂且意思相近的英文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例如将古时王公贵族的名字“伯庸”译为“Illustrious name”,即卓越人物的名字,这样既帮助读者一目了然地理解了原文的意思,又使其体会到相似的韵味,以此基本实现了“意美”的标准。
以上分析表明,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异,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常常无法完美实现字面意思的传递,但由于人类的感官是相似的,喜怒哀樂这一系列情绪常常引起共鸣,因此言外之意反而更易传达。诗歌以“炼词”来营造动人心弦的意境,在遣词造句方面的要求高于其他文学作品。霍克斯和许渊冲的译文都没能再现源文本所蕴含的古典美,许多词汇显得过于平淡。如“Bo Yong was my fathers name.”或“When I was born on Tiger' s Day.”这明显和《离骚》中的古雅措辞不相符。相比之下,杨氏夫妇译本选择使用典雅庄重的词汇如“sire”和“hath”,成功营造了古雅的诗意氛围,能够让目标语读者体味到源语文本的艺术风格。
(2)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大卫·霍克斯:Heaving a long sigh,I brush away my tears,
Sad that mans life should be so beset with hardship.
杨宪益:Long did I sigh and wipe away my Tears,
To see my People bowed by Griefs and Fears.
许渊冲:I sigh and wipe away my tears,oh!
Im grieved at a life full of woes.
霍克斯在翻译这句名言时使用逗号将第一小句断开,这在无意间削弱了原诗悲伤无奈、愤慨动荡之感。许渊冲译本忽略该句中表达诗人愤懑情感的重要字眼“长”,且在原文没有出现人称的情况下采用第一人称“I”作为两小句的开头,把客观存在的黎民之苦无形间转换为诗人的主观感受。杨氏夫妇选用“my people”,既用这一第三人称客观展现当时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煎熬,又传递了诗人以忠臣烈士的视角对黎民处境的无奈哀叹。同时,在翻译“长”这一形容词时运用倒装手法,完美再现了诗人悲天悯人的情怀,以此达到“意美”的境界。
(3)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
大卫·霍克斯:Yet,though cast off,I would wear my orchid girdle;
I would pluck some angelicas to add to its beauty;
杨宪益:First cursed me for my Angelica should wear,
Then cursed me for my Melilotus fair.
许渊冲:I make a belt of grasses sweet,oh!
And add to it clovers and thymes.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诗人常常通过意境与读者产生共鸣,因此在汉英诗词翻译活动中,只有正确理解诗中营造的意境并且将其中的情感传达给读者,才能传递原诗“意美”。《楚辞》以“香草美人”的意境著称,以上两句诗中的“香草”为“蕙”和“茝”,霍克斯将其分别译为“orchid”和“angelica”,这两种植物在英文语言环境中有“美好、香甜和纯美”之义。相较之下,许渊冲译为“grasses sweet”和“clovers and thymes”在“意美”方面则稍逊一筹。杨氏夫妇也选取了“angelica”一词,但却将其用于指代“蕙”。“蕙”由上半部分指植物的“艹”和下半部分表仁爱善良的“惠”组成,以汉语为母语者看到该字时很容易联想到美好的人或物,译者相应地也需要选择能带给目标语读者一样效果的单词。而“angelica”恰巧左半部分为“angel”(英文中义为“天使”),同样为目标语读者创造出真善美和圣洁的意境。杨氏夫妇将第二小句中另一植物“茝”译为“Melilotus”,该词右半部分恰好为“lotus”,在英文中义为“莲花”,即便目标语读者不熟悉“Melilotus”这一单词,也能够从右半部分的“lotus”推测出它意在借美好的花草代指优雅的事物,用独到的手法再现了原诗“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