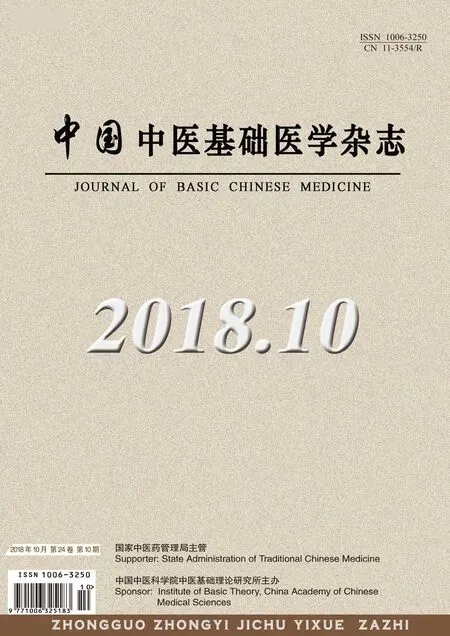民国名医祝味菊对中医药抗感染的认识*
农汉才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 100700)
祝味菊(1884-1951)祖籍绍兴,出生成长于成都,自幼习中医,遍览中医典籍,1917年考入四川军医学校攻读西医,后赴日本考察医学。回国后任四川省立医院医务主任等职,后又独立开业行医。1927年迁居上海继续行医,曾任神州国医总会执行委员,并先后执教于上海中医专科学校、上海国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并任新中国医学院董事会董事、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新中国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1937年,祝味菊与上海西医梅卓生、德国医生兰纳博士等联合开办中西医会诊所,首开中西医结合之先河。他主张中医应改革,自求发展进步,其主要著作有《伤寒新义》《金匮新义》《病理发挥》《诊断提纲》《伤寒方解》《伤寒质难》等,《伤寒质难》是其代表作。
祝味菊未留有医案专著,其医案均为其学生及后人的记录传载。根据目前可见的资料和初步统计祝味菊留存的医案约230余例,其中治疗感染性疾病的案例约40余则[1-13],其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就是治疗上海儿科名医徐小圃长子徐伯远的肠伤寒案。当时徐伯远已昏厥抽搐,西医救治无效,众人皆以为不治。祝味菊以中医强心扶阳、扶助正气之法救活了徐伯远,徐小圃因此改投其门下,祝味菊为此声名大振,在上海立住了脚根[1]169。民国时期,西医在中国传播渐广,细菌学说以其生物可见性深入人心。当时传染病流行也较广泛,中医能否治疗感染性疾病成为中西医论争的焦点之一。当时中医界的一批精英站出来,他们不但以临床实效来证明中医,更以中西医汇通的方式从多种角度阐明中医愈病的机理,说明中医的科学性,如恽铁樵、谭次仲、余无言、陆渊雷、阎德润等。祝味菊是其中的典范之一,他对中医抗感染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指导理论和生动的案例,下面仅就其对中医抗感染的认识作一粗浅的梳理。
1 三因鼎立
祝味菊认为感染性疾病即是“狭义之伤寒”,导致感染性疾病发生的原因有六淫、细菌等微生物及人体抵抗力状况,即“三因鼎立”的病因学说。“张仲景之所谓伤寒指广义之外感。外感因气候失常、体工失调而病,不必有细菌也。若夫狭义之伤寒,则所谓三因鼎立者是矣。所谓气候不适于人,而适于细菌之蕃殖者,因也;人身抵抗力不足,予邪以潜入之机者,缘也。体工不能杜患于未然者,因也;邪之得以客舍于所胜之地,吸浊以自存者,缘也。疾病之确立,无非因缘之凑合”[1]24。
祝味菊把六淫、细菌等微生物分别称为无机、有机之邪:“邪有无机有机之别:无机之邪,六淫之偏胜也,风寒暑湿燥火,及乎疫疠尸腐不正之气,凡不适于人而有利于邪机之蕃殖者,皆是也;有机之邪,一切细菌原虫,有定形、具生机,可以检验而取证于人者,皆是也。[1]22”
当时社会上曾有观点认为六淫仍可以统摄外感病因,细菌只是生于六淫。他认为:“细菌非生于六淫,六淫助菌为害。”他认为细菌在人体内外无处不存在,人体与细菌可相安相益,六淫是造成细菌异常为害的助因:“伤寒之成,有形之有机邪为主因,无形之无机邪为诱因,彼二邪者,狼狈为奸,每伺人于不察焉。[1]22” “六淫害正,言气候之不适于人,人之所恶,菌之所喜也。故六淫可以培养细菌,细菌得六淫之助,可以猖獗而为患”[1]23。 依于于有机无机之邪的定义,祝味菊认为温病学所说的“伏气”并不是六淫内伏,而是细菌的潜藏。伏气的致病,正是因为六邪诱发了潜藏的细菌,“感冒诱发菌毒,以表邪而动伏气。[1]30”
祝味菊的“三因鼎立”还将人体抵抗力的状况明确到病因学说中。他非常重视人体的自身因素,并对抵抗力在感染性疾病整个病程中的变化作了详细论述,这为其“五段”学说及“人病并重”的抗感染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2 对感染后症与证的认识
祝味菊认为人体感染后会引发抗邪过程,出现一系列的抗邪症状,包括西医所说的“炎症”。根据抵抗力与邪实的不同状况,认为抗邪的情况则可分为5种(“五段”),即六经证候。
2.1 生温与放温障碍
发热是感染性疾病最常见和最主要的症状之一,对于发热一症祝味菊有独特的见解和处理方式。他认为受邪与感染后的发热是因为人体生温与放温功能的异常共同导致,即以生温与放温来解析一系列的发热症状。
认为六淫侵袭会导致表闭,表闭则会出现放温障碍,正常的生温与放温不能平衡则会出现发热,体温升高。这种体温升高是有促使“达表”和治疗作用。如只有六淫侵袭而没有细菌感染也会“感冒”,会出现放温障碍、发热,有汗或无汗。
认为感染后,细菌的菌毒刺激大脑中枢会导致产热、发热,这种发热是动员血液加速产生噬菌体等“特异物质”以抗病菌:“发热者,敦促此种特异物质之加紧生产也”[1]35。“壮热无汗,或汗出不畅,是生温多而放温障碍也”[1]45。
对于发热的程度不同,祝味菊又将其分为“抗温”与“亢温”:“生理所需要者,名曰平温(成人体温常在37 ℃)……正气抗之,病理所需要者,名曰抗温(最佳38~39 ℃间)……抗邪太烈,矫枉过正,生理所难堪,病理所不需要者,名曰亢温。抗温为善温,亢温为害温(40 ℃以上)。[1]43”祝味菊对温度的辨证法为其后不以退热为目的的治疗方法以及某些热病反用热药等治疗方法打下了理论基础。
2.2 炎症
“炎症”是西医对于机体受刺激后产生的防御反应的概括,是感染后最常见的证候。祝味菊认为炎症的红肿热痛四大主征是“组织对付有害物质所起之反动也。其为炎也,欲以排除障碍之物也,欲以消灭有害之菌也,欲以拘困邪毒,令其限局于一部,勿使蔓延他处,盖有所为而发也”[1]126。
祝味菊认识到炎症是抗病的过程,是有益于人体康复的:“凡此工作,无非致力于自卫之道也。[1]105”基于此种认识认为见炎症不可一味地消炎,抗感染时不能一味地以消除症状为主,针对当时社会上滥用中医药苦寒之剂以“消炎”的风气,祝味菊提出了不同的抗感染方法:“伤寒之肠炎,自然之趋势也,疗病之机转也。[1]38”因此,他认为某些炎症是有益的,不应当全用寒凉的药物或抗生素来解消其抗邪之势。
2.3 六经病
祝味菊认为一切外感病包括感染性疾病,在抗邪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情况都不出张仲景的六经证候,并将其归纳为“五段”:“吾之所谓六经者,乃代表五种抵抗程度耳。[1]73”他认为太阳为开始抵抗,少阳为抵抗不济,阳明为抵抗太过,太阴、少阴同为抵抗不足,厥阴为最后之抵抗。一切外感病的抵抗过程都不出这5种阶段[1]73。
他认为太阳伤寒为人体对于邪毒开始合度之抵抗,因其先驱症状多见于表,故前人称太阳为表病。表病之主症为畏寒发热,发热之原因系邪正相搏,体温调节中枢受激;或为六淫外激致放温障碍,或为菌毒内激致生温亢进。太阳病发热的动机,对于六淫之邪是“欲酿汗而解表”[1]81;对于菌毒之邪,“欲令产生抗体,以消内在之菌毒”[1]81。
祝味菊认为少阳伤寒是人体对于邪毒抵抗持续不济未能协调也,但正气有可胜之潜力;阳明伤寒为人体对于邪毒之反应失之过激也,太阴、少阴伤寒都属抵抗不足。但它与少阳伤寒的抵抗不足有区别:“大凡具有抗力而未能发挥者,谓之少阳;无力反应则谓太阴、少阴。故少阳不足在标,太阴少阴不足在本。[1]97”
3 对抗感染方法的总结
3.1 抗生素与“病原疗法”
抗生素发明于20世纪30年代,祝味菊客观地接受了抗生素,对其疗效及局限性进行了评价,并将其与中医疗法和中药进行了比较。
认为一种抗生素只能针对某些病菌,并不能应对所有的感染:“配尼西灵仅可抵制较多种之病菌,对于人体亦非绝对有利者,初不足以应万病也。即如伤寒杆菌,已难胜任愉快,世岂有万能之药哉?[1]127”
同时也关注到抗生素引起的人体抗药性:“配尼西灵,近代杀菌消炎之专药也,用之有灵、有不灵……医用小量配尼西灵而频服之,人体血液中即产生一种抗配尼西灵体,此项抗体既多,虽顿服大量,亦无殊功云。[1]133”
祝味菊认为抗生素的治疗方法相当于中医的“病原疗法”,即只是针对某病的特效药,中医亦有相当于抗生素的中药,如“梅毒之于砒剂,不必再有硬疳、起胀、溃疡、结靥、落痂等过程矣”[1]70,“中医用雄黄、轻粉治梅毒,用使君子、鹧鸪菜治蛔虫,皆病原疗法也”[1]78。
认为中医除了有“病原疗法”,还有可以“执简驭繁”协助正气、自然疗能的方法,即“本体疗法”。
3.2 以扶助正气为主的中医抗感染疗法
祝味菊认为抗感染有“病原疗法”和“本体疗法”,本体疗法即是扶助和调整人体抗力(正气)以愈病的方法。
祝味菊认为人体具有普遍的自我保护、自我调节及自疗机能,这些机能即是中医所指的“正气”。他认为正气学说是中医理论最重要的核心,张仲景之学即是以“正气”为本的医学:“仲师《伤寒》《金匮》两书,为自来医家之宝函,其立法处方,无不以正气为重”[14],于是创造性地以诊疗人体正气的五段学说来阐释六经。对于感染性疾病的诊疗也不出五段法。
同时认为邪正消长之机是以阳气盛衰为转移,人体的正气、抗病能力往往体现在人体的“阳”,认为“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1]69。因此他经常通过和阳、通阳、扶阳等调整阳气的状况来扶助自然疗能,以此来治疗感染性疾病:“是以太阳伤寒,重在和阳;少阳有障,重在通阳;阳明太过,重在抑阳;少阴不足,重在扶阳,厥阴逆转,重在潜阳。[1]176”
对于感染性疾病,当时社会上流行灭菌消炎或中医的清轻之风,对于扶正、温补等方法视为相反的疗法[15]。对此,祝味菊作了特别解释:“狭义之伤寒,病菌所致。其治可用温否,方书有载。急性肺炎,其体力不足者,麻膏疗病,枣附强心,此千金越婢汤也……痢下赤白,细菌原虫之为患有也,实痢用清,虚痢用温,为治痢之要则[1]146-147。”
祝味菊使用扶正法治疗感染性疾病,除上述的徐伯远案外,另一典型的是叶翰臣肠伤寒案。叶翰臣是当时西医药学博士,患肠伤寒病已数年且反复难愈。见祝味菊时其发热、白血球显著减少。祝味菊用中药治疗后,8 d热退净又处一方调理,几天后体力复苏。叶翰臣对于此疗效很诧异,便在中央研究院对祝味菊处方中的每味药都做研究发现均无杀菌作用,便询问何故。祝味菊回答说:“夫愈伤寒者,伤寒抗体也。抗体之产生,由于整个体力之合作。吾人协调抗病之趋势,使其符合自然疗能,在此优良之环境下,抗体之滋生甚速,故病可速愈,非药物直接有愈病之能也。[1]154-155”
3.3 汗、清、温等疗法在抗感染中的作用
感染后如果不使用抗生素,祝味菊认为可以通过扶助和调整人体正气来愈病。在临证中,祝味菊常用中医治疗八法(汗、下、吐、和、温、清、消、补)中的汗、清、温等法来调整人体正气,对其在抗感染中的作用与原理有较为详细的阐释。
祝味菊认为出汗是人体感染后自疗的反应:“高热非生理所能堪,则持续出汗,藉以调节其放温,此合理之自然疗法也。[1]105”因此通过汗法,可以调整人体发汗的状况,调节体温,排泄毒素:“伤寒之机转在表,故汗液重于小便,汗法可以排泄秽毒,可以调节亢温,可以诱导血行向表,可以协助自然疗能,一举而数善备,此法之上者也。[1]106”如对于桂枝汤认为虽不能像抗生素一样直接灭菌,但通过汗法可以温阳达表,促进机体自然抗邪而愈病:“发汗解肌,虽不能消除菌毒之邪,然六淫之诱因得解,体温有调节之机,则芟芜去障,内在菌毒之邪势孤也,疾病之环境得以改善,则阳伸而邪达,抗体得以从容产生也。[1]82”
在治疗感染性疾病时,民国时期江南流行使用清法,祝味菊认为,清法可用来消散亢温,维持抗温。他认为感染后人体抗病需要抗温(38~39℃摄氏度),而“抗邪太烈,矫枉过正,生理所难堪,病理所不需者,名曰亢温(伤寒40℃以上)”[1]43,即40℃以上,就必须用清法调节至抗温:“伤寒之用清,中和亢热,而维持抗温也”[1]43。但并不是用清法直接来回复到正常体温:“一切清药,皆为抑制亢奋之用,设非有余,允宜远避者也。是故同是辛散,偏清则抑正而碍表,若非里气之亢者,不当选用辛凉”[1]84。
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治疗感染性疾病时,对于发热不足、抗邪不力的情况,祝味菊常用温法、补法(强心护阳)以“维持抗温”:“伤寒极期,正邪交搏,互争存亡危急之秋也,短兵相接,不胜即败,是以心用衰弱者,预后不良……中药枣、附之强心,绝少副作用,而药力之持久,又为西药所不及”[1]60。在使用温法时也非常注重配伍:“千金越婢汤,石膏与附子同用,一以制亢,一以强心。石膏之寒,已足抵消附子之温,然附子虽失其热,而不减其强心之用。[1]129”
3.4 “人病并重”的抗感染原则
祝味菊认为病原疗法即直接使用抗生素灭菌为 “治病”,通过调整与扶助正气抗感染为“治人”。在临证中他认为治人与治病都不可偏废,应人病并重[1]179:“治病不治人,其失必多;知人不知病,弊亦相等。人病兼治,效捷而功全,此上策也”[1]176。
认为每一种感染性疾病寻找特效抗生素是难以企及的:“无特效药,而能时时匡扶体力,亦可令正胜邪却,收化逆为顺之功”[1]78。因此,祝味菊认为医者必须同时掌握“治病”“治人”的方法:“医者治病,不能因病原不明而束手不治也,亦不能以特效药之阙如而屏不处方也。[1] 78”“病原疗法仅能适用于狭义之病原,而本体疗法则应用无穷,历万古而不变者”[1]79。因此在抗感染中,中医的“治人”疗法在应用范围上要比抗生素更有优势。
在临证中,祝味菊也常“人病并重”,在处方中常将具有消炎灭菌作用的中药与扶助人体自然疗能的药物同时使用:“譬如肺炎,高热多汗,欬呛气粗,胁痛顿闷,形瘁舌白而脉细数,此证候有余而体力不足也。法用麻黄开达肺气,协助自疗之机转;石膏抑制分泌,消除病灶之炎肿;佐以薤白、栝楼、芥子、杏仁、紫菀、郁金之属,各以其所长消减并发之证候,凡此者所以治病也。附子扶阳,枣仁强心,半夏温胃,牡蛎行水,鼓舞细胞,协力歼敌,所以疗人也。[1]128”
祝味菊认为中医能够“疗人”,是因为有系统的“法”:“中医之治病不尽在于经验药物,实有疗法可取。[1]155” “西医之专药可能疗专病,此为事实,无可否认。中医利用合理之方法,以疗无有专药之疾病。[1]154”因此他认为“法”是一种规律,可以重复应用,是符合科学原则的,也必将会重复再现,这也是对民国废医存药思潮的有力批判。因此,在科研中,他提出除了“药”还应以“法”为对象设计中医药实验,统计对比“治病”与“治人”的疗效[1]189。时至今日,中医的实验研究基本都仍以“药”为研究对象,较少有以“法”来设计实验的,这值得当今科研界的借鉴与思考。
4 启示与思考
当今医疗界面临着一个重大难题,就是抗生素的耐药性及细菌变异,甚至出现了对几乎所有抗生素都有抗药性“超级细菌”。西方医学在对抗生素的研究中也逐步感觉局限性,开始转而向东方医学寻求启示与突破口。20世纪以前的中国,中医药是抗感染的主力军。自抗生素被发明以来,医学界开始以抗生素理论检视中医中药,并发现一些中药也具有直接灭菌作用,如黄连、黄芩、黄柏等。祝味菊也认可这一点,但通过更深入的对比和提炼,指出中医在抗感染中还有更大的贡献,即中医可通过系统调整与扶助人体自然抗邪能力来间接灭菌,并认为这是“应用无穷,历万古而不变”[1]79。在以往中医理论中,也常提到“标本兼治”,但其这一整理,无疑为中医抗感染的理论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合理的阐释。
对于感染性疾病,医学界提出希望找到更多替代抗生素的中药与方剂,或者希望中医中药能发挥协同抗生素的作用,减少抗生素的用量,降低人体的抗药性,或者希望中医药在抗生素的使用过程中,对其他症状或副作用能起到支持治疗的作用。根据祝味菊的见解,在抗感染中中医不仅仅只是辅助治疗,不但有能直接灭菌的中药,还有系统的疗法来独立抗感染。对于当今不断变异的病菌病毒,以及抗生素日渐不力、品类缺乏的情况下,祝味菊所指明的这种中医独立抗感染的方法,无疑会为当今临床与科研提供新的思路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