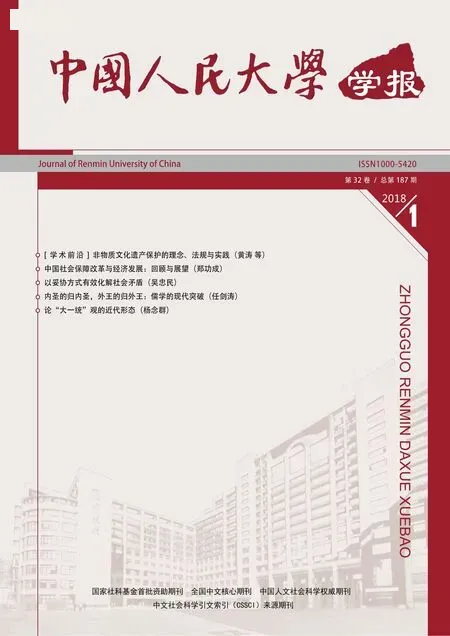“诗人之赋丽以则”发微
——兼论《汉志·诗赋略》赋史观的渊源与影响
曾祥波
“诗人之赋丽以则”出自扬雄《法言》,过去常将理解此语的关键落实在“诗人之赋”,造成歧说纷然(为行文便利,对前人研究的举证辩难分别见于文中相应部分,不赘言于此)。本文以为关键在理解“则”,对“则”的理解自然会指向“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内涵。过去对“则”不够重视,是认为“则”即“正”、“常”、“标准”,并无歧义。这当然不错。但这种泛化的理解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何种风格、意义、旨趣才是“正”、“常”与“标准”?其实并无明确指向性。由于《法言》的上下文语境过于简洁,其明确指向性也难以由《法言》揭橥,所幸《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也引述了扬雄此语,称: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杨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诗人之赋丽以则”在《汉志》文本语境中能得到更具体切实的理解,同时《汉志·诗赋略》的赋史观及其背后的诗学源流也能借此得以阐明。
一、作为文本的诗、赋分流及其内在依据
《汉志·诗赋略》对诗、赋两种文学类型初始概念的厘清,要点有二:首先,诗、赋之分仅在能否歌唱。“诗赋略”下分五类:前四类为赋,后一类为诗,在大的类别上一致,故合为一《略》。而诗、赋的区别,“不歌而诵谓之赋”,赋者为徒文,诗者为乐文(曰“歌诗”),区别仅在能否歌唱。其次,去掉歌唱这一环节,诗赋可以是同一文本。《汉志》先说到“可以为大夫”的标准,是登高能“赋”。*有学者认为“登高”指揖让庙堂之上,章太炎《国故论衡》指出:“登高孰谓?谓坛堂之上,揖让之时。赋者孰谓?谓微言相感,歌诗必类。是故‘九能’有赋无诗,明其互见。”参见骆玉明:《论“不歌而诵谓之赋”》,载《文学遗产》,1983(2)。再解释该标准的原因,大夫的事务职责要求他具备称“诗”谕志的能力。换言之,同一文本在歌唱时称为“诗”,不歌而诵则称为“赋”,诗、赋成为可以对等转换的同一概念。在人所周知的共识之下,还隐藏了更深层的问题似未得到揭橥,即:在不考虑表现体制(歌唱)的情况下,仅就文本而言,诗、赋的分野源于何时?《汉志·诗赋略》就“文本意义”上诗、赋的分流及其内在依据做出以下判断:
第一,诗、赋分野的时间在战国时期(春秋之后),代表作家是荀子与屈原。“登高能赋”、“揖让称《诗》”的行为流行于春秋时期,这时期的“赋”是一种“引述性”而非“创造性”的公共行为,采用的是“诗”的文本,表达的是公共话语、集体意识(如外交中的国家利益等),依附于诗,不具有独立性。赋转变为独立文体,“赋”这一行为成为“创造性”、“个人性”的文学活动,始于战国,以屈原、荀卿为代表。在这段文字中“诗”、“赋”互文对举,再次说明诗、赋概念在分离之初仍带有同义性,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
第二,更重要的是,赋从诗中分离出来,其概念变化的内在逻辑依据,是出于 “恻隐古诗”之义。就《汉志》的描述,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提出了最早的赋创作源头出于“失志”,从公共话语转向个人怀抱(“志”)的表达。其次,“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提出最早赋的代表作者荀卿、屈原的创作方式(“风”)源于古诗“恻隐”之义。“风以恻隐”者,虽失志悲痛(“恻”)而表达委婉(“隐”、“风”)。按,《说文》:“恻,痛也。从心,则声。”“隐,蔽也。”换言之,诗可以涵盖的情感因素十分丰富,喜怒哀乐皆可,而赋从诗中脱胎化育而出,只继承了诗众多丰富情感基因中的一种,即“失志”、“恻隐”的哀(“失志”、“恻”)婉(“隐”)之音,并且表达的方式属于风雅颂赋比兴六义中的“风”。
第三,从上述诗、赋分流的逻辑内涵变化背景出发,汉赋对赋的原始意义有一个背离与回归的过程。在《汉志》看来,荀卿、屈原之后,趋向“侈俪闳衍”的赋——也就是更符合我们今天对汉大赋的印象及定义的“赋”——逐渐偏离了“失志”、“恻隐”的哀婉之赋的初衷。直到作为“侈俪闳衍”作者行列中一员的扬雄,才首次从彀中跳出,自觉回顾、检讨这一偏离,从而做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判断。
二、诗、赋分流背景下“诗人之赋丽以则”新解
对“诗人之赋”、“辞人之赋”、“丽”、“则”、“淫”等关键词的梳理,对“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解读,在《汉志·诗赋略》的文本语境——即检讨赋由诗的“失志”、“恻隐”源头发展到汉大赋“侈俪闳衍”这一历史过程中对初衷的偏离——中进行,就有可能得到更具体切实的答案。
关键词之一:“诗人之赋”。既然赋的源头是基于“失志”、“恻隐”情感因素的“诗”,那么“诗人之赋”就是指保存了“失志”、“恻隐”之义初始面貌的赋。这里,“诗人”是指创作上带有赋的原初意义(以“诗”为源头)遗留痕迹的赋家,在《汉志》看来,就是荀卿、屈原。*有学者认为“诗人之赋”指《诗经》,如汪荣宝《法言义疏》:“诗人之赋,谓六义之一之赋,即诗也。”曹虹(参见曹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汉魏六朝赋研究》,载《学术月刊》,1991(11))从统计“诗人”一词用法的角度,也认为“古诗”指《诗经》。按,将“诗人之赋”的“诗”理解为《诗经》,这一点从来就没有异议。亦认同《诗经》说。另外,刘浏(参见刘浏:《扬雄“诗人之赋”辨义》,载《文艺评论》,2011(6))。但“诗人之赋”对应“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在《汉志》原文中十分清楚,显然是指向荀卿、屈原参见冷卫国:《“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载《齐鲁学刊》,2013(3)。
关键词之二:“丽以则”。长期以来,“丽以则”的“则”,被解释为“正”、“常”。这并没有错,但是什么才是“诗人之赋”的“正”与“常”尚欠分明,实际上没有一个具体指向。对“则”的理解,应该还原到“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具体语境,即《汉志》所言“诗—赋”文体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理解。在这个语境下,“则”应该理解为“恻(隐)”,即失志而哀(恻)但表达委婉(隐),即“恻隐古诗之义”的代称。“则”解释为“恻(隐)”,与传统上释“则”为“正”并不冲突,因为失志而哀(恻)但表达委婉(隐)就是“赋”刚从“诗”中剥离独立的初始源头,当然也可以视为赋之“正”体。合起来看,“诗人之赋丽以则”不妨写成“诗人之赋丽以恻”,即言想要恢复赋的本义写作的赋家,应该在写作时回归古诗“恻隐”之义,如同荀卿、屈原那样。必须指出,《汉志·诗赋略》所云“诗人之赋丽以则”引自扬雄《法言》,虽然古人引文可以有断章取义的惯例,但如果能够照顾、契合原文原意,自然更加相得益彰。扬雄论及赋、辞的其他文本,用上述诗、赋分流的历史观加以分析,同样涣然而解。《汉书·扬雄传》载:“雄之自序云尔……(以为)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班固:《汉书》,35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所谓“赋莫深于离骚”,盖因《离骚》仍保留了“失志”、“恻隐”的古诗之义,属于源头性(“莫深于”)的赋体,故仍称之为“赋”(《汉志》正将《离骚》归入“屈原赋二十五篇”)。而所谓“辞莫丽于相如”,则说明赋体发展到司马相如时,已经丧失了“古诗之义”,故只能称之为“辞”(也就是《汉志》所谓“辞人之赋”)。“斟酌其本”,很好地说明了扬雄从文体起源的代表性特征(“本”)历史地看待文体(诗—赋/辞)发展的眼光。笔者从文字学的角度尚未能发现“则”直接假借为“恻”的通行用例。一方面,“则”与“恻”字形相近,发音上“侧—则—塞—恻”皆为一声之转,同时“侧—则”、“则—塞”、“塞—恻”在意义上可通假,已经间接地形成了“则—恻”通假的可能性*考阮元《经籍籑诂》、王力《同源字典》等均无直接用例,但《经籍籑诂》认为“入声·十三职”以“侧—则—塞”一声之转,这与周朋升《西汉初简帛文献用字习惯研究》第一章第三节(吉林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统计结果(“则”可通假为“侧、测、责、樍”等,“恻”可通假为“塞”)相呼应,也就是说“则”可以通过“塞”达到与“恻”通假的结果。;另一方面,扬雄首用“则”指代“恻(隐)”,兼有“正”、“常”与“恻(隐)”的双重含义,这与他好弄奇字、造作《方言》、著书拟古的写作习惯也颇为契合。尤其是,“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则”指向“恻(隐)”的读解,在逻辑意义上完全符合《汉志·诗赋略》一以贯之的上下文语境,也符合扬雄《自序》的意义脉络。后人对内容上“则”指向“恻”的注意不够,或许正因为文字学上通行的通假例证不多而造成,但对征经拟圣、敢于自我作古的扬雄来说,这种写作方式并不算突兀。另外,“丽以则”之“丽”可通“俪”,指文字及句子、篇章的相并、排比,泛言赋的写作。当然,丽也可按照传统解释为华美,即“诗人之赋”外表华美,而内在有“恻隐古诗之义”,正因具有这样的内在,才属于源头性(“诗”)的赋。这里的关键点在理解“则”为“恻(隐)”,丽是次要的,因为接下来“辞人之赋丽以淫”,丽并无变化,无须辨析,可作同样的理解。
关键词之三:“辞人之赋”。与“诗人之赋”相对,“辞人之赋”的“辞”指“文本”,重在强调文本的“非音乐性”,也就是强调对源头性的“诗”的背离,换言之,辞人就是背离了赋的写作初衷(“诗”)的赋作者;辞人之赋,就是发展到了一种与其初始源头(“诗”)关系疏远阶段的赋,也就是“侈俪闳衍之词(辞)”的赋。唐人颜师古注说:“辞人,言后代之为文辞”,明确地指出“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淫者,失正、过当、泛滥之谓。“辞人之赋丽以淫”,是说“侈俪闳衍”的赋作者的写作已经完全偏离了赋的初始意义。
三、《汉志·诗赋略》文本与诗学观念渊源
“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内涵在班固《汉志》文本语境能得到更清晰的呈现,那么这一内涵的诗学观渊源是什么?以下从两个角度分析:
首先,我们知道《汉志》的底本是刘歆《七略》,那么班固有没有在其中孱入自己观点。已经有史家指出《汉志》并不代表班固本人的观点。如《汉志·六艺略·春秋类后序》认为孔子“与左丘明观其史记”而定《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唐人刘知几《史通》外篇《申左第五》指出《汉志》的这个说法与班固本集不同:“班固《艺文志》云:‘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有所贬损,事形于《传》,惧罹时难,故隐其书。末世口说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邹氏》诸传。’而于《固集》复有难《左氏》九条三评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说,而参差相背,前后不同。斯又不足观也。”*刘知己撰,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译:《史通》,30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诸如此类《汉志》与班固本集观点之悖,正表明《汉志》忠实地袭用《别录》、《七略》说法不予改动,并未孱入自己的观点。再来看具体与《诗赋略后序》文本相关的情况。班固《离骚序》对屈原的评价带有贬义:“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汉志》对屈原的评价则是:“楚臣屈原离谗忧国,作赋以风,有恻隐古诗之义。”换言之,屈原之作有失志悲痛(“恻”)而表达委婉(“隐”、“风”)的效果,即所谓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两种意见显然是对立的。*在刘歆之前的刘安、在刘歆之后的王逸都认为屈原之作可称“温柔敦厚”,可见刘歆的意见带有普遍性,而班固的意见颇为独特,这更能说明这一意见出于班固个人。《汉志·诗赋略后序》与班固自著文的评价截然相反,这恰说明《汉志·诗赋略后序》只是袭用《七略》的文字、观点,并非班固本意。因此,《汉志·诗赋略后序》的诗学观应视为刘歆《七略》的观点。*冷卫国同样认为《汉志·诗赋略后序》的诗学观即刘向、刘歆观点,而班固观点恰与此对立。参见冷卫国:《刘向、刘歆赋学批评发微》,载《文学遗产》,2010(2)。《汉书·扬雄传》载:“(雄)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刘歆子)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刘歆亦尝观之(《太玄》、《法言》),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向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班固:《汉书》,3583-35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从刘歆对扬雄的推崇来看,《七略》认同、采纳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等关于诗、赋流变的描述,是题中应有之义。*有学者认为,《诗赋略》的原文自“不歌而诵谓之赋”到“咸有恻隐古诗之义”为《七略》原文,自“其后宋玉、唐勒”到“观风俗,知薄厚云”为班固所增补。理由有三:(1)《七略》在《法言》之前成书。(2)刘歆准备拿《法言》“覆酱瓿”。(3)《诗赋略》的分类与后序具有评判标准上的不一致。参见俞纪东:《〈汉志·诗赋略〉“扬雄赋”绎释》,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笔者以为此三点皆不构成充分理由,略述如下:(1)刘歆与扬雄多有交流,扬雄的具体观点不必等待《法言》成书才可获知,且《法言》、《七略》的成书时间与写作时间不可等同视之,其间产生交集是很正常的。(2)“覆酱瓿”之说是刘歆评价世人对扬雄著述的看法,是刘歆为扬雄抱不平的惋惜与激愤之辞,绝非刘歆本人的态度,此点俞文有所误解。(3)关于《诗赋略》的分类,本文以为《汉志》所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序诗赋为五种。”其中“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句,可以与《诗赋略》五种分类“(一)屈原赋之属;(二)陆贾赋之属;(三)荀卿赋之属;(四)杂赋;(五)歌诗”参互对应,具体而言:“感于哀乐”者,对应“(一)屈原赋之属”与“(五)歌诗”,强调诗包罗人心的情感因素。“缘事而发”者,对应“(二)陆贾赋之属”与“(三)荀卿赋之属”,陆贾赋主“说事理”,荀卿赋主“状事物”。难以对应“感”与“事”、不可归类者,即“(四)杂赋”,这正是其之所以为“杂”的缘由。源于《七略》的《汉志》,在分类上采取了不同于文体发展历史线索的另一种逻辑框架,即以文体所针对的描写对象与主题进行分类,这与“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含义必须置于《汉志》对赋的起源与发展历史框架下考虑,形成了互补。因此,在另一种视角下,《诗赋略》的分类与后序的标准也并非不一致。扬雄的文学观由刘歆《七略》传递至班固《汉志》,形成了《汉志·诗赋略后序》文本形态。
其次,刘歆《七略·诗赋略》对扬雄的诗、赋流变观念的认同与采纳,在汉代今文齐诗、鲁诗、韩诗与古文毛诗四家诗学师法的背景下,有没有一个诗学师法的渊源呢?
刘歆《七略》承袭其父刘向《别录》,故有必要了解刘向的诗学家法。《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向本学鲁诗”。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新序〉辨证》以为非是:“谓刘向为习《鲁诗》及《韩诗》者,皆无以见其必然也……全祖望谓向之学在三家中未敢定为何诗者,独为得之。”*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471-475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据余嘉锡之说,不但不能确知刘向的诗学家法,更不能以刘向的诗学家法推断刘歆的诗学观。较之刘向诗学家法的隐晦而言,刘歆的诗学倾向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汉书·刘歆传》载:“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说明刘歆对《毛诗》的重视。另一方面,若《汉志》“赋源于古诗恻隐之义”能合于齐、鲁、韩、毛诗四家之某一家说,则可以定刘歆诗学家法归属,原因有三:第一,《汉志》直承刘歆《七略》而来,故其宗旨当更近于刘歆,而非刘向。第二,“赋源于古诗恻隐之义”是关于诗、赋本质定义的基本核心问题,属于诗学中的理论基础,在四家诗中应该属于带有区别性的“家法”要义。第三,刘歆对这一说法并非简单引用的撰述方式,而是作为《诗赋略》的核心观点写入《后序》,故对此说一定是完全认同的。
《汉志》所谓“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即“失志悲痛”(“恻”)而表达委婉(“隐”、“风”),即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这与儒家诗学的核心之一,即《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说、《毛诗大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表述的诗人写作心态、技巧手法完全一致。朱自清《诗言志辨》就已经察觉到:“诗教虽托为孔子的话,但似乎是《诗大序》的引申义。”*朱自清:《朱自清说诗》,4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另外,关于朱自清所说“托为孔子的话”,沈文倬认为《礼记》诸篇为七十子后学所作《菿闇文存》。参见沈文倬:《汉简〈服传〉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敏泽认为“温柔敦厚诗教也”虽非孔子原话,但反映了孔子及其门徒们的思想。参见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46页,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所以,刘歆的诗学观应当源出于毛诗,最为合理。关于刘歆诗学家法出于毛诗,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加以论证。齐、鲁、韩三家诗为今文,毛诗为古文。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认为毛诗为刘歆抵制《诗》今文三家经学而伪造:“博士传孔子学者,《诗》止齐、鲁、韩三家……歆伪为《毛诗》、《逸礼》、《周官·大司乐章》及《乐记》、《左氏传》,于是论议之间,斥三家《诗》‘取杂说非本义’……诋之唯恐不至,而盛称其伪作之书。后人无识,竟为所惑”,并举出毛诗为刘歆伪造的十五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217、21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此说为近现代学术史中的著名公案,人所熟知。伪造之说,虽不可信,然刘歆诗学观更近毛诗之说,却得到一种反向的有力旁证。另外有必要指出,即三国时吴人陆玑提出荀卿授诗学于毛公的说法,在唐代孔颖达《正义》中被再次提及,影响不小。如果属实,那么既然刘歆诗学出于毛诗,亦即间接师承荀卿,故承袭刘歆《七略》的《汉志》将“大儒孙卿”视为“有恻隐古诗之义”的两个代表之一(另一位是屈原),是顺理成章之事。这对本文的论证不无支持。不过,恐怕此点难以成立。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已经指出此说见于《经典释文·序录》引三国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而《序录》同时引用三国吴人徐整之说,提出另一条传承线索:“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康有为判断说:“自东汉后,《毛诗》盖盛行,而徐整、陆玑述传授源流支派,姓名无一同者。一以为出于孙卿,一以为不出于孙卿,当三国时尚无定论,则支派不清。”*康有为:《新学伪经考》,6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马银琴分析了这两种不同毛诗传承系统说法,认为陆玑系统存在不可解释的矛盾。参见马银琴:《荀子与诗》,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既然荀卿并未传授毛诗,那么源于毛诗之义的《汉志》文本以荀卿为“有恻隐古诗之义”的代表,其原因何在呢?笔者以为,刘师培《诗分四家说》的观点较为稳妥:“四家同出一源……观荀卿于《毛诗》、《鲁诗》为先师,兼通《韩诗》之说。则荀卿之世四家之诗仍未分立,嗣由荀卿弟子所记各偏,各本所记相教授,由是诗谊由合而分,非孔子删《诗》时即区四派也。”*刘师培:《诗分四家说》,14页,载宁武南氏校印:《左庵集》,1934。即齐、鲁、韩、毛四家同源,《诗》学至荀卿之时尚未分派。依此理解,则荀卿于此四家诗皆有传诗渊源之功,无论哪一家诗以荀卿有“古诗之义”,也都是合理的。
四、结语及余论:《毛诗》诗学观影响下的诗赋史建构
经过以上分析梳理,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条诗学观念影响赋史观念的传承演变线索:毛诗《大序》“温柔敦厚”诗教说(“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经过扬雄吸收运用,成为其赋史建构的核心理论来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的赋史框架可以简述为:赋由诗分流而出,秉持“虽失志悲痛而表达委婉”(风以恻隐古诗之义)的源头性标准,符合该标准的赋被称为“诗人之赋”。赋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偏离“恻隐古诗之义”的源头,走向文辞上的“侈俪闳衍”,这一阶段的赋被称为“辞人之赋”。扬雄的赋史建构为刘歆认同,被纳入《七略·诗赋略》,随后被班固《汉志·诗赋略》忠实地保留下来。
尽管班固《汉志·诗赋略后序》让扬雄赋史观与班固《七略》文本得到保存与传播,但若要追溯将“则”由具体指向“古诗恻隐之义”泛化为指向“正”的源头,始作俑者也是班固。班固一方面在《两都赋序》中说:“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抑亦雅颂之亚也。”*萧统编:《文选》,1-2页,上海,上海书店,1988。认同《汉志》中引用的《七略》“古诗恻隐之义”概念。另一方面又在《汉书·扬雄传》中说:“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靡丽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班固:《汉书》,35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在用“贤人(失志之赋)”概念的同时,将指向“古诗恻隐之义”的“则”直接等同于指向“法则”的“正”。这种概念内涵由“专指”转为“泛化”,从而消解了扬雄、刘歆文本中呈现出来的观念力度,阻碍了后世赋家对《七略》文本语境的深入辨识。就笔者所见,目前存世文献中这方面论述最早者之一魏晋之际皇甫谧《三都赋序》说:“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古诗之流也。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浸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8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皇甫谧这段话尽管从文字表面上看完全遵循《汉志·诗赋略后序》,其中的关键词如“诗人之作”、“贤人失志”、“古诗之意”一应俱在,但在内涵上已经完全看不到对“则”与“古诗恻隐之义”联系性的把握了。稍后如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三“长卿赋有天才”条说:“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葛洪:《西京杂记》,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居然隐约透露出“诗人之作(赋)”原本即有“典而丽”特点,司马相如之赋不过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这种理解更是完全背离了赋出于“古诗恻隐之义”的本义,而“典”恰是“正”的又一代称。就笔者所见,存世文献中“则”指向“古诗恻隐之义”较为明显的意义线索是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第三十一》说:“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刘勰撰,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文心雕龙校注》,41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诗人什篇”、“辞人赋颂”正是“诗人之赋”、“辞人之赋”的意思,“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正是“贤人失志,风以恻隐之义”的意思。特别是《章表第二十二》说:“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屈。”*刘勰撰,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文心雕龙校注》,30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这显然是“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另一种表述,而其中“(恳)恻”正对应着“则”,透露出“则”、“恻”在意义上互文指涉。刘勰的卓见可谓爝火微光。六朝之后,随着赋体创作的逐渐衰微,“则”指向“古诗恻隐之义”的意义线索基本消失。如元人杨维桢至正二年(1342年)为辞赋集《丽则遗音》所作自序说:“赋之古者岂易言哉!扬子云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子云知古赋矣。至其所自为赋,又蹈词人之淫,而乖风雅之则。何也?岂非赋之古者,自景差、唐勒、宋玉、枚乘、司马相如以来,违则为己,远矧其下者乎!余早年学赋,尝私拟数十百题,不过应场屋一日之敌尔,敢望古诗人之则哉!……因述赋之比义古诗,而不易于则者,引于编首,且用谢不敏云。”*杨维桢撰,黄清老评:《新刊丽则遗音古赋程式》,“中华再造善本”第一编,5-6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这是宋元时期将“则”作为“正”、“常”、“标准”来理解的代表性论述。
通过梳理这一赋史观念的流变线索,还可以借此对汉代今、古文四家诗学的一些传承线索及其意义再作思考:
第一,关于今文经学所谓“刘歆伪造《毛诗》说”的可信度。从刘歆对扬雄的推崇来看,“温柔敦厚”诗学观的传承线索应该是:《礼记》—《毛诗》—扬雄—刘歆。如果按照今文学家的说法,《毛诗》为刘歆伪造,那么这一线索则变为:刘歆—《毛诗》—扬雄。从学术理念上看,依照刘歆对扬雄的推崇,很难想象扬雄明知《毛诗》为刘歆伪造而成,还会服膺这一文本。从文本传播所需时间上看,如果扬雄对“《毛诗》为刘歆伪造”一事毫不知情,那么从刘歆伪造《毛诗》形成文本,再到文本流传产生影响,再到这一影响波及扬雄并形成相应的诗学观念及赋史建构,需要较长的时间,而扬雄与刘歆是同时并互有交往的朋辈,这在时间上也不合情理。所以,“《礼记》—《毛诗》—扬雄—刘歆”这条诗学传承线索,在“诗人之赋丽以则”概念流变的观照下,从一个此前从未曾为人所注意的角度,再次说明今文家“刘歆伪造《毛诗》说”的不可信。
第二,关于扬雄的诗学家法归属问题。自廖平力倡今、古文门户之别以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伪经传于通学成于郑玄考第八》“扬雄”条专论扬雄为“刘歆之友”、“传古(文经)学”者。*康有为:《新学伪经考》,170-171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也将扬雄归入古文经学范畴。尽管扬雄的古文经学基本倾向已经确定,但对扬雄的诗学家法,则很少有“证据性”的明确描述。近来王青《扬雄评传》从《法言》引《诗》异文的角度举出例证,认定扬雄服膺鲁诗,从而对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与否定,认为“要把扬雄视作古文经学派的代表是很困难的”*王青:《扬雄评传》,74-76、85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笔者以为,在“诗人之赋丽以则”观念基础上,可以对扬雄诗学倾向再作分析:首先,“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是扬雄诗学及以此建构的赋史的核心观念,我们判断学者的学术倾向与流派归属,应当以其学术思想的核心观念为准,而不为其他的枝节问题干扰。其次,扬雄、刘歆所处的时代属于汉代今、古文经学交接、混融、胜负未定的时期,一人而传习多家家法,然后由通行的今文经学转入新兴的古文经学,从而以古文经学为基本格局而带有今文经学的某些遗蜕,这类情况并不罕见,如前述刘向同时传习《谷梁》、《左氏》即是一例。故扬雄服膺《毛诗大序》之说,而间用《鲁诗》异文,并不奇怪。所以,较之“鲁诗说”仅以异文为证据,“毛诗”说的证据更接近扬雄文学观念的核心,在可信度上应该更高。再次,从廖平以来用今文、古文经学概念简单分析西汉学术其实并不合理,门户之见较重。而且四家《诗》同源,其诗学主张差异未必很大。对扬雄的诗学家法归属问题不作界限过于分明的划分,可能会更加圆融。
第三,还应当认识到“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作为《诗》古文经学的核心观念应用于赋文体发展的描述,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首先,就写作表达层面而言,新兴的“赋”不直陈其事,表达方式以委婉(“风”)为宗旨,具体手法就荀子、屈原作品来看正是“比(喻)”与“兴”(言他物以间接指涉引申)。也就是说,新兴的“赋”全面融合了《诗》六义的“风”、“比”、“兴”要素(雅、颂为诗歌体制而非表达手法,在上述语境中可以忽略不计),因此“赋”在文学史上成为《诗》之后可以取而代之的新兴抒情文体,是由具有综合性的优长因素决定的,逻辑上具有最大合理性。其次,就情感内容层面来看,新兴的赋的源头(“诗人之赋”)的情感内涵仅限于“恻隐古诗之义”,远不如《诗》内涵之丰富,必须要有所突破、扩展,成为“丽以淫”的“辞人之赋”(“淫”兼有“不正”与“过当”二义,前者是破,后者是扩),才能真正适应汉代新兴帝国的文化与情感表达需求。在这个意义上,“辞人之赋”在体制上虽然背离了“诗人之赋”的“恻隐”源头,但在内容上却超越了这一《诗》古文经学事后归纳、人为划定的概念界限,真正回归了《诗》的情感多元性,使得“赋”不但可以如荀子、屈原之作(诗人之赋)失志而哀(恻)但表达委婉(隐),也可以如后来司马相如等作品(辞人之赋)赞唱歌颂、喜怒哀乐、发扬蹈厉、无施不可,这才走向了文体的充分发育与成熟,有着进步意义。赋文体的发展需要突破单一源头、与时代相契合,扬雄、刘歆等人拘泥于事物的源头性、缺乏变化精神,故而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既要发掘出西汉诗学所总结但已渐遭遗忘的赋的文体源头特征,又要承认赋突破其源头特征的发展合理性,只有如此,才能走向理论逻辑与历史进程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