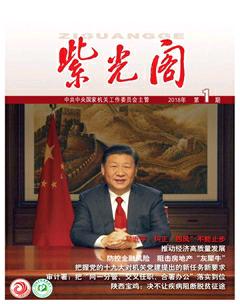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底色
唐鸣+祁中山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离不开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纳入十九大报告,回望我国历史上乡村治理的变迁,有助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体系。
古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逻辑
“皇权不下县”是古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奉行的基本法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以乡村基层组织为核心、国家间接控制与乡村社会自治相结合的治理体制,大体经历了从“乡遂制”到“乡官制”再到“职役制”的历史变迁。
先秦时期的乡遂制。西周时期,实行“国”“野”分治的乡遂制,全国设六乡六遂。乡为天子、诸侯、士大夫及工商业者的居住区域,乡之下设比、间、族、党、州,以户为单位,五五递增,分置比长、间骨、族师、党正、州长;而遂为农户居住区域,其下设邻、里、赞、鄙、县、遂,以编户组织而成,分置邻长、里长、赞长、鄙师、县正、遂大夫等官职。乡遂制实行的是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的结合,兼具军事、教化和监控的社会功能。春秋战国时期沿袭了乡遂制度,但也有变革。县下设乡、乡下设里,乡里制已成为基层行政组织,分别由乡长或有司掌管。但是由于春秋战国的大动荡,乡里制度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地方行政制度,而是更多地与军事组织关系密切。
秦汉时期的乡官制。秦王朝建立后,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将全国化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亭、里等乡里组织,十里一亭,亭有亭长;十亭一乡,设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四职,三老掌教化,有秩掌行政,啬夫听讼、征税,游徼负责治安,循禁盗贼。汉代在秦代乡、亭、里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里以下的组织,建立了什伍制度。里以上组织仍然沿袭秦制,置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但官职的隶属关系出现分化,“有秩”为郡府委任,其余都是县衙委派,其中“三老”地位崇高,但既无行政权,也无俸禄。
隋唐以后的职役制。隋唐时期,乡里制度发生较大变迁,其中“乡”的职能进一步削弱,“里”以下的乡村社会治理功能不断强化,开始了“王权止于县政”的新时期。隋文帝时,实行乡里两级制,乡以下以五家为保、五保为间、四间(里)为族(党),置保正、间(里)正、族(党)正,掌管核实户口、催征赋役。唐代基本沿袭隋时制度,里正负责“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等实际工作,而“乡”的职责开始简化,其官员多由六品以下没有实际官职的勋官充当,甚至由当地富户白丁出任。宋初基本沿袭唐的基层治理制度,里正、户长都是以服役人的身份从事工作。而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中的募役制度和保甲制度,更是将乡村治理中的职役属性更加强化。元代实行里甲制与村社制并存的制度。里甲的职责主要是管理户口,催征赋役,掌控治安,里正一般由上等户充任,轮流担当。村社主要负责劝课农桑,管理农业生产,处理民众实务,其首领不具有官员身份,只行职役之责。明朝的里甲制也是一种役政合一的体制。里正没有奉禄,但听命于地方官吏的差遣,担负“催征钱粮”和“勾摄政务”的任务。但到明中后期,随着统治危机的加深,开始于里甲之外,另设保甲组织,专职维持社会治安。清朝基本沿袭明制,县以下保甲制和里甲制并行。保甲掌社会治安;里甲主要掌赋役。保甲以人丁为主,主要控制人口流动,维护社会稳定;里甲以户为主,主要是方便征收税赋,保障财政供给。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乡村治理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傳统社会基层治理模式的变动,都与底层社会经济状况的变迁密切相关。乡遂制的实行迎合了夏商周奴隶制国家土地国有制生产方式的需要,乡官制正是维护封建大一统国家刚刚建立之初尚属娇弱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中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废弛、两税法的实行,地主阶级内部构成发生了变动,原来实行乡官制的乡里制度,开始向职役制转化”。第二,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组织及其职位设置具有官方或者半官方的色彩,但是政治国家的权力触角却并没有直接触及乡里社会。里甲等组织的掌权人多为乡村能人、经济大户、德高望重者,来源于本乡本土,并且与其在乡村中的社会角色密切相关,他们的职权更多地来源于国家的“认可”而非授权。第三,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模式体现了国家政权与宗族权力、底层社会自治权的一种平衡和博弈。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也是间接式的,其利用乡村社会的权威,实现了对乡村社会资源的汲取、社会的管控和文化的控制。在这种依赖的关系中,国家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同时乡村社会也获得了一定的自治权。
近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脉络
破旧立新、破立并举是近代中国乡村治理呈现的鲜明色彩。这与当时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时代交替背景密切相关。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适应变革需要于1908年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凡府厅州县官府所在地为城,其余市镇村屯集等地人口满5万以上者为镇,不满5万者为乡。城镇乡均为地方自治体。乡设立议事会和乡董,实行议行分立。乡议事会在本乡选民中选举产生,为议事机构。乡设乡董、乡佐各1名,负责执行议事会议决事项与地方官府委任办理事务,同时负责筹备议事会选举及议事事务。自治范围囊括了近代一般地方行政的基本内容,包括教育、卫生、道路、农工商务、慈善救济、公共营业及地方财务等事项。由此,乡开始成为一级行政区划和政权机构。这种变革开始改变了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的局面,也使得国家政权的触角伸入乡村底层社会,强化了对底层民众的控制和征敛。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颁布《县组织法》《乡镇自治施行法》《区自治施行法》等法规。这些法规规定区、乡、镇为自治单位,可以在不抵触中央和省、县法令规则的前提下,制定自治公约,选民可以直接行使创制权、复决权、选举权和罢免权等权利,同时要求完善并充实县、区、乡镇各级行政组织,使各类承担行政职能的人员纳入国家官僚体系之中。通过这些规定,县以下区和乡镇两级行政得到统一,中国传统社会以县为最基层的制度至此正式结束。endprint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其乡村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领导、发动农民运动,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民主革命政权。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同时期,都十分重视以开展广泛的土地改革推动基层政权建设。这是因为,一方面,土地改革可以打击和瓦解传统乡村社会的乡绅势力;另一方面,通过变更土地所有权又可以获得农民对革命政权的支持。当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乡村苏维埃政权、抗日民主政权等组织体制,也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扩大了农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度,改变了农民在乡村政治中的弱势地位。
从上述梳理可知,无论是晚清时期、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基层治理都一改传统社会以县为最底层政权的局面,国家政权开始逐渐延伸到乡村一级,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逐渐强化。但是由于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属性,国家政权并没有实现对底层社会的一体化控制,再加上传统小农经济的持续存在,使得近代的基层治理仍然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现代中国乡村治理的演进路径
调整、适应、提升是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治理运转的基本路径。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政权设置变更不断推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更新,先后经历了乡村并存制、乡政权制、人民公社制、乡政村治等阶段。
1950年至1953年乡村并立时期。1950年中央颁布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确立了乡村并存的基层政权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一是乡、行政村同为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但乡建制较小,通常由一村或者数村组成,人口覆盖多在500-3000人不等;二是乡、行政村实行议行合一。乡、行政村的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乡村权力机关存在,乡、行政村人民政府作为执行机关存在;三是在乡以上设区,作为政权实体或者县的派出机关,领导乡、行政村的工作;四是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尚不成熟、变动幅度较大,但为以后的基层政权建设累积了经验。
1954年至1958年乡政权时期。1954年宪法颁布后,农村基层政权出现较大变更,主要体现在:一是原有的行政村建制取消,统一为乡建制,设立乡政权;二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民族乡建制;三是乡政权的行政机关更名为“人民委员会”;四是乡之上不再设区建制;五是乡的规模有所扩大,且可以设置相应的下属机构。
1958年至1983年人民公社時期。195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进入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根据1959年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1978年中共中央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规定,这一时期,农村基层政权存在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实行政社合一体制,人民公社取代原来的乡建制,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又是集体经济组织;二是人民公社的规模大于乡建制;三是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四是强化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超越了社会生产力水平,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劳动者积极性的提高,也破坏了基层政权组织的正常运转。
1983年以后的乡政村治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的农村基层政权又经历了一次变革,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乡建制恢复,乡再次成为我国最低层次的国家政权。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成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广大农民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利,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但是在农村税费改革前的相当一段时期内,由于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的压力型体制没有根本改变,乡村关系发生异化,农民负担加重、农业发展滞后,“三农”危机涌现,最终催生了农村税费改革。新世纪以后,农村税费改革的启动,使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迈入新阶段,也给乡村治理带来新挑战。
基于梳理,我们发现:第一,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基层政权的变迁最终适应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需要。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将基层政权设置在乡一级,同时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既保障了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又保障了乡村社会的自主性。第二,农村基层政权的变革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人民公社体制迎合的是农业集体化的需要,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是乡政村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因此,乡村治理体系必须不断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构筑
展望面对新时代对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提出的新标准、新要求,未来乡村治理体系构筑也要有新判断。我们认为,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应具备几个特点:第一,乡政村治的基本结构应该保持稳定。大规模、普遍地乡镇撤销实不足取,服务型基层政府建设应该更加深入,以“五个民主”为核心的社区治理内容将更加丰富完善。第二,乡村治理更加重视共商共治。党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党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方式进一步改善;基层政府从管理到服务的职能转变进一步加速,协商型政府建设发力,政府、市场、社会的权责得到进一步厘清;社会力量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进一步放大,协同治理的价值理念和运作方式得到进一步认可;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活力进一步释放,居民融合度提高,以同一居住地为范围的新型城乡社会生活共同体将逐步形成。第三,乡村治理的地域边界最终突破。尽管城乡在自然地理风貌、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差别仍会存在,但城乡二元结构终将消除,乡村治理终将转变为城乡基层治理。第四,乡村治理的手段、方式和主体可选项更加多元。乡村社会法律规制和道德约束将协同发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理方略进一步贯彻落实;基层群众的自治基础和乡村社会精英的引领优势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唐鸣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导;祁中山为信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讲师、博士。本文部分内容为民政部委托课题“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沿革和现状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endprint